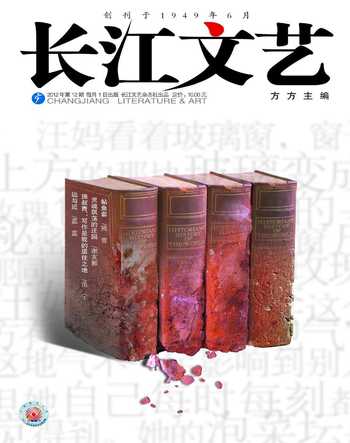跳舞的父亲
朱朝敏
在先前的墙壁和樟树中间,
父亲正在挥舞他的双臂,
满头白发犹如磨平的镜子反射着灼热的夏阳,
异常刺眼,
而那只白鸟蹲坐在墙头上,
它盯着父亲,
唧咕叫唤,
又不时拍打着翅膀,
应和父亲。
1
他的头发全白了。当然,早已经白了,只不过在国内一直染黑,而去卡尔加里妹妹那里一年,染黑的头发已被喀嚓剪掉,留在脑袋上的是父亲本真的发质而已。蓬松着,犹如霜打的衰草顶在脑袋上,格外耀眼。
我一眼就看见了他,虽然这趟航班人流沸腾。虽然白头发的脑袋不止父亲一人。但取托运行李的旋转机旁,白头发的瘦长男人,他双臂朝上笔直举起,然后弓起上身,双臂又朝后朝下收缩,动作缓慢有致。我马上想起,双臂被他当成了木桨在划。父亲前后划动手臂,推动他这艘木船,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腾挪。有人诧异地侧头看,有人嘴角浮现模糊的笑,有人漠然而过……父亲就凸显出来。他在跳舞。
这个老头子。我心中被压抑下去的气流砰然再起,太丢人现眼了……
父亲竟然滑起太空步,一头雪发在他扇起的风中微微颤动。人流逐渐虚空,父亲旁若无人地舞着,旋转机上巨大的行李袋孤独地滑来滑去。
他干什么呢?我突然想到怪异和反常。
父亲。我张口喊道。
啊——父亲侧脸,身体僵硬地保持着朝前倾斜的姿势,而双臂犹如被卡住般地停驻空中。他瞪大的双眼刚刚与我对视,脸上马上浮起笑意。我尝试着再次喊叫,父亲,并举起右手示意。父亲站直了身体,恢复了正常,哎地应答一声。我被挂起的心终于轻松放下,提示父亲取出行李。
呵,里外两重天啊。坐进车里的父亲,脱下刚刚套起的羽绒大衣叹道。
我唔了声,心绪重陷怅惘中。要说,一个大男人,已过而立的大男人,说什么怅惘似乎矫情了些。可这感觉竟是挥之不去。晓真昨天刚刚与我分手。分手就分手,这年头,分手犹如云卷云舒一样平常,早司空见惯习以为常了。可晓真是名如其人,率真……我有与之白头偕老的打算。还是……未免遗憾。遗憾不过瞬间,怅惘萦绕不去的是,晓真分手如此致辞:我以前认为写诗的男人是有品位的,可临了发现,诗歌杀死了男人谋生的好细胞,光有品位有什么用呢?我不过一个俗人,在消费品位前必须谋得安逸生活。我就失落了。晓真说的是实话啊,尽管她否认了诗歌,否认了我。要命的是,我明明知道晓真的实话犹如真理,却毫无勇气丢弃一些,譬如诗歌和诗歌培养出的坏脾气。
我说的是天气。坐在副驾座上的父亲可能觉得我心不在焉,完全侧过了脸,眼睛盯着我继续说道。
我不得不与父亲展开谈论。天气及其取暖。卡尔加里和中国湖北。父亲最有发言权,他侃侃而谈,从细节进行对比。他在对比中掀起兴奋的漩流,任其自由地沉陷。那是他的兴奋,与我何干?我是失落怅惘的,甚至愤懑。
……那只鸟,你知道是什么鸟吗?父亲再次侧身,眼睛盯着我问道。
哪只鸟?
你根本就没听,我再重复下,那只鸟全身雪白,尖嘴壳和眼珠子是红色的,它的腿脚很大,却不至于粗笨。
我摇摇头。什么鸟?我哪里知道。父亲转回身体,马上恢复他的兴奋。他不在乎我是否知道那只鸟,而仅仅想告诉我,他最大的兴奋是,在妹妹家的草坪上,春夏秋三季有一只大白鸟会在傍晚准时来吃父亲准备的鸟食。
你知道吗——冬天外面大雪封路时,白鸟居然有几天寻到窗台上看我。父亲又转过身,盯着我的眼睛。我从余光中捕捉到他自以为是的神秘。
2
你父亲变了。
母亲找到我,絮絮告状。她的眉头拧出一股怒气冲冲的绳索,朝我一鞭一鞭地打来。你父亲脾气简直坏透顶了,我不过回家迟点,他竟然摔破所有的碗。
所有的碗……你应该阻止他的,免得你们买新碗。我盯着母亲丰腴得近乎浮肿的面庞。她不是我亲生母亲,比父亲小了十来岁。要说,作为后母,她待我与妹妹不薄,守着我们送走青春、盛年而一直未育,直至现在退休在家。当然,这还归于父亲的一贯依顺,他对母亲几乎没有红过脸。
哪里阻止得了?我回家,他已摔破了所有的碗。母亲眉心间的绳索再次拧紧,抽在我身上——这个破脾气,伤人又伤己。
哪天我去劝劝他,不过你担待些,能够发发脾气,总比闷在心中要好。
是吗?母亲扬起浑浊的眼睛问道。她不是问,而是以问表达她的不悦。她根本不打算隐藏不悦,继续说,他有什么不快的?以前总是笑眯眯的,从你妹妹那里回来就变了个样……我的头顿时大了,摆手打住她的话,投其所好地建议,可能是在家闷得慌,干脆拉他跟着你跳舞去。母亲是我们这里广场舞的组织者之一,同时也是老年乐队的中坚分子。
白搭。母亲放下眉心的绳索,幽幽叹道,我来你这里之前,你父亲把阳台上我收捡的坛坛罐罐全砸了,扔进了垃圾箱,嗨,不晓得他哪根筋反了。
鸡毛蒜皮的小事。我在心中嘀咕。母亲见我不再接话,见好就收,转身离去。走几步又折回来,问,你和晓真——
分手了。
我早晓得会这样,那女子啊,太精明了,不适合你,我倒认识一个与你蛮般配的,喏,你也见过,就是我的侄女同同,她刚离了婚。母亲见我一副思索模样,从细节帮着我回忆同同这个女人。过年时,带着丫头来我们家拜年的那个,很漂亮,能说会道的。
我脑海闪现出嘴巴甜腻得淌油手脚麻利得生风的乖巧女人。她的确给我留下了印象,可惜与她的容颜无关。那乖巧劲,无话可说。本来是客,却在厨房里帮助母亲整出一大桌丰盛的宴席。
怎么样?想起来了吧,我帮你们撮合撮合。
再说吧,我明天出去参加一个诗会,要先准备下。我扎进卧室,把背影留给母亲。母亲轻微的叹息或者说嘲笑还是清晰地传进我耳朵里。她懂什么?要笑就笑,我何必质疑她?
晚饭时,母亲打电话让我过去吃饭。我警惕地问,是否家里来客了。母亲矢口否认,只说要我过去陪父亲吃饭唠叨下,她弄了几个下酒菜。
然而,父亲却不在家里。他的人呢?
母亲看我一眼,眉头的绳索拧得紧巴严肃。她解下厨房专用围裙,换上皮鞋,说道:跟我看去。
春光在傍晚时分挥洒着蛋黄般的光芒,又被闪烁的路灯切割遮掩。向晚的微风轻轻摇摆着路旁樟树,树下的道路上光影斑驳跳跃,仿若池塘藻荇四横。父亲正在藻荇边上,他踮着双脚位于墙壁和樟树中间,双手越过脑袋并拢,朝上举起,牵引着身子骨朝前蹦跳,跳着又转身朝后蹦跳。
模糊的光线里,父亲的举止滑稽可笑,却并不引人注意。也许,他以跳舞的名义锻炼身体而已。
母亲嗨了声招呼父亲,见父亲毫无反应,于是没好气地否定我的看法。说,这个呆子已经跳好长时间了,同同下午打电话告诉我,我还以为他不过锻炼身体,哪知到现在还在跳——你看他像是锻炼身体吗?
天完全黑了下来,路灯乳白色的光芒轻薄而漫不经心,华盖如伞的樟树黑黢黢地抱成一团,又在地上投射出浓重的黑影。父亲不再蹦跳,而是缓慢地前后伸出左右臂膀,配合左右脚,机器人般地走步。
母亲骂道,疯子。父亲疯了?我的心陡然跳了下。一个箭步,跑到父亲跟前,喊道,父亲。父亲抬起双眼,与我的目光碰在一起。他垂下双臂,恢复了正常,冷着脸色嗯了声应答。我朝母亲看,母亲已经转身径直回家去。
我和父亲一前一后跟在后面。我问父亲,在跳什么?
玩。
这样玩,不如跟着母亲去跳广场舞,一样锻炼身体。
我没必要锻炼身体。
那你跳舞干什么?
跳舞?没有啊,你真没看出我——干什么?
我停下脚步,回头直视父亲的眼睛,说,你烦母亲了,不想再顺着她,一次足矣,其实,她还是不错的。
父亲似乎没有听见我说的,并不停步,经过我时,又问:你真没看出我在干什么?
3
清江诗会,我意外碰到同同。她来干什么?
诗友老痞碰碰我肩膀,说,她来给我们出钱,没有她,我们开什么诗会?我想起来了,同同是搞文化策划的生意人。诗会要的不是写诗歌懂诗歌的人,而是同同之类的有经济实力的老板。她才是中心,诗会上酒席上。同同似乎推翻我以前见到她的表现,她稳重得体,虽然时不时流露出有产阶级的优越,但完全没有以前留给我的小女人做派。她称呼我“哥”,恰到好处地显示我们的亲密。
老痞拉我一边,再三嘱咐,要我套牢这个女人,不然他愿一试。喝酒碰杯时,老痞又言,其实,没意思的,很快你就会厌倦,因为转来转去,转到头却发现你转到的竟然就是曾经抛弃的东西。老痞和我同时仰脖,再同时碰杯再仰脖,舌头凝固在我们口腔里。老痞啪地摔了酒杯,我跟着摔了碗和筷子。然后,我们抱在一起,老痞的口水流在我肩膀上,但这次他的话肯定没有口水:就这样,哈,我们爷们,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顺——顺其自然——
同同喊道:哥,少喝点,你快醉了。
我瞪眼,舌头打结斥道:瞎,瞎扯。我肩膀上的老痞突然来劲,一把推出我,喊道:接住这个醉鬼,他醉了就到处写情诗。说着,我被推出,倒在同同张开的双臂中。
许多天以后,我接到老痞的电话,他问我和同同的关系进展如何。
我骂道,痞子就是痞子,狗嘴吐不出象牙来。
过誉了。我远不够痞子级别,目前在进修中,估计再混三五年诗歌后可能有望,倒是你本年度会直接晋级痞子大师。
疯了。
没疯,此言有根有据,上次在清江你喝醉的那晚,同同给大家敬酒时,夸你诗歌一流不是二流,预言本年度你搞个正规的诗歌大奖不成问题。
……
恭喜恭喜,苟富贵勿相忘哈。他妈的这世道,都在乳沟里发展得道,痞子的道,得首先装逼。
我挂断老痞的电话。要不,他后面的话会无法收场。我本不置可否,说穿了,我和老痞虽不至相同,却非不同道者。只不过我没时间听他的牢骚和痛斥。
母亲又跑来告状了,说父亲丢人现眼到家了,在小区里趁着上下班人群涌动的时间搞他的疯子舞,现在她出门就被各种眼神包围,好像她也成了异类疯子。母亲说了几遍“疯子”,我忍不住了,纠正,他没有疯。
没有疯?你回去劝他举止注意些,里外围着他参观,难道他是珍稀动物不成?还是耍人笑的猴子?
同同也电话我几次,说在公园,在商场某个转角处,在她公司附近的某个林荫场所,均看见父亲在跳舞。同同说“跳舞”这个词,犹豫逡巡,显然斟酌了好久,实在找不出合适的词语,才最终用上“跳舞”。
父亲的言语表示他很正常,只不过沉浸在他的怪异举动中,有什么大惊小怪地。我很不以为然。
同同又找到我的家来,顺便带一个花篮。花篮里,百合挤挤挨挨地,盛开的花瓣溢出,抛洒出浓郁的香味。她捧着花篮,放在我书桌上。看见我刚刚完成的诗歌,夸奖我写得好。我奇怪了,问,好在哪里?
同同哦了声,却指着百合花篮回答,百合又好在哪里?但我觉得只有它才能表达我想要说的,它就好了。我的确不懂诗歌,可我发现,我现在需要诗歌。她的回答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她夸奖的好,意思也明显,不过是她需要什么就喜欢什么,从而选择……诗歌进而写诗的人。可诗歌,对于她和老坯之流,毕竟是水和油的区别。她玩诗还是借此粉饰?
我一把揉烂刚打印出的诗歌稿,扔进垃圾桶。骂了句:狗屁。
同同变了脸色,眼神转向桌子上的百合花。我本来打算扔掉花篮,至少要转移下地方,那种香味我受不了,但最终忍住没有动手。
于是,我谈起父亲。同同以谈论父亲之名找我,我何不为父亲正名?父亲他很正常。同同显然不同意我的辩解,说,在公共场合不避耳目做出异于公众的举动,并把举动经常化,肯定是异常,至少也提示出思维走入边缘的信号。我陷入了沉默。同同继续说,幸好姑父还没有走火入魔,还有挽救的可能。
挽救?
是的,我们要趁早带姑父去医院检查。
4
母亲提出带父亲检查的建议,马上遭到父亲反对。父亲反应激烈,而且伸手推倒母亲在地。母亲坐在地上,呜呜地哭了。
同同电话告知:姑父不配合,伸手打了姑姑。
我火燎燎地赶到父母家,只看见母亲坐在地上淌泪。父亲不见了。
父亲没病,送他检查什么?我本来想说,却无法出口,只好搀扶起母亲。母亲虚弱着声音说,不要管我,把你父亲找回来。
他喜欢在外面——跳舞,就由着他去吧,反正又没有妨碍谁。
你真不了解你父亲啊,这次惹恼了他,我怕他跑远了。
我不禁一愣,随即拔腿就走。
路上,老痞来电告知,全国以屈原命名的诗歌大奖即将揭晓,你这痞师要杀出来了。
乱扯屁话。我对着手机呸了声,掐断通话。
但老痞的短信飞速而至:痞师,昨天在省城笔会,遇到终评评委,还有同同,同同是这次诗歌赛的大东家啊,你就顺着乳沟掘道道吧。
这个老痞。看着短信我摇摇头,心中却无名地滋生出兴奋来。但懒得回复老痞,我正在奉继母之命找父亲呢。若真像母亲所说,父亲跑了,这个说自己受够父亲的气的继母,丢手不管,到头只能苦煞了我。
哪里有父亲?
父亲在哪里?溜达完凡是能够看见父亲的大小场所后,给母亲打电话询问——父亲回家没有?
没有。母亲简单干脆地答复,啪地挂断了电话。她的确比我了解父亲,父亲这次彻底被激怒,真的离家出走了。
两天过去,问遍所有亲朋好友,父亲还是没有下落。我顿感不妙,去电视台和报社挂出寻人启事,许诺重金奖赏发现者。
母亲遽然老去,头发白了不少。她每天至少三遍电话询问:有你父亲的消息吗?
没有。
我这把老骨头可是丢尽了脸面,你父亲从你妹妹那里回来后,就和我对着干,现在又跑了,闹得熟人皆知,别人哪里知道情况呢?还不是以为我霸道逼走了他……母亲的哭腔里满是愤懑和委屈,仿佛此时她正在遭受不公正的审判。
我无言。同同打电话给我时,我趁机建议:你姑姑情绪很坏,有时间你去开导开导。同同欣然允诺。
我给自己找来了麻烦。母亲在同同开导她时,电话我回家坐坐。我推辞,工作忙,不便,要赶材料等等。母亲总有办法,“同同在这里呢,过来吧,我们一起说说话”,母亲打出同同这张主牌。我一回可以不去,可第二第三回我总得去。否则,当着同同的面驳她的面子,我似乎做不到,现在也没有这个打算。
东扯西拉地,说着说着,母亲就一左一右地拉起我和同同的手,放在她的膝盖上。以伤感而无限憧憬的语调说:多么好,要是你父亲不变,我们老少在一起,乐融融地,几多好——说着,母亲眼角渗出浑浊的液体。我趁机抽出自己的手,站起来去卫生间。哗啦啦的流水声中,同同劝慰的柔声传来:姑妈,别伤心了,姑父肯定没有走远,说不准——说不准什么情况?我拉开卫生间房门,走到她们身边。
……说不准他就在某个地方躲着,看我们后悔了,姑父说不准也就回家了。
是啊,同同说的有道理。我赶紧附和。母亲眼神望着客厅某处,好像那个地方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吸引着她,而这个特别的东西于她又陌生了些,她只好呆呆望着。
姑妈,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姑父这个样子——我们,别人都看在眼里,怎么能够怪你呢?哥,你说是不是?
是什么!父亲什么样子,他正常得很。我心中如此回答,但终究只是默然一笑。
嗯,你刚才分析得有道理,我们不能以正常人的思维来分析你姑父,很有可能他就在我们附近,躲起来了,先吓我们,要我们后悔,然后得意洋洋地回家,再由着他疯去——我能由着他吗?但凡你父亲回来,我们必须马上采取措施送他去检查治疗。母亲说着说着,把身子对向了我,严厉的眼神盯在我眼睛上。
她们的分析令人气愤,到底是把父亲当成精神失常的人了。父亲就是被她们的奇怪认识弄烦了才离家出走,现在,人都不晓得在哪里,甚至死活也是未知数——想到这里,我气不打一处来。同同立马捕捉到我神情的变化,扑闪着大眼睛看我,说道:哥,你别急,慢慢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颓丧就座。母亲再次一左一右地拉起我们的手,说,你们,真是心有灵犀啊,嗨,这倒是件喜事。
父亲始终没有露面,也没有丁点消息。已经进入夏天,老痞却来电告知,说他今天上午在清江古城溜达时,看见一个乞丐,浑身脏兮兮的,他却令人驻足,因为他的左右手心摊开,掌心中竟然站着一对大鸟,大鸟跟着老头跳舞,我仔细看了,那老头像你的父亲——不过,也不能确定,毕竟我还是几年前跟着你去你父母家吃饭见过他一面。
那你为什么不上前问问?你应该喊他,马上喊住他。我着急地说道,仿佛稍不注意,时机将逝,我只能迫不及待地提醒。
我是想喊的,可老头和那鸟简直绝配,舞得行云流水,我不忍心中途打断,结果……嗨,我电话响了,等我接完电话,发现老头和鸟……不见了。
你这个半吊子……我气愤得恨不能跑到老痞身边,揪他的耳朵,捶他妈的一拳。
老痞说,我今天不走了,守他三五天,保证给你好消息。
保证你个头。我啪地摁断通话。他那德行,说过的话等于放掉的屁,不如自己赶去。
5
同同从我母亲那里得到我去清江古城的消息,马上告知,你只能在清江古城待上一天,后天必须到省城黄鹤楼参加本年度诗歌颁奖会,你作为特等奖得主,不能缺席。
我还没有说话。同同的声音又传来:你放心好了,我姑姑跟你一起去清江古城,或者,就要姑姑一个人去,怎么样?
不,还是我去吧。
姑姑的心情……她要去总不能拦她,不如你们一起去,一天后你直接赶去黄鹤楼,姑姑在古城守几天,不正好?
同同的声音在手机里嗡嗡作响,略显出疲惫,却毫无无力感。这个女人,在短暂的两个月的时间里,把依顺完美地过渡到颐指气使,你却无话可说。我看着手机屏幕显示出“结束通话”几个字,脑海一片混沌,上十秒后,才呼出一口长气。
母亲跟着我来到清江古城。她没想到古城那么大,而老痞究竟在哪里见到与父亲相似的人,他始终语焉不详。母亲果断地建议,我们分开去寻,谁寻到了再联系。
此时,已是中午,古城上空的太阳圆球般地挂在我们头顶上,在街道和建筑上贴出明晃晃的镜片。我一路看来眼睛发花发虚。兜转近一个时辰后,我和母亲竟然在古城清江边遇到了。母亲唉唉叹气,直说,你父亲是娇生惯养的人,不会在正午吃饭小憩时分来搞花样的,我们转下去也是白搭。说着,从提袋里掏出小扇子扇风。看来她做了充分准备。
我建议,先去吃饭,黄昏时分再来溜达。
找了一家餐馆就坐,等待上菜的空隙。母亲又跑出去,询问:你们谁看见,手托着鸟儿跳舞的老头子?
没有人回答。
母亲抓住一个长相干净的老太太的手,再问:您老精神好啊,早上经常锻炼吧。老太太咧嘴笑了,手指着前面的清江回答:每天早晚都在这古城溜达几遍,爽气得很。
那是,您老可看见一个疯老头子,双手举着白鸟跳舞吗?
老太太的笑容迅疾瘪了下去,坚定地摇头后,转过她单薄的身体。
饭毕,母亲以坚忍的毅力,依次询问开着店铺的商家和摊贩,但没有一个人说看见。母亲生气了,在眉心拧起坚硬的绳索,朝着我一鞭一鞭打来:你那个朋友是不是神经病?他说的那个像你父亲的人,这里的人都没看见,他骗我们来这里什么意思?
不急,我再打电话问问。我慌忙拨响老痞的电话。电话里的音乐此起彼伏,却始终无人接听。母亲更气了,一口咬定,那个神经病痞子是在寻开心。我心中苦涩不已。老痞再痞,机德还是好的,他不接电话,只能说明他中午醉了,此时烂在床铺上。但,无法解释给母亲听,因为她手中掌握着颠扑不破的真理:这里没有一个人说看见像父亲的人。
我们只有等待黄昏来临。但那有多少希望呢?按照母亲的理论,如果老痞真是骗人,白天是白等,晚上是瞎等,等等等,我们都是疯子不成?可是,已经来了,况且,老痞毕竟是我的朋友,近无冤远无仇的,在父亲消息几近零点的状况下,不信也得信下,哪怕他真是如同母亲所说的“神经病”。
如母亲所言,我们白等也瞎等了。老痞却来了电话,问我找他有什么事情?母亲盯着我,拧起她坚硬的眉心绳索,我只有顺着母亲思维问他,你看清楚没有,该没有犯浑吗?是不是在清江古城看见一个手托白鸟的老头子?
老痞嘻哈着笑了,说,妈的,老子成屈原了,举世浑浊惟我独清,刚才同同也打电话问我是不是编瞎话,我至于吗?
可只有你老痞一个经过古城的人看见,而他人皆不见。我无法反驳母亲的定论:神经病,疯子,精神病患者。
第二天,我径直去省城黄鹤楼,母亲回家。
打的刚到黄鹤楼,遇到老痞。他笑嘻嘻地祝贺我,乳沟得道,一日成器。老痞后面闪出一个胖乎乎的男人,说是当地出版社老总,夸奖我的诗歌直面当下(此时,老痞做了一个怪动作,手指裤裆),媒体到处推介,受众面广泛,出版社有意出版我的诗集版税从优云云。老痞左臂笼住我肩膀,右手一把抓住胖男人的手,瞪大他的门缝眼,嚷道:您是慧眼识珠啊,我们是当地“屈子风”诗社的主创人员,一直倡导“诗歌直面当下(还是裆下?)”理念,勤于耕作,多年不辍,得到像您这样有远见的老总首肯,幸哉,如若多出这样的诗集,您可以做到市场与文化双丰收……胖男人哈哈大笑,不时点下脑袋,并双手呈上金灿灿的名片,要求我们多联络,一起做好诗歌事业。
诗歌事业?就在我为这四个字纠结时,老痞猛地一拍我肩膀,伸出右手,喊道:
快看——是不是你家老头儿?
我顺着老痞的右手食指看去,看见一个蹲在地上的老头的背影,他双脚踮起,双手朝前微微伸出合并,双掌中站着一只灰色鸽子。老头踮着双脚朝前移动,而鸽子安然地在掌心左右环顾。
父亲。我叫道,拔腿跑上前。
灰鸽子受到了惊吓,扑棱起双翅,咕咕几声,飞走了。老头站起来,追了几步,没有追上,转过身,怒容满面地朝我们吼道:乱嚷什么,谁是你父亲?
不是父亲。虽然从背影我已经估摸不是父亲,可是我担心稍纵即逝啊。
在武汉的夜晚,父亲出现在我梦里。他举起双臂,滑起太空步,接着又放下臂膀,左右打开,上下拍打,拍打中,父亲飞了起来,越飞越高越远。我着急了喊道:父亲,你干什么呢?父亲侧过脸,神秘地朝我笑问:你真没看出我在干什么?
他在学鸟飞。我醒来,脑袋和心胸一片空洞。房间黑乎乎地,因长期封闭空气缺少流通的憋闷气息在黑暗中沉郁地压来,我眼睛酸涩肿胀,只好闭上。父亲再次出现我眼前,他兴奋地告诉我,在妹妹家的草坪上,春夏秋三季有一只大白鸟会在傍晚准时来吃父亲准备的鸟食。你知道吗——冬天外面大雪封路时,白鸟居然有几天寻到窗台上看我。
6
早上起床,我接到母亲电话,父亲回家了。我立即叫父亲接听电话,但父亲拒绝了。母亲说父亲带回一只大白鸟,他正在拾掇阳台,给白鸟安家。接着母亲压低了声音说,你和同同回来后马上联系医院——我粗暴地打断母亲的话,你别再吓跑了父亲,父亲好好的,去医院干什么?
早餐时,我决定马上回家。老痞瞪大门缝眼,嚷道:疯了,你要上台领奖,还要发表获奖感言,要接受媒体采访,晚上,出版社宴请我们谈论出版诗集事宜,一样都不能缺席。
不行,我必须赶回家,你帮我应付下算了。我起身就走。
刚进家门,母亲的埋怨迎上:这么大的人了,做事总有分寸吧,撇下同同在那里,你不出声不出气地掉头就走,她多被动啊,她可都是为了你啊。
父亲。我叫道。
母亲冷声一笑,说,害怕我绑了你父亲不成?我绑得了吗?拦都拦不住,他又丢人现眼地跳舞去了,这下更热闹了,还带一只鸟跳。
在先前的墙壁和樟树中间,父亲正在挥舞他的双臂,满头白发犹如磨平的镜子反射着灼热的夏阳,异常刺眼,而那只白鸟蹲坐在墙头上,它盯着父亲,唧咕叫唤,又不时拍打着翅膀,应和父亲。父亲周围,有三三两两的人围着指点,一边观看一边嘲笑。一个两三岁的女孩子,跟在父亲后面也挥舞起双臂,但很快,一个老太太抱走了女孩子。女孩子哇哇哭泣,老太只好放下她,伸开双臂围成栅栏,任由女孩子在栅栏里扑腾跳跃。老太显然不放心栅栏的安全,不住地叮嘱:小心,那个老疯子会打人的。旁边马上有人接着说,不要紧,老疯子发狂我们就打死他。
我眼眶一热,想张口说什么,却无法出声,只好转身而去。
母亲在同同回来后,又发动同同说服我,欲送父亲去医院。因为父亲实在不像话了,他竟然在某个夜晚,突然站在阳台的露台上,挥舞双臂。我拒绝并警告她们,如果再提医院的话题,我会做出出格的行为。母亲虚白着脸,看同同。同同视而不见,转移话题问我,出版社出版诗集的事情,你在准备吗?
我点点头。
趁早好,时间晚了,意义就小了。同同转过脸安慰母亲:姑姑,哥现在是大忙人,姑父暂时要姑姑多劳烦,会有改观的。
你们俩的事情……母亲的口舌结巴了。
同同直直地把眼睛看向我。我低头,仍避开不了同同强烈的注目,于是干脆抬头问母亲:你们愿意我娶同同为妻?母亲忙不迭地点头。
父亲呢?我得问问他的意见。
同同信心十足,准备好丰盛的晚餐,和我一起在客厅里等候父亲回来。天色逐渐黯淡,星光布满天穹时,父亲带着白鸟回家了。白鸟站在他的肩膀上,高傲地抬着头颅审视我们,跟着父亲一步一步回到客厅,再回到阳台上。我和同同的目光一刻也不曾离开父亲。直至父亲喂完白鸟返回客厅,同同站起来,喊了声姑父好。父亲点头示意坐下。同同把目光转向我,我突然有种担心:当着同同的面问父亲,如果……似乎对他们俩都有伤害。于是,邀请父亲去阳台上说话,此际,母亲跳出来,抢先一步,说要和父亲商量下家庭重大决策,并随手带上客厅通往阳台的大门。
我和同同坐回刚才的位置,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谈话。同同问我:“‘屈子风诗社除了编刊物外,还有什么活动?”“本来活动多着,可由于资金限制,活动就限制在刊物发行上。”我耸耸肩膀。同同哦了声,建议道,可以把文化策划加进去,结合当地活动举办一些大赛,闹出影响,再做下出版事宜,策划大型文化活动,做出品牌,很有前景……
就在我心潮起伏时,客厅里的门打开了,母亲怒气冲冲地坐回沙发上。我跑到阳台,看见父亲站在露台上,伸开了双臂,双臂犹如鸟翅翩翩翻飞,而白色的大鸟不见了。我顿时心跳狂乱,一把抱住父亲的大腿,父亲摔倒在我怀里。
我害怕父亲失控,忙不迭地叫道:明天我帮你找回白鸟。
不用找,明天它看见我伸开双臂,就知道我在等它,它会回来的。父亲站好,神色安然地回答。接着,他的脑袋凑到我跟前,眼神荡漾着极度神秘的色彩,说,你要好好地疼爱自己,否则最后连鸟都会抛弃你。
他说的什么意思?我纳闷极了,转而想到同同所说的规划“屈子风”的事情,于是问父亲:我要和同同结婚,你同意吗?同同正好走到阳台上来,邀请我们吃饭。父亲笑咧着嘴巴说,你们信不信?只要我站在足够高的地方张开双臂,白鸟就会看见我,就会飞回我身边。
父亲张开臂膀,在客厅里走起鸟步,继续问,你们看我像一只鸟吗?说着,他踮起双脚,滑行到餐桌边,双臂齐齐朝后举起,而脑袋下垂,嘴巴触进饭碗中。他在学鸟啄食。
同同看着我,眼神惊诧而迷茫。我低头吞饭不语。
她拉我准备结婚用品时,我问她,如果有一天我也喜欢上一只鸟,甚至仿效一只鸟时,你会认为我疯了吗?
同同镇静地回答道,没有那一天,你只能想象事业有成的晚年生活,那时你就是金言玉行的大家了,与一只鸟有什么关系?!
责任编辑 何子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