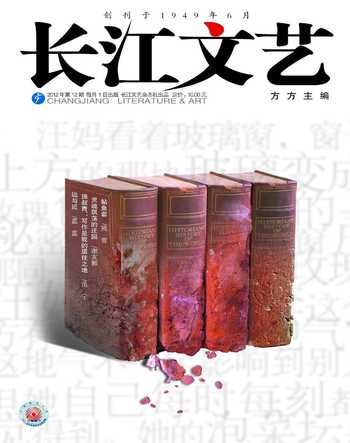幽凉
阎刚
刘保长走近那放哨的,
他就觉出了几分的异样。
刘保长断定他不仅仅是放哨的,
刘保长试探性地问他:
这家可是这地头的富户,你咋不进去淘点货呢?
那汉子并不吱声,也不看刘保长的脸,
也许他压根就不想与刘保长对视。
刘保长运足了气大喝一声:
赵狗子,你伤天害理,居然带人来抢你舅舅家了!
日军打过来的时候,河口平坝上的人都跑了,就只剩下房子。那些房子都显得很安静。这地头上的房大多是草房。草房就是用麦秸和茅草搭盖的。这种房子在河口很适用,据说冬暖夏凉。
河口平坝上不是没有有钱人,而且还大有人在。秋四就是其中一个。他在平坝算是够有钱的了,他买了一件狗皮袄子就是证明。这皮袄他很少穿。秋四似乎给自己立了一个规矩,房外不下雪起冻凌他是不能穿的。他也怕人说他摆阔呀。平坝上的人都清楚,要做成这么一件皮袄至少得杀四条大腊狗。而狗对于河口人来说又是十分特别的动物。据说,河口先前让饥荒折腾得可以。似乎什么都吃了,连谷种子也没能幸免。好家伙,这时从江北游来了一群狗。河口人怎么也舍不得把这些活蹦乱跳的狗杀了充饥,它们毕竟是一条条命呀。他们也得到了回报,精明的河口人看见那些大毛刷样的狗尾巴上居然粘着谷子。这些谷子终算救了河口人的命,他们就用这些谷子把一畈一畈的水渍地种活了,满畈满畈的都是香稻啊。所以河口人对狗就有了这么多的情结。他们怎能让一个大活人去剥一条狗的皮呢?
秋四年纪并不大,五十有六。秋四实在是抵挡不住河口冬天的严寒,背部的幽凉让他难以忍受。他这才托人去城里做了那件狗皮袄子。起先,他请了一位老先生来瞧病。老先生望闻问切一番后,说出了一句叫秋四倒吸一口冷气的话:风湿。秋四知道,河口这地儿的人常年与水打交道,风湿病就是这么来的,一犯病不就彻底断了水活么?老先生开了几服中药,叫秋四进城里去抓。出门后顺便说了一句,最好做一件狗皮袄子,那玩意儿对付风寒就是好。
这是一个大的忌讳。虽说四只腊狗不是他秋四亲手所杀,但一旦披了它们的皮,无疑就成了帮凶,帮凶当然是要不得的。这会预示什么事情要发生么?秋四那时还不知道。
这事当然不止秋四一人拿不准。但秋四为了能再下水干活,比如犁田,比如下网打鱼等,他得照老先生说的办:吃药和穿狗皮袄子。寒冬腊月,天寒地冻,这皮袄着实解决了祛寒的问题,但他心里终究还是有几分不踏实,原因当然是他不合时宜地披着四条腊狗的皮。
秋四家的房不是草房,是地道的瓦房,而且是青瓦盖的。他家的房子自然跟河口平坝上的草房对立起来了。说是鹤立鸡群也不为过。这平坝上的房子,不可能做成高宅大院,这里的居民压根也没有把河口建成城市的想法。建成了城市,雨季来了洪水谁挡得住。这里坚守的仍然是水进人退,水退人进的生存法则。从这个角度来说,在河口盖这种草房也算是经济适用的了。
秋四家做成青瓦房自然在河口这平坝上又不合时宜了。
秋四的皮袄是四条腊狗还是更多的腊狗皮做的,他家住的是什么房子,已经显得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日本人从江北打过来了。
日本人打过来是在夜晚,他们上岸前在船上就放了一阵乱枪。河口人看见那枪是朝天上放的,红猩猩的子弹弹道飞线足以让平坝甚至河口所有的人撤到后山上去。
那一夜, 河口的草房烧了不少,在那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日本人正好点着了照路呀。瓦房总归是瓦房,加之糊上粘泥的芦苇壁子不容易着火,当然就能保留下来了。这就是秋四家的瓦房依然能伫立河口的原因。
这一回日本兵真的就只是过路,日本兵是一路西去的,再则河口这地段平平坦坦的,非用兵之地,不宜久留。
即使这样,河口人还是不敢轻易回来,他们早听说日本人很无人道,他们可以将人头砍下挂在树枝上。万一碰上日本人咋办。
秋四自然不能把自己的家产都搬走,包括那件皮袄。
第一个回河口平坝打探情况的是刘保长。其实,刘保长也不愿冒这险,但他没办法,他毕竟是这里的头儿。刘保长是双腿打着颤回河口平坝的。他远远就看见平坝上少了好些间草房,宅基上只剩下几堆黑不溜秋的灰烬。草房着火后,烧得很彻底,除了那些糊了泥巴的芦柴壁子倒在灰堆里,其余都被烧了。
刘保长一进河口,着实吓了一跳。他看见还有一群日本兵或者是与日本兵差不多的人,在那些还没有被烧掉的草房前后转悠。刘保长这时想退也来不及了,或许是他并不想往后退。他清楚这时向后退的严重后果,后山的林子里可是一村的男女老幼啊。
刘保长硬着头皮继续往前走。他已经豁出去了,大不了在日本人的刀下做个冤鬼,死了河口还会有人念记他。
刘保长走近后,他紧张的情绪一下子松弛了下来,原因是,这拨在河口翻箱倒柜的人并不是日本人,或者说是一群会说中国话的日本人。语言是最具认同感的,即便是东洋人,说几句地道的本地话,那也少了几分狰狞。
刘保长走近才发现,这些转悠的人确实不是日本人,可能是从江北跑来的。他们都穿着粗蓝大褂,挎着个口袋在挨家挨户地翻值钱的东西。刘保长站在那伙人面前,“哎哎”地叫了几声。但并没有人理会他,他们照翻不误,这时的刘保长也没有办法了。他倒担心这伙江北人也会一把火把剩下的草房一齐烧了。刘保长明白,河口的草房里多半不会置值钱的物件,生活所需的器皿也是粗制滥造的。因为河口这地儿不对付乱兵匪患,也得对付洪水呀!这大水一来就得往后山退,水一退人又回来了。这样的生存条件能允许购置值钱的玩意么?
刘保长突然想到了秋四家的那件狗皮袄子。他知道秋四昨夜只顾逃命没来得及带走那件皮袄。
刘保长来到秋四那间青瓦房前时,他就看到了这样一幕:大门里有人进出,里屋有人翻箱倒柜,而外面还有一个放哨的,也提着一条鼓囊囊的粗布口袋。刘保长走近那放哨的,他就觉出了几分的异样。刘保长断定他不仅仅是放哨的,刘保长试探性地问他:这家可是这地头的富户,你咋不进去淘点货呢?那汉子并不吱声,也不看刘保长的脸,也许他压根就不想与刘保长对视。刘保长运足了气大喝一声:赵狗子,你伤天害理,居然带人来抢你舅舅家了!
赵狗子两腿发颤,辩解说,他们去抢我舅舅家,我并没有进去呀!刘保长说,无耻之徒,你怎么不进去抢呢?赵狗子动了几下嘴皮,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刘保长看出了赵狗子的心事,就说,你舅舅家也没啥值钱的,细软银票都带走了。但还有一件狗皮袄子,你得给你舅舅留下,这是你舅舅为治寒病专门买的。赵狗子应允了,他回头说服了那伙■ ,那件狗皮袄子终算是留下来了。若干年后,河口人再回想这件事,又觉得那纯粹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失误。
时隔几年,秋四的狗皮袄子还十分周整。他穿时总罩上一件罩衣,贴肉的也有衬衣,而且是那种在河口十分流行的土布衬衣,厚实无比。秋四穿着这种衬衣,又套着狗皮袄子,面对严寒,就有了更多的自信。
河口农会成立之前,秋四有近百亩田产,虽然全是水渍地,但也是地呀,秋四是这地头的富户,他当然就成了分果实的对象。这样一来,秋四的那件狗皮袄子也就保不住了。它也被作为“果实”给搜走了。
其实,那件狗皮袄子也并没有走多远,就在秋四家里放着。只是秋四那几间瓦房再也不是秋四的了。它也成了“果实”的一部分,现在成了仓库。秋四一家人都挤在近旁的那间只有几张芦席大的柴房里。
秋四的灾难来自那个冬天。秋四是不可能再穿上那件已被没收的狗皮袄子了,而那个冬天又出奇地寒冷。秋四难受至极。他甚至想象是不是可以扎进水里,或许那样还好受一些。秋四想象的完全是谷粒泛黄的六月天。
赵狗子来河口看他的四舅,也是在那个冬天。那时河口已经落过好几场雪了,满地一片银白。赵狗子想到这景象,就料定他四舅是万万受不了的。赵狗子来看他四舅还缘于心中的一个结。因为,他毕竟趁乱与人来河口抢劫过,而且还抢了四舅家。四舅家产被没收,总不能无动于衷吧?
赵狗子来看四舅,他带了一包花生米和一小壶莲子酒。他想这些东西是他四舅眼下急需的。天寒地冻,四舅没了那狗皮袄子靠什么扛下去呢?
赵狗子见了四舅就说,四舅,我来看您了,您知道我看您一回多不容易。秋四说,也多亏你了,我现在这样子给你丢脸了,也不知我这条老命保不保得住。早知道会是这样,我置那些水渍地干啥。赵狗子说,四舅,这些都不说了,我知道您有寒病,这大雪天的,我就带了一罐莲子酒,您可以挡挡寒了。秋四却摇摇头,说,这不管用,还是那件狗皮袄子好呀。赵狗子这才知道他四舅是多么不舍那件狗皮袄子。赵狗子就想,要是闹日本兵那阵子干脆把它抢过河去,兴许四舅这会儿还能穿上。
这时,赵狗子看见四舅蜷曲在墙角的一堆金黄色的稻草上,像一只冻僵的腊狗,他就下了决心,要去农会的仓库,给四舅偷回那件狗皮袄子。
赵狗子是在那个雪夜的子时干的。田野全是白茫茫的,映着一层淡淡的月光。赵狗子是从原来秋四家的后檐下挖洞进去的。他挖洞很小心,赵狗子知道他四舅的后檐墙壁是芦柴壁子。他几乎整个冬天都在与芦柴打交道。所以赵狗子对付芦柴特别有办法。
赵狗子取回了那件狗皮袄子。他四舅已冻得不行,像刚出壳的雏鸟,一根羽毛也没有。赵狗子迅速给四舅披上了那件狗皮袄子。秋四颤着声说,你算是害苦我了,也害了你自己。我再穿上这狗皮袄子就等于罪加一等了。赵狗子说,我们不能逃么?赵狗子一开始还没把事态想得这般严重。秋四说,真的得逃了。他俩一口气逃到江边,那里是一片密实的芦苇荡。
秋四和赵狗子逃到芦苇荡里。他俩在雪地里留下了脚印,赵狗子和秋四穿过芦苇荡来到江边。这里再没有积雪了,只有软软的泥。赵狗子说,我们下水吧,顺着水走就没人知道我们的去向了。秋四没有反对,他还巴不得让自已的脚印早点消失。秋四离岸好远了,赵狗子却在岸边叫道,四舅我就不来了,您就穿着狗皮袄子走吧。秋四站在水里骂道,老子早就晓得你狗日的会来这一招的。
几天之后,秋四的尸体才在下河湾找到,但那件狗皮袄子却早已不知去向。平坝人说,这或许是一件好事。
责任编辑 向 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