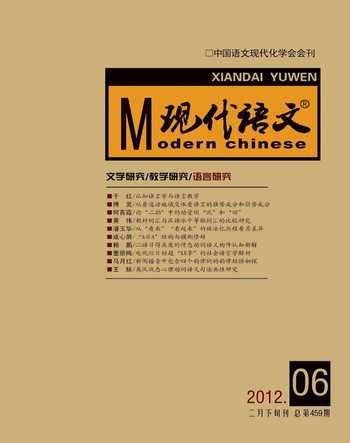《郑樵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后记
摘 要:专著《郑樵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1月出版,此为本书后记。这篇后记写于2011年9月9日。
关键词:郑樵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民国语言学史语言学思想史
专著《郑樵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是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郑樵小学研究》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修改的内容主要包括:对部分内容做了一定的调整和增删,对个别字句进行了一定的润色,书后加附三篇论文。
在本书付梓之际,我想要做出三个方面的说明。这些说明,既与本书学术有关,又与本书写作无关,就算是与本书有关的相关解释吧。
一
学问本身,让我敬畏。
关于语言学这个学科,历来就有很多不同声音,这其中包括对“文献”的看法问题。对于文献的意见,近百年来,一直有两个极端的看法:一是文献死学没有思想,二是文献实学不含水分。这两种极端的看法,既存偏颇又有道理。先说道理,故纸堆一旦钻进去就很难抬起头仰望天空,中国文献浩如烟海,哪里还有时间抬起头来喘口气呢?躲进故纸堆里定然没有站在大草原上、大海边那种“海阔天空”的视野。再说偏颇,如果一个人只顾仰望星空,不管脚下的土地,時间久了大概也会得颈椎病吧?这就是两个极端。
例如,民国时期的大学者钱玄同就是一个极端的人,他先是好古(古文字文献),后是疑古(喜拼音文字),“以今日之我与昔日之我挑战”,剧烈极端。但是,钱玄同也有一些平和的学术过渡,并非完全那么剧烈。比如说,钱玄同1918年著有《文字学音篇》,书中有些观点后来屡有改变:1929年著《广韵四十六字母标音》用国际音标给《广韵》四十六母“标音”确信无误;1932年著《古音无“邪”纽证》就试图在“证”了;1934年著《古韵二十八部音读之假定》则用起了“假定”这样科学而豁达的情怀。钱玄同的“标音”“证”“假定”三个关键词,类似于三段“语言学断代史”,分别修正了他在《文字学音篇》中的某些结论。我们通过这三个“关键词”,梳理出了钱玄同的“语言学思想史”,而这个“语言学思想史”又能够说明钱玄同在学术上有着平和的一面,并非无限的剧烈。
文献很重要,但文献只是语言学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文献研究中常有这样的情形:一个字要推敲三五年,“句读”点错了一处要羞愧好几载,某本书没有读绝对不能假装看过,更不能列为参考文献。这是一种严谨的朴学作风,对此我表示深深的敬畏(传统中所说的“校雠学”一名就是仇人相对,那似乎不仅仅是敬畏,还很有些仇恨在里边)。只要一想到这样的朴学作风,我就觉得后背直抽冷风;对此学问,我异常虔诚,我怀有万分的敬畏情怀。我的这本书,花了我很多的心血,我也希求这本书能够做到严谨、无误,但我依然不敢保证本书连一个字、一个标点都不会出错。当然,就纯粹的学问层面上而言,我相信我并没有仇人。
对待学问本身,我怀有无限的敬畏。当然,敬畏之外,我希望我还能够拥有一种豁达情怀!
二
学问就是学问本身,学问不是学者。学者本人就是学者,学者不是学问。
然而,学问之外,学者也要有自己的生活。中国有着自己的国情,社会背景、时代年轮、民族心理、经济基础、人生阶段等等,大到“背景”小到“柴米油盐”,都在影响着每一个学者的实实在在的生活。
豁达是一种境界,它或许并不会受到铜臭的左右。然而,“困窘”并不会轻易溜走,要应对各种各样的“困窘”则需要一种极大的豁达情怀。在困窘面前,在2008年那个“烟花三月下扬州”的季节,复旦大学博士生李开学陨落了,陨落在那个春暖花开里。这种不幸如果是发生在建国初期,如果那可以看作是为了“革命事业”,李开学博士定然要被沉浸在“烈士”的肃穆空气之中。非常不幸的是,李博士不是生活于革命年代,而是在一个“大经济时代”。在这样的大经济时代中,竟然有无数身披着校长、“大教育家”的“道学家”们在强调“素质教育”,在痛斥“功利教育”,在鼓吹“通识教育”和“人的全面发展”。这,完全让人无言以对!2008年,国家对非定向博士生的生活补贴每月不足300元,2009年年底开始(有些学校从2010年元月开始)国家规定非定向博士生的生活补贴每月不得少于800元(如山东大学自己规定每月不得少于1500元),这个举措竟然痛斥了“功利教育”本身。呜呼哀哉!在这里提起这个不幸的事件,我绝对不敢有什么其他的引申,我要刻意不破坏那种肃穆空气。
然而,“困窘”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确实也会有社会上的一大批人并不理解。这种不理解,如同社会上的人先前把大学生称为“天之骄子”,后来随着高校急剧扩招又把大学生称为“人之渣滓”一样,种种不理解都曾存活于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人生历程之中。“困窘”也许有很多,“困窘”也许一丁点儿都没有,有没有“三座大山”抑或“五座大山”因人而异,学科不同,情况也会有所不同,日子过得快乐似神仙的博士生也有啊。
全国地区有差异,地区不同,生活水平、生活状态也不尽相同。我2003年工作时全部收入每月700多元钱(算进课时费扣除水电费和房租),春节临近还要面对那“八千里路云和月”,那几年是我人生中最为灰暗的谷底。非常幸运的是,我于2005年申请到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经费7万元,这个项目经费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我和我爱人读完博士。当时考取博士时,可以读非定向,但提档案走要交违约金,读定向博士则连那微不足道的博士生生活补贴都享受不到。就这样,我们只能“坐吃山空”,这个“山”主要的就是我申请的这个社科项目,这个“山”主要就是那来回八千里的“山路”。对于这个项目经费来说,我当时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因而可能“经营不善”,也由于我报账比较规矩,我都是严格按照基金经费管理办法来做,能够报销的主要就是我们寒暑假的“铁道费”。那时我也会偶尔回一趟山东老家,或者往返苏州、山东,或者往返四川、山东,这也需要一些“铁道费”。所以,我的这个项目能够支撑我们读博士的,主要是献给铁道部的这一部分,其他方面的“坐吃山空”我们确实再也没有什么“山”了。一个普通老师,即使偶尔有幸获得了个项目,那些项目经费还是得精打细算地省着点花。对于文科的项目来说,经费开支的大头是差旅费(需要社会调研的项目更是如此)、购书复印打印费,项目结题成果如果出版的话,出版费也是一大笔钱。
随同全国繁荣之大潮,最近几年我所在的单位的条件比以前稍有改善;加之我们已经博士毕业了,迈过了那一个“人生阶段”,我的生活不再如过去那样暗淡得那么厉害了。这也让我现在回想,一个脚步与一个脚步之间有一个hold,也许只差一步路程。能够支撑那么一步路的,也许只有信念,也许只能依靠信念。想到这里,人,似乎又很容易豁达起来了!
三
一个小小的启动,和无数大大的感谢。
本书成稿数年来,我并没有拿出它来申请什么“高级别”的项目,主要是我觉得我已经很难再突破这个题目很多了。我对于那些“项目”的理解是,一个项目就要资助一种可以深入的“思考”,就要资助一种存在希望的“突破”;而作为一个“既成”的成果,如果作者自己都觉得不能够再做出较大的“突破”,那还是不要去申请为好。
当然,这本书还是一个小小的“启动”基金项目的成果。本书是“西华师范大学科研启动项目‘宋代语言学家个案研究(项目编号:10B021)”的成果。在本书整理、修改基本完成之际,相关领导曾善意提醒“按照学校内部规定,没有挂什么厅级以上项目的专著,学校不一定会认定为专著”,本着从俗的原则,我还是临时抱佛脚地申请了一个名目的项目,即“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郑樵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于是,本书也就算作是这两个项目的结题成果吧。同时,本书还得到了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申博学科学术专著出版资助提供的部分出版经费,特在此致谢。西华师范大学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老牌本科院校,在改革开放中慢慢落伍了,现在她想奋起直追,这么一个并非很富裕的学校也开始注重学科建设并给予本书以部分资助,这不得不让我感谢!西华师范大学的有些学科还是很强的,就文学院内部而言,现已有一些兼职博导(例如古代文学专业的赵义山教授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兼职博导),汉语言文字学、语言学相对弱一些,我们只是人家的“支撑学科”罢了。
这本书的成果虽然没有打算去申请什么项目,但是,关于与这本书相关的学问我却思考过,甚至还思考过几年时间。在这个思考的过程中,我也与相关的学术前辈、同人研讨过与本书有关的许多问题,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感谢!
本书主体部分的底稿原为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在此我还要感谢苏州大学的八位老师,包括我的博士生导师张先生,还有汪先生、朱先生、王先生、徐先生、马先生、姜先生、高先生。他们八位先生或者对我的学位论文有所指导,或者对我的读书、学习有所指导,在此我都要感谢他们!我的硕士生导师西华师范大学的查先生对我的这个书稿也有所批评、指导,在此我也向先生表示感谢!
在本书基本定稿之际,我曾请求过两位学术前辈赐序予我。第一位是我的博士后合作导师唐子恒先生,第二位是从事学术研究六十多年的资深博导赵振铎先生。唐子恒先生,为人随和、低调,先生对学术充满着无限的热情与真诚;唐先生豁达、睿智,先生对学界同人、子弟怀有深情厚谊,先生是我一生的榜样,从今往后我要洗心革面、一心向善、潜心研究。赵振铎先生是四川大学的资深博导,八十几岁的高龄依然非常健硕,赵先生现在还在带博士。我与赵先生是在几次四川省语言学会年会上认识的,赵先生的学识让我佩服,但我们私下交往很少。后来,我原来的一个师弟投到赵先生门下读博士,我又和赵先生又有了这么个间接的联系。我这个师弟在读硕士期间我和他很熟,后来他硕士毕业后到新疆工作过几年,那以后我们联系少了些,2010年他在赵先生门下读博士以来我们也只是偶尔联系一下。基于这两个层面的原因,一是我和赵先生虽不熟却本相识,二是我师弟从中帮助、请求赵先生赐一书序予我,赵先生这才答应给我写一篇序言。只是我在写此后记之时,赵先生的书序尚未写就,我想,赵先生学问博大精深,赐予我的这篇序言很可能是纯粹在谈学问吧。承两位先生的序言,我定要把学问好好地做好,不辜负先生们的一片心意。在此,我再次感谢唐先生和赵先生!
我选择在9月9日这一天来写这篇后记,是因为我模糊记得有“九月九日憶山东兄弟”那首古诗以及隐隐约约听过“走走走走走啊走,走到九月九”那首老歌,想必没有人愿意承认诗歌亦如戏文吧。九月九日千佛山有庙会,此时的济南还是别有一番气象。不过,我还是喜欢十几年前的千佛山,那时千佛山、燕子山等等都是绵延一体的,现在的千佛山似被一条崭新的宽敞大道隔断了。这样一来,我不知道那些小燕子们还能不能很方便地去拜佛了?
(薄守生四川南充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637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