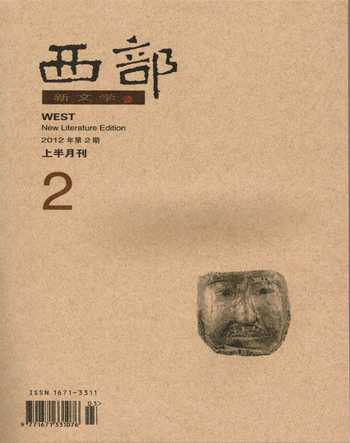班果等
郭建强 选编
班果
土耳其
突厥的铁蹄 奥斯曼人的弯刀
席卷 像从地图的某个边角开始
世界在经历一次折叠
土库曼的羊皮 铺展
直至爱琴海边
而塞尔柱人的毡帐,最终在
拜占庭辉煌的宫殿之侧 驻扎
君士坦丁堡或者伊斯坦布尔
名称并不重要
蓝色清真寺的塔尖 圣索菲亚教堂的塔顶
共同支撑着你城市的上空,并且有
同样的鸥鸟栖落,清洁工人
每日得清理同样的白色有机物
你卸下了马具,弯刀早已生锈
并且陈列在博物馆
你西装革履,品着咖啡
回味着小亚细亚的历史
复杂而纠结的历史
一个陈旧的帝国,一个相对年轻的共和国
城市早已变成了马圈
坐骑嗜油,但必须以欧IV的标准排放
是的,成为欧洲是一种标准
从法律到相貌,我很难为它做出区别
城市干净有序,草皮经过修整
行人目光温和,打量着这群黑头发
黄皮肤的异乡人,礼貌而克制
但在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山区
一位乡间农民的驴子却大发脾气
农民拽它的头向西,它却执拗地向东
又尥蹶子,又甩头
无论如何都不肯顺从
亚洲的血在体内呼啸
曹有云
风景
物质庞大坚硬
音乐之水绕行远去
千年极寒提前抵达秋天
人们慌乱抢购体温
货币坚挺的幕布遮蔽信仰冰冷的天空
美少年在浩瀚的阴影之海黯然神伤
词语锋锐的尖端放弃争执
相忘于江湖
天下喧嚣
有少女在张灯结彩的走廊无声抽泣怪异
紊乱命运之相
你腹中闷死多年的诗歌
无人倾听而烂成废墟之丘
站立孤绝的高原雪峰凝望凛冽星空
怀念远古大海青春之魂
葛建中
都兰遇雪
风水宝地中的都兰
云彩独占鳌头
蒙古词语中的温暖
酒中我找到了家乡
黄叶爬上枝梢
溪水静静地流
树上麻雀喧闹
风中枸杞悄悄地红
都兰远山在阳光下变色
麦地里农夫日日稀少
马道上,转场的牧狗在叫
待宰的牦牛群走过断桥
去迎接愈趋浓重的暮色
在树叶将落未落时
在又一个微曦的清晨
我仰首迎接深秋的初雪
郭建强
脊椎,脊椎
困苦缓慢地、缓慢地上涌
掠过荒凉的腹腔,生有裂缝的心脏。
喉间一片黑暗,锯齿状的疼痛延绵不绝。
谁能拒绝阳光的情意?可是,
爱,如此艰难,谁又能承受阳光的情意?
脊椎,脊椎。
无法描绘这浸泡世界的液体,
胶质的泡沫,梦中的影子,明亮而且幽晦。
谈论,其实是猜测,或者是感知,其实是等待。
命运亮出它的形体:也许是黑犬,也许是
明月。
脊椎,脊椎。
两粒微小的浮尘在空阔的宇宙对舞
绝望的火焰,绝望的花朵
飘摇清澈的眼睛。更习惯哭泣:一只手掌
在暗夜高举,而船儿安静地沉落水底,
溅起的鸟群带着神话般的轻盈。
脊椎,脊椎。
漫长的战事,漫长的别离,漫长的日月
我们是如此热爱生,如此热爱死,
热爱清晨的圆号与长笛。
体温、血液相互触摸、融和、飞旋着汇合于
河流
这是最后,是至深的温暖和芬芳。
脊椎,脊椎。
吉狄马加
嘉那嘛呢石上的星空
是谁在召唤着我们?
石头,石头,石头
那神秘的气息都来自于石头
它的光亮在黑暗的心房
它是六字箴言的羽衣
它用石头的形式
承载着另一种形式
每一块石头都在沉落
仿佛置身于时间的海洋
它的回忆如同智者的归宿
始终在生与死的边缘上滑行
它的倾诉在坚硬的根部
像无色的花朵
悄然盛开在不朽的殿堂
它是恒久的纪念之碑
它用无言告诉无言
它让所有的生命相信生命
石头在这里
就是一本奥秘的书
无论是谁打开了首页
都会目睹过去和未来的真相
这书中的每一个词语都闪着光
雪山在其中显现
光明穿越引力,蓝色的雾霭
犹如一个飘渺的音阶
每一块石头都是一滴泪
在它晶莹的幻影里
苦难变得轻灵,悲伤没有回声
它是唯一的通道
它让死去的亲人,从容地踏上
一条伟大的旅程
它是英雄葬礼的真正序曲
在那神圣的超度之后
山峦清晰无比,牛羊犹如光明的使者
太阳的赞辞凌驾于万物
树木已经透明,意识将被遗忘
此刻,只有那一缕缕白色的炊烟
为我们证实
这绝不是虚幻的家园
因为我们看见
大地没有死去,生命依然活着
黎明时初生婴儿的啼哭
是这片复活了的土地
献给万物最动人的诗篇
嘉那嘛呢石,我不了解
这个世界上还有没有比你更多的石头
因为我知道
你这里的每一块石头
都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个体生命
它们从诞生之日起
就已经镌刻着祈愿的密码
我真的不敢去想象
二十五亿块用生命创造的石头
在获得另一种生命形式的时候
这其中到底还隐含着什么?
嘉那嘛呢石,你既是真实的存在
又是虚幻的象征
我敢肯定,你并不是为了创造奇迹
才来到这个世界
因为只有对每一个个体生命的热爱
石头才会像泪水一样柔软
词语才能被微风千百次地吟诵
或许,从这个意义上而言
嘉那嘛呢石,你就是真正的奇迹
因为是那信仰的力量
才创造了这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永恒
沿着一个方向,嘉那嘛呢石
这个方向从未改变,就像刚刚开始
这是时间的方向,这是轮回的方向
这是白色的方向,这是慈航的方向
这是原野的方向,这是天空的方向
因为我已经知道
只有从这里才能打开时间的入口
嘉那嘛呢石,在子夜时分
我看见天空降下的甘露
落在了那些新摆放的嘛呢石上
我知道,这几千块石头
代表着几千个刚刚离去的生命
嘉那嘛呢石,当我瞩望你的瞬间
你的夜空星群灿烂
庄严而神圣的寂静依偎着群山
远处的白塔正在升高
无声的河流闪动着白银的光辉
无限的空旷如同燃烧的凯旋
这时我发现我的双唇正离开我的身躯
那些神授的语言
已经破碎成无法描述的记忆
于是,我仿佛成为了一个格萨尔传人
我的灵魂接纳了神秘的暗示
嘉那嘛呢石,请你塑造我
是你把全部的大海注入了我的心灵
在这样一个蓝色的夜晚
我就是一只遗忘了思想和自我的海螺
此时,我不是为吹奏而存在
我已是另一个我,我的灵魂和思想
已经成为了这片高原的主人
嘉那嘛呢石,请倾听我对你的吟唱
虽然我不是一个合格的歌者
但我的双眼已经泪水盈眶!
注:嘉那嘛呢石,即玉树以“嘉那”命名的嘛呢石堆,石头上均刻有藏文经文,其数量为藏区嘛呢石之最,据不完全统计,有二十五亿块嘛呢石。
江洋才让
青海留言
“冥冥中的青灯为何不亮?”
可世俗的黑雪却已覆盖了神的庭院——
一对硕大向上的野牛头
犄角
千疮百孔
以艺术之象征,依然独对着永恒的
人类天空。
我眼含愤怒、饥饿,在现世的宣纸上
抒写着自己的诗化人生——
几次无功徒劳的穿越。
羊子环绕的湖泊。
冻醒的身躯。
死亡之吻。
以及神秘之石上永恒的偈语。
潜意识中反复出现的诗句:
“冥冥中的青灯将由谁点燃?”
在结古怅望光芒发源的地方
如今我已伫立于你高拔的方向
头顶毛发像钢针
深入空阔
感觉这首陈旧的诗篇注定要被埋葬。
埋葬的还有:古老的民谣
一罐救命的青稞
几粒石子。
这些人们眼中最可怜的陪衬……
哦,西藏的雅砻
光芒发源的地方,
孕育圣婴最初的精血,祭司高贵的神态
已缓缓凸视。
和着谁的泪水,弹着世间这普遍的琴弦
灰烬纷飞中
低吟:
地平线上兄弟们的情谊。
落雨涟涟中
高歌:
姐妹们初乳的春天。
一只耳朵中:雪豹在哭泣。
另一只耳朵:鹰在怒吼。
刘大伟
雨若琴声
源自天籁,抚过夜晚幽深的湖
树木传导淅淅沥沥的琴音
那是古筝上轻轻跃动的音符
在潮湿的音域里缓缓入城
请一定携带悲情之爱的秘方
去拜谒赋诗而歌的女子,阅读她
幽婉如水的情殇。时间之空城
飞蛾闪烁,摇曳着破碎的夜灯
请一定饮完这坛深深埋藏的老酒
在醉意的琴音里拥抱她隔世的守候
需要聆听,那些喃喃的细语
那些落满红叶的诗句。一定要安静
夜晚之湖被投进过多的假如
那些敏感的涟漪扩散了谁的孤独
城外山青,一场绵绵落雨
一把雨中燃烧的焦尾琴
流淌出汉风唐韵,蚀了月光
以及初秋竹黄的隐痛。江河如诗
垂钓者用蓑衣裹起往昔,鱼竿深入
一场雨的印记。远处,雨若琴声
越过河床和秋日静穆的密林
梅卓
女湖之美
她是美的。当四季轮转
绿雨到白雪
飘向女神的黛眉青眸
她早已看断世间百态
仍愿意红颜不变
犹如浓烈的一声惊叹
悬挂在大地的心脏
草尖上的风已经吹走千年
湖波上的花朵依然灿烂
她是美的。当传说蔓延
时光和空间
容纳高僧大德的颂词
也容纳了凡夫俗子的祈祷
她欲言又止
却从没有停下繁洐的脚步
她的美丽如此有力
并非沉默的高原未曾诉说
创世前的第一道彩虹
漂染过她的松石
宇宙间的第一道闪电
装点在她的珠冠
还有第一个秘密
尚鲠在她的胸间
还有第一句歌谣
曾透露她的忧伤……
留下大自然的馈赠:
一个节日——
关于美
关于看到美时
眼睑上方突然而来的压力
那是承袭了怀旧的液体
是呈献给节日的贡品
晶莹剔透毫无杂念
清洁一如湖水
呈献、呈献——
为她盛大之美
也为自己
马丁
树的伤痛
——与MZ君在仙米林间的三言两语
啊?噢。
我是说伤痛树的伤痛
你看那棵树半腰分枝的地方
一次阵痛之后
就连时间也没能愈合的伤口
我是说多少人游走仙米林间
又有多少留意树的伤痛?
我是说我的发现与注目
对于伤痛的树是一次抚慰
还是更深的刺痛?
我是说树的伤痛是大致一样的伤痛吧
而人的伤痛却各有不同
我是说树以裸露的伤口述说苦难
谁为人类切入内心的阵痛开具处方?
啊?噢。
马钧
鱼群是液态中穿梭的飞鸟
翻卷的云朵比之于翻卷的浪花
更宜于营造沉思的情景
诗歌说出秘密的同时又营造秘密
白色的灯罩弃在路边的榆树墙边
像是被人残暴摘取的头颅
身首异处无人惊骇它玄秘的警示
碎叶铺地秋雨湿重
无伞可举的行人一任视线迷离
昨夜把盏的欢颜转眼被妻子剧咳的痛楚
消弭
走在大街上的脑海
反复播放的是X光片上咳断肋骨的裂隙
喉结突出胡子剃过一茬又茂密一茬
我还在时间的河岸喘息
泅渡抑或溺毙
剧烈地拍击河水不过也还是顺水而下
鱼群是液态中穿梭的飞鸟
马用四蹄飞翔
而我只能赤足踩踏沙土
积累一层又一层肉茧
马非
等车
一辆红色的的士
又一辆红色的的士
第三辆红色的的士
……
他坐在马路牙子上
看着鱼贯而过的
红色的士
开始很急
现在不急了
他在等
他就是不相信
在这座城市里
全是红色的的士
他在等
一辆不是红色的的士
然后招手
坐上去
马海轶
乡间邮递员
1980年代初见他时
他是四十开外的老天真
连滚带爬从山上下来
就像一只成精的山猫
有点疯癫,没有正经话
仰面发出奇怪的笑声
先喝茶抽烟卖关子
然后才把信、电报和汇款单
交到等它的人手里
或许还有包裹。包裹里
有茶叶,有糖,或许
还有死在外面人的骨灰
他走村串户多少年
给人们带来喜讯和噩耗
让他们笑,让他们哭
让他们在哭笑声中翻跟头
暮色中,他离开村庄
回到镇上,回到小砖房
咀嚼哭笑之后的清静
以及乡村不为人知的故事
古人说得真好啊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转眼三十年过去,他
应该是七十多岁的年纪
2010年,另一个邮递员
告诉我:“他说看够了
奇怪的是,说过之后
没过三月,他双目失明了。”
撒玛尔罕
山那边的世界
我们随时都会碎满一地
——题记
翻过最后的那座山。那边的世界
一种冷使我感觉不到心跳
一双时间的手不断摧毁城堡
无法计算路程和年月,无法辨别昼夜
没有欲望,所有的灵魂一贫如洗
甚至没有一行美丽的诗句
无尽的黑夜是最真实的世界
罪恶和虚伪呈现原本的面目无法遮掩
无法赞颂或者厌恶任何生灵
甚至无法吟唱与赞美无关的音符
我曾经的爱情开始出现:
就像玻璃碎片一样
棱角与棱角之间,每一个触点都是伤刺
像黑夜中无法比拟的黑云涌起漫天罪恶
像秋风中的落叶撒满一地忧伤
我曾经的孩子:
成为一个行者,歌者,幽灵
依然记得人间的爱与恨
主啊 请容许我沉默,聆听我的忧郁
我是你那只迷途的羔羊:我恐惧,寂寞,失落
只等
你出现!带我走向回家的路
带我回到流淌着蜜汁和琼浆的地方
主啊我需要考验和勇气
需要更多的时间,需要漫漫旅途
最终在葡萄园的凉爽中品尝美酒
寻找所有的亲人和朋友
注目你出现的光晕
宋长■
男人的高陆
1
秋深。青海男子西望:大雪直压昆仑,飓风 堆垒寂地。
父亲仍在沉默。他的疆域,花开伏地,人往 高处,
有不可言状的惊悚之象。
他直视雪峰一侧睾丸覆盖半个草原的种
牛,颇为得意。
他的世界似是雄性具象的组合。
灵魂游牧之地,一片阒寂。在痛中痛啊。
2
男人。
男人的心史是被血泪铆定的记忆。他想起 黎明,
一块巨石爆裂——众草向上的力量改变着
命运,
天空成唯一的去向,他的目光砸开冰河。
涌动。涌动。
他在碰撞中进行生命和生命的对接。
3
男人在生活中奔走,一次次被黑夜淹没。
他掩怀潜行。前方不可预知。前方是一柄 断剑?
一抹红光?一场大雪?一次没有交锋的战争?
一弯清冷的残月?前方是两个顽童捣乱的 一盘棋?
是昨夜?是今天?是尖叫?是觳觫?
是雄鹿撞向峭岩的一瞬?前方是父亲吗?
前方仅是等待男人的生活。生命中必须踏 上的大道。
他想从大地下掏出太阳。
4
那时,夜的流苏沉如飞瀑。男子有些恍惚:
废墟上一朵黄菊笑了,虚掩的雕花木窗
内,绣花女子
将一滴血染上花茎,那时,大风吹动青海,
女子吹熄灯盏,无眠复起,念想之人尚在
远方。
在众水低啸的寂地,他裸身走向大河,母
亲的血啊,
男子泪落高陆,在生命逆溯的路上,
他察知的秘密从苦难开始。
而月下想他之人,久坐无眠。青海下起大雪。
5
太阳升起。男人的高陆缓慢展开:心在上
午走一月的路程,
在下午也走一月的路程。
他把种子放在大地下面,他把河水浇在大
地上面。
他把他举到天空,青海的天空,你的儿子
长着你的骨头,
流着你的血。你看他在大地绝望的时候降 下时雨,
他的确只是火焰水和火焰的保护者。
男人,男人,你生活的地方,你就是一切。
肖黛
来世
秋天过来了。过去的却是另外一个人
在另外一个人旁边的秋天
我画下了细雨,引发冷风景
却没有什么值得赞美
没有谁的目光掉进水里
飘动起来,经过灰白色的晚上
让时间一样的冰雪
结成我的两只将老的纽扣
被举证在就要露面的冬季
便就是漫长的行走止步于门前了
光线黏稠,鼻息声留在外面
其他的空白来历不明
亮晶晶的,变成我最为重要的部分
而那另外一个人的旁边有孩子哭着
哭着长大……哭着才能长大
长成那另外一个人的模样
使我的辨识再度开花结果
秋天真的过来了,过去的那个人笑呐
采花摘果的好像什么事情也不曾发生
杨廷成
高处的青稞
七月,金黄金黄的阳光下
青稞的子孙们站在高高的山塬上
被浓醇如酒浆的秋风熏醉
它们尽情地歌唱与舞蹈着
欢呼于河湟谷地丰收的季节
这些古老如青铜的物种
从神农氏粗粝的指缝间洒落
沿着刀耕火种的岁月一路走来
是向往太阳的抚摸与温暖吗
把梦幻肆意地绽放在西域的高地上
早春的冽风中扎根
盛夏的月色里抽穗
金秋的天空下成熟
青稞们把沉甸甸的麦穗深深地垂向土地
是向养育了自己的大地母亲感恩、鞠躬
青稞,站在高处的青稞
是一群群铮铮铁骨的高原男儿
威风凛凛地站成让人仰视的风姿
在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高度
以烈酒的品质,绽放生命的奇迹
衣郎
握紧青海高原
怎样用残缺的文字说出唯美
说出拆散的梦和对媚俗时代的拒绝
九月来临我始终找不到自己的影子
找不到关于青海高原确切的描述
和那一次梦境里灵魂和大地的默契
就在这个夜晚我握紧一支笔
握紧青海高原上这些贫瘠里鲜活的词语和
高昂的头颅、生硬的大地、贫穷以及
男人的黑和女人的红
敬畏里充满信任和忧伤
它用大片大片的田野和河流接纳着
足迹、歌声、流浪
还有男人怀里的刀子,女人怀里的种子
——爱恨里繁衍着的生生不息
在威远镇光阴里散发着血气和火焰
早起的祖母口中念念有词
孩子们:主语是命运,谓语是灵魂
你们听到的是前世的回声
我们酿酒,穿粗布衣服
和着单调的皮鼓音乐跳舞
陶器在炉火中烧制
马匹打盹老人不语
情绪里有雁声阵阵车声隆隆
我在诗意和虚华之间顾此失彼,乐不思蜀
面对文明古国的石头、金子和青铜乐器
我们握紧的是沾血的毛褐还是遗弃的铧犁
穿过记忆,许多人醉在了葡萄美酒里
我停下脚步。光阴里有凋落和再生
还有一群孩子的金色年华
抛开思想的翅羽
站在古老的城镇
拳头里紧攥着善意的春天
握紧上午的人群下午的车流
握紧一只杯子,杯子里的水和那个送水的人
它们之间如此贴切的关联让修饰词眩晕
握紧夜的寂静和漫长
渐次亮起的街灯和行色匆匆的脚步
给青海高原的苔藓和泪水弓箭和矛头
深夜的钟声窗纱筛碎的月光
给自己活着的理由、写诗的理由和爱的理由
给你沉默,略显偏执的亲近
握紧一首宿命的诗歌打开它
划出一道裂痕
和北方一起迎风看岁月浮沉
几千年前我在青塘旧城里注视过一尊陶器
五个女人在跳舞祭祀神灵
历史里注满了水分
我醒来的那个早晨
水是我的另一个梦境
现在 我终于写下了这高原上雾气里的麦香
写下它:真理飞翔的轨迹
一条河和一条江的颜色竹片上的传说
抛开旧灰尘和书籍里迷失的假象
握紧指缝间的光阴
握紧孩子信口说出的谜底
把信仰放在高处把身体伏到最低
我们都是大地的孩子
时间把彼此拴在一条线上相连却不相关
我依然记得那整夜的雨声浸没呼喊的年代
守着粮仓连乌鸦都饱含泪水
我们握不住年轮的滑行
许多人埋头冥思时间与命运的双向选择
握紧山河的棋子点破残局
大西北的黄昏啊暗了下来。夕阳的斜面陡 增苍凉
汉子们把脸埋进掌心里
思考麦子和光亮
古诗词里的长云孤城在史册里漫步
马蹄声哒哒而来旧时代的挽歌布满山冈
想起雨我就想起德令哈这个小城
闪电曾划破它的内心诗人的笔
在石头间画下那个温柔的姐姐
姐姐就是你你是布哈河上空的鹰
鹰是青海高原的翅膀
我注定要一生行走在青海高原
坐在山顶像青海王一样
看子民们放牧青春
手背上无边无际的天空
手心里无边无际的大地
山谷里回荡情歌孩子们长成男人
冷峻的高山充满隐喻的河流
工业时代四平八稳的文明
我穿过它们,但没有回头
我只想给微小的事物一种依靠
给它家的含义和触手可及的疼痛
让飞蛾握紧火的内核
熟悉黑暗还要被黑暗捉弄
我从青海高原坚硬的内心里退出
守在影子里给自己继续写下去的力量
五岁的时候我手里握紧的是沙包,姐姐
的手
十岁的时候我手里握紧的是铅笔、红领巾
二十岁的时候我手里握紧的是准考证、
通知书、派遣单
三十岁了我握紧的是银行卡、身份证、手
机和
别人的眼神
但我只想握紧青海高原
握紧它白天给我的脚步
夜晚给我的激情
握紧高陆上的秋天
镰刀里锋利的言辞
酒杯里的乾坤
握紧一首诗的寂寞和寒冷
赵秋玲
属于记忆的蓝湖
初夏已属于记忆
属于与我毗邻而居的——蔚蓝的大湖
属于从笔尖刚刚滑落的那滴湖水
我们就这样在挽歌中相遇了
玉波飘荡唤醒水中鱼群
那种沉稳和从容沉潜在水中
让我怦然心动
仅仅是一瞬间
一瞬间莫名的伤感和思念
凌空切入灵魂那么锋利……
我不是一个涉水者
却庆幸在行走的路上遭遇《蓝湖》:
“有一种夜晚像倒悬的蓝湖”
这个水雾搅着蓝光的夜晚终于来临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捂住伤口
看到大湖的伟岸襟怀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在寒冷的蓝光中
找到暖怀之物
当表达与沉默同样具有美的质感时
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在某种疼痛中想起我
就像想起湖水中一尾金色的裸鲤
就像今夜我想起法国歌手包琳娜·巴桑
张正
疯子
从前有个疯子
他吃掉墙根的野草它们在他肚子里小声
歌唱
他追逐的女学生在下午的风里狂奔像参
加运动会
他住在两面相对的镜子里不需要方向感
他在楼梯昏暗的拐角抚摸那些不肯离开
的光线
他跳上一面墙壁好像站在竖起来的水面
有一次,他跳进了自家的
印着“北海公园”的年画里不再出来
母亲要给他送饭就得大声喊他
他从远处的亭子里探出头来厉声说
“你端进来!”
——仿佛解除了头上的一切咒语
栏目责编:东海 舒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