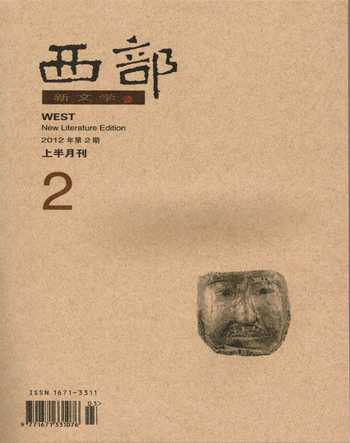父亲的画像
刘小骥
父亲让我学画,是我八岁生日后不久发生的事。他领我去见一位姓李的老师,把练习本上的习作和各类涂鸦拿给他看。他笨口拙舌又满怀憧憬地对那位脸上坑凹不平的男人说着些什么,而我,目光早已游离到室外:公交车排放的尾气,红烟囱冒出的黑烟,游戏机房屏幕上“吃豆子”的游戏,远比鲜明却失真的画作要吸引我。不过,决定权不在我手中,李老师说可以一试。此后,我的手中便多了一样东西。
对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于筒子楼的人而言,画笔、小提琴、二胡、笛子和舞蹈教室大约可以构成共同的经验,除此之外,你还能嗅到公共厕所的腐败气息和狭长走廊的油烟味;消灭害虫的公告贴在每幢楼的楼栋口,蟑螂、耗子的死亡习以为常,带糖浆的药片总会哄骗它们自投罗网;骄傲的化工厂工人们,每天都穿着整洁干净的蓝灰色工作服出出进进。孩子们却是野的,无法无天的他们不是拿水枪把晾挂在外面的被褥喷湿,就是偷偷熄灭假想敌人家的煤炉。而父亲,似乎不属于这里的一分子,高瘦的个子、细长的手指、架在鼻梁上的金属眼镜框以及他手中的世界名著,多少和这里的氛围格格不入。他的神态多少有些呆气,言行也让人怀疑他还活在中世纪。
学画,大约可以看成哄骗小女生的伎俩之一。这是我稍大一些时才明白的。而在最初,在父亲把我送进李老师画室的那几年,固执己见的他监护着我的一举一动。从画室回来,他把我幽闭在家,让我一遍又一遍,忠实地描摹自然界景物,就连屋内的桌椅板凳和茶杯,也被计算其列。你到底学会些什么?有时候,他会这样问我。学画初期,我进展缓慢,看不出任何好兆头。
老师没教过我。我这样回答,毫不犹豫,理直气壮。
混账!他是最好的老师,你一定是在偷懒找借口对不对?父亲的耳根都红了。那时的他,从不给我辩驳的机会。
李老师是否是位好老师,我想事实永远强于雄辩。他和我的父母是同一年进厂的,没结婚也没分到职工宿舍,化工厂电影院二楼的录像厅旁边,是他的画室,也是他的起居间。他不介意锅碗瓢盆装点的屋子,也不在意在哪里生活。沉溺于自我世界的他,不爱和人打交道,有位阿姨倒是经常来看他。
李老师,今天画什么啊?茶杯我已经画过了。当他再次把茶杯和苹果搁上静物台时,我提出了抗议。这是很巧妙的,无伤大雅的抵制。他点点头,没解释太多就拿走茶杯并换上砂锅。苹果还原封不动地躺在那儿。他坐在我面前示范了几分钟,然后回到自己的画架前,把一盆盆颜料泼到画布上,自己也因此弄脏了。这实在让人提不起兴致。半小时以后,我才知道他在等人。
李老师女友的到来,远比画室正在发生的一切有趣得多。首先,我会被她身上的香水味吸引住,其次,我会看到《大众电影》上明星烫卷的头发。她的身体很轻,从身旁掠过时带着丝丝甜风。倘若李老师没空搭理她,她便冲我挤挤眼,说,和木头人呆在一起有什么意思呀?走,我们下楼去玩!眼看拽不动我的胳膊,她便示意李老师下达命令。在他的允诺下,我和她下楼去了电影院。
林阿姨最爱看的电影是《庐山之恋》,还爱拿从杭州捎来的手帕揩眼泪。不过在我看来,佐罗在坏蛋门前留下的“Z”字比男女们相爱要酷得多,而朝鲜战场上的飞机大炮、“狼牙山五壮士”们的慷慨就义也给我留下这样的印象:解放全人类远比学画有意义,倘若有机会的话,我宁愿吃草根树皮也要远赴沙场。
林阿姨不明白这些有什么好,我同样无法知晓男女之间有着一辈子也弄不清的秘密。我喜欢她腋下的体香、看不到汗毛孔的皮肤和浅浅的酒窝。我想,李老师真够幸运的,他怎么蠢到宁愿要画画也不愿陪她玩的地步?
小鬼,你在想什么呢?林阿姨在我鼻子上拧了一下,说我满脑子坏水。我假装听不懂这些话,偎依在她怀中。
林阿姨领我看电影的事,不久之后就被父亲知道了。审讯完毕,他没收了我的玻璃弹子、拿橡皮筋扎好的洋画和一抽屉的小人书。随后,他在我面前提到《约翰·克利斯朵夫》、《三巨人传》、《红与黑》、《巴黎圣母院》,等等。毋庸置疑,他要拔苗助长地将一颗幼芽扶正,然而,他怎么能指望一个不到十岁的孩子能被修辞学迷住?词汇,很快就从另一只耳朵里出来了。为了给玻璃弹子和小人书复仇,我焚烧了一双从衣柜里偷出来的袜子。作为惩罚,我跪到搓衣板上,面向筒子楼走廊里经过的每一个人。门是敞开的,因而孩子的委屈和愤怒暴露无余,更多的是耻辱。若干年之后,我会拿犹太妇女们赤裸着身子排队走向焚烧炉的那一幕相比较:那一刻,我恨不得马上死掉。
二十八岁那年,我曾把关于父亲、李老师和林秀珍的故事讲给妻子听。真是那样,还是另有特别之处?我的话不足以吸引文婕,同为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出生的她有过相似的经验,幼年曾学过舞蹈的她左腿肚上留有一块至今也抹不去的伤疤。我对她说,其实也没有别的,化工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宣布破产,国有企业变成了民营企业,两千三百多名职工下岗,我的父母也在其列。
李老师怎么样?林秀珍呢?他们一定结婚了吧。文婕期待地望着我。诚然,每位观众都希望故事朝好的方向发展:正义战胜邪恶,爱情战胜死亡,真理永恒不朽。然而,事情总会逆风而行。在我升入初中以后,世界变得疯狂而混乱:工人们因下岗而拦马路,厂门口隔三岔五地发生流血事件,你分不出谁是英雄谁是暴徒。而更能抵达我内心深处的则是另一件事:李老师和林秀珍分道扬镳,林老师去了深圳之后,她就再没浮现于我的视野。
让我们收拢线头,你会看到林阿姨还有厂长女儿这一身份。按她的说法,李老师只要答应她不参与工会抗议和示威计划,她便能委托自己的父亲帮他安排新工作,就算不安排工作,现有的资产也足够他俩共度余生。一句话,林秀珍向李老师表达了她的爱。
在谈条件,算是交换?李老师笑了。他撂下画笔,回头对她说,厂是怎么垮的,你我都清楚,傻瓜和笨蛋的唯一区别就是,傻瓜明知不可以却偏要尝试,笨蛋却是永久性地把自己丢掉……我是傻瓜,但不是笨蛋!说完这话,他拉上画室窗帘,说想自己清净一会儿。林阿姨无奈地退了出去。
翌日上午,李老师出现在职工代表大会终极谈判厅里。他站起来发言,厂长因利润、支出、抚恤金、工龄买断费而不住地擦拭脸上的汗水,却始终没碰桌上的茶杯。谈判以一大拨工人涌进来,把厂长和书记堵进厕所而告终。再后来,就不必细说了。
关于李老师是否爱林阿姨,我曾征求过父亲的意见。父亲没有正面回答,而是望着我说,因为药苦你就可以不吃,因为学画难你就可以不画了?他的牙缝中夹有菜叶,似乎讪笑我不明白其中端倪。他的目光凑得更近些:李老师要去深圳了,他推荐了孙老师。这周末,我们就去见她。
孙老师和父亲年纪相仿,她的丈夫是某小学的校长,她没去工作,在家开设了青少儿美术班,主攻素描和水粉,为中考和高考做准备。孙老师的家比筒子楼的职工宿舍要大得多,梨黄色的木地板,干净得不忍心触碰的茶几上方墙壁上,挂了几幅她的水粉静物习作。
买这些东西干啥呀?孙老师让丈夫把礼物收好,然后招呼父亲和我坐下,摆上果盘,倒茶给我们喝。在她面前,父亲显得拘束,他时而翘起二郎腿,时而又把腿放下来。
您也是老师?孙老师对穿着白衬衣和蓝西裤的父亲说。
我喜欢读书。父亲不自然地给自己点上烟,说,我在化工厂的车间上班,工厂垮了,还好,又被返聘回去了。意识到孙老师不喜欢烟味,他赶紧灭掉。
人家以前都羡慕铁饭碗的。孙老师垂下眼睑,把手中的橘子掰成两半,递给我一半。她在纸巾上揩了揩手,抬头对父亲说,以前,来我这里学画的孩子们也不收钱的,不过老是送东西也不好意思。说到这儿,父亲使眼色让我去画室熟悉一下将来的朋友。二十分钟以后,父亲叫我出来,说从下周开始,他会送我过来学画。
每周两次,父亲领我去孙老师家学画。周三和周五下午放学,他骑自行车接我,一道回家,用快镜头吃过晚餐,再乘公交车去武昌学画。从汉口到武昌,要转两趟车,还要走二十分钟左右的路。车上通常很挤,很难找到座位。为了让我舒适一些,他连推带搡地帮我来到窗户旁边,并为此和人争辩、谩骂。没人怕他。人们会对他说,要不是看在小鬼的份上,一定饶不了你!父亲呢,当然也没动武的可能。从体型上看,对方一只胳膊就能降伏他。他余怒未消地盯着对方,似乎眼神也有杀伤力。从车上下来,他依旧愤慨未消地告诉我对方如何无理,不愉快的时光只有当我进入画室才全然瓦解。确定平安无事,父亲离开孙老师的家,下楼闲逛,消磨时间。一个半小时以后,他回来接我,去车站乘车,在途中盘问我今天都学了些什么。我说每次都能学到新东西,孙老师特别强调创造力。
和李老师相比,孙老师自有一套教育学生的方式,跟她学画的不少学生都拿过省、市的大奖,有几位还去了中央美院进修。不得不承认,数不清的奖状和勋章把我从低迷情绪中拯救出来——她已准备让我参加全国少儿书画赛。做为三位候选人之一的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父亲。
昊昊,不要错过机会,给你老子争口气!父亲搂住我的肩膀,大声宣布即将一鸣惊人的我是好样的。母亲说整幢楼的人都听到了,他却认为至高无上的荣誉就是应该让所有人知道。然而,当后来他听说参加比赛要塞红包时,面部肌肉便松垮下来。从孙老师家中出来的他小声嘀咕着,怎么处处要钱?买笔要钱,买纸要钱,买颜料要钱,参加这样的比赛还要给评委好处费?他摇着头,过了好久才发现他已把我领向一条和车站方向截然相反的路。父亲转身拽着我往回走:给钱就给钱,反正最后还是要靠真本事说话!
你爸爸还真可爱!当我说到这里,文婕忍不住笑起来:没想到他也有转弯的时候,我以为他不会刹车呢。
如果真是那样,你早就是画家夫人了,才没必要和我整天颠来跑去的。我告诉她说,那时的父亲并不理解世界的疯狂,生活不可能因他的意志一路绿灯,父亲当时的处境,比他刚进化工厂的时候要糟糕得多。
关于父亲刚进化工厂的事,或许母亲更有发言权,还在娘胎里的我不可能从肚脐眼里探出头来窥探一切。母亲告诉我,父亲曾有过更好的前景,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她怀上了我,父亲放弃了升入大学的机会。
进城,恋爱,结婚,生孩子,似乎一夜之间就发生了。每天值夜班回来,父亲一边复习一边照顾哭闹不停的我。母亲体虚,而我又是早产儿,他没听母亲的建议去找书记帮忙,尽管书记说他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同志。
让我去求他?不要侮辱自己的人格!父亲数落着母亲。此后,每逢撞见厂领导,他便绕道而行。他皱着眉告诉自己,就算打声招呼,也有背叛阶级群众的嫌疑。他比党员更在意自己的言行。
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工作、换尿布,喋喋不休地争吵、和解之中,父亲的高考热情逐渐磨成了白色。父亲被返聘回新厂上班之后,母亲对他说得最多的话便是:干的活比谁都多,得罪的人却不比任何人少……你怎么就不能克制一些?四十多岁的人了,还和青工较真……你不给他们台阶下,谁给你面子啊?!
你不懂,做人要有骨气,要对自己也要对别人负责!父亲没和母亲多谈就把注意力放回我身上。每月学画的钱已经不少,如今还要给评委塞红包,最重要的还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原则上的妥协和背叛。在把红包交给孙老师的那天,父亲用力拧着我的耳朵说,要是你第一轮就被淘汰了,仔细你的皮!
对于从未对艺术持有过高奢望的我而言,参加比赛并没太多压力。和关云长“温酒斩华雄”一样,我很快便以全省第五的成绩进入复赛,预备参加秋季全国决赛。把作品送去北京的前一阵子,孙老师说红包已经不能解决接下来的问题。她让我悄悄跟她去书房取一件东西,关于决赛的题目和送去参赛的作品,她已经替我准备好了:那是一幅关于地球和宇宙的想象之作,地球不过是龙嘴里的一颗明珠,银河系的星星,则是巨龙身上闪光的鳞片。孙老师胸有成竹地告诉我,只要我反复临摹,将之牢记在心,便会如黑马一样卓尔不群。
这不是抄袭作弊吗?!父亲拒绝了孙老师的好意,他和孙老师辩论、争执,嘲讽她真正关心的并非孩子们,而是可以拿之炫耀并获取更多利益的资本。您怎么能这样?!父亲说。孙老师一直没开腔,她当小学校长的丈夫则不停地拿烟在一旁劝父亲消气。父亲没去接过他的烟,他鼓着眼睛,走到我的画架前取下画板,随后拉着我的手离开了孙老师的家。路上,他没对我说任何话,但我已经明白,事情没有挽回的余地了。
母亲得知这件事之后,把父亲模范标兵的红本本和奖状全都翻出来,摊放在床上。她对父亲说,佩个大红花,发几张奖状糊墙,管用吗?你要面子没人管,昊昊的前程被耽误了,没谁同情我们家……活了一大把年纪,现实点儿好不好?再这样迂腐下去,我都懒得理你!母亲的嘴都气歪了,她一屁股坐在床上,止不住地喘气。父亲没像以往一样动怒,而是赔笑着安慰了她好半天。母亲头也不抬地对他说,去把米淘了,饭做了,今天,我什么事也不会干!
母亲谅解父亲并不意味着生活已经朝好的方向发展,父亲还在为美术老师的事犯愁。在没找到新老师之前,他扮演起教导我的角色:我在窗前画画时,他便在一旁看书,试图用高尚的情操感染我,用精神高于物质的思想推动罗盘旋转。当他一遍又一遍地描摹灵魂、真理、自由和博爱,当他认定盲人荷马比正常人更能洞悉世界,当他反复用米开朗基罗的驼背、梵高拿生命去捍卫艺术举例子时,伟人的灵魂却如烟雾般消散:我所看到的只是八个样板戏。当然,这也是我们和睦相处的一段时光。中考前夕,父亲接到李老师从深圳打来的长途。他问父亲我是否还在学画,他让父亲送我去美专念书。
美专的寄宿生活让我见到了更多的老师: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在此也就不一一列举。每周只有两天我会在家见到父母,把学校的生活讲给他们听。我告诉父亲说,文化课和专业课的时间各占其半,几何石膏模型的课程已经结束,下周我们将素描罗马青年头像,随后是“海盗”石膏像,高三那年,便可以绘制复杂的“大卫王”了。
父亲对我的话和习作极为满意。他既不知道我经常逃课,也不知道我每天下午放学会借自行车载女友出去玩。有什么比绘画更能吸引女孩子的?
来,我给你画张像吧。哈哈,不会叫你脱衣服,身体坐端正就行!类似的伎俩屡试屡成,碰到钉子也不用怕,那会被当成艺术家的个性:我和其他男生的长发、士兵靴、牛仔裤乃至刻意蓄起的长指甲,总会俘虏那么一小撮女生。东方不亮西方亮,绘画是和女生搭讪最有说服力的幌子。
一盏盏红灯很快就把父亲请到班主任的办公室去。把时间推到十多年前,你会看到一位高高瘦瘦、气色不怎么好的中年男子满脸愠怒地带着垂头丧气的少年从大门出来,夺过他的书包,搜空他口袋里的零钱,把他推到马路中央并对他说,我花钱就是让你干这个的吗?啊?!你这不争气的杂种,永远不要回来!那一刻,你大约会联想到儿时遭受体罚的我,此时的羞辱已经增添了千万倍:人们都在看我,老师,同窗,好友,还有坐在另一辆自行车上,不再是我女友的她。
爸爸,我再也不敢了!也许,我可以这样告饶,乞求原谅的同时,痛改前非。然而,你怎能指望少年放下自尊,活在不可避免的耻笑和谎言中?我选择背叛、逃离、复仇。失踪两周之后,母亲凭借自己的本能,把我领回了家。
表面看上去,重新回到画架前的我变成了三好学生,不再旷课,文化和专业成绩直线上升也表明父亲的行为是有积极意义的。而在家的种种迹象,也验证了父亲和我之间的和解,没人知道基督山伯爵已经在监狱里绘制出用来逃脱的地图,也没谁知道特洛伊的战争会因木马而改写。下面,我将进一步说明:
高考那年,学校分发了志愿表。我把表格拿回家,当着父亲的面拧开墨水瓶,恭敬地把自己的志愿填上去。每一志愿都表明我的理想是升入美院和其他艺术院校,一、二、三栏中塞满了我的理想和父亲的理想。当天晚上,我没能睡着觉。第二天清晨,我第一个赶回学校开门,迅速从抽屉里取出另一份表格,填好,随后带着昨晚填好的表格去了趟厕所。揉皱的纸团被水冲走的那一刻,我感到快意。
父亲没觉察到我的秘密。高考前的营养品,与日俱增的绘画书籍,不断叠加着巴别塔。在口音被上帝变乱以前,父亲谨小慎微地避免和我发生冲突,每天和我交流,让我学着放松,不要有太大精神压力,就算第一次失败还有第二次,海明威都说“人可以被打倒但不能被打败”……在拳手即将和人交战的最后时刻,做为教练的父亲终于看到从木马肚中出来,汹涌而来的敌军。站在书柜前的他一下子傻了:昊昊,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我闭上眼睛,等待着有始以来最大的羞辱,等待着被摧毁然后重生。然而,那一拳没能落在我的脸上,父亲的拳头把书柜的玻璃砸烂了。他的手在滴血,我没再看他。
去另一座城市念财经专业,是我和父亲都没料到的。临行的那天,只有母亲陪我去火车站,父亲不肯过来,对我将来的出路也是不屑一顾。卧铺票已经卖完了,因而当我坐在硬座车厢,百无聊赖地从旅行包里掏出火腿肠和方便面时,两包黄鹤楼的烟吸引了我的目光。我偷偷吸烟的事父亲觉察到了,我篡改志愿的事他也并非全然不晓:烟盒下压着一封父亲写给我的信。信中说,班主任和专业老师曾就我要报考金融专业的事征询过他的意见。
也许,我们之间永远也不会理解,但至少我想要学会尊重。这是父亲在信末捎给我的话。当然,他不会忘记狠狠地抽我一鞭:如果将来一事无成,当心我把你的屁股踢烂!
既然父亲知道我已篡改了志愿,为何那一刻还要把拳头砸向玻璃柜?是他大脑突然短路,还是理想主义者总把脚步放在虚空的云上,以为自己迟早会飞起来?金融数字不能回答我的问题,大学毕业后的觥筹交错不能回答我的问题,文婕不能回答我的问题,母亲也不能回答我的问题。实际上,在外漂泊的日子里,我极少能想到父亲,和他比起来,我更关心薪酬、谈判技巧、房价涨跌等现实问题。
生意没有预期中那样顺利,第一年赚钱,第二年亏得更多,反反复复,周而复始。朋友们说我不善于经商,因为我会把赚来的钱很快散掉,或者投入到不可预期的事物之中。他们说我的个性和赌徒还有所区别:赌徒们会设想有朝一日连本带利地赚回来,而我,对金钱的渴望并没嘴里说得那样有兴趣。
你很矛盾啊。和文婕结婚之后,她经常说我言行不一,对事物难以保持持久的兴趣。而在父亲出席我们婚礼的当天,她却看到另一个和我迥然不同的形象。
是基因变异还是别的什么?文婕也不能清晰表达。我只知道她和父亲谈过一次,就被他吸引住了。他的语调、声音对她而言有某种说不出来的魅力,这让我妒忌得发疯。
你已经被他影响了,不是吗?文婕说。
才没有,我和他是不一样的人。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我既不考虑崇高也不那么渴求精神上的慰藉。我努力工作,却没有成为企业家或大老板的宏愿。我在婚后第四年时来运转,在异地买下第一套房。那年冬天,母亲给我挂来电话,叫我回家一趟。那一年,我三十三岁。我三十三岁这年,父亲患上了白内障。
回家的那天,父亲并没有迎接我,母亲却在车站等了我好半天。我和母亲回到筒子楼,进屋。父亲穿着毛茸茸的拖鞋,背向着我吸烟。我喊了一声。他说,进来吧。随即,他把烟递给我抽,长城牌的。他执意要帮我点燃,火苗在我眼前晃了半天也燎不到烟上。他的眼睛蒙了一层白翳,他说只能看到我的轮廓,后天他就要动手术了。
爸爸,你不会真的害怕吧。我想让谈话变得轻松一些。
害怕?你老子从来就没发过抖!父亲粗声粗气地哼了一声,让我去取普希金的书念给他听。他执意让我念出声来,才不管这样做是否矫情。我开始朗诵。他比孩子更任性地挑毛病,说我的普通话就像给蛤蟆伴舞一样。读到一半,他摆手说,不读了,并叹息说,时代早已变了。这让人难过。我说,爸,今天不管你要求什么,我都听你的。
好,是你说的。父亲把母亲打发走,又递给我一支烟,随后,他让我把靠椅放在屋子中央,让我帮他画像。
现在?我怀疑他在故意刁难我,我都有十多年没拿过画笔了。
笔和纸都在衣柜上面。父亲说。看来,他早就预谋好了。
我从衣柜上面取下画夹,解开活结。里面规矩地摆放着不同型号的铅笔,橡皮擦则放在夹层。画夹一边的隔层里是素描纸,一共六张,纸页因潮气泛黄却依然平整如初。在开始画像以前,父亲提到李老师当画廊经理人的事以及孙老师因肝癌过世的事。对他而言,熟悉的人越来越少,世界越来越陌生。人啊,真是从出生以后就一步步迈向终点。他叹了口气,扶正眼镜框,说,开始吧。
我拿图钉固定好画纸,观察他,却迟迟没能动笔。我没有把握能完成这幅画,我知道自己早已不擅长这个。好不容易开始了,我又用橡皮擦揩掉刚打起的轮廓。我感到虚弱无力。
有那么难?父亲把身子调正了一些,说,你不可能再找到和我一样棒的模特。
我笑起来,拿铅笔勾出大致轮廓,在五官周围标上记号,连接点线,绘制他肥厚的眼袋、鹰勾的鼻梁和比常人略短的下颌。与此同时,父亲把眼镜取了下来,让我画没戴眼镜的他。
这样?我停下笔问他。
画你看到和想到的吧,放松点儿。父亲这么对我说,并尽量把自己逐渐下垂的脑袋抬高。屋内没有空调,于是我把取暖器挪到他脚边。此后,我们再没说话。四十分钟过去了,我把画好的素描肖像送到他手边。他把眼镜压低些,退远了看,不满意到翕动嘴唇。几秒之后,他把画交还到我手中,说,真差劲儿,把它收回去吧。
爸,你一直想要我成为另一种人,你知道我不是。我不满地对他说。
你很聪明,但至少有一点,我比你强很多,你从来都没……他摇摇头,恢复居高临下的姿态,吩咐母亲铺床。和过去一样,末尾总是不愉快。不过今天晚上,他想和我睡在一张床上看电视。
晚上,电视只看到一半,父亲就睡熟了。待我关掉电视,他却翻了个身,似乎太静会影响他的睡眠。我给他拉上电热毯,嗅到老年人才有的潮霉味。他的假牙套就放在床头柜上的玻璃杯里,被水浸泡着。没有了牙套的他嘴巴朝内凹陷,皴皱的皮肤把他的嘴唇拽进口腔,枕头上还有几缕发丝。看了一会儿,我钻进被褥,尽量让自己的身体靠近床沿。我想这样他会舒适些,至少我心里认为这样。随后,我闭上眼睛,设想时间并未向前推进。正如他说的那样,我们之间从未相互理解,男性荷尔蒙哪怕在温馨的时刻,也会因龃龉而发生战争。我感到难过,我终究是他的儿子。父亲如今老了,我想的是这个。
第二天醒来时,我发现父亲不在床上,母亲也不在家,大约下楼买早点去了。我回过身,看见父亲正站在靠窗的墙壁旁边,脚下垫着一把靠椅。他摸索着墙壁,取下镜框,把他和母亲在庐山的合影取了出来。不多久,镜框又挂回到墙壁上。
父亲依然站在椅子上没下来。他久久注视着墙壁上的画像,他的,也是我的画像。我听见父亲孩子般地哭了起来。在父亲从椅子上下来以前,我没惊动他。
责编:柴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