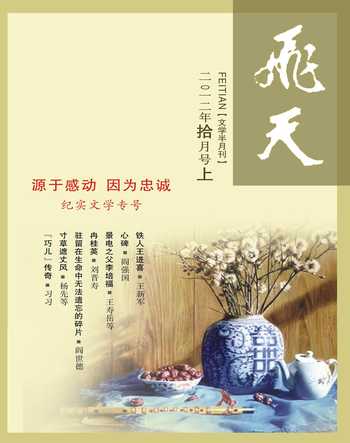心碑
六十年代打洞七十年代打洞八十年代继续打洞
而立之年挖土不惑之年挖土天命之年继续挖土
横批:两把黄土
——甘肃书法家赵正撰写的一副对联
题头的对联是送给韩正卿的。
关于韩正卿,那该是一本书。
1990年秋,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去了地处甘肃河西走廊干旱山区的民乐县农村,希望访问到几户60年代初,来到大西北又定居到乡村的上海等地支边青年。我们想跟村民打听,因为要说的都是一些过去的事,可没找到一户留到乡村的上海支边青年,却从乡亲们口中不时听到一个人的名字,很多乡亲都在打听这个人,这个人就叫韩正卿。
那时韩正卿离开民乐已十年了,我们也不大清楚他去了哪里。乡村信息闭塞,乡亲们也无从知道在民乐干了八年的韩书记现在在哪里,当了什么官。乡亲们扳着手指计算韩书记的年龄,说他们乡里人没法再看到韩书记了,他们的儿子、孙子也可能没机会见到韩书记;韩书记骨头硬,命也长着哩,但总有走的一天,他们没法表达对韩书记的感激之情,已经给儿孙们交代,有今天的好日子,有以后几辈人的好日子,都是韩书记的功德,他要走了,要给他立碑,要给他修衣冠冢,要修庙给他上香,要后代辈辈记着韩书记,吃水不忘挖井人啊。
这让我们突然想起中央新闻制片厂的纪录片《红日照东江》,从那里我们开始寻觅一个把丰碑立在人民心中的共产党人的足迹。
东江八年
“这辈子,我与八字有缘啊!”
1996年秋的一个下午,我和作家马步升去韩正卿家采访。在省委分给他居住的一楼两户的小楼前,看着花红树绿、优雅干净的环境,我们心里有点羡慕。在客厅,向阳的一面摆满花木。落坐仿真皮的沙发上,我们不由惊讶,那沙发已经起毛了,扶手的一端已经有了破口,真叫简陋破旧。整个客厅,除了一台较大的电视机,看不到一件现代化的家具,也看不到入住时装修的痕迹。听了我们为采访定西几十年的发展变化而来,韩正卿说:“八年,我在定西八年。这辈子,我与八字有缘啊。”
韩正卿,1934年腊月初七出生,甘肃宕昌韩院乡人。父亲是位饱学秀才,在地方上颇有德望。在他五岁上,父亲就给他做人生的启蒙课,教他读《四书》、《幼学琼林》、诸子百家、唐诗古文;教他临习王右军、柳公权、褚颜诸大家法帖;教他怎样做人……韩正卿自幼喜欢写字绘画。到青少年时,已是家乡有名气的小画家,逢年过节,街坊邻里画窗眼、贴花墙裙,都请他画。1949年5月他小学毕业,9月参加工作。当时,岷陇一带解放,军队招收知识青年。韩正卿报名应招,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防岷县粮恭区的62军骑兵营搞支前和区政权建设。在好梯乡当了三个月副乡长,当时他年仅14周岁。1952年他调干校学习,结业后留地委,1954年任武都地委秘书。1956年6月1日调省委组织部,在党群政法干部处工作。1965年下放锻炼,在武都东江任公社书记,共八年。1972年调民乐任县委书记,差九天整八年。之后调定西地区任专员,后任地委书记,一干又是八年七个月零五天。1987年3月,他被任命为中共甘肃省委常委,两年后也是阳春三月的日子,他离开定西到“引大”工程任指挥,兼任两西(定西、河西)农业建设指挥部指挥、甘肃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又一个八年开始了。
“这人,往死里苦哩”
武都东江,山大且陡,耕地很缺,加上海拔低,雨水多,洪涝灾害严重。那里的土地大都挂在陡坡上,叫作“挂田”;山沟口洪水制造的平掌子上的则叫“撞田”,撞上洪水侥幸能收点就收点,不能收就只能血本无归。
韩正卿来到东江后,决心和“撞命运”的生活来一番较量。在东江治山治水治地自然是很苦的事情,但韩正卿早就明白“好日子是苦出来的”道理,那时候他年轻力壮,虽然是公社书记,却同社员一起平田整地,修渠垒堰,七斤重的镢头他一口气能抡200下,从白龙江边往半山上背沙子一整天都不知歇气。上头给他派的干部却都怕跟着他吃不起这份苦,不敢来。
社员们服他,说:“这人,往死里苦哩。”
俗话说,不苦不来。好日子是苦出来的。在东江治山治水治地,那可是很苦的事情,韩正卿扛起这个“苦”字,不声不响地行动。他带领社员修渠筑坝,凿山开洞,夯起2000多米河堤,修了两条盘山渠道,搞出3000多亩水浇地,结束了东江没有旱涝保收地的历史。
“怕啥,弄不好去当社员”
有个当年省委组织部共过事的老莫,到武都出差,顺便到东江看他。找到公社,公社干部指指山坡上的破庙:“到他家找去。”
老莫来到那破庙,见韩正卿身穿麻布坎肩,脚穿麻鞋,坐在庙门槛上拴背篼绳儿。往庙里一瞧,一家大小全在。他惊奇地说:“你怎么把老婆娃娃安顿在这里?”
韩正卿笑着说:“讲究啥呢?有吃的就行了。”
韩正卿在破庙里操心老莫吃了喝了,领上他上山看工程。二人站在山顶,和省城里下来的老莫比,韩正卿就像个大山里的农民。眼前,五条沟,五股山洪,全被拦入盘山渠,山下是平展展的土地,绿油油的庄稼,五水归一的壮观令客人赞叹不已。
“这工程,没说的。可是换成我,我不敢搞。”客人说。
“为啥?”老韩问。
“吃的苦太大,担的风险太大。”客人说。
当时正闹文化大革命,上头的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你不抓革命只搞生产建设,自然是很担风险的。
韩正卿抽着纸烟,沉默地望着这半壁收拾过的山河,徐徐地说:“怕啥?弄不好去当社员,我还是个好劳力。”
那年头,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政治干扰成了人们有苦难言的事,可韩正卿尽量排除干扰,全力以赴抓生产。他看到东江人多地少,而白龙江北岸的石头沙滩未开发,种庄稼不成,但种经济林行。东江气候温暖,日照充足,适于栽桔树,他就狠抓桔园建设。他亲自选地,亲自背土背石头;到外地引进优良品种蜜桔。经过几年如一日的苦干实干,东江变了,这里不再是洪水成灾,荒滩野草。地里产量高了,桔园一片接一片,金色的蜜桔缀满枝头,东江成了金桔飘香的美丽山村。由于他的带动,武都其他公社都搞桔园建设。
“韩 院”
1992年冬,身为省委常委的韩正卿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宕昌县韩院乡。乡政府大院被乡亲们围得水泄不通,地委和县上的领导忙着维持秩序。人群中钻出一对农村夫妻,径直在韩正卿面前站定。
“叫爷呀,快叫爷!”农妇从身后拽出一个拖鼻涕的尕娃,这尕娃怯怯地往前挪了两步,韩正卿连忙上前抱了起来。这农妇便是他的长女。大女儿出生时,韩正卿正在东江战天斗地,无暇顾及,送回老家交给父母照料,自此便在老家成长、成家,做了地地道道的农民。年龄三十几看上去倒有四十多,大冷天只穿了一条长不及踝的单裤。木讷憨厚的女婿因为是拜见泰山大人,特意借了一顶新帽子扣在头上。见此情景,陪同者中不少人流下了眼泪。多年来,每当大女儿来信诉说家里断粮了的时候,韩正卿便吩咐老伴寄些粮票和钱去。韩正卿的姐妹以及外甥们都是农民,现在多生活在韩院。大哥年轻时是村里一顶仨的壮汉。1960年春上进山修水库,饿死的时候怀里揣着半块馍,想是要回家留给老娘吃的。
民乐八年
“吃的是韩爷挣下的饭”
民乐,县城紧靠祁连山脚。站在县政府大院里,便可尽览那白雪和冰川覆盖的山峰,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把峻峭的山体装扮得十分壮美。民乐的天空蓝得发亮透明,民乐的蓝天上的云朵白絮一般,这里的大自然干净得一尘不染。
民乐,是个靠雪水灌溉的地方,它东接山丹,那是古战场,焉支山下的广阔牧场为远古的一次次战争喂肥了多少战马。民乐的西边是张掖,当年隋炀帝西巡曾到那里举办了震动世界的27国交易会。丝绸之路的辉煌至今不衰。
然而民乐却很穷,很贫困。这里地高,不便灌溉。这里天寒,庄稼生长受到霜冻的危害。这里戈壁沙漠不断侵蚀着良田。
祁连有雪,而民乐的土地却干涸荒芜着。
我们去民乐的那一年,正值河西大旱。在这样的旱年代,想民乐那样的旱山区,庄稼几乎会绝收。但眼下乡亲们心里很踏实,这就更清楚地看到了当年韩书记带领全县人民所做的惠及子孙的水利工程所带来的好处。
“当年我们没少怨韩书记啊!”乡亲们这么说。
“韩正卿只抓粮棉油,不分敌我友。”当年社教工作也没少教育他,“只抓长远,不看当前。”“平调劳动力,劳民伤财,把百姓弄得太苦没饭吃。”
在祁连山下的古战场上,韩正卿摆出了新的战场,他指挥大兵团作战。那时,几乎没有什么机械,全靠人海战术,万人会战,指挥部就设在地上挖下去的“地窝子”里。
“运动”不断,只要没被撤,他依然履行指挥官的权利,他命令:每个劳力每天要求拉0.7个压实方,所有干部上前线。“谁要阻挡我修水库,天王老子都不行!要干就是铁蛋,不叫干就滚蛋,干死了就完蛋。”
他一身农民装束,像个生产队长。民乐农民都说他:“干起来烧着哩,不要命。”
他明白如何从根本上改变民乐的落后面貌,就这样,修成了双树寺和瓦房城两个库容达4800万立方米的中型水库,保灌41万亩,有效灌溉46万亩,半山坡搞了20多万亩的水平梯田,引种了优质苹果树。
数年后,人们回过头,无不惊叹当年的壮举:“回头看路子走对了。当时没有韩书记逼我们艰苦奋斗,哪有今天?”
十年后,二十年后,你到民乐去,问他们吃粮怎么样,老百姓说:“吃的好着哩,吃的是韩爷挣下的饭。”
韩书记已经叫成韩爷了,虽然乡亲们很少再见到他。
“背个粪筐羞了你的脸?”
提到当年韩正卿的工作方式,乡亲们还说到这样一件事:韩正卿号召全县积肥,也让干部下乡背着粪筐去拾粪,干部们觉得伤脸,但韩正卿自己早背着粪筐下乡了。他从这村走到那村,路上拾的粪倒在下一个村,又背上空粪筐到下一个村去。我们听了几个韩正卿背粪筐走乡串村的故事,如今已带上了浓厚的传奇色彩。
当然,韩正卿并不要求民乐的干部都这样。干部看见韩书记背粪筐挂不住脸时,韩正卿总说:“我背个粪筐羞了你的脸?”
当年,民乐的县委书记背粪筐下乡,报纸争相报道。中国县太爷如此者也就这一个吧。但韩正卿心定气闲,依然我行我素。只是这样的时候并不多,或者说仅是他与民同甘共苦中自然而然的一件小事。他所说:“甘肃这地方,不是一天两天干的,笨功夫、慢功夫就是硬功夫。”
“不如我们社员的家”
在民乐,县委书记韩正卿家的炕坏了,韩正卿让办公室的同志找人修一下,请来了三个社员。社员们边修边问:“这是谁的家?”办公室的同志开始不想说,后来见他们问得心切,便说:“这是县委书记老韩的家。”三个社员听后愣了神,睁大眼睛把这个家端详了好一阵子,说:“我们原想书记的家该有多豁亮,没想到还不如我们社员的家!”
这话没有说错。韩正卿的家同普通社员的家没有什么区别:两间土房风剥雨蚀,房顶上长满了茅草。进到家里,两盘土炕各占去两间房子的一半。外房炕上铺着一张塑料床单,塑料床单下面是一块毡和一床旧棉毯。靠墙的地方,一面堆着两床被褥,一面放着两个装衣物的油漆箱子。炕的另一头立着一个旧碗柜。里间,掀开那块打着补丁的蓝格子土布门帘,炕前有一张吃饭用的矮方桌,四个一尺高的小方凳,还有一个竖起来可当凳子用的缠电线的木头轱辘。外屋墙上还挂着一只纸盒喇叭,这就是他家的收音机。
八年前,当韩正卿就任民乐县委书记时,组织上派了一辆解放牌汽车去帮他搬家,全部家当装上也没半汽车。两个司机相互伸了伸舌头,悄悄嘀咕他“寒酸”。也有人认为,当了县委书记,过几年会“发”的。八年过去了,韩正卿的家还是那个老样子。
事实上,韩正卿在不同的地方,关于他家的简朴媒体多有报道。在民乐时他说:“一个县委书记要掂得出自己的分量,民乐县18万人的这个“大家”和自己的一个“小家”,哪个重?将来大家都富了,我的家也会阔起来的!”
其实,并非他经济条件不如那些普通社员,他顾的是“大家”,很少想过把自己的“小家”建成“县官”、“领导”的家。而且,他不想从他的家走到农民的家有任何台阶,更不想农民走到他家有任何台阶。
“能把石头晒破哩”
民乐一直旱,太阳便显得格外给力,用韩正卿的话说:“能把石头晒破哩。”除了发展水利事业,大规模兴建水库,韩正卿也在一直探索适宜当地生产发展的产业。
一日,韩正卿来到民乐园艺场,场长武学经端出一盘梨请他吃。他尝出梨的味道好、皮薄、肉细、核小、味道甜,是个好东西。它形状像苹果,其实味是梨。问是什么梨。武学经说是苹果梨,原产地延边,1968年他们园艺场引进培育成功,从平凉弄来的野山梨作母本嫁接。韩正卿到园子里看看,苹果梨只有18亩,有些树被驴啃坏了。他支持武场长把苹果梨发展起来。民乐荒滩这样多,种不了庄稼栽苹果梨。韩正卿对民乐有个水利建设加林网化的计划,经过调查思考,他把苹果梨纳入这个计划。从此,他口袋装着苹果梨,走到哪,宣传到哪。慢慢的,园艺场搞大了,民乐的农民都栽起苹果梨来。1987年,民乐的苹果梨到了北京,参加全国优质农产品展览,被评为全国第一。消息传到苹果梨的老家,吉林延边的专家来到河西走廊考察,他们不解,为啥你们从我们那里引种来,反而比我们的好?
定西八年
“把山沟跑遍”
80年代初,韩正卿来到苦甲天下的定西。他到定西又是八年,先后任地委副书记、行署副专员、地委书记。
他头年到定西,第二年就到时属定西地区的靖远县兴堡子川搞电灌工程。这是一个高扬程电力提灌工程,是改变靖远县北部干旱面貌、发展农业生产、解决群众温饱的翻身工程,总投资1.04亿元人民币,是甘肃省“两西”建设的重点项目。韩正卿以他吃苦耐劳、敢打硬仗的顽强作风和领导才干,精心组织施工,同工程技术人员、灌区群众共同努力,艰苦奋战,于1984年完成总干渠并调试上水,1985年、1987年北、东干渠相继通水。
作为一个地方或部门的领导,尤其是主要领导,自然要抓大事。定西民间有个顺口溜,对解放以来坐镇定西的五位地委书记都有褒贬。这里不提其他,只说给韩正卿的是:“韩正卿坐定西,把山沟跑遍。”他对全地区进行调查研究,各个县跑,各个沟跑,在农民家三进五出,串炕头拉呱梯田,谈治坡,说种草,经过充分的调研,提出了一个治理定西的大决策:十个三。通过三十年努力,办成三十件大事。可谓心存长远!证明他确实对这块干旱之地涉足之深,对这块贫瘠之地有不因艰险而止步的不移之志。
三十件大事,有人也许会把他当一个会做表面文章的领导。因此,这里更想说一说他工作的细节。
“十两柴,烧十斤开水”
定西过去最严重的问题是自然植被的破坏。定西历来缺煤,缺少燃料,过去农村群众每年铲草皮20多亿斤,破坏天然植被300多万亩。老百姓要吃饭!韩正卿明白,在没有其他燃料的情况下,无法做到如今天封山育林种草这一点,也不能严令禁止,他也不忍心让老百姓没有“柴火”。能不能在节约燃料这一点上做文章呢?他来到定西燃料公司,向两位具有丰富改灶经验的老工人请教。他们告诉韩正卿,外地有种“回风灶”比旧炉灶省柴三分之二,花钱不多,技术不难,很适合在定西推广。第二天,他又去找老工人,请他们教自己盘一台“回风灶”。他让工人师傅们在旁指点,自己卷起袖子,和泥、垒灶,盘成一台“回风灶”。点火一试,完全符合“回风灶”规定的“十两柴,十分钟,烧十斤开水”的节柴标准。为了取得良好的效果,他通过”三西”办公室的同志与中国农科院的同志邀请辽宁、四川、陕西、宁夏及省内最优秀的改灶技工,让他们拿着各自最好的节柴及省煤图纸,来定西。
在随后的一次会议上,韩正卿给各县的领导干部送一把瓦刀,把他们带到景泉朱家店村,教大家盘灶技术。他先示范一遍,然后让他们各自动手,自己来回检查,直到每人盘出合格的“节柴灶”。“眼过十遍,不如手过一遍。”后来他组织全地区七个县的县委书记、县长集中到定西县友谊村薛何家社搞现场改灶比赛,他亲自参加,优胜者还发了一台40元的小收音机。不用他再多说了,各县领导干部都知道下一项工作该干什么,该怎么干了。不久,定西乡村家家都用了“节柴灶”。数年后,在中央财政支持的“三西”移民工程中,有部分移民到甘肃河西走廊,定西人到河西最惊叹有那么多的“金贵”柴草,而河西人更惊叹定西人竟然能用一把麦草烧开一壶水。
“1986年4月18日这一天”
韩正卿容不得基层干部对工作马马虎虎,对布置的任务敷衍塞责。我们从定西采访回到兰州,采访韩正卿。他只问我们定西的情况,问我们是否了解最基层的定西老百姓。他很少说他自己,他说,他在定西八年多,应该有个说法,但不是我们说,是让历史说,让老百姓说。末了,他送给我们根据他工作日记整理出的《岁月行吟》这套书。他年少上私塾时,对古体诗词颇有兴味,以后不论工作在哪里,条件有多差,闲暇唯一的爱好是写几句古体诗,以抒当时胸臆。这《岁月行吟》依他的说法是“记事第一,写诗第二”,所以更多的文字是记事。随手翻开其中的《定西卷》,看到几页表格,有些不解,细读之后,便深深体会到他为何在干部群众中有那么高的威望和好的口碑。
我们照搬一小节。
在全乡掀起春季造林高潮的时候,我在一些地方看到了这样一些现象:一个乡的干部从山林中挖来两米高的云杉、油松,整整齐齐地在进入县城的公路边栽了两行,一拔即出,原来都是无根之木。一个乡发动数百人在一座荒山上“打歼灭战”,栽种着全部枯死的油松苗。听说有个村一个早晨就完成了每户栽种200株油松苗的任务,一看,全部“密植”,一妇女将公社百株的两捆苗木,挖了两个坑埋上,也算“完成任务”。还有一个县的林业局长由于不负责任,导致三万元的针叶树苗成为干柴。这怎么得了!对这类事除了进行适当处理,并作为“反面教材”,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教育之外,从技术上解决针叶树苗保栽保活的问题也十分必要。
让别人做到,自己必先做到。如何把好从树苗出圃到定植这一重要关口呢?经请教林业专家,认为“水桶泥浆单株移栽”的方法比较可靠。具体办法是:将二年生的针叶树苗从苗圃挖出之后,立即装入糊状腐质泥浆的水桶之中(树苗三分之一在泥浆中),拉运到定植地单株移栽(不浪费树苗)。经亲自试验种植90多处,只要在一周左右栽种下去,保证基本都成活。
1984年和1986年春季造林时,我在汽车上装着水桶泥浆树苗到90多个单位的院子里进行了试种,在71个乡政府的院子里给乡干部“做了样子”。这里,公布一份我在定西、通渭各乡泥浆栽种树苗的统计表:
水桶泥浆单株移栽试验树木数
1986年4月18日
定西县
……
下面是几十页这样的数据记录。这是他每到一乡一村栽树的记录,也是试验的记录,有人说自己的“地方”种不活树,他亲自栽给你看,看活不活,能活多少,也为自己下一步的检查提供了依据。
“1986年4月18日这一天”,韩正卿在定西栽树,知道定西几个乡情况的人都能看明白,这一天,他跑了多少路,又栽了多少树,而后在深夜再把这些记录下来,以备自己检查指导。在那个年代,哪怕是贫困的定西,来自上面的支持并不多,更没有如今天那么多项目,为了定西摆脱贫穷,书记的形象几乎是在挣扎中摸索、挣扎着前行。
看了这一日子的记录,我久久无语。
看了这几页数据记录,仿佛看到一个为改变定西贫穷面貌奋斗不息、鞠躬尽瘁的共产党干部劳累的身影。
“五子登科”
定西,离大海遥远的定西。定西,苦甲天下的定西。
定西天旱,往往旱极后,晒光了麦田,又涝,年仅300多毫米的降水量,一两次涝便挥霍精光。大量的水土流失使有点养分的土地越来越贫瘠,越来越寸草难生,农作物欠收、绝收。定西通渭县的一份资料上表述,全县水土流失面积2400平方公里,占全县总土地面积的99.6%。所以几代定西人都在改造山河,战天斗地修梯田。
跑遍了定西的韩正卿,上任不久就提出改变定西恶劣环境的真知灼见。他与专家、干部和群众一起研究、制定彻底改变定西贫穷落后面貌的战略对策。本着有水路的走水路、无水路的走旱路、水路旱路都没有就另找出路(移民)的原则,提出了治山治沟的“五子登科”战略,即“头上戴帽子(山上种树),腰里系带子(半山造梯田),脚上穿靴子(山下修沟坝),找到新路子,狠劲抓票子,票子找到不再饿肚子”。
若干年后,我们去定西大坪村采访,时值冬天,眼前一片苍黄,不细看,感觉不到变化。和我们同行的安定区委宣传部的同志却给我们描述了另一番景象:林草盖山梁、梯田绕山腰、塘坝蓄绿水、暖棚种蔬菜、住宅标准化。这该是多么喜人的画面,冬天却看不那么真切。我们绕山梁而走,脚下的确覆盖一层细黄的小草,可以看出在这个秋夏植被保护得很好,没有被破坏的迹象。牛羊呢,牛羊都圈养了。山腰平缓处是裸露着黄土地颜色的梯田,土地打耱得很细,很平整。山沟脚下是打起的土坝,土坝很高,里面没有蓄水,这梯田,这塘坝,完全可以实现“小水不出田,大水不出沟”。换句话说,大坪人的土地,除了风吹一点,再不会离开大坪了。
使定西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水土流失,从根本上得到了遏制。这是定西有今天的发展变化的开始和基础。
引大八年
“骑虎不下,背水一战”
严酷干旱的自然条件,决定了我省农业生产受制于水。
兰州以北60多公里的秦王川盆地,地势平坦,土地肥沃,但由于常年干旱缺水,成为一片涸竭的“死角”。秦王川以西100多公里的大通河,水量充沛,适于灌溉,但却与秦王川相隔千山万壑,成了一条流浪的“弃河”。大自然无情的阻隔使川水相离。“川原浑且重,形势殊悬隔。犹如龙门,神禹凿不得。”为把大通河水引到秦王川,几代人曾为之上下求索不已。
1977年9月,省政府正式将引大入秦工程列入基本建设项目。这是中国引水史上的奇迹。
工程总干渠、干渠和支渠共长868.17公里,是”引滦入津”工程长度的3.7倍,成为我国目前最大的跨双流域调水自流灌溉工程。
工程要穿过长110公里的隧洞群,这在我国水利史上绝无仅有,堪称“地下长河”,比“红旗渠”上的180个隧洞还长79公里。其中长15.73公里的盘道岭隧洞为全国最长的引水隧洞。
工程中,长2.17公里的庄浪河渡槽为全国最长的引水渡槽;水头落差107米的先明峡桥式倒虹吸,在亚洲也属最大的同类工程之一。
工程的艰巨性是世界罕见的。总干渠的80%是穿山凿洞,而这些山洞穿过的地质层之复杂和多变,全国少有。其中一些地段堪称“世界地质博物馆”,要在这里修成引水隧洞实为“世界性难题”。
这的确是一项浩大而艰巨的工程。
最穷的省,干这样一项全国最大的引水工程,行吗?
省委反复研究考虑人选,这个人选找到了,省委决定让韩正卿担任“两次上马,两次下马”“第三次准备上马”的甘肃引大入秦工程总指挥。两次上马又下马,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硬汉子去啃硬骨头了。临危受命,他立下军令状:“骑虎不下,背水一战,完不成任务解甲归田。”1994年9月25日,引大入秦工程全线通水,方圆1000公里地势平坦的千古旱塬秦王川有水了,每个人都明白这对大西北还不怎么富裕的甘肃老百姓意味着什么,老百姓送给韩正卿的大匾上写着:陇上大禹。
“国际凿洞大赛”
如今的“引大入秦工程”方案,是从1956年就开始踏勘设计的。几经周折,20年后,1976年11月以民办公助形式上马。当时,尽管“三年任务两年完”的口号十分鼓舞人心,但仅凭一腔热情毕竟是不够的。土打土闹三年,隧洞挖掘进度尚不足一公里。照这样的速度,光是总干渠上那33座共长75.14公里的隧洞,就得花去220多年时间才能贯通。韩正卿深知这一点,世界性工程,靠甘肃以至国内的技术力量完成,难度可想而知。经国务院批准,甘肃破天荒地采用国际招标形式,组织工程建设。
静寂的深山峡谷,变成了“国际凿洞大赛”的竞技场。正是在这种激烈的现代化竞争中,中国的施工队伍受到严峻的考验和难得的锻炼。
意大利CMC公司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隧洞掘进设备——双护盾全断面掘进机,只需在32开书面大小的键盘上操作,轻而易举地创造了同类隧洞掘进连续六个月月进尺千米以上、最高日进尺65.6米的世界纪录;仅用了一年零一个月,就贯通了11.649公里的30A隧洞。
日本(株)熊谷组在号称“地下地质博物馆”的盘道岭隧洞,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新奥法”施工,风风火火地干了五年,以坚忍不拔的工作作风、科学严谨的管理方法,终于成功地解决了这个所谓“世界性的难题”,凿通了当今世界上最长的引水隧洞。
面对国外先进的技术设施和管理方法,国内一些施工单位急起直追,学习技术,更新设备,改善管理,使自己的观念、体制、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全面向国际先进水平靠拢。
在凿掘隧洞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铁道部第十五、二十工程局,曾被誉为“中国的穿山甲”,但在这次“国际凿洞大赛”中,一开始却有点不适应。他们及时调整指导思想,把参加这项工程建设作为培养骨干、锻炼队伍,以提高适应市场、驾驭市场能力的大好机会。在资金周转发生困难的情况下,铁二十局以较低的价格卖掉一个办事处大院,购置了所需的先进设备,扭转了被动局面。
韩正卿说:引大,要出技术,出人才,出精神。
“引大精神”
从引大开工后,韩正卿一直在琢磨:这么大的工程没有强有力的制度不行,要制定管理大纲,从规章制度上加以约束。经过悉心的研究和考虑,他用三个半天口授了他的想法,经党委和基层讨论,最后修改定稿成十章70条长达一万字的管理大纲。
韩正卿从当公社书记起,他总说的一句话就是:“我图的就是让老百姓吃饱饭,富起来。”所以,当他召开引大工程第一次职工大会时,就提出了“引大精神”——“三动一奉献”,即:动感情、动脑筋、动真的,为工程建设做奉献。
动感情,就是对贫困老百姓动感情。这是引大精神的灵魂和基石。这几句话也最能体现韩正卿的个性和品格。韩正卿说:“陇中农民祖祖辈辈盼水,如盼水妈,盼水爹,盼水爷爷,盼水奶奶。他们苦啊!”每逢至此,他都很动感情。
在引大精神的感召下,引大工程所有干部职工悄悄地克服了自己的一切困难,默默地做出了许多牺牲。他们取消了节假日,年年都在大干100天、大干150天、大干200天中度过。1989年到1993年四年中掘进了60公里,一年等于过去的13年。
“刀斧不入,软硬不吃”
身负重任,也手握重权,在“多国部队”的承包商眼里,他就是“韩老板”,代表政府的“老板”,可能就有“周旋”的余地。
韩正卿的秘书这样说:“引大工程几百公里分布在山沟里,每次下工地,都由我带着方便面、西红柿、黄瓜之类。离开工地,车往路边一停,蹲在地上就吃了,从不吃承包商的饭。”
这也是韩正卿定的规矩,他为引大工程提出又一个口号:“刀斧不入,软硬不吃,一切按合同办事。”他经常讲:“大家要廉洁自律,不要工程搞完了,有人戴上手铐子进监狱。”这么大的工程,每年投入三个多亿,累计就是多少亿人民币!大家眼看着他们的“韩老板”,从不吃承包商的一口饭、抽承包商的一支烟。所以在承包商面前,腰杆子硬硬的,执行起合同来毫不留情面。
一次,国内某承包商在总干渠8号楼的衬砌中弄虚作假,用水泥袋填充。韩正卿火冒三丈,马上召集全线承包商来开现场会,他踩着泥水,冒着呛人的烟雾,不顾塌方的危险,钻进洞中……这家承包商被通报批评,教育了中外施工单位。
为官一任,造福四方。韩正卿,用几十年的足迹实践了这句话。陇上父老熟悉他,感恩他,亲切地称呼他“韩爷”、“韩青天”。我们无需再说什么。他已经在陇原大地上竖起了一道丰碑,那丰碑在老百姓的心中。
阎强国,发表中短篇和长篇小说及报告文学多篇(部),计300多万字。曾获庄重文文学奖、敦煌文艺奖等多个奖项。现为甘肃省作协副主席,《飞天》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