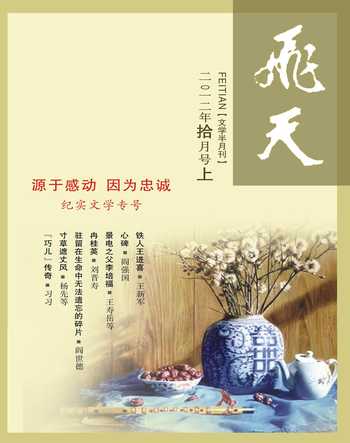驻留在生命中无法遗忘的碎片
每一个无法忘记的碎片,诠释了每一个个体的生命的重量,同时也镌刻了时代挥之不去的烙印。
——题记
王万青,男,汉族,1944年12月出生,1987年7月入党,甘南藏族自治州玛曲县人民医院原外科主任。感动中国2010年度人物,2010年获“第七届中国医师奖”,2010年度十大“陇人骄子”,2011年全国优秀共产党员,2011年甘肃省优秀共产党员。
走进一间普通的标准间,我看到桌子上铺开的报纸,上面均匀地摊开一粒粒金黄的玉米粒。很温暖的阳光透过窗棂,在这片金黄上跳跃。
宴席结束得有点匆忙,正要出门,酒店赠送的瓜果盘才到。王万青犹豫了一下,还是张开了口:“能不能找个塑料袋装起来?要不可惜了……”陪他的工作人员立即张罗,王万青接着要求,“看那菜,羊肉、青菜、肚块,还有那、那个……都给我装了吧,我下午吃,明天的早饭也有了……”
工作人员脸上有着明显的尴尬。服务员脸色微微红了一下,看一眼王万青,再看一眼,似乎知道了这个人的身份,但什么都没说,按照他的要求尽数装好。
王万青满意地笑了。
很大一个塑料袋最终落到我的手上,我帮老人提了,走进他下榻的宾馆。走进一间普通的标准间,我看到桌子上铺开的报纸,上面均匀地摊开一粒粒金黄的玉米粒。很温暖的阳光透过窗棂,在这片金黄上跳跃。
再也直不起腰的凯嫪疾走几步,抢在我的前头,收起铺开的报纸。但王万青似乎把它们铺开得更彻底:“昨天有人给我们给了几个玉米棒子,我们吃不了。扔了,又觉得可惜,就剥下来,晒干了拿回去还可以吃……”
凯嫪不再收拾了,老人笑笑,无可奈何地看了王万青一眼,任凭没有包好的报纸再一次摊开,让那些金黄清楚地在我眼前展露。我抓起一粒,扔进嘴里。我说:“很香呀,很有嚼头。”
两位老人开心地笑了。
就在这一瞬间,两位老人在我的心里骤然高大起来,一种从心底流溢的温馨,一下子把我们融为一体。这种感觉,绝对不是“2010年感动中国年度人物”、不是“陇原十大骄子”等概念所能给我的。我看着王万青,看着这个1.8米还多一点的老人正在真诚地憨笑,看着他1960年代典型的知识分子的“分头”里面的白发,一种欣慰在心底慢慢荡漾开来:这个就是我想知道的王万青,这个才是真实的王万青。
凯嫪洗了头,认真辫着发辫——除了她棱角分明的藏族妇女的脸型,这个发辫也是她民族风格的唯一特征。在我和王万青交谈的过程中,老人把白的、黑的发丝,整齐光滑地辫在了一起,似乎把青春和过去的岁月交织在一起,配了王万青的独白,给我立体而丰满的再现。
尽管我清楚我们的交谈是在这个档次还不错的宾馆里,但是,老人平缓而忧郁的讲述,还是把我带到了我熟悉的玛曲,我熟悉的草原,以及我不熟悉的他们过去的岁月里。
一个高大瘦弱的年轻人,孤独而执著地走向了广袤的草原。这里的一切他都很陌生,这里的一切,注定又将属于他……
远处,阿米欧拉神山巍然耸立,静静守候在黄河第一湾。山顶的經幡飘曳出一种独有的情致。
其实,玛曲在藏语里本来就是黄河的意思,黄河十八湾玛曲首当其冲,所以又叫首曲。在这里黄河得到40%的水源补给,30多万公顷的水草地是母亲河生命得以旺盛的源泉。
但1969年的玛曲,留给24岁的王万青只有两个冷冰冰的形容词:荒凉,紧张。
100多间简陋的平房很不规则地铺开在草原上,和城的概念相去甚远。街道上——如果能称为街道的话——来来往往的多是马匹、牦牛、羊只,尽管王万青早有思想准备,但荒凉的概念还是侵袭了他的全身。驻扎在此的骑兵连不时挥舞着马刀跃马疾驰而过,又给了他一种本能的紧张。
好在逗留在玛曲的时间并不长。几天后的一个早上,王万青坐上县上为他拦截的一辆大卡车,请司机顺路把他捎带到玛曲县的阿万仓乡卫生院。这里,才是他今后工作的地方。
秋天的风很冷,颠簸在卡车上的王万青裹紧了身上厚重的棉袄,但冷风仍然吹进了他炙热的胸怀。湛蓝的天空,翻卷着很有质感的云团,天高地远的寂寥,让大卡车像一只甲壳虫一般蠕动。沿途,星星点点的湖泊河流隐没在盛开的花朵中,草原上这些美丽的花朵在寂寞绽放。不见村落,不见牧人,甚至找不到牛羊。王万青举目四顾,“天苍苍,野茫茫”的诗意给他的全是清冷的感觉,突然,有些担忧的恐惧袭上心头: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方,如果车坏了可怎么办?
这种担心一直陪同他来到了阿万仓乡政府大院。卸下行李之后,并没有一个人出来迎接,王万青四处找人,没有一个人影。有点失望的王万青孤零零地坐在空旷的院子里,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和犹豫。
五味杂陈。在不到一年里发生的有关他命运的事情,似乎在一瞬间里挤满了这个空旷的院子。1968年,24岁的王万青在当时卫生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上海医科大学完成了六年学业,面临人生第一个抉择。
然而,就在他面临何去何存之际,母亲突然被划为地主。从“革命小将”一夜间变为“地主子女”,命运和王万青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这个在上海出生从未离开过上海的“地主子女”,在地图上圈定了两处自认为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区——甘南藏族自治州和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王万青如愿被分配到甘南藏族自治州。
按照那个年代的要求,走向社会的大学毕业生必须接受一年时间的劳动改造。来自全国各地的100多名大学生,被编为连、排、班,在甘南州临潭县总寨修筑水渠。在洮河水的喧响中,王万青开始了每天都单一而机械的生活:抬石头,搬石头,接受自己从未經历过的劳动锻炼。与此同时,当地老乡贫困的生活给了他很深的印象,艰苦之余,王万青庆幸自己的选择,他确实来到了最艰苦的地方。而这种在大上海生活的年轻人所无法想象的荒凉和贫瘠,给了他那个时代必然的自豪和思想,“被需要”的感觉给了他坚守和执著的勇气。
被需要是一种踏实的基础,和主观的追求吻合而相互给力,这种氛围,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在王万青的心中发酵,最终形成“想干一番事业”的理想。所以说,半年之后当得知劳动锻炼将结束要走向工作岗位的消息后,王万青主动写了一封信,再一次要求组织把自己分配到最最艰苦、最最需要的地方去。
这种要求,遭到了一同前来甘南的几个同学的不解,先是好言相劝,后来干脆骂他“神經病”,但王万青坦然一笑,“死也不后悔”。
没人能够理解当时王万青心中真实的想法,但这个想法和当时的环境吻合,血气方刚、目标坚定的背后,掺合了王万青想证明自己的情感,想用自己的追求和选择,给母亲一种安慰,或者是给所有怀疑母亲、怀疑他们出生成份的人一种证明。
王万青如愿以偿。他来到了玛曲,但最终的分配,让他心头泛上一丝淡淡的冰凉。特别是坐在这个空旷的乡政府大院,这种感觉愈发明晰:任何事业都需要一定的基础,玛曲已經够艰苦的了,在这个荒凉的乡上,还有干一番事业的基础吗?
走,还是留?这些想法在王万青的脑海里翻腾。
阿万仓地处玛曲西南,平均海拔在3500米以上,高原灼热的阳光洒在这个年轻人的身上,大院里充溢着陌生、孤独的氛围,牲口粪便的气味固执地游来荡去。最后,王万青终于对自己作了决定:既来之则安之吧。
三个多小时之后,乡政府的文书笑眯眯地向他走来,说乡上的其他干部都下乡了,自己也出去办事了。简单的寒暄之后,王万青被带到了电影队的库房,这就是他栖身的房间。
收拾好床铺之后,王万青感到了口渴。是的,自从来到甘南,这种干渴一直挥之不去。似乎不仅仅是单纯的口渴,缺少水分和想要喝水的欲望,占据了大半个脑子。家乡的空气带足了水分,吸一口就会滋润了整个身心。而在高原,每呼吸一口气,似乎都会被带走很多水分;这还不算,最终榨干皮肤,不仅让他脸上有紧巴巴的感觉,那双嘴唇,也时常皴开了,掉着一片片干皮。
王万青来到了灶房门前,想要喝水的欲望让他急不可待,他盛了一点水,但一股很重的味道钻进了鼻子,他无法下咽,身体的需要又让他欲罢不能,最后,他加了自己带来的一点过锰酸钾,一口气喝完了水。
但是,干渴的感觉还是没有缓解。王万青大口喘着气,失落的眼神滑落湛蓝的天空,追逐一片云朵,消失在遥远的天际。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个从大上海来的大学生,一个家庭出生有问题的大学生,似乎很难让人一下子接受:为什么要放弃城里的生活?为什么会来到这个荒凉的地方?害怕站错队的乡干部只能小心地加以提防;害怕引火上身的人们,会本能地和他保持距离……王万青清楚这些,而这些东西,远比干渴给他更多更深的焦灼。这一切,只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应对了。
一个高大瘦弱的年轻人,孤独而执著地走向了广袤的草原。这里的一切他都很陌生,这里的一切,注定又将属于他……
把自己很快从困境中解脱出来的人是聪睿的人,能很快面对现实而坦然处之的人是勇敢的人,自然,能把苦难吞进肚中轻松前行的人,是一个乐观的人。
照进窗棂的阳光少了一些,但很火辣,这个温度很适合两位来自高原的老人,我想要求开空调的念头只能打消。王万青喝了一口开水,又吃了一块带来的水果。当年干渴的感觉似乎又回到他的身上。那些經历,让老人眼中闪过一些复杂的光泽,很像在宁静许久的水面激起波澜,荡起一圈圈的涟漪,但很快归于一种淡泊和宁静。凯嫪斜躺在我们对面的床铺,用右手支着花白的头颅,王万青的讲述,不时给她一种惊讶的神情,但更多的是思考——也许,在王万青思想的世界里,还有凯嫪不曾到过的地方。
“当时心里真的很悲凉!我是来干事业的,为什么要遭受这样的待遇?”王万青呵呵一笑,挥挥手,不再继续这个话题。
在玛曲停留的一个星期里,他住在玛曲县革委会的招待所里,简陋的硬板床,摇曳一团火苗的煤油灯。县城是有一台柴油发电机的,但每晚只发两个小时电,只向主要的政府部门供电。王万青报到之后,就急急忙忙赶到了县医院。
“所谓的县医院,那时的条件太差了,不如上海一个乡医院的条件。”王万青想起了它留给自己的最初印象,呵呵大笑,“我到医院之后,发现所有的医生、护士都在擦拭煤油灯罩,擦得很认真,当时觉得很好笑,但后来明白了,灯罩擦不干净,晚上就看不清楚。”
在此后相当长的岁月里,擦灯罩也成了王万青必须具备的生活技能,水洗、呵气,然后用棉布认真清除污垢,直到还原出玻璃原有的光泽度。“我的视力现在很不好,主要就是那时在煤油灯下看书的结果。”
县医院条件虽然艰苦,但一些基本的医疗器械还是有的,具备了一些干事业的基础和条件。可是到阿万仓卫生院之后,王万青感到了失望:乡卫生所只是两间土坯房,两女三男的医务人员,都是卫校、中专毕业生,而全部的医疗设施只有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那时,阿万仓乡尚未通电,根本无法展开基本的医疗救治。
更糟糕的是,因为交通不便,出门巡诊必须骑马;饮食习惯不同,基本见不到大米、白面。更为困难的是语言不通,当地群众基本都说藏语,不会说也听不懂汉语,而王万青一口浓郁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连当地汉族干部听起来都很吃力……
草原的夜色很清冷,但很美。不加修饰的安静和美丽,更能衬托出心中的孤独。苍茫的夜色中,一个年轻人吹响了竹笛,“小时候,妈妈教我一首歌”的旋律,清亮地在夜色笼罩的草原上流淌,令人为之一动的笛声,一会爬上云团,一会在草尖上飘过,湿气凝结成珠,从草叶上滑落,一颗,又一颗……
“我爱绘画,我爱吹笛子,心情不好的时候,就爱一个人吹上一阵。”王万青的大笑,把我从想象中拽回来,“既然选择了,就没有回头的说法,面临的一切,都是对我的挑战,只有战胜这些困难,我才能去做别的事情!”
把自己很快从困境中解脱出来的人是聪睿的人,能很快面对现实而坦然处之的人是勇敢的人。自然,能把苦难吞进肚中轻松前行的人,是一个乐观的人。
王万青首先解决了干渴的问题。他为自己准备了两只保温水瓶。大的两磅,小的一磅,外出时可以背在身上。他很快搞好了和厨师的关系,每次水开之后都能灌满自己的水壶,当然,王万青总会给厨师一两毛钱的报酬。至于语言关,王万青专门准备了一个小本子,把一些看病时常问的话,如“你哪里不舒服”、“哪里受伤了”、“头疼吗”、“咳嗽吗”等等,尽可能准确地用谐音标注上去,然后背下来,连说带比画,试着与前来看病的牧民交流。通过这个办法,仅用了几天时间,王万青就能独立看病了。来卫生院看病的群众基本都是些头疼脑热的小病,这对科班出身的王万青来说是小菜儿一碟,每每药到病除,大家都对他竖起大拇指。
更关键的是,王万青接受了当地的主食:揪面片。“吃惯了,感觉还是蛮好吃的。再说了,揪面片是当地最好的主食,不习惯也得习惯。”不久,他学会了骑马,学会了简单的藏语,在牧民家里,他能大口吃糌粑、喝酥油奶茶。
“只要有恒心,人可以适应任何生存环境。”王万青很轻松地对我一笑。凯嫪的脸上,也露出一抹会心的微笑,大概是想让王万青稍事休息,老人张开了嘴。她的汉语虽然流利,但似乎没有多余的词语,能讲清楚一件事情,却没有过多的形容词。
“曼巴在草原是受人尊敬的。”凯嫪欠起身子。老人说,她的父母前后生养了十个孩子,可是因为生病,只活下了四个。“家里穷,请不起医生。”凯嫪的神情有些激动,“请一次医生看病,不管好不好,都要送一只羊,或者一头牛。”缺医少药的生存环境,让许多人得病之后很快撒手人寰。
王万青接过了凯嫪的话题,脸色变得沉重起来。他说,凯嫪说的这些情况,是真实的。他在玛曲的所见所闻,都给了他从未有过的震撼。许多可以活下来的人,都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死去。“感觉到生命的尊严得不到维护,一个人就这样死去,实在不应该。”
我的问题脱口而出:“那你是否记得自己第一次骑马、第一次出诊的相关情况呢?”
老人看我一眼,很干脆地回答:“1969年8月8日。”
能把时间记得如此清楚,这一天,显然对王万青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这一天,显然给了王万青一生无法忘记的记忆。
被需要是一种绵亘的幸福,被肯定则是一种融为一体的相依相守。在需要和肯定中,王万青感觉到了自己的价值,这种感觉一旦产生,他的双脚已經在这片土地上扎根,他的事业和追求,已經萌生新的枝叶和希冀!
这一天,两位牧民骑马疾驰进卫生院,急速奔跑的马匹喷着粗重的水汽,一同进来的还有一匹备好鞍鞯的马儿。这情景,立即让王万青感觉到一定有重病的牧民需要他的救治。简单了解了一下情况,他才知道,一位老猎人在自制火药的时候发生了爆炸,身体被严重烧伤,还有一位妇女高烧不退,请求医生出诊。从两位牧民的脸上,王万青看到了他们的期望和焦急。他二话没说,立即准备好相应的药物,跨上为他准备的马匹,和两位牧民赶往病人的住所。
草原的秋天,更能领略到秋高气爽、天高地远的风景。8月的草原,收获了一年的精华,也尽情展示了一年最美的风采,湛蓝的天空,蓝得令人目眩,厚厚的草甸子,绿得率性而丰满,而五颜六色的各种花朵,恰到好处地让了无边际的绿色灵动起来。膘肥体壮的牛羊懒洋洋地甩着尾巴,远处,不时有牧人打马走过,而牧羊犬的叫声,倔强地从密密实实的牧草中钻出来。
这是王万青第一次骑马出诊。正当他陶醉在这美丽的景色中时,胯下的马儿突然受惊,一个蹶子把他摔下马背。王万青本能地用右手去撑地,随着一声清脆的响声,钻心的疼痛让他身不由己地在地下翻滚。两个牧民吓坏了,连忙扶他起来。
汗水从头上流下来,剧痛成为麻木之后,王万青挣扎着查看伤情,原来是右臂肘关节脱臼。所掌握的医疗知识告诉他,唯一的治疗方法就是复位,而且越快越好。在这空旷的草原,只能自己为自己治疗了。
第一次出诊遭遇这样的磨难,让王万青有点哭笑不得。在那一瞬间里,刚开始工作就要结束生命的恐惧涌上他的心头。两个牧民脸上不仅仅是失望,更多的是害怕。他们商量要不要送王万青回乡上治疗。王万青苦笑着摇摇头,就这样回去,也太丢人了。王万青拒绝了牧民的好意,他脱光上衣,看着脱臼的肘关节,咬着牙,要求牧民牵着伤臂的一头,帮助自己复位。
在牧民用力的拽拉下,又是一声清脆的声响,王万青痛得流下了泪水。他感觉到脱臼的关节回到了原处,挣扎着取出纱布,在牧民的帮助下固定复位的肘关节,把右臂吊起来。给自己治疗完毕,牧民认为这个医生要打道回府了,没想到王万青果断地要求继续前行。牧民心中的欣喜溢于言表。
到了病人家,王万青发现老人的烧伤已經开始感染,再不及时处理,有生命的危险。而此时他的右手指已經毫无知觉,他给自己扎针、按摩,待恢复知觉后,立即给老人清创、敷药、打针。随后,他又赶到发烧的病人家里,为病人听诊、做皮试、打针……处理完毕,已是深夜。那一夜,他就睡在病人家的帐篷里,疼痛尚能忍受,出师不利的懊恼却令他辗转难眠。
第二天,看到病人开始恢复,王万青又做了进一步的治疗并留够了足够的药品之后,这才回到卫生院。这时,他的胳膊已經肿得连衣服都脱不下来了;随后一周,肿痛依然不消。乡上和卫生院都害怕了,找了一匹老实乖巧的老马,把他送到县医院进一步拍片诊断,结果是右臂轻微骨折,关节腔积血。
担心留下后遗症,影响今后的工作,王万青请假回到上海,在上海第五中医院找到一位老中医治疗。治疗过程中,王万青发现中医的治疗手法在基层非常适用,于是,他边治病边跟老中医学习。半个月后,王万青养好了伤,带着新学的几招临床实用中医技术,回到了阿万仓。
第一次出诊,遭受磨难的同时,王万青为自己赢得了肯定和赞誉。“曼巴”在藏语里是医生的意思,根据王万青的特征,当地藏族群众称他“曼巴细尔”(藏语,眼镜医生)或“曼巴扛且”(藏语,大脚医生)。
美丽的草原是一个滋养故事的沃土,故事一旦诞生,就会像疾驰的马儿一般传遍四方。在一遍遍的传述中,每个故事都像盛开在草原的花朵一样可人心意。在玛曲草原上,至今流传着这个曼巴细尔救人的故事。1984年的一天,一名叫南美的十岁牧童被牛角顶穿了肚子,外露肠管都已变色。万分焦急的家人将奄奄一息的南美送到了乡卫生院。当时,南美的血压都已經测不到了,必须立刻做手术,但乡卫生院根本不具备做手术的条件,如果转院救治,必须翻一座山、过七道河,如此折腾,孩子性命难保。征得家长和乡里领导的同意后,王万青把两个办公桌拼在一起,当作手术台。一个电灯泡加上一把手电筒,充当了“无影灯”。实施麻醉后,王万青冒着很大的风险,为南美做了坏死肠管切除手术。手术后十多天,南美开始进食了。南美得救了!一时间,牧民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纷纷竖起大拇指夸赞这位神奇的曼巴细尔。
阿万仓乡方圆1000平方公里,共有牧民3000多户,散住在草原的各个角落。在长达40多年的行医生涯中,他多次在牧民帐篷中救死扶伤:在牛粪堆上为大出血休克的产妇实施胎盘剥离术;在夏窝子(夏季放牧点)中彻夜守候、人工呼吸抢救患肺炎心衰的新生儿;他还为一名70岁老人成功地做了肛瘘手术,解除了困扰老人大半辈子的痼疾;成功地从死神手里夺回一名急性高原肺水肿牧民的生命……这些遭受病痛折磨的生命,在他妙手回春的作用下,像盛开在草原的花儿一样重新绽放生命的花朵。
被需要是一种绵亘的幸福,被肯定却是一种融为一体的相依相守。在需要和肯定中,王万青感觉到了自己的价值,这种感觉一旦产生,他的双脚已經在这片土地上扎根,他的事业和追求,已經萌生新的枝叶和希冀!
直到王万青临走的那天,父亲才留下一句话:“你要娶了人家姑娘,就要负责到底,不能变心。”父亲简单的话里,蕴含了深意:不能变心也意味着永远无法回到上海。
和众多的读者一样,我很想知道王万青和凯嫪的爱情故事。当我问到一个问题时,王万青摇摇头,凯嫪却点点头。
这个问题是:你是为凯嫪而留到草原的吗?
王万青摇摇头,是因为除了自己的妻子、儿女,还有他的事业,还有他对生命的尊重和努力;而凯嫪之所以点点头,自然有自己的感悟和思考。
我突然明白,王万青很多的选择,都跟自己的事业和追求有关。
1970年夏天,为了更好地普及医疗知识、培训乡村医护人员,王万青被派往红原大队培训赤脚医生。计划中,只有四个男的,并没有培训女同志的打算。但是凯嫪所在生产队的队长却突发奇想,一个劲问王万青要不要女同志?王万青没说要,也没说不要,只说先看看再说。
一个傍晚,暮色沉沉,生产队长带来了凯嫪。这是王万青第一次见到后来要成为自己妻子的凯嫪。“怯生生的,站在帐篷外面,黑不溜秋的,刚下工,也没洗漱,低着头,不说话。我也看得不大清楚,觉得只要不是傻乎乎的,就可以来学习,就点了点头。”想到当初见到凯嫪的情景,王万青率真地呵呵大笑。
凯嫪白了他一眼:“那个时节,他可是很有名气。上海来的大学生,大个子,又很会看病,威信高得很。”
凯嫪忘不了第一次和王万青的对话,但在整个对话的过程中,她始终没有抬头看一眼这个来自上海的大学生。
第二天,凯嫪打马前来报到。朝阳嫩红的光温暖地包围了医疗队的帐篷,另外几名男学员也赶到了帐篷前,瘦高的王万青走出帐篷,看看自己的学生。他问凯嫪:“上过学没?”
凯嫪低着头回答:“上过。”
“会说汉语吗?”
“会一点。”
简单的对话结束之后,凯嫪就参加了培训。培训内容除了正常的上课之外,还要到各个生产队巡诊。这个时候,王万青就带着学生们,骑着马,往返于各生产队之间。
凯嫪学习认真,还很勤快。每到一处,她总是跟男学生一样,在草地上搭建帐篷,然后一个人到附近捡拾干牛粪,生火烧水。
在诊疗中,会说汉语的凯嫪成了王万青与牧民交流的纽带。牧民们通过凯嫪,对这位来自上海的“曼巴”有了好感。而王万青对凯嫪的评价是:“漂亮、勤快、善良,很了不起。不怕苦,不怕脏,是个好姑娘。”
这个好姑娘给王万青的印象还有“很勇敢”。在培训学生扎干针的时候,王万青发现凯嫪学得很认真,为了准确找到穴位,这个姑娘經常在自己的手腕上练针,当几个男学员哆嗦着不敢下针时,凯嫪已經手起针落。
敬仰和崇拜,能让女性很快爱上一个人,而欣赏和赞叹,能让一个男人很快对一个女人产生好感。也许,王万青主持的赤脚医生培训班,在培训乡村医生的同时,也埋藏下了自己爱的种子,只是他自己当时未曾觉察罢了。
1971年的一天,王万青骑着马路过一个放牧点,忽然发现远处有几条黑影正飞快地向着自己的坐骑扑来。
“藏獒包围了我的马,马一惊,马鞍子的肚带就断了,我连人带鞍子摔了下来。”王万青昏了过去,好几个小时都没能醒来。就在乡亲们围在他床边不断为他祈祷时,王万青所教的那位女学生却躲在家里痛哭。她的嫂子忍不住责怪了几句:“曼巴是你什么人?这么大哭,成何体统!”
凯勒告诉父亲,她要一直陪着他,直到他醒来。一天一夜的守护,王万青终于醒了。“我躺在帐篷里,受伤了不能动弹,只能用眼睛看来看去。我这位女学生坐在对面的炉子边,不看我,也不说话,只是偶尔用眼角扫我一下……”
伤愈后不久,一天,凯嫪突然跑来对王万青说:“我阿爸、阿妈要把我嫁给你,你答应吗?不答应,我就得嫁给别人了。”
当时,凯嫪18岁,按照当地的习俗,该出嫁了。心里只有王万青的凯嫪不想嫁给别人,于是,大胆地跑来表白。
王万青认真地考虑了很久。
“成为藏族人的女婿,最大的好处是当地藏族群众会更加认同、接受自己,有利于开展工作;最大的坏处则是今后可能就回不了上海了。”王万青权衡再三,决定接受这份感情。
为了自己的终身大事,王万青请假专程回了一趟上海。得知王万青的决定后,父母沉默不语。那时,跟他一样的大学生已經大批回城。
直到王万青临走的那天,父亲才留下一句话:“你要娶了人家姑娘,就要负责到底,不能变心。”父亲简单的话里,蕴含了深意:不能变心也意味着永远无法回到上海。
带着这句嘱咐,王万青回到了阿万仓。
1971年2月10日,王万青给自己办了一个像模像样的婚礼。他从上海带来的两包糖果,来不及分就被大家一抢而空;卫生所里的几个人集体出动,还请来了卫生院做饭的大师傅,为大家做了几桌丰盛的酒席;这是一桩在藏区的汉藏合婚的喜事,前来贺喜的人们笑得前仰后合,村庄的上空弥漫着过节般的喜庆。
“请卫生院的同事们吃了一顿,就算把婚结了。”王万青至今还记得那顿饭的花费:一只羊9元,又买了些萝卜、白菜,一共花了15元。
婚后的生活简单而平静。与以往不同的是,王万青不再单独出行,每次巡诊都有凯嫪陪伴。阿万仓乡方圆1000平方公里,3000多户牧民如星星般散落在草原上。那时,卫生院只有一匹马,每次出诊前,凯嫪就跑到娘家借来两匹马,两人各骑一匹,另一匹驮帐篷、锅碗以及医疗器材。
每到一个地方,王万青忙着给牧民看病,而凯嫪则搭建帐篷,拾干牛粪做饭。遇到沟通障碍的时候,凯嫪便上前“翻译”。
也许是有了藏族女婿的特殊身份,王万青与当地牧民亲近了许多。在王万青的培养下,凯嫪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护理人员。1982年,凯嫪正式转为卫生院的在册员工。这期间,调进调出卫生院的医务人员不下30人,始终不走的只有他和凯嫪。
在阿万仓工作的20年间,王万青夫妇骑马并肩,走遍了阿万仓草原的每一个帐篷,为生病的牧民群众送医送药,为每一个适龄儿童及时接种,为全乡3000多人建立了门诊病历,使全乡90%的牧民有了自己的健康档案。“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这边的牧民用马刚送回来,那边的牧民牵着牛已經在等。”凯嫪回忆说,有时,病人多的时候,王万青连续几天几夜都不能休息。
王万青担心被人误解,说他想通过考研找一个与凯嫪分手的借口;可另一边,是他已魂牵梦萦了十年的家乡。然而最终他放弃了离开草原的念头。考研变成了一个看得见却摸不着的梦,而上海也离他越来越远了。
毕竟是从大上海来到偏僻的玛曲,两地之间的差异,不论是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有着天壤之别。“上海是生我、养我的故乡。说不想回上海,那是假话。”谈到这一点,王万青直言不讳。
“如果我是他,我绝对不会来这个地方,吃的不适应,穿的不适应,又没有亲人和朋友,为什么要到这儿来呢?”凯嫪理解丈夫,可她也无能为力。但从另一个方面,恰好说明了王万青的过人之处。
王万青说:“多年来,我无数次跟自己斗争过,但思前想后,还是选择留了下来。40多年里,藏族同胞给予了我尊重和认可,每次出诊或路过牧民帐篷时,总有热情的召唤和香甜的奶茶相伴;每每走上街头,一句句‘曼巴,扎西德勒的问候也让我倍感温暖。”
一个敢于寂寞的人一定能战胜孤独,并且享受孤独。无数个夜深人静的日子里,王万青都会遥望家乡的方向黯然伤神,可是当他面对无数需要救助的病人时,这一切烦恼又都抛在脑后。他用自己的行动,维护自己的事业和爱情。无需多的理解和同情,也无需多的解释和表白,他对自己的信念选择了坚守。
王万青感叹,他的父母、兄弟姊妹一直未曾来过甘南,未曾来过自己工作、生活的地方。他说父母亲养育了他们四个儿女。他的大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成都;他的两个妹妹一直在上海工作,平时对老人多有照顾。以前,王万青每年回家探亲都要带一些土特产,可是家里人都不爱吃,以后他索性不带了。他每次回家都想给父母留点钱,可父母总是坚决不要,本来也不宽裕的他以后也就不再坚持。
父母在世时,王万青第一次带凯嫪回上海拜见公婆,那时他们已經是两个孩子的父母了。他给老大起了一个名字叫团胜,这个带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名字让老人一听就摇起了头,但老人说,男孩子,无所谓,团胜就团胜吧,民族团结胜利更好。老二的藏族名字叫久美其,老人听着不习惯。第二天,当着他俩的面老人郑重宣布:“孙女的名字我改了,以后就叫其美。”
老太太给她的藏族儿媳妇扯了一套红条绒的料子,在上海量身做好了;但是,挑红颜色的面料,却是王万青的主意,因为藏区最流行的就是红色,而红色穿在妻子的身上,总有一种难以描述的美丽。母亲总是顺着儿子的心意。老父亲给王万青送了一只欧米茄手表,嘱咐他每年一定要拿到上海去清洗一次;父亲去世多年以后,王万青才恍然大悟,那是父亲每年都想见到儿子的一种特有的含蓄和暗示。
娶妻,生子,做事业,王万青延续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生活。日子,就在这种重复中悄然溜走。
但是,王万青还是记住了令他动容的事情。那时,他的主要工作在乡卫生院,而凯嫪在生产队。多的时候两人各据一方。有一次,王万青闲了一些,思念孩子的心情让他立即打马向凯嫪所在的生产队赶去。凯嫪不在。他们的孩子拴在桌子的一端,另一端拴着一头藏獒。不远处,就是成群的牦牛。
“当时的情景,让我的心里很酸楚。我知道藏区的很多孩子都是这样长大的,但我的孩子不应该經历这样的危险呀。”王万青说,发狂的牦牛往往会踏平帐篷,而把藏獒和孩子拴在一起,是为了震慑牦牛的疯狂以保全孩子。他知道凯嫪既要干生产队的活,又要照顾孩子,实在是不容易呀。
后来,四个孩子相继出生。王万青整天在卫生院忙碌,而照顾孩子的重任完全落到了凯嫪一个人的身上。遇到出诊,凯嫪就把三个大的留在家里,把年幼的老四用绳子绑在后背上,骑马出门。
王万青喜欢画画,闲下来的时候,他坐在山包上,画青青的阿万仓,画美丽的藏族姑娘。这时,凯嫪就跟在他的身后,帮他拿笔墨、画架。画完成了,她是他的第一个观众。
怀念家乡的时候,王万青經常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望着窗外草原的星空,唱忧伤的俄罗斯歌曲。此时,凯嫪悄悄地站在窗外,静静地聆听。
工作上遇到挫折的时候,凯嫪总是真诚地对他说:“没事,工作如果没了,你就到我们生产队,我养活你!”
“文革”后期,支边医务人员和插队知青们陆续离开了甘南草原,返回上海。平静的草原生活缓缓铺展,时光流逝。可眼看着一起支边的医生护士、插队知青们回了上海——那个自己日思夜想的故乡,王万青有了一点念想。现实的牧区生活和文化差异,也曾动摇着这个上海人原本要“扎根草原”的决心。
“如果要在阿万仓永远生活下去,是不合适的。上海是我的家乡,我还是要回去,我不会忘记父母,我也不会忘记上海。”这样的想法在王万青的心里一次次出现,以至于让他有了“铁了心也要回到上海”去的念头。
1978年,高考恢复,王万青决定考研。他翻出大学时的书本,满怀信心地开始复习。
在阿万仓的土房子里,王万青点上油灯,专心复习。妻子凯嫪坐在一旁,看着丈夫奋笔疾书,不言不语。有一次,王万青从书堆里抬起头,竟发现妻子在悄悄抽泣。“那种哭,淌着眼泪,轻轻的,没有一点声响。她跟我说,你考研究生,你要出去……”
凯嫪没有把话说完,但是王万青感觉到“她很伤心,虽然不反对,但也不怎么赞成”。
妻子的眼泪让王万青心里非常难受,“我也思考了,也许我能考上研究生,但是考上了究竟是好事情还是坏事?凯嫪不可能跟着我走。草原上的人是不愿离开草原的,因为换一个生活环境,他们可能无法生存。所以如果我离开,那个结果,可能就是家庭破裂。”
王万青担心被人误解,说他想通过考研找一个与凯嫪分手的借口;可另一边,是他已魂牵梦萦了十年的家乡。然而最终他放弃了离开草原的念头。考研变成了一个看得见却摸不着的梦,而上海也离他越来越远了。
1983年,王万青在上海进修学习了一年。其间,有单位愿意接收他,有人甚至张罗着给他介绍对象。在玛曲,风言风语也开始满天飞,有人跟凯嫪说:“王万青不回来了,已經买好了家具,等着跟别人结婚呢。”
“有人说,我是为了凯嫪留在了草原,其实只对了一半。”王万青说,“凯嫪离开了草原,就像鱼儿离开了水。”而他考虑更多的是想在草原上干一番事业。
“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草原的感情越来越深,真的不想走了。”
于是,王万青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企盼儿子能到上海接受良好的教育。經妻子同意,他们八岁的儿子被送到了上海。1987年,这个孩子也走进了医学院的大门。
“草原上需要大夫,我不能随便走。”王万青对自己说。但在内心深处,他忘不了自己的經历:两次意外受伤时,牧民群众自发端茶送饭、精心照料;每次出诊或路过牧民帐篷时,总有热情的召唤和香甜的奶茶相伴;逢年过节,經他诊治的病人会专程赶到家中,送来冰糖、酥油等礼品,表达谢意,家住县城的患者更是天天过来看望;每每上街,一句句“曼巴,扎西德勒”的问候也令他温暖、感动。2003年,王万青退休后,还时不时有病人找到家中,请他看病,这让他越发体会到人生的价值和被人需要的幸福,因而也更加不愿离开玛曲。
同样是生活在大城市的年轻人,同样有着高学历,但当年王万青的那种万丈豪情,恐怕已經很难在今天的年轻人身上找到。有网友说,看到王万青的事迹后,他最大的感触是感动。他说,大学生在择业时应该像王万青那样,追求崇高,追求理想,到需要自己的地方去,到更能发挥自己作用的地方去。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未来十年国家对西部的投入将越来越大,西部也将越来越需要人才,大学生到基层、到西部就业既是对自己的锻炼,也是服务基层群众、支援国家建设。看了王万青的事迹,每个大学生都应该对自己的人生、理想有新的思考。
“我学了很多,但用得很少。”老人抬起头,眼神里充满了遗憾和内疚,“我立志攻克癌症,但是在今生已經不可能了。我老了,年龄大了……”
1987年,甘肃电视台拍摄的黑白纪录片《啊!青青的阿万仓》播出,开头的一幅画面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辽阔而寂寥的大草原上,坐着一个戴黑框眼镜、穿一身运动服的清瘦男子,他的眼睛凝望着远方,用笛子吹奏出思乡的曲调……
这个人就是王万青。他用自己的信念和执著,改变着阿万仓人们的生命质量,也改变着人们对自己的认识。也可以这样说,当人们普遍被物欲蒙蔽了心灵时,他的坚持和奉献,如同清凉的甘露,给活在当下的人们、给这个浮躁的世界一丝清凉和滋润。
1987年,王万青在阿万仓的生活将满20载。这年,他已經43岁了。“一切都很突然,事先没有一点儿征兆。”
那天,忙活着的王万青突然接到一个通知。他立马开始打点行李,并翻出了压在箱底的一套始终舍不得穿的衣服。几天后,穿着这身衣服的王万青来到北京,走进了人民大会堂,荣获“全国民族团结先进个人”称号。这是20年来,国家和阿万仓草原给他的最高回报。
“说老实话,我实在太普通了。国家那么大,民族那么多,况且我们医务人员也很多。我是一个乡里的小大夫,是很渺小的。”但王万青始终觉得,“工作虽小可意义很大,生活的意义也很大。”
早在阿万仓草原“出名”的王万青,这回真的出名了。甘肃省卫生厅根据他的业务能力,评聘他为主任医师,并打算将他调至玛曲县人民医院担任外科主任。这回,王万青却不愿意了,他更希望“留在草原上给牧民们看病”。后来几經组织上做工作,他才同意回到县城。
在玛曲县医院,王万青是专家。除了主持外科工作外,他还担负着医院的教学和培训任务。直到今天,这个在大都市长大的上海人却还拒绝使用电脑。“电脑费眼睛。以前在阿万仓草原的煤油灯下看书,把眼睛看坏了,我还想在有生之年里多看几本书。”
2007年,一群城市里的大学生打算重走王万青当年的离乡路,去草原寻访他。去之前,大学生摄制组拨通了王万青家的电话,问他有什么要带的。
“王大夫,我们要从上海出发了,您有什么要带的吗?”王万青的回答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有没有《新民晚报》?哪怕过期的也行!
“40多年了,回上海的念头时时会涌上心头……”王万青说,父母在世的时候,定期会给他寄来上海的《新民晚报》。在报纸上,他感受着家乡的气息。至今,他时常会想起上海的芝麻糖。父母去世后,他已經很长时间没有再看这份承载家乡味道的报纸了。离开故乡40多年,他依然渴望了解上海的点点滴滴。在拿到报纸的那一刻,王万青流泪了,他迫不及待地想从字里行间感受牵挂多年的上海,感受留存在记忆深处的家乡的气息。
2007年,上海医科大学创建80周年庆典邀请函寄到了王万青的手中,邀请他作为学校百名杰出学子回母校参加隆重盛大的典礼,邀请函的落款为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王生洪的亲笔签名。这份邀请函至今仍被王万青珍藏着,是最令他骄傲的东西之一。
如今,退休后的王万青还經常在家里为牧民们看病。
40多年,王万青离开大上海来到阿万仓,在缺失一种亲情的同时,却也收获到足以让他温暖的另一份亲情,这份亲情来自凯嫪、来自草原、来自他的第二故乡。
谈到40多年的寂寞和坚守,王万青的眼睛有点湿润。他说:“我向父母亲索要的太多,但回报他们的却又太少,一想起来就觉得心里难过。”
在王万青的记忆里,父母亲给他寄过很多东西,有吃的,有穿的,还有用的。为了满足他的要求,父母还专门给他寄过多年的《新民晚报》。父母临过世的时候,他都赶回去了,但是,父母亲从来没有来过他工作的地方,这也是让他嘴上不说、心里却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他在上海的所有亲人,也都从未到过他在阿万仓或者玛曲的家。然而,他在这一方面情感的缺失,却由凯嫪的父母及家人给予了补偿。
至今,他保存的一张黑白小照片上,是凯嫪的父亲赶着马车来接他们全家回家过年的情景。王万青说:“我们在阿万仓生活工作的20多年中,每年大年初一,无论雪有多大,他老人家都要亲自接我们全家回家过年的,这份情,我今生今世都无法报答。”
凯嫪家的亲戚们,至今还是他们家逢年过节往来不断的最重要的亲友团队。他们四个出生于斯、成长于斯,如今又都共同生活、工作在这里的孩子们成家之后,又带给他们更多的亲朋好友。王万青生活其中,其乐融融。如今,住在阿万仓乡的其美小两口租下的房子,就在当年王万青他们工作生活了20多年的卫生院的隔壁。其美在家操持,丈夫在外做生意,日子还算过得去;他们的大女儿王进已經从护校毕业,小儿子正在县城读初中。这两个孩子都是王万青一手拉扯上的学,如今,他俩都还在老人身边。对于大孙女的选择,王万青无比自豪,他说:“这可是我们家最杰出的代表啊!从她算起,我们家已經有三代人在玛曲从事医生、医护职业,一想起这些,我就感到特别的满足和幸福。”
退休后的王万青住在玛曲县医院右侧的一院小平房里。推门进去就是厨房,穿过厨房,院子里有两畦不大的菜地,青翠欲滴的菜园正对面是一排南北朝向的平房。现在,王万青除了应邀外出作报告外,大部分时间就在这里。“我的眼睛不太好使,但我会用画画的方式记录我的一生。一幅画,就是留在我心中的记忆,再配一点文字说明,就会连成我的一生了。”
王万青的回忆录,不是文字,是图画。王万青退休后,把自己走过的人生驿站和难忘的工作生活场景用艺术的语言,一一记录在大大小小的画布上,这些融入国画、油画、唐卡元素的生命记录,散发着牧区的气息,跳跃着高原的精灵。图画的内容,有草原风光、牧歌情调,有羊、马、牦牛、藏獒,有背水、打酥油的妇女,有他自己骑马出诊的背影。
他创作的数百幅绘画常常把他的思绪带回到栩栩如生的青春岁月。40多年前,他第一眼看到的阿万仓乡卫生院,只有几间土平房,墙皮剥落,后墙用木头支撑着。医生只有听诊器、血压计、温度计。出一次诊得走四个小时的路程,后来骑马、骑牦牛、坐狗拉雪橇,再后来,才有了拖拉机、摩托车。他曾經跪在牛粪堆上为一位难产的藏族妇女做胎盘剥离手术。有个名叫南美的九岁男童被牛角扎破肚子,肠子露在外面……
每作完一幅画,王万青都会沉浸在画面里,不管是美好的还是酸涩的记忆,都会给他长时间的沉思。留存在记忆深处的碎片,闪烁着生命的光泽,给他感动的同时,又给别人更多的思考。
如今,王万青头上有许许多多太多的光环。采访即将结束时,我问老人:截至现在,您有没有遗憾?您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没想到,王万青垂下了花白的头颅,笑容在老人脸上消失得干干净净,沉思良久,老人才张开了口:“你也许不知道,我小时候的理想不是医学,而是电子学、电磁波之类的……”
小时候,王万青就读的上海中学在东南亚都很有名,这是一片孕育理想的沃土,他的志向是做一名科学家,主攻方向是电子学。但是,他们最爱的老师却患癌症不幸去世。“老师去世后,我怎么也想不通,这么好的一位老师,前几天还和我们说说笑笑的,怎么说死就死了呢?”悲痛之余,王万青改变了自己的初衷:学医,一定要学医,攻克癌症,让更多身患癌症的病人重获生的希望!
“我学了很多,但用得很少。”老人抬起头,眼神里充满了遗憾和内疚,“我立志攻克癌症,但是在今生已經不可能了。我老了,年龄大了……”
老人的遗憾让我内疚,我急忙说:“您已經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了。”
凯嫪也说:“你呀,总是这么不知足!”
王万青不再说话,他看着窗外。窗外阳光灿烂,灿烂的阳光和桌子上金灿灿的玉米粒一样富有生命的质感和重量。看着老人,我突然想起感动中国人物颁奖词对他的褒奖:只身打马赴草原,他一路向西,千里万里,不再回头,风雪行医路,情系汉藏缘。四十载流年似水,磨不去他对理想的忠诚。
春风今又绿草原,曼巴的故事还会有更年轻的版本。
是的,这个曼巴细尔的生活还在继续!
阎世德,曾发表中、短篇小说多篇,出版长篇报告文学《崛起太空——媒体人眼中的中国航天》等三部。现居兰州,职业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