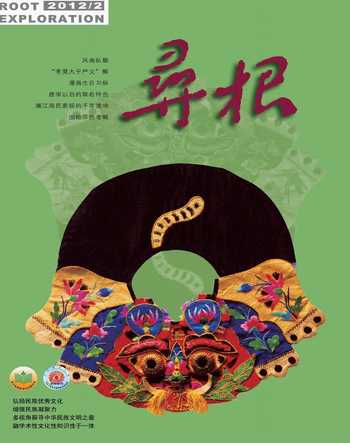煮粥思源
吴正格
“粥”的本字是“鬻”。字中的“鬲”,为最原始的煮粥器,是猿类进化为人类的物象标志。“粥”置“鬲”上,兹证是野蠻到文明的食象标志。人以口喝粥,“人”加“口”就成了“史”。因而,这一碗粥里就装得下中国历史。
史官们皆说:黄帝始烹谷为粥,但非指黄帝是粥的发明者。黄帝“艺五谷,抚万民”(《史记·五帝本纪》),该解释为那时候已有谷物,种谷、食谷渐成各个氏族部落刀耕火耨的生存行为,从而发轫并崛起一个米食氏族—这大概是不会错的。
“粥之食,自天子达。”(《礼记·檀弓上》)中国自有了天子,喝粥就上下成习。天子喝粥,有两种情况。一是本纪之光,囿于农耕伊始,谷少食缺,想到“神农憔悴,尧瘦癯”这句话,黄帝若能顿顿喝上粥,算很奢侈了。二是商以降,食物已丰,天子得以宴乐,为解腻消膻,就拿粥溜溜胃。但还得这么说,古代人阶层越高,吃干饭的次数越多;阶层越低,喝粥的次数越多。及至穷庶贫民层面,喝粥几是一年到头的正餐了。所以,要说历史上的粮食总产量,十居其一用于饭, 十居其九用于粥,应该是可能的比例。
如果穷原竟委,国人最初喝粥,所用其谷为何物?应该是粟(小米)。原因是粟为国产,源植中原。“粟”字原带“禾”形,是最早的甲骨文字之一,粟的食用便从流传的程序中得到见证。纪元以后,帝王祭祀的谷物通常为麦、黍、麻、稻和粟。前四种谷物都要搭配动物供祖,唯粟被记载为“农乃登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吕氏春秋·十二纪》),引文中的“新”,即是新粟。用新粟祭祀,正说明粟的先端存在,也意示粟太平常了,太平常的东西正是太古老的。所以,粟就成为做粥的启蒙物,后人如翘首北辰,为感念粟的福祉,就把它认作是口粮的象征和钱财的化身。如“征赋钱粟,以实仓库”(《韩非子·显学》),“粟,禄也”(《广雅·释诂》)。在粟之前,先民仅懂得将兽肉饪熟而已,尚无具体的膳目区分;粟之后,有了粥饭,就是含义具体的食品了。这是中国的文明曙光中顶要紧的一抹旖旎。遥想远古的晨空中飘忽的炊烟,是人世间最初的生态象征;粗陋的茅泥屋里,正完成着从兽食到人食的真正转型,一个生涩的历史已被饪熟。从这里你能触摸到中国人口的生殖脉根。一个从弱小到强壮民族的血管里淌的是什么?首先是粟的流液,然后才是稻粱菽的米浆。
若从营养价值的视阈去考量中外历史中的民族繁衍,就会发现,米食民族的性早熟,强势于面食民族的生殖。因为,米蛋白质的氨基酸中,精氨酸的含量比麦要超出许多;而且,在形成精子的主要部分—核蛋白质的精蛋白中,精氯酸的含量也大得多。也就是说,米蛋白较麦蛋白容易形成精子。纪元以后,兽多于人的生番状态不断改变,构建文明的现象层出不穷,使蠻赫的大自然渐退边隅,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国人懂得了“五谷为养”(《黄帝内经》),形成了以粥饭为主食的“共识”,从而使“主食”这一词语成为解读中国人口发展的原始课题。
有个已被我们遗忘的“人口粥节”,很能揣度先民们对粥与人口生殖关系的认知:
(腊月)二十四日……此日市间及街坊叫卖五色米食……叫声鼎沸。其夜家家以灯照于卧床下,谓之“照虚耗”。二十五日,士庶家煮赤豆粥祀食神,名曰“人口粥”,有猫狗者,亦同焉。不知出于何典。(吴自牧《梦粱录·卷六·十二月》)
这虽是南宋时期的事情,但你若是读过孟元老追记北宋汴京的《东京梦华录》,就清楚北宋亦有此节。所以,这是整个宋代共有的节日。无疑,用“人口粥”祭食神,是祈愿人丁兴旺。但吴自牧不明其故,足见此节来历久远得到南宋时已经模糊不清。以我的测断,这与晋隋之期与粥有关的神鬼之事相系。南朝吴均《续齐谐记》载:吴县人张成,晚归于宅,见东南隅站一妇,并对他说:“此地是君家蚕室,我即此地之神。明日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于上祭于我。当令君蚕桑百倍。”张成照办,从而蚕桑果获大收。以致后来,每逢正月半,养蚕人家皆制肉粥,攀屋祭于顶,并诵:“登膏糜,狭鼠脑,欲来不来,待我三蚕老。”以祈蚕丰之运。由此,形成了江南的蚕桑节。这个情节,与“人口粥节”的由头有些类似。又据《五千年皇宫秘史·猫鬼作祟》记:隋文帝独孤后之弟独孤陀为延州刺史,家有一婢女,事猫鬼。独孤后和司徒杨素之妻患病,无药能治。巫医说是“猫鬼疾”。隋文帝早闻陀有一婢女事猫鬼,怀疑陀从中作祟,乃传此婢,亲作验证,命她咒使猫鬼入宫。是夜半,此婢置粥一钵,以勺击之而呼:“猫女可来,无往宫中久之。”呼毕,脸色煞青,腰身扭动,形如被猫抓拽之,慌说:“猫鬼已至。”
如今看来,此婢是故作之为,有造假乱真的本事。但在隋朝,就容易使人相信。所以,文帝即怒,将陀革职查办。这个猫鬼馋粥害人的故事,可能是“人口粥节”的来历。想到宋人在此节前夜,家家用灯照亮床底,这是驱猫鬼的举动;而且,以粥祭食神时,“有猫狗者,亦同焉”,这又是戒备猫狗抢粥害人,怕断了传宗接代的香火,狗也随猫沾光。这看上去是迷神信鬼,但想到在帝制和神权中过惯日子的老百姓,这种消灾行为反映了他们为繁衍后代、濡养生灵而守护食粥家园的虔诚愿望。
还应该说到,中国历代都是农耕立国,农民种地靠天,俭守田庐,且要纳税完粮,实是不易。有个粥节,也是寄寓着对五谷的尊重和珍惜。
这方面,一些体恤民负重轭的帝王,也不垂拱而治,懂得养民以粟的道理。西汉刘向《新序》记:邹穆公用糠秕喂禽,有臣谀请喂粟米。穆公正色道:“粟米,人之上食,奈何其以养鸟……鸟苛食邹之秕,不害邹之谷也;粟之在仓与在民,于我何择?”他宁愿用粟米换秕,也不糟蹋粮食。这类良风美尚,还有“孙叔敖相楚”(《韩非子·外储》)、“晏子相齐”(《晏子春秋》)、“箕季谏魏文侯”(《新序·刺奢》)等记载,他们都是作则于己,吃粗粥糙饭,提倡“粝餐之食”的,当为最早的勤俭治国的范例。
至于黎民苍生,家薄资微,耕种自给,数口嗷嗷之外,还要关顾添丁延代之计,因而辈辈为粮而累。所以,食粥是他们过“小日子”的基本家策。因为其一,饭米之数用于粥,一餐能充两餐,省粮;其二,粥是米和于水之物,米烁利膈养胃,省水;其三,煮粥时加盐酱蔬菜,饭、菜、汤皆备,省钱;其四:粥法简易,只需水火为之,省力。对此,清人赵翼《檐曝杂记》里有《煮粥诗》为记:
煮饭何如煮粥强,好同儿女熟商量。
一升可作三升用,两日堪为六餐粮。
有客只须添水火,无钱不必问羹汤。
莫言淡泊少滋味,淡泊之中滋味长。
赵翼写过《二十二史记》,被后人评为“精辟中肯”之作,兹见他对农耕立国的政事有较深的体验。他曾出知广西镇安府,改革常平仓谷出轻入重之弊,颇得政声。由这位深谙国情、体察民食之人写出《煮粥诗》,就有了米食民族亲近粥的历史况味,读来令人感觉贴实而真切。
(题图:小米为国产,源植中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