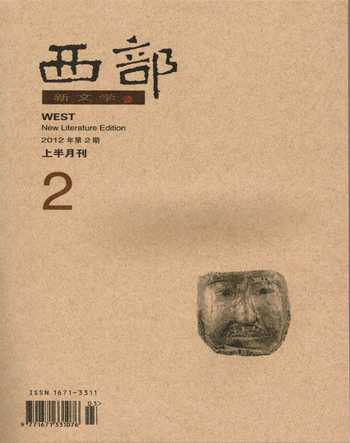小说三题
向祚铁
饥荒
史载:明末,关中连年旱灾,城中小儿,旦出,暮多不归。
小山的死
小山来到了城外,眼前的景象让他不知所措。大地上见不到一株庄稼,也见不到一个农民,太阳把日光笔直地射到地面。光秃的大地向天那边铺去,直到和球面的天空接合起来,形成简单而又严谨的密封。
小山终于明白了,今早拖着木棒从街上走过时,那些瘫坐在廊檐下的人们为什么会用讥讽的眼光看着他。是啊,这次旱灾确实与以往任何一次都不相同,它进行得非常沉寂,令人窒息。
今天早上,小山下定决心,无论如何要来郊外碰碰运气,为了给自己增加信心,他非常细心地削了一根枣木棒,他把木棒的一端削得很尖,可以方便地戳瞎野狗的眼睛。小山拖着木棒,尽量放轻脚步,以免惊醒睡在廊檐下的人们,否则,人们会因为自己受到打扰而把他痛打一顿;另外,小山瞧不起他们,不想和他们有什么交往。可是,那根枣木棒却一点也不体会小山的心情,它在小山身后蹦■着,把街石敲得乱响。这样,人们全醒了,可出乎小山意外,他们没打小山,只是不感兴趣、同时又略带讥讽地瞧了他几眼,就又翻身睡觉去了。
现在已是正午,太阳晒得小山发晕;没有一丝风,天空蓝得就像浸过油似的。小山见不到一个人,他把眼睛竭力眯缝起来,一点点地扫视着远处的农舍,屋顶上的茅草泛着黄光,使大地显得更为寂静。小山竭力想听到一些禽畜的叫声,但他没有听到,他也没有听见人们偶尔的嘈杂声。
小山出城时,本来还抱着一丝希望:无论如何,农村总应有些可吃的东西吧。现在,他失望了。他不甘心,用木棒在垃圾堆里拨弄,希望能发现一块骨头,这样就可以让舌头不停地舔下去。这时,他看到一只野狗在垃圾堆的背阴处,正啃着什么。小山慢慢走近,看到它啃的是一只人手。小山一阵欢喜,因为野狗和乌鸦不同,它们不吃腐尸。他对准狗屁股,用力打了一棒。野狗一惊,丢下人手,跑开了。小山扔开棍子,捡起人手放到鼻子下闻了闻,果然没有臭味。但野狗只跑了一小段路就停了下来,当它看到眼前只是一个瘦弱的少年时,便肆无忌惮地扑上来,咬住小山的右脚。小山用拳头打它的脑袋,又试图用手去掰开它的嘴巴,但是野狗咬得更紧了。小山无可奈何,只好把人手还给它。
走了一段路后,小山想起他的棍子忘记拿了,于是停下来。可野狗并没有理解小山,当看到小山还没有走开时,它愤怒地露出尖锐的犬牙。小山为了消除误会,把眼光离开那只人手,也离开野狗。他趴下身子,把目光局限于那根木棍,一步步地向前爬去。可野狗并没有理解小山的一片苦心,它认为这是一种偷袭。它瞪圆双眼,大嗥一声,那声音就仿佛喉咙里夹着一块骨头。小山只好放弃拿回木棍的念头。
黄昏时,小山还在城外游荡。城外和城里一样没有炊烟。太阳慢慢地落向远处的平原,天空和大地也由此被它慢慢拉近。小山不想回城,他宁愿就这样永远地游荡下去。他看着那方方正正的县城和郊野,想起塾师所讲授的“棺椁”:“棺,内棺;椁,外棺。”现在,小山就夹在这两层“棺”之间,暗自怀着一种古怪的愉悦心理,鬼魅似地游荡。
这时,远远地,一家农舍的烟囱上,一束烟柱躲躲闪闪地升了起来,就像一个小偷般犹疑,然而最终慢慢地、笔直地进入天空。尽管它又细又弱,却那样地明显。小山振奋了,他朝炊烟走去。为了给自己惊喜,小山故意低着头不去看它。过了很久,小山抬头一看,那烟柱却依然那么远。小山在心里不断地给自己解释:“那儿有烟柱,并且可以肯定是炊烟。它看起来之所以还有那么远,只是因为我走得太慢,只要不停地走下去,我就一定会到那里。”
大概到了半夜,小山终于来到一个村庄,素白的月光照着村街两旁密密麻麻的农舍,但村子里没有灯光,也没有任何声音。小山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这时,他看到了火光。在村街尽头的一所茅屋里,火光从墙壁的缝隙透射出来,通红通红的。门是开着的,小山走了进去,只见灶台上烧着一大锅水, “咕嘟咕嘟”地翻滚着,地上胡乱地躺着几个人,一个老人正在往灶膛添柴。
“老伯,你这是在做吃的吗?”
老人把地上的人都摇醒,然后回答道:“是啊,从傍晚起,我们就一直准备做羊肉汤呢。”这时,有两个人从背后抓住小山的手臂。小山立时明白了这一切。
老人得意地哈哈大笑,对大家说:“留着我毕竟是有用的,要不是我想出这么一个办法来,大家只有等死。”
其中一人不耐烦地问小山道:“你还有什么要求吗?我们会尽量满足你的。我们这样做,你不能怪我们。”
“我只是想喝口羊肉汤。”
大家都忍不住笑了:“愚蠢!有羊肉吃,我们还杀你干什么?”
小山不甘心地说:“那你们烧这么一大锅水干什么?”
“等你下锅啊。”
小山沉默了,过了一会儿,说道:“今天,我从城里出来,就预感到我会被吃掉,特别是被那只野狗打败后,连棍子都拿不回来,我就知道没用了。我朝这儿走来,只是不甘心而已,只想有个了断。现在,我终于走到这儿,看见这炊烟,这火光了。”
小山停了下来,大家的脸在火舌里忽明忽暗。
“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们吃掉我后,把拉出来的屎放一块儿,用来培植一棵小树。我希望给自己留个标记——要是没有小树,一棵草或一块苔藓都行。”
一个县令的作为
今天,我那沉寂多时的县衙来了一位老妇人,说她的儿子出城好几天,至今未归,请求县里派人去追查此事。临出门时,她突然放声大哭:“他一定死了,他一定被吃掉了。”
我叫上几个捕快,骑着仅剩的一匹老驴,准备出城。我们走在寂静的街道上,躺在廊檐下的人们都站了起来。我很久没有出城了,也很久没有和他们见面,看到这么多饥饿的眼睛盯着我,我赶紧用力踢打老驴。可它就是不肯走快点,看到大家都注视着它,它还自鸣得意呢,想尽力延长这种荣耀;也许它被吓坏了,因此才走不快。
本来,我可以从驴背上下来,这样能走得更快,但我没有跨下驴背尽快地走出城门,那只是因为我所害怕的事发生了。有几个老年人相互看了一眼,迟疑了一会儿,走到街上,迎面跪下来,口中喃喃不清地说:“老爷,老爷,救救我们吧,给一点儿吃的吧。”
这个问题总是在困扰我,可我一直解决不了。我假装没看见,想从他们身边走开,可人们纷纷走到街上。这还没有完,妇女们拖着小孩从屋里走了出来,一边走着,一边把她们干瘦的手臂露出来,希望我能看到她们暴突出来的青筋。人们仰着焦渴的脸,将我和捕快围住了。
捕快们喝道:“怎么?你们想威胁老爷?”
看得出,他们在虚张声势,根本就无心考虑我的安全问题,只不过有我在场,他们不得不敷衍一下。我止住他们,从驴背上跨下来,把缰绳交给那几个老人。人群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马上,他们就兴奋起来,抬起那头驴,簇拥着走向县衙前的广场。老驴支着又高又尖的耳朵,瞪着双眼,回头看着我,还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人们在广场支起大锅,将那头驴做了肉汤。
城外的荒郊那么大,我们这几个瘦骨嶙峋的人来到这儿,就如同一撮灰掉进灰堆里,消失得无影无踪,又怎么去追查那件案子呢?即使追查出凶手,又能怎样呢?他说不定巴不得我们把他杀了呢。吃人容易中毒,有时甚至会带来死亡。凶手必须把肉皮烙得起泡,把泡刮掉后,还得细细地清洗,这样,肉吃下去才不会中毒。凶手肯定没有耐性去细细地洗肉,多半是胡煮一通,就吃起来;说不定他都厌倦了,干脆躺在一旁,让自己和肉一齐慢慢地烂掉。对这种人,我又能怎么办呢?杀一儆百?大家都在等死,又能“儆”谁呢?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应承那老妇人,现在连驴子也没有了,我干脆和捕快一起回城了。
县衙里养有四匹好马,都膘肥体壮、毛色光亮。我竭力养好这四匹马,主要出于以下考虑:第一,这四匹马实在是生气勃勃,我不忍心杀它们;第二,在死气沉沉的今天,我想保留这最后四个健壮的生命,定期地牵到街上去游行,以唤起人们对生命的记忆和热爱;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把它们留做传信之用,必须和总督大人取得联系,请求援助。当晚,我决定给三边总督写封紧急公文,明天派人骑马送去。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派衙役告知人们,说我已派人去向朝廷求援,大家要振作起来,别失去希望,因为只要朝廷的援助到达这儿,大家就能活命。如此这般反复鼓励大家,衙役走街串巷地打着铜锣,把我的话传给大家。人们变得兴奋起来,都纷纷走向城墙目送那位信使。这天早上,信使特意漱洗洁净,还把以往的干净衣帽穿戴好。他接过公文,抖擞精神,大步向在街心上等候已久的白马走去。阳光照着他,熠熠发亮。白马载着他,扬起一团灰尘,迅速地向荒郊跑去,这团灰尘越来越远,越来越小,一直融入黄得发亮的大地,慢慢地消失了。——人们这才三三两两走回家,等待救援的到来。
一个月过去了,没有丝毫回音,我只好又派遣一人一马去报信。这次,人们不再关心,只是躺在廊檐下,看了几眼在街心上飞跑的马匹。一个月过去了,又一个月过去了,仍然毫无消息,而我已发光了我的马匹。发送第三匹、第四匹马时,我已不抱希望。我心里明白,它们会和前两匹马一样消失得干干净净。
他们四人一定是连人带马被吃掉了。我所治辖的这个县方圆几百里,他们刚出城时,人强马壮,又满怀希望,当然显得生机勃勃,沿途的村民也奈何不了他们。但跑不了一百里,就会人困马乏,路边又没有可供打尖的饭店,他们人单势孤,自然会被村民吃掉。没有人能走出这个县。朝廷一直不知道我们的情况,即使全县的人都死光了,朝廷也不会知道。只有到了明年十月份我县还没有缴税饷时,朝廷才会想起我们,派使臣来将我押送入京,交大理寺问罪。到时,使臣看到的只会是一堆堆骨头——甚至连骨头也不会有,在他眼前的只是一片荒地,没有任何生命或生命的记忆——甚至一株草!而在后人看来,我们同古楼兰王国一样,神秘地从大地上消失了。
开始我还抱着一丝侥幸,要是巡抚大人来我县检查吏治,那我们的情况就可以上达圣聪了。但我马上就否定了这一想法。巡抚大人不会来我县检查吏治,因为我县的穷苦是众所周知的,官吏根本无法去贪污,而且他来这儿也得不到供奉。即使他来了,也走不到我们这儿。开始几十里路由于随从众多,随从们又都带着亮闪闪的刀枪(必须承认,在阳光下,这些刀片是很亮的,而且威风凛凛),村民们决不敢行凶,甚至还会恭敬地给巡抚大人行礼。但走不了一百里路,他们就会由于饥饿和困乏而无力抵御。先是随行的牲畜、坐骑越来越少,后来,人员也慢慢变少。大概在我县行进了一百多里,巡抚大人会发觉轿子不动了,他大声喝叫轿夫,良久,没有人答应。他纳闷地走到轿外,就看到一群手拿锄头、木棒的村民,路边烧着一大锅开水。然后,人们就举着手舞足蹈的巡抚大人,把他扔进大锅做了肉汤。
抓阄的结局
城里的人越来越少,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尽管我成天躲在县衙里。也不知在里面躲了多久,有一天,我终于想起那廊檐下的人们,不知他们还剩下多少?我走到街上,整个县城空荡荡的,见不到一个人;挨挨挤挤的房屋还和以前一样,只多蒙了一层尘土。我来到城外的荒郊,没有一丝风,仿佛什么也没发生,甚至时间也忘记这儿了。那些农舍,歪歪斜斜地还在。我想去那儿探听一下情况,或许能找到活人。在半路上,我碰到一个人,他躺在路中央,一双手不停地往肚皮上撒土。我问他县里人去哪儿了,他拍拍肚皮说:“都在这儿呢。”
他显然憋很久了,见到我,话就像泄坝的水一样,从他嘴巴里往外淌:
有一天,村里的人不约而同地聚到社庙前。村长把我们男人招到一块儿,说他有办法了。大家都来抓阄,每次选出一个人来做肉汤。为了表示公正,村长用力拍着胸脯,说他也和大家一起来抓阄,而且做阄的木片也由五位耆老去做,他决不插手。老爷,因为我们都有可能找到活路,而且这个办法又很公正,大家又能够天天聚到一起了,就像元宵节舞龙灯一样,非常喜庆,我们男人立刻同意了。不过,我们劝村长就别抓阄了,因为一个村不能没有村长,而且他又为我们费尽苦心想到了出路。村长大声抗议:“我难道连死的权利也没有吗?”这句话说得既有分量,又有道理,我们便不再劝他,但大家都受到了感动,纷纷表示,抓阄的事由我们男人去做好了,妇女就用不着抓了。妇女们正聚在场地的那一边,叽叽喳喳地商量着什么。我们过去把这决定告诉给她们,她们坚决不同意:“凭什么不让我们抓阄?当然,我们不能咬定这是阴谋,但毕竟让人感到纳闷。让我们也来抓阄,我们和你们就变得一模一样,我们也就放心了。”
当时,我们还商量好,白天太热,都回家里睡觉,晚上天气凉爽,大家聚到社庙的场地上。篝火照得大伙的脸通红,水在锅里咕嘟咕嘟地滚开着。被选中的人,悄悄地和厨手走进庙里,不久,肉块切好了,就拿出来做汤。小孩们在场地上欢叫着到处乱跑,老人们围着篝火谈家常,谈鬼怪狐狸精。那时,村子里是多么地安宁呀。后来,村里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就到其他村去转悠,教给他们这方法,可我老是抓不着汤阄。整个农村我都走遍了,我想,城里也许还有人,和他们去赌一次吧。我刚走到这儿,就碰到一个人从城里出来,他告诉我,城里人也都在抓阄,被他吃光了,他正准备去农村找人呢。
“于是我俩又抓了一次阄,结果就只剩下您眼前的这个人了,老爷。”
南岳
天快黑的时候,伯伯从南岳赶回来了。他歪歪扭扭地走了进来,一直从堂屋走到灶屋,把门槛踢得“砰砰”作响。他就像只破水袋似的,磕磕绊绊地走了回来。当时,奶奶正在往灶膛里添柴禾,烟子呛得她不停地咳嗽,咳得就像只风箱,眼泪都流出来了。伯伯一见到奶奶,他忍了多日的一肚皮泪水,终于哭了出来。他本来一直忍着没有哭,但是,一回到家里,他就哭了出来,就仿佛在他的心里打下一眼井,泪水汩汩地往外流。
本来,奶奶不同意伯伯带婶婶去南岳进香的,但婶婶一定要去,她躺在床上滚来滚去,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南岳圣帝,奶奶只好同意了。可这又管什么用呢?婶婶还是被阎王派人收走了。
从去年冬天起,婶婶就不停地咳嗽。开始的时候,大家都说这是地气太寒,钻到婶婶的心里去了,来年开春时,阳气会旺盛起来的,到时她就没事了。开春后,田埂上冰碴子都“嗦嗦”地融掉了,黑黑的泥土又软又黏,在脚趾间钻来钻去;天气非常暖和,可婶婶的病却没有好起来。她躺在床上不停地咳来咳去,不停地往木地板上吐痰,一大块一大块地往外吐,床下积了一堆又一堆的痰,人一走在木板上,它们就颤巍巍地抖动着,就像魔芋豆腐。奶奶不停地往痰堆上铺灶灰,灶灰刚开始时又白又干,可过不了一会,马上就变得湿乎乎的,粘成一团了。奶奶不停地往外扫痰,可地板刚扫干净,还来不及干,婶婶就又开始吐了,她张着黑洞洞的一张大嘴,一块块地往外吐。奶奶忧虑地说,婶婶的血气都化成痰了,等她把痰吐干净,血气也就耗干了。
刚开始的时候,家里的老鼠都被婶婶的咳嗽吓坏了,每晚它们从地洞里探出脑袋,一听到咳声,就吓回去了。可时间一久,它们不仅习惯了这一切,甚至公然藐视起婶婶来了。它们成群结队地在木板上走来走去,钻进谷仓里偷谷子吃,不停地咬木板、磨牙齿,磨得“咯吱——咯吱——”作响。婶婶躺在床上,吓得一动也不敢动。老鼠在谷仓里闹够了,就跑到婶婶床上,窜来窜去。它们的脚上、毛上和嘴巴上沾满了痰,在婶婶的头上和手背上踩来踩去,有些老鼠还用尖嘴巴掀开婶婶的嘴唇。
对于这一切,婶婶又能怎么办呢?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老鼠在她身子上面作威作福,她没有力气驱赶它们了。她一天天地消瘦下去,脸变得又青又灰,脸上的肉也被一丝丝地抽走,眼眶又深又黑,就像两个灶洞似的,黑得吓人。她的皮也越来越松垮,越来越干皱,就好像一个皱皮袋,里面装了一堆叮当作响的骨头。大家心里都明白,婶婶的阳气正一点点地被鬼收走,她正在一步步地往死路上走。
为了不让老鼠把婶婶吃掉,为了把婶婶从死路上解救出来,堂哥说,让他陪婶婶睡觉吧。他睡在婶婶的脚那头,把婶婶的脚心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肚脐眼上,让自己的阳气一丝丝地顺着婶婶的脚心往上爬,爬到婶婶的心里去,这样,鬼就不敢来收魂了,他也就会有妈妈了。但婶婶还是没有好起来,她一天天地病下去了。夏天到了,她还把自己紧紧地裹在絮被里头,就像一条过冬的蛇蜷在里面,一动不动,手脚冰凉冰凉的。
婶婶说,南岳圣帝的第一个生日到了,她要去朝山,或许去南岳圣帝那儿化一碗仙水喝下去,她的病就会好起来的。奶奶说现在天气太热,劝她等到九月份再去,那时是南岳圣帝的第二个生日,天气也凉快下来了。但她已等不及了,她哭叫着说现在就去,她只剩下几口阳气了,等不到九月份了。就这样,她和伯伯两个人嘴里哼唱着朝山的圣歌,向南岳走去。伯伯搀扶着婶婶,走出村子,来到大路上,才发现朝山的香客有很多,密密麻麻地走在路上。大家低着脑袋,簇拥着往前赶路。太阳直筒筒地照着大家的脑袋,汗水顺着手臂往下流,汇到手指尖上,“嘀嗒——嘀嗒”地往下掉。人们一群群地往前赶,汗水就像下雨一样,一串串地往下掉,把路上的尘埃砸了一个又一个的洞。人们踏起一阵阵尘土,大家的耳朵里、鼻孔里,到处都是灰尘。灰尘蒙住了大家的视线,人们在里面不断地呼叫着自己的同伴。这时,有人唱起朝山的圣歌,另一些人跟着唱了起来,这伙人唱累了,另一伙人又接着唱下去。大家就这样流着汗,唱着圣歌,不停地往前赶去。
到了晚上,大家在路边生起了火,在里面添了艾草,把蚊子都熏跑了,它们挥舞着纤小的长腿,鸣叫着跑走了,来不及跑的蚊子则低垂着尖尖的嘴,一只接着一只地往下掉。大家一群一群地围着火堆,不断谈论着南岳圣帝显灵的事情,火舌一闪一闪的。地面经过太阳一整天的炙烤,热烘烘的,人们就睡在地上。婶婶把布包垫在地上作枕头;但她怎么也睡不着,骨头硌得生疼,她翻来覆去不得安宁,她坐起来,听南岳圣帝显灵的故事。
婶婶就是听了这些故事后,第二天才坚持要改成进拜香的。因为有一个妇女也得了婶婶这样的病,只剩最后一口阳气了,但她一步一跪地拜到山顶的正殿,病就好了。婶婶听着听着,眼睛发亮了,她许愿说,她也要进拜香。第二天赶路时,伯伯扶着婶婶,一步一挨地走着。婶婶跪了下去,又站了起来。她不停地磕头,额头磕破了,血还没流出来,灰尘就糊住了她的伤口,皮肉不停地烂下去,黑乎乎的。她的脸上、手上,全身上下都粘满了灰尘,只剩下两个深凹的眼眶还露在外面。伯伯扶着她,走得越来越慢。香客们一个接一个地从他们身旁走过,他们都低着头,不断地哼着圣歌,影影绰绰地,一个接一个地走了过去。
伯伯眼看婶婶不行了,劝说她回家去,但婶婶却死死地抓住他的手,不肯松开,怎么也不肯回头。她不断地向南岳圣帝忏悔自己的罪过,她流着泪,祈求南岳圣帝饶恕她救救她。她跪了下去,又死命地抓住伯伯的身子,就像抓住一根枯树干,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她的眼睛亮了起来,说听到南岳圣帝的声音了。她走路时也更有劲了。是啊,谁都以为南岳圣帝会救她的。奶奶每天在堂屋里给南岳圣帝烧化香火,他都爽快地领受了,没有一点为难之处,纸钱和线香都恭恭敬敬地燃着,一点烟子都没有,烧完后,还能清清楚楚地看到纸钱上的印戳,它们一个挨一个地趴在纸灰上。每次占卦,那两个竹根■都是一个朝上,另一个朝下,紧紧地趴在地上,端端正正是一个圣卦。奶奶还在神龛角落里放了一碗米饭,那碗饭静静地躺在那里,一动不动,颜色一天天红了起来,味道却一点都没变,没有馊味。这种种兆头使得奶奶也宽下心来。
但婶婶最终还是倒了下去,她像具水袋似地倒了下去。那时,正下着暴雨,谁都没想到雨水会来得这么突然。乌云一团团地跑了过去,它们从身子里放出一条条火闪,雨水就哗哗地浇了下来。婶婶已走不动了,她的嘴巴大大地张开着,老是闭合不拢,就像刚杀的鸭子似的,张着嘴不住地喘气。她的裤子磨破了,两个膝盖骨兀兀地突了出来。她还在不停地磕头。她来到了回头崖,她额头上的血不停地渗到石阶上,很快就被雨水冲刷掉了。她额头正中的皮肉早已磨烂,里面塞满了尘土,这时雨水把它们都洗走了,露出白森森的骨头。但婶婶已顾不得这么多,就要到山顶了,就要见到正殿里的南岳圣帝了。她不断地跪了下去,额上的骨头在石头上碰得当当作响。
一群进拜香的香客围成一个圆圈,他们穿着紧身的玄黑衣服,头顶上缠满黑布,上面插着香火。他们唱着圣歌,不停地转着圈走动,香火的红火头在不停地抖动,不停地转动,汇合成一片恍惚的火点;雨点纷纷离离地溅在石头上,变成一片片明亮的水花。大家都没注意到,婶婶爬了过去,爬进圆圈里头去了。她跟香客们一起唱着圣歌,跟他们一起不停地转动。很快,她就倒下去了。她浑身浇得透湿,衣服湿沉沉的,死劲地把她的身子往下拽。就这样,婶婶像破朽的木屋一样,“喀喇喇”地倒下去了。伯伯站在人群外面,眼看着她倒下去了。
事后,香客们把婶婶放在柴堆上,放在柴堆的最上头。婶婶干枯到了极点,就像一束穿着衣服的柴禾,在上面一点也不显眼。火焰燃起来了,她随着柴禾一起噼噼啪啪地烧着。伯伯坐在旁边,一直没有做声,看着香客们做着这一切。他用衣服从灰堆里包起一捧灰,一声不吭,就这么走了回来。伯伯一路上都没有哭,一见到奶奶,他就哭了出来,奶奶摸着他的头发,不停地抚摸着。
这时堂哥哥带着他的一长串妹妹从山上回来了。他们看到了伯伯,他们没有多问什么,就明白了。他们昂着一个个圆脑袋,大声哭了起来。他们就这么不停地哭,眼泪从他们的脸上流了下来,就像流着一沟沟脏水。
一个由林场改造而成的高山农场
刚刚过世的表兄和我一样,都喜欢在马椎峁上种苕。因为马椎峁是块沙地,种出来的苕又甜又脆。每到农历九月,当太阳慢慢地落到峁下去的时候,夜风总会挟裹着沙粒,将焦枯的苕藤吹得东倒西歪,远远看去,就好像疯婆娘在乱晃自己的头发。
“这样好,这样的苕才有咬口。”表兄总爱这么说。
我很同意表兄的看法。农场里其他人把苕种在山窝里,虽然苕的个儿比我们的要大,但嚼起来松松垮垮,就像塞了一嘴巴的岩石粉。我们的苕则不同了,我们不把苕放在地窖里面,而是把它们摊在二层楼板上,让寒风吹够了,到冬天才吃。那时,苕身子变得结结实实,每吞咽一口苕肉,都要嚼半天,直咬得太阳穴发胀。
可令我无法想通的是,像表兄这样一个聪明的人,临死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蠢事:儿女们跪在他的床下,落气纸燃起来了,烟子从纸钱缝里慢慢升腾起来,他的脸皮开始变灰,他却开口讲话了,要儿女们在他死后,把他“种”在马椎峁。
马椎峁背后几乎就谈不上有什么玄武山,它孤零零地矗在那里,就好像刚剃了光头,脑后空荡荡的,没有任何一座山前来保驾;右边的煞手又像只饿虎似地扑了下来。——具体后果我无从知晓,但肯定不会是处好穴场。
出丧的那天,连山下的人们都来了。大家抬着棺材,朝天放着三股铳,就像一线蚂蚁,向马椎峁移去。穴坑早已挖好,人们把棺材放了下去,开始往上面撒土。孝女们嚎叫着跳下去,要父亲别离开她们。她们戴的尖顶孝帽在坑沿上时隐时现。旁边的妇女一边劝解,一边要拉她们上来。这时,突然下起了大雨,雨珠子就好像一口口唾沫似地砸在灰土上。人们慌了,七手八脚地往穴坑里撒土。孝女们哭喊得更厉害了,眼泪和着脏土不停地往下淌,仿佛春天发桃花汛时浑浊的河水进入了她们的体内,不停地冲打着她们。
那一天,我没去送表兄出门,但我非常伤心。这不仅是因为我将永远和他隔着一层土,更重要的是,以后再也没有人和我一起回忆农场以前的情形了。
那时,我们也有过好日子,不像现在,一到十月,所有的山坡都一片荒凉,石块四处耸立着,就像一个个巨大的鸡蛋朝着天空。天还没黑下来,夜风就跑到我们岭上来了,也不知它们从哪儿来的。有人说,山那边瑶人居住的岭上,有个蛇洞,风就是从那儿穿过来的。它本来是从蒙古那里跑过来的,它一路前来,刮过牛羊的尸骨和蒙古人的毡包,只要它经过的地方,人们都缩在被窝里,听着它从屋顶上刮过去之后,才敢出门收拾残局:掀落的瓦片,倾倒的篱笆,牛栏屋顶被刮翻的杉树皮……这就是我们岭上的夜风。它仿佛刚被刺瞎了眼,吼叫着从这个山窝跑到那个山窝,又从山顶跑到山脚。山坡上什么也没有,只有几株枯了的苞谷秆,像钢丝一般发出“咝咝”的叫声。夜风像条蟒蛇,身子紧紧地拧着山岭,它把坡上所有的土都裹走了,一粒不剩,就留下一块干土板,溜光梆硬,像一块没毛的干牛皮。
我们围着火塘烤火,谁也不敢出门。有时,夜风挟着土坷垃,重重地甩在墙壁上,把木墙板撞得“砰砰”作响。老辈人都说,当初开荒时放的火太大,把山给烧伤了,这是老天在讨账。真的,这夜风什么都要:松脱的瓦片,晒谷场上的衣服,甚至冻结在院子里的萝卜叶和鸡毛,它都一片不留地刮走了。
表哥带着他的两个儿子,在院子里手忙脚乱,把鸡和鸭子风风火火地往屋里赶。雄鸡伸着脖子四处乱飞,可它在黄昏时又看不清东西,总是撞在堂屋的门槛上。这是最后一只雄鸡了,如果它死掉的话,我们就再也听不到鸡叫声了,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农场将会彻底沉寂下来。表哥伤心地捡起倒在地上的雄鸡,怒气冲冲地咒骂着。但是风很大,话刚从表哥的喉咙里骂出,还没来得及到嘴唇上,风就把它刮走了,刮到那一望无际的天空里去了,干干净净,半点也不留。
“现在,它连话也不让我们留下半句。总有一天,它会连我们的记忆也刮得一丝不剩的。”表哥伤心地叹着气,夜风把他的衣服吹得胀鼓鼓的,仿佛在他体内装了一架鼓风机。
表哥总爱跟我聊天,因为,我们相互是对方记忆的“钉子”。通过我这颗“钉子”,表哥能把自己的记忆牢牢地钉住,把每个山头的原来面貌一丝不差地回忆起来。他历数着山上一株株的黄柏、油枞、拐枣树……就仿佛在清点着他手上的一条条掌纹。他总是叹息说,一夜之间,我们的山坡被人连山皮带树木一起都给“揭”走了。
那年冬天,乡长带着一班人马来到山上,他们放起了大火,火焰烧得树枝“噼噼啪啪”作响,野兔和山鼠惊惶失措地四处乱跑。野兔身上带着火,沿着山脊跑走了,而山鼠则只能在树根下四处乱钻,“吱吱”地叫个不停,终于,它们身上的火越来越大,火焰里传出一股焦臭的肉味。那一次,一定蒸死了所有洞穴里的青蛙和蛇。第二年开春时分,大家上来挖山的时候,不时翻出死了的黄土蛇和青蛙。青蛙翻着雪白的肚皮,朝着天空,一动也不动。乡长却得意地宣称:“林场里一切动植物都已歼灭,如今只剩下纯粹的土壤,我们将栽培出最纯粹的庄稼来,里面没有任何杂草,也没有任何动物的痕迹——甚至连麻雀屎都不会沾上一粒。”
就这样,我们的林场变成了农场,变成了“高山上的粮米仓”。我们的名气很大,方圆几百里的县领导都来参观,看这“最纯粹的庄稼”如何寂静地在山上生长。
那时,天下着大雨,通往农场的马路被冲刷得只剩下石子,白森森的就像马路的背脊骨。吉普车卡在水坑里,人们走下来,使劲推它,车轮在水坑里不停地转动,搅起来的水花溅到人们的脸上。人们不停地抹着脸,喊着号子,就像推一头赖在田里不动的牯子。
甚至连省里都知道我们,还派人来给我们录了像,在电视上播放。
但是,我们的日子却越来越不好过。庄稼一年不如一年。高山上的泉水冰冷得很,它们冷透了水稻的根,我们的水稻枯瘦下去了,像一根根野猪的鬃毛,就等待着完全瘦死的那一天。老鼠也跟我们作对,它们在土下面挖了四通八达的地洞,把我们的土豆、苕都搬走了,我们看到庄稼在土上长势很好,以为会大获丰收,实际得到的只有苕藤。它们连南瓜也咬,傍晚时大风吹来,攀在土坎上的南瓜藤带着南瓜左右翻转,我们看到南瓜背面老鼠咬的洞,黑乎乎的,就像谷仓。
山那边的瑶人怪我们的野兔跑到了他们那边,吃他们的苞谷,非常讨厌我们。甚至传言说,要是我们敢去他们那里,就要给我们送上几鸟铳。山下的农民也不喜欢我们,因为科学家在报纸里告诉他们:“植被遭到严重破坏,将会导致水土流失甚至泥石流。”他们一口咬定,是我们的泥石流冲烂了他们的猪栏,冲走了他们的猪。他们常常趁黑夜时分,上山偷我们的南瓜、苞谷和薏米。
这就是我们的处境,我们什么坏事也没干,但所有的惩罚全找上了我们。
我们的鸡因为没谷子给它们吃,每天一大早,就走了出去,到山坡上四处闲逛,希望能找只蚯蚓或者土蚕来润润嘴。山坡上的土块越来越硬,这使得我们的鸡拨土时也越来越费事。它们的脚趾和嘴变得又尖又硬,仿佛一把把刀钩。它们在消瘦下去,形销枯立,精瘦得如同寺院里的老和尚。母鸡也不再为我们下蛋了,有时,它会蹲在草窝里,非常痛苦地拉一个蛋下来,仿佛拉的不是蛋,而是一块石头,上面还沾着血丝。下完蛋,它也不再拍着翅膀打鸣,因为它知道,我们不会扔一把苞谷让它补补身子。如同完成一件任务,它匆匆忙忙地逃走了。
总有一天农场会完全沉寂下来的,到那时,只有寒冬时节的夜风在吼叫。
如今,表哥这颗“钉子”死去了,再也没有谁来给我把原来的记忆牢牢“钉”住。我的记忆在逐日地欺骗我,它们正在向农场现在的面貌一步步地靠拢。我伤心地知道这一点,但又无能为力。我已经记不起那棵杨梅树的位置了,当初,它曾给我们那么多的欢乐,虽然它结的杨梅比羊眼珠还要小,但它酸得够劲,能把我们脸皮里所有的水分吸到舌头上来,变成甜津津的口水。如今,虽然我对那棵杨梅树的存在深信不疑,可却不知该把它置于何处,仿佛它所处的是另一座山,那座山已被大风刮到天边去了,取代它的是现在这座丑陋、荒凉的山,——而我们却不得不在这座山上生活下去,无所适从。
我知道,我将变得和我们的青年人一样。在他们眼里,看不到一点希望,也没有任何美好的记忆。他们的目光黯淡,仿佛荒凉的山岭已进入他们体内。他们认为,他们生来就是如此,命运一直就在前方等着他们,无可更改。
从写作修辞到写作技艺(创作谈)
在我此前断断续续十余年的创作中,作品几乎全部是追求“惊艳”叙事效果的短篇小说。如果将短篇小说对应为动物的话,它最好是猎豹:身体结构的全部优点乃至缺点,都是为着极速猎杀这唯一目标而来。
在某种意义上,为了达到“惊艳”的效果,叙事需要从“常识”中逃逸出来,融合夸张、荒诞、隐喻、诗性意象、非线性叙事等诸多写作修辞来达成,给读者的眼球划一剃刀。我前些年的作品,基本上遵循这一美学追求。
随着生活阅历的增加,我逐渐感到,如果想将小说作为一项终身事业来从事的话,除了上述的写作修辞,作家更应发展出内化的写作技艺来。
对于写作技艺的追求,意味着作家需要真正融入传统、乃至创造出自己的传统。对于传统的追求,不是简单地从某一两位大师那里学习一套写作秘笈,然后突发性地让文学圈为之一惊,这固然能取得江湖式的成功,但也容易让作者本人走火入魔,在惊艳一枪之后,极易陷入写作难以为继的尴尬境地。
对有着终身写作意识的作家来说,写作成为对其个人才气的园艺过程,而不是对个人才气的放纵自流。写作成为劳动之一种,它会带来艰辛,也会带来健康的疲劳。一种原始的兴奋促使写作的发生,但这是一种有着高度自觉意识的兴奋,作家本人并不会兴奋过头,为写作、为作品注入过多和过高的意义。意义即资本,作家应自觉地避免成为资本运作高手。一篇小说作品,最珍贵的特性是“成器”,而不是“成道”。当然,这并不排斥读者会通过作品而体验到“道”。
为了让写作技艺不陷入尴尬的“空转”,成为有内容的技艺,作家需要关注自己的欲望、生活的经验、历史的经验,更重要的是他人的真理。如此,方能通“俗”。通“俗”,意味着丰富的人世内涵,也意味着作品的当代性。
写作技艺的修炼,意味着作家不自视为特殊者,而是像各行各业的手艺人那般坚忍地干着活,同时过着主流的生活。作家自有其特殊性,其特别之处不亚于环卫工人,也不亚于金融市场的骗子。但具体的特殊性的形成,有如树木动物在地层深处的“煤化”过程,而非作家主动套上某种形状的外套。
写作修辞的掌握,能让作家吃上青春饭;而写作技艺的修炼,则让作家成为真正的劳动者。
栏目责编:孙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