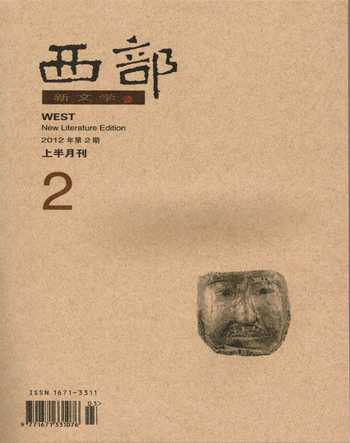有时候,姓虞的会成为多数
弋舟
我们租住的地方,理论上应该叫做城乡结合部,但现在很多事情,除了在理论上站得住脚,实践起来都会有些模棱两可,因为实践中的一切,都变得似是而非了,不再像石器时代那么泾渭分明。
这块叫做“雁滩”的地方,据说二十年前还是一片农田,当年兰城的男青年,稍微有些抱负的,如果弄上个“雁滩”姑娘,都会有些气短,被人问起,不禁就要含糊其辞,反应快的,随口会将姑娘们的出处说成是“城东的”。雁滩就在兰城的东边,这一点是不含糊的,就好比东京,理论上也是在兰城的东边一样。可事情说变就变了。今天的雁滩,哪里还见得到农田?全部是楼了。雁滩姑娘们摇身一变,都成了抢手货,因为卖了地,她们都成为了有钱人家的闺女。然而在理论上,此地依然是要被冷静地视为城乡结合部的,大批的外来者盘踞在这里,来来去去,就像当年的庄稼,一茬一茬的,等待着被这座城市收割。
像我们这样的寄居者,在兰城的雁滩比比皆是。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可目标却未必是同一个,当然你要笼统地概括一下,五湖四海的目标也能够被你在理论上总结成一条定律什么的。我们的房间在雁滩一栋四层小楼的顶层,四壁连带房顶都没有经过粉刷,预制板直接裸露着,楼面的外墙也没有任何装饰,倒是表里如一,那种水泥特有的灰白格调,让这一带的楼体呈现出一种堪称肃穆的气氛。周边几乎没有什么植物,一切都暴露在白花花的阳光里,到了夜晚,即便万家灯火,也显得是旷野无人。住在这里也有一种别样的好,那就是,尽管周遭甚嚣尘上,但只要你认得几个字,或者有一颗还算焦虑的心,那么,你就会感受到某种非常突出的宁静之感。
我们一共是四个人,我,小王,小虞和老虞。我姓李,被大家唤作小李。大学毕业后我就在雁滩这个范围内辗转栖身,白天乘车去市里面打工,暮色四合的时候跑回来挤进架子床睡觉。最让我难以释怀的是,我常常需要把自己在夜晚投奔的那个地方叫做“家”。下班的时候,跟同事们打招呼,不免要说“回了”。可是回哪儿了呢?回宿舍了?回出租屋了?都不大合适,好像也不太符合汉语的规范,约定俗成,也只能大大咧咧地吵吵:“回家了回家了。”这么吵吵完,自己的心里不免就会有些发虚,因为毕竟是夸大其词和虚张声势了,其后的归途,就会感到有些凄凉。
小王年纪与我相当,也是大学毕业后混到雁滩来的。余下的二位,本来也乏善可陈,大家不过是五湖四海,不过是萍水相逢,但好玩的是,他们居然都姓虞。关于姓氏,我们能说些什么呢?你看,我姓李,据说这个姓如今已经是第一大姓了,如果谁当街大叫一声“老李”,估计应者云集,会有不低的回头率。小王也比我差不了许多,我打工的那家公司,就有十数个小王。可是,在我们蜗居的那个二十平米的狭小空间里,我和小王,居然成为了少数。我们的另外两个同屋,都姓虞。为了将他们区别开,只有把年纪稍大的那一个叫做了老虞。老虞其实也不老,只比我们大个三两岁,可是没办法,谁让我们遇到了这种状况呢?——有时候,姓虞的会成为多数。
“对于老虞这个人,你们了解多少呢?”有一天小虞向我们发问。
是啊,对于老虞这个人,我们了解多少呢?这么说吧,最先被压缩进这个二十平米空间里的人,是我和老虞。我们在一个夏日的午后循着楼外张贴的广告不期而遇,我眼前的这位乍一看还是蛮普通的,就像所有毕业三五年后依然没着没落的青年,整个人的外观,就是一种“城乡结合部”的风貌,但当时,我看着老虞,觉得他有些没来由的别扭。后来我算弄明白了,可谓恍然大悟——原来这个老虞是把衣服统在裤腰里的。这应该是老虞让我别扭的地方。说起来也没有什么充分的理由,衣服统在裤腰里,本来不是个问题,但不知道有谁统计过没有,把毕业三五年依然没有着落这些因素都参考进去,这样的一部分年轻人,有多少会是将衣服统在裤腰里的?老虞他栖身雁滩的出租屋,谋生于一家卖汽车配件的小公司,天天骑一辆需要弓背塌肩的自行车,行程大约都在五十公里上下。这么一个人,却像写字楼里的小开一样,习惯把衣服统在裤腰里,可不是他妈的有型极了?
后来小王加入了我们的队伍,再后来才是小虞。没什么可说的,我们四个年轻人已经将那二十平米最大化地分摊了。被分摊了的,当然还有我们捉襟见肘的购买力和没有着落的人生。这样你就会明白了,为什么我会在这间出租屋里感受到非常突出的宁静之感。因为我已经极大地分摊了自己,把什么都匀了出去,涣散了,不宁静才怪。
所以从理论上讲,我应该是最了解老虞的人,毕竟是我俩先占领的这二十平方米。但我也不能肯定,这个小虞会不会比我和小王掌握更多的材料,谁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呢?——在这个狭小的罐头瓶里,两位姓虞的成为了多数。他们会由此更亲近一些吧?于是我和小王就自觉地将小虞的发问当做了一个设问句,认为他一定是要自问自答一番的。
果然是这样。以下就是小虞给出的答案:
老虞他其实挺孤独的(可我们几个缩在同一罐头瓶里的年轻人,乃至满雁滩的人,乃至全兰城的人,乃至尘世中的所有人,有谁是不孤独的呢?)。尤其被我们老虞老虞地喊着,就更让他和我们有了一些隔阂,他可能会觉得,本来还算年轻的自己,莫名其妙一下子就苍老了吧?就是说,是我们把老虞喊苍老了,是我们把老虞喊孤独了。你们知道的,老虞几乎没有休息日,双休日咱们都还睡着的时候,他照例会扛着他的自行车下楼,出门。起初我也和你们一样,以为老虞的公司业务繁忙,或者这家伙兼了职,打了双份工之类的,可后来我知道了,不是这么回事。谁让我也姓虞呢?我当然要比你们更关心一些老虞。其实老虞他在周六周日这样的时候,和我们一样,也是无所事事的。他扛着车子下楼,出门,好像是要去上班一样,其实呢,他根本没什么事儿,不过是摆出了这么一副架势。唉,老虞干吗给咱们装神弄鬼呢?依我看,他就是这么个人,孤独呗。当然,我有时候也觉得孤独,你们八成也孤独过(何止八成啊?),可咱们基本上不会在星期天的早晨也把自己弄到街上去。你们要换一种方式来理解老虞。也许换十种方式,该不理解还是不理解,也许你们连半种方式也懒得换,老虞的事儿你们压根就不放在心里,谁也不能指责你们。关键是,谁都得承认,理解不理解一个不过是挤在同一间出租屋里的伙伴,原则上的确并不重要。谁管谁呀,就像老虞把衣服统进裤子里,即便再怎么让人看了着急,也只是他自己的事儿。
我跟你们说个事儿,你们肯定都没留心过。冬天的时候,有天夜里我上厕所,老虞在里面,门没关,他正站起来提裤衩,可把我吓了一跳——他居然把上身穿着的保暖内衣仔仔细细地往裤衩里捅。恐怖吧?就是从那一刻,我决心要亲近亲近我的这位老哥。
有些事儿我们没试过,不知道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就比如说,我们住在这二十平米的空间里,本来算是个挺稀罕的缘分,可大家谁都没有尝试过要彼此亲近。太累了,跟人打交道太累了,大家天天回来的时候都是一副大势已去的狼狈相,谁还打得起精神给别人示好?可是如果有一天你们试着拍下对方的肩膀,没准儿对方也会亲热地捅你一拳。当然,拍下肩膀、捅上一拳也没那么重要,大势照样还是已去。反正老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主动接近他,不过就是多点个头,打个招呼什么的,他就有一出没一出跟我讲了些他的事儿。
下面这些事儿,就是老虞说给我的:
有一个周日,老虞出门时咱们照样睡得东倒西歪。把自行车扛到楼下,老虞思考了一下去向,然后骑上车子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转起来。谁能想得到呢?周日的清晨照样会形成上班的高峰——我们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安息日啦。自行车在街面上汇聚成一股洪流——这还是让人有些想不到吧,原来我们依然活在一个自行车的王国里,尤其在每一个含辛茹苦的清晨。老虞裹挟在浩浩荡荡的洪流中,因此也具备了方向感。他和清晨奔波的人们一同前进,一同追赶时间,东走西奔,渐渐地洪流开始消退,最后变得稀稀拉拉。清晨的空寂一下子突现出来,变得有些荒凉。
已经是十点多钟了,老虞仍在大街上骑行。这时大街上又渐渐热闹,但性质迥异,与那股胼手胝足的洪流相比,此时上街游荡的多是些闲散分子了。
骑到雁滩桥头时,老虞看到了那个卖糖炒栗子的家伙。一口大锅支在路边,一堆炒好的栗子上竖插着标价,露出“五元”,不知道下半截隐藏了什么玄机。老虞有一瞬间的踟蹰,他在盘算,买一斤栗子权作午饭是否划算。而且他也通晓这些小贩们的把戏——在标价上搞鬼,在秤盘上搞鬼,出其不意地讹诈一下没见过世面的人。不料摊主满脸堆笑地招呼他:“哥们,来啦!”说着用报纸包上一包栗子塞了过来。老虞没有推辞,自己不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人,这个他有把握,而且,有时候,我们内心的算盘总是会屈从于一包劈面而来的栗子。老虞坐到自行车的后座上,用两条腿支撑住平衡,一粒一粒剥食。他已经有了主意,待会儿撂下个十块八块的就走人——这正是老虞平常中午吃快餐的标准。
“怎么样?”摊主关切地问。这是个其貌不扬的家伙,长得除了像个卖糖炒栗子的,什么也不像。
“嗯,不错。”老虞不动声色地回答。
“那就好那就好,我真是有点为你担心。”
“什么?你说什么?担什么心?”
老虞一怔,感觉他们说的并不是同一个话题,对方可能并不是在问他栗子的滋味。
“酒精中毒啊!”卖栗子的顿足说,“那天你喝太多了,要不怎么会直接送到医院去呢。”
“你记错了吧,”老虞说,“认错人了?”
“别逗了,要不你就真的是喝傻了。”卖栗子的忧心忡忡地揉着自己的下巴,“老吴是怎么说的?小五你迟早有一天会喝废的,可不是吗,我看你就快被他说中了。”
尽管捧着一包栗子的老虞表情看起来是在说:嗨,蠢货,你他妈的认错人了,不过没关系,谁都有走眼的时候。但有那么恍惚的一瞬间,他真的感到自己被一股神秘的风卷走了,落在一个昏暗的小酒馆里,以小五的名义与这个卖栗子的还有一个什么老吴推杯换盏,劣质白酒哽咽在喉头,但依然无法阻挡内心那种卑微的、粗糙的、患难与共的温暖。
这时候两个打扮得很时髦的女孩走过来。她们都穿着那种底子很厚的鞋,窄小的短裙把屁股勒得紧绷绷的,上身是颜色漂亮的短风衣,两只背包背在各自娇小的肩膀上。她们从糖炒栗子面前走过去,又走回来。
其中一个说:“怎么卖啊?”
卖栗子的大概认为这样的顾客不适宜他的买卖方式,因此表现得不是很热情,指指那块韬光养晦的标价牌,眼睛向天上翻着。
“你没长嘴吗?”另一个女孩厉声喝问。
卖栗子的被吓了一跳,咕哝道:“你们没长眼睛吗?自己不会看。”
两个女孩对视了一下,让人以为她们会共同喊出两个字:扁他!
但她们只是对视了一下,然后异口同声道:“来一斤。”
卖栗子的伸手去包炒好的栗子,不料一个女孩尖声细气地说:“我们要吃现炒的。”
卖栗子的说:“这就是现炒的。”
女孩纠正他:“这是炒好的,不是现炒的,我们要吃那种边炒边卖的,你炒给我们。”
卖栗子的愣了片刻,大概觉得挺有意思,嘿地笑出声,然后就挥舞起一把铁锨,在那口大锅里翻炒起来。两个女孩不屑地撇撇嘴,她们不计较这个家伙的傻笑,她们要吃现炒的栗子。等待的时候,两个女孩开始议论起某件衣服的优劣。不好,太长,穿上像个嬷嬷。挺好啊,嬷嬷才好呐,性感。
而此刻的老虞,不可自拔地滞留在了那个昏暗的小酒馆里。这里面有污秽凄苦,也着实有一种很温暖的东西让他流连忘返,只是梦幻酒馆里现在多出了两个时髦的女孩,她们坐在另一张桌子边内容混乱地交谈着,正在说嬷嬷,突然一拐,就说起了某个明星。不喜欢,鼻子太短,还翘起来,像猪八戒。自己养的狗还不了解什么毛病,他就是想搞我,滚他奶奶的蛋吧,我有那么好搞?好像又是说某个男朋友了。
“现炒”的栗子炒好了,卖栗子的鼻头累出汗珠来。两个女孩接过她们的栗子,先各自剥一粒,其中一粒热气内聚,“砰”地炸开,惹得两人夸张地一阵尖叫。该付钱了,老虞很紧张,他想象不出卖栗子的恶劣把戏会在这两个女孩面前遇到什么打击。卖栗子的心里显然也没底,指向那块牌子的手指在颤抖,它已经露出了真面目:二十五元。两个女孩顾自小心地剥食着热栗子,你十元,我十元,其中一个再多翻出五元,全部扔在那口大锅里。这太令人失望了,好像憋足了劲一拳打出去,却打在一团空气里。卖栗子的又是半天回不过神,用不可思议的眼神瞅瞅老虞,随后他气愤地骂一句:“臭鸡!”
已经走出几步远的两个女孩同时回头,像两只凶恶的母鸡那样齐声断喝:“呔!”
这“呔”是兰城的用法,断喝出来让人显得很够劲儿。
卖栗子的不由自主缩了一下脖子,换上了一脸的无辜相。时间一下子凝固啦,是一个对峙的局面。两个女孩将信将疑地瞪了他半天才扭脸而去,叽叽咕咕地评价:“这货,长得像某某某一样。”
老虞终于将自己从那个小酒馆拖拽出来了,骑上车子准备离开。刚才他几乎要忘乎所以地陷入到一场纠纷中去。没人知道老虞的内心经历了一场什么风暴。他诧异地发现,如果那两个姑娘和卖栗子的发生冲突,那么毫无疑问,他会坚定地站在卖栗子的一边,并且拔拳相助也是说不定的。这也说得过去,喏,这个卖栗子的才对我们的老虞嘘寒问暖过,让他从满街的无良小贩中脱颖而出,成了一个与老虞貌似相识的人。但这个发现仍然让老虞不禁有些发抖,他基本上是个温顺的人,从来没有滋生过什么豪情,可刚才内心那股片刻的、气势汹汹的波澜,又是多么接近一种“豪情”的指标。老虞觉得他在那一个片刻热烈地介入到了世界之中。
卖栗子的在身后喊他:“这就走啦?少喝点,你少喝点啊小五。”
老虞作出了鉴定,这个家伙张冠李戴,里面并没有什么阴谋——他压根就没跟老虞要什么十块八块。老虞并不想纠正他,相反,他现在非常渴望自己就是那个被朋友担心着的、义薄云天的小五。
“老虞说他那天骑着车子在兰城打了个来回,”小虞惆怅地对我们复述,“有一股没法儿跟人说明的情绪让他一路迎风流泪,他不得不停下了几次,掏出手帕来擦眼睛——见鬼,你们没听错,我说的就是手帕,老虞他还是个裤兜里随时塞着手帕的人。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可是小虞啊小虞,你跟我们扯这些干吗呢?我,小王,作为两个听众,不禁都觉得有些尴尬,好像突然被人强迫了什么似的。何况小王这时刚丢了差事,正操心如何再就业。我们都有些拿不准,这个小虞一反常态地跟我们絮叨起来,是基于怎样的一种心情?
小虞好像是铁了心,有种要砸烂什么的狠劲儿,他自顾喋喋不休地往下说:
有些事儿说出来不像是真的,因为这些儿事儿会让人觉得难以理解。可生活里还是需要有些真实感吧?否则咱们可不是都活到梦里面了吗?——还他妈的是个噩梦。好比,咱们现在呆的这间屋子,总是真的吧?月租四百,每个人摸出的那张红票子总是真的吧?雁滩桥头总是真的吧?咱们天天从那儿至少打一个来回,这一点没谁怀疑过吧?好了,老虞就此每当途径雁滩桥头的时候,都要逗留一下,跟那个卖栗子的点下头,也没到拍肩膀捅拳头的地步,他不过是格外看重这家伙的那声叮咛——少喝点,你少喝点啊小五。
有那么一个阶段,老虞身不由己地活成了一个莫须有的“小五”。就是说,他觉得自己在被人牵挂,那感觉,就好像一个人在夜里,自己抱着自己,管自己叫:亲爱的。老虞他对这种感觉着迷啦,像是被一个命令部署进了这个角色。这个卖栗子的家伙是什么人?一定和咱们不是一路人。比如,他能把标价五元的招牌换成二十五元,比如人家一定住得比咱们好,挣得比咱们多,比如好歹咱们都有一张大学的文凭。可这些都构不成差别,我们之间的不同只在于,无论这个家伙是看走了眼还是犯了癔症,总之他能指鹿为马,热烘烘地牵挂自己的同类。这可能就是打动老虞的地方了。
我们读了大学,人生不过是一个人均五平米的格局,这么戏剧性地、徒劳般地空忙活,也许谁都会在途经雁滩桥头那种地方的时刻,灵机一动,望着桥,望着河,陡然生出些别致的念头。这不,那一天,老虞在周日又骑车来到了这个卖栗子的家伙面前,他们交头接耳了一番。可能这一天的老虞出门时并没有什么打算,那时候我醒了,他不过是看了我一眼,什么都没说,更没打什么招呼,可是我在心里跟自己说:老虞他这是要出去吃苦头哇。
然后你们都知道了,咱们的老虞就此不告而别。至于他干吗去了,遗憾得很,我也无从知晓,我只知道他是跟白胖子去了趟河南。半年后,他又回来了。
——老虞是在一个黄昏回来的。那时我们三个人刚刚挨过了一天,也是次第进屋不久,个个人仰马翻,不外乎是大势已去的架势。看到老虞,大家当然有些吃惊,但也只是面面相觑了一番,就好像他还和半年前一样,不过是推销了一天的汽车配件归来。大家眼睁睁地看着老虞爬上了自己的那张架子床。让我们觉得心头一紧的是,我们都发现了,老虞衬衫的下摆令人心碎地垂挂在裤腰的外面。于是谁都知道了,这个老虞在半年的时光里,便已历尽了沧桑。
交代一下雁滩桥头吧。兰城是被一条大河拦腰截断的城市,我们委身的雁滩,靠着一座雁滩大桥和城市的主体连接在一起。雁滩桥是我们每日必过的一条通道。曾几何时,我每次跨越这条通道,都觉得自己是蠕动在一根笔直的肠子里,清早被输送进去,黄昏被排泄出来。这种感觉使得我每次靠近雁滩桥头之际,都会觉得腹胀如鼓。
如今从小虞的嘴里,我们知道了老虞失踪的前传,那不能算作一个确凿的前因,也不是太有说服力,但是不知怎么搞的,从此每当我路过雁滩桥头,遥望这截城市的肠子,心里都会多少生出些巴望。我也渴望有一个随便什么破人,将我就地拦下,宛如一个奇迹,以一种我从未感受过的热情招呼我,然后平地起妖风,将我也裹挟到一种卑微的、粗糙的、患难与共的温暖里。这种事儿没什么好说的,我们这个被理论说明着的世界,在实践中,总是会时不时出些故障,事情通常就是这样达到平衡的,就好比,有时候,姓虞的会成为多数。
我们写作时的态度(创作谈)
读写经年,越来越认识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写作的时候,我是另一个人。这不是说,写作之余我就完全是一个两面三刀的家伙,我没那么自觉,只不过在那些时刻被浑噩地裹挟在了日常的道德评判与价值评判之中。而现代小说到了今天,还用说明吗?——那种对于日常的反动与冒犯,已经成为了它存在的基本价值。但是且慢,这样的表述本身便有问题。诚如贡巴尼翁所言:“现代性并不指向清楚、明晰的观念,也不指向封闭性的概念。”当某个概念指向了清楚、明晰和封闭的时候,已经与现代性背道而驰。那么我们换种方式吧,不说概念,说一说态度。如果说小说是一个想象和虚构的世界,这个世界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小说家写作之时以真实的态度和方式向已有的任何既定的“道德”边界提出疑问。如此冗长的句子,想说明什么呢?其实所谓“真实”,原本并没有那么玄奥,我们可以用一个小学生的认知水准来衡量这个“真实”,它大约是:不粉饰,不试图辩解。更进一步,我们以一个写作者的态度来丰富这个“真实”,还可以为它加上这样的说明:不试图走上某种轨道,更不试图以“反动与冒犯”的名义,建立某种新的道德边界。我之所以将此视为自己写作时的态度,不过是因为我惧怕将之奉为一项原则。原则这种东西太坚硬,诚如我们的生活,我们之所以提笔作文,无外乎就是为了抵抗这样那样的坚硬吧?如果生活的坚硬是一种“真实”,那么,我们的写作便是在建立“一种具有否定性的真实,存在和感受的真实”。并且,倘若“没有这样的真实,任何关于自我的征服都是不可能的”。听起来似乎蛮沉重的,可不是吗?写作岂是一件轻忽虚飘的事?如果我们有着一个写作者的起码自尊,都会承认,当我们进入到那一个“写作者”的自己时,必定是严肃的,恳切的,乃至沉重的。当然这不妨碍作品那种必要的轻灵,但至少我本人是怀疑的,一部有着“轻灵”之美的小说,可以出自一只吊儿郎当的手。才子我们已经见过不少了,这是一个才子泛滥的时代,并且不可避免,才子们在这个时代多少都会将才华用于了混世。不是说才华可以忽略,而是说,相对于我们今天的一切,矫枉过正,我们更应当盼望匠人。铁匠,木匠,锻工,镟工,乃至诗人,小说家。把这些行当放在一个序列里来考察,兢兢业业,严肃认真,这些根本的从业态度,想必是基本的常识吧?那么,我们写作时的态度,就以此为参照好了,因为,不如此,我们无以去质疑边界,无以成为日常之外的另一个自己,无以窥探与触摸“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