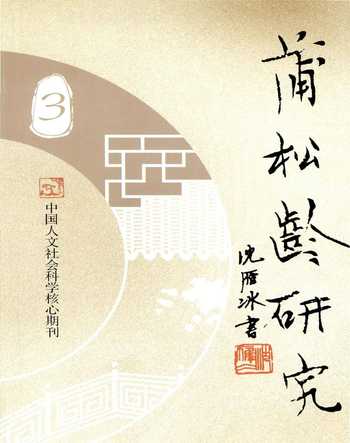《世说新语》的玄味、禅意、儒情和悟性
谭莹 史平
摘要:《世说》所反映的时代是一个充满玄学气味的时代,但又时时闪现着禅意和儒情。弱水三千,味异旨同,刘义庆在有意无意中又在显示和倡扬着悟性,《世说》实在是一部闪耀着多道光芒的书。本文将玄味、儒情、禅意、悟性分开来谈,是为了叙述方便,实际上这四者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常是以一种综合的形式出现。可以这么说:玄味、禅意和儒情是魏晋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三把锁,而开锁的钥匙却只有一把,那就是悟性。
关键词:世说新语;玄味;禅意;儒情;悟性
中图分类号:I207.41文献标识码:A
《世说》所反映的时代是一个充满玄学气味的时代,但又时时闪现着禅意和儒情。弱水三千,味异旨同,刘义庆在有意无意中又在显示和倡扬着悟性,《世说》实在是一部闪耀着多道光芒的书。
一、玄味注于探索哲理中
《世说》所反映的时代,其意识形态领域是以玄学为主要特征的,是“玄风独振”的时代,而玄学又是通过清谈来向外显示和加以深化的,这在《文学》、《言语》等篇章中都有集中的记叙。《言语》在全书中列第二,《文学》在全书中列第四,总体来讲份量也比较重,《言语》有108则,而《文学》也有104则,是全书的重头戏。玄学的创始人何晏与玄学大师阮籍、嵇康等在书中占有显要的地位。而清谈的内容主要有:有无之辩、言意之辩、声无哀乐论、养生论、圣人有情无情论、才性四本论等,从各方面“祖述老庄,立论以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世说》对上述问题都有涉及,如《文学》8记王辅嗣与裴徽对话:为什么老子对“无”十分强调,“申之无已”,王回答说:“圣人体无”但无又不可以为训,即无法全面解释,“故言必及有”,老庄亦如此,这实际上是生命起源问题,“万物之本”的问题。当时“贵无”和“崇有”成为争论的焦点。最后以“崇有”占上风,“万物非生于无,乃自生耳”。裴散骑在辩论大会上“理至甚微,”博得“四座(包括对手)咨嗟称快。”《文学》21记载:
旧云,王丞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
指王导精通“三论”,而且以之解释其他,成为三把钥匙,“无所不入。”但这三论究竟是什么内容,则没有详细记载。
情的问题,儒家主张“以礼节情”,道家主张“守性忘情”,《世说》则肯定纯情,赞扬钟情,以多个事例作了回答。《惑溺》2则记千古情种荀奉倩对妻子的一片深情:
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
虽然“获讥于世”,但这个“世”是指当时一般人而已,并非刘义庆所认同的。在刘看来,这种浓情却是感人至深的。王戎干脆明说:“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这表明情是不存在“无”的,只是因人而异。而有名望的知识分子正应该是情种。《文学》57大书无情论者王苟子的失败并灰溜溜地走了:
僧意在瓦官寺中,王苟子来,与共语,便使其唱理,意谓王曰:“圣人有情否?”王曰:“无”。重问曰:“圣人如柱邪?”王曰:“如筹算,虽无情运之者有情。”僧意云:“谁运圣人邪?”苟子不得答而去。
《世说》中还记载钟会专门研究“才性四本”的问题,写成《四本论》一书,想找大专家嵇康求教,但心虚,不敢面呈,“于户外遥掷,便回急走”(《文学》5),他的《四本论》是论才性的“同”、“异”、“合”、“离”的,也未必一无是处,但却不敢给嵇康看,可见该问题的敏感性、尖锐性。也有可能钟会的论文主旨是“才性同合”是为司马氏服务的,所以不敢面对正直渊博的嵇康。“四本论”后来的专家是殷浩,但他是真正的学术研究,《文学》34中记他理论的完备性,“无可攻之势”,连著名的高僧支道林与之辩论时都“不觉入其玄中”。
《世说》中记“玄”之处,都是略其内容,详其论述、清谈、论辩时的情态,各有风度、各不相让,针锋相对,妙语连珠。论辩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有众人对一,有一对一的,也有自己对自己的等等,论题正确(不存私念为自己的政见辩护),论述有据,还要风度翩翩、从容儒雅,才能取胜,得到大家的承认。
书中还记载了一些谈玄时的丑态,如强词夺理,胡搅蛮缠乃至破口骂人的,这都不得玄味,惹人厌烦,被当时人看不起。
由上可知《世说》中的玄味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对玄学核心理论的探索、阐述;一是对人生、对世间万物的认识和表达,这种认识的表达都充满了幽玄深远的朦胧之意,悲喜交织,哀乐难分,“不着边际”,“只可意会”,“妙处不传”,一是在辩论或行事中突出自然、潇洒的风度,“若神仙中人”,“明惠若神”,这样美妙的风姿、朦胧的语言、幽深的道理就使玄味更为浓郁了。
二、儒情扬于立德立功立言中
历来人们都说《世说》是一部清谈之书,确实它所反映的时代是以玄学为特征的,然而玄学只不过是它的表面现象,作者真正要弘扬的实际上还是儒家的立德立功立言之说,热情赞扬的还是儒情,也就是一种传统的、切实的入世精神和美好的道德情操。这首先表现在许多章节皆是以德居首。全书开宗第一篇就是《德行》篇,共列47条,起着统领全书的重要作用。对于德高望重之人,倾注了热情的笔墨,大加赞美。如《德行》第一则记载陈蕃“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并记载了他如何礼贤下士的美德。《言语》第一则也类似,写边文礼见袁奉高虽举止失措,但不失贤者之风。《政事》第一则记陈仲弓为官时,严重处罚“诈称母病求假”的人谓其“不忠不孝,其罪莫大”。《文学》第一则是记大儒郑玄超过老师而又智避迫害之事,赞儒之情特别明显,紧接于后的二条也都有关,一条讲他得知服虔也在注《春秋传》,许多想法与自己相同,他便停止了自己的写作,把自己已经注好的部分无偿地提供给服虔。另一条是讲郑玄家的奴婢都很爱读书,而且活学活用。作者在字里行间洋溢着赞美和敬佩。《方正》第一则是写陈太丘的儿子陈纪责备来宾不讲信用,违背礼仪,使他惭愧而去,《赏誉》第一则又是记载陈蕃赞扬周子居“真治国之器”,还具体地说周“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品藻》第一则也是记陈蕃的,记他与李元礼的功德究竟谁先谁后,结论是“陈仲举强于犯上,李元礼严于摄下,犯上难,摄下易。”所以陈在“三君”之下,李居“八俊”之上,比陈差一点儿。《贤媛》第一则更开宗明义地称陈婴“少修德行,称著乡党”如此等等,或思爱国立功,或思为民求安,或赞举贤授能,或斥奸佞贪婪……这些都是儒家忠孝爱民之情,都是儒家“立德、立功、立言”信条的形象演示。由此可见刘义庆对德行的重视,对儒情的显扬。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多处记载了这些名人对下一代的培养教育。有的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有的看到孩子进步很高兴,有的看到别人孩子好很羡慕。这种“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感情也是儒情。因而我们有理由说《世说》是一部洋溢着儒情之书,正是在赞扬立德、立功、立言。应该指出的是孔孟等所强调的儒情是纲常名教、君臣尊卑、孝悌忠恕、以礼制情等,人应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德、立功、立言”都有具体明确的要求,但秦汉以前比较灵活。《世说》所扬的就是偏于灵活的。纲常一字未提,名教只偶而说了一两句,如“名教中自有胜地”(乐令指责胡毋彦国等人公然裸体的),君臣关系也是宽谐多于紧严的,阮籍与晋帝,简文与桓氏即是。君臣还常常开开玩笑,“君有戏言”,“臣有漫语”(东方朔)。同样孝悌忠恕都是强调合理性,君王、主子滥杀(如石崇杀美人)都是作为反面例证。对“杀身成仁”者(如罗企生)则赞美之情溢于言表。至于情礼关系则明显反对“发乎情止乎礼义”,而提倡“发乎情,不必止于礼义。”王戎说:“情之所钟,正在我辈”,阮籍更是出格,可以与嫂子授受相亲,可以醉卧邻女身旁,并说“礼岂为我辈所设”,这都说明《世说》所尊奉的儒情是有选择,有发展的。
三、禅意显于心灵超脱中
魏晋时的“玄”是当时儒道的综合,但就其渊源来说,是偏重于道的,因为它直接由老庄之学发展而来,在《世说》中也有所反映。追溯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魏晋时期与玄学合流,它走的是先依附玄学、继而发展玄学、丰富玄学,最后取代玄学的道路。正是在这种互相交融又互相发展的过程中诞生了禅。生活在东晋后期的僧肇(374-414)将佛教般若学与中国玄学相结合,“取庄生之说,独有会心”,强调“用寂体一”,即体一如,静动相即,从形而上的本体转到主体人的实践方面来,“圣人乘千化而不变,履万惑而常通者,以其即万物之自虚”,“至人处有而不有,居无而不无”,这正是庄子“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理想人格的化合,实际上是老庄化的佛学。后来又经智顗(539-597)发展(创天台宗),提倡“定慧双修”,为慧能(638-713)创立禅宗奠定了基础,这是刘义庆以后的事了。所以本文只是谈禅意,是僧肇前后《世说》中所体现出的禅意。禅有着深湛高明的哲理,又有着豁达恬淡的人生智慧,它的意蕴不在文字中,而在于人的直觉和悟性。这种淡然、闲雅、自适、高远的人生境界就是禅意。这些方面在《世说》中也比较明显,其中的禅意也别有风味,当时主要凸现于淡漠名利中。书中有个不很起眼的人物——谢灵运(385-433),书中记载了他好戴曲柄笠,为人不解。但他却是位禅学大师,笃好佛理,兼通梵文,曾参与《涅般经》的润色,与慧远、竺道生过从甚密,曾据“顿悟成佛”旨义,写成《辨宗记》,调和儒释,指出人人皆可成佛。其《山居赋》直接描绘了生活和信仰,颇具禅意。另一位也很少提到的人是陶渊明,他的诗“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更具禅意。再如当时有位高僧慧远,一辈子“讲论不辍”,弟子如有懈怠,他就说,“桑榆之光,理无远照,但愿朝阳之晖,与时并明耳”,并即“执经登座,讽诵朗畅,词色甚苦,高足之徒,皆肃然增敬。”然而当时像他这样的“苦行僧”毕竟是少数,大多数的士人甚至僧侣则是执著于世俗红尘,他们追求一种隐于街市的生活,于享受放纵之外求一种心灵上的自由和超脱,于玄、佛、道中各取所需,找到自己的精神寄托和安慰,在世情的涨涨落落中寻得一种心灵的平衡与协调,获得一种“定性”。在他们看来,追求的是超越经验的内心自悟,外界的是是非非、风雨晦明、沧海桑田全是一片浑沌,合我心者是,不合我心者非,不需要格物,不需要分析判断,只需要人的心灵空灵澄彻时进行全副身心的直觉体验,就能向存在的本源突进,获得终极经验,得到对宇宙对人生的总体性根本认识。这种精神上的解放和自由就是禅意的获得。这在《世说》中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如僧人都喜欢与权贵、名士来往,有的还是皇帝的座上客,禅意自在其中。
竺法深在简文坐,刘尹问:“道人何以游朱门?”答曰:“君自见其朱门,贫道如游蓬户。”(《言语》48)
这说明当时追求的不是形迹而是心境,一味地修道求佛并不代表就能得道,如果没有慧根的话,那只是做无用功,如果具慧根灵性,一下子便能悟出其意旨所在,获得人生的大智慧。这种人生智慧的取得、禅意的领悟,主要见于当时那些思辨能力强、文化修养高的名士和高僧。他们能言善辩,风度好,积极参加各种社交活动,也追求享乐的生活,追求名利,即使佛教徒之间也争名(如支道林和于法开),僧人也养宠物,有的还特别得痴情,如支道林在知音殁后伤心不已,再也没有心思讲经辩论,而且日见苍老,仅仅一年后就去世了。这些看起来虽都是所谓的“俗情”,然而透过这种种“俗情”,他们达到的是一种超越世俗之上的意趣,那就是任心纵欲,真率自然,心游万仞,物我两忘,这就是禅意之所在。
四、悟性寓于日常追求中
禅,在梵语中是沉思之意。其思维方式的特征可以概括为:一、非理性的直觉体验。抛弃逻辑思维程序,大跨度的跳跃。二、瞬间顿悟,如闪电火花,突然触发,物我交融,升华解悟。三、不可喻性,不可言传,即使以动作、语言来表达,也是狂乱、含混的。四、活参。随意联想,天地山河,鸟兽草木,皆可体现答案、认识、奥秘。但不管怎么说,其核心问题是禅意的获得。而禅意的获得就靠悟。悟是一种直觉,特点是没有任何思维活动作为中介。《世说》是一部突出悟性的书,生动具体的事例很多,首先它专设《捷悟》一章,在《文学》、《赏誉》等篇中也有很多事例。可看出《世说》中的悟性包涵极广,不仅仅指禅意的获得,透彻理解生活中的一切都要“悟”。
(一)对学问的领悟。教者强调言约旨远,学者贵用心领会,如《文学》21记载王导讲“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然而“宛转关生,无所不入”,作为一个教者,他将自己所领悟到的“三理”加以阐发,几乎关系到人生的方方面面,可见王导是个极有悟性之人。至于为学者的领悟贵在心领神会,如《文学》64记:“提婆初至,为东亭第讲阿毗昙。始发讲,坐才半,僧弥便云:‘都已晓。”悟得可真快!别人才讲了一半,他就全知道了,从此也可看出人资质不同,领悟能力便不同。如乐广解释问题只用麈尾在桌上捣几下就行了。
(二)对事件的领悟。特别是一些隐藏天机的事,聪明的人能觉悟到危险性,马上采取正确的措施以免祸,如郗司空的上司正怀疑郗有篡逆意,而郗不知,上书陈述自己想有一番作为,儿子一看不对,连忙撕掉了,重写了一个表示自己老迈无能、请求退休的报告,上司反而消除了忌心,更加信任他了。(《捷悟》6)
(三)对人生的感悟。书中常常写到一些赫赫有名的将领,在事业旭日东升之时,却常常生出一种岁月无常、人生苦短之叹,如著名的“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就是一种对于人生的感悟。
(四)对自然美的妙悟。书中这样的记载很多,如他们常常谈到家乡山川之美、风景名胜之美、名山大川之美,“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的名句就是从此而来,可见他们对山水的流连之情。有时他们还用山水之美来比喻人,悟人之美。如此等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文将玄味、儒情、禅意、悟性分开来谈,是为了叙述方便,实际上这四者是不可分割的,它们常是以一种综合的形式出现,是“一石四鸟”式的,例如众所熟知的“新亭对泣”的故事,正有对自然的妙悟(风景不殊),又有对事件的领悟(正自有山河之异),国仇未报,也有对人生的感悟(人生易老,时光迅速),应当抓紧现在,共筹兴国大计,“当共戮力王室”就尽含其中了。诸如此类,往往是一个例子既有玄味、禅意,又有儒情和悟性,只是各有侧重点罢了。因为本来玄学、佛教、道教、儒学从一开始便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存、互相发明的,在发展过程中又不断地获得补充和完善,而对于它们的正确理解和把握,全都靠的是悟性。可以这么说:玄味、禅意和儒情是魏晋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三把锁,而开锁的钥匙却只有一把,那就是悟性。
(责任编辑谭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