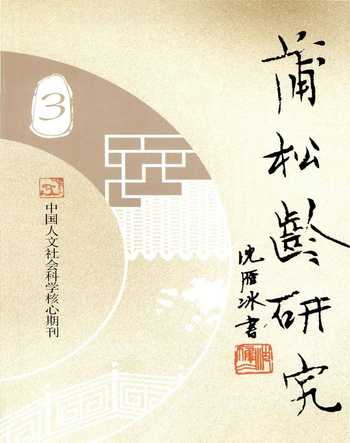漫谈《仇大娘》戏曲剧目(续)
李希今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续2012年第2期]
四、瓯剧《仇大姑娘》
郑朝阳于1981年改编的瓯剧《仇大姑娘》,完全不同于以上的三个传统戏。这个新编戏是以仇大姑娘为全剧的中心人物,设置了仇大姑娘与娘家人:继母邵氏、同父异母的两个弟弟仇福、仇禄,仇福之妻银风、以及仇大姑娘与外人魏明、赵阎罗的多种人物关系的矛盾纠葛与戏剧冲突,致仇大姑娘与其有利害关系的人物,发生大幅度逆转、发展变化,从而成功地完成了改编者全力塑造的仇大姑娘。
改编者为出场前的仇大姑娘设置的情境是:从事件上讲,仇大姑娘的父亲仇仲外出经商,途中遇匪下落不明,家财已被仇福赌博挥霍一空;嗜赌如命的仇福要将田产出卖还赌债,家中无人阻止得了仇福这败家行径。从人物关系讲,继母邵氏无力教其二子,更是娇惯仇福;才结婚过门数日的仇福之妻银凤无奈无助。作为情境的前史,仇大姑娘与其父、继母的关系,早从当初的紧张转为淡漠。用继母邵氏的话讲,是仇大姑娘“一向恨我入骨”,“赌气远嫁他乡去,从此不回娘家门”。用仇大姑娘的话讲:“离家二十年了!”“可怜亲生娘亲,一病身亡。老父因无儿子,继娶后母,是我年小不懂父亲苦衷,出言不逊,触怒老父,将我远嫁外郡。我一气之下,发誓永远不登娘家大门。”
此次,仇大姑娘赶回娘家,若不是老管家征得仇福之妻的同意,去登仇大姑娘家门,告知娘家的变故,接回仇大姑娘,仇大姑娘恐怕暂时还是不会回来的。况且数日前仇福成婚之时,仇大姑娘念亲情,尽管托人送来了银子以示祝贺,但是毕竟没来参加弟弟的婚礼。如此看来,二十年不曾回娘家的仇大姑娘此番登了娘家门,可谓“临危”受托。
仇大姑娘随老管家急速赶回娘家,初衷是为阻止仇福一再败家的行径。这也正是该剧以仇大姑娘为核心,及以仇大姑娘与仇福之间关系发展变化为中心情节之根。从全剧十场戏:惊变、堕落、分家、卖妻、引祸、遇父、买第、训弟、试弟、团圆,集中展现仇大姑娘与仇福正面交锋,致关系发展变化的是第三、七、八、九场戏。
在《分家》这场戏中,仇大姑娘与仇福一见面,先是以两个人物“打背供”的表演,彼此探视,力寻对方的心思。姐对弟本有心“狠狠骂来重重责”,想到“怕只怕,心急热粥难下嘴”,于是强忍性子没发作。弟见姐“脸白态凶人可畏”,本欲对姐讨好,却“怕只怕,拍马反被马踢腿”。接着,姐对弟单刀直入问道弟常去赌场,“还顺手吗?”弟不敢隐瞒,老实回答了姐:三天时间,就将“老管家带回来的父亲银子全输光,还欠下人家五百两银子”。这时姐以“不相信”为由,调出了弟的幕后推手魏明。姐在清楚弟已被魏明掌控、弟也完全依赖于魏明的情况下,想的是如何利用魏明对弟的影响力,尽力保住娘家的田产不再流失。于是,仇大姑娘在挑明这个家的田产中有她已故生母的随嫁田产,且她此次回娘家,要“长住不走”时,先使仇福原自认为他个人有权出卖家中的田产用以还赌债的打算落空。
继而,仇大姑娘抓住仇福急于还清赵阎罗赌债的心理,迫使仇福提出与魏明事先商议的办法:分家。他提出要以他该分的那份田产还赌债。此时,仇大姑娘眼见全部保住家中的田产已不可能,只得同意仇福提出分家的主张。至于如何分,是姐弟的一次较量。姐先摆明田产全在父亲名下,逼仇福主动提出田产分三份的方案。其结果仇大姑娘在被迫分家、这场与弟的交锋中,为娘家总算保住了三分之二的田产,为二弟仇禄及继母保住了母子二人活命的一份田产。当分家进入立文书程序时,仇大姑娘仍不忘牵住魏明,不仅让魏明代劳写文书,还让其以“中人”名义,抓住魏明也捺下了手印。至此,仇大姑娘在经历了想保住家中田产不成,转而力争到家中的三分之二的田产没有丧失,而且在“分家”的整个过程中,与对手的较量中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最终既应了仇福分家的意愿,也使家中其他人,尤其是继母邵氏也不能不认可、不能不服之理的分家方案。这一切充分体现出了仇大姑娘深谋远虑、足智多谋的个性特性。
在《买弟》这场戏中,仇大姑娘与仇福为主要矛盾的焦点,是为筹银赎父。情境是仇福逃跑流落在关外,恰与被劫父亲相遇,仇福为赎父回家来筹银。仇大姑娘既为年迈父亲备受艰辛难过落泪,又为“家产被败尽、无力筹借赎父银”焦急、发愁。此时,仇大姑娘提出的办法是:赎父的一千两银子,由姐弟三人分头承担。仇福欲外出挣钱,被姐阻拦。在仇福也承认他既不会种田,也不会做工,更不会做生意,甚至为此痛恨自己“平生不务正业”,以致沮丧之时,仇大姑娘提出由她“买弟为奴”,并须立下卖身文书,由老管家监管劳动。待仇大姑娘筹到救父的三百两银子,以及她为仇禄需付的三百两银子,她再为仇福拿出四百两银子,一并凑足一千两银子,再在限期内去赎父。仇大姑娘此举,虽然开始并不为家中人理解,甚至护犊子的继母,还为子成其姐奴隶与仇大姑娘争辩:“这三家财产,全是你管,他们哪有分文啊?”仇大姑娘当即驳继母:“仇福一份早被他赌光,是我在公堂上打官司赢来的,还有他什么家私?仇禄一份,还不够他读书吃用,哪里还有闲钱多下?你真不明白道理呦!”听了此言的邵氏,大概想到自大姑娘回娘家后,素日仇大姑娘不仅善待她这个继母,吃,喝,看病,还严加管教仇禄只读书,不干事,这个家全靠仇大姑娘一个人支撑。加之仇大姑娘摆事实,言之处处在理;又见仇福都甘心情愿由其姐安排他,因此,此时继母也只有认可的份了。由这场戏,突出展现了仇大姑娘内热外冷、善于运筹谋划的个性。
“矛盾的解决,不是第一个解决了,才来了第二个,而是第二个、第三个矛盾的出现,往往隐伏于第一个矛盾的解决过程中。作为艺术家能不能觉察它,不只关系作品的思想深度,而且关系情节结构和人物塑造的艺术水平。”(王朝闻《论凤姐》)这不仅从前面讲的那两场戏中能看到这点。同样在其后《训弟》这场戏中更见如此。仇福“为奴”半年,虽然他没有明着对姐抱有怨言,但是并非甘心进行“劳动改造”。作为其弟仇禄也不忍过着自己念书、兄长受“日里劳作”之苦,于是向他师父范举人“恳求借银”。范举人虽然“动情相助”愿“为仇福赎身”去救其父,但是他要当面与仇大姑娘说道此事。这样一来,仇大姑娘面临的不止是与仇福一个人的矛盾,还有好心办不妥事的范公子,一时糊涂的小弟仇禄,以及只晓得护犊子的继母的诸多矛盾。仇大姑娘再次以她的聪明才智,即以仇福之妻的“灵牌”给在场所有人上了一课,妥善解决了看似他与范公子的主要冲突。范公子在懂得了仇大姑娘的心思,理解了仇大姑娘一心为教育仇福改掉旧日他那好吃懒做、游手好闲、沉迷赌博的恶习,成为勤劳有用之人的良苦用心后,心悦诚服地收回了他原本为仇福赎身的借银;与此同时是仇福幡然省悟,认识到自己不该“逃避为奴”的错误,决心从此“重做人”,做一个“吃大苦”、“耐大劳”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继而是仇禄痛苦的自责;而此时尴尬的继母得到的是仇大姑娘命人“扶母安歇去”的优厚待遇。这场戏进一步塑造了仇大姑娘那锋芒毕露的特征里,隐藏着爱怜、温柔的个性特点。这两点本不相容,但在仇大姑娘身上却是互相依存的。这正是由仇大姑娘出于对娘家亲人们真挚、热诚的爱所决定的。总之,在仇大姑娘与仇福为主要冲突的矛盾纠葛中,关系不断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它经历了仇福对其姐由不知、误解、无奈、顺从、到释怀、理解、感激的磨历过程。最后,仇大姑娘才得以令仇福等亲人心悦诚服的结果。
如果说,仇大姑娘与仇福等亲人的戏剧冲突,主要从情和理上呈现出仇大姑娘的聪明才智、有情有义,那么,剧中仇大姑娘与魏明及赵阎罗等人的冲突、较量,则主要从理和法上呈现出仇大姑娘的沉着冷静、足智多谋的个性特点。比如在第四场《卖妻》的结尾戏,赵阎罗带众赌徒到仇福家抢仇福之妻银凤。尽管仇福在此前狂赌时被逼与赵立下了卖妻的字据,但是,到了眼见自己才娶亲不久的贤妻被赵等强夺时,他还是不忍、不舍了。于是,欲护妻的仇福遭到赵的拳打脚踢;被带上来的银凤,不仅对赵骂不绝口,而且拼命挣脱欲护仇福,结果是赵拔出匕首欲刺仇福,却刺到了银凤身上。仇大姑娘闻声,手拿菜刀带仇祥等赶来。“直奔赵阎罗。赵欲逃,被仇大姑娘抓住衣领,赵阎罗脱衣逃下。仇大姑娘追到门口,一想,回身在银凤胸口一摸。”当即命仇祥等人“快抬走”。紧接着“仇大姑娘把赵阎罗衣服搜索,摸出匕首和卖妻文书”。
正是由于仇大姑娘取走了在现场的这些证据,因此在紧接下场《弥祸》戏中,在姜屺岵为女状告传言中的“仇福杀妻”的公堂上,仇大姑娘又在仇福已被魏明连唬带骗出逃、赵阎罗拒不讲事情的真相情况下,凭着这些证据,迫使赵阎罗低头认罪。继而,仇大姑娘又以赵阎罗借银纵赌,连仇福老婆都被赢去,可见家财全落到他的腰包;如今仇福外逃,姜女生死不明,姜亲家着实可怜;望老爷责令赵阎罗归还仇福财产,若是姜女身死,供奉姜亲家;若是姜女未死,也好让他养老终生,直陈县太爷。其最终致县太爷做了如下判决:“有赵某者,绰号阎罗,乃赌鬼中之魁也。享赌鬼血食,掌赌鬼生死,刮赌鬼财,淫赌鬼妻;无恶不作,令人发指。故而人神共愤,必须诛之。食血者血偿;谋财者以财还。赵夺仇财已供认不讳,自应全部归还。”仇大姑娘代表仇家与赵阎罗的官司打赢了!这既保护了仇福夫妻,又夺回了仇福被诱骗的田产。于是,一个有勇有谋的仇大姑娘活脱脱立在了舞台上。
纵观全剧,它的“亮点”是仇大姑娘在父亲由改过自新的仇福赎归、全家同庆大团圆的喜庆时刻,竟不顾全家人真诚地挽留,毅然决然地在呈账薄给老父,表明“人变好,家业成,老父归家我告退。五年收支笔笔在,未取分文落自袋。”之后,她“空手来时空手归”的行动和动作。至于这个戏的意义,正如戏的尾声所指:“世上若有私心者,看完《仇大姑娘》应惭愧。”
以上四个层次不一的《仇大娘》戏曲剧目,除川剧本《巧团圆》不值一提外,其余同作改编本是各有千秋,但愿拙文对后改编者有点参考作用。
(责任编辑李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