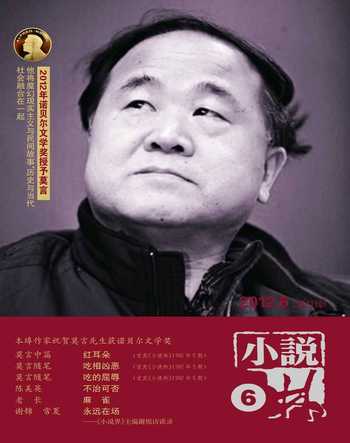小说诞生于对沉默的渴慕
刘立杆
按照普鲁斯特的说法,小说诞生于对沉默的渴慕,而不是相反。这种悖谬同样伴随着我的写作——非关意义或虚荣的泥淖。它更多源自一种贪婪,一种急切,一种想把自己从窗口抛出去的徒劳冲动。这足以证实,生活在别处的陈词滥调在小说里同样适用。
我不知道这个矫情的说法,能否作为自己当初突然放下小说的借口,那种类似文学乌托邦的幻灭感,和生活激情的丧失。事实上,隔了十多年重拾这门古老的手艺,我的困惑似乎被时间放大了。
小说的危机并非自今日而始,这种危机感延续到现在,已经不同于上世纪30年代本雅明关心的小说和“个人经验的凋零”,或是“生者深沉的迷惑”。今天的写作者是以互联网嘈杂、汹涌、无处不在的含混话语为背景的。交流和发声是如此轻易,经验的传达和信息的获得又是如此快捷,在一个每个人既是作者又是读者的时代,人们还想从小说里寻找什么?即使一个写作者的自大可以充满他的房间,大概也不得不受此困扰。更何况,自我如今已经成了一个令人徒增烦恼的贬义词了。
抛开这些大而化之的思考,在碎片化、数字化的世界里,我能想象的写作似乎就类似档案管理员的工作,他力图在堆积如山的资料中归纳、整理、分类、编目,却又因此倍感迷失和虚无:他渺小的工作越严谨,档案归置得越清晰,关注的世界就越模糊,生命就越苍白。这个多么有些丧气的说法,就是写作《每个夜晚,每天早晨》的基本感受——尽管我多么不愿意谈论具体的、个人的写作。
在诗和小说间频繁切换必然会带来两种文体界线的模糊,还有随之而来的紧张。我喜欢这种紧张感,又往往因此为规则、无知和个人才能的缺陷所误。比如在过去的写作中,回忆一度是我迷恋的基本主题——但那与其说是因为记忆的诗性本质,还不如说回忆经时间过滤的天然秩序让人安心。换句话说,我甚至还不能胜任一个档案管理员的工作。作为一个小说学徒,我还没有尝到虚构的乐趣。
最传统的说法是,短篇作为生活的横截面,必须具备钟表般精巧的结构。结构能力既是我小说写作中的缺陷,也是眼下这个阶段思量最多的。最近我甚至时常纠结于这样一个顽念:去研究一本毛线编织大全。而写这个短篇的初衷,多少是为一个开放性结构所鼓舞。在最初的构想系列小说里,位于南京拉萨路的那间房子就像一个舞台,各色人等在固定的视角里轮番登场;每个短篇既构成独立的一幕,又互相穿插、重叠,互为背景和理由。只要还有一个观看者,这个舞台似乎就可以无穷无尽地演下去。而我担心的,是如何从这些乏味的肥皂剧提炼出养分,如何从陈旧的故事发现生活新鲜的热气……我还需要不断对付自己时不时跑出来的厌倦,否则,有关人生的痛苦经验不过是堆无聊的呻吟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