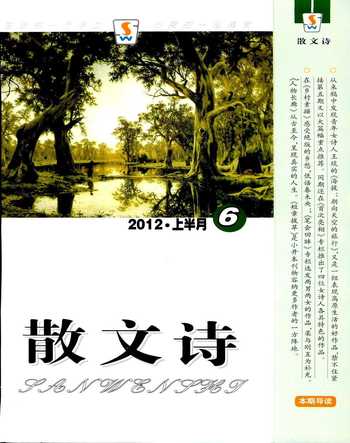2011年游记
韩若冰
岱音塔拉
沙漠,五角枫。四月的绿,稚嫩而狂妄。
安分的是敖包的石头,任春风的缠绵塞进每个缝隙。
石头的心,也是石头。
不像我,见到敖包,已经两眼湿润。
沙子,沾满我的面包片,混进我的蟹籽酱。沙子,从手背揉进我的眼睛。
我只能进一个陌生的毡房,讨水——
讨一群豪放的乡音,讨一碗羊汤一盏烈酒沙子。只是想,讓我的双颊更粗糙更绯红。
我没懂这个地名,也没懂敖包上方的钢叉、麻绳、红布,只是仿佛远古,已经注定我的到来。
合掌朝拜,之后,隐没于沙。我把围巾挂在科右中旗公路的枯树上,遥远,回头望。
像粉玫瑰曾经开放,就在岱音塔拉怀抱里。
葫芦岛
看过众多的海之后,觉得葫芦岛有一点冷。
五月,海风吹透我的棉布短风衣。
一种思念,如湿滑的绿苔,仿佛停止生长。
海岩沉默、坚实、洁净,好像不曾有人来过,特别是这样深的夜,半个月亮,面色苍白。
看不清脚印,看不清灰白的浪花怎样消失。
海,呼吸那么粗重,贴近我的耳根,贴近我的眼睫毛。我,已经冷得发抖。
远处,灯火温暖。
海的味道,盛在碗里;酒的味道,斟在杯中。
新的一天,已经从鲜美的宵夜开始。大海,被木炭烤热了瞳孔。
孟姜女庙
我知道,我哭不倒一块最薄的青砖。
我知道,再冷的日子来临,我也做不成那件针脚密实的寒衣。
我习惯等待。从劈开葫芦的刀刃开始,从秦时的第一轮明月开始。
等得山海关的草木绿了又黄,等得老龙头的潮水退了又涨。
等白了,我十六岁的黑发。
是我,成了这尊雕像。
站得骨头生疼,迈不开脚步。眼泪,再也不能流淌,呼唤,堆砌在喉咙口。
看堂前的燕子,飞来飞去的春秋。
瓦楞,生了草蓬;回廊,长了红锈。
是我,成了这尊雕像。
棉絮早就霉烂,在包裹里,抱在我的心口,飞雪的黄昏,我绝不哭。
我知道还会有天崩地裂,我不眨眼睛,我不抗拒粉身碎骨。我也无法抗拒,就像被注定——今生,我已经等不到你,等不到那一具白骨。
我只能一字不说,是我,成了这尊雕像。
笔架山
谁的诗篇没有写完,就沽酒去了。满眼都是绿。才迷路了吗?
短亭在哪里?哪里又是长亭?
锦州的海,好似盛了水的砚台,一直在等一块唐代的陈墨。
诗人,在笔架山口,挽起青衫的衣袖。
又不能久留。海水会在某个时辰,淹没惟一的路。这样,每一眼都很珍重。
一生,有多少这样的初相逢,匆匆。
别说再来,除非有那传说中的神笔,抹平大海,也抹平光阴,抹平一切原委和初衷。
回头时,太阳从容地西下了,喜鹊,很多,老妇人一般喋喋不休,关于蝴蝶的来世前生。
我不相信,山脚下这些高大的松树,经不住一个空洞的茧壳的轻重。
一定是风,从海上吹来,或者是那散发的诗人,不小心撞落了一支笔,和茧里的翅膀、五更的梦。
碣石镇
渔船,把大海拖走了。历史,把岁月带出那么远,只剩一块石碑和尘烟。
淳朴的小镇人,不知道锁二乔的铜雀台,和锁不住的清凉月色。
后来知道,许多杜康解不了的忧,许多老马到达不了的地名,就那么一生。
就那么一生,短在刹那,剑起剑落。
白了长须,旧了红袍。江山还在,美人留下无音的七弦琴,音入旷野。
传说就是传说,小镇还是小镇。
豆萁还在釜下,轻歌曼舞,火的颜色一直涂抹到赤壁那每一朵血腥的浪花。
红色,宛如英雄的相思,沾在刃口。
最后,成为一斑腐锈,随墓碑一同,出土。
阿尔山
漠河夏日的阳光,晒透了我的白衬衣和水晶镜片。我,毫不犹豫,躲进你的绿你的泉水。
细小的榛蘑,刚入夏,一片一片围坐在林阴里,松鼠的孩子,拖着美丽的尾巴,后退到草丛深处。
菟丝花,温柔绕指。每一棵白桦树,都睁大眼睛。听着松针轻轻落下……
红尘,飘在车窗里,泊在森林外。
这里是阿尔山的森林。我的魂灵,被蒸馏为一颗露水。停留在叶脉尽头。
如果真的被岁月遗忘了,就在这棵白桦树下,就讓白桦树的眼睛,安静地合上。
讓落叶覆盖夏季,讓厚雪覆盖我的头发。
桃花堤
我走不完这千里,又舍不得停下,桃花,落在我的脚步里,桃花,落在三月的回廊上。
如此短暂花期。
整个漫长冬季缝制的嫁衣,跌落湖心,昨天天天之色,你是谁的发妻?为谁憔悴如灰?为谁瘦弱如丝?为谁,夜里结子?
花瓣如雨,拍打我的视线。颜色,红得讓人眩晕。纷乱如麻,有风吹入这桃花的雨帘。
红流苏,抱紧我微凉的双肩,温暖着我,我不敢停下脚步。真的。
停下。我怕,我是这千里堤上的一株悲情的桃花。
盘山
这次登高,我终于承认自己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