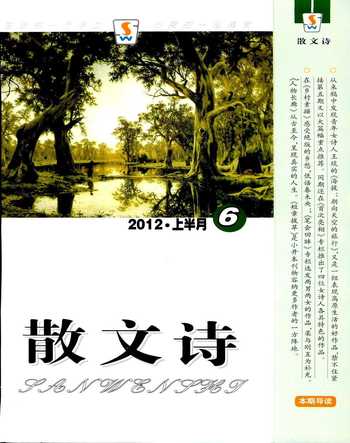绝版的乡愁
王文海
枝上乌鸦的啼叫像一个隐忍的笑话。
青草之上,黄土之下,月色之中。石头里开出的花叫死心,骨头里开出的花叫心死。我的亲人,不知化作了哪只蝴蝶或蜜蜂,使得这个春天依旧无法辨认真伪;低于心头的苍茫和高于山头的沧桑,让一只燕子徘徊良久,无法落下。
又想起一沟一沟拥挤过来的山丹丹花了,朴素的山谷顿时娇艳得手足无措,像涂满了红脸蛋的姑娘偷偷地笑,悄悄地用眼角瞄人。怕人看出来她的惊喜,又怕人看不出来她的变化,她局促、紧张、兴奋而忐忑,粗重的喘息让不规律的心跳成为春日的错别字,并且无法涂改。
我其实更愿意相信沟沟峁峁里藏着的真理。如一棵草或者一块石头的长久坚守,被一束阳光温暖起来的鸟巢,爬满了老年斑的柳树皮的微笑,抑或一只蚂蚁在寻找乐园的路上幸福地陶醉。泥土和草丛能教给我的,远远要比无数的教材内容更生动、更实在、更易贯通彼此的心灵。让无为成为一种境界,让无上成为一种高山仰止的风景。
永远不会再有年少的时光能齐眉我内心的茂盛。让炊烟软软地飘着,让暮色缓缓地罩着,让肠胃小声地歌唱窑洞内的灯火,让我攥着绳子背着一捆青草挪腾出的手慢慢擦去汗珠,让在村子西口的狗吠声掀起莫名的悸动。这是一天的尾声,担水的人晃着身子从雾色中走出,那些黑瞬间就缝补了他们撕开的裂缝,然后一切又归于平静,一切像从未发生。
想起我的姥姥时,散开的雾气又重新聚集。有时模糊反而让一切又都变得亲近而真实。说穿了。我对乡村的依恋,都被拴牢在姥姥永远忙碌的背影上。这个背影自己放大又缩小,她的气息布满了整个村庄的每个角落。我的记忆被拴在一只鸡满院子“咯咯”乱叫的兴奋里;被拴在那只猫良久窥视锅里食物的沉静里;被拴在一大缸的水满了又空了的重复里;被拴在躺在草垛上用一个下午追逐一匹白云的坚定里;被拴在田野里找寻鸟鸣的欢畅里;被拴在村西的一根小路上永世走不出的归途里。
童年里滞留的山村的印象对一生有多大的支配作用呢?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有发现,等我发现的时候已经完全是她的摸样了。我就是土炕上那把变秃的扫帚的样子;我就是窗户上新贴的最美的窗花的样子;我就是那盏扑朔迷离的煤油灯睁不大眼睛的样子;我就是院子里那块棱角分明的磨刀石的样子;我就是那只绵羊不知所措惊叫时的样子;我就是静静挂在门后等待收获的镰刀的样子;我就是那眼已干涸多年的枯井的样子;我就是那只喜鹊飞走时留下的空白的样子;我的身体里没有我,累计起来的是村庄酣睡的样子、走动的样子、打饱嗝的样子、忧伤的样子、欣喜的样子、麻木的样子。
村里的亲人熟悉的面庞一个接一个消失在风中,可是我还能清晰地听到他们走路时的动静,甚至他们的咳嗽声、叫唤一只小狗时的亲昵声。没有谁真正离开过村庄,他们都在一辈接一辈认真地经营着清贫的生活。村子后山坡上的坟堆越来越多,可是村子的热闹却有增无减。
对一根炊烟的命名会耗费我的一生。因为关于村庄,这是一门大学问。我越深入其中,我才会越感到自身是作为一粒尘埃在真实地飘动。一头驴的“厄哇”声,命运在交替显现。站在背光处,我看到哲学爬上了屋檐的高度。屋檐之上的苍茫和屋檐之下的幸福,是所有哲学命题绕不过去的二元理论。当一只老鼠半夜出来偷粮的时候,透人窗口的月光照出了那些蹑手蹑脚的身影,作为黑夜的引领者,老鼠的出现,是隆重而严肃的事件。它们洞穿夜色,它们贯穿村庄,它们是村庄不灭的灯盏。
狗吠声里,黄昏把村庄当作最后一笔水彩画收入画框。莜面、豆面、荞麦次第上炕,山药蛋、玉米面成为农人最坚强的风景线。冒着粗气的大锅是孩子们凝视的焦点。呼喇呼喇的风箱煽动着鼓舞和希望。连那只猫也受到感染,安静地伏在炕头,好似等待着巨大的喜悦。木门吱呀被推开,四舅给骡子们拔草,最后一个归来,他连手都来不及洗,抢先吃了几口腌咸菜,辘辘饥肠让灶台变得崇高而神圣起来。
这该是一天中最安谧和惬意的时光了。煤油灯下,姥爷又开始言词闪闪烁烁地重复那些似有似无的鬼故事;尤其是说到只离二里地的邻村发生的事情,我们紧张而惊恐的眼神总会望向窗户和房门。也会说到本村。这让我们夜里起身小解都不敢出门。可是渴望倾听的欲望战胜了无边的恐惧,从那时起确立了对神鬼的敬畏心情。长大后才渐渐懂得,敬畏神鬼,其实是人类在敬畏自身!
油菜花开的季节,村庄才显示出她的富裕。那些金色可以随意被任何人带走,可以带走田野的各种矿藏,带走蝴蝶的最初的迷茫,带走风里的传说,带走白杨树林边一位姑娘的眺望。
雪落北国。落在窑洞上、土路上,这时的村庄就如一幅安然的石版画,一动不动,安静得让人会突然心疼。只有村东头率先升起的一缕炊烟让好似睡着的村子醒过来,接着狗叫了,接着雪地上会留下轻轻的猫的爪印,接着有人干咳着出门了,接着石版画开始立体化了,接着大雪又下了一天一夜。
我至今都不知道那么多大雪都是怎么融化掉的?因为我以为那些大雪足够封闭住整个世界了。我以为大雪可以断绝一切的联系,甚至连春天也找不到来这里的途径了。我们好像暗无天日地在雪天里等待着。等待着看不见的机会。
忽然三两滴鸟鸣就从树枝上落下来,忽然静止的一切好似集体行动起来。后来离开村子多年我才明白,村庄的耐心和潜力是惊人的,村庄的生命力就如那些野草一样,枯荣有时,生命无期。
走千里走万里,总是走不出村子的叹息。在繁华的都市,我也总能听到一头牛“哞”的叫声;能听到一只母鸡下蛋后神气的呜叫;能听到日夜不停的那些聒噪的蝉鸣。天南海北的穿梭之间,面对满桌的佳肴,举起的刀叉总在空中顿住,那股悠悠飘过来的苦菜香味呵,不由自主中又让我泪盈眼眶。
现在才不断感慨,是村庄确立了我一生的信仰,是村庄教会我一生的知识,是村庄给了我的名字和道路,是村庄的诗意让我学会了歌唱。我是村庄飘落外面的一枚树叶,终究是要回到村子里去的。
回到村子里,就像回到了自己的身体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