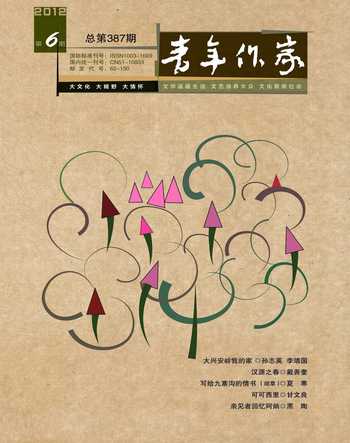故乡的老母柑
从我记事起,已人到中年的伯娘就一个人住在老屋。据大人们讲,伯娘年轻时也曾有个儿子。男孩怪伶俐的,长大后被伯娘丈夫带去见大世面,不幸暴病去世。丈夫过世后,伯娘成了“五保户”,享受农业社的救助。听人说,像她这样死了儿子后又死了丈夫的寡妇,对别人家有儿女是心怀妒忌的。然而伯娘却并不是这样,高兴时,她还挺喜欢小孩的。记得有一次,她给我们这些不懂事的半截子娃娃讲“熊家婆”的故事,又叫我们猜谜语,说猜到了奖励好吃的。那谜语的谜面是:“麻屋子,红帐子,里面住了个白胖子。”就这么个“花生”做谜底的简单谜语,只想着奖赏的我们,却怎么也猜不出来。不过,虽然没猜出来,伯娘还是将早已准备好的老母柑,每人给了一瓣。这一吃不打紧,倒把我们这些小馋鬼惹得垂涎三尺。也许是少吃则香的缘故,那一瓣清香、鲜甜而又略带酸味的老母柑,竟然引发了后来我们去偷摘树上老母柑的欲望。
“老母柑”是我们那地方给柚子取的土名。为什么这样称呼,无从考证。成熟的老母柑比足球略小,表皮淡黄,往里是厚厚的海绵状白色肉皮,与果肉不易剥离。剥开每瓣果肉外面的薄皮,去掉嵌在果肉中的核,那一块块晶莹闪亮、饱含鲜美果汁的淡绿色果肉,香甜带酸,回味悠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家乡还是穷乡僻壤,在我们穷孩子的眼中,老母柑不亚于王母娘娘的蟠桃。
老母柑不只是美味佳果,对于穷孩子来说,还大有用场,给童年带来好多好多的乐趣。比如,在玩打仗抓特务的游戏中,将半个老母柑厚皮当做钢盔顶在头上,被认为是非常时髦且令人眼红的事。再如,八月十五中秋节,正是老母柑果实长成的时候,将数尺长的细竹竿一端削尖插入老母柑中,再在老母柑上插满点燃的香烛,手举竹竿,或上下或左右或弧形或圆圈地舞动。黑夜中看去,犹如流星飞舞,煞是好看。斯文人管这叫“舞动星香球”或“耍流星”,而我们叫“耍香宝”。那可是比晚上听故事分月饼更刺激的事呀!当然,要说刺激,莫过于用老母柑当足球踢了——虽然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足球为何物、有何规则,但是沿袭家乡民俗的我们,实实在在地是在踢“足球”了:场地因陋就简,或选在农家晒坝,或选在学校操场,或选在寒场天的街巷;双方队员无定数,只要对等就行;当然,更没有带网的球门,只要把老母柑踢出对方底线便为胜。对于半截子娃娃,老母柑大小适中、软硬适度,当做足球自然是再合适不过。激烈竞技带来的刺激,真是妙不可言!常常是老母柑还是青皮的时候,我们就心痒痒的,想摘一个来当球踢。孩子的这种心情,大人们自然是不能理解的。
苍老道劲的老母柑树,扎根在离老屋不远的地坎边上,高大的树干和粗枝略向地坎处向阳方向倾斜,终年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在蓝天白云下,老母柑树好似一把撑开的大伞。那生机勃勃的青枝、卵形阔大的绿叶、素洁的白花、硕大的果实,都散发出沁人心脾的清香。从它身旁路过的人,都会情不自禁地停步,耸耸鼻子嗅一嗅。过了开花期、挂果期,累累的老母柑就沉甸甸地压弯了枝头。就像馋猫渴望挂在屋檐下的干鱼,我们的眼睛都望绿了。可怎么才能摘到一个老母柑来当球踢呢?壮实憨厚的莽子抓了抓光头头皮,说:“甩石头去打!”可用了许多石头,只打落了一些树叶。头发长身子瘦的猴儿说:“我有办法!”他紧了紧有些下垮的裤腰,去家里搬来晾衣竿,在一端绑上皮筋弹枪,想用“丫”形木权去扭断老母柑的果柄,仍然无济于事。
俗话说:久走黑路,总要遇到鬼。我们偷老母柑的行为果然被伯娘发现了。她拿了一根响篙子,晃动着尖尖脚走到树下,扬了扬,响篙子便发出“哗哗”的震动声。她凶巴巴地说:“你们这帮放牛娃儿也太捣蛋了!老母柑还是青皮子就开偷,不等它黄熟恐怕早被偷光了!你们知道不,这棵树可是我的一个‘银行呀!我还巴望着卖果子来添补糊口呢!下回再让我逮到,我认得人,这响篙子可认不得人!”
响篙子是把三尺来长的竹子下半截划破成竹片制成的农家竹器。使用时,只要手握上边的柄摇动,下边的竹片就会发出“哗哗”的响声,可驱赶家禽。当然,它又被大人赋予了新的功能——打孩子。但凡像我这样调皮捣蛋的娃娃,都尝过它的滋味。用娃娃家的话来说,就是“响篙子打人,响得凶,痛得松”,比起“楠竹笋(毛竹片)炒(打)腿鸡肉(屁股)”来松活多了。所以,等伯娘转过背一走,我们又我行我素了。伯娘不得不再次转回树下,责问我们为什么老招呼不听。我们只好明说想踢老母柑的本意。伯娘没有说话,却去老屋取来了一把弯弯的镰刀,绑在长竹竿的顶端,伸到树上,刀口对着一个老母柑柄,轻轻往下一拉。只听得“嚓”的一声,一个老母柑便落了下来。机灵的猴儿赶紧跑到高地坎下的草丛中,抱起老母柑,吹了声口哨,我们便跟着跑去,找地方踢老母柑了。
深秋是下果的季节,黄澄澄的老母柑压弯了枝头。伯娘请人来下果,好拿到场上去卖钱。除了老母柑这棵“摇钱树”,她还有两个“银行”:一个是泡菜坛,另一个是鸡屁股。伯娘靠多吃咸菜下饭省钱和卖鸡蛋攒钱。此后,每逢收获老母柑的日子,我们也学伯娘在竹竿顶端绑镰刀,偷偷摘老母柑尝鲜。由于我们个子矮又不得法,常常要站到高高的地坎边去操作,听到老屋窗口传来伯娘的干咳声,就停手躲起来。这时,就会看到伯娘手腕上挂着一只竹提兜,出现在老屋前门门口。我们都知道提兜里放着鸡蛋,为了防止碰坏,伯娘把它们埋在糠壳里,上面盖一方蓝底白花的土布。伯娘推开腰门,跨过高高的门槛,迈着尖尖脚,一摇一晃地向通往乡场的大路走去。说是“大路”,那只是相对老屋后阳沟那条少有人走的小路而言。其实这大路也是“晴天一块铜雨天一包脓”的黄泥巴路。看到伯娘颤巍巍的姿态,特别是下坡时的样子,我们真担心她跌倒。不过,等她走远了,我们又继续行动。由于这时没有了后顾之忧,常常会大有收获。
到了冬天,地里显得荒芜了,树叶枯黄飘落,光光的枝丫在风中颤抖。只有老母柑树依然生机勃勃,只是经过风雨洗礼,枝干更道劲,树叶变深绿了。树梢向阳方残留的老母柑所剩无几,在阳光照耀下熠熠闪光,好像童话中的金果子,着实惹人嘴馋。听大人们讲,那些果子果实硕大、果色金黄、果肉鲜美,是主人有意留在树上保鲜的。据说那才是一树果子中的珍品。“烂市”过后,物以稀为贵,将它拿到市场上,可以卖个好价钱。但一般人家都不图那个利,而是留着自家享用,或招待贵客,或馈赠亲朋,以表诚挚。我们家就曾经得到过那样珍贵的礼品。那果肉的味道果然特别,吃了叫人一生难忘,想来应该不亚于《西游记》中的人参果吧!
我们又在打那“人参果”的主意了,想再用长竹竿绑镰刀下果子,可是够不着。这方法显然过时了。有什么好办法呢?这时我们才悟到:留在高土坎外树梢上的“人参果”,还有防盗的用意。不要说我们小孩子家,就是大人,如果不上树也摘不到。“上树?”机灵的猴儿猛拍小脑瓜说,“有了!”我说:“什么有了?你神秘兮兮的干啥?总不会是有了孙悟空的七十二变吧?”他说:“算你猜对了,还真与孙猴子有点关系!”说罢,便像个猴儿一样手脚并用,刷刷刷地爬上了老母柑树,找了一个树杈骑着,叫我们把带镰刀的长竹竿递给他。他握着竹竿,用顶端的镰刀去勾树梢的果柄。也许是被枝叶挡着了视线吧,好一阵子,只听得“嚓嚓”的响动声,只见树枝闪动树叶飘落,却不见有果子掉下来。
“咳咳——!”正在这时,老屋窗口传来了伯娘的干咳声。在树下望风的我们生怕猴儿受惊跌下树来,赶紧小声传话:“喂!有情况,暂时别动,别发出响声!她看不到你!等她走远后,我们给你报信再动!”说完我们也找地方躲了起来。
我们一等不见伯娘开门,二等不见她出门上街。今天怎么了?性急的莽子心里发毛,非要亲自去探个究竟。他蹑手蹑脚地去窗口看了,回来时学着电影《平原游击队》里打更人的样子,大摇大摆地用短木棍敲着手中的破竹筒:“梆!梆梆!”还做着鬼脸吆喝:“平安无事喽!平安无事喽!梆!梆梆!”不用说,这次我们终于不慌不忙地获得了一个“人参果”。
大家在慈竹下吃得正欢时,一个被我唤做“大嫂嫂”的中年农妇走了过来。她手里拿着一把草药,板着脸说:“嗨呀,你们这帮捣蛋鬼在这里呀!知道不?你们闯下大祸了!”
“啊?!”我们不约而同瞪大了眼睛,停止了咀嚼,一个个呆若木鸡,“我们闯祸了?”
“你们敢说没有?”大嫂嫂说,“伯娘从窗口发现你们有人上树偷老母柑,怕走前门上街惊落树上的人,就改走后阳沟的小路上街。下坡时尖尖脚踩到青苔滑倒,一提兜鸡蛋全打碎了,人也跌伤了,右脚踝部又青又肿,像泡粑一样。是我割猪草发现了,才将她背回家的。现躺在床上直呻唤哩!”
哦!以往每次偷果子时,老屋窗口传来的干咳声,是伯娘有意预先提醒,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不致惊慌中跌下高土坎呀!我们面面相觑,一个个心里难受,口中的老母柑也顿时没了滋味,吃起来像啃木屑一般。平日间莽子和猴儿都管我叫“叔珥”,我年纪虽小,辈分却不小,这时自认为有责任,说:“大嫂嫂,你带我们去看看伯娘好吗?”
“这不,我正要去将草药捶烂给她敷伤哩!”大嫂嫂说。
我们随大嫂嫂来到伯娘的床前,大家都低着头红着脸,躲在大嫂嫂的身后,用手扯衣角,不敢做声。大嫂嫂打圆场说:“伯娘,偷果子的鬼豆子给你赔不是来了!他们怕你把这事告诉他们家的大人,晚上挨打吃‘楠竹笋炒腿鸡肉哩!”见我们没人开腔,她转过身来把我们让到床边,“哎,不要不好意思嘛!平常叽叽喳喳像闹山雀,怎么现在都哑巴了?给伯娘赔个不是不就得了!”
我们将没吃完的老母柑还给伯娘,哽咽着说:“我们再也不偷你的老母柑吃了!”
伯娘动了动身子,突然伤痛加重,咬了咬牙皱了皱眉,说:“其实,在我们这山旮旯里,能在一起是缘分。摘了别家的一个果子或黄瓜、地瓜什么的解解渴解解馋,本算不得偷。乡里乡亲的,不要说得那么难听!我也不会告你们的状。不要把这事放在心里!娃娃们若不捣蛋,不都成傻子了吗?”
读书、升学、工作,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伯娘早已作古,我也历尽人生的沧桑。这次回故乡,特意去看了老屋旁边的那棵老母柑,它竟然和儿时见到的一样。是啊!儿时的许多事都渐渐被我淡忘了,唯有故乡童年的老母柑一直伴随着我、留在我心里……
作者简介
黄培锦,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宜宾市诗词楹联学会副会长;在省级以上文学期刊发表多篇小说,已出版长篇小说《阿大王》,短篇小说《牛郎智女》于2010年获中国作家杂志社“金秋笔会”全国征文评比一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