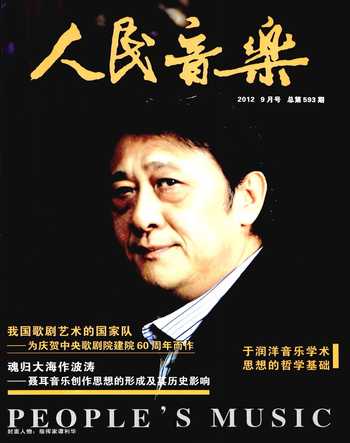浪漫精神与现代技法的完美结合
美国作曲家斯蒂芬·艾伯特(Stephen Albert,1941—1992)是罗马大奖、普利策奖和格莱美奖的获得者。在20世纪音乐日渐拒斥情感表达,远离浪漫主义精神之时,艾伯特将浪漫主义精神与现代创作技法相结合,创作出感人至深的音乐作品,被视为新浪漫主义音乐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主要作品声乐套曲《唤醒逝者》(To Wake the Dead,1978)、交响曲《河水奔流》(Rivermnning,1983)、室内乐《远山》(DistantHills,1989)、《大提琴与乐队协奏曲》(1990)等均体现出鲜明的新浪漫主义音乐风格。
一
1941年2月6日,艾伯特出生在纽约,在幼年的家庭生活中,他受到了古典音乐的熏陶。8岁时,艾伯特开始学习小号,并在学校和交响乐队中演奏。小学六年级,他又开始学习圆号与钢琴。13岁时,艾伯特在一个夏令营中写下了他的处女作——一部钢琴组曲。在老师的鼓励下,夏令营结束回到家中之后的他依旧坚持创作,后来他向家里人宣布了自己的理想:成为一个作曲家。读高中期间,艾伯特师从艾利·席格美斯特(Elie Siegmeister)学习作曲,并在埃斯彭音乐节(AspenMusic Festival)师从过米约。
1958年中学毕业后,艾伯特进入了伊斯特曼音乐学院(Eastman School of Music),在那里,艾伯特师从伯纳德·荣格,维纳·巴露,艾伦·艾维·麦豪斯等。在伊斯特曼音乐学院期间,艾伯特创作了不少较为短小的作品。
1960年,艾伯特离开了伊斯特曼音乐学院,赴斯德哥尔摩跟随瑞典作曲家伯劳达进行了短暂的学习,之后,进入了费城音乐学院,师从哈里斯和卡斯泰多。卡斯泰多强调调性语言的重要作用,这对艾伯特影响巨大,在他日后的创作中,调性成为最为核心的因素。
1962年秋季,艾伯特进入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大师班,师从罗奇伯格学习对位与音乐分析。作为新浪漫主义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罗奇伯格对艾伯特也有着重大的影响。正是罗奇伯格帮助艾伯特明确了重要的音乐观念:首先,音乐应该触及灵魂;另外,对于音乐而言,从过去的资源中汲取营养并仍然拥有现代作曲家的印记是可能的。次年,罗奇伯格离开该学校,于是艾伯特也毅然离开。罗奇伯格在艾伯特心目中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艾伯特是一名成功的作曲家,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教授。他曾连续两次获罗马大奖;1985年,凭借交响曲《河水奔流》获普利策奖,还曾获麦克道威尔侨民奖(MacDowell Colonyhnowships),以及两次古根海姆基金会奖(Guggenheim fellowships)等。艾伯特于1985-1988年任西雅图交响乐团的驻团作曲家。还曾与芝加哥交响乐团、美国国家交响乐团、匹兹堡交响乐团、费城交响乐团、纽约爱乐乐团、巴尔的摩交响乐团等著名乐团有过合作。他曾任教的学校有俄亥俄州立学校、费城音乐学院(1968-1970)、斯坦福大学(1970-1971)、斯密斯学院(1974-1976)、茱莉亚音乐学院(1988-1992)等。
二
艾伯特对浪漫主义音乐中情感表现的魅力青睐有加。他清醒地看到,20世纪下半叶的许多作曲家为了逃离情感的表现而使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他曾经这样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20世纪50年代早期以来的许多音乐创作都不是能够吸引我的那种类型。这些作品没有能量让我离开旧有音乐所拥有的魅力。而且,我感到这类作品的实践者们处于一种不切实际的逃离某种类型的情感表现的沉重负担之下。”
艾伯特的创作很好地实践了他的音乐观念,具有强烈的情感表现特征。他最为著名的两个作品——声乐套曲<唤醒逝者》、为大提琴和乐队而作的交响曲《河水奔流》——都是表现性风格的典型例证。艾伯特正是凭借这两部作品而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声望。
《河水奔流》曾获普利策奖,由马友友演奏的版本获格莱美“最优秀的当代作品奖”(1995)。该作品根据英国文学家卓斯的长篇小说《芬兰人觉醒》而作,是一部表现深切的人类情感的优秀作品,也是艾伯特最受欢迎的一部作品。该作品中的河流指的是爱尔兰首都都柏林的母亲河——利菲河。这条河流经一个名叫“亚当与夏娃”的教堂。正如亚当和夏娃站立在人类历史的开端,河流与教堂等因素便位于整个作品的开端,暗示着伊甸园、两性、人的堕落以及拯救的愿望。“河水奔流”还暗示了时间之流,正是在这时间之河中,世界万事流淌而过。正如该作品所依托的文学作品《芬兰人觉醒》中的描述:“河水奔流,流过亚当和夏娃之地,从沙滩之角到海湾之边……”
《唤醒逝者》所依托的文本也是《芬兰人觉醒》。该作品为女高音和室内乐队而作,题献给作曲家的妻子。第一乐章《它是如何结束的》,开始便用弦乐的弱奏营造出一种沉思默想的氛围,随着长笛和钢琴的加入,又似乎为这种略带忧伤的沉思加入了些许的激情。女高音进入时,所有的乐器都停止了,纯人声的旋律显得清澈透明。第二乐章《河水奔流》(与其交响曲同名)的特征是孩童般的风格。钢琴在高声区演奏简单的、不断重复的分解和弦,制造出一种类似于音乐盒或是玩具钢琴的声音效果。女高音的曲调节奏欢快,如同儿歌一般。第三乐章《祈祷》充满了甜美而忧伤的情绪:接下来是专门为乐器而写的段落,其中运用了卡农的手法;第四乐章《遗忘、记忆》,乐谱上标明“柔和、简洁、难以忘记”,长笛的中低音区那富有磁性的音色加上女高音优美超然的旋律线,将听众带入了悠远宁静的意境中。在第五乐章《草地上的小鸟,芬先生》中,逐渐聚集的情感爆发成狂热的庆典,随着一个新主题的引入,乐曲到达了高潮,象征着当芬兰人又活了过来时的欢欣。末乐章《涌出》揭示了一个必然:男人最终会在战争中倒下。于是乐曲又转到宁静、甚至是绝望的氛围,最后结束在女高音的延长音上,给人意犹未尽之感。
在这些作品中,作曲家的核心目标都指向了20世纪许多作曲家都极力回避的因素——情感表现。因此,艾伯特的作品常常因性格鲜明而富有个性特征的曲调而令人难以忘怀,深切、丰富的情感表达给听众以强烈的震撼。
三
以情感表现为出发点,调性思维成为艾伯特创作中贯穿始终的重要因素。在周围的许多作曲家都投身于无调性、序列音乐的创作,对调性音乐唯恐避之不及之时,艾伯特却始终遵循了调性思维的逻辑。
对调性因素的使用是艾伯特缜密思考之后做出的选择。他说:“如果你是一个年轻的作曲家,曾经被告知调性音乐的传统已经用尽了,同时你自己又感觉到,现代主义者们的反叛——从德彪西到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以及贝尔格——也同样几乎燃尽了,此时你将朝向何方?你应当寻找些什么?”
对于十二音作曲技法,艾伯特认为它更多关注的是作曲家的音乐需求,而不是音乐表现的需求,他指出:“勋伯格将其十二音作曲技法与我的调性音阶隔离开来,而且,这种尝试看起来过于关注了我们个人的音乐需求。”出于自己的艺术追求,艾伯特选择了调性的语言:“自从在费城音乐学院跟随卡斯泰多学习之后,调性逻辑的组织就已经成为我创作的方式。”
确实如此,艾伯特完全避开了同时代的许多作曲家更为关注的序列主义、先锋音乐的创作实践,坚持采用了调性语言进行创作。比如,《唤醒逝者》第二乐章的曲调便明确建立在C大调上,最后以具有十分强烈的终止感的D多利亚调式结束,伴奏也是基于调性逻辑和声性模式。
虽然艾伯特的音乐经常是有调性的,但他又没有仅仅局限于调性的语言,而是时常将无调性、双调性、多调性等具有20世纪特征的创作因素引入其中,与调性因素极为融洽地结合在一起。比如,《唤醒逝者》第二乐章的旋律从表面上看起来像孩童一般粗糙,而且旋律建立在C大调上,似乎没有什么艰深的艺术性,但艾伯特使用了B与降B、E与降E的交替使用,来构成较为模糊的调式感觉。该作品的第五乐章《忘记,回忆》的曲调虽然一直明确地处于G混合里迪亚调式,但其伴奏声部却是无调性的色彩性写法。尽管由于这样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的并置导致了极度的不协和,但力度的层次却从头至尾都是宁静、纤细的,使该乐章整体的优雅风格得到了充分的保证。
该作品是艾伯特以传统的调性语言为核心,同时并用其他多种现代性因素以服务于音乐表现并达到作品整体感的极好例证。因此,有批评家将艾伯特评价为“富于技巧的、高度清醒的作曲家,他有着拓展调性因素以求创新的清晰感觉,那些吸引听觉的作品是一个自身原创性的、富有表现力的整体。”
四
以情感表现为基本出发点,艾伯特不仅选择了调性写作手法,同时还在旋律、主题变奏、曲式结构等多个方面体现了浪漫主义精神与现代创作技法的结合。
艾伯特的作品往往具有可听性极强的旋律。批评家威格勒这样写道:“他的音乐如此丰富,充满了那么多的优美曲调,这些作品会使听众认为以前曾经听过艾伯特的音乐——仅仅是因为这些曲调是那么的难忘。”具有丰富可听性的旋律源自作曲家表达情感、打动听众的愿望,于是,作曲家在精神层面上与浪漫主义时期的先辈们更为接近了。
艾伯特十分擅长使用主题材料变奏的手法。在其作品中,新的主题材料经常直接由旧有主题变化而成,在这一点上,他与浪漫主义的主题观念非常接近。因为主题的循环使用,正是浪漫主义时期的一个惯用法则。格劳特曾指出浪漫主义作品的这种特性:“浪漫主义交响曲或清唱剧往往通过不同乐章应用同样的主题——或一成不变或经过变化——而求得新型的统一。”比如,在艾伯特的《唤醒逝者》中,第一乐章的主题后来又出现在第四和第五乐章,而第四乐章中的主题C又在末乐章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艾伯特没有像20世纪的许多作曲家那样回避传统的曲式结构,他的不少作品便直接使用了奏鸣曲式、变奏曲式等传统曲式。但他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积极运用具有对比性的戏剧性材料、织体以及配器等要素来明确曲式,而不是仅仅依靠调式调性的布局。例如,交响曲《河水奔流》的第一乐章“雨之音乐”便是一种“变体奏鸣曲式”。从曲式结构的外观来看,呈示、展开上类似于奏鸣曲式,然而整个乐章只有一个主题及其变化,没有出现第二主题。呈示部包括了主题及其4次变奏(A、A1、A2、A3、A4),展开部中将A3、A4进行了展开,再现部中使用的是A4。此作品中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奏鸣曲式的轮廓特征,但却与传统的奏鸣曲式有着本质的差别:其结构设计往往依据织体、配器和戏剧性材料等因素,而不是调式调性与和声发展逻辑的结果。因此,艾伯特许多作品的曲式结构以主题与主题之间的区分得以展示。
在传统的曲式观念中,“调式调性的逻辑比戏剧性结构逻辑更为重要。”因此,调式调性的逻辑是曲式结构中的一项重要因素,尤其在奏鸣曲式中,调式调性更是核心的要素。然而,艾伯特仅仅保留了奏鸣曲式的外观,却抽去了奏鸣曲式的核心要素——调式调性,显示了对奏鸣曲曲式的回顾,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创新。
五
植根于调性思维、清晰的旋律、可辨的曲式结构、充盈的情感表现与交流——这正是艾伯特音乐创作风格的最为重要的目标所在。其作品实践了一条将浪漫主义精神与现代创作技法给予结合的道路,这也正是新浪漫主义音乐的根本特征之所在。音乐材料的非语义性与表情性决定了音乐艺术情感表现的可能与重要,艾伯特正是在身边的诸多作曲家回避情感表现、反叛旧有经典之际,将目光投向了过去,大胆地追求浪漫主义音乐精神,并与现代创作技法完美地结合,创作出了大量优秀的作品。笔者认为,以完全回避情感表现、颠覆传统经典的方式去寻求音乐艺术的继续发展是不可取的,如何在传统的音乐艺术宝库中吸取精华,并为当下所用,才是我们应当认真思考的问题。正如艾伯特曾指出的:“在‘旧风格中,仍然有许多事情要做。”
刘瑾广州大学音乐舞蹈学院教授,副院长,硕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张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