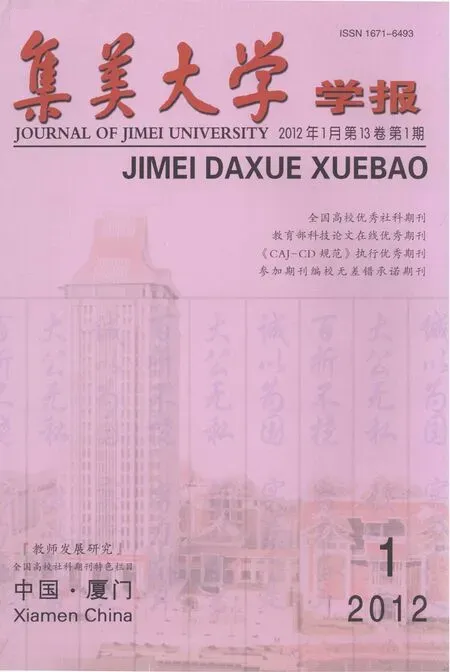中学语文教材个性解读视野中的误读问题
孙桂平
(集美大学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中学语文教材个性解读视野中的误读问题
孙桂平
(集美大学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误读”是成型的阅读理论。将“误读”理解为个性化阅读的一种状态,有理论依据。可以将“误读”引入中学语文阅读教学过程。对于中学生体味文本时出现的“误读”情形,并不太需要介意。引导学生尊重文本及解读史,是避免“错读”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误读;个性化阅读;语文教学;解读史
中学语文新课程标准特别关注学生个性化阅读能力的培养,指出“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要珍视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认为教师要“重视对作品中形象和情感的整体感知,注意作品内涵的多义性和模糊性,鼓励学生积极地、富有创意地建构文本意义”[1]。根据这一指导精神,“误读”是否应该作为一种个性化阅读方式而加以积极提倡,近年来成为中学语文教学研究界争论的热点之一。反对者认为:“误读”与个性化阅读绝不能混为一谈。个性化阅读强调的是建立在文本基础上的个人阅读体验的差异,与“误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是基于文本的合理解读,表现为个体对文本感受的差异性,没有错误性可言;后者是脱离文本的无稽之解,没有合理性可言[2]。赞成者则认为:任何意义上的阅读都是一种误读[3]。在言语生命动力学表现论的视界下,对文学作品与一些实用类文章的阅读,都是可以而且必须误读的!误读是通向自由想象、情思创新的必由之路[4]。我们认为,从学术角度看,“误读”已然被公认为是成型的阅读理论;但其对于中学语文阅读教学实践的意义,仍然需要深入讨论。由于误读现象在文学解读过程中最为常见,本文主要联系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阅读的案例来论述这一问题。
一
将“误读”理解为个性化阅读的一种状态,从学术角度看,其理论依据是充分的。中国古人的诗歌阅读经验非常丰富,对于“误读”的肯认就形成了两大宝贵传统。一是“《诗》无达诂”。先秦时期的知识分子有“赋《诗》言志”的习惯,所引《诗》句为时人所知,但往往弃其原意而用其衍生之义。如据《论语·八佾》的记载,孔子在与学生对话时,曾引用《诗经·硕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诗句的原意是形容卫庄公夫人庄姜之美,孔子却用来说明“绘事后素”的道理。又如《春秋左传》中存在不少“赋《诗》言志”的例子,但其解读方式一概如清人曾异撰在《复曾叔祈书》中所论: “左氏引《诗》,皆非诗人之旨”。[5]以“赋诗言志”为渊源,中国诗歌接受史形成了“故意曲解”的基本解读路径。传统之二是:受“六经注我”这一学术思路的影响,中国诗歌形成了尊重读者心灵体验的良好氛围。比如,欧阳修在《唐薛稷书》中说:“得者各以其意,披图欣赏未必是禀笔之意也。”[6]清代相关论述尤其多,如贺贻孙在《诗筏》中说:“凡他人得意者,非作者所谓得意也。”[7]袁枚在《程绵庄诗说序》中说: “作诗者以诗传,说诗者以说传。传者传其说之是,而不必尽合于作者也。”[8]至谭献《复堂词录序》,阅读者与诗人心灵难以契合的误读问题,就被总结为名言:“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读者之用心何必不然。”[9]上述经验说明,“误读”是中国文学阅读的普遍经验,古人并从学术层面认识到了“误读现象”的合理性。
“误读”作为阅读史上普遍而客观存在的文学接受现象,在西方学术界已经发展为成型的文学批评理论。在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误读”现象及其研究得到了关注和强调。作为美国耶鲁解构主义批评学派的干将,哈罗德·布鲁姆在1973-1976年间推出“诗论四部曲”,其中《误读图示》继承了并推进了其早期作品《影响的焦虑》中所提出的“影响即误读”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强调想象与误读、延迟与修正等诗歌批评范畴的系统理论。[10]布鲁姆甚至宣称: “读者能够获得的最好的东西,就是一种出色的误读”,并认为误读是一切文学艺术作品和人类难以摆脱的命运,作家在误读中创造,读者在误读中接受,作品在误读中流传。而“一切阅读都是误读”,也就自然地成为解构“追求释义与正解”等传统阅读观念的宣言。[11]实际上,德·曼的修辞理论和德里达的延异理论,毫不留情地摧毁语言运作中所包含的各种意义体系,为“误读”的必然性找到了内在依据。至今,“误读”在文艺批评领域内,已不再是一个贬义词,而成为具有创造性阅读方式的代名词。
从哲学原理看,良好的阅读状态实际上也是从量变向质变点逐渐累积的过程,如果质变可以被理解成接近于正确阅读,那么处于量变状态的阅读在性质上一定是不太正确或不够完整的,并以其具有试错的意义而为“误读”提供足够的价值空间。从心理学的一般原理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描述了个体心灵对他人文本进行释义的可能性。而“人心相异,各如其面”的成语又告诫我们,读者要想彻底理解文本的意义并由此透视作者的心灵情感,那几乎是徒劳的妄想。既然对文本全面彻底的正确理解只是理论虚设而不会是现实存在,那么“误读”就具有必然性价值。另一方面,既然可以确认“误读”不可能是对文本全面彻底的正确理解,那么“误读”的意义也只能是相对性的。或者说,“误读”作为阅读的终结状态,那无疑是错误的阅读。若以“误读”作为正读的起点或趋向正读进程中的构成环节,那就是个性化的解读。
据上所述,将“误读”作为个性化阅读的一种方式引入中学语文阅读教学过程,在理论上是可以成立的。这就要求,教师在从事中学语文阅读教学时,不能将针对文本的某种或某些释义,处理成绝对正确的知识点,或者安排为进入考试程序的标准答案。显然,类似的狭隘观念认可了绝对正确的文本解读事实上存在,而这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
二
与自由自主的阅读状态相比,中学语文阅读教学存在更多诱发“误读”的主客观因素。其中有些是出于不可克服的原因,比如按照规定,译文在中学语文教材中占有一定的篇幅,而其中有不少是外国文学精品。但不同的语言文字体系在文化背景、表达风格与读者期待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无论翻译家水平多么高,翻译态度多么认真,翻译过程都必然会出现针对原文的减义、衍义和变义现象。或者可以说,译文的阅读教学相对于母语作品的阅读教学而言,存在一种先验的“误读结构”。更为主要的问题在于,编者有时会遵照意识形态的要求,或者根据自己的文化立场,对选入语文教材的作品进行更动。比如有的论文提到,中学语文教材所选录的《我的叔叔于勒》是删节版,这就强化了阅读教学的意识形态色彩,对原作的主题、风格造成了有意误读。删节版教材对新课标背景下教学改革的直接影响是压缩了学生的文本解读空间,使阅读教学难以达到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并获取独特感受的教学目标,而语文教学的人文精神培养也必然会受到负面影响。[12]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朱自清的名作《荷塘月色》,可能是考虑到“未成年人不宜”的社会伦理要求,该文中录入的《西洲曲》等文字在以往经常被编者所删减。在这里我们没有必要去议论编者的是非,但由此必然会导致的误读情形,则显然不容忽视。此外,中学语文教学面对的是一些心智尚未成熟、社会阅历不够深广的青少年,而入选教材的作品则多数蕴涵着成人的世界观和历练的心灵感情。这一特殊场境决定了,即使教师能够思路清晰地进行阅读教学,也很难保证学生很好地接受理解。曾经有一位中学语文教师就告诉我,他自己就进行诗歌创作,他不仅聆听过舒婷本人亲自说明《致橡树》的写作经过,也全程参观了著名中学语文教育研究者孙绍振解读这首诗的讲座,他觉得他对这首诗的理解应该是深入而准确的。让他感到苦恼的是,即使他以最为简洁明了的方式进行讲解,学生仍然会由于不理解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社会文化而按照当下社会年青一代的生活观念对该诗进行误读。可以说,在中学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中,“误读”现象不仅无法避免、经常出现,而且成因复杂,表现形式多样,对此我们要抱以宽容的态度。
有一点现在也许要明确:我们应争取让所有中学语文阅读教学过程的参与者意识到,“误读”不是错误的阅读,而是具有参考意义与发展前途的个性化阅读。按照新课标,个性化阅读能力是中学语文教学的长远目标之一,其关键在于学生能否培养出不断生成质疑精神和问题意识的阅读习惯。在不与他人交流的情况下,单个学生对文本产生误读的情况可能导致偏见,这的确令人担心。但在一个班级或其它学习群体中,如果大家能够坦诚地进行讨论,那么形式多样的“误读”就不仅能活跃参与者的思维,而且有助于形成丰富复杂的阅读生态,并促使“误读”在健康的阅读氛围中往“正读”的方向不断转化。
另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我们也该坦然面对了,即,与中学生一样,教材的编者与传道、授业、解惑的教师不仅也是“误读”现象的生产者,而且在有些情形下,正如上文所述,学生的“误读”就是由教材的编写者与教师所直接诱导的。如果我们一定要将学生那里随时随地都可能出现的“误读”现象当作洪水猛兽而加以纠正的话,那么罪魁祸首有时恰恰就是语文教材的编写者和使用教材的教师。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知道自己在不同程度上也难免是教材“误读”的制造者之一,那么我们在从事阅读教学时,也许就不会拿着所谓的“标准答案”、 “中心思想”和“知识点”等生硬的标签强求一致的阅读理解,而宁愿以民主的姿态寻求“师生彼此对话”的交谈氛围。
或许,语文阅读教学对于学生最大的意义,就在于试图通过文字来体验他人的心灵、情感与思想,为自己累积一种有韵味的成长经验。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如果学生体味文本的过程是认真而富含意味的,那么存在一些“误读”的情形,以及出现阅读最终不能抵达作者心源等情况,就并非是太需要介意的问题。
三
事实上,“误读”对于语文阅读教学的积极意义是明显的。在有些情况下,“误读”是对文本的拓展想象,其结果让人愉悦。即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一联为例,我们可以通过诗歌上下联在修辞手法上经常存在着“互文性”,理解出“月光松影浸润在清泉中流淌”的妙境,由于这是诗人没有明确说出或是根本就未曾设置的景象,大概算是一种“误读”。但这样的“误读”使诗意变得更为深厚,并让读者的心智升华到与诗心契合的高度,自然就属于上乘的延伸阅读。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误读”通常与质疑精神、问题意识等个人素养联系在一起,如果加以适当地引导,这就是创造力的萌芽。正如有的学者所论述的:阅读不应片面地要求学生“正确”或“准确”地识记,有些学生不忠实于原意的即兴发挥,也许胜过老老实实地复述,因为这恰恰表明了他们具有创造的天赋。而最为重要的是,“误读”体现了学生在阅读过程中通过试错而不断成长的权利,由此更容易形成令人经常满怀信心的健康的阅读心态。根据生物科学家的研究成果,试错是动物界最基本的学习方式,也是最符合生态原理的学习方式。[13]根据波普尔的试错理论,人们对于人情事理的认识,通常都是一样的:即本能地利用试探和清除错误的方法,简称为试错法。从哲学层面说,试错法是生物机体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所采用的基本方法,因此具有普遍的意义,可以应用于诸多领域。照此推论,由于“误读”在方法论上具有试错的价值,因而应该在中学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中推广。而大量的中学语文阅读教学实践也表明,基于认真思考的“误读”为阅读教学提供了试错空间。较之直接领受“近乎正确的解读”,由“误读”而渐趋“正读”,这更加耐人寻味,也更能体现教学相长的教育要义。
当然,误读作为个性化解读,也是有边界限制的。正如论者所认识到的:“误读”既有超越突破文本自身的一面,又有受制于文本自身规范和限制的一面,它是一种被引导和受限制的创造。[14]在中学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中,这种边界在操作层面上经常处于模糊状态。其不良表现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以为凡是与众不同的新异观点就是“个性化阅读”,如认为李清照《如梦令》 (长记溪亭日暮)是豪放风格的;再则是将没有经过认真深入思考的错误理解当作“个性化阅读”,如认为《背影》中的父亲翻越栅栏是违反交通规则;三是将不通读文本抓住文字片段即信口雌黄的意见视为“个性化阅读”,如认为鲁智深拳打镇关西是施暴场面。那么,教师作为中学语文阅读教学过程中的主导者,当如何防止“误读”偏离个性化阅读轨道呢?
引导学生尊重文本及解读史,可以说是最基本也是最有效的方法。伊塞尔说过:“文本的规定性也严格制约着接受活动,以使其不至于脱离文本的意向和文本的结构,而对文本的意义作随意的理解和解释。”[15]文本在阅读教学中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至于防止“误读”偏离个性化的具体路径,台湾学者傅伟勋“创造的诠释学”理论可以借鉴。傅伟勋将“创造的诠释学”分为五个循序渐进的辩证的步骤或程序:(1)原作者实际上说了什么?(2)原作者真正意味着什么?(3)原作者可能在说什么?(4)原作者本来应该说什么?(5)作为创造的诠释学家,我应该说什么?[16]当然,这一诠释程序还可以被推进。因为某一“误读”在阅读教学过程中的价值,不仅是与作家本意相比较而能够存在,更是与其它多种“误读”形态相参照而得以确立。据此我们可以在上述五个步骤之外在加上两条:(6)除了我与原作者之外,还有别的诠释者说了哪些有意思的话; (7)作为创造的诠释学家,我所说的与他人有什么不同之处。一般地说,中学语文教师如果能够坚持这七大标准,大致就能引导学生将作为“个性化阅读”的“误读”与“常识意义上的错读”区分开来。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 (实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2]卢金明,霍术东.文本“误读”: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 [J].现代语文,2006(7):54.
[3]韩笑.误读与误读的意义 [J].飞天,2009(14):12-14.
[4]潘新和.误读:阅读教学的新宠[J].语文教学通讯,2010(12)卷首.
[5][清]曾异撰.纺授堂文集[M].清康熙57年刻本。
[6][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 [M].北京:中华书局,2001.
[7][清]贺贻孙.诗筏,清诗话续编本.
[8][清]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28[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9][清]谭献.复堂词录序,载唐圭璋《词话丛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0]李琪.“误读”之维:布鲁姆的诗歌批评 [J].作家杂志,2010(1):109-110.
[11]哈罗德·布鲁姆.误读图示 [M].朱立元,陈克明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1.
[12]张占杰,辛志英.有意误读的缺憾——谈中学语文教材《〈我的叔叔于勒〉的删节问题》[J].石家庄学院学报,2010(2):109-112.
[13]尚玉昌.动物的试错学习行为 [J].生物学通报,2006(1):11-13.
[14]徐克瑜.论文学接受中的正读、误读与歧解 [J].文艺争鸣,2009(7):140.
[15]伊塞尔.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236.
[16]彭启福.文本的误读与意义的创生——谈谈傅伟勋“创造的阐释学”中的“误读”概念[J].学术界,2009(1):148-149.
The Misreading Problem in the Angle of Personalized Interpretation on the Teaching Material for Secondary Language
SUN Gui-ping
(Chinese Language School of Jimei University,Xiamen 361021,China)
Absrtact:The theory of misreading is systematic.We can regard the phenomenon of misreading as a kind of personalized interpretation.The phenomenon of misreading isn’t negative factors,instead it has positive impacts o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for reading.Guiding learner to respect the text and related history of interpretation,this may be one basic and effective way to avoid the phenomenon of wrong reading.
misreading;personalized interpretation;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history of interpretation
G 633.3
A
1671-6493(2012)01-0043-04
2011-05-23
孙桂平 (1973—),男,安徽枞阳人,集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诗学、语文教育。
(责任编辑:孙永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