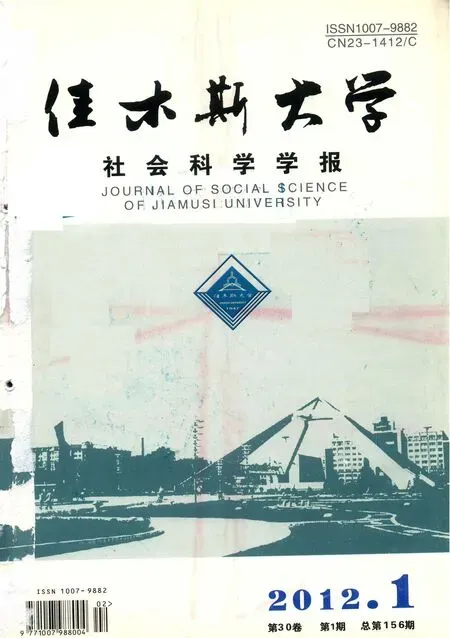浅论《碧奴》的悲剧文化意蕴①
王春艳,程丽蓉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637002)
浅论《碧奴》的悲剧文化意蕴①
王春艳,程丽蓉
(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南充637002)
孟姜女故事在不断的重写中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意蕴,丰富了我国源远流长的悲剧文化。本文主要从文化符号学视角分析苏童小说《碧奴》的悲剧文化意象和悲剧内涵。首先从悲剧特色入手探析小说对孟姜女故事的传承,然后从文化符号学角度分析文本对碧奴悲剧的建构,并进一步探究“碧奴式”悲剧的文化内涵。最后总结孟姜女故事重写的当代意义。
碧奴;悲剧;意象;文化符号
当代孟姜女传说故事的重述小说以后现代主义为文学背景,融入了大量的西方创作技法,使孟姜女形象更为丰满,小说传达的思想更具时代性与内蕴性,艺术手法更具中西合璧的魅力。
一、《碧奴》对孟姜女悲剧故事的继承与创新
孟姜女形象虽几经发展,但她内外兼美的品质——貌美而又博学,知书识礼,真诚善良,善恶分明,敢爱敢恨,为了追求爱情,不怕艰险,千里寻夫,撼动着从古到今人们的心。同时本故事贯穿孟姜女千里寻夫的具体情节,经千年发展大致如下:由于朝廷要修一座长城,男主人公被迫离开妻子去服役,妻子因思念与担心丈夫的安危,忍受艰辛,从千里之外寻到长城,却知丈夫早已不堪残害,葬身于长城下,因过于悲恸,感天动地,孟姜女居然哭倒了长城。孟姜女故事人物在波澜曲折的情节推动下,演绎出这样的思想:人民对封建暴政的痛恨和对自由幸福生活的渴望与追求。
苏童的重述神话长篇小说《碧奴》,在原孟姜女传说中加入了大量的中西结合的现代叙事手法,以揭示当代社会文化语境下人们的精神诉求,其叙事技巧和文化内涵融古今中外,将当代叙事手法与传统叙事手法相融合,全知叙事视角与人物叙事视角相结合,很多时候人物叙述者又是故事感知者。全篇故事省略掉了孟姜女故事的大部分情节,只留下寻夫与哭倒长城殉夫的情节,并着重渲染寻夫之前准备与寻夫途中所见人事,特别突出孟姜女全身各个器官都可“哭泣”的意象,使小说在意蕴层面更具张力。
二、《碧奴》的悲剧文化符号与内涵
孟姜女故事最突出的特点是悲,暴政下的爱情之悲、人生之悲。品味完原故事,读者不禁感到悲从中来,不可抑制,从而思考是什么让一对纯情的爱人天人永隔。爱,自有人类以来,便是人之本性,人之常情,可是为什么传说故事里男女主人公连这最基本的人的权利都不可拥有呢?是暴政,它先剥夺了人的生存与自由的权力,再剥夺了爱人与被人爱的权力,使读者千百年来深为故事的悲情而怆痛,使历时的人们与读者不断地对孟姜女故事进行传说与重写。
1.哭与悲剧的关系及文化蕴含
哭因生命的诞生而开始,由生命的结束而终止。哭在人的一生中扮演了无数角色。乐极生悲,因悲而泣,哭与悲可谓一对孪生兄弟。哭在中国古典文学中是一个特殊的文化符号,以哭为特点上演了一幕幕悲情故事。泱泱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华夏儿女的历史功勋不胜枚举,可谓“一将功成万古枯”,有多少的成就之果是结在万千百姓的血泪之树上,中华民族苦难的血泪史,纵横千年的泪水,这个深重的痛苦由谁来担负与倾吐?是女人,是女人们的眼泪,女人沉痛的哭泣,蕴含了人类对自己命运的自觉与反抗,人类对自己命运的挣脱却颓败,但仍然在不服输的思想下苦苦地抗争,争取自我的实现与追求人生的真谛。哭得天人合一、感天动地。
苏童的小说《碧奴》首要的特点是哭。因哭,苏童版本的孟姜女故事主旨就发生了变化。女主人公竭尽哭之能事,哭得耐人寻味,哭也成了全文的主线。整本小说,利用后现代的叙事方法,场景变化下的每个结局几乎都使女主人公的泪水充溢,或腐蚀陈腐,或感天动地,山水草木为之动容,何况人乎?尽管小说里的次要人物都非善类,但是碧奴的泪水还是感化了他们。可是“哭”的场面虽然宏大铺排,但是读者感不到那个原传说故事的“悲”情,更多的是读者对“恶”的厌恶,同时激起对善的渴求。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说:“小说家有三种基本可能性:讲述一个故事(菲尔丁),描写一个故事(福楼拜),思考一个故事(穆齐尔)。”[1](P115)在这部小说中苏童采用民间狂欢的笔法来描述故事,从而引起作者和读者同时沉思何为善,何为恶,是不是自己在生活中不经意间就做了一回“恶人”。在这个物质丰裕,精神浮躁的时代,苏童的碧奴能引发人们反省自己的魂灵,这有多么难能可贵。苏童在小说中正是通过渲染灰色的色调,铺排哭的场面,来削弱原故事的爱情与反抗强权的主题,更多的是加强恶与善的对比度,从而塑造一个控诉的主题,控诉世态的炎凉,人性的险恶,引起人反思自己,反思时代与社会。在这个意象上,作家文笔着墨的轻重,起承转合的安排大多与原孟姜女故事文本分离,在情节上运用的加、减、变的手法,使原故事的主旨意向与情感倾向发生了转移。
2.长城与悲剧的关系及文化蕴含
长城——中华厚重文化的象征。长城代表着是中华民族智慧与毅力,在文学、音乐、美术等艺术世界里,长城象征力量,坚不可摧的民族力量,在战争中,它能抵御外敌入侵,向世界各民族显示中华儿女的信心与能力,这种强大的示威,表明当时政权机构的强大不可侵犯。可是在孟姜女故事文本中,读者再也看不到那样一个长城,它是女主人公悲愤控诉的对象,女主人公不惜一切泪水将其哭得墙倒城摧,它是什么?是政治统摄下的强权对低层民众的压迫。它看起来坚如磐石,可它是多少代中华儿女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来修筑成的,有多少具尸骨被埋在长城下?对于一个普通人,一个平常的百姓人家,有多少人愿意把自己的孩子、丈夫、父亲送到那座不得不修的长城下?修了长城,外敌就不再入侵了吗?有了长城,蒙古人一样踏平了中原,满人一样进了关。多少历史旧事证明了一个国家能不能安宁,不取决于一座看似可以抵御外侵的城墙,而在于它的军事、经济、科学的实力有多强,而最终决定这些的因素在于这个国家全民的思想水平、文化素质有多高。人,才是根本,国强,在于每个人强,每个人团结一致的思想稳固了,这个政府的统治长会长久,这也正是儒家所说的“仁政”的要领。用人们斑斑血肉修筑长城,而不是采取措施让百姓安居乐业、开拓思想、积极进取,这种灭绝人性、毫无人道的强制政治行为,只会让这个民族的人连最基本的生存权利都没有。1943年,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发表了《人类动机的理论》,他提出了著名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有一个从低到高的发展层次。低层次的需要是生理需要,即吃穿住行的需要,向上依次是安全、爱与归属、被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要。自我实现指创造潜能的充分发挥,追求自我实现是人的最高动机。生理需求是人类最基本最低层次的需求和欲望,较低层的需求被满足之后,就会不断往高处的欲望发展。满足生理需求之后就追求心理满足和社会认同,再之后就想被爱,被尊重,希望人格与自身价值被社会承认。[2]从古今中外来看,这几个层次的需求是人类的共同特质。而在当时那样一个连人最低层次的生理需要都得不到基本保障的国家,人们何来长足发展,又何来众志成城,一心向国?国家是以个体才能相加或相乘的集合体,当每个人的能力得不到很好的发展时,这个国家又怎么可能富强?
孟姜女故事中的“长城”不再是人们众志而成的城,而是每个人、每个家庭血泪树上结出的恶之果,它的命运只能是倒下,倒下的不是长城,而是一种政治、一种生活、一种命运。再横看当代几本孟姜女故事的小说文本,长城的倒不再仅仅是对女主人公所代表的下层人们命运的颠覆与抗争,而更是一种深层的思考:长城需要建吗?要建,它的雄伟,它的建筑技艺,以及暂时对外敌的抵御还是有益于时代与人类的。但是它的建立不能强迫人民用血肉来筑,而应该是人类运用高智慧与高科技来自觉地建成,这样的长城才真的是中华民族国富民强,社会仁义和谐,人人实现自我的天堂世界的象征,而不是人民苦难的代名词。
3.泪与水和悲的关系以及文化内涵
《碧奴》中有很多关于“水”的意象,如:乳汁、河水、泪泉(池塘里的)、雨水、洪水,更不要说贯穿全文的泪水了。液体状的物质,是流动的,多么像人生动态的悲欢离合,随时变化,流动易逝,生命易逝,人生易逝。水从上而下地流走着,载着许多哀愁,付诸一江春水,终成为一场空虚,人生喜怒哀乐,利己算计,都不过一弯终逝去的流水,所以人生应该去追寻真理,这与名利无关。人们追逐永恒,千年前的古人就明白这个道理,要千秋万古名,所谓“立功、立德、立言”,永恒是一种德行。在《碧奴》中苏童塑造的女主人公显然是欲树立一种高贵的穿透古今、流芳万世的至情至理的品德。孟姜女成为了一个文化符号,她意指着多层意蕴:知书达礼的道义妇、爱情忠贞的绝世美人、反抗礼教和强权的勇士、人类精神(灵魂)的救恕者。她,惟爱、惟美、惟善、惟真……最符合人间普世价值取向。人生百态的哀愁疑是一弯春水终逝去,同时“水”厚德载物,含蓄地暗示碧奴的真、善、美的品质能感天动地,感动世人。碧奴内外兼美,可谓“上善”,她若水一般,可容纳万水千山,也可润泽万物生灵,包括人。小说中碧奴舍己救人,即使那些人都会害自己,也一心感化他们,最后她美好的品行就能感化苍生,使众人落泪,心意回转,良知重现。
4.坟墓与悲剧的关系及文化内涵
《碧奴》中多次提到与坟墓有关的意象(土坟、以坑为坟、棺材……),曲折地隐喻死亡是多么正常,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充满了变数,生命易逝。小说多处写到人找不到自己的坟墓,暗喻人们心灵的飘零无依,找不到归宿。活着,寻找身体的居所;死后,是心灵的归途。活着身体到处飘零,心灵浮动不安,死后灵魂怎可找到安栖之所呢?北山上的祖先魂灵到处游荡,找不到自己的坟地;老妇人死后变成青蛙跟着碧奴到处奔走寻找儿子;芹素的棺材被落在异地的水洼里,不愿下沉……这一组意象组成了一种不言而喻的意境:人身体死了,想要安息,可是人的灵魂却没有了归依,找不到了自我,当然不知道如何安放。让人欣慰的是女主人公碧奴,对自己是葫芦的归宿一直了然于胸,出门寻夫前摘葫芦、洗葫芦,意识到自己将死,弥留之际找小鹿人的挖坑为墓,要安放自己的灵魂,很显然这是一个心如明镜的女子。小说涉及人物众多,出场安排如老舍的戏剧《茶馆》,不同场景不同人物出场,却只有店家是不变的,意蕴来表现当时社会全貌,从面广中见意深。对于穿行于寻夫路上的碧奴,遭遇了形形色色的人物,她真是做到了“世人皆醉,我独醒”,在她那里有一个真正的“为人”的是非黑白的度量标准,所以对于别人非正常人的异化行为,这个女子的作为,正好表明她清醒于世,才会毫无疑问地确立自己死后如何安放。
男主人公被葬于长城城基下,意指强权对真善美的压制,女主人公的哭泣象征反抗,眼泪能使长城倒塌,这是真情战胜强理的民意体现,千百年来,众心所向,以至于孟姜女故事流传至今仍然脍炙人口,为大众喜闻乐见,不仅民间口口相传,更是引得一代代文人学子以其为蓝本大肆铺排解构。
5.路与悲剧的关系及文化内涵
孟姜女不再仅仅是一个女人,在从古到今的口口相传中,她所意喻的符号意蕴有几次扩展:从最初的知书达礼的烈女到爱情忠贞的楷模,再成为反抗礼教和强权的勇士,到苏童文中人类精神(灵魂)的救恕者。
苏童《碧奴》中的女主角一直走在寻夫路上,这条“路”是希望的征程之旅,是无奈的深陷之途,是绝望的不归之路。每段经历的路程,女主人公都会有一个不一般的情况。开始寻夫,她走在希望之路上,所以能昂首挺胸阔步向前迈;寻夫中途,她身陷无辜,却无能为力,所以只能任人摆布,随波逐流;机缘巧合,路的终点,企盼已久的希望,几经蹉跎,终于实现,虽到了胜利的彼岸,却只不过是一个华丽的结束,女主人公走的是一条不归的黄泉路。她殚精竭虑地爬着找到自己丈夫所葬之地,实现了自己的理想,却以自己生命的终结来完成了波折坎坷的寻夫之旅,这条女主人公自设的黄泉路也为她的忠贞殉夫唱响了一首千古绝唱。古往今来,孟姜女寻夫的路是在其征程未开始前就清楚自己必死无疑的末路,所以她的行程是一场毫无悬念的苦旅,她一寸寸迈出的步伐,一点点接近目标的过程也就是女主人公身体一步步走向死亡,而她救恕世人的精神品质得到一幕幕彰显与升华的过程。女主人公哭倒长城,并与城同绝,叙述达到高潮,却戛然而止,不再赘述,一个华丽的结局,再次引读者深思与回味。
苏童的长篇小说《碧奴》,并没有按故事的发展顺序对事件的来龙去脉做完全叙述,而是每一小节(节名)下自成一个片段(或画面),每一节都只是一种情景展示,每一节从叙述开始到结束都没有小的故事结局,后一小节也不再接着前一节的事件来叙述,全文呈现出片断的粘贴,以展示画面的方法来组织叙事,缺少的故事情节需要读者在接受故事的过程中能再创造性地完善,叙述顺序完全没有按故事顺序来延展,这就能唤起读者的阅读兴趣,调动读者的积极性,根据上下文与读者自身情况来填补故事空白。
碧奴的寻夫征途,贯穿着一条暗线。从开始她站着走的状态到任人摆布,例如被鹿人抬着去做鹿王坟的守墓人;作为百春台死去的小偷门客的妻子,被人用铁环锁在棺材上,被牛车拉着走;再到体力消耗殆尽,只能爬着走。三种状态中,任人摆布的境况持续最长,女主人公路遇之人都是为自身利益而不惜一切损人的“恶”人,尽管碧奴是一株洁白的莲花,却身陷淤泥,力不从心,这是女主人公寻夫途中最痛苦的日子。在陌生的旅途上,由于自身力量太过渺小,只得任人摆布,随波逐流。在邪恶的世俗中,碧奴对自身的命运是不可知的,在与“人性”抗争却无效后,只能被迫任人宰割而无奈地奔走,这些都意味深长地书写了每个人人生中的不可知性与无可奈何性。
三种运行状态,是伴随着女主角身体一点点地被消磨,体力渐渐不支的情况下而产生的。碧奴的寻夫征程,唱响了一曲人生绝唱,暗示了每个人的人生之路中都会遭遇到的生活:对希望的生活不懈追求;竭尽全力后面对生活无能为力的失望,甚至绝望,只能随波逐流;当命运机缘巧合再次升腾起希望之光时,拼死追求以期实现夙愿的坚忍不拔。
三、孟姜女故事重写的当下意义
进入21世纪,随着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后工业化时代的到来,粗鄙的物质化,精神的匮乏,当尼采惊呼“上帝死了”之后,人类信仰面临危机。从古老的神话传说中汲取精神营养也成为世界性课题。为此英国坎农格特出版公司(Canongate Books)发起的“重述神话”项目。苏童作为这一项目的参与者,积极发掘中国古典文化资源,参与当下的世界精神文化建构。一部《碧奴》可谓人生百象。损人利己,明哲保身,见风使舵,弃车保帅,落井下石,见死不救,装模作样……碧奴的好心助人成了多管闲事,多次害得自己身陷绝境却被世人认为是疯子。到底这个世界怎么了?人们还有什么信仰?是非曲直何在?人们魂归何处,死后哪里安放?是什么使这个世界颠倒了?是对金钱、权力、身份、生活的向往与追逐。人为了满足一己之欲,导致了一个怎样的结果。日月无光的世界一片昏暗,碧奴哭诉着内心的呐喊,不是控诉,更多的是希望,希望人们早日觉醒;是救助,正常的欲求虽需要,可是做为“人”的良心不能丢。不然这个世界就成了“非人”的世界了,这样生活在里面的人,有灵魂的,成了妖魔鬼怪;没有灵魂的,不过是行尸走肉而已。苏童的小说《碧奴》营造的一个个悲凉之境,蕴含着丰富的人类社会文化内涵。
[1]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董强,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马斯洛.人类动机的理论[M].许金声,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I206.7
A
1007-9882(2012)01-0101-03
2011-10-12
王春艳(1982-),女,四川南充人,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2009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程丽蓉(1972-),女,四川南充人,博士,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责任编辑:张 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