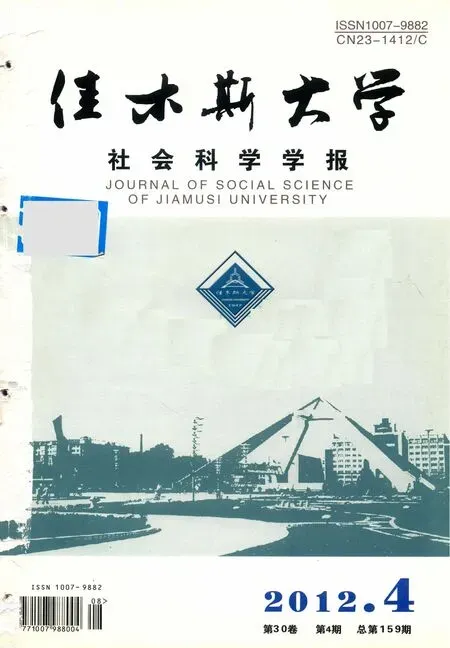时代背景下的知识分子形象探因
——以王朔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为例①
张艳阳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合肥230039)
时代背景下的知识分子形象探因
——以王朔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为例①
张艳阳
(安徽大学文学院,安徽合肥230039)
王朔的作品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深入人心,并且在当时成为一种“王朔现象”,这其中有着一定的原因。王朔对传统知识分子光辉形象的颠覆与反叛所引起的争议足以供人们津津乐道一段时间,在吸引普通读者眼球的同时足以让另一些学者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进行玩味。然而,王朔对知识分子形象的颠覆有着既定的因素。其中既不乏自身独特的经历,又有时代的烙印,它们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
王朔;知识分子形象;反叛;时代背景
谈到王朔,知识分子形象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他作品中对传统知识分子的“启蒙者”、“立法者”、“精英”形象的颠覆让我们不得不反思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在特定的时代中所处的地位、扮演的角色。文学是时代的产物,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文学形态。当然,由于时代的不同,知识分子所处的地位是不同的,其笔下的人物形象也不尽相同,知识分子身上所体现出的时代烙印是抹之不去的。
知识分子是社会中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群体,其最早出现是在19世纪的俄国。“它指特定的一群人,它们在大学受过教育,大部分历经西方文化的教养,自成一个有别于传统阶级结构的社群。”[1]但王朔以“反智主义”的方式使知识分子形象呈现出委琐与庸俗的特征,用反讽与调侃的方式暴露知识分子的负面形象。这种着力丑化与贬低知识分子形象的“反智”叙事有着一定的原因。“‘顽主’是特定的社会历史时期中的产物,‘顽主’及其生活是毋庸置疑的客观存在,它的出现有广泛的社会背景,具有某种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合理性。”[2]
一、自身经历在文本中的照应
王朔独特的经历对他的反知识分子写作姿态有着深刻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王朔的亲身经历塑造了他,他是时代的产物。王朔在《动物凶猛》中写到:“我一点不担心自己的前程,这一前程已经决定:中学毕业后我将入伍,在军队中当一名四个兜的排级军官,这就是我的全部梦想。”[3]可以看到在《动物凶猛》中,前部分大都与作者的经历非常相似。“我”逃课、泡妞、打群架,“我”由于“不用学习那些后来注定要忘掉的无用的知识”而使自己的动物本能得到了空前的解放。“一切都无须争取,我只要等待,十八岁时自然会轮到我。”而实际上,王朔本身也是如此——1958年出生,在文革中经历了中学时期,毕业后入伍,毕业后做过许多工作,随后便成为一个自由作家。
王朔作品中经常出现的“小时候”和“部队大院”这一概念便足以说明他童年及少年的经历在文本中的影响之大,在《浮出海面》中出现的那套父母单位分配的房子,在《我是你爸爸》中出现的马林生所居住的大院,就是分配的房子,《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中众人狂欢的地点也是主人公父母单位分配的房子,这都和王朔早期的经验不谋而合。特别是在《动物凶猛》中,许多意象的出现都与王朔本人的经历相吻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这一贯穿始终的形象便是王朔的少年时期。王朔在《自选集序》中写到:“挑选这些篇目是因为这些东西或多或少都含有我自己的一些切身感受,有过去日子的斑驳影子。”[4]
在少年时期,王朔便遇到了文化大革命,这时期正是其思想逐渐成熟之时。但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人们普遍没有受过正统的教育。文革对一代人的摧残是抹不去的伤痕。在反观文革的“清洗”中,人们对待它的态度莫衷一是。王蒙通过《春之声》中岳之峰等人的描写体现了改革开放后知识分子那种迷惘的心态,那种身份窘迫,精神困厄的表征,而张贤亮则克服了这种焦虑,他通过章永这类知识分子形象来展现在文革中知识分子从身份的遗失到再确认的历程。而王朔则没有潇洒地摆脱文革对他的毒害。因为他的人生观、价值观等对世界认识观念的形成恰恰是在文革时期,正是这段时光扭曲了他对世界的看法。王朔同样在《自选集序》中写到“:我成长过程中看到大多知识被滥用,被迷信,被用来歪曲人性,导致我对某些自称知识分子者的不信任,反感乃至仇视。”[5]在中学时期王朔看惯了那些妄自尊大,自认为知识在手,便把它们变成恃强凌弱的资本的老师的丑恶嘴脸。因此这不得不使他对知识分子存在一种偏见。这种偏见便体现在他的作品中,成了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反叛与颠覆。
二、历史沿革中的知识分子形象的身份确认
文学作品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既是作家的自我画像,也是对知识分子本性的书写,和作家所处的时代也有关联。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多少都会是作家对时代背景下的知识分子的隐含了自我意识的精神写照。我们不能只看到王朔自身的原因,同时也应对知识分子本身进行反思,对知识分子这一特殊群体的特性进行梳理,从而找出其身上的弊端与缺陷。王朔用反讽的方式揭示了知识分子身上固有缺陷。例如在《我是你爸爸》中,对马林生的描写则是“反智”的方式,王朔对马林生的描写已近完美无缺,对马的心理活动昭然若揭。他是一个有点装腔作势同时又富于幻想的人,但在对待儿子时又时而施点暴力,时而与儿子称兄道弟,他的这种极其特殊的矛盾心理难道不能反映出他身上固有的弱点吗?王朔把这些小人物常见常新的动态勾画得惟妙惟肖。我们无不被《你不是一个俗人》中的赵舜尧的虚伪,《顽主》中宝康的卑俗,《我是你爸爸》中刘桂珍的霸道等知识分子之行径所深深吸引,让人发出对这些形象的“堕落衰败”的喟叹。
知识分子在充当启蒙者、立法者的同时也存在委琐、庸俗、自大等缺陷,在自身所体现的无限优越感中,他们始终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古往今来,有多少抒发自己的怀才不遇与忠贞抱负不都是其依附性的表现?毛泽东曾经说过:“他们不过是一张皮,依附在哪个阶级,就为哪个阶级服务。因此,他们具有较强的依附性、软弱性、虚伪性。”[6]
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群体的强烈要求政治参与的呼声源远流长,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孟思想就要求积极入世,儒家工具主义倡导知识分子应致力于国家大事,并且要求在政治参与中传承自家的思想观念,这种思想统治人们达两千年之久。一方面是知识分子想要通过入世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另一方面统治者把他们当作参与国家统治和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文人在任何朝代的政治统治中的意识都是非常强烈的,他们试图通过权利的获得来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实现自我身份的确认。
不难发现,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大都是与政治分不开的,例如屈原、王维、王安石,他们不是位居高位者,就是想通过启蒙者的角色实现自我身份的确认。
然而到了科举制废除的近代,知识分子的政治参与意识有所减弱,但仍然大部分存在。知识分子权利的丧失使其日益处于边缘状态。近现代以来,知识分子把他们的思想、愿望诉诸于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借以抒发自己的抱负与实现自我身份的确认。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出现以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都使得知识分子不得不依附于政治而存在。由于他们本身的敏锐性,使得要求走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形象们表现出了与时代、社会的不相协调。特别是在受极左思想影响的文革时期,知识分子被贬低为“臭老九”,地位更是处于社会的边缘。“只有在经历了接连不断的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之后,只有在被剥夺了人权,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自己是一个‘人’,我才明白我也应像人一样用自己的脑子思考。”[7]
知识分子的人生遭际是现当代作家创作中的重要题材,作家通过对知识分子形象的书写致力于探索他们的心路历程。例如鲁迅的《伤逝》,钱钟书的《围城》、谌容的《人到中年》都是反映不同历史时期的知识分子形象。这其中也写到知识分子身上的缺陷和性格上的弱点,只不过王朔是以一种颠覆性的笔调来写。人物形象的负面效应掩盖了他们身上的光芒。譬如古德白教条、刘书友的自私、关汉雄的孤傲、王明水的萎靡等。他笔下的这类知识分子的负面形象经王朔的加工便显得那样令人可笑,发人深省。在80年代诸多反观文革的作品中,知识分子形象的那种自私、庸俗和盲目的优越感暴露无疑。
三、商业大潮侵袭下的无所适从
20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出现转型,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面对信息爆炸和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文学被重新放置在一个新的空间,在这里传统的意识形态被消解,代之而起的是由商品化、文化消费共同构成的新的空间。文学创作不再是充当历史的书写者和政治权利代言人的角色。知识分子形象充分体现了在当时时代背景下受经济秩序的冲击所失去的优越感。
在社会转型期,经济利益的追逐也以不可阻挡之势侵入文学这块曾经圣洁的领地。王朔身上那种经由“大院文化”所带来的优越感开始下滑,被现实冲击波从高空中拍打在现实的泥土上。《看上去很美》中的方枪枪、《动物凶猛》中的少年“我”等这种“小时候”形象经常在王朔作品中出现的概念是作为对现实的对照面而出现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中王明、吴迪、胡亦均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迷失方向的一群人,面对商业大潮,他们只有用一种寂寥的方式呈现内心的苦闷与彷徨。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他们显得无所适从,只有在狂欢中来展现内心的苦闷。
陈思和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分为三类:庙堂、广场和民间知识分子。显然,依自己的才华和经历,王朔无疑属于民间知识分子之列,由于知识分子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所以王朔反抗、嘲笑前两类知识分子,隐含着对知识标准、价值标准的不屑。因此王朔是文化转型时期的产物。他很聪明地站在了知识分子的对立面对其进行批判、讽刺。这种顺应转型期的商业化的写作模式不仅给自己带来一定的知名度,同时也获得了一定的物质上的满足。
像王朔这样的知识分子本身就是一个综合体,一方面,他把世界过于精神化,给自己贴上崇高的标签之后又贬低物质存在,因此在商业大潮来临之后,以王朔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显得苍白无力。另一方面,由于中国知识分子本身所具有的优越感使得他们往往在政治权利方面找得依附,他们自身标榜的崇高使其难以接受庸俗,因此便陷入两难的境地。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象是: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他们不得不面对转型的时代语境。王朔便是顺应了时代转型的商业写作作家,他以笔下的“顽主”、“多余人”的形象在阐明着精神信仰与道德自律的缺失。他们有着知识分子的身份但内心却迷茫不已,体现出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对自我身份的焦虑。
特定历史背景塑造了王朔和他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显然是处于尴尬状态中矛盾的结合体。“王朔现象”得以在八九十年代出现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是离不开的,我们姑且不去评价王朔作品本身的好坏,但他以笔下的反知识分子形象足以使其成为当时的一个“现象”,并且在当时乃至以后的很长时间引起人们的争议,单就这点来说,王朔于自身而言是成功了。
[1]俞可平.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知识分子[C]//赵宝煦.知识分子与社会发展.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35.
[2]常清华.论王朔的顽主世界[J].郑州大学学报(社哲版),2009:12.
[3]王朔.王朔自选集[M].北京:华艺出版社,1998.
[4]沙莲香,等.中国社会文化心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22.
[5]巴金.随想录[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I207.42
A
1007-9882(2012)04-0103-02
2012-05-20
张艳阳(1989-),女,安徽宿州人,安徽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责任编辑:黄儒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