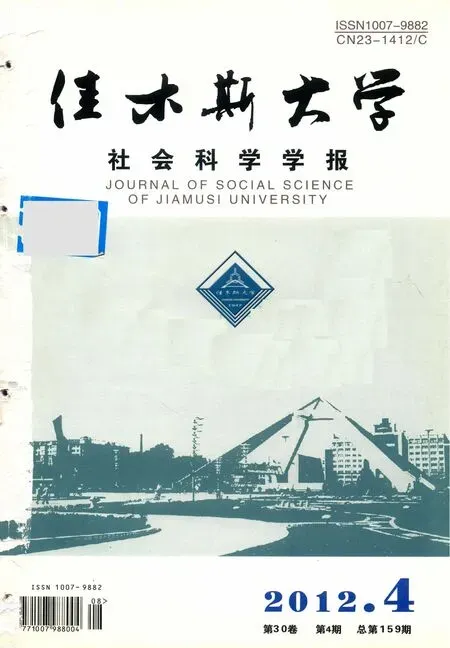从自欺到自由的勇气
——浅析《可以吃的女人》中玛丽安的存在意识①
杜 婷
(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山西临汾041004)
从自欺到自由的勇气
——浅析《可以吃的女人》中玛丽安的存在意识①
杜 婷
(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山西临汾041004)
加拿大“文学女王”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十分关注在男性统治的世界中妇女的命运和生存状态。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可以吃的女人》将人类生存的基本活动“进食”当作一个象征,诠释了传统社会施加在女性身上的压力。存在主义最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人的生存的思想和自由的意识。从存在主义角度解析《可以吃的女人》,可以看出女主人公玛丽安从自欺状态走向自由状态的发展历程,从而呈现出其作为一位女性回归自我、挑战命运的勇气。
阿特伍德;存在主义;自欺;自由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1939-)是加拿大享有国际声誉的小说家、诗人和文学评论家。她的小说大多以妇女生活为题材,小说的女主人公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职业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受到传统价值观的束缚,在婚姻家庭与社会中处于边缘性地位。《可以吃的女人》(The Edible Women,以下简称《女人》)是阿特伍德的第一部长篇小说,1969年出版后立即引起评论界的注意。该书探讨了在男性占主体的世界中女性心理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以及她们对自己的生存境遇做出的选择和突破。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玛丽安是个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女性,从表面上看,她的工作与爱情都比较顺利。但玛丽安在内心深处却始终觉得在各方面都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随着婚期的临近,她渐渐无法正常进食。最后,她决心摆脱这种社会施予的压力。在婚礼之前,她烤了一个女人形状的蛋糕,将这个“可以吃的女人”作为自己的替身献给她的未婚夫,从而与过去的一切一刀两断。
“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是西方20世纪一种重要的哲学与文化思潮,不仅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文学创作与人们的精神状态,同时也成为理解人的生存状态与存在处境的重要的方法思路。借助存在主义思路,我们可以更好地窥见《女人》中人物的生存困境与存在意识。本文即选择从存在主义视角对这部小说进行解读,主要采用存在主义思想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的相关理论,对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玛丽安进行解析,揭示其从在焦虑中的“自欺”状态走到自由解放状态的精神历程,从而见证其面对社会压力时进行选择的勇气。
一、生存中的焦虑状态
在《女人》中,女主人公玛丽安经常处于一种潜在的焦虑处境中。萨特指出,“我的存在引起焦虑是因为我自己对这种处境的反应产生了怀疑。”[1](P208)所以,焦虑作为一种精神状态是人物对自身的生存处境或存在境遇的心理反馈,这种反馈首先表现为“怀疑”。玛丽安的焦虑感的产生就是来自于对生活现实的某种怀疑。在这种状态中,一个存在者能意识到他自己可能有的非存在,体验到自己的有限,这是人之为人的自然焦虑。
在小说第一章,玛丽安带男友彼得去公园大饭店的酒吧与多年不见的好友伦见面,她的舍友恩斯丽装扮成天真少女不请自来,意图结识伦并让他成为自己怀孕计划的免费人工授精的替身。玛丽安看到这一情形非常恼火,却为是否该拆穿恩斯丽而左右为难。吃饭时玛丽安因焦虑而离开座位,彼得和伦几乎没有注意到她的举动。玛丽安无意识地落下眼泪,这体现出她内心的焦虑及受到忽视成为“他者”的委屈。彼得和伦完全掌握了聚餐时的话语权,而玛丽安只被当作舞台上的道具。玛丽安意识到自己只处于一种边缘的存在状态,她的第一个反应是非得出去不行。他们刚走出饭店,玛丽安就猛地跑了起来,她漫无目的地拼命奔跑,而这正是玛丽安在焦虑中逃避现实的表现。
在奔跑中玛丽安被彼得截住后,他们四人一起去伦家做客。彼得和伦在音乐中畅谈,而恩斯丽决心扮演一个文静小女孩的角色。玛丽安再次意识到在男性话语环境中自己只能做个旁观者、局外人,于是她就躲到了伦的床下,把他们看作“上面”,而自己在底下的世界自得其乐。这是玛丽安在焦虑中做出的异常反应。
玛丽安的焦虑意识同时体现在工作环境中,她工作的办公室占三层楼,楼上是主管人员和心理学家,那里都是男子,负责同客户洽谈,他们的办公室装修得奢华而现代。而下一层的调研人员全是家庭主妇,她们计件取酬,挣钱不多,而且无论怎么努力也不可能晋升到楼上去。令玛丽安心烦意乱的还有她被迫参加公司的养老金计划,被动地接受自己不感兴趣又不曾参与制定的规则。玛丽安的焦虑显现为对自我把握的缺失。“焦虑是从存在的角度对非存在的认识”[2](P29),玛丽安潜意识中认识到自己无法把握自我,受到男权社会的压迫和威胁,而焦虑正是在不能应付威胁而产生的痛苦之情。
人在焦虑中处于一种迷茫停滞状态,这停滞状态下有两种选择:一是选择“自欺”,逃避所焦虑的现状,掩盖焦虑的情绪;二是选择超越,冲破迷茫,寻找方向,继续前行。玛丽安无意识地选择了“自欺”,她对自己的焦虑处境进行了逃避。
二、焦虑状态下的“自欺”
人们面对焦虑时,最常见的形式就是选择逃避。玛丽安即是如此,她采用形式是“自欺”。自欺并非表面的自我欺骗,而是构成一种深层的心理动向。“自欺”(mauvaisefoi)作为存在主义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首先提出的。“自欺”为意译,直译为“坏的相信”,是指一种介乎真诚与欺骗之间的状态,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自我欺骗”。萨特认为:“我能有在焦虑内部虚无化的能力。这种虚无化的能力在我逃避焦虑时使焦虑虚无化,在我为了逃避焦虑而成为焦虑时,这种能力本身化为乌有。这正是所谓的‘自欺’(mauvaisefoi)。”[3](P79)
在《女人》中,玛丽安作为一名知识女青年意识到女性只能是男权社会中的“他者”,而她却在内心深处通过使这种认识“虚无化”,从而将焦虑隐匿在意识的背后。但是焦虑并没有消失,自我的处境也没有改变,现实的问题仍然存在,这就是其“自欺”的体现。这种逃避既是对未来的一种努力,同时也在企图消除过去的威胁。玛丽安认识到在过去的工作生活情境中,她确实受到某种压迫和威胁,为摆脱这种威胁,她认为努力扮演好彼得太太这个角色是唯一的出路。
在办公室聚会时,玛丽安注视着同事的身体,认为她们就像办公室里的桌子、椅子、电话一样只是具有某种形状的客观存在。萨特在他的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中将存在分为两部分:自为的存在(being-for-itself)和自在的存在(being-in-itself)。自在的存在是指重复不变的物质存在,即是其所是,他是人类和动物、植物共有的存在;自为的存在指的是变动的、有意识的存在,它仅为人与人所共有。“自为的存在规律作为意识的本体论基础,就是在对自我在场的形式下成为自身。”[3](P118)玛丽安把同事看作物因为只看到她们自在的存在而没有看到她们自为的存在状态,因为父权制社会确立了女性的“他者”地位,女人的“自为”存在长期被剥夺,以至于女性忽视了自身及彼此自为存在的权力。玛丽安觉得这些女人构成一片厚厚的马尾藻的海洋,让她透不过气来,但她却没有意识到自己也是这些女人其中的一员,她内心要掩盖这一事实。萨特认为,“对于实行自欺的人而言,关键恰恰在于掩盖一个令人不快的真情或把令人愉快的错误表述为真情。”[3](P84)他指出,生活中常有这种情况:人是一个角色而不自知,或者人根本不去成为一个角色,这就是“自欺”。玛丽安认为某个坚实清晰的东西可以证明她的自为存在,结婚后她就可以不用再干这份枯燥的工作,不用参加养老保险计划,“西摩事务所保险库里某个地方某只看不见的手正把我的签字给抹掉了。”[4](P93)其实这是一种焦虑状态下的“自欺”行为。
在接受求婚后,玛丽安觉得彼得注视她的次数越来越多。当他们躺在床上时,彼得会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她,彼得的注视对于玛丽安有着一种根本的剥夺性和侵占性。萨特认为,“人的‘自欺’正来自他在明确感觉到被他人‘注视’的时候。既不愿意或不能够正视他人的‘注视’,也不愿意或不能够正视被他人‘注视’着的自己。”[3](P51)彼得的注视让玛丽安意识到自己成为客体,自己的主体性被剥夺。他的注视如古希腊女妖美杜莎的眼睛,让玛丽安似乎面临着被化为一块顽石的死亡威胁。
“自欺”的本质是自我的超越性与事实性分离了,“自欺”是一种人生的分裂,既分裂于自我又分裂于环境。玛丽安在焦虑的状态中选择“自欺”的生活方式,即是对自我存在本身的否定,又是与周围生活环境的分裂。
三、“自欺”状态下的延缓
自欺并非一时的意识,往往具有一定的“延缓”性。这种延缓自欺是对自欺自身的一种维持,从而能够将焦虑一直掩盖下去。可以说,焦虑没有停止,自欺就往往不会停止。主人公玛丽安在“自欺”中就经历了一段延缓的过程。
玛丽安在答应彼得的求婚后,她告诉恩斯丽“在我的潜意识中,我也许一直想嫁给彼得。”[4](P87)这句话其实也是为了说服自己承认嫁给彼得是个正确的选择。在超级市场购物时,玛丽安认为对两种不同牌号的同类商品做出选择,其中没有多少理性成分,而且这让她有种厌恶感。玛丽安在自欺状态下对选择进行了逃避。“最近一段时期,她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像个旁观者一样,以一种心不在焉的好奇心情,观察自己的一举一动。”[4](P118)随着婚期的临近,彼得常带她出席一些朋友的酒会,但玛丽安在那里大多只是保持微笑,一句话也不说。在自欺中,人们把自己的存在确立为一种是其所不是,或不是其所是的存在。
到了彼得举行最后一次晚会的日子,玛丽安花了一下午的时间做发型、买衣服,都是为了迎合彼得的喜欢。在装扮前洗澡时,她在水面上看到自己的身体觉得并不是真正的自己。这时玛丽安还处于自欺的分裂状态,并且努力让自己保持这个状态,因为她自认为这是自己的该有的状态,如果走出自欺后果不可预知。在晚会中,玛丽安告诉自己应付的还行,她认为这热闹的晚会场景就是彼得内心世界的真实反映,而正是自己唤起了彼得的内在本性,这使玛丽安体会到了一种存在感。但是当她透过时间走廊幻想彼得四十五岁时的情景,自己却不在这情景中。她继续寻找,看到一个身穿红衣服毫无立体感的小女子就像一个纸做的女人,这使她顿感陌生和迷茫。彼得的照相机闪光将她唤回了现实,玛丽安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未来会处于一种丧失自我、毫无个性的自在的存在状态,那是种空虚的存在。
这时,玛丽安觉醒趁早脱身还不算太晚,她大胆做出选择,选择离开酒会,离开彼得。她走出大门,沿着大街奔跑起来。但这次不再是逃避,而是勇敢的做出了选择,选择打破“自欺”状态,超越自我,这是玛丽安“自欺”延缓状态的终结。
四、走向自由的勇气
玛丽安从订婚到解除婚约的过程,是一个打破自欺状态、寻求自我的发展历程。玛丽安的反抗主要是以奔跑与拒绝饮食两种方式呈现出来。
对于奔跑,文中有三次详细的描写,这三次奔跑体现了玛丽安自我意识觉醒的递进过程。第一次是玛丽安、彼得、恩斯丽与伦第一次聚会从酒吧出来后,她开始无意识的没有方向的狂奔。这次奔跑是玛丽安对焦虑处境的逃避,正因为没有方向,最后只能再次回到彼得身边,并答应了他的求婚,这表现了她对命运的妥协。第二次奔跑是玛丽安从彼得的酒会上偷偷逃出来,沿着大街奔跑,她的目的地是洗衣房,到了那里找到邓肯她就会有一种安全感。此时的玛丽安已经走上了反抗之路,但她还并不清楚反抗的方式和途径。她认为邓肯能给她一定的指导或者邓肯能让她体会到自己是真实存在的。这种存在感能给予她勇气继续走下去,继续突破现状,超越自我。第三次奔跑是酒会后的第二天,玛丽安不知从酒会上逃跑后如何回去面对一切,邓肯拉着她在陌生的城区拔腿飞跑。在奔跑中玛丽安似乎看到身上的红色连衣裙在空中破裂,如羽毛纷落。这象征着过去的处于自欺状态中的玛丽安在奔跑中粉碎、在反抗中毁灭。而突破自欺状态的“我”,是个全新的玛丽安。这次奔跑把玛丽安带到了空旷的原野上,回归大地是回归自我、自我重建的一种形式。这是玛丽安反抗命运成功的曙光。三次奔跑体现出一种反抗意识的递进过程,象征着玛丽安由焦虑、自欺到超越自我的发展历程。
玛丽安的第二种反抗方式就是对食物的抗拒。随着婚期的临近,玛丽安的身体开始渐渐无法正常进食。萨特指出:“吃,事实上就是通过毁灭化归己有,就是同时用某种存在来填充自己。这种存在被给定为严格说来的温度、密度、滋味的综合。总之,这种综合意味着某一存在。”[3](P781)玛丽安拒绝接受食物,体现出她拒绝接受存在本身或者说她拒绝接受食物的整体向她提出的存在方式。这是身体作为自为的存在向她提出的抗议。阿特伍德研究专家克罗·安·豪威尔斯(Coral Ann Howells)在《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一书中说,玛丽安“身体的厌食形成了歇斯底里式抗议话语的一部分。”[5](P28)玛丽安意识到彼得一直想占有自己。占有,就是想通过一个特殊的对象占有世界。在爱情中,恋爱者希望自己对被爱者来说代表世界上的一切。恋爱者想先天的作为对别人自由的客观限制而存在,这符合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spinoza)的说法,自由只能被自由所限制。玛丽安想摆脱这种自由的限制,于是就做了一个女人形状的蛋糕作为自己的替身送给彼得。她通过做蛋糕来代替自己表明自我存在意识的觉醒,体现了她对自我存在的肯定。自我肯定指的是对某种(至少是潜在的)威胁或否定自我的东西的克服。
在玛丽安走向自由的路程中,除了自身存在意识的觉醒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作为一位女性,在与男性的可能性交流中获得的成长。对于她突破“自欺”状态的过程中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邓肯。文学批评家W·J凯斯(Keith W.J)认为:“邓肯代表的是玛丽安的本能,是一个精神向导,可以给予她智慧。”[6](P48)这个瘦小古怪的男人确实让玛丽安有一种真实感、存在感和被需要感。邓肯这一形象体现了玛丽安的自我意识和存在意识,他代表自欺状态下另一个真实的玛丽安。邓肯作为一名英语系研究生,关注时间、死亡和情欲等人生的基本存在概念,可见他对人的生存状态和存在境遇有着严肃的思考。他客观地告诉玛丽安,她走进了一个自己创造的死胡同,得自己想办法走出来。这暗示玛丽安该打破“自欺”状态,勇敢地做出选择,面对自我,拥有存在的勇气,这种存在的勇气显示了存在的本性。
小说结尾处,玛丽安请邓肯吃那个没有吃完的女人形状的蛋糕,这表示男性与女性的关系趋向于一种和谐融洽的状态。存在主义哲学先驱索伦·克尔凯郭尔(Soren Aabye K ierkegaard)指出,一方面人在当下生存中有自我超越性,另一方面人对自我的超越不可脱离现实的生存,它是在“关系”中得到定义的。玛丽安拥有了走向自由的勇气,勇敢的超越自我,但这种超越是不能脱离社会关系的,她仍然要在她的现实中去选择属于她的生活道路:结婚或者工作。不过玛丽安与邓肯同食蛋糕体现出的平等与和谐,正是女性所追求的理想的存在状态。
生命是一种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存在的力量得以自我实现出来。玛丽安由自欺走向自由的过程,体现了女性回归自我、挑战命运的勇气。这部小说也折射出作者阿特伍德面对女性面临的各种现实问题的关切及促进性别平等的自觉。
[1]万俊人.于无深处——重读萨特[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
[2]P.蒂利希.存在的勇气[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
[3]让-保罗·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等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4]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可以吃的女人[M].刘凯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5]Coral Ann Howells.Margaret Atwood Second Edition[M].New Y ork:Palgrave Macmillan,2005.
[6]Keith,W.J.Introducing Margaret Atwood’s The Edible Woman[M].T oronto:ECW Press,1989.
I106.4
A
1007-9882(2012)04-0069-03
2012-06-18
杜婷(1988-),女,山西晋中人,山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责任编辑:陈如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