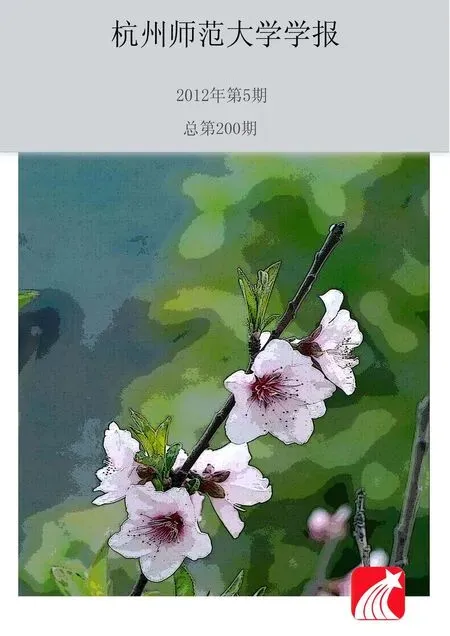重思南社的文化政治与“近代性”
张春田
(香港科技大学 人文学部,香港 999077)
文学研究
重思南社的文化政治与“近代性”
张春田
(香港科技大学 人文学部,香港 999077)
既有历史编撰学中的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对独特的中国“近代性”的理解均有不足。面对巨大的时代变动特别是革命,南社群体发展出用以呼应的“情感结构”与文化政治。在共和危机到来时,他们遭遇了有关“介入”的困境。一旦改变视野,南社与“近代性”仍有很多值得探索的空间。
南社;历史编撰学;文化政治;近代
一 历史编撰学中的两种范式
无论将“20世纪”看作是“漫长的”(如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fighi])还是“短暂的”(如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阿瑞吉所理解的“20世纪”开始于1873年的大萧条,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特殊阶段;而霍布斯鲍姆则从革命和社会主义所造成的断裂的角度,以1914和1991年作为“20世纪”的起讫。 Giovanni Arf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 New York: Verso, 2010,new and updated edition; Eric J. Hobsbawm, The 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91, London : Abacus, 1995。,也无论将“20世纪”建构为“战争与革命的世纪”、“恐怖与极权的世纪”或者“资本主义与自由的胜利的世纪”,[1]对于中国而言,“20世纪”翻天覆地的变动与转型在历史上无疑是罕见的。这是一个独特的政治、思想与文化创新的时代,也是一个深刻地改变普通人的信仰、伦理价值和日常生活的时代。我们今天以及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都生活在20世纪的影子里,不管情愿与否,都无法轻易告别。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与解释20世纪中国波澜壮阔的进程,不仅是一个成熟的历史文明共同体的自我需要,更是继往开来,发展出竞争性的普遍性论述的起点。
从政权更迭的角度看,20世纪中国经历过三个阶段,即晚清(1911年以前)、民国(1911-1949)与共和国(1949-)。但在内地传统的历史叙述中,更多使用的是另一种分期方式,即近代(1840-1919)、现代(1919-1949)与当代(1949-)。以鸦片战争为近代中国的开端,以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为近代化的初始阶段,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现代起点,而以新中国的建立作为当代时间的开始。这种分期学正好呼应了“革命史”叙述中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三阶段的模式,或者毋宁说前者是以后者为前提的。更重要的是,三阶段不是三个均质的、空洞的时间阶段,而是被认为在线性向度上处于由低到高的进化、发展序列中,贯穿于这个序列的一条红绳则是“革命”。*中国历史分期问题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核心是唯物史观解释中国历史的有效性,参见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翁贺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六章,第149-184页。毛泽东总结了20世纪3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的唯物史观的成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中提出了解释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框架,即“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对近现代中国历史性质作出了系统的论断。收《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584-617、623-670页。新中国成立后,这样的分期被依据形势补充完整,并加以普及化与合法化。在历史编撰上的体现之一,即是胡绳在1954年把1840-1919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讫,然后再细分为若干阶段。这后来成为史学界的主流观点。参见胡绳《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历史研究》,1954年第1期,第5-15页。
以这种分期意识与论断为基础,“革命范式”建立了起来。它承担着将革命历史自然化,确证政权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功能,在界定革命性质、讲述革命起源、描绘革命进程、展现革命图景时,遵循了一整套的语法规则和标准。它不仅需要根据现实的政治功利,对于历史变动进行选择、组织、辩护、增删、修饰和改写,随时准备调整结构,更新脚本,与时俱进;而且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化(institutionalized)过程,又将自身经典化,排斥了任何“非法”的另类叙述,成为想象和讲述历史的唯一方式。
在“革命范式”下,从1840到1919年差不多80年时间被归为“近代”时期,位置暧昧。一方面,这段时期在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上已经出现了诸多新变,从而不同于“古代”;但另一方面,作为真正“现代”(更准确地说是“革命”)历史的前奏和准备阶段,其政治、经济、思想与文化变革的意义更多在于过渡性,甚至只能作为“此路不通”的负面教训。毛泽东以“五四”作为“旧民主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的分水岭的论述,集中代表了“革命范式”对于“近代”的态度。他认为:“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五四”以前,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而“五四”以后,“共产党人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成为了文化生力军。领导阶级也发生了变化,“五四”以前中国的文化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而“五四”以后中国文化革命的指导者则变为无产阶级。历史主体和文化形态的变化,逻辑地导致“近代”因为不够“革命”而需要被替代。毛泽东强调:“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它的失败是必然的。”*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57-659页。胡绳的《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围绕“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坚持“三次革命高潮”,可以说是“革命范式”关于中国近代历史研究的代表作。
毛泽东的论述奠定了“革命范式”关于“近代”的讲述基调。通常的历史讨论会着眼于“反帝反封建”问题的探索,而且以为“五四”准备了哪些历史条件的思路来取舍和评判近代人事。相较于“五四”的创造性断裂,资产阶级被认为在“近代”显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在“革命范式”的进一步展开中,“五四”越来越被凸显,成为古代中国与现代中国的分界线。如此,“近代”的“前史”意味更加强烈,成为了“古代”的一个尾巴。*比如,在大陆大学中文系的学科体制中,“近代文学”通常隶属于“古代文学”教研室;讨论古典文学为主的“中国文学史”的课程和教材,一般也都会把下限设置在“五四”,从而把“近代”纳入“古代”领域,而“五四”以下才是“现代文学”的学科领地。
这种强烈的历史目的论式的史观,在最近30多年来,受到了很多质疑和挑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现代化范式”以现代化的追求来替代革命进程,作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剧情主线”(story line)的尝试。事实上,以“现代化范式”为核心的叙述,已经成为今日中国历史编撰的新主流,可以称之为“现代化范式”。
“现代化范式”一方面从1976年以后改革开放的建设大业中汲取历史势能;另一方面也受到西方(特别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知识生产的深层影响。从费正清的“冲击-反应”模式到列文森的“传统-现代”模式,都着眼于中国的政治与社会朝向现代化的“永久性变化”,也都强调变化的动力首先来自西方的外来冲击。*参见Ssu-yu Teng and John K. Fairbank,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4;费正清等《东亚文明:传统与变革》,黎鸣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关于费正清的中国史观的评价,参见王新谦《对费正清中国史观的理性考察》,《史学月刊》,2003年第3期,第13-18页。虽然这种较为明显的西方中心主义思路,在其后倡导“中国中心观”的汉学家们那里受到反思和批评;*参见柯文(Paul Cohen)《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林同奇译,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费正清的学生詹姆斯·佩克(James Peck)则更为敏锐地揭示了费正清所代表的现代化理论的误区,他认为现代化理论的要害在于它本身自以为是,以亚洲国家独立的保护人自居,假定美国天生就具有以非暴力方式促进社会进步的能力,缺乏自我批判的精神。所以,只有通过反躬自省,才可以准确地、公正地理解和同情中国的革命以及世界其他各地的解放运动。参见龚忠武《试论费正清及其哈佛学派的得失成败》,《北京大学研究生学志》,2008年第3期,第17-23页。但是,以现代化为指向的衡量标准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只不过汉学家们开始发掘有利于中国向现代转变的各种内在条件和基础。不仅汉学家,一般的社会学者也开始抽象地使用现代化的指标来衡量中国。*如吉尔伯特·罗兹曼(Gibert Rozman)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此书英文版出版于1982年,后由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翻译为中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通过对中国人追求现代化和打造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实践的叙述,“现代化范式”似乎实现了把中国现代史整合进西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进程中,中国不再因为“革命之谜”(the mystique of revolution)而外在于“普遍”的世界史。[2]
随着西方历史学界的现代化叙事的引进,“帕森斯化了的韦伯”及其他社会科学界的现代化理论的翻译和介绍[3],更主要的是中国正在发生的市场化现实的刺激,20世纪80年代以来,内地的历史学界也开始明确地从现代化角度讨论中国近现代史,到了90年代这种叙事更加明确和普遍。*如罗荣渠主编《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是国内较早介绍比较现代化理论的著作;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第一卷,1800-1949)》(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是国内第一本从现代化变迁的角度系统地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著作。应该说,“现代化范式”对于重新发掘和确立中国“近代”尤其是清末民初的政治、经济、思想与文化的开拓性意义,贡献甚大。原先在“革命范式”中湮没的大量历史人物、事件与文化实践,以及军事、司法、教育、财政、传媒、卫生、城市、家庭、娱乐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建设与日常生活变迁,正是在“现代化范式”的支持下,得以重新浮出水面,得到正面评价,并成为历史研究中的显学。就像有学者为颠覆人们对“近代”的刻板印象,特意提出“近代有多现代”的追问一样*王德威语。参见李楠、徐金柱《近代有多现代?——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国际研讨会综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6期,第189-199页。,这些研究也努力扭转“革命范式”下近代“被压抑”的局面,为其在“现代”的星空上标示出显著而耀眼的位置。与此同时,革命想象与实践则被视为现代化的阻碍而打入另册,近代历史上与革命相关的历史实践也逐渐淡出研究者的视野。[4]
如果说“革命范式”的背后,有马克思主义阶级革命的逻辑在支持;那么我们也不难发现启蒙理性对于“现代化范式”的根本影响。从康德以降西方思想传统中的启蒙理性,相信个人主体性的生成,相信理性的力量能够“为自己立法”,接受现代性的一系列合理化分化,认为启蒙的社会规划具有超越传统文化与伦理的普遍正当性。*关于启蒙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最早源于康德的思考。参见福柯(Michel Foucault)《什么是启蒙》,汪晖译,收入汪晖、陈燕谷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第422-442页。更详细的关于启蒙问题的各种反思及回应,参见詹姆斯·施密特(James Schmidt)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徐向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启蒙理性不仅仅是思想方案,更在西方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并伴随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而获得文化霸权。
时至今日,把现代化等同于人类幸福的迷思即使在经验意义上也遭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而对启蒙理性的反省更是20世纪批判理论不断突进的重要收获。从法兰克福学派批判工具理性对人的物化以及产生新的专制,到后殖民批评指责西方将地方性的现代性经验普遍化到充满历史差异的、不平衡的全球空间中[5],都让我们意识到“现代化范式”的陷阱所在多是。换言之,任何一个文明共同体的“现代”的建构都不能简单照搬他者的经验,不能由一系列固定的观念或物质清单构成。单一的现代化迷思应该被复数的、具有反思性的“现代性”所取代,并且应该通过具体化的主体来检视、选择和打造。
上述关于历史分期与叙述范式的讨论提示我们,在处理中国的近现代历史问题时,偏执于哪一端(无论是传统革命范式、还是现代化范式),都存在明显的缺陷。章永乐套用尼采的话,把20世纪革命胜利者带有历史目的论色彩的自我肯定的、建立革命道统的叙事,以及与之相反的,痛感20世纪历史的动荡与苦难,把历史未实现的其他可能性树为新的道统的“遗憾/后悔史学”,一并称为“纪念碑式的历史”。[6]他试图在宪政与国家建设的视野中,寻找响应这两种叙事的新可能。我以为他的这种取向是重要的。对于中国近现代史编撰而言,如果排斥了有关革命的思潮、论争和话语实践,就无法理解中国现代民族国家建立的基础以及这一新的政治形式所要应对的难题。借用裴宜理在一篇演讲中使用的标题,即“研究中国政治:焉能告别革命”。[7]而同样重要的,如果忽视了在“革命”正典(canon)建立之前,纷繁复杂、多声复义的“革命”想象和实践;忽视了“革命”正统之外,中国人对日益严重的整体性意义和政治危机的其他回应方式(或者直接称之为“现代性试验”),忽视了文化复兴的渴望,那么,就无从把握完整的中国经验,也无法解释传统到现代的延续性。“革命范式”更多关注的是中国历史的特殊性,“现代化范式”则更多关注中国与普遍性相符合之处。然而,正如酒井直树所分析的,这种对立更是一种同谋:
持有普遍主义观点的人和持有特殊主义观点的人各自都说他们与对方不同。与双方所宣扬的相反,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是相互加强和相辅相成的;它们之间从不存在真正的冲突;它们彼此需要,而不得不努力寻求一种对称的相互关系,以避免一场对话式的碰撞,这种碰撞势必会破坏它们所谓安全和和谐的独白世界。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为了隐蔽自己的毛病而互相认可对方的毛病,恰似两个同谋犯的狼狈为奸。在这一点上,国家主义这样的特殊主义决不可能是对普遍主义的认真的批判,因为二者是同谋犯。[8]
如果如酒井所说,普遍性与特殊性是相互配对的现代性组织装置,两者在貌似对立的关系中分享着共同的对于世界的同质化理解,也受制于资本主义历史及其想象的视域。这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相互配对”所具有的强大的吸附力,往往使得各种本来具有挑战性的历史叙述尝试,重新被组织进一种固定的位置而失去批判性。在对于中国“近代”的思考和描述中,我们就很容易发现如下颇为讽刺的现象:“在中国发现历史”最后变成“在特殊的中国发现普遍的历史”,“多元的主体”不过以另一种形式被重新组织到西方普遍主义单一中心的支配结构之下。从这个意义上说,需要对“革命”和“现代化”都先“打上括号”悬置起来,将“革命范式”与“现代化史范式”之间的对立关系改变为对应性、参照性的关系,更后设地反思两者的共谋关系,进而超越革命/现代、地区/全球、特殊性/普遍性的二元对立的框架,重新确定讨论问题的平台,以发展出替代性叙述结构来。*比如,汪晖“反(资本主义)现代性的现代性”的概括和描述,即是一种尝试。而刘禾则突破传统的讨论主权的方式,以符号在主权想象与帝国冲突中扮演的角色,对晚清国际政治建构出一种替代性讨论框架。王德威则尝试从“抒情传统”在现代的延续和发展的角度,给中国现代性带来新的论述。参见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关于现代性问题答问》,《天涯》1999年第1期;刘禾《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杨立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9年;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北京:三联书店,2010年。最近一本访谈集,汇集了近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重要学者的各种思路,参见郑文惠、颜健富编《革命·启蒙·抒情——中国近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学思录》,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11年。
二 何谓“近代”
“革命范式”的“近代的失败”,或是“现代化范式”的“近代的成功”,都是在绝对主义观念中看待“近代”,却回避了对历史过程的流动性和独特性。按照张灏先生的说法,大致从1895年开始至1920年初,是中国思想文化的“转型时代”:
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就前者而言,主要变化有二:一为报纸杂志、新式学校及学会等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大量涌现,一为新的社群媒体(intelligentsia)的出现。至于思想内容的变化,也有两面:文化取向危机与新的思想论域(intellectual discourse)。[9]
可以补充的是,这个阶段发生的不仅是思想文化领域的转型,还包括现实政治制度的转型。这是中国由传统帝国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最为重要的历史阶段。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遭遇到的严重危机在这个阶段达至顶峰,挽救危亡、重建社会秩序的各种方案竞相涌现,而影响20世纪中国发展的基本政治力量、话语实践、意识形态与文化认同也在日渐形成。如果我们把“现代性”的概念充分地历史化和开放化,放置在晚清以降中国具体的历史和空间语境,尤其是传统/现代、东方/西方、连续/断裂相互交织的多元背景中去理解和解释;那么,完全可以说,1895年以后的二十多年(即革命史中的“近代”,与现代化史中更倾向于使用的“清末民初”)所负载的历史经验和文化表述,恰恰构成了中国“现代性”最真实、最丰富、最紧张的部分,在现实与符号关系中指向一种新的集体性的自我意识的生成。
以1895年作为中国现代转型的开始,与传统的革命史之独标“五四”,其取径上的差异不言而喻。但这种对于“近代”意义的强调,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在一个毋庸置疑的“现代”的视野里来理解“近代”。追问“近代到底有多现代” 这样的方式,在我看来本身充满着问题,显然限制了我们对“近代”进行分析和诊断的能力。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对“近代性”的讨论,更具有启发性。他不是把作为地区性的、欧洲的“近代”(日语中用“近代”翻译modernity)的概念看作是不证自明的,可以作为解释中国的当然“方法”,相反,他提出:
如果要在本来和欧洲异体的亚洲看透“近代”,那就只有上溯到亚洲的前近代,并在其中找到渊源。也就是说,以亚洲固有的概念重新构成“近代”。[10]
他对明清中国思想和制度的研究,正是希望找到一系列新的概念来重构“近代”。比如,他对“乡里空间”和“乡治”的发掘,对“公论”和“封建”的重新探讨,对辛亥革命的渊源再解释,都体现了以“千年”为单位在历史纵深中理解中国的努力。在他那里,中国不再仅仅是对象,而是从对象的位置上解放出来,可以提供一种重新认识世界史的“方法”。[11]
虽然,沟口雄三所用的“近代”一词基本相当于汉语中的“现代”,但他对“近代”的批判性论述,却为我们重新使用“近代”这个概念来表述中国的“早期现代”(early modern),提供了某种基础。这里的“近代”,不再是依靠任何抽象的理论可以整合起来的叙事,而是充满不间断的运动与抵抗的张力场;不再是作为进化论和目的论意义上通向“革命”或“现代”的过渡,而是传统中国机体形态的蜕变与再生。“近代”同时具有对“现代”的追求和超越的双重性,或者更准确地说,始终保持着相对于经典现代性的差异性。它的内在逻辑就奠定在它既是民族主义的又是世界主义的,既是文明主义的又是跨文化的主动性之上。
或许引入一个比较的对象,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近代”的这种主动性。这就是日本的“近代”。日本在明治时期“脱亚入欧”,学习西方,在亚洲首先实现了全面现代化的过程。然而,这种没有挣扎和抵抗的快速“转向”,在竹内好看来,是一种缺少主体性的“优等生文化”。在写于1948年的《何谓近代》一文中,他对于“日本式”和“中国式”的现代模式进行了比较:
回心以保持自我而反映出来,转向则发生于自我放弃。回心以抵抗为媒介,转向则没有媒介。…… 我认为日本文化在类型上是转向文化,中国文化则是回心型文化。日本文化没有经历过革命这样的历史断裂,也不曾有过割断过去以新生,旧的东西重新复苏再生这样的历史变动。就是说,不曾有过重写历史的经历。因此新的人不曾诞生。在日本文化中,新的东西一定会陈旧,而没有旧的东西之再生。[12](PP.212-213)
竹内好认为日本的现代化过程中没有抓住抵抗的契机,因此始终没有克服奴隶性,未曾真正地获得独立。他摒弃了一般的对于先进/落后、成功/失败进行区分的标准。这在他对辛亥革命和明治维新的比较中,显得更加鲜明。他说明治维新的“成功”,应该被看作一种“失败”;而辛亥革命尽管“失败”了,却是“有生产性的革命”,“从内部不断涌现出否定性的力量”。[12](PP.214-221)
竹内好所谓的“抵抗”不能被简单化为反现代,因为竹内好再三强调“抵抗”是具有自我否定性质的“挣扎”。如果我们要为这种“挣扎”找到具体的历史形态,那么,中国“近代”所经历的自强、改良、变法、革命、启蒙等等多重关于“何种现代”的尝试和波折,以及这种尝试和波折在文化政治上的表述与影响,即深刻地呈现出这种自我否定、又自我坚持的真实而矛盾的过程。从“帝国”到“国家”的转型中,中国与17世纪以后主流的“世界革命”潮流既相容、又相异。对英法“双轮革命”(dual revolution)模式的超越*“双轮革命”是霍布斯鲍姆提出的两种基本的历史运动模式,即以英国工业革命为代表的和平渐进变革和以法国政治革命为代表的激烈颠覆变革。参见E. J. Hobsbawm, The Age of Revolution,1789-1848(New York: A Mentor Book, 1964), p.17。,对独立主权的坚持,对朝向平等的“亚洲的觉醒”(孙中山语)的期待,等等,都是竹内好所谓“拒绝自己成为自己,同时也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的挣扎状态。[12](P.206)这正是竹内好孜孜以求的东方理想,也是沟口雄三坚持以中国为“方法”所要探索的历史对应物。
三 南社的文化政治
在这样的视野中,成立和活跃于清末民初的南社(1909-1923),就显现出其独特的价值,作为一个面对历史窗口的具体个案,它为我们触碰“近代”的难题性提供了很多有意思的资源。
南社在中国近代是一个重要的文化和文学群体,但同时他们也应该被视为一个特殊的政治群体。这样说,首先是因为“南社”成立的初衷就是为反满汇集力量,其社名直接表明了与清廷南北对峙的政治志向。*关于南社命名,宁调元在《南社诗序》中解释说:“钟仪操南音,不忘本也。”首次发表于《民吁日报》,1909年10月29日,收《南社丛刻》第二集第一卷,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6年影印本,第139页。陈去病《南社长沙雅集纪事》说:“南者,对北而言,寓不向满清之意。”见《民吁日报》,1909年11月26日;又见《太平洋报》,1912年10月10日。柳亚子后来追溯时也说:“旧南社成立在中华民国纪元前三年,它底宗旨是反抗满清,它底名字叫南社,就是反对北庭的标帜了。”柳亚子《南社纪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00页。还因为很多南社社员在清末民初的政治、社会和文化变动中,都是显赫一时的人物,参与了辛亥革命、反袁斗争等实际的政治活动。南社的几个中坚人物——陈去病、高旭、柳亚子都是同盟会中坚,而同盟会和后来国民党中的要人黄兴、宋教仁、汪精卫、陈其美、于右任、邵力子、叶楚伧等都加入过南社。同盟会会员(及国民党党员)与南社社员双重身份的重合,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高旭就曾说:“当胡虏猖獗时,不佞与友人柳亚庐、陈去病于同盟会后更倡设南社,固以文字革命为职志,而意实不在文字间也。”[13]当时那么多人聚集到南社大旗下,还是有大体一致的政治追求和期待,即推翻清朝,建立现代共和国家。从1909年建立到1923年旧南社告终、新南社成立,14年间,南社成员发展到1100余人,*南社至1916年已增至800余人,最多时达1178人。南社社员还先后组织了长沙分社、福建分社及淮南社、辽社、粤社、酒社、消夏社、觉民社等分支团体。遍及政治、文化、教育、学术、新闻、出版、军事各个领域。正如Denise Gimpel所说,在1911年革命前后,南社人通过政治和文学发表,建立了极其“广泛的影响”。[14]在多重身份的纠结之中,南社社员作为一支活跃的政治力量参与到民国政治文化的创建之中。1912年宁调元在广州成立南社粤支部,同年8月宋教仁在北京设立南社事务所,这种有总部有分支的组织方式显然带有现代社团的特征。因此,南社不能被简单地视为“民间的文人雅集”[15],而应该被看作一种特殊的政治群体与文化政治形式。
南社的文化政治特征集中体现在通过文化想象和实践来面对整体性的现实忧患的姿态上。一方面,南社群体发扬了江南的地方性知识和历史传统资源,在新的全球格局中将之转化为打造新的民族共同体的行动;另一方面,南社群体发展出多种表征和介入危机的文化实践形式与策略,着力于革命文化的语言、情感、象征和仪式层面的重构。其集会、宴饮、刊刻、办报、诗歌唱和、评论写作,其实都具有某种公共性,对清末民初的舆论转变与民意流动厥功甚伟,尤其是“革命”从舶来理念转变为现实中痛痒相关的认识和情感诉求,南社群体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暴力行动与议会/政党政治之外发生作用的文化与象征实践,挑战并拓展了现代政治的定义与界限,应该在一个新的理论视野中予以重思。
有鉴于此,我认为有必要重新思考如下三组关系,这三组关系对于南社而言至关重要,而以往的南社研究不免有所忽视。
第一,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关系。按照阶级决定论的陈词滥调,南社中大多数人在阶级身份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应该信守资产阶级民主文化;可实际上他们中的很多人始终没有放弃对传统“封建”文化的钟情。于是以往文学史通常就把这种矛盾和错位解释成革命派“颓唐堕落,与遗老们互相唱和”[16]。但事实上在描述南社社员的身份时,一开始就会遇到一个界定的困难,即他们是心忧天下的传统士绅,是诗酒风流的旧式文人,是共和国家的现代公民,是政党或政府中位居高位的技术官僚,是积极参与舆论空间的新型报人,还是打造新的都市文化的“轻性知识分子”*“轻性知识分子”是张爱玲在《诗与胡说》中提出的概念。具体讨论,参见倪文尖《“轻性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的表意实践——以张爱玲为中心的讨论》,收入高瑞泉、山口久和主编《中国的现代性与城市知识分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53-172页。?似乎上述任何一种定位,都无法加诸南社社员。你当然可以说是因为南社极为庞杂,涵盖面广,三教九流皆纳入其中;但是,即使是几个南社核心成员(如陈去病、高旭、柳亚子、苏曼殊、马君武、周实、宁调元),无不都是跨越多重身份,纵横多个领域,置身于新旧之间。那种清楚绝对的分类对他们而言并不适用。更重要的是,他们也都在近代的历史变化中同时进行着自我身份的适应和调整。
南社群体身份混杂的问题在他们的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关系上,表现得最为突出。简单地说,政治认同把民族共同体的基础建立在政治法律制度或者公共的政治文化之上,而文化认同更多地诉诸历史传统遗留的文化、语言、学术、道德或宗教。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这两种认同之间往往存在紧张关系,如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所论:
民族具有两副面孔。由公民组成的民族,是民族国家民主正当化的源泉,而由民众组成的天生的民族,则致力于促使社会一体化。公民靠自己的理论建立自由而平等的政治共同体;而天生同源同宗的人们则置身于由共同的语言和历史而模铸的共同体中。民族国家概念包含着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之间的紧张,即平等主义的法律共同体与历史命运共同体之间的紧张。[17]
这种紧张在现代中国也有表现,比如许纪霖在对张佛泉和张君劢的研究中,就抽象出两种民族主义类型。[18]然而,这种“理想型”的论述在清末民初的语境中,并不完全适用。因为我们从南社群体身上正可以看到一种把共和国家的政治认同与文明价值的文化认同相统一的诉求。南社群体总体上既推动反满革命,建立新的共和国家,并且在恶劣的环境中继续坚持共和与民权;同时又明确坚持主权的连续性,树立文化自觉,强调华夏文明和道德的吸引力,拒绝文化与文明的断裂。南社群体对于文化传统并非没有取舍地一味拥抱,但他们确实始终坚持一种植根于民众生活世界的旧邦新命、内在转化的理想。这里体现出一种对正当性的复杂理解与探索,换言之,在新的历史局势面前,他们致力于把政治的“正当”与文化价值的“好”统一起来,创制一种稳定的、连续的、承继历史的共同体认同。这当然不仅是南社群体,更是晚清文化主义者们的乌托邦理想。他们从诗教、国学等传统资源中找出路,在文学写作和日常生活领域都自觉承继传统的风格,以“五四”以后的全盘西化论来看,似乎是荒谬的。但站在全球化的今日重新反思,或许他们会启发我们进一步思考传统与现代性、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关系、第三世界文化身份等诸多问题,而我们又该如何评价他们的洞见与不见?
第二,政治与“情感结构”的关系。文化认同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情感需要。英国文化研究学者雷蒙德·威廉斯所谓的“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近代”革命的情感面向,应当具有启发性。威廉斯解释道:
我们所讲的是冲动、克制、语气等特征元素;尤其是意识与关系中的感情元素:并非感觉与思想的对立,而是思想作为感受,以及感觉作为思想:是现在处境中、在活生生的相互联系的进程中的实际意识。我们因此而界定那些元素为一种“结构”:一个整体中存在特定的内部关系,彼此立即互相扣连并存在张力。然而我们也是界定一种尚在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经验,它经常未有给人认识其社会的一面,被视为私人的、特殊的、甚至是个别的,可是在分析之后(虽然极少有另一种状况)不难发现它有着逐渐呈现、扣连、支配的特点,而这是它特有的构造。[19]
“情感结构”描述的不是单一僵化的观念或者概念的传播,而是意义体现于感官与感性形式的过程,是一种在活生生的历史进程中普遍的主体性的生成与更新,着眼于观念和感觉、认知和审美、意识和无意识、话语和欲望的交融作用与共振。从而超越了庸俗化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构架和社会-政治的层次隐喻,能够更深入也更全面地揭示意识形态的作用机制。而更有意思的是,在不同的历史时刻,政治与“情感结构”之间会形成利用与反利用、服从与反抗、协商与拒绝的种种复杂关系。
裴宜理在讨论中国革命时,认为激进的理念和形象要转化为有目的的实际行动,“不仅需要有益的外部结构条件,还需要在一部分领导者及其追随者身上实施大量的情感工作。”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唤起普通的中国老百姓的情感”这方面有很大差异,而这是构成他们斗争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20]在具体的政策、党派纷争、正规机构运作之外,我们必须重视“情感”在政治文化中的重要功能。高度情感化的政治,其实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不断上演。时代的“情感结构”的形成,依赖于政治或美学理想,也依赖于日常生活的实践。
影响“情感结构”的因素有很多,但语言文字无疑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换言之,“情感结构”本身是政治与诗学的辩证的体现和结果。而我们很容易发现,以文字召唤、书写和回应革命,“欲凭文字播风雷”(柳亚子语),正是南社社员们的寄托与能事。无论是那些抒发豪情壮志的诗词,还是那些挥如椽之笔、作不平之鸣的报刊文章,或是友朋知己之间互诉衷肠的书信,甚至在访古、追悼仪式上发表的祭文,南社社员面对历史的危机与暴力,言志抒情的冲动都贯注其中。而通过这些书写在同人之间的私下流传与在更广大的公共空间里的传播,更多的阅读大众也被牵涉其间。不管是革命的动员激发献身的冲动,抑或革命的幻灭引起颓唐的感伤,南社社员的作品实在是革命诗学的最佳例证,同时也是我们触碰时代情绪气氛的依凭。
从南社群体切入探察“情感结构”,有两个特别的意义。一是能够在一个中观的层面去观察清末民初的政治文化转型。相对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等人的显赫位置,南社群体在知识和文化资本上都逊色不少,当然他们也不是普通百姓,他们关于“革命”的言说和行动,更能代表主要是江南地区的中层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二是能够和中国传统关于“抒情”的相关论述结合起来。借助“抒情”的视野,我们不仅希望对南社群体交游唱和的交往/创作形式,乃至于他们对传统文类形式(如旧体诗)和艺术媒介(如书画)的坚持,有一些新的理解;而且,从向往“崇高”到沉湎“感伤”,他们在革命前后的情感脉动,正有助于我们探查和反思清末民初政治的感性层面。从“情感结构”的形成与变化中,我们怎样反观和反思政治,解释20世纪的历史变动?又是否能重建一种新的与生活的想象性关系?
第三,南社盛衰与民国共和制度起伏的关系。现有南社研究一般倾向于从个人矛盾或文学趣味之争的角度去解释南社的衰落,但我认为无法忽视背后的中国资产阶级与公共领域的结构性转变。尽管南社社员大多有着各种身份和职业,但他们组织和加入南社这个社团,本身就表述了某种集体意图。南社盛衰与民国共和制度的起伏两者表现出某种同时性,这提示我们注意南社的解体背后,民初的共和危机,尤其是汉娜·阿伦特所谓的“公共性”的危机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阿伦特在当代语境中,试图重振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政治性的论述传统,对代议民主制度提出了严厉的批判,强调“政治行动”和政治参与的重要性。与近代自由主义对公私问题的看法不同,阿伦特把公私领域的区分追溯到古希腊人对“城邦生活”与“家庭生活”的区分。她认为政治行动必须体现在公共领域,私人领域和社会领域的过度扩张,会使得政治被功能化,危害政治行动的落实。*阿伦特说:“社会领域既非私人领域也非公共领域,其出现可以说是相当晚近的现象,它与现代同时萌芽,而其展现的政治形态则是民族国家。”因为社会领域的出现,现代人倾向于将政治变成了“集体的家政学”(collective housekeeping)。参见Hannah Arendt: Human Condi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pp.28-29。所以她特别坚持通过“言谈”与“行动”的重要性,因为沟通论辩是维持公共领域得以不坠的关键。*关于阿伦特的政治哲学,特别是她所提倡的“协议制度”(council system)的讨论,参见江宜桦《自由民主的理路》(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八、第九章,第183-221页。高度的社会参与程度,是保证公共领域的前提。
“参与性”的兴起与退化,在南社的整个过程中确实有很多表现。南社的准备期(大致是1903至1909年),正是社会性的反清活动日渐高涨的阶段。南社的很多社员正是在拒俄运动、国粹运动、安葬秋瑾等活动中集结起来的,他们踊跃并且创造性地进行政治行动。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共和制度的建立,南社达到了它最兴盛的阶段。这并不是就有多少南社社员担任了政府高官而言,而是着眼于南社在促成公意的形成上的关键作用。比如南京临时政府最重要的《临时约法》,主要由景耀月、张一鹏、吕志伊、王有兰、马君武组成的五人起草委员会起草,而参与者多达30余人。起草委员会中,景耀月、吕志伊、马君武都是南社社员。又如柳亚子在1911年曾到临时总统府任秘书,但他三日即辞职,到上海办报。这是很有象征意义的行为。20世纪初年,南社成员创办或参与了大量报纸和杂志,进行文化生产与知识生产,在报刊上交换个人理念,与大众对话,影响不知名的读者。比如陈去病,1903年协助章士钊办《国民日报》,1904年开始任《警钟日报》编辑,1907年南下汕头编《中华新报》。1910年同盟会在上海创办《中国公报》,陈为主要撰稿人。1911年6月,在苏州创办《苏报》。武昌起义后,应江苏都督程德全之邀,办《大汉报》。1912年1月,在上海发起创办《黄报》。同月,赴绍兴任《越铎日报》总编辑。6月改任杭州《平民日报》总编辑。此外在《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天铎报》《大风日报》《民国日报》等发表大量文章。还创办或编辑《二十世纪大舞台》《江苏》《复报》《国粹学报》《江苏革命博物馆馆刊》等。柳亚子在大众媒体的活跃程度不亚于陈去病,一心打造公共论域,与大众对话。
开拓言论事业是南社群体的一致追求。清末开始,南社社员掌握了不少大报,如《民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天铎报》《民声日报》《太平洋报》《民权报》《民国新闻》《民主报》《中华民报》《生活日报》《民权画报》的编辑权。凭借这样庞大的媒体网络,南社社员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民国初年的社会舆论。不少报纸鲜明地以“民权”相标榜,捍卫共和制度。虽然1913年前后,一些报纸被袁世凯政府查禁停刊,但南社成员又办起大量杂志(如《民声丛报》《春声》《七襄》《民权素》等),继续以“民声”、“民权”相标榜。1916年,叶楚伧、邵力子又创办了重要的《民国日报》。
凭借大众传媒,南社社员在公共领域自主地表达意见。比如在民国建立之初,柳亚子等力主北伐,反对与北方袁世凯妥协;虽与当时临时政府的主流观点相悖,但柳亚子等依然直率地发出自己的批评。但也要看到,一旦南社中人更多地进入议会/政党政治和官僚制度中,其中很多人也迅速地与独立的“公共性”相脱离,作为导致南社解体重要原因的贿选事件,实际上就表明了官僚政治的腐化力量。而同时,伴随着袁世凯的压制和各种各样的共和危机的到来,一些南社社员(如湖南、广东等地部分社员)深感颓唐,自觉或者不自觉地退缩回私人世界。南社群体很快分化与沉寂,渐渐丧失了文化场域的领导权。另一些人虽然依然努力经营媒体与文字事业,也逐渐淡出原来的圈子,形成新的同人团体,更多依托印刷资本主义和面向都市文化(如包天笑、周瘦鹃等)。那么,值得追问的是,南社在公共领域的“领导权”的挫折意味着什么?如果再联系到哈贝马斯所描述的,因为资本和国家权力的渗透和干涉所导致的“公共领域的重新封建化”[21],更可以追问,在民初南社成员所掌握的媒体中,是不是也有这样的现象凸现?看似繁荣的媒体事业,究竟是公共领域的建制化,还是本来就缺乏根基的“景观社会”?从袁世凯帝制阴云到党治时代即将来临的十来年间,舆论界逐渐形成把激活政治的希望放在文学的“革命”/革新之上的意识。从《甲寅》到《新青年》,从章士钊到陈独秀、胡适,新一批报刊媒体和文化人出现,讨论“国本”问题,打造新的文学文化,这意味着什么呢?南社此间的衰落,与他们面对这种文学位置/功能的调整的反应,有没有联系?这种转变,不仅促生了“现代文学”之诞生,也是“新文学”典律及其排斥机制的自我生成。
总结以上三组关系:面对“被译介的现代性”(translated modernity)[22],如何探索建诸文化差异性的“活在现代的传统”;巨大的时代变动特别是革命,激发起怎样用以呼应的“情感结构”;以及在共和危机到来时,如何选择立身姿态,又怎样遭遇了有关“介入”的可能与不可能。一旦我们改变视野,南社与“近代性”仍有很多值得探索的空间。
[1]阿兰·巴迪欧.世纪[M].蓝江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1-4.
[2]Benjamin I. Schwartz.ReflectionsontheMayFourthMovement:ASymposium[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3.
[3]罗岗.“现代化”的期待,还是“现代性”的忧思——从“韦伯翻译”看90年代以来的“西学想象”[M]//许纪霖,罗岗,等.启蒙的自我瓦解:199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界重大论争研究.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07.325-361.
[4]阿里夫·德里克.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5,(春季卷):135-141.
[5]Dipesh Chakrabarty.ProvincializingEurope:PostcolonialThoughtandHistoricalDifference[M].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7.
[6]章永乐.旧邦新造:1911-1917[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2-13.
[7]Elizabeth J. Perry. Studying Chinese Politics: Farewell to Revolution[J].TheChinaJournal,2007,(57).
[8]酒井直树.现代性与其批判: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问题[M]//张京媛.后殖民主义与文化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396.
[9]张灏.转型时代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与文化史上的重要性[M]//张灏自选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109.
[10]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M].索介然,等译.北京:中华书局,1997.7.
[11]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M].孙军悦译.北京:三联书店,2011.
[12]竹内好.何谓近代——以日本和中国为例[M]//赵京华译.孙歌.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
[13]高旭.无尽庵遗集序[M]//郭长海,金菊贞.高旭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512.
[14]Denise Gimpel.LostVoiceofModernity:AChinesePopularFictionMagazineinContext[M].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1.21.
[15]栾梅健.民间的文人雅集——南社研究[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
[16]游国恩,王起,等.中国文学史:第四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423.
[17]哈贝马斯.包容他者[M].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35.
[18]许纪霖.共和爱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现代中国两种民族国家认同观[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4):1-13.
[19]Raymond Williams.MarxismandLiterature[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132.
[20]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J].中国学术,2001,(第8辑).97-121.
[21]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曹卫东译.北京:学林出版社,1999.170-171.
[22]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M].宋伟杰,等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7.
RethinkingCulturalPoliticsofSouthSocietyand“ChineseModernity”
ZHANG Chun-tian
(Division of Humanities,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ng Kong 999077)
Two mainstream paradigms of historiography, revolution and modernization, failed to effectively interpret “Chinese modernity.” South Society community developed their structure of feeling and cultural politics to face with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the late Qing. And they experienced and tried to respond to crisis of republicanism in the early Republic. It is possible to enrich our understanding of South Society and Chinese modernity, once we change our theoretic perspective.
South Society; historiography; cultural politics; “Chinese modernity”
2012-02-24
张春田(1981-),男,安徽芜湖人,香港科技大学人文学部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思想与学术研究。
I206.5
A
1674-2338(2012)05-0075-10
(责任编辑:沈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