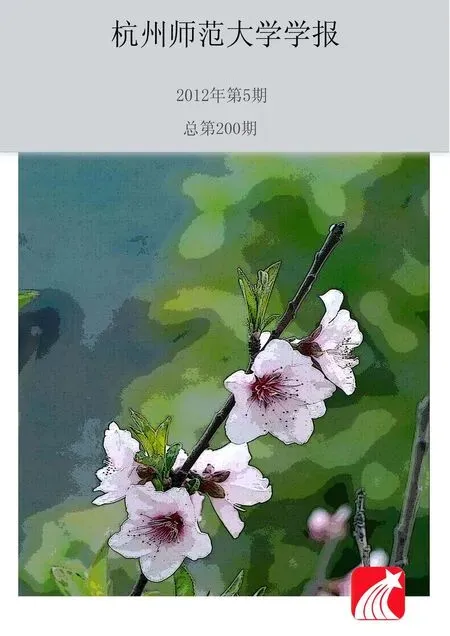诗性时历
——《月令》与汉代祭事诗关系探析
张树国
(杭州师范大学 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36)
文学研究
诗性时历
——《月令》与汉代祭事诗关系探析
张树国
(杭州师范大学 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36)
《礼记·月令》是上古时代具有经典地位的时历书,同时也是政书,对天子岁时祭祀的种类和举行仪式的季节及功能具有规定性,为汉以后帝王们所恪守。岁时祭包括五郊迎气、社稷、山川、宗庙等“大祀”,同时也包括诸如高禖、大雩、驱傩、八蜡等祭仪。五郊迎气以五神帝为诉求对象,祈祷四季平安;社稷之祀为祭祀土谷之神后土、后稷,祈年报功;山川之祀在上古时代具有疆界、川源、财用等多重信仰,在秦汉时代发展为封禅告天这一国家祭典;宗庙祭祀列祖列宗。《乐府诗集·郊庙歌辞》及历代礼乐志中记载的汉代祭事诗是汉代帝王们岁时祭祀中的仪式用歌。汉代祭事诗在祭祀对象、用牲、日期及仪式过程等方面体现了《月令》的影响,具有周期性、表演性和象征性的特点。
时历;月令;祭事诗;汉代;文学史
一
上古时代的时令书如《尚书·尧典》《夏小正》,《逸周书》中的《周月解》《时训解》,以及《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等,基本上“是以农事为主之行政月历”。[1](P.503)汉代月令分为三种,一是来自秦相吕不韦及其门客编纂的《吕览》“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系统,刘向《别录》归属于“明堂阴阳”。二是汉宣帝时魏相所上《明堂月令》系统,《汉书》卷74《魏相丙吉传》记载:
(魏相)又数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曰:东方之神太昊,乘震执规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离执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兑执矩司秋;北方之神颛顼,乘坎执权司冬;中央之神黄帝,乘坤艮执绳司下土。兹五帝所司,各有时也。
魏相为西汉宣帝时丞相,这是《明堂月令》较早见诸西汉史籍,常为祭祀歌辞所征引。三是诸如《大戴礼记·夏小正》《逸周书·周月解》等虽未有月令之名而有其功能的作品,为先王“敬授人时”之作。另外,出土文献敦煌悬泉驿汉代《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为西汉平帝年间王莽执政时的文字,其中《孟春月令十一条》中有“敬授民时,曰扬谷,咸趋南亩,禁止伐木,毋杀幼虫”等记载。东汉崔寔著有《四民月令》,是了解汉代风俗的重要资料,里面的祭祀内容基本上属于“民间祭祀”,不属于本文研究的范围。本文根据礼典中的《月令》研究天子岁时祭仪的种类及其功能,探讨汉代国家祭祀与仪式歌辞之关系,这些岁时祭歌保存在《礼乐志》《祭祀志》《音乐志》之类的志书中。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中的《郊庙歌辞》共12卷,收录比较全面。因为涉及早期诗歌艺术与历法、祭祀仪式之间的关系,后两者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汉代祭事诗的基本内容及艺术功能。
二
《礼记·月令》的天象纪事,除极少数外,可以说与《吕氏春秋·十二纪》《明堂月令》完全一致。其星象的观测年代,据陈遵妫先生研究,当在鲁文公七年(前620)前后,即以此为中心的前后一百年间。[2]《月令》物候为90种,杨宽先生认为“《月令》出于占候卜筮之学”,出自《明堂阴阳》。[1](P.487)值得重视的是,《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在记载星象、物候的同时,记叙了一年内天子在明堂的活动和岁时祭祀的内容。《吕氏春秋·十二纪》为秦相吕不韦纠集门客所纂辑,故“多杂秦制,又博采战国杂家之说”[3],对《逸周书·时训解》《周月解》及《管子·四时》多有借鉴,后来为《礼记》所收录,称为《月令》。郑玄曰:“名曰《月令》者,以其记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吕氏春秋·十二纪》之首章也,以礼家好事者抄合之。”《隋书·音乐志一》载梁天监(502-519)中沈约奏答,言汉初典章灭绝,诸儒得到片简遗文,“与礼事相关者,即编次以为礼,皆非圣人之言”。其中,“《月令》取《吕氏春秋》,《乐记》取《公孙尼子》”。《隋书·牛弘传》记刘谳云:“今《明堂月令》者……不韦鸠集儒者,寻于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不韦安能独为此记?”文中“物勒工名,以考其成”、“命之为畅月”等皆为秦制。
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帝国的隐喻》一书中提到了《月令》的三个权威版本:一是在公元前3世纪编纂的《吕氏春秋》中(即“十二纪”);二是在公元前2世纪编纂的《淮南子》中(即《时则训》);三是在公元前1世纪编纂的《礼记》中。这三种典籍经过无数的注释、复制、研究和编纂,成为儒家和道家的共同经典。这一历法及其宇宙观从公元前3世纪到1910年这段时间内一直都未曾改变。[4]实际上这三部经典文字大体相同,只是稍有出入而已。其思想源于齐学的阴阳五行学说,《管子》中的《幼官》《四时》可以说是“月令”政治的早期文献。西汉成帝时刘向在《别录》中将《吕览》“十二纪”归入《明堂阴阳》,后为戴圣收入《小戴礼记》,逐渐为学者所注意。《汉书·成帝纪》记阳朔二年(前23)诏书云公卿大夫“所奏请多违时政”,要求其“务顺四时月令”。汉末王莽奏起明堂、辟雍、灵台等礼仪性建筑,征通晓《书》《诗》《周官》《月令》等人才,“皆诣公车”(《汉书·王莽传》)。东汉时代的社会风俗深受《月令》影响,汉章帝于建初五年(80年)冬,采纳马防上书,“始行《月令》迎气乐”(《后汉书·肃宗孝章帝本纪》)。《后汉书·律历志下》云:“若夫用天因地,揆时施教,颁诸明堂,以为民极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大司备矣,天下之能事毕矣。”值得注意的是,汉代专设《月令》师主持“时节祭祀”(《后汉书·百官志四》)。《隋书·天文志上》提到汉蔡邕《月令章句》12卷,《隋书·杜台卿传》记杜台卿采《月令》,触类而广之,成《玉烛宝典》12卷,成为《月令》研究的重要文献。
值得注意的是,在《夏小正》及《逸周书》中的《时训解》《周月解》等文章中,帝王活动以及岁时祭祀的内容很少。而在《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中都被合理地编织进了以阴阳五行学说为核心的大体系。其叙述时历、物候、音律、祭祀的次第,据蔡邕《月令章句》云:
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故先建春以奉天,奉天然后立帝,立帝然后言佐,言佐然后列昆虫之别。物有形可见然后声音可闻,故陈音。有音然后清浊可听,故言钟律。音声可以章,故陈酸羶之属。群品以著五行,为用于人,然后宗而祀之,故陈五祀,此以上皆圣人记事之次也。[5](P.977)
本文主要研究天子岁时祭与古代郊庙歌辞创作源流之间的关系,对星象、昆虫、音律、气味等“群品”不作研究。根据《吕氏春秋·十二纪》《月令》制作下表:

夏历祭日方帝神祇分季王居明堂礼祭祀活动春甲乙太昊句芒孟春天子居青阳左个天子迎春东郊,以元日祈谷于上帝;祀山林川泽。仲春天子居青阳大庙择元日,命民社;祀高禖;荐寝庙。季春天子居青阳右个荐鲔于寝庙;命国难(通“傩”),以毕春气。夏丙丁炎帝祝融孟夏天子居明堂左个天子迎夏南郊,用礼乐。仲夏天子居明堂太庙祈祀山川百源,大雩帝,用盛乐。季夏天子居明堂右个养牺牲,以共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祠宗庙、社稷之灵。中央土戊己黄帝后土天子居大庙大室秋庚辛少昊蓐收孟秋天子居总章左个天子迎秋西郊;荐寝庙。仲秋天子居总章大庙天子乃难(傩),以达秋气;荐寝庙。季秋天子居总章右个大飨帝。冬壬癸颛顼玄冥孟冬天子居玄堂左个立冬之日,天子迎冬于北郊;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腊先祖五祀。仲冬天子居玄堂太庙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渊泽、井泉。季冬天子居玄堂右个大难(傩),旁磔,共郊庙及百祀之薪燎;赋牺牲,以共皇天上帝、社稷之飨;乃命同姓之邦共寝庙之刍豢。
上表体现了古代帝王一年内的“明堂”生活和主要祭祀活动。明堂祭祀属于国家祭祀礼仪中的“天子祭祀”,即天子在一年中的宗教祭祀活动,体现了“自然法”对天子宗教义务的规定,强调天子的行动影响自然宇宙的运转。明堂传说很古老,黄帝时称“合宫”,帝尧时称“五府”,夏代称“世室”,殷代称“重屋”,周代始称明堂,是古代最为重要的礼仪性建筑,清代阮元《明堂图说》、王国维《明堂寝庙图考》等都有精到的分析。金文中著录许多“亞”形族徽,实际上是明堂的象形。艾兰(Sarah Allan)认为“亞”形体现了古代庙宇的布局,一个太室或是一个中庭连着四厢,体现了古代宗教仪式里的“中心象征”。[6]明堂又称为“天道之堂”(《大戴礼记·盛德》),后魏李谧《明堂制度论》云:“夫明堂者,盖所以告月朔,布时令,宗先王,祀五帝者也。”[5](P.2931)体现了上古人君同时也是“祭司王”的理念,天子在其中燮理阴阳,宗祀其祖,颁朔布政,同时也是祭祀乐舞演出场所。《吕览》“十二纪”记载的明堂为五室,分为青阳、明堂、太庙、总章和玄堂,代表着春夏秋冬和东南西北中不同方位,对汉代以后的明堂建筑有深刻影响。据宋代徐天麟《两汉会要》统计,自武帝元封二年(前109年)作明堂于泰山下始,前后五次于泰山明堂祠五帝。平帝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奏请于长安设立明堂。光武刘秀于中元元年(56年)初营明堂、辟雍及灵台,明帝永平二年(59年)祀五帝于明堂,光武帝配。由汉章帝直至灵帝皆有明堂之祀。《后汉书·百官志》:“明堂及灵台令各一人,掌守明堂灵台,掌候日月星气,皆属太史。”郊祭、社稷五祀、山川、祖庙与明堂祭祀关系密切,《月令》等书既保存了古代的礼仪习俗,同时又形成了传统的约束力,对汉代以后以帝王为中心的国家祭祀礼仪产生了规定性,使其成为能够证明其统治合法性、王权神圣性的最有效的手段,保存在《乐府诗集》中《郊庙歌辞》中的大量颂神歌曲以及郊庙乐舞就是献祭圣坛上的作品。
(一)五郊迎气诗 《月令》中,规定了天子“五郊迎气”的制度。即:孟春之月,天子迎春于东郊;孟夏之月,天子迎夏于南郊;孟秋之月,天子迎秋于西郊;孟冬之月,天子迎冬于北郊。同时“先立秋十八日,天子居大庙大室”。据古人看来,春夏秋冬四时更替,以及12个月的产生,是由于“五行”之气的迭相作用。迎气仪式早在西周时代已有记载,《周礼·春官·籥章》云:“中春,昼击土鼓,龡豳诗,以逆暑。”《国语·周语》记载了“瞽告有协风至”,王斋戒迎气的习俗。《月令》:“是月也(指孟春之月)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斋。立春之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斋戒”是天子五郊迎气以及大祭开始前必备的礼仪行为。“凡斋,天地七日,宗庙山川五日。”(《西汉会要》卷五)蔡邕《孟春章句》云:“斋者,所以专一其精不敢散其志,然后可以交于神明者也。”[7]古人在进行祭祀典礼前要清心寡欲、净身洁食,然后才可以与神明交通,实际是进入仪式过程的必经阶段,西方学者称其为“门槛(limen)”阶段,通过斋戒使自己与日常生活中的各种事物分离,从而跨过人神之间的这道“门槛”,而进入到仪式的世界里。[8]
《月令》中,“五帝”及“五神”是天子迎气仪式诉求的对象。黄帝与后土位居中央,土德;太昊、句芒居东方,木德;炎帝、祝融居于南方,火德;少昊、蓐收居于西方,金德;颛顼、玄冥居北,水德。除“五帝”外,“五神”当源于上古时代专门管理“五行”的官职,《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史官蔡墨之语:“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这“五神”在《月令》中是作为“五帝”的“配神”被祀奉的。《汉郊祀歌十九章》中有《五神》一诗,“五神相,包四邻”,指“五神”辅佐“五帝”保佑下土。
自汉高祖之后,先秦时代的“五帝”、“五神”就被青帝、赤帝、黄帝、白帝、黑帝所取代了(《史记·封禅书》)。泰山明堂建于武帝元封二年(前110),《汉书·武帝本纪》云:“元封二年,作明堂于泰山下。”太初元年(前104)行幸泰山,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祀上帝于明堂,武帝前后五次幸泰山明堂。《汉郊祀歌十九章》中的四言诗如《帝临》及四首“邹子乐”(《青阳》《朱明》《西颢》《玄冥》)为泰山明堂祀歌。[9]《南齐书·乐志》:“明堂祀五帝,汉《郊祀歌》皆四言。”《帝临》一诗记载了太初元年改历(即太初历)事,汉武帝时明土德之运,“帝临中坛”之“中坛”指土位为中;“制数以五”,土数为五。《西颢》诗“隅辟越远,四貉咸服”,记载武帝灭南越(事在元鼎五年,前112)、迁东越(元鼎六年,前111)、平朝鲜(元封二、三年,前109-108)的武功。“隅”音假为“宇”、“寓”,“辟”通“僻”,意思是说将僻远的南越、东越之民安置下来。“貉”指古代朝鲜,《汉书·高帝纪》:“北貉、燕人来致枭骑助汉。”师古曰:“在东北方,三韩之属皆貉类也。”“四貉咸服”指武帝平朝鲜后,将其地分为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所谓“四貉”也。这五首作品应作于太初元年(前104),后用来五郊迎气,“五郊互奏之”(《史记·乐书》),为后汉所遵循。
(二)社稷祀歌 上古时代社稷神为邦国守护神,建国要设其社稷之壝,征伐要行宜社之礼,祭祀至为隆重。在《月令》中,社祀具有全民性,体现了“国家祭祀”与“民间祭祀”两种形态。东汉马融注释《郊特牲》“社所以神地之道也”云:“社祭后土,稷祭后稷。”相传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之官,“后土”即社神。“稷”为“田正”,相传神农氏时代有“烈山氏”之子名叫“柱”的为稷官,“自夏以上祀之”。后来周人始祖弃善于稼穑,称为稷神,“自商以来祀之”。《月令》将“社稷五祀”与方位、季节、颜色明确对应起来。汉代社稷祭祀多与北郊祭地及后土祀典重合,如汉武帝元鼎四年(前113)立后土祠于汾阴睢上,以后多次幸河东祠后土。宣帝世依然。汉成帝建始二年(前31)听从丞相匡衡的建议,将郊天祀地的场所从雍郊五畤、河东汾阴移至长安南北郊,以后虽有反复,但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大司马王莽将这一制度最终确定下来,从此都城南郊祭天、北郊祭地的基本格局得到确立。社稷之祀与原始农业祭关系密切,《汉书·郊祀志》记载,西汉初年汉高祖令天下立灵星祠,并创作灵星舞。“灵星”指东方苍龙七宿左角之天田星,为后稷所配食,主谷物丰收。《后汉书·祭祀志》记载其舞容:“舞者用童男十六人。舞者象教田,初为芟除,次耕种、芸耨、驱爵(通‘雀’)及获刈、舂簸之形,象其功也。”主要模仿春耕、夏锄、秋收这一劳动过程。《汉郊祀歌十九章》中有《后皇》为祭祀汾阴后土之诗,作于武帝元鼎四年(前113)。
(三)山川祀歌 山川祀是古代岁时祭典中的重要内容。《月令》中,孟春、仲夏、季冬都有山川之祀的内容,如“孟春之月……乃修祭典,祀山林川泽”、“仲夏之月,命有司祈祀山川百源,用盛乐”、“仲冬之月,天子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源、渊泽、井泉”等。上古先民本来居于山川之中,章太炎《神权时代天子居山说》认为:“古之王者,以神道设教,天子为代天之官,因高就丘,为其近于苍穹,是故封太山、禅梁父,后世以为旷典。”古代天子、诸侯主持山川之祀,有望祭、禜祭及临时性的散祭。秦汉以后,山川之祀主要集中在封泰山、禅梁父,告成功于天。《史记·封禅书》记载,秦始皇统一全国后,曾“令祠官定天下名山大川之祀”。汉武帝于元封元年(前110)到征和四年(前89)前后八次登临泰山,并于山上立明堂之祠。《郊祀歌十九章》中《帝临》及四首“邹子乐”、《天门》等诗作于泰山明堂。古人相信泰山之巅为“天门”,《天门》诗中言“大朱涂广,夷石为堂”,指泰山明堂前用朱丹涂饰道路,垒石建成明堂。武帝于泰山封禅寓求仙之意,《天门》可称为游仙诗。东汉光武帝中元元年(56年)、章帝元和二年(85年)、安帝延光三年(124年)都有幸泰山、柴告岱宗之举(见《后汉书·祭祀志》),而流行东汉的谶纬之书如《河图括地象》等都有许多泰山祭祀的内容。
(四)宗庙祭歌 天子岁时祭中,宗庙祭祀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诗经·小雅·天保》:“禴祠烝尝,于公先王。”禴、祠、烝、尝是对先王之庙的四种岁时祭祀。《礼记·月令》有明确的记载:仲春“天子献羔,先荐寝庙”,季春“天子乃荐鞠衣于先帝,荐鲔于寝庙”,季夏要“养牺牲”“以祠宗庙”,孟秋“天子尝新,先荐寝庙”,仲秋“以犬尝麻,先荐寝庙”,孟冬“腊先祖五祀”。古人“不死其亲”,先王崩陟之后,立庙以象之。《后汉书·祭祀志下》云:“说者以为古宗庙前制庙、后制寝以象人之居前有朝、后有寝也。《月令》有‘先荐寝庙’,《诗》称‘寝庙奕奕’,言相通也。庙以藏主,以四时祭。寝有衣冠几杖象生之具,以荐新物。”此说又见蔡邕《独断》、应劭《汉官仪》,“庙”中安放祖先神主,“寝”中陈列祖先的衣冠和生活用具,随时供奉新鲜食品,如同活着一样。[10]《礼记·王制》云:“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祖有功而宗有德”是宗庙制度的价值标准。清代赵翼论证“西汉诸帝多生前自立庙”[11],庙有“庙主”,即祖宗牌位。《乐府诗集·郊庙歌辞》卷8-12保存了由《汉安世房中歌》到五代时期的宗庙乐歌。《汉安世房中歌》作者存在争议,《汉书·礼乐志》:“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魏明帝时缪袭奏《安世歌》“无有《二南》风化天下之言”,而改为《享神歌》。《安世》组诗为叔孙通于高祖驾崩后所制宗庙祭乐,时间为惠帝初年,组诗采纳了唐山夫人所作四首楚声杂言作品,清代朱乾《乐府正义》有论述。诗中四次提到“帝”,如“承帝之明”、“受帝之光”等,《礼记·曲礼》:“措之庙,立之主,曰帝。”皆指“先帝”刘邦而非上帝。
东汉比较重要的国家祭祀,据《续汉书·礼仪志中》记载:“正月上丁,祠南郊。礼毕,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五供毕,以次上陵。”“世祖庙”即武帝庙。“上陵”之礼起于西都,据《后汉书·祭祀志下》云:“秦始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弗改,故陵上称寝殿,起居衣服象生人之具,古寝之意也……自雒阳诸陵至灵帝,皆以晦望二十四气伏腊及四时祠。庙日上饭,太官送用物,园令、食监典省,其亲陵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具。”《宋书·乐志》中保存的《汉铙歌十八曲》中有《上陵》一首,作于西汉宣帝时,与陵寝祭祀制度有关。
另据《宋书·乐志》记载,东汉章帝于元和三年(86年)自作诗四篇:“一曰《思齐皇姚》,二曰《六骐驎》,三曰《竭肃雍》,四曰《陟叱根》。”为宗庙食举乐作品,旧典无说。据笔者考证,“思齐皇姚”出自纬书,《宋书·符瑞志》记载尧将禅位,五老相谓曰:“河图将来,告帝以期,知我者重瞳黄姚。”同书记载大舜母握登感虹而生舜于姚墟,目重瞳。“黄”、“皇”同音假借,“思齐皇姚”即“思齐大舜”之意。“六骐驎”亦取材于纬书,《春秋命历序》记载“辰放氏”“驾六飞麟,从日月飞”[12],宋罗泌《路史》卷四《前记四·因提纪》云:“辰放氏是为皇次屈,渠头四乳,驾六蜚麐,出地郣而从日月,上下天地,与神合谋。”据此可知,《六骐驎》盖取义纬书中的祥瑞而为诗。章帝时祥瑞屡臻,《东观汉记》卷3记载:“元和二年,凤凰三十九,麒麟五十一,白虎二十九,黄龙四……载于史官,不可胜记。”“竭肃雍”之“肃雍”出自《周颂·清庙》:“於穆清庙,肃雍显相”,《毛传》:“肃,敬。雍,和。”言诸侯于宗庙中祭祀先王保持恭敬和美之仪容。“陟叱根”唯见《宋书·乐志》,王应麟《玉海》卷106引蔡邕《礼乐志》作“涉叶相”,不知出自何典。这四首诗加上旧有食举乐曲《鹿鸣》《承元气》二曲,共六曲为“宗庙食举”。同时《宋书·乐志》保存有“汉太乐食举十三曲”:
一曰《鹿鸣》,二曰《重来》,三曰《初造》,四曰《侠安》,五曰《归来》,六曰《远期》,七曰《有所思》,八曰《明星》,九曰《清凉》,十曰《涉大海》,十一曰《大置酒》,十二曰《承元气》,十三曰《海淡淡》。
《鹿鸣》为先秦《诗经》古曲,《远期》即《远如期》为汉宣帝时作,与《有所思》并载于《鼓吹曲辞·汉铙歌十八曲》中,其他诗篇则不为人知了。
《礼记·礼运》云:“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于国,所以列地利也;祖庙,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傧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除五郊迎气、社稷、山川、宗庙外,前表中所列“高禖”(郊禖)、蜡(腊)祭及驱傩等,也构成了天子“岁时祭”的主要内容。其中,高禖来自上古时代的求子巫术,蜡祭源于原始农业祭时代的“丰收祭”或称“感谢祭”,与求生殖、求丰收的产食文化密切相关;驱傩为古代年终驱除厉疫之风俗。这些祭祀的功用正如郑玄《诗谱序》所云:“法象天地群神之为而为之政,政成而神得其所,则事顺人和而德洽于神”[13],指出上古时代神道设教之旨。
三
《月令》与古代国家政治生活、宗教礼仪密切相关,部落时代的神祇被合理地编织在四时祭典中。《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淮南子·时则训》这三部时历书内容变化不大,彼此之间应有承袭关系。除了众多的物候、星历、音律等方面的记载之外,这一“诗性时历”详细记载了天子明堂活动及岁时祭祀的内容,通过这些礼仪行为来调整自然节奏与社会秩序,与后起的《明堂月令》一类作品属于国家祭祀领域的经典,类似米尔恰·伊利亚德所说的“宗教历法”[14]。本文所谓“天子岁时祭”属于“国家祭祀”,由“天子”主持,包括郊祀、宗庙、社稷、山川、雩祭求雨、高禖、蜡祭、驱傩逐疫等节庆内容,宗教诉求的对象是上帝(包括五方上帝)和祖先以及一些来自图腾时代的神灵。先秦时代的“五方帝”(太昊、炎帝、黄帝、少昊、颛顼)及“五神”(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与图腾渊源很深。但秦汉以后,这五方帝神逐渐被新的五方帝即青、赤、黄、白、黑所代替,具有时空混一的特点。《乐府诗集》中的《郊庙歌辞》卷1-8记载汉至唐的《明堂乐歌》及《五郊迎气乐歌》,基本上都是歌颂这一五方帝的。汉宣帝时丞相魏相所上《明堂月令》中的一段话几乎成了郊祀歌辞创作的套语。
《月令》与汉代祭事诗之间存在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方面《月令》规定了天子岁时祭的仪式,“天子”这一宗教性的称呼通过周期性的祭典而不断强化;它具有一种自然律令的性质,规定了祭祀对象、物品和日期;另一方面郊庙歌辞是岁时祭仪上的歌唱,而呈现为一种独特的“诗歌范型”——《月令》规定了祭歌的时间和祭祀对象,祭仪提供了过程、用牲和祈愿,祭事诗必须符合仪式的需要,其内容及功能是仪式化的,具有周期性、表演性和象征性的特点。
所谓“周期性”,是由于这些祭仪是在每年固定的时序和日期必须举行的。从人类学的角度来说,“举凡献祭、图腾崇拜以及节期祭仪,弗雷泽几乎都归源于法术。”[15]这些“法术”即所谓“公共巫术”。哈里森(Jane Ellen Harrison)在《岁时仪式:春天的庆典》中说:“所有的原始历法都是仪式历法,构成这种历法的无非是一连串举行庆典的日期、一系列不断再现的具有特殊属性和意义的日期,周而复始的周期性形成其基本模式。”[16]“月令”的“令”类似于“自然法”,这些仪典成了天子在一年“十二纪”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正如涂尔干所说:“社会集团借助于这一方式(指仪式)周而复始地自我确立”,而祭事诗则是在周期性的祭典中频繁演唱的,从这一角度来看,这些诗篇又是“颂神诗”。
所谓“表演性”,指仪式本身实际上就是在表演。郑振铎的《汤祷篇》将《吕氏春秋》《墨子》中记载的商汤求雨的仪式搬演成一出活剧,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17]而周宣王雩祭求雨的场面在《大雅·云汉》一诗中有生动的再现。马伯乐(Henri Maspero)认为蜡祭仪式“广泛地表现出一种扮模的特性,在节庆中,青年们和孩子们带着假面具扮作猫神和虎神”。[18]社稷祭仪上表演的“灵星舞”再现了一年四季的劳动场面,是一个模仿型的仪式。宗庙祭仪中采用“尸祭”召唤祖先神灵加以祭祀的方法很像是原始戏剧的搬演。相比较来说,《郊庙歌辞》中用于赞礼的歌唱比较呆板,歌辞难免千篇一律,而仪典的过分重复和周期性也消磨了人们的热情。
所谓象征性,“天子”通过仪式连接了神圣与世俗两个领域,这一仪式是以天地人相参的信仰体系作为基础的,对神灵来说,这种仪式只能是象征性的。比如“王”字在甲金文中为象形字,“象刃部向下之斧形,以主刑杀之斧钺象征王者之权威”[19],但在儒教定于一尊的情况下,却获得了新解释,《白虎通》:“王也者,天下之往也。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类似解释见于《韩诗外传》《风俗通·皇霸》《大戴礼记·盛德》及《春秋繁露》之《深察名号》《王道通》等篇。古代一些大有为的帝王如秦始皇、汉武帝、光武帝、梁武帝、唐太宗、武则天及唐玄宗等往往热衷于郊天祀地、封禅、明堂及宗庙之类的祭典,将祭祀权与王权紧密结合,是因为这些仪式象征了世俗王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同时也在证明其来源的神圣性,而郊庙歌辞则成了帝王们“动天地”、“感鬼神”的媒介。
就文学表现来说,古代的“月令”书可以说都是优美的散文诗,是“诗性时历”。除《吕氏春秋·十二纪》《礼记·月令》及《淮南子·时则训》外,其他如《夏小正》和《逸周书》中的《周月解》《时训解》,以及汉代崔寔的《四民月令》、隋杜台卿的《玉烛宝典》等书,都具有田园诗的风味。如《礼记·月令》对“孟春之月”物候的描述:“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天气下降,地气上腾,草木萌动。”这种诗化语言贯穿了《月令》全篇,而各种祭礼被合理编织进了这种诗意表述之中。葛兰言(Marcel Granet)曾说:“中国古代的祭礼是季节性和田园性质的。”[20]这些祭祀来源于原始村社时代的农业祭,部落时代的神祇被编织在五方上帝的序列之中,部落时代的祭祀与祈祷也被编织进祀典之中,而上古时代的祭歌无疑是这些仪式上的歌唱。这些仪式一方面发展为后来被称为“天子祭祀”和“皇帝祭祀”的国家祭典,另一方面发展为民俗性的节日庆典,生动地体现了文学艺术发生期的原始状态。
[1]杨宽.月令考[C]//杨宽古史论文选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中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494.
[3]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299.
[4]王斯福.帝国的隐喻——中国民间宗教[M].赵旭东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36.
[5]马国翰.王函山房辑佚书[G].扬州:广陵书社,2007.
[6]艾兰.亞形与殷人的宇宙观[J].中国文化,1991,(1):31-47.
[7]杜台卿.玉烛宝典(影旧钞卷子本)[G]//黎庶昌.古逸丛书.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4.406.
[8]维克多·特纳.仪式过程——结构与反结构[M].黄剑波,柳博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6.
[9]张树国.汉武帝时代国家祭祀的逐步确定及《郊祀歌十九章》创制时地考论[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10]杨宽.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16.
[11]赵翼.廿二史札记[M].北京:中国书店,1987.21.
[12]安居香山,中村璋八. 纬书集成[G].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878.
[13]冯浩菲. 郑氏诗谱订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97.
[14]米尔恰·伊利亚德.神圣的存在:比较宗教的范型[M].晏可佳,姚蓓琴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56.
[15]叶·莫·梅列金斯基.神话的诗学[M].魏庆征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29.
[16]简·艾伦·哈里森.古代艺术与仪式[M].刘宗迪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29.
[17]郑振铎.汤祷篇[C]//郑振铎古典文学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100.
[18]管东贵.中国古代的丰收祭及其与“历年”的关系[J].“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0,(31):191-262.
[19]方述鑫.甲骨金文字典[K].成都:巴蜀书社,1993.21.
[20]葛兰言.中国古代的祭礼与歌谣[M].张铭远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9.170.
ThePoeticCalendar——OntheRelationshipbetweenYuelingandtheSacringPoemsoftheHanDynasy
ZHANG Shu-guo
(Research Center for Ancient Literature and Documents,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36, China)
Book ofRites-Yuelingis a classical calendar as well as a political book in the ancient time. It includes the regulations of the kinds, season and function of imperial sacrifices, which were observed by the emperors after the Han Dynasty. The season’s rituals included meeting with deities in five suberbs, worship cults of Hou’tu and harvest deity,and the rituals of mountains, rivers and ancestral temples.The Han sacring poems recorded inYuefuPoetry-RitualLyricsand other annals of rites and music were used in the imperial sacrifices by emperors,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by cyclicity, performance and symbolism. They were all influenced byYuelingin terms of sacrificial object, animal, date and process.
calendar;Yueling; sacring poems; Han Dynasty; literary history
2012-02-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汉-唐国家祭祀形态与郊庙歌辞研究”(09BZW021)、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汉-唐郊庙歌辞研究”(06JA75011-44024)的研究成果。
张树国(1965-),男,辽宁阜新人,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古代文学与文献研究中心教授。
I207.2
A
1674-2338(2012)05-0068-07
(责任编辑:沈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