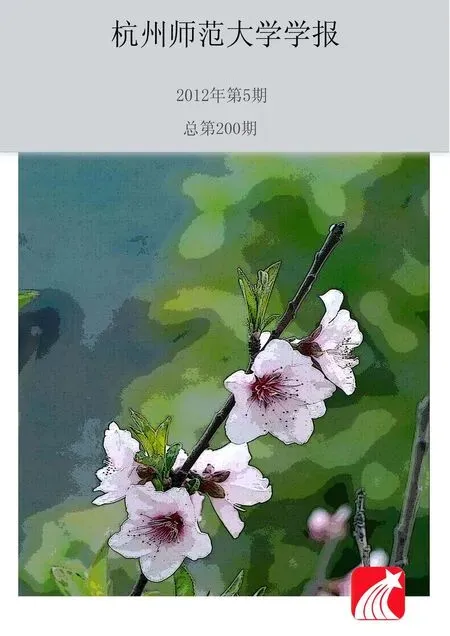既判力、再审制度与司法公正
刘练军
(杭州师范大学 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0036)
法学研究
既判力、再审制度与司法公正
刘练军
(杭州师范大学 法学院,浙江 杭州 310036)
既判力、再审制度和司法公正之间关系紧密。既判力强调的是同一主体不能就同一案件或同一争议事项重复提起诉讼,对于业已判决的案件或事项法院不得再次受理或重新作出判决。法院是既判力的首要维护者。再审制度以轻视乃至无视生效判决既判力为前提,它是有原罪的,在纠纷解决等诸多方面存在有限性。司法公正只能是一种有限的程序公正。坚持司法实质公正,必将对司法判决既判力构成毁灭性挑战,同时又为再审制度的生成和兴盛提供了土壤与温床。人民法院应引导人民祛除实质公正的传统观念,理解并接受法治之真谛:程序公正。
司法;既判力;再审制度;程序公正
2010年3月,陕西省国土资源厅(以下简称陕西国土厅)举办具有法院合议庭性质的“山东煤矿采矿权属纠纷协调会”,否决了陕西榆林中院和陕西高院就陕西省横山县波罗镇山东煤矿采矿权纠纷案所作的生效判决和裁定。*对此事件的分析可参见刘练军《行政机关的有限法治——陕西国土厅否决法院判决事件评析》,载胡锦光主编《2011年中国十大宪法事例评析》,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124-139页。身为行政诉讼被告的陕西国土厅非但拒不执行法院判决,还组织“协调会”公然否决法院判决,委实让人匪夷所思,一时之间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滔滔议论。
笔者陋见以为,此起宪法性事件是这样“炼”成的:再审制度导致判决在同一法院和上级法院面前皆无既判力可言,模仿效应使得作为一方当事人的陕西国土厅亦跟着不尊重、不履行法院判决,判决对当事人缺乏应有的既判力。而在“无钱无剑”的法院面前,陕西国土厅是行使行政权的强势国家机关,陕西国土厅不履行乃至公然否决法院判决事件将行政公权力与司法权之间不平衡、不对称尤其是前者不尊重后者的非理性与反法治关系状况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
此起事件酿成的逻辑表明,如果想从具体制度上认识并化解行政机关与司法部门之间的问题和矛盾,就应从再审制度入手,将问题追溯至如何定性司法审判:司法所谋求和所能实现的到底是有限的程序公正还是无限的实质公正?当事人和法院的诉讼目标应为最好的审判还是最后的审判?准此,与其从行政权和司法权这种宏观维度审视此起宪法事例,毋宁从司法审判的制度设计和制度目标这种技术性维度来考量和省思。
一 既判力及其维护者
公元前399年,克里托劝说在狱中等待执行死刑的苏格拉底逃跑,决然要为服从司法判决不惜含冤而死的苏格拉底反问:“当公开宣布的法律被它没有公职的百姓取消并且破坏,因而失去了它们效力的时候,你想象这个邦国还能生存下去而不被颠覆吗?”对于有人抗议“法庭裁决一旦公布便须遵守”这则信条,苏格拉底反问道:“我们是不是要说:‘对,我确实意图毁坏法律,因为国家在审判我的时候,通过了一个有缺陷的判决,对我造成了伤害?’”[1]2500年前,苏格拉底就为维护判决既判力而不惮舍身赴死,21世纪的我们岂能不认真对待法院判决既判力?
司法判决不能没有既判力,就像生命不能没有阳光、法律不能没有效力一样,此乃不证自明之公理。既判力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法学概念,《元照英美法律词典》解释说:“有合法管辖权的法院就案件作出终局判决后,在原当事人间不得就同一事项、同一诉讼标的、同一请求再次提起诉讼。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是最终的决定。”[2]与此类似,《布莱克法律词典》将既判力的组成要素概括为这样三项:(一)对事项早先已有判决;(二)根据案件本身作出了最后判决;(三)所涉及的是相同事项或与最初提出之事项相关联的事项。[3]
从这两个权威法律词典解释可知,既判力强调的是同一主体不能就同一案件或同一争议问题重复提起诉讼,对于业已判决的案件或事项法院不得再次受理或重新作出判决。既判力的此等含义告诉我们,无论在程序方面还是实体方面,司法判决既判力的有无与司法部门即法院是否认真对待判决既判力关系甚重。
当事人乃至与案件关系不大甚至毫无关联的其他人是否就同一案件或案件所涉及的同一事项重复提起诉讼是他们的权利和自由,包括法院在内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很难合法正当地限制乃至剥夺他们受宪法保护的申诉权。但一旦他们行使其手中的申诉权正式向法院就既决案件或既判事项进行重复乃至反复提起诉讼时,法院就需要考量既决案件和既判事项本身的既判力而裁定是否受理其起诉。生效判决案件被法院重新受理从而失去其既判力的可能性越大,则判决既判力就越弱小,司法权威就越低微,这直接影响到法治的能否实现。司法判决对当事人是否具有既判力,事实上决定于司法判决对作出它的主体即法院能否率先产生实然的既判力。质言之,司法部门即法院才是既判力的首要维护者。
对此论断,我们还可以从逻辑推理和经济学两个视角予以较为精细的论证。
首先,我们从常识性的逻辑推理视角来检视。我国学者曾研究指出:“如果把既判力理解为司法机构作出的终局裁判在法律上所产生的特定的权威性效力,那么,既判力可以包含以下三类法律上的拘束力,即消灭力、确定力和形成力。进一步分析,可分解为四种具体的司法拘束力,它们分别是:终局司法裁判对诉讼主体诉权的消灭力;终局司法裁判对既决事项管辖权的消灭力;终局司法裁判对涉讼事实的确定力;终局司法裁判对涉讼权利义务关系的形成力。”[4]但如果法院不率先认同并捍卫判决所具有的这四种力,那么这四种力必定难以在判决后真正形成并发挥其功能。司法判决既判力的有无,关键在于法院自身能否率先尊崇判决既判力并受其严格约束。
法谚有云:“裁决一经做出,法官即停止作为法官。”法国法学家解释说:“法官一经宣告判决即对案件停止管辖。法官停止管辖是既决事由权威效力的直接结果。这种权威效力禁止法院重新受理它已经做出司法权性质的裁判决定的诉讼请求。”[5]美国杰克逊大法官亦有类似的评议:“一项民事或刑事判决在这种意义上通常会产生既判力,即它有拘束力并且是确凿无疑的——即使有新的事实被发现、即使有新的法律理论被提出,除非某法律条款同意准予重新审判,而这一般由审判法庭自由裁量且在时间上是有限的。”*Brown v. Allen, 344 U. S.443,543(1953).这些评议旨在强调,司法判决一旦宣告,其对作出该判决的法院和法官首先得具有既判力,就像它对当事人形成既判力一样。当事人不得再次提起诉讼,法院和法官亦不能再次受理和重判。这是既判力的两个维度,且相对前一个维度而言,后一个维度更为关键。
除了以上逻辑推理视角外,我们还可以从经济学视角来解析法院是既判力维护者这一论断。
美国波斯纳法官曾从经济学视角探讨过既判力问题,他说:“法院不允许(已决案件)的相同当事人之间再就相同的权利主张提起诉讼(res judicata),这可能是令人惊讶的……其答案是,再诉是需要成本的,但由于我们无法决定前后矛盾的一系列结果(A诉B,结果败诉;A再诉B,结果胜诉;为此B又再诉A以补偿对A的赔偿,结果B又胜诉;依此无穷)何者为正确,所以减少错误成本的收益在总体上为零。无论这一诉讼链在哪一环断裂,我们都没有任何理由认为最新的判决会比以前与之相矛盾的判决更正确。”[6]波斯纳所言极是。不顾既决案件或既判事项的既判力而一再提起诉讼的都是败诉方或判决对其构成不利影响的其他人。对于他们为了其心中理想化的实质公正而不计成本地将诉讼无限延续下去的非理性行为,法院理应合法合理地阻止。且单从经济学上考量,法院亦必须为维护判决既判力而坚决终止那些没完没了的马拉松式诉讼。
首先,对业已生效的既决案件或既决事项重新审理,这对日益捉襟见肘的司法资源——这在当代各国皆然——来说是不堪重负的。将判决既判力束之高阁的缠讼、滥诉行为严重影响了有限司法资源审判功能的有效发挥,与应然上的司法资源分配帕累托最优原则背道而驰。其次,对于双方当事人而言,不顾判决既判力的缠讼或滥诉行为亦是非经济的。进入诉讼程序之后,当事人正常的生活钟摆随之停止,工作、事业、家庭都必须随时准备“满足”因诉讼而起的各种需求。重复诉讼必然严重扰乱他们的正常生活。因此,严格遵循审级制度是每个法院的法定义务,该终止的时候法院必须毅然为诉讼划上永久性句号,否则,对于诉讼另一方当事人及社会而言,诉讼就沦落为一场毫无正义可言的漫长噩梦。美国倡导法律改革的领袖人物——霍华德律师曾痛陈道:“公众对司法的信任并不是建立在设立赔偿额上限或者是对被诉概率的更好理解之上的。信任只能建立在司法机关将诉讼控制在合理边界内所作的不懈努力。”[7]霍华德所呼吁的“司法合理边界”当然包括法院为守护判决既判力而坚持将诉讼控制在有限的审理次数之内。
总之,身为生效判决之母的法院是既判力的首要维护者,它维护既判力的重要方式就是坚持“一事不再理”原则。不无遗憾的是,我国的再审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一事不再理”这种普世司法准则。
二 再审制度及其多重有限性
在我国种种具体的诉讼制度中,受学界和实务界探讨尤其是诟病最多的恐怕非再审制度莫属。有关再审制度的改革也因此成为近年来司法改革的重中之重。所谓再审制度,简言之,就是法院依职权或应检察院和当事人的申诉要求对判决已经生效的案件再次审理的制度。再审制度是我国把司法公正视为实质公正的法律文化“遗产”,是我国现代司法对实质公正的传统正义观的制度化回应。作为“实事求是,有错必纠”这一基本诉讼原则的衍生物,再审制度的合法性渊源于我国三大诉讼法对“以事实为根据”的诉讼认识论理念的认可及弘扬。但在司法实践中,我国再审制度业已演变为无限再审,总括而言,它存在五个方面的无限性即“启动主体无限”、“再审事由无限”、“再审审级无限”、“再审次数无限”和“再审期限无限”。[8]
面对再审制度身上犹如沉疴的难以控制的诸种无限性积疾,曾有人提出了十余项具体的完善建议[9],此诚值得我国司法制度设计者参考和汲取。本文拟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就再审制度的多重有限性略陈管见。
首先,不管经历几审,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始终都是主观有限的。我国的上诉审和再审与域外法治成熟国家最大的差别在于它是一种事实和法律的全面审理,导致上诉审在诉讼中的审级价值难以得到体现和发挥。初审法院与上诉法院乃至最高法院在职责和功能方面基本雷同,此乃我国司法体制及审级制度的中国特色,它导致“多一级法院只是增加了一层行政级别而已”。[10]现代审级制度的基本要求在我国审级制度中没有得到应有的体现和保障。在如此审级生态下运转的再审制度,也就注定只能是事实和法律双重审理的一再重复。不特此也,“实事求是,有错必纠”原则还是再审制度的理念渊源。但关键问题是,案件的客观事实会因复审次数的增加而变得水落石出吗?它可能像其曾经发生的那样完璧无瑕地呈现在其实距离它发生愈来愈远的再审法官面前么?
任何再审法官都不曾亲历事件的发生过程,它对事实的判断和认定需要以司法之外的资源如证人证言等作为媒介,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导致法院所认定的事实与实际发生的事实之间可能产生出入。[11]不宁唯是,经验法则还告诉我们,这种出入会随着审理次数的增加而扩大。因为时间和空间的变幻不会使曾经发生的事实在包括法官在内的人类面前变得更加清晰,恰恰相反,时空的拉长只会导致事实变得愈加模糊难辨。美国现实主义法学事实怀疑论代表人物弗兰克曾提出“事实即猜测”的著名论断。他说:“所谓实际发生的事实其实是经历了两次反应后的结果,第一次是经由证人的反应,第二次是经由那些必须‘认定’事实的人的反应。初审法官或陪审员对证词的反应充满着主观色彩。这样,我们在主观的基础上再添主观。所以,认为初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是主观的一点也不过分。”[12]在美国,上诉审仅仅是法律审,任何案件的事实审理都止步于初审法院。美国法院如此之事实认定规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我国再审过程中事实审理一再上演的制度设计么?面对美国初审法院不回避事实认定的主观性,我国案件事实认定的客观主义想象与法定要求又该何去何从呢?
其次,再审制度在纠纷解决方面的有限性。通过再审解决纠纷尤其是客观公正地解决纠纷,是再审制度设计时的初衷。但不胜枚举的现实案例足以证明,对既判力业已发生的既决案件的再审在化解纠纷方面的功效是非常有限的。试图实现实质正义以化解纠纷的再审制度往往陷入循环再审的圈套而难以自拔,最后的结果多半是纠纷化解日渐渺茫、司法公正渐行渐远。
复次,再审制度对权利救济的有限性。再审制度既然在纠纷解决方面功效有限,那它必然在救济当事人的权利上不像预设的那样药到病除、权利新生。因为进入再审诉讼程序之后,当事人的权利能否切实获得救济,取决于再审对纠纷的解决程度。唯有纠纷彻底解决了,双方当事人均服从判决从而再审判决能产生事实上的既判力,此时当事人的权利救济才能落到实处,此其一。其二,迟来的正义就是非正义。即便经过再审之后,纠纷终于得到了解决,但这对于一方当事人而言,这种正义亦难免是一种迟来的正义。面对这迟来的正义,历经漫长的再审耗费、从物质到精神都为之元气大伤的当事人体悟最深的恐怕不是什么权利与正义而是成本和疲惫。概言之,于正常审级制度之外再叠床架屋设置的再审制度,其救济权利之功效委实不容高估,试图通过再审来救济权利的思维明显违背基本的司法效率规律。在法治成熟国家根本没有我们这么多的再审,其原因就在于此。
最后,亦最为重要的是,真正能进入再审程序的既决案件是有限的。既然有再审制度,那法理上所有符合再审要求的申诉案件都应该机会平等地进入再审程序;但在司法实践中,受司法资源紧张等因素的制约,数量不少的既决案件当事人的申诉根本无法进入再审程序。为解决当事人申诉难难题,2007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民事再审机制进行了修改(参见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第3-9条)以消解实践中非常突出的申诉难顽症。但修订后的民事诉讼再审理由被细化的同时再审的受案标准亦被大大放宽,结果是涌入法院的再审案件比修订前明显增多。而在法院法官数量并未适应民事诉讼法的修订而扩编增加的情况下,或者只有比修订前更为有限的再审申请被准予进入再审程序,或者再审受理之后案件比以往更加漫长地处于等待实质再审状态。无论是哪一种结果,在合法合理的诉讼期限内,现行再审体制都只能有限地再审一部分甚至是相当小的一部分理应再审的案件。毫无疑问,我国一直无法有效破解的再审难顽症还会继续“顽”下去,此诚再审制度之宿命。
总之,再审制度以轻视乃至无视生效判决既判力为前提,而维护判决既判力堪称是司法和法治的生命线。当已然生效的判决既判力因再审制度而被灭失,则再审判决的既判力又如何?直面再审制度如此不一而足的重重困境,我们最该思考的问题或许是司法公正到底是何种意义上的公正,即它是有限公正还是无限公正,是实质公正还是程序公正?
三 程序公正而非实质公正
再审制度背后所体现的是我国传统的一种不看过程、唯重结果的实质公正观念。司法公正等同于实质公正的法治观念,驱使人民为了个案的实质公正而不计成本地将诉讼进行到底,幻想只要锲而不舍地坚持下去总可以如愿地收获其内心所向往的实质公正。但一个又一个活生生的案例告诉我们,此等司法公正认知感性有余、理性不足,是非常片面的。
任何法治语境下的司法制度都难以满足人民对公正的实质性和无限性要求。因为司法制度本来就不是一种感性的制度,它是一种理性的甚至是机械的依法定程序运作的制度装置。司法诉讼一旦在法律上终止了,其结果无论对错,都不会推倒重来。一旦它放弃包括审级制度在内的既定的基本诉讼规则,陪着缠讼或滥讼当事人以再审的名义“耗”下去,则司法制度迟早会脱离法治的轨道而堕入人治的深渊。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现实:“在争议解决的这一范围内,审判的主要价值在于,它为争议的停止提供了一个确定的点。从审判中得到的判决允许争议者停止试图在彼此之间获得平等的举动。在这个意义上更重要的是达到息讼止争的目的而不是达成一个公平的解决办法。因为一个无休无止的争议经常会造成生理上、社会上和经济上的成本,而这些成本无论是当事人还是社会都没有能力去承担”。[13]有鉴于此,司法所追求的公正只能是一种有限的公正,是既定诉讼规则下的程序公正、过程公正。它不以当事人在诉讼中赢得实质公正为目标,其目的在于化解尤其是终止争议,从而保护当事人和社会所需的不被纠纷诉讼过分干扰的正常生活秩序。
我国曾有学者总结了司法六个方面的有限性即“功能的有限性”、“公正的有限性”、“时间的有限性”、“审级的有限性”、“效力的有限性”和“群众满意度的有限性”。[14]其实,可将这六个方面的有限性归纳为一个:公正的有限性。功能、时间、审级和效力等方面的有限性皆为司法公正有限之因,而所谓群众满意度有限性则不过是司法有限公正的一个果而已。笔者不欲从时间、审级等视角详论司法的有限公正,只拟从结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的维度来反证司法公正只能是一种有限的程序公正,无限的实质公正既非司法之旨趣所在,亦非可欲可求之善果。
首先,所有司法判决都只能是一方胜诉、一方败诉。如果案件当事人双方均坚持实质公正论,都紧跟对方的步伐不达实质公正誓不罢休,则司法判决就只能像钟摆一样在两极之间持续摇摆。这将是一个初始判决即一审判决一再被“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个过程持续时间越长否定次数就越多,判决每被否定一次,其权威性和合法性就被减损一次,其有实然既判力并切实得到当事人履行的概率亦随之降低一分。是故,再审制度最终能否满足当事人不惜成本去追求的那个所谓实质公正,结果不能不令人怀疑。而现实生活中既决案件经过一再的再审之后,当事人又转身奔向信访之路不就是对这种怀疑的一个绝妙回应么?
“法院变更其判决的频率愈高,那么其判决的合法性就愈低。”*Planned Parenthood of Southeastern Pa. v. Casey, 505 U.S. 833,866(1992).这是来自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忠告。当我们的法院不认真扮演判决既判力维护者的角色而频频依职权主动启动再审或应申诉被动进行再审时,应该想想这个忠告。如果法官自觉或不自觉地抛弃了司法有限公正信念而沦落至司法实质公正论的践行者,那将意味着我国现行两审终审制的全面沦陷,司法权威自然亦随之扫地以尽。“无论何时,当一个法院的判决由另一个法院来审查时,一定有一部分判决被推翻。这说明(人们)在观点方面存在差异,在由不同的人所组成的不同法院里发现这一点很正常。然而,被高一级法院推翻并不意味着正义因此而得到更好的彰显。毫无疑问,如果有一个超级最高法院的话,那也有相当一部分被我们推翻的州法院的判决再次被推翻。不是因为我们不会犯错误才是最终的,而仅仅因为我们是最终的我们才不会犯错误。”*Brown v. Allen, 344 U. S. 443,540 (1953).杰克逊大法官的这段箴言道出了上级法院尤其是终审法院司法权威之“秘笈”。司法最需要的不是所谓的正确判决尤其不是实质公正观念所认定的那个正确判决,而是最终的判决。当再审制度使得最终的判决变得遥遥无期时,那所谓的司法实质公正不同样是遥不可及么?
其次,司法一旦放弃程序公正而转向实质公正,必将是判决既判力消亡而再审制度长存。在再审程序一再粉墨登场的司法场域中,伴随着既判力消亡的还有法律的可预期性和确定性。而随着法律的可预期性和确定性消亡的必将是法治的沦丧与消亡,也就不可能赢得任何的公正——包括实质公正。人类的公正寻觅史表明,可欲的公正只能是一种法律之下的公正,它是最终通过司法裁判予以实现的一种客观的有限的程序公正。而实质公正是一种主观性的难以按既定法律规范裁量的公正,在终极意义上它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公正。坚持要借助只能实现程序公正的司法审判来谋求主观性的实质公正,则不但实质公正不可得,而且还陷司法于不义。
司法要成为名副其实的司法,其生效判决一定得有既判力。对判决生效案件的再审必须是例外,且一起案件最多只能有一次这样的例外而绝不应让这种例外反复上演最终变为常规,所以,再审案件数量——无论是相对数量还是绝对数量——都必须非常之小。在法理上,司法判决在法律规范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它是合法的有效力的个别规范。即便是那些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司法判决,在它由于是“非法的”因而被其他法院的判决在一定程序下加以取消之前,它也还应是生效的。[15]如此维护司法判决的权威和效力,其良苦用心在于这其实是在维护法律的权威和效力。一旦司法判决可以被再审制度朝令夕改,则法治的可预期性和安定性就荡然无存。法哲学家拉德布鲁赫曾指出:“能够独自为不正确判决的既判力加以辩护的还是法的安定性。”[16]即使明知不正确的判决都要像苏格拉底那样维护其既判力,它对于法的安定性是绝对的不可或缺。
美国坎贝尔大法官曾在判决意见中评论道:“公共秩序的维护、社会的和谐以及家庭的安定要求能胜任的法庭所作出的明确判决应该被当作无可辩驳的法律真理一样接受。这种原则如此深入地根植于法学信念之中,以至于注释者曾指出,既判力能使黑的变为白的,弯的变为直的。任何别的证词都不能动摇它所产生的真理假定,亦没有证据能减损它的法律效力。”*Jeter v. Hewitt, 63 U. S. 352,364 (1859).众所周知,被称为“世纪审判”的辛普森案就是这种“既判案件视为真理”的最好注脚。[17-18]尽管绝大多数美国人对辛普森的清白高度怀疑,但面对陪审团作出的无罪裁决,包括检察官和受害者亲属在内的美国人民不是呼吁上诉或启动再审,而是服从和接受这种堪称毫无实质公正可言的刑事判决。何以如此?因为美国人深信司法公正就是一种程序公正,只要司法审判程序合法,那判决结果就自然合法,而凡是合法的判决就有既判力,要视为真理,必须无条件接受,这就是法治的真相。一部人类法治的发展史就是程序公正不断被强化、实质公正日益被淡化的程序与实质嬗变史。美国法兰克福特大法官坦言:“自由的历史极大程度上是遵循程序保障的历史。对刑事司法的有效管理几乎不可能无视法律所施加的程序公平。”*McNabb v. United States, 318 U. S. 332, 347 (1943).人类司法经验史证明,相对于实质公正,程序公正因多一些客观、少一些主观而更加可靠、更值得信赖和追求。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所谓司法公正就是一种有限的程序公正,对此不管我们无奈也好、无助也罢,都必须虔诚地接受。坚持司法实质公正,必将对司法判决既判力构成毁灭性挑战,同时又为再审制度的生成和兴盛提供土壤与温床。实质公正司法观在我国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成为我国司法文化的本质特征,此等传统司法认知是司法判决屡屡丧失既判力和屡屡被再审的重要文化根源。唯有不断宣传和强化程序正义的正确司法观,才能慢慢铲除实质正义司法观,判决既判力在我国才能迎来它的黎明和春天。唯有如此,彻底改革再审制度的环境与条件才有可能逐渐形成并走向成熟。
四 结语:人民法院理应引导人民
曾有学者沉痛地指出:“我国独一无二的再审制度极其严重地危害了司法判决权威性,使法院不成为法院,判决不成为判决,相应地,诉讼也就不成为诉讼了。诉讼成为一场有始无终的疲劳战。我们在制度设计时,本着善良的愿望,奉行‘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着意为国民塑造一个崭新的‘人民法院’,然而,其结果却是南辕北辙,理想与现实相去甚远。”[19]笔者以为,造成这种“南辕北辙”、“相去甚远”之后果的重要原因在于,在“人民法院”与“人民”的关系上我们完全颠倒了。由人民法院引导人民才符合逻辑与理性,而像现实这样由人民引导乃至支配人民法院委实就反其道而行之了。何以这么说呢?
首先,前文已述,以终结诉讼为使命的既判力对于司法判决绝对不可或缺,司法即人民法院自己才是判决既判力的首要维护者。人民法院要维护判决既判力就不能不引导受其管辖的人民,因为无视判决既判力并申请再审的就是他们。我们要告别人治历史传统,走向现代法治,就必须首先祛除根深蒂固的传统实质公正观,让程序公正观占领人民心中的那块正义高地。这第一步当然是人民法院本身不应随便依职权启动再审,否则它还怎能指望其作出的司法判决对当事人以及社会产生既判力呢?第二步就是在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要耐心、细心地——可以适当借助当事人律师的力量——向当事人灌输司法公正首要的程序公正理念,像美国法学家弗里德曼那样告诫他们:“只要判决是依法作出的就是对的,即使你们对结果感到遗憾,也不能说它是错误的。法律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在很难判明是非时作出判断……一个裁判也可能判错一个球,但是大家都必须服从,比赛才能进行下去。”[20]总之,在司法问题上应该是人民法院引导人民,而不应是相反,否则的话,司法不但无能化解纠纷,而且极有可能沦为人民公然不守法乃至违法牟取私利的工具。
需要指出的是,一切都以人民法院依法裁判为前提,任何非法裁判自然因带有非法之“原罪”而不可能拥有真正终结诉讼意义上的既判力。人民法院所依之法乃是人民——通过其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制定的,所以,人民法院其实是受人民控制和制约的。认识到这一点,就大可不必担心人民法院引导人民会导致人民法院反过来主宰人民、凌驾于人民之上。
其次,从结果主义上看,如果人民法院不引导人民以重建并夯实人民对法院的信任,则人民法院在人民心中的地位将进一步下降,其化解纠纷的功能亦将随之持续地衰变减弱,结果是人民法院愈来愈缺乏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我国的法治之路将越来越步履艰难。
我国司法公信力正遭遇着漫长的寒冬,提升司法公信力以拯救司法和法治已是刻不容缓。而在这场拯救行动中,作为司法主体的人民法院当然得首当其冲,忧深思远。那么人民法院该如何去提升人民对它的支持与信任呢?首先,人民法院要在一个个个案中不厌其烦地向双方当事人亦即人民说明司法判决注重的是程序和证据,其“基本目标是解决争议或者加强社会控制,而不是去认定事实”。[15]在英美国家,当陪审团参与审判时,在陪审团裁决之前法官都会就本案的法律问题向陪审员作必要的指示,所以,陪审制度具有我国普法意义上的法治教育功能。在法官的陪审指示上,我们的陪审过程做得很不够,甚至一些法官都不知陪审指示为何物。职是之故,人民法官在个案审判过程中必须认真补上这一课。在个案诉讼中不是人民法院引导人民就是人民左右人民法院。如果人民法院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占据主动,结果必然是司法和法治的被动。
“一个法院能使一个原告重新取得一方土地,但是它不能使他重新获得名誉。法院可以使一个被告归还一件稀有的动产,但是它不能迫使他恢复一个妻子的已经疏远的爱情。法院能强制一个被告履行一项转让土地的契约,但是它不能强制他去恢复一个私人秘密被严重侵犯的人的精神安宁。”[21]法学大家庞德的这段话其实是在告诫我们,司法的救济功能不是无限的,相反,它是很有限的。司法诉讼只不过是众多纠纷解决方式中的一种,它仅仅能确保法律下的程序公正。当这种有限的法治司法被我们人民普遍接受之时,将是我国司法既判力彰显发力、再审制度成为例外之时,亦将是我国法治宪政真正建成为期不远之时。
[1]柏拉图.苏格拉底最后的日子[M].休·特里德尼克,谢善元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67.
[2]薛波.元照英美法律词典[K].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1189.
[3]Bryan A Garner.Black’LawDictionary[M]. Waterlooville: The West Group, 1996.1312.
[4]张英霞.司法既判力论要兼及司法既判力与司法公信力的关系[J].法律适用,2005,(1).
[5]让·文森,塞尔日·金沙尔.法国民事诉讼法要义[M].罗结珍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5.252.
[6]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下)[M].蒋兆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750-751.
[7]菲利普·K·霍华德.无法生活——将美国人民从法律丛林中解放出来[M].林彦,杨珍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00.
[8]刘青峰.司法判决效力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282-286.
[9]虞政平.我国再审制度的渊源、弊端及完善建议[J].政法论坛,2003,(2).
[10]傅郁林.审级制度的建构原理——从民事程序视角的比较分析[J].中国社会科学,2002,(4).
[11]Geoffrey C. Harzard Jr. Preclusion as to Issues of Law: the Legal System’s Interest[J].IowaLawReview,1984,(70):88.
[12]杰罗姆·弗兰克.初审法院——美国司法中的神话与现实[M].赵承寿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23.
[13]马丁·夏皮罗.法院:比较法上和政治学上的分析[M].张生,李彤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63.
[14]景汉朝.认识司法的有限性[J].理论前沿,2004,(22).
[15]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M].沈宗灵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179.
[16]拉德布鲁赫.法哲学[M].王朴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80.
[17]Jonathan J. Koehler. One in Millions, Billions, and Trillions: Lessons from People v. Collins (1968) for People v. Simpson (1995)[J].J.LegalEduc.,1997,(47):214.
[18]Felman,Shosana.TheJuridicalUnconscious:TrialsandTraumasintheTwentiethCentury[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
[19]何兵,潘剑锋.司法之根本:最后的审判抑或最好的审判?——对我国再审制度的再审视[J].比较法研究,2001,(4).
[20]宋冰.程序、正义与现代化——外国法学家在华演讲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153-154.
[21]罗·庞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M].沈宗灵,董世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31-32.
ResJudicata,ReviewSystemandJudicialJustice
LIU Lian-jun
(Law School,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36, China)
The essence of res judicata is to explain where res judicata effect comes from and how it should be treated theoretically. Borrowing the search achievements in civil action, the essence of res judicata of administrative judgment should include the determinative forces of substantive law and procedural law. Issue and putting into effect of rules of evidence for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 means the transformation of our country’s judicial idea. Among them, the one that is worth reviewing and making criticism is the review system of our country. So, in order to realize criticism and innovation of the system, we have such work to do: to re-recognize the substance of justice, reinvent our country’s idea of procedure value and to combine the one which is on the basis of administrative litigation’s special features, all of which will be important steps in the course of perfecting judicature mechanism after enforcement of the rules.
judiciary; res judicata; review system; procedural justice
2012-06-05
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项目“转型期国家司法哲学、制度和技术研究”(2011SHKXZD014)的研究成果。
刘练军(1973-),男,江西都昌人,法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治中国化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宪法学和司法制度研究。
D926
A
1674-2338(2012)05-0121-08
(责任编辑:沈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