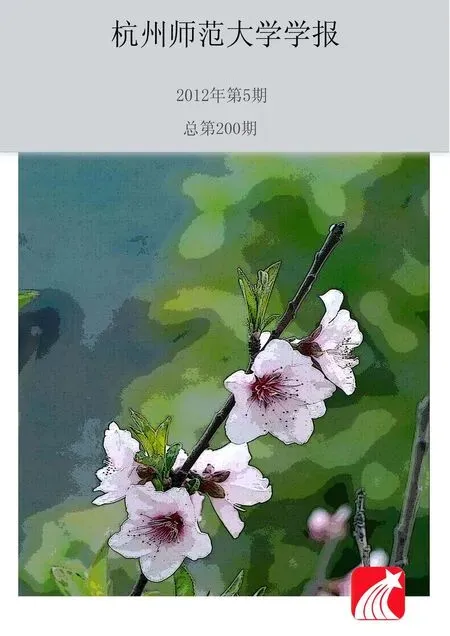永明诗新论
——以沈约为中心
戴 燕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文学研究
永明诗新论
——以沈约为中心
戴 燕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永明诗人将“四声”运用到文学写作当中,不过短短十来年,就令中国诗歌转向了以声律为基本特征的新主流。在沈约等人的努力建设之下,永明诗不但提出了自己明确的主张,并且付诸大量的创作实践,同时还编制有配合新诗理念而又服务于创作实践的工具性的韵书,甚至于,对于诗歌是否符合新的理论以及新的审音办法的评判标准,似乎也在计划之中。像这样有一套完整设计的诗歌改革,在中国诗歌史上,还是第一次。
永明诗;齐梁文学;沈约;四声;声律
“永明诗”的出现,在公元5世纪,令诗歌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向,它的意义,在中国文学史上怎么评估都不过分。自从陈寅恪的《四声三问》发表,大家都知道成为“永明诗”所倡导的诗歌声律基础的汉语“四声”,它的发现是受了印度佛教文化的启发,对“永明诗”的尊敬从此有增无减。但问题似乎也就出现在这里。在陈寅恪典范式研究的强力主导下,文学史领域对于“永明诗”本身的认识,因为纠结在声律的问题上,而面临着局部化、碎片化,作为一个文学运动,它的整体面貌反而越来越不清楚。那么,该如何来描述和评价历史上的永明文学?如何来回答一个最简单的提问:永明诗人将“四声”运用到文学写作当中,不过短短十来年,以十年之功而使诗歌发生这样大的逆转,他们是怎样做到的?
这里面有一个关键人物,就是沈约(411-513)。《南齐书·陆厥传》对“永明诗”有如下描述:“永明末,盛为文章,吴兴沈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毂。汝南周颙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南史·陆厥传》基本相同,只是在“以此制韵”下,增入“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徴不同”几句。这一段常被引用的文字,简要概括了“永明诗”的代表人物及其基本特征,沈约显然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人。
《梁书·沈约传》叙说沈约生平,写到他去世,而后有一段小结,讲了七点:第一说他左眼重瞳、腰有紫痣,第二说他藏书居京师之冠,第三说他用人不计前嫌,第四说他为人情深意重,第五说他历仕三朝、博物洽闻,第六说他诗不如谢朓、文不如任昉但诗文兼备,第七说他昧于荣利、乘时借势,类乎山涛。总结这七点,目的是要说明沈约天赋异禀、胸襟宽大,有过人的见识和才学,而又处世庄重、圆润,所以堪称“一代之英伟”。其中第四点,是讲入梁以后,在梁武帝召集的宴会上,“有妓师是齐文惠宫人,帝问识座中客不?曰:‘惟识沈家令。’约伏座流涕,帝亦悲焉,为之罢酒。”文惠太子的宫人在多年以后仍然认得出沈约,当然可以理解为是由于沈约在永明年间曾经频繁出入文惠太子的东宫,宫中之人因而都与他相熟;不过这个故事,也从另一侧面证明了沈约在当时声望日隆,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正是这样一个沈约,以他在理论、创作以及韵书等各个方面的成就,奠定了永明文学的基础,并使它播及后世,源远流长。
一
南朝文学发展最盛的两个时期,一个是梁武帝的天监年间,一个就是齐武帝永明时期。*《北史》卷83《文苑传序》:“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萧赜在位的这11年,被称作“永明之治”,史书上有“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声舞节,袨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盖以百数”的形容[1]。而永明文学的发达,又与文惠太子萧长懋(458-493)、竟陵王萧子良(460-494)和随郡王萧子隆(474-494)这兄弟三人的“好文”分不开。*参见赵翼《廿二史札记》卷12“齐梁之君多才学”。文惠太子懂声律,“从容有风仪,音韵和辩,引接朝士,人人自以为得意”[2],竟陵王“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焉”[3],随郡王是齐武帝所称“我家东阿也”[4]。沈约、王融、谢朓、周颙和他们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沈约最早是以“文学”之才受到文惠太子的礼遇[5],“时东宫多士,约特被亲遇,每旦入见,影斜方出”[6],在由虞炎、范岫、周颙、袁廓等以“学行才能”著名的东宫文士当中*《南史》卷44《齐武帝诸子·竟陵文宣王子良传》:“文武士多所招集,会稽虞炎、济阳范岫、汝南周颙、陈郡袁廓,并以学行才能,应对左右。”,自然拔得头筹,成为领袖式的人物。与此同时,他又以“文学”之士的身份为竟陵王子良所招,成为西邸常客,而与谢朓(464-499)、萧琛(465?-531)、范云(451-503)、王融(467-493)、萧衍(464-549)、任昉(460-508)、陆倕(470-526)诸人结成“竟陵八友”*《梁书》卷1《武帝纪》:“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高祖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南齐书》卷48《刘绘传》:“永明末,京邑人士盛为文章谈义,皆凑竟陵王西邸。绘为后进领袖,机悟多能。时张融、周颙并有言工,融音旨缓韵,颙辞致绮捷,绘之言吐,又顿挫有风气。”。沈约在“竟陵八友”中年纪最大,在晚辈谢朓的眼里,他是“冠世伟才”,诗乃“丽藻天逸”[7];在随后大写宫体诗的萧纲(503-551)眼里,他也是“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梁书》卷49《文学上·庾肩吾传》引萧纲《与湘东王书》。据《梁书》卷4《简文帝纪》记载,萧纲“六岁便属文”,又“雅好题诗,其序云:‘余七岁有诗癖,长而不倦’”。,与谢朓及任昉、陆倕一样。因此,尽管有舆论认为“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文章,约兼而有之,然不能过也”[6],不承认沈约的诗文创作水平一流,但这并不妨碍沈约在西邸享有盛誉。不管怎么说,就像吉川忠夫说的那样,沈约在永明年间的文坛,以诗文之才崭露头角、获得尊崇,这一时期,是他一生中“真正幸福、充实的年代”[8]。
永明五年(487),沈约奉敕编撰《宋书》,历时一年完成。这部史书,由于传主的作品载入过多,曾招致赵翼“繁简失当”的批评。在赵翼举的例子当中,有一则便是《谢灵运传》,他不明白传中何以收入谢灵运的两个长篇赋作《撰征赋》和《山居赋》,竟然长达万余字*赵翼《陔余丛考》卷6。据稀代麻也子统计,《谢灵运传》计有13 000字。见《〈宋书〉谢灵运传について——沈约〈宋书〉における表现者称扬の方法》,《中国读书の人政治と文学》,第168页,创文社,2002年。。其实,录入传主的这两篇赋作,除了体例上的限制以及编纂时间太短等客观因素之外*周一良说,沈约修史只用一年时间,是因为绝大部分沿用了何承天、徐爰等人的旧史,只有永光元年以后到宋亡的十多年由他补足。见《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周一良集》第1卷,第528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不排除沈约是有意而为之。因为对他来说,谢灵运还是一个同时代的前辈,他“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写,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的盛况,犹在目前,而他的作品也还能够引起共鸣。特别是在《谢灵运传》的最后,沈约写有一段“史臣曰”,被萧统(501-531)当成独立的“史论”,以《谢灵运传论》为题收入《文选》,而被林田慎之助称作“沈约的文学史”,都证明了这恰恰是沈约的用心所在。宋文帝设文学馆,与儒、玄、史三馆并立,标志“文学”始为独立的一科,不过《宋书》里面却未设“文学传”*沈约另有《宋(世)文章志》30卷,见《梁书·沈约传》《隋书·经籍志·史部簿录篇》,当是承袭挚虞《文章志》体例,而著录兼评论刘宋一朝作家、作品。宋代文学兴盛,故傅亮有《续文章志》,宋明帝有《晋江左文章志》,丘灵鞠也有《江左文章录序》。,也没有文学专论,《谢灵运传》的“史臣曰”,可以说就是《宋书》里最重要的一篇文学文献。*参见兴膳宏《〈宋书谢灵运传〉をめぐつて》,《中国の文学理论》,第78页,筑摩书房,1988年。它从文学的发生即“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讲起,自“遗文不睹”的虞夏以前,一路讲到刘宋时代,的确呈现了一个文学史的概观。*该篇收入《文选》卷50“史论”部。刘知几《史通·杂说下》评论“沈侯《谢灵运传论》,全说文体,备言音律,此正可为翰林之补亡,流别之总说耳。如次诸史传,实为乖越”。但周一良在《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中却表扬《宋书》中最体现作者特色的,就是序或论部分,从中可以看到沈约“对历史发展的洞察能力”,其中《谢灵运传论》“叙述魏晋以来诗歌流变,并表达了自己所主张的声调谐和理论”。见《周一良集》第1卷,第514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
所谓“文学史的概观”,是说在“史臣曰”中,既看得到对于各个时代文学潮流的总体描述,如说“自汉至魏,四百余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说“有晋中兴,玄风独振”,说“自建武暨乎义熙,历载将百,虽缀响联辞,波属云委,莫不寄言上德,托意玄珠,遒丽之辞,无闻焉尔”;也可以在各个时代的不同背景下,看到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个体,如“周室既衰”而有屈原、宋玉,再到贾谊、司马相如,以及其后的王褒、刘向、扬雄、班固、崔瑗、蔡邕、张衡,又如“至于建安”而有二祖陈王,“降及元康”而有潘岳、陆机,“爰逮宋氏”而有谢灵运、颜延年,等等。从这些作家身上便可以推断,沈约的这一文学史,基本上是辞赋与诗歌的历史,也或者说是辞赋向诗歌递进的历史。*林田慎之助以为在“沈约的文学史”中,最重要的文学体裁是韵文,韵文当中,是诗,因而它是先秦战国到六朝刘宋时期的韵文史。而据林田慎之助的分析,钟嵘、刘勰在对史诗的描述上,都深受沈约的影响。《中国中世文学评论史》,第267-270页,创文社,1979年。它反映出沈约意识中的文学主流,非诗即辞赋,到了建安以后,诗便蔚为大国,占据垄断地位。这当然也正是南朝时的时代意识,无论是《文心雕龙》的首述骚、诗,还是《文选》的首列赋、诗,又或是诗歌评论集《诗品》、诗歌总集《玉台新咏》的出现[10],无一不表现出诗是这一时代上升最快、最有影响力的文体。
值得注意的是,在结束以上文学史的叙说之后,沈约写道: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自骚人以来,此秘未睹。至于高言妙句,音韵天成,皆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谢、颜,去之弥远。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谬。如曰不然,请待来哲。
这是一段有关诗歌声律的理论阐述。沈约以绘画和音乐作为旁证,来说明诗歌的和谐之美,是要在差异中实现的,只有在不同或对立的元素按照一定规则合理配置的情形之下,才有可能制造出层次丰富、变化无穷的艺术。绘画之美,在于它色彩万变;音乐之美,在于它音高万变;文学的美,也要靠文字声调的错综,要靠轻重、长短、高低不同的每一个字,连缀成句、成段,才能构成错落有致的和谐音响。*逯钦立《四声考》认为沈约声律说,是针对谢灵运体的疏慢阐缓而言,谢灵运诗双声叠韵连篇,双叠字多,则一音拗口,以至辗转不断,故曰阐缓或冗长也。见《逯钦立文存》,第498页,中华书局,2010年。而这种仰赖于声调的错综变化创造出来的和谐,又势必要经过一定纪律和规则的约束。*郭绍虞称此是“人为的声律”,并强调肇端于沈约。见《永明声病说》,收氏著《照隅室古典文学论文集》上编,第21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从这一段阐述中可以看到,沈约理想中的诗歌,其实是一种听觉的文学,它的音效,是要在聆听的过程中实现。绘画靠的是色彩,音乐靠的是音高,这种听觉文学的最基本素材,便是文字的声韵调。
在这里,沈约用了一个极为主观的肯定句式:“妙达此旨,始可言文。”紧接着,他又强调这一理论,在从前的诗人那里,不是“曾无先觉”,就是“去之弥远”,而要实现这样一个诗歌理想,只有“请待来哲”。从这里又可以看出,这一“史臣曰”,分明是一篇关于新诗的时代宣言。
在“永明诗”的三位代表作家中,王融也有过撰写类似理论文章的计划,《诗品序》就说他“常欲造《知音论》,未就而卒”[11](《序》),又从钟嵘记述的王融谈话里面,可以知道他的意思和沈约大致相同,因为他也说:“宫商与二仪俱生,自古词人不知用之。唯颜宪子论文乃云‘律吕音调’,而其实大谬。唯见范晔、谢庄,颇识之耳。”就连语气都好似沈约的“自骚人以来,此秘未睹”云云,其中透露出强烈的自负和同样强烈的责任感,仿佛在迎接历史上新的一天到来。
二
钟嵘(约468-518)的《诗品序》对五言诗在齐梁时代的风行,有过如下描述:“今之士俗,斯风炽矣。才能胜衣,甫就小学,必甘心而驰骛焉。于是庸音杂体,各各为容。至使膏腴子弟,耻文不逮,终朝点缀,分夜呻吟。”有“沈诗任笔”之誉的任昉(460-508),年轻时不善于写诗,尽管“当世王公表奏,莫不请焉”[12],可是他总以不能作诗而深感压力,到了晚年,还沉湎在五言诗的写作练习当中,全然不顾自己“既博学,动辄用事,所以诗不得奇”,结果被人误解为才华已尽。*钟嵘《诗品·中品》。又据《南史》卷59《任昉传》,昉“晚节转好著诗,欲以倾沈,用事过多,属辞不得流便,自尔都下士子慕之,转为穿凿,于是有才尽之谈矣”。
沈约“年二十许,便有撰述之意”[13],不过在永明之前,他的兴趣都在史书,曾编纂晋史、撰写起居注。五言诗的大量写作,大概是要到永明时代以后,因此他现存的五言诗中,可以确信为作于刘宋时期的,就只有《游钟山诗应西阳王教》一首,可是一旦进入永明时期,五言诗的产量便大大增加。*参见网佑次《中国中世文学研究——南齐永明时代を中心として》,第13-14页,新树社,1960年。网佑次并据沈约《宋书自序》考定,沈约20岁时已立志撰晋史,25岁开始修晋史,37岁尚未完成而又奉敕撰宋史,永明五年40岁时受命撰《宋书》,翌年完成,由此可见沈约早年用力于史书撰述,并以诗文闻名,要在齐以后。林家骊据《文选》李善注系于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但林家骊以为《江南曲》《少年新婚为之咏诗》《石塘濑听猿诗》《梁甫吟》《湘夫人诗》等都作于刘宋时代,见氏著《沈约研究·沈约事迹诗文系年》第341、344、345、346页,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
以《文选》所录其五言诗为例:
1.《应诏乐游饯吕僧珍》(天监五年[506])
2.《别范安成》(建武三年[496])
3.《钟山诗应西阳王教》(入齐前)
4.《宿东园》(梁以后)
5.《游沈道士馆》(永泰元年[498])
6.《早发定山》(隆昌元年[494])
7.《新安江水至清浅深见底贻京邑游好》(隆昌元年[494])
8.《和谢宣城诗》(建武三年[496],谢朓有《在郡卧病呈沈尚书》)
9.《应王中丞思远咏月》(建武三年[496]前后,并收入《玉台新咏》)
10.《冬节后至丞相第诣世子车中作》(永明十年[492])
11.《直学省愁卧》(建武年间)
12.《咏湖中雁》(未知)
13.《三月三日率尔成》(永明九年[491])
以上13首五言诗,一首为宋以前作,一首为梁初作,一首撰作时间不明,其余8首均为永明或者是稍后几年所写。*这13首诗的系年,参见《文选》李善注、陈庆元校笺《沈约集校笺》。《文选》收入沈约永明时期或稍后的五言诗,比例远在其他时段之上,绝非偶然。
《玉台新咏》收入沈约的五言诗,也有43首,其中如《登高望春》《昭君辞》《少年新婚为之咏》《拟三妇》《古意》《梦见美人》《效古》《初春》《悼往》《塘上行》《秋夜》等,为拟古诗;而《咏柳》《咏箎》《脚下履》《咏鹤》(或为江洪作)等,为咏物诗;另外还有8首杂言诗《八咏》与《赵瑟曲》《秦筝曲》《阳春曲》。这些诗,虽然难以判定它们的年代,不过从内容推断,大部分也都是齐梁时所作。
现存沈约五言诗中,还有一部分与东宫、西邸文士唱和之作:
1.《奉和竟陵王抄书》,王融有同题作*《沈约集校笺》,第372页,陈庆元考是永明五年(487)作品。。永明五年(487),“竟陵王子良移居鸡笼山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黄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3]。
2.《从齐武帝琅琊城讲武应诏》,王融有同题作*据陈庆元考定,此诗作于永明六年(488),见陈氏校笺《沈约集校笺》卷10,第338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年。。永明六年(488)九月,“车驾幸琅邪城讲武,习水步军”[14]。
3.《和竟陵王游仙诗二首》,王融同时所作《游仙诗应教》存五首。[15](PP.356-359)
4.《奉和竟陵王经刘瓛墓》,永明八年(490),随郡王萧子隆作诗,沈约与竟陵王萧子良、虞炎、柳恽、谢朓等奉和*《沈约集校笺》,第388页,陈庆元考作于永明八年(490)。网祐次考为永明七年(489)作,第61页。。
5.《侍游方山应诏》,王融有同题作*《沈约集校笺》,第393页,陈考永明八年。。永明八年(490),“……世祖幸方山,上曰:‘朕经始此山之南,复为离宫之所。故应有迈灵丘。’灵丘山湖,新林苑也。”[16]
6.《饯谢文学》。永明九年(491),随郡王子隆为镇西将军、荆州刺史,谢朓“转王俭卫军东阁祭酒,太子舍人、随王镇西功曹,转文学”[17]。沈约作诗,虞炎、范云、王融、萧琛、刘绘等有同题作,谢朓有《和别沈右率诸君》。*《沈约集校笺》,第396页,陈考在永明九年(491),网祐次考为永明八年。
7.《行园》。建武五年(498),沈约为国子祭酒,作诗,谢朓同时有《和沈祭酒行园》*《沈约集校笺》,第370页。陈庆元考沈约为国子祭酒在建武三年(496)至永泰元年(498),诗亦作于此间。但据《南齐书·谢朓传》,建武初,谢朓为中书郎,四年出为晋安王镇北谘议、南东海太守,稍后迁尚书吏部郎,可知谢朓在都大约是建武四年、五年,故诗亦作于此际。。
现存沈约诗还有《奉和竟陵王郡县名》《奉和竟陵王药名》等,同时可见王融、范云等人的同名作品。另外,又有以《阻雪》为题的五言诗联句,参加联句的人有沈约、谢朓、江革、王融、王僧孺、谢昊、刘绘。
据《南齐书·乐志》:“竟陵王子良与诸文士造奏之,人为十曲。道人释宝月辞颇美,武帝常被之管弦,而不列于乐官”。[18]《乐府诗集·杂曲歌辞》收录这些题为《永明乐》的五言乐歌,有沈约一曲、谢朓和王融各十曲。从这些歌辞中,还可以看到当日“联翩贵游子,侈靡千金客。华毂起飞尘,珠履竟长陌”(沈约)的盛况,并体会到这种豪奢、奔放的生活带给人“生逢永明乐,死日生之年”(王融)的巨大的幸福感。这大概就是在经历了齐末的政治动荡以后,沈约再见到文惠太子的宫人时,“伏座流涕”、百感交集的原因吧。
在永明时代,沈约既提出了明确的诗歌主张,同时也开展了大量的写作实践,所以钟嵘《诗品》对他的评论就涉及作品和理论两个方面:“观休文众制,五言最优。详其文体,察其余论,固知宪章鲍明远也。所以不闲于经纶,而长于清怨。永明相王爱文,王元长等,皆宗附之约。于时,谢朓未遒,江淹才尽,范云名级故微,故约称独步。”[11](《中品》)
三
据《南史·王僧孺传》记载:“竟陵王子良尝夜集学士,刻烛为诗,四韵者则刻一寸,以此为率。(萧)文琰曰:‘顿烧一寸烛,而成四韵诗,何难之有?’乃与(丘)令楷、江洪等共打铜钵立韵,响灭则诗成,皆可观览。”[19](卷46)这是永明年间文士聚会写诗的一个场景。永明九年(491)三月三日,齐武帝在芳林园修禊宴招群臣,并令王融作《曲水诗序》,据王融说,群臣中也有45人赋诗。[19](卷46)稍后梁武帝时也还有类似的诗会,如“魏中山王元略还北,高祖践于武德殿,赋诗三十韵,限三刻成。(谢)徵二刻便就,其辞甚美,高祖再览焉。”*《梁书》卷50《文学下·谢徵传》。据称,谢徵“父璟,少与从叔朓俱知名。齐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璟亦预焉”。
当五言诗写作成为一个流行事物,被用于社交场合、娱乐活动,人人都能写、随时随地都能写的时候,永明时代的诗人们很快就面临着一种新的压力,那就是成名要快。像刘孝绰(481-539)便是如此,《梁书·刘孝绰传》说:“高祖雅好虫篆,时因宴幸,命沈约、任昉等言志赋诗,孝绰亦见引。尝侍宴,于坐为诗七首,高祖览其文,篇篇嗟赏,由是朝野改观焉。”一顿饭、七首诗,便一举奠定刘孝绰在朝野的地位。张率(475-527)自少年时起,就懂得要刻苦磨炼诗艺,以期一朝成名:“年十二,能属文,常日限为诗一篇,稍进作赋颂,至年十六,向二千许首。”*《梁书》卷33《张率传》。张率12-16岁,正值永明年间。这是诗歌被迅速普及化、大众化带来的一个后果,是诗人们所要付出的代价。既然人人都可以成为诗人,那么唯有多写、快写才能脱颖而出。
这种写诗的时间、数量的压力,同样显示在私人的交往当中。据谢朓《酬德赋序》说,沈约曾“以建武二年,予将南牧,见赠五言诗。予时病,既以不堪莅职,又不获复诗。四年,予忝役朱方,又致一首。迫东偏寇乱,良无暇日。其夏还京师,且事宴言,未遑篇章之思”。连续得到赠诗,却都未能在第一时间奉答,使谢朓心中倍感压力,于是不得不写下长篇的《酬德赋》,来表达对于沈约的感恩之情:“沈侯之丽藻天逸,固难以报章;且欲申之赋颂,得尽体物之旨。”
像这样,要在有限的时间里赋诗,单靠才华是不可能成功的,因此要有张率式的练习,还要有方便使用的工具,使每一个乐于写诗的人都有条件制作出自己的快捷产品。
在永明文士里,最先提供这种工具的,就是“善识声韵”的周颙。根据《南齐书·周颙传》的记载,周颙(441?-491?)“音辞辩丽,出言不穷,宫商朱紫,发口成句。泛涉百家,长于佛理”,既是一位博雅之士,口才也是一流,“每宾友会同,颙虚席晤语,辞韵如流,听者忘倦”。他是个素食主义者,时常独居山中,卫将军王俭(452-489)问他:“卿山中何所食?”他回答说:“赤米白盐,绿葵紫蓼。”*据《南齐书·王俭传》,王俭于“永明元年,进号卫军将军,参掌选事”,又据《文惠太子传》,永明三年,于崇正殿讲《孝经》,少傅王俭以摘句令太(子)仆周颙撰为疏义。则两人问答,是在永明年间。文惠太子问他:“菜食何味最胜?”他又答:“春初早韭,秋末晚菘。”*据《南齐书·文惠太子传》,文惠太子“素多疾,体又过壮,常在宫内,简于遨游”,因此对周颙的山中生活很是好奇。前一个回答音调低昂互舛、色彩错综搭配,对得工整,后一个回答季节、食物也对得巧妙。
周颙运用自己独特的语音知识,编撰了一部《四声切韵》。这是一部韵书,它的特别之处在于以平、上、去、入四声来分析、归纳汉字*《文镜秘府论》天卷《四声论》引刘善经《四声指归》说:“宋末以来,始有四声之目。沈氏乃著其谱论,云起自周颙。”周颙死于永明之年,他的《四声切韵》也就在这一段时间内发酵。,而由沈约、谢朓、王融等人所推动的整个“永明诗”理论,就是建立在这种汉字声调的分析上面的。因为拥有一套新的审音办法,周颙成了对“永明诗”的理论最有贡献的语言学家。他的贵戚出身、语言天分以及优雅的言谈风度,很为年轻学子崇拜和模仿,这使他的《四声切韵》也能够“行于时”*《南史》卷34《周颙传》。但逯钦立《四声考》却以为“此事《南齐书》不载,此书《隋志》亦无目,疑为唐人依托,而不出彦伦之手。且此书今佚,无以见四声之略矣”。见《逯钦立文存》,第468页,中华书局,2010年。,有非常强的号召力。

从《南史·陆厥传》“时有王斌者,不知何许人。著《四声论》行于时”的记载中,可以想见编撰有关“四声”书籍的,还不只周颙、沈约两人,也有籍籍无名之辈染指其间。这也从侧面证明了在五言诗流行的时代,谈论与之相关的“四声”也蔚为风尚。因此,《文镜秘府论·天卷序》说:“沈侯、刘善之后,王、皎、崔、元之前,盛谈四声,争吐病犯,黄卷溢箧,缃帙满车。”这一类的书到了唐代,积攒得越来越多,竟然造成混乱,使“童而好学者,取决无由”,完全搅乱了正常的写作环境。
利用汉字平上去入声调的不同,造成五言诗“低昂互节”的音效,其原则,是沈约在《谢灵运传论》所说:“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可是落实到具体的写作上面,就要靠“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这样的技术性规范,否则还是难以保证写诗的时候,真正做到“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徴不同”。沈约总结了五言诗在用字方面的八种忌讳,统称“八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傍纽、正纽。[20](《论病》)这几项禁令,一是要确保五言诗的音调既错综起伏又不至于拗口,二是要确保五言诗字句齐整而有清晰的节奏。
把握上述原则,在沈约这些永明时代的诗人看来,就能写出铿锵悦耳的五言诗,写出理想的“听觉”作品。而《四声谱》这一类韵书,也就是为人们实现这一诗歌理想所制造出来的文字工具库。只要翻开韵书,总能够在需要的部类找到读音合适的字,将它们精心搭配起来,便会编写出一首声韵和谐的五言诗。
周祖谟曾分析齐梁时的诗文作品,指出在这一阶段,韵文押韵的部类比刘宋时要更加细密,其中“谢朓、沈约审音最细,用韵最严”,并且《文心雕龙》每篇末尾的八句赞语也都押韵,分韵非常严格。[21]这样的成绩,可以看成是《四声谱》这种文字库的功劳。
四
自从“文士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逾于往时”[22]。沈约、谢朓、王融都是创作力极其旺盛的诗人,萧绎就曾感慨:“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谢朓、何逊。”[23]他们在文坛上的声望又都很高,沈约就有“当世辞宗”的称誉[24],而王融也能凭借他的文名,帮竟陵王子良从边地招募到强悍的兵士*据《南齐书·王融传》说:“融文辞辩捷,尤善仓卒属缀,有所造作,援笔可待。子良特相友好,情分殊常。晚节大习骑马。才地既华,兼藉子良之势,倾意宾客,劳问周款,文武翕习辐辏之。招集江西伧楚数百人,并有干用。”。
在这几位永明诗人中,由于沈约的地位最高,声望也最高,他称赞谢朓“二百年来无此诗”[17],表扬何逊“吾每读卿诗,一日三复,犹不能已”[23],都能让他们声名鹊起。而刘勰写完他的巨著《文心雕龙》,“未为时流所称,勰自重其文,欲取定于沈约。约时贵盛,无由自达,乃负其书,候约出,干之于车前,状若货鬻者。约便命取读,大重之,谓为深得文理,常陈诸几案”*据周振甫考证,《文心雕龙》的完成,是在建武三、四年(496、497)前后。见《文心雕龙注释·前言》,第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沈约的重视,果然也就让他及《文心雕龙》的命运发生了改变,他后来得到昭明太子的赏识,不能不说是有这一前因的。[25]
然而正所谓树大招风,针对永明诗,尤其是沈约的理论,很快有了两种尖锐的批评意见。
一种意见的代表,是年轻的作家陆厥(472-499)。陆厥的五言诗,在当时人眼里写得不算好[32],可是他颇有革新的勇气,“诗体甚新变”[26]。针对《谢灵运传》“史臣曰”,他写信给沈约,首先质疑其所谓“自骚人以来,此秘未睹”的说法,认为“前英早已识宫徴,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论所申”,意思是不能由于前人没有这方面的专论,或者是专注于“情物”而非“章句”,就说他们根本不懂。其次,他认为前人率意作文,并不在音韵上刻意下工夫,“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独宫商律吕,必责其如一邪”?所以要说不知其中奥秘,也只能说他们“未穷其致”,而并不是“曾无先觉”。[26]陆厥以“初生牛犊不怕死”的精神挑战沈约的权威,抗议他们这一批人居功自伟,把文学声律当成自己的发明。信中连带着还批评了范晔,因为范晔也曾自诩“性别宫商,识清浊,特能适轻重,济艰难”,而贬低“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像沈约一样抬高自己。
陆厥于永明九年(491)获州举秀才,去世时才28岁,他同年长自己大约30岁的沈约辩论,多少有些年少气盛,未必了解沈约他们的用心所在*郭绍虞在《永明声病说》一文中已说过:“陆厥《与沈约书》谓‘历代众贤似不都谙此处’,实在未曾搔着痒处。”见《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未曾搔着痒处”,原因即在于隔代之人,且地位悬殊,立场必定不同。。沈约在永明时代已是半百左右的人,为文惠太子所亲重,官至中书郎、御史中丞,又刚刚编完《宋书》,地位和影响都远非陆厥所能及,因此,他的回函简明扼要,也颇有居高临下的姿态。他还是强调:
第一,“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高下低昂,非思力所举”,也就是说,别看声调只有宫商角徵羽,文字却是数万,有什么办法能将这数万之文字归于五声之中?这是很不容易办到的事情。
第二,“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何况复过于此者乎”?这是说,要从几万个字中挑选出十个字来,配成一组音调错落和谐的五言诗对句,那又是难上加难。总之,如果没有合适的方法把文字归类,方便作诗的人选取,那么,“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的蓝图,其实是很难实现的。
他还说:自屈原以来,过去的作家对这种“曲折声韵之巧”一向不很重视,看作是“非圣哲立言之所急”,因此,就算是体会得到这五音的差异,也不会去考虑它们实际上怎样“参差变动”,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前世文士便未悟此处”。最后,他又用音乐来做比喻说:一个人的音乐,原则上说都是一致的,“美恶妍媸,不得顿相乖反”,不过事实上人们却不时地发挥失常。为什么呢?就是因为缺少一个不变的章程、式样,尽管“韵与不韵,复有精粗,轮扁不能言,老夫亦不尽辨此”,文学也好,音乐也好,是否音韵和谐,远非言语所能表达,靠的是经验的积累和内心的感悟。
沈约的言下之意,仍然是在坚持编制声谱十分重要,因为它能让写诗这件事,变得有所凭据、有规则可依循,同时也能让诗歌评论变得有所标准。据此,他也很清楚自己的真正贡献,就在于按照新的审音办法编了一部《四声谱》。这也正是日后韵书的滥觞。
顺便说一下,文学史学界受陆厥质问的影响,时常讨论究竟是周颙还是沈约最先发明“四声”,怀疑沈约“把发明权据为己有”。事实上,陆厥批评沈约,不是说他抢了周颙的发明权,而是说“四声”论自古已有,不必等到他们这一批人来发明。以后见者带有审视、特别是挑战的眼光来看,这一说法,也不见得没有道理,只是陆厥实在忽略了历史长河的转折,有时的确是个人推动的结果。
《颜氏家训·文章篇》记载:“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觉,若胸臆语也。”第一条易见事,指少用典。第二条易识字,指不用难以辨认的字,也就是用常见字。《金楼子·杂记》说:“何敬容书名,‘敬’字大作‘苟’,小作‘文’,‘容’字大作‘父’,小作‘口’。陆倕弄之曰:‘卿名‘苟’既奇大,‘父’殊不小。敬容不能答……不辨‘屯’‘乇’两字之异,答人书曰:‘吾比乇弊。’时人以为笑也。”这就是字难以辨识的例子。第三条易读诵,指便于诵读。这三条相互关联,总起来说,就是不要用典,不要用生僻字,要一见之下便能认得、能理解、能念声,而使人一听便知道内容,知道在说些什么东西。因为要“易读诵”,听觉的作用和效果便凸显出来*郭绍虞以为四声制韵,是诗歌吟诵的需要。参见其《永明声病说》。。
可以为补充的,是刘勰《文心雕龙》里的《声律论》一节。刘勰也小沈约20多岁,但他与沈约的立场相似,同样认为文学的声律和谐,要在“吟咏”中实现。他说音乐是有乐律的,因此,歌唱时要先定音高,“古之教歌,先揆以法,使疾呼中宫,徐呼中徴”,而琴也是依此来调音的高低。但文章却是内心的无声独白,而“内听之难,声与心纷”,缺少一定的准则,容易“摛文乖张而不识所调”。所以,要调文章声律,必定要“寄在吟咏”,一旦吟咏出声,就能体会到声律之妙:“滋味流于字句,气力穷于和韵。异音相从谓之和,同声相应谓之韵”。
当沈约他们推动的诗歌改革成为一股潮流的时候,另外一个问题也很快暴露出来,那就是写作实践跟不上理论。不但像刘勰这样的理论家自身准备不足,如弘法大师所批评的:“理到优华,控引弘博,计其幽趣,无以间然。但恨连章结句,时多涩阻,所谓能言之者也,未必能行者也”[20](《四声论》);即便是写了很多诗的沈约,也有与他自己标榜的理论脱节的时候:“约论四声,妙有诠辩,而诸赋亦往往与声韵乖”[26]。因此,针对这一现象的批评声音也乘势而起,以钟嵘(约468-约518)的《诗品》为代表。
钟嵘与陆厥、刘勰大体为同一代人,永明三年(485)入国学,自梁武帝天监三年(504)起,又与刘勰同在临川王萧宏帐下供职。《南史·钟嵘传》记载:“嵘尝求誉于沈约,约拒之。及约卒,嵘品古今诗为评,言其优劣。”认为由于沈约没有像对待刘勰那样提携钟嵘,钟嵘就将怨气发泄在《诗品》里。这一条记载是否可信,姑且不论;其《诗品序》云:“观王公缙绅之士,每博论之余,何尝不以诗为口实。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竞起,准的无依。近彭城刘士章,俊赏之士,疾其淆乱,欲为当世诗品,口陈标榜,其文未遂。嵘感而作焉。”从这一段自述里,便可以知道他的撰写《诗品》,首先是受了与沈约等人有过唱和的刘绘的启发,其次是他也想通过评论的方式,来宣示自己的诗歌主张。
钟嵘的主张是,五言诗只要写得“清浊同流,口吻调和”,就已经达到标准,没必要禁忌太多,而使其失去自然之美。他也有与陆厥相似的疑问:“昔曹、刘殆文章之圣,陆、谢为体二之才,锐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闻宫商之辨,四声之论。或谓前达偶然不见,岂其然乎?”只是他认为,过去的诗“皆被之金竹”,“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所以只要能配合音乐,就可以说是谐韵,“与世之言宫商异矣”。然而今天“王元长创其首,谢朓、沈约扬其波”的所谓宫商四声之论,是以“不被管弦”为前提的,不被管弦,要求自然不同,“但使清浊同流,口吻调和,斯为足矣”,何必要像王融他们所误导,“务为精密,襞积细微,专相陵架”,“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又何况,一般诗人都已经了解到要防止蜂腰、鹤膝之病。因此,他宣称:“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使清浊同流,口吻调和,斯为足矣。至于平上去入,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然而,弘法大师因此批评钟嵘“徒见口吻之为工,不知调和之有术”(《文镜秘府论·四声论》),就是说他不知道随意天成与刻意布置的区别。也因此,推动永明诗律,而“为后进士子所嗟慕”的谢朓,“见重闾里,诵咏成音”的沈约,都被他置之中品;曾在他面前高谈阔论“宫商与二仪具生,自古词人不知用之”的王融[11](《序》),以及被陆厥讽刺过的范晔,更被贬在下品。
除了陆厥、钟嵘,据说梁武帝萧衍也不喜欢“四声”之论。他曾问朱异说:“何者名为四声?”朱异回答:“‘天子万福’即是四声。”他接着反问:“‘天子寿考’岂不是四声也。”[20](《四声论》)又有一说是梁武帝向周捨发问,周捨所举四声之例为“天子圣哲”。“天子万福”也好,“天子圣哲”也罢,都是用尽心思想出来的逢迎梁武帝的话,可是梁武帝听了,也并未就此改变自己的主意,照样“竟不遵用”。
虽然有质疑的、反对的声音,有梁武帝不予支持的表态,然而在沈约这一齐梁文学界、思想界第一人的努力建设之下*吉川忠夫认为:在六朝门阀贵族社会,寒门为了争取到社会地位,往往要去掌握被贵族占有的文化。寒门出身的沈约,就是以他卓越的文学才能而成为齐梁文学界和思想界第一人的,也正是史书上所说“建武以后,草泽底下,化为贵人”的一个典型。见《沈约の传记と生活》,第199-229页,同朋舍,1984年。,永明诗不但提出了自己明确的主张,并且付诸大量的创作实践,同时还编制有配合新诗理念而又服务于创作实践的工具性的韵书,甚至于,对于诗歌是否符合新的理论以及新的审音办法的评判标准,似乎也在计划之中。从理想到理想的一步步落实,像这样有一套完整的设计,在中国诗歌史上,这还是第一次。这一次,便改变了诗歌的发展方向,使得以声律为基本特征的诗歌,成为中国古典诗史上的主流。
[1]萧子显.南齐书·良政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2.
[2]萧子显.南齐书·文惠太子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2.
[3]萧子显.南齐书·武十七王·竟陵文宣王子良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2.
[4]萧子显.南齐书·武十七王·随郡王子隆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2.
[5]萧子显.南齐书·虞炎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2.
[6]姚思廉.梁书·沈约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7]谢朓.酬德赋序[M]//曹融南.谢宣城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1.
[8]吉川忠夫.沈约研究[M]//六朝精神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84.210.
[9]兴膳宏.《宋书谢灵运传》をめぐつて[M]//中国の文学理论.东京:筑摩书房,1988.78.
[10]网佑次.中国中世文学研究——南齐永明时代を中心として[M].东京:新树社,1960.137.
[11]钟嵘,曹旭.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12]姚思廉.梁书·任昉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3]沈约.宋书·自序[M].北京:中华书局,1974.
[14]萧子显.南齐书·武帝纪[M].北京:中华书局,1972.
[15]陈庆元.沈约集校笺[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5.
[16]萧子显.南齐书·徐孝嗣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2.
[17]萧子显.南齐书·谢朓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2.
[18]郭茂倩.乐府诗集·杂曲歌辞[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9]萧统.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0]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
[21]罗常培,周祖谟.齐梁陈隋时期诗文韵部研究[M]//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351.
[22]姚思廉.梁书·文学上·庾肩吾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3]姚思廉.梁书·文学上·何逊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4]姚思廉.梁书·王筠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5]姚思廉.梁书·文学下·刘勰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3.
[26]萧子显.南齐书·陆厥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2.
NewDiscussiononYongmingPoetry——OnShenYue
DAI Ya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It was only about ten years that the Yongming poets applied “four tones” into literary writing, but this brought about the new mainstream of Chinese poetry which was characterized by sound and rhymes. Through the effort of Shen Yue, who was the first person in the literary and ideological world of the Southern Qi Dynasty and the Liang Dynasty, Yongming Poetry not only put forward its own viewpoints, and had a lot of creative practice, but also edited rhyme books which embodied the idea of new poetry and served for creative practice. Furthermore, the criterion for judging whether a poem corresponded with the new theory and new approach to tone examination also seemed to have been planned. Such a complete and well-designed reform of poetry is the first one in Chinese poetry history.
Yongming Poetry; Qi-Liang literature; Shen Yue; four tones; sound and rhyme
2012-08-24
戴燕(1961-),女,安徽芜湖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古文学史、近代学术史、日本近代中国学的研究。
I207.2
A
1674-2338(2012)05-0059-09
(责任编辑:沈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