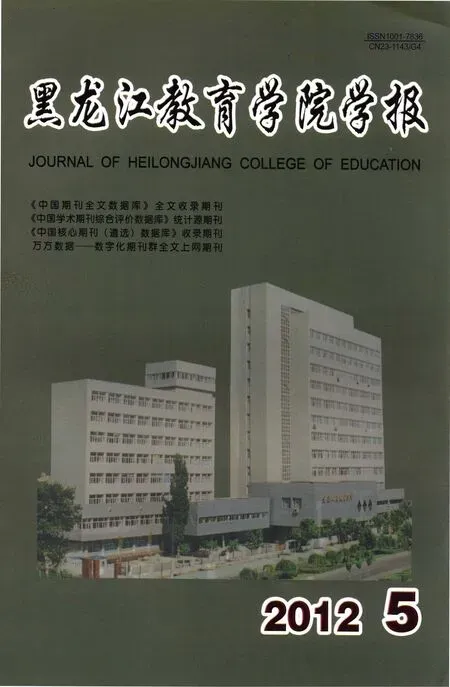英源外来词译借的文化学审视
王催春
英源外来词译借的文化学审视
王催春
(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杭州310018)
以当代汉语中出现的常用英源外来词为对象,从文化学的角度分析英源外来词译借所涉及的语用策略,并探讨中国文化语境在外来词译借中的作用,即在表音、释义的汉语字、词选择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对中华民族文化心理、形象思维方式以及汉字文化意义等因素的顺从。
英源外来语;翻译;文化语境
引言
各民族之间多层次、多渠道的交流使不同的文化互相碰撞,作为文化交流的载体,语言在被用来学习、吸收外国文化的同时,本身也作为文化现象之一被借用[1]。汉语中的英源外来词,是汉民族文化与英美文化相互接触、交流和融合的产物,现已成为汉语词汇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英源外来词的借用,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和社会现象,它与接受方的文化体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的译借与使用,体现了英、汉两个民族在社会与文化心理的对接[2]。研究英源外来词译借过程中的文化现象和文化价值,不仅从语言学上非常必要,从文化学的角度来讲,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英源外来词译借的文化语境顺应
文化语境在所有翻译中都是最重要的因素,其重要性大于任何法规、任何基本词义[3]。外来词汉译的重构过程很大程度上受到文化语境的制约,译借的成果与否就在于能否理清字、词的文化意义和韵味,恰当、准确地选择汉语字词,以顺应中国的文化语境。
被译借的外来语所代表的都是汉语固有词汇中所缺乏的概念,尽管关于外来词的译借一直存在所谓的“音译”和“意译”之争,然而,无论“音译”还是“意译”,译借来的外来词,其使用的环境和使用者都是切实存在于中国文化语境之中的,因此,其译借的唯一宗旨即是符合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顺应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满足中国人对外来语的认可和使用[4]。纵观近三十年出现在汉语中的大量英源外来词,有的很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有的却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排斥,甚至销声匿迹。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本族语言、文化因素在外来词上反映不足或反映失当[5]。
外来词的传入首先是听觉上的,我们往往会先根据外来词的发音,再考量其所代表的实物意义或现实意义,作为汉译的一个要素。在译借过程中,中国人喜欢在本族语中寻找适应新词构词与表义需要的词根和词汇,用接近或相似英文外来词发音的谐音译词,并且带上实际的汉语语素意义。如“bungee——蹦 极”、“shock——休 克”、“blog——博 客”、“media——媒体”、“talk show——脱口秀”等,这些外来词的译借都符合汉字表意特征,即所谓的“望文生义”的心理反应。其次,外来词的字、词选择是否得当,还要得到生活在汉文化中的人们的心理认可[6],这种心理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外来语的产生、流行或淡出。如“Cocacola——可口可乐”和“honey month——蜜月”,一个“乐”,一个“蜜”,正是因为符合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才被广为接受和使用;还有“TOEFL——托福”,“福”,一个映射吉祥的字眼,把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展露无遗。再看“hacker——黑客”一词,把它音译为“黑客”,除了两者读音上相似外,汉语的文化因素,如“黑”字引发的贬义和负面联想也不容忽视。又如“AIDS”一词,最初有“爱滋病”和“艾滋病”两个最为常见的翻译版本,最后“爱”字为“艾”所替换,正是因为“爱”在中国人心目中是与“爱情”、“友爱”等字眼相联系的,把“爱”与“病”串连成词,心理上难以接受。汉文化这种求雅避俗的心理也体现在医药等专有名词的选择上,很多药品的中文名称都带有“宁、灵、康、平”等字眼,如“Bufferin——百服宁”(感冒药)、“Loratadine——开瑞坦”(抗过敏药)、“Reserpine——利血平”(抗高血压药)、“Shampoo——香波”、“Pentium——奔腾”、“Johnson——强生”、“Pizza Hut——必胜客”、“shermons——席梦思”等,这些字的选择充分映照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语言禁忌和祈福心理。
外来语的意译也体现了对汉语语言和文化语境的顺应,意译词的创造、选择和传播实际上就是创造者民族文化和民族心理的历史积淀。当外来事物反映的文化不被接受时,我们便尽可能地利用我们自己语言中的已知信息,便于国人认知和理解,以缩短文化交际的过程,减少和避免文化冲突[7]。汉字是表意文字,联想综合与形象思维是中国人思维的主要方式,在翻译过程中,应加大对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的考量,用中国人一目了然的方式意译出的新词汇,才能为中国人所接受。如对“cement”的认识过程,开始被译为“水门汀”,之后又改叫“洋灰”,最后才意译为“水泥”,皆因在使用该物质时需用水搅拌成泥状,“水泥”一词不仅形象,而且“ce”与“水”发音近似,体现了音意兼顾的翻译技巧;类似的还有“massage”、“fairplay”等词的翻译,最初以“马杀鸡”、“费厄泼莱”的音译法原封不动地借入汉语,终因意义无法对接而传播受阻,最终按照中国的文化内涵意译为“按摩”和“公平竞争”,方为大家所接受。再如“black horse——黑马”、“hot line——热线”、“bull market——牛 市”、“cold war——冷战”、“soft landing——软着陆”、“knowledge economy——知识经济”、“green food——绿色食品”、“super market——超市”、“white collar——白领”、“fast food——快餐”、“bachelor mother——单身母亲”、“broad band——宽带”等,都是译者对中国文化心理顺应的成功之例。另外,中国人善直观思维,喜用物品的直观印象及功能命名,如“country music——乡村音乐”、“gap generation——代沟”、“emotional quotient——情商”、“computer——计算机”、“violin——小提琴”、“city bring——城市带”、“millennium bug——千年虫”、“soap opera——肥皂剧”、“data bank——数据库”、“background music——背景音乐”、“streaking——裸跑”、“tube baby——试管婴儿”等,译文的处理很好地遵循了语言的经济原则和语法原则,也方便读者在源语词汇和汉语词汇中找到一一对应的信息关联[8]。
二、英源外来词译借的汉字文化意义顺应
汉语字词是形、音、义三位一体的结构单位,意义的传递要以“形”和“音”作为载体。在创造性地译借、吸收外来词时,应根据汉字的构造和文化意义选择相应的汉语字词,着力体现汉语语音及汉字表意的属性,以其鲜明的汉语语音和极富表现力的语义色彩,与汉语固有词汇形成有机和谐的整体。
1.音意兼译
音、意结合,是外来词翻译的最佳境界,也是归化和异化策略综合运用的体现。在不影响原音、原义的基础上,根据外来词的发音,利用表示类属信息的偏旁部首给人以暗示,这是从形声字的造字方法中得到的启示。例如:“lemon——柠檬”,取“木”字旁说明它的植物类属,用“宁蒙”译其音;“uranium——铀”,选用“金”字旁表示它的金属类属,用“由”译其音;“helium——氦”,用“气”字旁表明这是一种气体,用“亥”译其音;再如:“mango——芒果”、“nickel——镍”、“chrome——铬”、“chiffon——雪纺”等。在物名和科学术语翻译中,这样的译借方法使用最多。
其次,在外来词译借过程中,常采取意译性质词、音译其剩余部分的方式,将因翻译而损失的信息得以补偿,既保留了外来语的语音特征,又兼顾汉字意义[9],这种外来词的翻译方式在中西文化交流时最为有效。例如:“icecream——冰激凌”,意译“ice”为“冰”,音译后半部分为“激凌”,读者一眼就能看出此物为与“冰”有关的制品;再如:“utopia——乌托邦”,选取“子虚乌有”的“乌”,表达“空想”之义,再以“邦”字,给人以“邦国、国度”之意,明了、贴切;还有“minishirt——迷你 裙”、“gene draft——基 因 草 图”、“Nobel Prize——诺贝 尔 奖”、“Wall Street——华 尔 街”、“break dance——霹雳舞”、“Salad oil——色拉油”、“milk shake——奶昔”等,就算不懂彼此的语言,说听双方都可以根据对方说出的事物,了解其所指代的事物、想表达的意思。
2.语素释义
在译借过程中,对中国自身文化的深刻考虑是外来词能否被广泛接受的重要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译借手段就是在音译词后添加表类别或属性性质的汉语语素,点明它的性质及种类,,将源语词汇中明“无”而实“有”的含义在译名中显现出来[10]使译名“增值”。如:“Hula-hoop——呼啦圈”、“bowling——保龄球”、“ballet——芭蕾舞”、“Jazz——爵士乐”、“jeep——吉普车”、“buffet——自助餐”、“bar——酒吧”、“beer——啤酒”、“rifle——来福枪”、“golf——高尔夫球”、“rally——拉力赛”“internet——因特网”、“domino——多米诺效应”、“Dink——丁克家庭”、“sauna——桑拿浴”、“topology——拓扑学”等,都是通过类属语素与音译巧妙结合,如同汉语本土词汇一样亲切、自然。
结束语
作为一种异质的语言文字成分,外来词在被借用的过程中,直接受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思维方式以及汉字文化意义的制约。凭借着强大的消融能力,汉文化将所吸收的外来文化加以消化、改造,并根据汉语汉字系统自有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将其汉化[11]。汉语言正是在一次次外来词、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兼收并蓄,吐故纳新,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1]欧阳笃耘.英汉翻译中文化差异的处理方法[J].长沙大学学报,2000,(3):40.
[2]王欣.文化语境顺应对言语交际的阐释力[J].外语学刊,2008,(4):103 -105.
[3]Peter Newmark.Approaches to Translation[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113.
[4]廖开洪,李锦.文化语境顺应对翻译中词义选择的制约[J].山东外语教学,2005,(5):92 -95.
[5]郭鸿杰.从形态学的角度论汉语中的英语借词对汉语构词法的影响[J].上海交通大学学报,2002,(4):104-108.
[6]赵爱武.从外来语引进之三大高峰看其特征[J].语言与翻译,2005,(1):47.
[7]史有为.汉语外来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108.
[8]翟英华.关于现代汉语外来词规范问题的几点思考[J].佳木斯大学学报,2003,(2):55.
[9]胡清平.音意兼译外来语中译之首选[J].中国翻译,2001,(6):28 -31.
[10]潘文国.汉语音译词中的“义溢出”现象[G]∥英汉语比较与翻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574-597.
[11]王述文.文字建构与心态文化[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9,(2):62 -65.
On Cultural-context Adaptation of English Loanwords Interpretation
WANG Cui-chun
(Zhejiang Water Conservancy& Hydropower College,Hangzhou 310018,China)
The pragmatic strategies of English loanwords interpretation are discussed in the paper in the view of cultural-context adaptation based on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vocabulary.The func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context is alse analyzed in translating English loanwords into Chinese,in which the Chinese cultural psychology,national thinking mode,as well as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and lingering charm of Chinese characters must be taken into full consideration in the selecting process of phonetic representative and semantic interpretative words.
English loanwords;interpretation;cultural context
H136.5
A
1001-7836(2012)05-0138-03
10.3969/j.issn.1001 -7836.2012.05.056
2012-03-07
杭州市2011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英源外来词译借的文化学审视”(课题号:C11YY15)研究成果
王催春(1969-),女,浙江上虞人,副教授,从事应用语言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