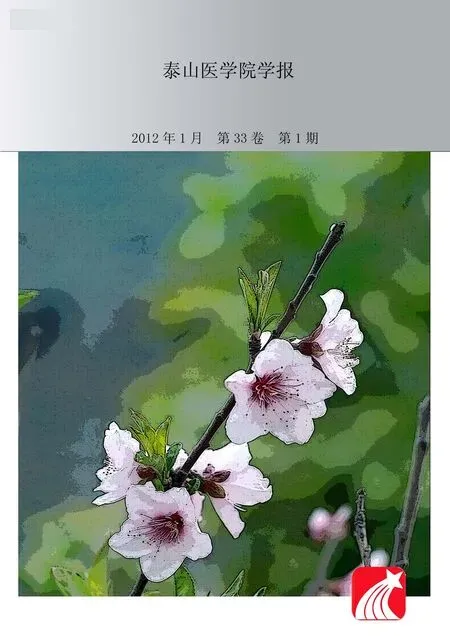生物样本库
——转化医学与第六次科技革命
王庆宝
(泰山医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6)
1 生物样本库的发展与现状
生物样本库,又称生物银行(biobank),主要是指收集、保存用于各种研究而非用于器官移植的人类各种生物样本,包括组织、全血、血浆、血清、DNA、RNA、生物体液,或经初步处理过的生物样本,以及与这些生物样本相关的各种临床资料、病理、治疗与随访等信息数据,是按严格的技术标准专业化收集、运输、存储、管理和使用的资源库[1-2]。
生物样本库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上百年前已经出现。公元18世纪,意大利解剖学家Morgagni(1682~1771年)通过解剖大量尸体后发现,不同的疾病是由不同的器官形态变化所致,因而创立了器官病理学(organ pathology)。在那个时期就应该有了最早的简易的生物样本库。随着上世纪中叶冻存理论和技术的发展,1949年George Hyatt创建美国海军组织库,1952年捷克斯洛伐克R.Klen建立了University Hospital Hradec Kralove组织库。1999年英国成立的UK Biobank,是目前比较大的样本库,到2010年底已经入库了50万人共1500万份的血液和尿液样本。
美国从1987年开始就出现了专门的生物样本资源库,2001年欧洲生物样本库(Eurobiobank)建立,随后,英国、奥地利、澳大利亚等国家也相继建立了自己的生物样本资源库。在亚洲地区,韩国、日本、新加坡也都拥有国家生物样本库网络。2009年9月,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NCI)开始筹划建立美国第一个国家级肿瘤生物银行。有科学家认为,该样本库建设是美国医学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美国《时代》杂志更是将这个国家生物银行建设列为"2009年改变世界十大规划之八"[3]。
国际生物样本库已呈现网络化、联盟化的趋势。目前,西方国家样本库已朝着网络化发展,样本分散储存在多个加盟单位,而信息统一管理,通过网络方便查询,使生物信息资源利用率大为提高。在北美、欧洲等地还出现了一些全国性的样本库联合会,以规范样本库技术、协调成员单位间的相互合作,实现资源共享、联合研发,大为提升了基础医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为生命科学研究提供了国际间的大平台[4-6]。
我国是人口大国,疾病生物样本资源极其丰富,是任何一个国家无可比拟的。我国的生物样本库建设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1994年中国科学院就建立了中华民族永生细胞库,而后,山东省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北京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泰州(复旦)健康科学研究院、SBC芯超生物银行等专项生物标本资源库也相继建立。1996年建立的北京大学临床肿瘤学院肿瘤组织库、2004年天津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与美国癌症研究基金会(NFCR)联合建立的肿瘤组织库、湘雅医院等医院的精子库、天津脐血库等。目前,我国生物样本库的建设仍存在样本管理无序、分散而不集中、封闭而不开放、样本流失、缺乏标准化流程、缺乏质控体系与信息化管理、临床资料残缺不全(尤其治疗与随访资料)、伦理学与法律不健全等重要问题[7]。
2009年,我国成立了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组织生物样本库(生物银行)分会,全国60家知名医院及科研院所共89名委员组成了第一届专业委员会。该分会秉承"珍惜样本、执行标准、充分应用、维护产权"的宗旨,在全国范围内积极组织活动,使我国生物样本库有序、规范、健康发展[8]。近几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江苏等沿海省份已纷纷开始建立生物样本库和相应的协会机构,现已成立各级转化医学研究平台达到30多个。
2 生物样本库是转化医学的支撑和源泉
转化医学的概念是新的,但内容并不是新的。在医学形成之初,转化医学随之出现。当初的医生们面对病人及病情,利用当时的条件和自然环境探索或加工制造药品、器械等,用来为病人解除病痛,或防治疾病的流行,这就形成了最初的转化医学内容。我国汉代的名医华佗就从麻黄中提炼出麻沸散并用于临床麻醉就是例证。自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随着自然哲学和科学的发展,尤其是人体解剖学和《血液循环》理论的形成,使医学进入到实验医学的时代。由于物理学和化学的快速发展而出现了"物理医学"、"化学医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病理解剖学的发展以及X线的发现,牛痘接种的成功等引领了当时基础研究中的成果可以在临床实践中迅速应用,推动了临床医学的大发展。英国的Flamming于1929年从青霉菌中发现了青霉素,二次世界大战中青霉素挽救了无数士兵的生命。自1953年DNA双螺旋结构发现以后,引发了基因工程和分子生物学的重大革命,基础医学研究突飞猛进,但很多成果难以直接应用到临床,出现了实验室与临床的脱节。这个时期,临床医生和医疗器械公司、厂家则特别注重技术的发展。就外科领域来说在显微外科、器官移植、微创外科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物理和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促生了CT、磁共振、超声及内窥镜,它们的应用使医学诊断水平大幅度提高。但基础医学研究的成果却没能快速有效地转化到临床实践中来,在临床上没有得到更大的发挥和体现。这种发展的结果导致了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割离,彼此之间的共同语言、沟通和交流逐渐减少。因此,从基础医学到临床医学之间形成了一道屏障,有人称之为"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之间的死亡谷"[9]。
自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尽管基础医学和临床医学都得到了飞速发展,但双方在半个多世纪发展的进程中都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鸿沟--癌症的问题、糖尿病、高血压及心脑血管疾病、艾滋病等重大难题没有实质性、突破性进展。这使得医学及生命科学的研究者们重新反思--在转化医学中寻求新的答案。
转化医学(translational medicine)或者称为转化研究(translational research),是倡导实验室与临床研究双向转化的模式[10]。1992年《Science》杂志首次提出"从实验室到病床"(bench to bedside)的概念[11],1994 年开始出现转化型研究[12],1996 年《Lancet》杂志首现转化医学这一新名词[13]。转化医学的关键是在从事基础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之间首先打破固有的屏障,建立起紧密的联系与合作,从临床实践中发现问题,将其凝练成基础医学研究的课题进行研究。即临床医生提出问题,交由基础医学研究人员进行研究,再将基础研究的成果快速转化为临床所应用的,新的预防、诊断、检查和治疗方法,新药物和健康保障措施,更快地受益于病人和民众。同时,临床上出现的新问题又能及时反馈到实验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形成良性循环和互动,推动临床医学和基础医学更加深入全面的发展。
转化医学是生物医学发展特别是基因组学和蛋白质组学以及生物信息学发展的时代产物。标准化生物样本库是基因组、转录组、蛋白组等生命科学研究与生物医药研发最重要环节[14],是众多重要科研成果快速产业化、应用到临床,实现转化医学的重要保证,也是生命科学与生物医药技术自主创新体系中至关重要的环节与保证,是最宝贵资源。
样本库的建立能有效地为人类直接探究疾病发生、发展和转归机制提供具体研究对象,尤其是罕见样本、少见样本和重大疾病样本,能进行有针对性或突破性研发;样本集中,避免了单兵作战长期积累的劣势,能够缩短研发周期,早出成果、快出成果。规范标准化的样本库可有效地保留离体生物组织在短期内的生物学活性,避免基因的降解、蛋白的变性等。样本库资源不仅能满足加盟单位自身的研究需要,同时可向其他医院、科研机构和高校的研究者提供各种符合科研要求的标准化病例标本和正常对照标本[15]。同时生物样本库的建立能有效加强研究部门、研究者之间的相互合作,协同研发。
3 如何应对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来临
2011年4月,根据中国科学院的部署,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开展了"第六次科技革命的预测研究",完成了《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16]一书。
该书认为:从人类文明和世界现代化的角度看,第六次科技革命(约2020~2050年)有可能以生命科学为基础,融合信息科技和纳米科技,提供解决和满足人类精神生活和生活质量需要的最新科技。从科学角度看,第六次科技革命将是一次新生物学革命;从技术角度看,它是一次"创生和再生革命";从产业角度看,它是一次"仿生和再生革命";从文明角度看,它是一次"再生和永生革命"。第六次科技革命的主体部分将包括:整合和创生生物学、思维和神经生物学、生命和再生工程、信息和仿生工程、纳米和仿生工程等。
从世界科技发展的历史来看,我国已经痛失了前四次科技革命的机遇,使我们的科学技术长期落后于发达国家,在第五次科技革命中我们也仅仅是跟踪模仿者,尽管在经济上有了大的发展,但在科技上并没有取得巨大的成就。这不得不令我们深入反思:如何应对新的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来临?在新的科技革命中我们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一书提出了很好的对策和建议。
从生物样本库建立和转化医学的角度看,我们处在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前夜应该做些什么?笔者有以下几点思考:
(1)我国是人体生物样本的大国,在政府的关心支持下,在企业的参与下,建立省级、国家级标准化、网络化生物样本库完全可行。这有利于对重大疾病的诊治、预防实现新突破,有利于实验室和临床之间快速而有效的转化,有利于为迎接第六次科技革命的到来奠定基础。
(2)目前,高标准的生物样本库要在保存样本生物活性的时间上做出进一步的努力和探索,从而有利于更为真实地研究揭示从分子-细胞-组织-器官-人体的双向关系,有利于探究重大疾病的机制和生命的复杂现象。因为现在对分子、细胞的各种研究综合起来也不能解释器官和人体的功能和复杂现象。
(3)以生物样本库和转化医学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为支撑和起点,转变固有的思维模式,在偶然性和必然性当中寻找认识重大疾病和生命现象的突破点。以现有科研资源为基础,以改变思维方式为路径,以建立新的理论体系、符号体系、技术体系为方向,立足于现实的难题提出假设或假说,长期孜孜探究,有可能取得进展或突破。
(4)转化医学的内涵,不仅表现为医学方法、技术、药品等方面的转化,还应拓展为生命科学新思维、新理念、新理论、新观点等方面的转化,这样才能使转化医学从"量"的转化发展到"质"的转化,使之与新的科技革命的思潮相顺应。
[1] Asslaber M,Zatloukal K.Biobanks:transnational,European and global networks[J].Brief Funct Genomic Prmeomic,2007,6:193-201.
[2] Sgaier SK,Jha P,Mony P,et al.Biohank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Needs and Feasibility[J].Science,2007,318:1074-1075.
[3] Alice Park.Biobanks[J].Time,2009,173,11.
[4] Horell SR,Coffin CM,Holden JA,et al.Preservation of RhlA for functional genomic studies:a muhidisciplinary tumor bank protocol[J].Mod Pathol,2001,14(2):116-128.
[5] Diaz JI,Cazares LH,Semmes OJ.Tissue sample collection for proteomics analysis[J].Methods Mol Biol,2007,428(1):43-54.
[6] Meermans G,Roos J,Hofkens L,et al.Bone banking in a community hospital[J].Acta Orthop Belg,2007,73(6):754-759.
[7]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生物样本库标准(试行)[J]. 中国医药生物技术,2011,6(1):71.
[8] 张小燕.中国医药生物技术协会组织生物样本库分会成立大会会议纪要[J].中国医药生物技术,2010,5(1):76.
[9] Katz AM.The"Gap"between bench and beside:widening or narrowing[J].Cardiac Failure,2008,14(2):91-94.
[10] Zerhouni EA.NIH goadman[J].Science,2003,302(5642):63-72.
[11] Choi DW.Bench to bedside:the glutamate connection[J].Science,1992,258(5080):241-243.
[12] Geller RB,Karl JE.Adult acute leukemia:a need for continued translational research[J].Blood,1994,84(11):3980-3981.
[13] Geraghty JA.Denomatous polyposis coli and translational medicine[J].Lancet,1996,348(9025):422.
[14] 郜恒骏,朱明华.重视消化系疾病组织生物标准化样本库的建立[J].中华消化杂志,2008,28(2):73-74.
[15] 王青,林爱芬,周文君.我院人体组织生物样本库的建立和应用[J].中华医院管理杂志,2010,26(2):150-153.
[16] 何传启.第六次科技革命的战略机遇[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