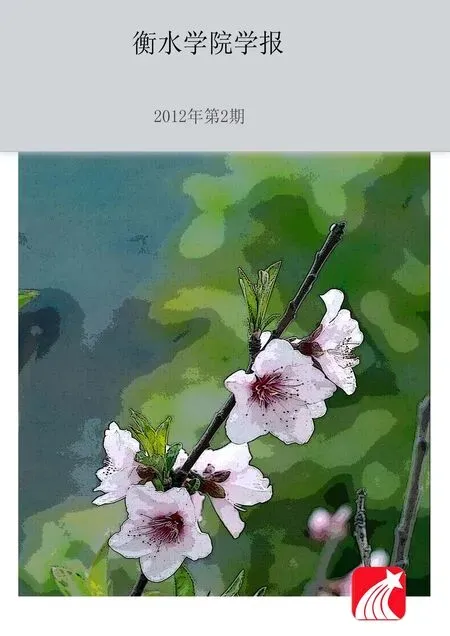先秦文学史研究的新贡献——《先秦文学编年史》简评
边家珍
先秦文学史研究的新贡献——《先秦文学编年史》简评
边家珍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
目前通行的几种文学史的先秦部分及几种先秦文学断代史,内容安排上大都分为5部分,即原始歌谣与上古神话、《诗经》、历史散文、诸子散文和《楚辞》。相对于秦汉以后的文学史的论述,先秦文学史较为缺乏历史发展进程的展现,较为缺乏对具体的、不同时段文学的历史与学术文化背景的叙述。陆侃如先生曾说:“文学史的目的,在鉴古以知今。要达到这目的,我们不仅要明白文学史上的‘然’,更要知道‘所以然’。如以树木为喻,‘然’好比表面上的青枝绿叶,‘所以然’好比地底下的盘根错节。我们必须掘开泥土,方能洞悉底蕴。”由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赵逵夫先生主编,赵逵夫、贾海生、韩高年、裴登峰诸先生共同撰稿的《先秦文学编年史》(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可以说做到了陆侃如先生所说的“掘开泥土”的工作,全书在编年体的基本架构中,以中国传统的编年体为主要形式,编排、考订了自夏代至秦朝两千年间文学家的生平事迹、著作篇目、著作年代及相关史实等等,建构了富于民族特色的先秦文学编年史体系,对先秦时代包括佚诗和歌、诵、谣、谚、箴、铭、颂、赞以及有文学性的散文作品进行了全面清理,对汉代以来尤其是清代以来的有关研究成果加以总结、分析、比较,确定或大体上推断先秦文学作品的真伪、时代、作者等问题,使得先秦时期大量繁杂纷乱的文学史料有了一个清楚的线索与条理,为先秦文学史研究的进一步展开及理论研究上的突破提供了很好的基础。
《先秦文学编年史》为读者提供了相对全面和立体的先秦文学发展历史,有助于从时间的“纵轴”与空间的“横轴”上了解、把握某个特定时段的文学创作情况及整体风貌。例如,我们欲了解周公摄政时期的诗歌创作,阅览《先秦文学编年史》相关条目后便可对周公摄政这一特定历史背景下的诗作有了一个“历时性”的总体了解:
前1041年 周成王二年周公摄政二年
周公作《微子之命》,封微子于宋。
管叔、蔡叔作乱,周公兴兵东征。周公忧王业之将坏,故陈《七月》以明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既诛管、蔡,作《鸱鸮》以明其志。
前1040年 周成王三年周公摄政三年
周公东征期间得命禾,陈成王之命而作《嘉禾》。
周公东征凯还,劳归士而作《东山》之诗。东征士卒喜得生还,有人作《破斧》之诗。
前1039年 周成王四年周公摄政四年
周公东征归来,豳人述其进退为难之事而作《狼跋》。
周公作《康诰》、《酒诰》、《梓材》,徙封康叔于卫。
周公作《唐诰》,封唐叔于夏虚。
蔡叔既没,周公作《蔡仲之命》,复封其子蔡仲以奉其祀。
前1037年 周成王六年周公摄政六年
周公制礼作乐,作《周礼》、《誓命》、《大武》。
周公尊后稷以配天而作《生民》。
前1036年 周成王七年周公摄政七年
三月十四日,周公在洛邑南郊祭天,歌奏《昊天有成命》之诗;以后稷配天,歌奏《思文》;以先王配享,歌奏《天作》。
周公在明堂祭祀文王以配上帝,歌奏《我将》之诗。
周公在文王庙中祭文王,歌奏《清庙》、《维天之命》和《维清》之诗;在武王庙中祭武王,歌奏《时迈》和《般》之诗。
三月二十一日,周公安抚庶殷众士,作《多士》。
同时,从“共时性”的角度,我们还可以藉此了解同是在周公摄政时期产生了哪些重要的文章,以便于与此期的诗歌进行多方面的比较参照,如孟子所谓“知人论世”者,从而有助于认识上的开拓与深化。
著者在书中对不少文学作品的真伪、作者问题进行了细致而令人信服的考证。如《晏子春秋》一书,唐代以降多视为伪书,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前言》考定为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编成。银雀山出土汉代初年的简本《晏子春秋》后,伪书说不攻自破,但吴则虞说仍然影响很大。著者在借鉴高亨《〈晏子春秋〉的写作时代》、董治安《说〈晏子春秋〉》、谭家健《〈晏子春秋〉简论——兼评〈晏子春秋集释·前言〉》等文的基础上,又提出新的证据,认为《晏子春秋》一书是战国中期齐人淳于髡在齐威王、宣王朝搜集晏婴的佚著、言辞、事迹及传说故事编成(见《先秦文学编年史》下册,第1105-1109页)。
在《先秦文学编年史》中,著者十分注意对历代出土的先秦文献、特别是对近几十年出土的金、甲、简、帛文献中与先秦文学相关的文献的搜集、考释,将它们按时代的顺序同传世文献一起加以系年,显示出它们在整个先秦文学史料的相对位置和相互关系。同时,著者在考辨一些问题时,除了利用传世典籍外,还十分注意考古文献资料的使用,如对于学界存在的《离骚》为西汉刘安所作的说法,著者就结合考古文献,从3个方面进行了辩驳(见《先秦文学编年史》下册,第1167~1168页),这里笔者略作归纳:其一,1977年阜阳汉简中有《离骚》《涉江》残简,出土器物上有“女(汝)阴侯”铭文及漆器铭文纪年等资料,墓主应为西汉第二代汝阴侯夏侯灶,其人卒于文帝十五年(前165年)。这样,阜阳汉简《离骚》作年的下限不得晚于此年。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年)刘安入朝,武帝“使为《离骚传》”,距文帝十五年已有26年。其二,《离骚》“摄提贞于孟陬兮”所用并非夏正,从1942年长沙子弹库战国墓出土帛书可证。帛书所标十二月名,正月为“取”,实即“陬”之省,则“摄提贞于孟陬兮”就是先秦楚人的说法。其三,从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帛画所展示的神话传说内容看,那种认为《离骚》中的神话传说大部分来自《淮南子》等文献的说法亦有不妥。这3点依据考古文献进行的驳论,逻辑性强,颇有说服力。
著者对于作品系年的不同说法,有比较、有选择,或择善而从,或排众议而立新说,摆出自己的看法。资料充足、根据充分的,给予精确的系年;史料不足的,则提出大体的推定。《先秦文学编年史》中涉及《诗经》篇章作年的地方很多,《诗经》作为一部诗歌总集,不仅作品数量多,而且创作时间跨度大,又因商周存世文献不足的限制,要想做到篇篇准确系年确实很难。尽管有关《诗经》的系年中也不乏启人疑窦的地方,或不无可商之处,但从总体上说大都是合适的,较之明代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对年代的认定显然更具严谨性、科学性。例如,关于《大雅·桑柔》一诗的作年,著者在参考宋儒、清儒及近人诸说的基础上,结合诗篇具体内容加以分析推断,提出此诗“当作于国人逐厉王之后不久,应在当年,诗中尚未反映出共和主政之事,也就是说,当作于厉王三十七年”(见《先秦文学编年史》上册,第334页),反映出著者对史实精细、准确的把握。
在作家交游的考辨方面,著者也下了很大功夫。例如,孟子与“稷下先生”淳于髡有过不少交往,并有关于“礼”“名”“实”“贤人”的论辩。著者指出,从《孟子·告子下》所载孟子与淳于髡的名实之辨的文字中“夫子在三卿之中”一语,可推断是孟子游齐时(齐宣王朝)与淳于髡的辩论无疑(见《先秦文学编年史》下册,第1124页),所言颇有道理。
钱基博先生曾说,文学史“所以见历代文学之动,而通其变,观其会通”,乃因“事”“文”“义”的协调,“设以人体为喻,事譬则史之躯壳耳,必敷之以文而后史有神采焉,树之以义而后史有灵魂焉”。“事”“文”“义”的结合与协调,无疑也是《先秦文学编年史》的编著者所力求达到的目标,长达6万字的《前言》以及上、中、下各册之末的《西周文学综论》《春秋文学综论》和《秦代文学综论》就是证明,这些文字重视理论总结,体现出著者对先秦文学的认识,时见新意。笔者这里想再提一点不尽成熟的想法或者说建议,比如说前述周公东征时期的诗文创作,可否视为更小一些的“单元”,在此单元之后略仿《史记》《汉书》论赞之体,加上编者案语式的文字,作简明扼要的分析与归纳。其它可视为“单元”者仿此,如宣王中兴时、“二王并立”时的诗文创作亦相对比较集中,皆可加总结性案语。如此,便可起到红线穿珠般的贯通作用,有助于在编年体中更好地融贯文学史之义。当然,这关涉到全书的体例问题,整体做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这里提出来仅供参考。另外,如果著者能在书末附一个按拼音顺序编排的人名、篇名《索引》,当更有利于此书的查阅与利用。
众所周知,史实的考订工作是相当不易的,需要付出艰苦的劳动,有时写在书上仅仅十几个字、几十个字,但其结论的背后往往凝聚着著者大量的心血。由于时代久远、史料阙如等因素,可以想见,《先秦文学编年史》的编撰会遇到许多困难,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需要耐心和细心,需要甘坐冷板凳的精神。赵逵夫先生等殚思竭虑、兢兢业业,历数年而后成书,追求真知的精神令人感佩。笔者相信,不论从著作的内容与编撰的方式方法上,还是从治学精神的感召力上来说,《先秦文学编年史》的出版对于先秦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开展都必将发生积极的影响,起到有力的推动作用。
注释:
①见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序例》,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
②何天行《楚辞作于汉代考》(中华书局1948年版)中即持此说,朱东润《离骚底作者》(载《光明日报》1951年3月31日)一文也认同这一观点。
③明代何楷《诗经世本古义》以时代为次序,对《诗经》的篇目进行了重新编排,上自夏少康之世,下至周敬王之世,分为二十八卷。书中对《诗经》作品的作者、年代的推断多有附会,如《陈风·月出》篇有“舒窈窕兮”“舒忧受兮”之文,即指以为夏徵舒;《硕鼠》一诗,则指以为《左传》之魏寿馀,此类颇不少。
④参见钱基博著、傅道彬点校的《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责任编校:耿春红)
2011-10-10
边家珍(1965-),男,河南杞县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I206.2
A
1673-2065(2012)02-0126-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