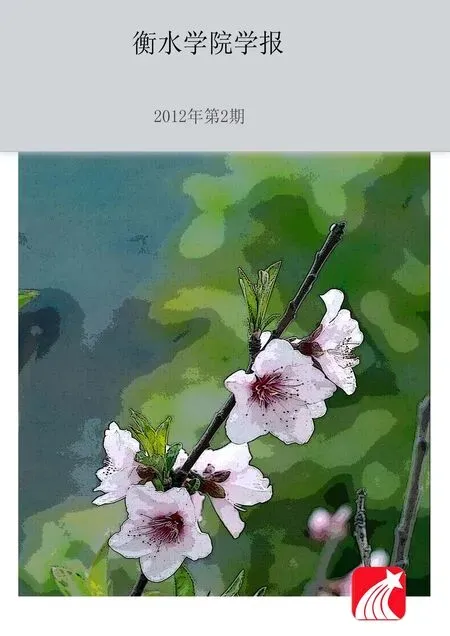贺贻孙对《诗经》抒情主体的彰显
李兆禄
贺贻孙对《诗经》抒情主体的彰显
李兆禄
(滨州学院 学报编辑部,山东 滨州 256603)
明清之际贺贻孙诠释《诗经》重视抒情主体的作用。结合具体作品,贺贻孙从“情”着眼揭示诗人的创作心态与动机;强调主体构思在诗歌创作中的积极作用,突出主体的移情作用,指出不同主体面对相同现象产生、抒发的情感不同;诠释《诗经》中的代拟抒情方式。贺贻孙对文学4要素中主体(作者)的突出与强调,丰富与发展了《诗经》的文学诠释。
贺贻孙;《诗经》;《诗触》;抒情主体;代拟抒情;文学诠释
《诗经》除少数作品的作者自道名姓和创作目的外,绝大多数诗篇作者情况不明。历来学者诠释《诗经》时很少涉及作者,对作者在创作中的作用则更少论及。《毛诗序》往往指出诗人的创作目的、原因,涉及诗人的创作心态,但流于简单和曲意附会,更将“变风”“变雅”视为“国史”所作。这表明,汉儒对抒情主体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还不是很重视。朱熹通过涵咏诗篇,体悟到有些作品的主人公即是作者本人,尤其是描写男女恋情的作品;但在当时的思想意识下,朱熹只能说这类诗是“淫奔者自作”,这种认识束缚着朱熹对创作主体的客观评价。贺贻孙受明代中后期情欲主义思潮的浸染,又长期隐居深山,较少经学包袱,能正确看待、评赏《诗经》抒写的多种情感,对抒情主体在创作中的作用也能予以肯定。当学界纷纷将目光投向因发展了孔子“兴观群怨”说、注重读者在接受《诗经》过程中的能动作用的王船山时,为了解明清之际《诗经》文学诠释全貌,审视梳理与王夫之同时而稍早、彰显《诗经》抒情主体的贺贻孙的文学诠释状况与成就,则显得尤为必要。
贺贻孙对《诗经》抒情主体的彰显体现在揭示诗人创作心态与动机,强调主体的构思作用、突出主体的移情作用及诠释《诗经》的代拟抒情方式等方面。本文拟以贺贻孙的《诗经》学著作《诗触》为参照,论述其对《诗经》抒情主体的彰显。
一、揭示诗人创作动因与情感
“诗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人受内心情感的迫促,发而为诗。贺贻孙深谙此理,洞悉诗人创作心态与动机。《诗序》以为《大雅·桑柔》是“芮伯刺厉王”之诗,贺贻孙诠释芮伯写作此诗时的情感状态云:
召公、凡伯、卫武诸诗,虽同一忠尽,然反覆托喻,尚有望其悔恨之意。芮伯则满腹忧愤,无可抒写,欲哭不能,欲詈不敢,惟有托之咏歌,凄婉缠绵以吐热血、以洒涕泪而已。
周厉王壅塞谏路,残暴荒政,小人当道,再加天降灾祸,致使举国哀恫。面对如此现实,芮伯忧愤满怀,无可发泄,只有借诗以抒怀,宣泄愤懑。从上引文字,可见传统诗论“发愤抒情”“不平则鸣”观念对贺贻孙的影响。正因诗人巨愤在怀,才超越召公、凡伯、卫武讽谏厉王之义,已无“望其悔恨之意”“直谓之刺可也”。再如,旧以为《周南·关雎》是赞美“后妃之德”的诗,至于作者何人,历来说法不一,贺贻孙认为此诗是“宫中之人”被后妃之德深深感染、“满心惊喜爱重”之情无所表达,故作此诗以达之:
为是诗者,不过宫中之人既见后妃,倾心向化,故以“窈窕淑女”反覆咏叹,谓如此有德之人,得之不易,追思未为“君子好逑”之时,即寤寐中安能求而得之?今既得矣,惊喜爱重,无可仿佛,惟有写之“琴瑟”、“钟鼓”而已。
可见,贺贻孙认为,芮伯、“宫中之人”都是因受现实生活的刺激而产生了强烈而难以排遣的情感,“惟有”诗歌才可以宣泄,于是形成创作冲动,将自己的情感形诸歌咏,发为歌诗。
贺贻孙重视情感在《诗经》创作中的作用,还表现在诠释时往往触及诗人的情感世界、内心深处,剖析诗人的精神世界。如诠释《小雅·节南山》作者家父之情云:
七章言天下将乱而无所归也。家父自谓,我驾非无肥牡,其项领可以无所不骋,而遥瞻四方则蹙蹙而无可骋者,盖忧乱之甚,虽以四方之大而常若无以容身者。作者至此,词促情迫,视此身为桎梏,视宇宙为囹圄矣。
《节南山》第七章云:“驾彼四牡,四牡项领。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骋。”诗人乘车四顾,茫然不知所归,并没有直接抒写当时自己的心情。贺贻孙却从诗人自我形象的描绘中,感悟到了悲愤、压抑与苦闷。《小雅·十月之交》末章诗人以自己与他人对比,抒发了对现实的愤愤不平之情,诗中写道:“悠悠我里,亦孔之痗。四方有羡,我独居忧。民莫不逸,我独不敢休。天命不彻,我不敢俲我友自逸。”贺贻孙对诗人心理、情感的剖析尤见深刻:
八章叹己之忧劳以终一篇之意也。章内四“我”字,徙者对居者言之也。此时天下大病矣,宁复有羡者、逸者而曰“四方有羡”、“民莫不逸”者?盖身在忧内,但见他人之乐,如身坐鼎镬者见夏畦挥汗烈日中,辙羡其清凉也,盖伤心至此已极矣。末二句无可奈何自解自慰,不怨之怨,可以深于言怨者也。
以生动的比喻评析“我”忧之深。接着点出“末二句”是伤心之极的“无可奈何自解自慰”之语,把诗人的痛苦与无奈剖析得淋漓尽致。末二句,朱熹诠释云:“此乃天命之不均,吾岂敢不安于所遇而必我友之自逸哉?”认为“我”安于天命;今人蒋立甫则认为表达“我”“要尽力挽回天命”的决心。2人的诠释虽都有一定道理,但皆不及贺贻孙的诠释更能把握、揭示诗人当时那种面对残酷现实无能为力、而又苦苦挣扎的复杂心情。正因如此,贺贻孙进一步诠释曰“不怨之怨,可以深于言怨者也”,换言之,这种写法更能表达诗人对现实的怨愤与批判。或许由于贺贻孙目睹耳闻明朝末期朝政的昏聩与腐朽,因而擅长挖掘同为衰世的周厉王、幽王时期诗人的悲苦之情。《毛诗序》认为《大雅·召旻》是“凡伯刺幽王大坏”的诗,第五章写道:“维昔之富不如时,维今之疚不如兹。彼疏斯粺,胡不自替?职兄斯引。”贺贻孙剖析此章表达的诗人那种绝望中含有希望而实绝望的无聊之情尤为精辟:
盖幽王之世,贤奸倒置,故诗人绝望于王而反致望于小人,不能使君子登朝而但欲使小人退位,明知君子不能去小人而尚冀小人之或避君子。盖无聊之思不必然之词也。
二、突出主体构思在诗歌创作中的能动作用
文学创作,尤其是诗歌创作需要作者虚心静气、全身心地投入,是精神高度集中的活动。贺贻孙以前的文论家对创作时的心态多有论述,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说作者构思时“疏瀹五脏,藻雪精神”,陆机则在《文赋》中说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诗经》作为生动展现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六百年间人们生活习俗、情感思想的艺术作品,内涵丰厚,艺术高超,这自然与诗人的精心构思、辛勤创作分不开,但在贺贻孙以前鲜有人提及。贺贻孙以自身写作的辛酸甘苦,体贴到《诗经》作者创作时的思维与心理。
《大雅·灵台》共三章,首章写庶民主动助文王筑台知识;次章写台建成后庶民游台,此时“鹿适其性,鸟乐其天,鱼忘于水”,写尽物类之乐;三章写文王游台并作乐。全诗写了文王筑台、“庶民攻之”之事,又写了庶民、文王游于灵台之景,还写了文王于辟雍作乐之事,表现了文王与民同乐的融洽和谐之象,形象展示了“民始附”时周族的兴盛与生机。此事此景,是如何被写入诗中、表现周祖兴盛时气象的?孔颖达曰:“其民因所见而乐之,诗人因所闻而纪之。”在孔氏看来,“诗人纪之”只是将其所见所闻原封不动记录下来,没有论述诗人写作时的精神劳动。而贺贻孙注意了诗人写作时的主动性:“此皆乐文王之语,诗人隐括之而成章。”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是“此皆乐文王之语”,一是“诗人隐括之而成章”。分别概括了诗的主旨与主旨何以呈现两个问题。诗中并没有出现“乐”字,但综观诗中之事之景,处处洋溢着“周民乐文王”之意。“周民乐文王”之意是诗人精心组织剪裁素材、提炼加工创作的文学作品呈现出来的(“隐括而成章”)!“‘於论钟鼓’二语换章叠用”即是诗人“隐括”手法之一,通过这一“咏叹不尽之词”的“换章叠用”,读者才得以见“文王之乐未艾,而民之乐其乐又可知也”。
贺贻孙认为《诗经》一些诗篇的“言外之意”“含蓄”之美,是诗人精心构思创作出的审美意味,是诗人刻意创造形成的,如诠释《齐风·猗嗟》云:
此诗若无发首“猗嗟”二字,《偕老》篇若无“云如之何”四字,竟是一篇赞词。然赞叹有余处即是不足处,若曰威仪技艺则既美矣,言其有余则其不足者可以意会也。“展我甥兮”,虽属微词,然不必凿破,凿则呆矣;“以御乱兮”,言外之意亦不必说出。大凡诗人妙处在不可说,其可说者皆非诗也。
《序》以《猗嗟》为“刺鲁庄公”之诗,但诗中并无一语提及庄公,读者只能从个别“微词”如“猗嗟”“展我甥兮”中“意会”寻求其讽刺之意,即诗人之讥刺之意在言外不可说处,而这正是“诗人妙处”,是诗人有意创造而成的讥刺艺术。
明代中后期对《诗经》的文学评点赏析,往往只着重于诗篇的章法、句法与字法而忽视使用这些手法的主体,解《诗》者很少注意诗人在形成诗歌艺术境界中的主导作用。贺贻孙在《诗触》中经常提及诗人对这些手法的选择与运用及其形成的艺术效果。兹举几例以见之:
(《小雅·天保》)篇中九“如”字,前后相叠,祝之不足,又再祝之,出没错综,此诗人用笔之妙也。
(《小雅·瞻彼洛矣》)三章言福禄而不及讲武,错落互见,此作手之妙。
(《大雅·皇矣》)七章凡两举帝,谓文王往复覶缕,妙甚。天无口而谓天无心而怀天无形骸彼此而曰予曰尔,皆诗人点缀之奇也。
贺贻孙重视创作主体的能动作用,还体现在他认识到不同主体面对相同现象产生、抒发的情感不同。中国传统诗论很早即有“感物说”与“移情说”。“感物说”可简单理解为“触景生情”,“移情说”则是把自己的情感投射到事物上面。贺贻孙显然受“移情说”影响更大,诠释《小雅·四月》云:
首三章自伤也。夏则苦暑,秋则苦病,冬则苦风,此三时者本无美恶,但得意者触景皆喜,失意者触景皆悲耳。
造物主把一年分为春夏秋冬四季,并无好此恶彼之意,但征役大夫常年在外跋涉,栉风沐雨,不得回家与家人团聚以享天伦,其心情可想而知。在这种经历、心境下,春夏秋冬,都会令他们产生伤感悲哀之情,即“夏则苦暑,秋则苦病,冬则苦风”。这里,贺贻孙充分突出了诗人抒发情感时的主导性。再如,贺贻孙借诠释《卫风·伯兮》曰:“征役劳苦之情一也,出于君上之口则为悯惜,出于室家之口则为怨思。此诗有怨思而无悯惜……”同是表现征役劳苦之情事,君上所作,体现出对臣下的怜悯与爱惜,而室家由于饱受夫妻离别之苦,创作的诗篇则流露出缕缕凄怨与思念。可见,贺贻孙认为不同抒情主体因身份、经历等不同,面对现象产生的情感也会有很大差异。
三、诠释《诗经》中的代拟抒情方式
《诗经》除第一人称、第二人称、第三人称的抒情方式外,还有一种“代拟”他人抒情的特殊抒情方式。这种“代拟”的抒情方式是《诗经》的一项重要创造,特点在于诗人与抒情主体的“分离”。“代拟”的抒情方式,是我国一种重要的抒情方式,古人诗文集中以“代”字开头的文学作品非常多,这是传统文学的一个特色。《诗经》首开代他人抒情之先河,历代诗人虽效仿《诗经》创作了大量代他人抒情的诗作,但直到贺贻孙,还没有人详细深入地论述《诗经》的这一抒情方式。
贺贻孙指出“代拟”抒情方式的诗篇有《周南·卷耳》《魏风·陟岵》《豳风·东山》《小雅·四牡》《采薇》《杕杜》《小弁》等。为论述方便,现将贺贻孙对上述诗歌有关“代拟”抒情方式的诠释话语摘录如下:
(《卷耳》)此诗不过宫中之人以后妃思念君子之诚曲为摹写……大率房中之乐无所不具,以为君子不在,宫人作此乐章代为抒写,可也;以为宫中原有此乐而宫人奏于后妃思念之时以写忧伤,无不可也。
(《陟岵》)“父曰嗟”以下四句,有蕴结语,有怜爱语,有叮咛语,有慰藉语:低徊宛转,似只代父母作思子诗、代兄作思弟诗而已;绝不说思父母、思兄,较他人所作思父母、思兄语,更为凄凉。
《东山》之诗,周公所以体恤军士而慰劳之者至矣。
(《四牡》)此诗与《鸨羽》篇同意,但《鸨羽》出于行役者之口,则为哀怨;此出于劳使臣之言,则为体恤耳。惟其体恤,故能周知其痛苦而代之言曰“岂不怀归”,又曰“王事靡盬”,忠孝备、恩义兼矣。……“翩翩者鵻”三句,代为伤悲之语。……贤者所忧,人君能忧其所忧,则其感之也至矣。……五章……代言岂不思归、作歌来告,欲使君上知衔命之臣有此苦情耳。……盖劳使臣者逆探其情而为之辞云尔。
《采薇》、《杕杜》诸篇所以悯劳臣者,至矣。又从为之念其室家、计其归期,若是其周也。
《杕杜》之劳还也,但述其未至之思而已。盖举人情之最笃至者为体悉也。使此诗出于室家所自作,则与《雄雉》、《君子于役》诸篇同一哀怨矣。惟下之人不言而上之人曲尽其情代为言之,彼见九重之上不独悯我勤劳,且能念我家室,即令我家室自陈其痛苦不过如是恺切也。夫是以感激奋励乐为之死而不辞矣。
贺贻孙对这几首诗的诠释都突出了诗人代抒情主体言说其情这一特点,如诠释《卷耳》,强调的是“宫人”对后妃思念之情的“代为抒写”,凸现了作者与抒情主体的分离。从以上几段引文,可以发现贺贻孙对《诗经》“代拟”抒情方式有以下3点认识:其一,《诗经》中的代拟抒情方式有局部代拟和整篇代拟两种。前者如《陟岵》,整篇是自抒在外思亲之情,但每章自第三句或代父、或代母、或代兄抒其思己之情,是局部代拟。其他都是整篇代拟。其二,贺贻孙认识到代拟抒情方式的艺术效果和感染作用,如评《陟岵》,“绝不说思父母、思兄”,但是“较他人所作思父母、思兄语,更为凄凉”;“还役”看到“九重之上”“不独悯我勤劳,且能念我家室”则“感激奋励乐为之死而不辞矣”。虽不免过誉,但此类诗篇的激励作用还是应该肯定的。其三,贺贻孙认为,《诗经》代拟抒情之诗达到很高艺术水平的原因有二:一是诗人做到了“逆探其情”“周知其痛苦”,即真正体会了解、全面深刻把握抒情主体的情感;二是“曲为摹写”“曲尽其情”,即通过各种艺术手法描摹抒情主体的复杂情感。
对《诗经》代拟抒情方式,《毛诗序》《毛诗正义》都有所阐释,贺贻孙正是继承前代的成果又推陈出新,真正做出了《诗经》代拟抒情方式的文学诠释。如《毛诗序》与《毛诗正义》对《四牡》的诠释:
《四牡》,劳使臣之来也。有功而见知则说矣。……
作《四牡》诗者,谓文王为西伯之时,令其臣以王事出使于其所职之国,事毕来归而王劳来之也。
《毛诗序》极为简单,没有提及代拟抒情的作者,也没有论述所抒之情。《毛诗正义》则认为是“第三人”叙述文王“劳来之”之事,迂回难明。而贺贻孙结合诗文,抓住诗中所写之情,诠释较为合理。贺贻孙顺承《毛诗序》一派诠释《诗经》“代拟”抒情方式,并取得一定成绩。但应注意一点,这些诗篇在今天看来,与其说是“代拟”,毋宁说是诗人“自抒其情”更为合理。
四、结论
现代接受理论认为,作者、世界、作品与读者是文学4个既互相独立又互相联系的基本要素。贺贻孙因注意了抒情主体即作者的存在和主导作用,诠释《诗经》往往能从细微处体味诗中蕴含的丰富情感,做出合乎《诗经》文学身份的解读。贺贻孙与其同时而稍晚、突出读者能动作用的王夫之的《诗经》文学诠释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对《诗经》学的发展作出了一定贡献,应受到学界的充分重视。
[1] 费振刚,叶爱民.贺贻孙《诗触》研究[G]//中国诗经学会.第二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467.
[2] 孔颖达.毛诗正义[M]//十三经注疏.阮元,校刻.北京:中华书局,1980.
[3] 贺贻孙.诗触[M]//续修四库全书:6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4] 朱熹.诗集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91.
[5] 蒋立甫.诗经选注[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1.
[6] 潘啸龙.《诗经》抒情人称研究[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2):140-149.
Stress on Lyric Subject inIllustrated by He Yisun
LI Zhao-lu
(Editorial Department, Binzhou University, Binzhou, Shandong 256603, China)
He Yisun, who lived during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llustrated that the effect of lyric subject was valued in. Combined with concrete works, He Yisun revealed the poets’ creative mind and motivation from the aspect of feeling. He emphasized the positive effect as well as the empathy effect of lyric subject in poem creation. And he also pointed that, to the same phenomenon, different lyric subjects express different feelings. He Yisun illustratedlyric way inThe stress on lyric subject-the author of the four key elements of literature by He Yisun enriched and developed the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of.
He Yisun;;; lyric subject; lyrical of “Dai Ni”; literary interpretation
(责任编校:耿春红 英文校对:杨 敏)
I222.2
A
1673-2065(2012)02-0029-04
2011-07-10
滨州学院课题资助项目“清代《诗经》文学诠释史论”阶段性成果(2009Y09)
李兆禄(1971-),男,山东惠民人,滨州学院学报编辑部副教授,文学博士,黄河三角洲文化研究所研究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