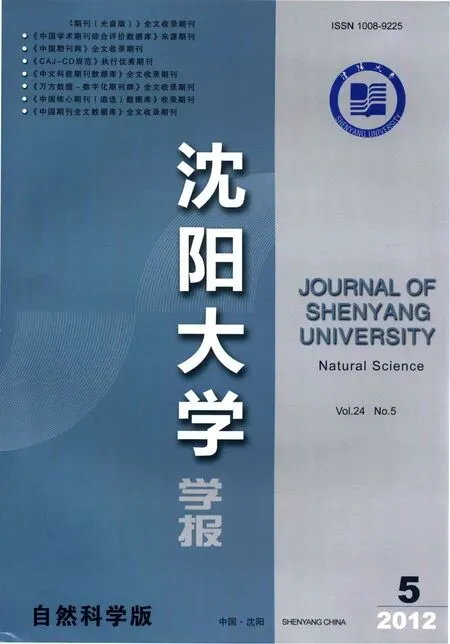论中国哲学中“进化”的宇宙观及其影响
韩立坤
(沈阳大学 政法学院,辽宁 沈阳 110044)
鸦片战争前后,虽有西方科学、文化、宗教的渗透,洋务运动时期也明确欣赏与认同西方器物文化,但儒家哲学中的宇宙观、人生观、认识论、历史观和价值观依然支配着民众的道德选择和价值取向,就连表面上“大讲西学”的维新先驱王韬、郑观应等人,在根本的信仰上还是认同儒家之道,例如,王韬认为“夫孔之道,人道也,人类不尽,其道不变[1]”。中国传统社会正统儒家思想的稳定性和顽固性如果不因外力的打破,是否会在一个封闭的国家中永远恒久而无所改变,正如梁漱溟曾认为,如果没有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文化自身不会发展出科学一样,都是我们无法回答的问题。但事实上,严复之后,儒家天道观和宇宙观的稳定性和永久性轻易地被外来的文化动摇了,而其中进化论所带来的对宇宙大化流行的根本特征的新“描述”更是不费吹灰之力就取代了统治千年的儒家宇宙观。应该说,无论持何种立场的学者,都无法否认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思想界所思考、争论的各种问题中,“制度”之“变”、“思想”之“变”、“社会”之“变”、“方法”之“变”都或隐或现地相互贯穿。因此,进化论除了带给中国作为科学知识的“进化论”、作为社会组织发展规律的“社会进化论”之外,在哲学层面和思维方式上也带来了巨大影响和变革,因此更是一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普遍 “宇宙观”。从此意义上说,在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大背景下,以进化理论为核心,考察与反思近代以来进化思想在中国的接纳、发展、流变在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中的影响,就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需要说明的是,与其他在中国文化或哲学的某一领域内代表着“先进性”“现代性”“合理性”的西学最显著的不同在于,进化论作为一种外来思想理论,明确而客观地在中国表现为一种“全能式”的“普遍有效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为近现代中国从“前现代”到“现代”社会的转型,提供了可以解释一切社会和文化的问题,消解一切不同思维方式、思想主张间矛盾的理论模型。正是从“进化论”这种形而上学的普遍“合理性”以及表现出的巨大指导能力着眼,在近现代中国将“进化”上升为形上学的“主义”也就更能突出此理论的系统性和普遍意义。并且,这种从科学研究中诞生的“推断”型的“进化论”正如自身理论突出的“适应”“进化”等特征一样,也在进入中国后“适应”着急速变化的社会环境和理论需求而“进化”着“进化论”自身。
一、“进化”思想从科学向形而上学的转化
就理论内涵而言,诞生在西方的进化论,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复合体”,其本身被西方思想家加以复杂的解读。与其在西方的特征类似,“进化论”从“生物进化主义”到“社会进化主义”的理论演变或“变异”的过程,同时就是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过程。那么,要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进化主义对中国近现代社会变革和文化发展的影响,就必须回到进化主义本身。进化论本是达尔文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在生物研究领域提出的理论。在其名著《物种起源》中提出包括人类在内的动物 “本能”“生理结构”“情感”“心智”甚至道德都会经历一个长期的进化过程。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即《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的作者赫胥黎,就是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坚定支持者。而斯宾塞除了将达尔文的理论以“进化”(英语中有“进步发展”之意)一词来概括和界定外,还将其本属于生物领域的进化论推广到社会领域,从而发起“社会达尔文主义”。由此,达尔文的进化论以及其衍生的理论给人类学、哲学和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观都带来了更加巨大的影响。事实上,西方的进化理论在中国同样引起重大的反响。这是因为,即便是在持各种相互排斥甚至是矛盾哲学主张的思想家那里,都在宇宙观上或多或少地表现出宇宙万物进化发展的观念。实际上,几乎所有的近现代思想家和哲学家,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胡适、李大钊、陈独秀、梁漱溟、朱谦之、熊十力、张东荪、金岳霖、张岱年等,都对宇宙进化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进行过研究和论述。这样,作为自然科学的理论形式不但延伸到人文社会科学,更经过中国哲学家们的提炼和创造而变成具有科学形态的、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哲学理论。可以说,“作为科学知识的‘进化’学说,逐渐‘主要’成为一种(影响至大的一种)普遍的宇宙观、世界观、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意义上的进化主义。”[2]344事实上,从维新派、革命派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进化主义不但逐渐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发展观、价值观和社会秩序观,还与思想理论尤其是哲学变革息息相关。在哲学形而上学的层面,进化主义实际上已转变为最具普遍性、最无争议的宇宙观或本体论。总的来说,自然科学的进化论落实在思想界转变为“进化主义”,这就体现了真正的在形而上学或本体论的高度对这种外来的变动宇宙观的融合和新释,而这进一步影响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基本特征、问题意识、理论取向等方面。
从思想史和哲学史的视角来看,“进化主义”作为哲学本体论和世界观,在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形态正是与现实社会不同阶段急需解决的课题与任务而同步的。早期进化主义随着科学和技术一起被传教士传播进来;严复亲身感受到英国的富庶和中国的贫困,急需“能为中国寻找出路的世界观”,因此,他将“天演”作为进化主义的指示词,这就向中国社会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普遍宇宙观意义上的社会进步发展法则;在维新变法时期,有康有为的“变法”“富强之道”“三世进化的历史图式”和梁启超提倡的“天演之公例”“合群”“强权主义”以及“乐观进步主义”;变法后激进革命派章太炎、孙中山等仍将“进化主义”作为普遍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虽然其也依然体现为“进步”“发展”等基本内涵,但已经被激进的知识分子添加了许多更加动态的因素,如“革命”“激进”“顿化”“剧烈”等新内容,从而与进化论本初意义上的含义明显不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进化主义”在理论上更加具有普遍世界观和宇宙观的意义。“进化主义弥漫在‘五四’不同人物和许多思潮之中,构成了一种普遍的‘论式’,甚至比‘科学和民主’还更有市场。”[2]202;而从20世纪20年代中国哲学家自觉融合中西方哲学建立体系化的哲学开始,进化主义在哲学形而上学的高度继续发挥重要的基础性作用。无论是以梁漱溟、朱谦之、熊十力为代表的生命主义哲学,还是以张东荪、金岳霖、张岱年为代表的实在论哲学,都从宇宙发展的层面采用了进化主义的某些理论,主张一种不断发展、变化的宇宙本质。
二、作为“公理”的进化主义
考察进化主义在近现代的发展,除了从思想史的视角梳理进化主义理论在思想家著作中的解读和运用之外,还可以从进化主义理论本身涉及的哲学内涵进行审视。通常而言,一种文化系统或社会系统,有什么样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历史发展观。后者在哲学层面逻辑的从前者派生出来。中国文化中的宇宙观主流就是儒家传统的宇宙观。儒家思想最初认为,社会历史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例如,孔子认为殷礼是以夏礼为基础有所损益,周礼以殷礼为基础有所损益,即肯定历史现实是有所变动的。但是具体的历史虽是变化的,其却总是依照一个一般的规律。发展到孟子那里,认为“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滕文公下》),即主张历史发展的兴衰每隔一个阶段就会循环往复。而由此得到的社会发展观或历史发展观,就是一种“循环论”的基本模式。从另一方面说,传统的宇宙观倾向于天不变道亦不变,宇宙的本质定义和基本结构是永恒不变的,甚至价值系统和验证的标准也是永恒不变的。值得注意的是,如果仍然坚守这种传统的天道观,那么尽管现实社会接近衰败,但形而上的宇宙之道并没有因为统治者的无能而改变,并且,以此在永恒不变的宇宙之道观照下,未来可预计时间内一定会重新出现美好的社会。事实上,近代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已经明确反对复古主义与循环论的历史观[3],认为社会“日进而日盛”[4],严复认为“世道必进,后胜于今”[5]。胡适在考察进化论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时,曾指出了其对中国文化中天道永恒认识习惯的瓦解。他曾以荀子的“古今一度也,类不悖,虽久同理(《非相》)”为例,并引杨倞注说“类,种类,谓若牛马也。”“言种类不乖悖,虽久而理同。今之牛马与古不殊,何至于人而独异哉”等言论来论证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本质永恒等特点。胡适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让人知道没有永久不变的真理,“方才可以起一种知识上的责任心。”[6]
事实上,进化主义在近现代中国所起的作用远远不止于此。应该说,进化主义自从被知识分子接纳的那一天起,就是一种不简单的认识观、历史观、社会发展观,而是体现为科学性、进步性、价值性的适用宇宙万物的宇宙观或形而上学。具体来看,与古代社会文化中永恒的天道观或循环历史观相比,坚信“进化主义”的思想家认为,社会的“进化”“进步”是直线的、全面的、不可逆的过程。并且,中国的进化主义者相对于“自然进化”而言,更加注重“人为进化”。在一些哲学家那里,宇宙本体论已经不再是静寂不动、永恒不变的与人无涉的存在,甚至,在进化主义影响下,宇宙本体论不但是变化发展的,更是在人类自身积极努力参与和推动下的变化发展。在中国的进化主义者那里,既然宇宙本质就在于不断的前进、发展、变化日新,那么在中国社会的急迫转型课题要求下,等待、顺应这种变化的洪流就不如人们积极创造、改变社会环境,配合甚至推动这种普遍客观的宇宙观。因此,客观环境主导的进化就变成以主观意志、心力、自我创造为动力的进化。这种巨大的转变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虽然在19世纪90年代以前,直接以生存竞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和进步为主要特质的进化主义或社会达尔文主义并未成为一种新的世界观或主流意识形态。但一个急需解决衰弱现实的巨大力量足以让原本自然科学意义上的进化论发生转向,即进化主义转向了作为“科学性”的和“进步性”的哲学理论和宇宙观。这种转变甚至在进化主义传入的早期就体现出来了,“近代早期的历史进步或进化主义,其突出表现就是用带有‘价值’和‘理想’的尺度去划分历史阶段和判断历史变迁,并用具有历史趋势、历史必然性以为的‘运会’去强调历史的‘不可逆性’。”[2]41这样,作为“思想观念和世界观”意义上以及“整个社会革新”意义上的进化主义在中国的登场,以及宇宙观的进化主义在“公理”层面的“规范性”所挟带的绝对优势,就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客观宇宙和社会发展本质的理解。这也是进化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根本含义和最重要的价值。而进化主义这种特殊的“规范性”得以实现的前提,则应归为进化主义与其他西学理论相比的“科学性”和“进步性”。
鸦片战争后的近代中国,在实用性和功利性的强烈取向下,在自然科学挟带着技术与工具层面巨大可见成就的威势面前,西方的“科学”俨然已经成为最有效用和说服力的新价值代表者。我们可以暂且不论科学技术的现实效用,从理论层面,在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著作中,已经在形而上学理论中比附和糅合了自然科学的基本概念,从而增强论证的重要性;而后期以“科学”面目出现的种种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西学思想则更深入地融入到思想家的创作中。如,新文化运动前后部分思想家自觉追求“科学”的哲学。但是,即便表现为科学性和进步性,无论是实用主义、生命哲学、分析哲学、还是新实在论,等等,从在中国的受众及影响来看,都无法跟进化主义相比。这是因为,进化主义所提供的宇宙“变化”“发展”以及“完善”的种种特质完全是自明性的,可以作为最基础性的本体设定为任何其他理论学派所利用。正是从理论普世性的“主义”立场,“进化”才上升为形而上学的高度,具有“公理性”或基础性的特征,在近现代哲学史和思想史、政治思想史上发挥作用。
[1]王韬.弢园文录外编[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10.
[2]王中江.进化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一个新的全能式世界观[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3]祝小楠.论康有为的法国大革命观[J].沈阳大学学报,2008(4):94-97.
[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9:72.
[5]王栻.严复集:第5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1360.
[6]欧阳哲生.胡适论哲学[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