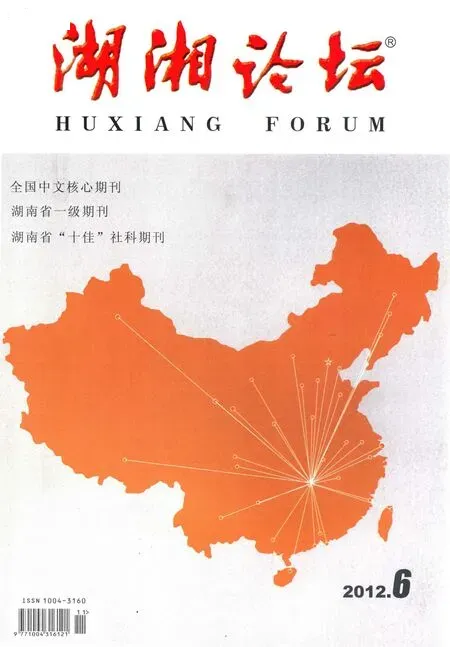自恨空漂泊,无由见老成
——论周紫芝的辞赋创作
刘培
(山东大学,山东济南250100)
自恨空漂泊,无由见老成
——论周紫芝的辞赋创作
刘培
(山东大学,山东济南250100)
周紫芝的辞赋清晰地展示了两宋之际文风由深刻沉郁向平易而富于生活气息的转向。而这种转变的重要原因是朝廷在靖康之难后没有能积极团结朝野各种力量以形成同仇敌忾的氛围,而是在对金国的政策上包藏私心,态度暧昧,尤其是秦桧专国时候的高度专制,把文人朝政强行推出政治之外,推向求田问舍和享受生活。周辞赋中所表现的由沉郁愤懑到空幻失落再到随俗沉浮的转变,正是那个时代文人心路的一个缩影。
周紫芝;辞赋;两宋之际;专制;靖康之耻
周紫芝字少隐,宣城人,生于元丰五年(1082),卒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是两宋之际重要的文学家之一,他的辞赋创作取得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且其创作的各个时期既体现了个人的人生经历和艺术追求,又展示了那个时期士风文风的一些重要特征,思想内容和艺术创作均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周紫芝继承了北宋末期辞赋的悲凉格调和高自标识的精神,又展示了南宋初期文学所具有的追求平淡自然和淡然忘世的特点。从深于忧患到忘怀天下,周的心路历程是对两宋之交文人思想转变的形象诠释。周紫芝现存以赋名篇的作品15篇,他的散体文创作深染辞赋的痕迹,其《祭野鬼文》、《祭陶靖节先生文》、《吊英布庙文》、《告巨木文》、《代王无功祭杜康文》等也是杂体赋。
一、高自标识与失路徘徊:周紫芝早年的辞赋创作
有学者把周紫芝称为“隐逸诗人”,其实他是个进取心很强的人,只不过他把仕途上的不得意通过张扬隐逸情怀来缓释罢了。周在科场一直不顺利,直到南宋绍兴十二年(1142)六十岁时才解褐步入仕途。此后由于得到秦桧的赏识,官场颇为通达,他也因此对秦桧感恩戴德,写了不少阿谀奉承秦的主旋律文章。周对秦桧的谀美被看做是他人生的一大污点,其实,在秦桧专国的高压态势之下,士大夫鲜有能免之者,在秦桧当国的那个时期,一个不被看作“另类”甚至“发动”的文人,就是要紧跟形势,与时俱进,和高宗以及秦桧等政治中心保持一致。可以说,高宗时期的专制政治,对当时士风文风的走向具有决定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仅仅因此而苛责周紫芝。
早年的周紫芝颇具诗人气质,他曾说:“昔余为童子,未冠入乡校,方学科举文。文成,掌教者善之,于是长者稍从而称其能焉。余曰:‘是足以得名,不足以名世也。’乃喜诵前人之文与其诗,往往为之废业,而前日之称其能者,悉咍之不齿也。一日,先君戏为客言是子肩有诗骨在法当穷而又好诗穷固必矣。’自是好之不衰,如人饮酒,日甚一日,然卒亦不能工也。中年取少时所作而诵之,悉皆弃去,可呕也;老来取中年所作而诵之,则又皆弃去,可笑也。”[1]P162,169或许是由于这个原因,早年的他对文坛动向和政治氛围非常敏感。徽宗时期国势日蹙的状况和文坛盛行的悲凉衰飒之气在他的赋作中留下了清晰的印记。他早期的辞赋如《哀湘累赋》、《思隐赋》、《吊双庙赋》、《感士不遇赋》等颇多悲伤感慨之词。
《哀湘累赋》从激愤的情绪来看和他早年的情感基调一致,当是他年轻时候的作品。湘累,指屈原,这是扬雄的《反离骚》对屈原的称呼。不因判罪而死叫“累”,屈原自投汩罗江,所以称他为“湘累”。屈原是当时文人们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因之楚辞的各种编篡研究的集子产生了不少。《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记录有周紫芝的《楚辞赘说》四卷,还说他尝为《哀湘累赋》,以反贾谊、扬雄之说;又为此书,颇有发明。由此可以看出,他的《楚辞赘说》和这篇赋的思想是一致的,都针对汉代人对屈原狷介过激扬主上之恶的湛身行为的指责予以反驳,张扬屈原忠心耿耿的一面。其实在当时,屈原作为“忠”的化身已经被请上神坛。周紫芝对时代风尚的关注由此可见一斑。对屈原的尊崇正反映了徽宗以来读书人对朝廷的疏离,有识之士企图以此来扭转世风,也因为此,当时表现屈原忠心精神的作品往往浸染着一种深沉的悲凉之气。周的这篇赋也是这样,作品主要表现扣天阍请命而为鬼蜮魍魉所阻的景象,这正是北宋末期政治生活的形象写照。可见,当时的“屈原热”与徽宗的昏聩和朝政的昏暗有着密切的关联。赋中是这样为屈原辩护的:“嗟夫人之何心兮,谓累死之弗祥。盍远引以避地兮,岂兹国之焉良。视怀禄以偷生兮,较一死而孰良?彼谗邪之并植兮,势溷溷其日昌。顾若人之高介兮,亦何羞乎彼臧。纵有目之不明兮,岂鸾鷟之同行。倘中心之不懵兮,宁不辨乎羶香。曾椒兰之不垢兮,亦灵修之可伤。虽摈斥而不用兮,亘千古而益光。”作者避开了儒家出处行藏的古训,而是强调了忧患天下的使命感和保持高尚人格的重要性。这正是当时人们解读屈原的着眼点,它突破了君臣之道的种种礼义上的纠结,重在弘扬屈原精神在当时政治生活中的意义
《吊双庙词》是周紫芝在政和七年(1117)年三十六岁时去京师参加科考路过南京应天府(今商丘)谒双庙时写下的一篇赋作。张巡许远在宋代颇受人们关注,如苏颂的律诗《和次中双庙感事》、祭文《祭双庙祈雨》,刘敞的《双庙记》,梅尧臣的《谒双庙以下湖州后诗》,刘摰的《代留守张方平留阏伯微子张许三庙奏》、律诗《次韵次中题双庙》,孔武仲的《双庙赋》、王象之的《张廵许远双庙辩》,等等。周的这篇赋同样是在旌表张、许的气节,所可注意者,在于他指出安史之乱祸出“中壼”:“繄唐祚之中微兮,肆虺枭之旁午。产奇祸于中壸兮,滋乱离于下土。痛渔阳之肇乱兮,怆播迁之失所。倏电击而雷奔兮,巻百城而莫御。纷披靡而俱下兮,等列侯以群竖。独睢阳之二老兮,守危堞而不去。”主昏臣奸,政治腐败,国家外强中干,一旦乱作,貌似强大的王朝如蚁穴溃堤,瞬间分崩。北宋末期的政治形态正如安史之乱前夜的玄宗朝一样,暴风雨前的宁静让有识之士忧心忡忡战战兢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篇赋的结尾,通过阴郁的气氛描写,暗示了王朝末日将临和作者深深的担忧:“迄百年其如梦兮,悼英魂而蹲舞。予西征而过宋兮,撼扊扅而扣户。怅烟火之依微兮,复巫觋之弗驭。号悲风于木末兮,盼霰雪其欲雨。斞斗酒以一酹兮,慰孤怀之迟暮。倘神灵之犹在兮,尚复聆听于斯语”。
当然,最使周紫芝感到苦闷的是仕途不售。像当时的许多文人一样,周紫芝的自我期许很高,因此,科场的挫折给他心理造成的伤害也就越大,越深刻。在《感士不遇后赋》中,他既表达了对命途多蹇的激愤又通过理性的超越来缓释个人的痛苦。赋曰:
士固有抱负伟器而陆沉于厄穷无聊者,十常八九。余尝较成败于适然,齐死生于顷久。然后知达者未必以智而得,穷者未必以愚而取也。故回蚤死而跖寿,雄终穷而莽达。何侯万钱而陈平糠籺,季子六印而原思百结。阳货当国而孔子环辙,万石朱轓而冯唐白发。历方册之所载,虽不可以数计,而周知大抵皆贤智之不遇,例颠沛于覆车之辙也。
他历数古往今来之数奇之人,折射出内心的压抑和对自己的才能高度期许。然而,命运无情,百无聊赖中他只能自己设法排遣内心的不快
彼殊不知皇天之平分,较锱铢于反覆。似赋予之殊偏,究所用而皆足。鹤长不足断,凫短不可续。鸟黑不日黔,鹄白不日浴。鹪鹩巢林不过一枝,偃鼠欲河期在满腹。盖窘于寿者达于仁,薄于利者富于德。贵不在其身者,其裔必昌;志不施于时者,其名必馥。安蓬枢者不应有愧于华厦,穿败裘者不必多羡于苍玉。昔人有牧羊而寝者,因羊而念马,因马而念车,因车而念盖。遂梦曲盖鼓吹,身为王公。昼松风之聒寝,忽惊悟而无踪。付浮生于梦境,倏万化之扫空。亮无往而不遇,靡有困而不通。倘领会于斯意,听造化之攸终。
在立功无望之后,他寄希望于立德、立言来找回自己的自信和尊严,甚至通过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把前途交给命运等思想来抚平内心的苦闷。这段自我排遣之词,是对董仲舒、司马迁等以来这种题材的赋作的超越。
周紫芝辞赋中的悲凉情绪,既是末世气氛在其心灵的投射,更是他命途多舛的真实反映。由于他的人生经历没有触及到政坛的脉搏,因之,他的文学创作对民生苦难的关注不充分,尤其是对徽宗朝的乱象在其作品中没有直接的反映,即使是金人南渡,他逃入山中避难以及家乡遭金人铁骑蹂躏这样的人生经历,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表现,可以说,早年的周,是一个悲哀落魄的局外人。他的《新城赋》是为褒扬吕好问守宣城时修缮城防而作。周的家乡宣城在金人南下时深受兵燹,他也因此流落山中避敌。但是这些独特的人生体验在这篇赋中并没有得到饱满的表达,而是模仿《诗经·公刘》的筑城描写,放笔铺排劳动的场面,以此来展示吕与宣城民众同心协力积极御敌的动人景象,赋的结尾,表达了收复失地的愿望:“公时与宾客而周览兮,泪雨下而交颐。念北狩之既远兮,渺法驾其何之?客起舞而寿公兮,愿效节于守陴。公亦友松乔而不得兮,反云旌乎霄涯。屏四方其安堵兮,岂陋壤之足焉。俨余冠以从公兮,聊望云而裴回”。其实,这篇赋是表达战乱流落的好题材,作者似乎有意回避那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即使是眷恋故国的意思,也说的有点冠冕堂皇,言不由衷。不仅是周紫芝,当时的多数文人似乎在努力遗忘切身感受“靖康之耻”,努力处身事外,在江南的明山秀水间尽快安顿下自己的心灵超然世外旁观时变这是当时的普遍现象。
并不是说周紫芝没有反思现实批判政治的作品,而是这样的作品其思想性和现实针对性都不强。在《蜂衙赋》中,周紫芝把人间的政治与蜂巢进行对比:
夫蜂以众集,其尊在王。日以朝事,盖理之常。有不安宅,王于易方。视王所至,众翼而翔。奔逸以趋,顾虞祸伤。王之所止,不飞以扬。聚都成国,复坐明堂。曰君曰臣,礼仪跄跄。平居无事,臣礼则臧。忠不弃主,犹在抢攘。嗟乎!朱轮华毂,貂冠绣裳。剑佩戛击,以朝明光。朝趋秦庭,暮馆汉章。官崇禄丰,主圣臣良。时危势倾,胡越相忘。孰知夫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与夫唯主所在,与为存亡者乎?故曰:死生以之,巍巍堂堂。背主弃国,是谓不祥。
只是指责臣子不能对君主效忠到底,如果这是在讽刺靖康之祸时的为臣者以及宋廷分崩离析的状况,未免失之皮毛。同样的作品还有《造雹赋》。作品通过守宫(壁虎)[2]能衔渠水作冰雹以为患人间,暗示朝中小人可以给国家带来大患:“守宫微虫……藏于山阴,发坎而视,碎如凝氷,是犹未足以为怪也。乃若雷电成章,山泽通气,阴云四起,冻雨立至,则轰然有声,起于蛰户,激为飞雹,散落无数,大或如卵,小或如雨,殒草杀粟,伤人摧羽,为物之病,盖有不可胜数者矣”,“嗟此有生,眇然其细。乃能含水造雹,毁瓦破块,配此霰雪,以为虐疠,是何其怪。如此徒使汉儒论之,惟咎阴阳,春秋书之,指为灾异。季武子之问申丰,犹莫知其计也。至归咎于藏川池之氷,弃而不用。曾不知考厥咎灾,以及斯类也”。作品有讥刺徽宗朝小人当道酿成大祸的用意,但是这样的指责缺乏对当时朝政的理性而深入的认识和分析,只是一种愤激情绪的表达。其实,在当时,人们普遍地缺乏对靖康之难的理性认识,出于为尊者讳和党争的需要,他们多从君子小人的偏狭视角来声讨童贯等,甚至波及到王安石,周紫芝自然不能超越此种窠臼。
二、漂泊感与空幻感:中年周紫芝的辞赋创作
进入南宋以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周紫芝依然落魄,也许由于生计的原因,他不断奔走于宣城、江宁池州杭州兴国庐山等地过着类似于清客的生活,逢迎官宦,流连诗酒。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强烈地感到,自己可能一事无成,终老贫困。这种悲凉甚至空幻的情绪成了他的情感基调。《钱塘胜游录序》是周紫芝在绍兴十五年(1145)写的一篇文章,当时他虽然步入仕途,依然饱含辛酸地写道:“崇宁间,余以事适越,道由钱塘,留数日而后行。时方厄于羁旅,不得从诸公游,然犹能一再至西湖,以观览湖山之胜,自是而西湖未尝一日不在胸中。后三十余年再至,则前日游观之地、登临胜处,十已失其八九。虽湖山无恙,不减昔时,而金碧漫漶,草木凋衰,烟云惨舒之状,鱼鸟游泳之乐,无复故态。如王、谢子弟穷愁病瘁,流落草野,虽骨尚在,而文采风流自然索寞,殊复可怜。余尝自谓方钱塘全盛,则不得从容舒啸其间,更兵戈百战之后,始得朝夕于此,是为可恨。况复官冷食贫,居无尊酒可以自乐,出无胜事可以同游,唯野服曳杖,时携小辈间至山中尔”[3]P162-163。这段文字可以概括周一生的情感经历,年少时的落魄无奈,中年的穷愁悲酸,老年的从容自在。但是,由于敏感的他经历了过多的磨难,形成了漂泊感和空幻感的情感基调。他的辞赋也在着力表现着漂泊悲凉和对人生终极价值的思索与否定。
虽然一生都在汲汲于功名富贵,但是周紫芝又对这种追求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甚至否定,这种矛盾,其实是他心如悬旌旗无所依归的反映,这也是那个高度集权而又腐败荒唐的末世在士人心里投下的浓重阴影。在《蝇馆落成赋》中,他把人世间比作蜗角蝇头之域:
子周子生于蜗牛之国,居于坎井之间。地止一席,屋止一椽。下饮蹄涔,上窥醯天。凭蚊睫以顾盼,附蠛蠓而周旋。虽伛偻以尽日,聊嬉戏而蹒跚。是曰‘蝇馆’,宅于蝇颠。念此有生,坎凛多艰。先人敝庐,载筑载焚。一岁之间,十徙九迁。分窗共户,或哀王孙。遭嗔蒙斥,亦怒其颜。蓬庐逆旅,莫适为安。
建炎三年(1129)金人扰宣城,周紫芝的家因此化为灰烬,此赋写的就是这件事。或许是为了减轻心里的痛苦,作者以极其达观的态度来审视自己的处境,认为人处天地之间,如巢蝇头,微不足道。否定人生,否定人生的价值,遁入虚无,以此来忘却人生的痛苦赋中对世俗社会所追求的种种富贵生活依次做了彻底的否定:“况乃自昔佞幸专嬖,权臣擅美。富家巨贾,高门大第。家僮五百人,步障三十里。奇祸忽作,室瞰百鬼。朝存华屋,暮掩蔂梩。嗟乎人生,电忽如此。视吾舍馆,岂不巨伟!”在逃避现实苦难方面,周紫芝继承了元祐学术的传统,通过深刻的反思,借助道家和释家的思想来舒解人生的苦闷,而当时的众多文人,则选择了放弃崇高,走向世俗、庸俗的人生。面对人生道路的挫折,周紫芝多通过逃离人世的景象描写来纾解,《隐居赋》描写“迫世故之寒饥”而希望远离人世间的场景:
俨余冠之峨峨兮,曳余裾之纚纚。发余轫于南山兮,渐余裙于天池。森九关之虎豹兮,夐杳隔乎霎霓。始艺兰之百畹兮,植杜蘅于江蓠。同草木之零落兮,风雨秽而不治。尘冥冥而昼晦兮,石齿齿其輈摧。知薰蕕之卒不可以同处兮,畴鸾鹜之并栖。世聱牙而不吾与兮,吾亦惝恍而沉思。暗奄苒其不再得兮,吁既逼于崦嵫。颓龄倏其几何兮,竟迷途之与阶。恫奋飞之不能兮,乖素心之幽期。藉隐默以自强兮,终厚颜之忸怩。慨夫骥之逸足兮,犹未就而衔羁。岂执维之不可脱兮,将生刍之不可以肥。幸盐车之未驾兮,岂空谷之难追。卜余居于法渊兮,反余佩乎江媚。制芰荷以为盖兮,结薛荔以为帷。雕桂树以为栋兮,采辛夷以为楣。食雕胡之既实兮,饮坠露之未晞。信尚友于千古兮,乐天命于以奚疑。
这不是隐居,而是成仙。作者想借助《离骚》中非人间景象的浪漫描写,来建立一种超出世俗观念的价值体系。自己在人世间得不到认可,那么就应该在虚无缥缈的境界中寄托灵魂,甚至是佛家的“法渊”!作者极为细心地描画这种非人间的景象,正是为了求的心灵的安宁。这段模仿楚辞的描写从字面上来看没有多少新意,但是,它透漏出周紫芝内心深沉的漂泊感和空幻感。
深深的失落和孤独使得周紫芝一直在苦苦寻找人生的寄托。《招玉友赋》是一篇借酒浇愁的作品。“玉友”指酒。在形影相吊的寂寞中,作者把酒描写成一位儒雅高贵的友人,借此以宣泄对人生的不满:“昔郦寄卖禄以全国,常山戮余以报私。曾岁月之几何,倏胶漆之已离。外表表其冠玉,中屹屹而险巇。伟兹友之穆清,交逾久而益夷。岂甘醴之易坏,亦浩浩其无疵挽夫君而与游视余子其奚为又何必慕青州之从事,追逸轨而并驰也耶?”人世险恶,唯有与酒为友才能获得心灵的解脱。周的诗文中描写酒的不少,如《玉友初成戏作二首》等,大都表现落寞无奈而借酒陶然。《酹三贤赋》是周紫芝在游览西湖时创作的一篇作品,他追念与西湖相关的三位高人白居易、林逋、苏轼。白居易、苏轼怀忠而见放的经历引起他的共鸣:“痛二老之不遇兮,越今昔而同俦。岂鸾鹗之不可以争飞兮,抑驽骥之难与并游。岂枘凿之不可以相入兮,抑亦臭味之异乎薰蕕。弃珠玑而贵鱼目兮,斥禄耳而驾罢牛。笑蹄涔之沮洳兮,转龙骧之巨舟。”世上恶人当道,俊杰之士倍受排挤压抑,这个主题在周的赋作中多次出现,这是他一生耿耿于怀者。周并不看重白居易、苏轼的那种随遇而安的中隐思想,而是青睐于林逋的与世俗绝缘:“独高人之前知兮,遂遐举而莫招。爰卜宅于兹山兮,旅麋鹿而友渔樵。却鹤书而不受兮,恐晓猿之怒号。草萋萋其春荣兮,叶霏霏而秋凋。阅四时不改其操兮,孰谓山中之不可以久留。”即使是朝廷征召,也却而不顾,他向往那种放浪于湖山的闲云野鹤般的生活。这当然不能看作是周紫芝真实的人生理想,而是一直愤激情绪的表现,是对人生深深的失望与幻灭。在《和陶彭泽归去来词》中,作为布衣的他甚至要彻底“归去”,放弃进取心和责任感。
三、遍历沧桑归于平淡:周紫芝晚年的辞赋创作
绍兴十二年(1142),周紫芝的人生终于有了转机,这一年,他参加科考并因此步入仕途。之后,他投靠秦桧,官运还算亨通。解褐这一年,周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早年心中的匡济报国的热情早已消磨殆尽,优裕的生活扫去了苦闷和落魄的情绪,他的心境逐渐归于平淡,以一种平淡而细腻的心态品味着安逸生活的滋味。和他交往密切的曾协和葛立方等都是趋奉秦桧并且极力与主旋律保持一致的人,都在鼓吹与金讲和的重大意义,都在赞美秦桧的勒石功勋,周自然也和他们一样,对秦桧和国家的“中兴盛世”积极献谀。
周紫芝留存下的辞赋中能够断定解褐以后所作的非常少,这或许与他心态的变化有关,辞赋这种长于宣泄的文体与他丰腴的生活显然是格格不入的。这个时期他为秦桧写了许多的近乎肉麻的贺文还写了那篇给他在文坛上取得“声誉”的《大宋中兴颂》。不过,晚年的周紫芝并没有蜕变成一个市侩的老帮闲,他似乎看破了人世间的纷纷扰扰,变得淡泊而优雅。《吊英布庙文》应该是他晚年居住九江时的作品,英布事楚时曾被封为九江王,这篇作品或许是对当地先贤的追思之作。赋曰:
繄楚汉之方兴兮,顾雌雄之未判。唯智者之见机兮,当方决而中断。始冠军之就戮兮,恨老增之见晚。悟使者之一言兮,遽投策而归汉。建王都于楚丘兮,俾故乡之改观。虽富贵之遂志兮,曾不戒夫盈满。威震主而不祥兮,宜避祸而远引。彼群夋兔(qun,同狡兔)之穴空兮,韩卢烹而不免。致主意之见疑兮,功臣惧而交惋。视越醢而信禽兮,分死生于夜旦。上印授而乞骸骨兮,追乔松而游汗漫。无尺籍之与寸兵兮,疑可释而冰泮。王料敌以如龟兮,何目眦之弗见?渡清淮而反田里兮,享寿康于安晏。盖无罪而杀大夫兮,士当去而不可缓。况勇冠于诸侯兮,复功高于既叛。何此理之不明兮,徒衔冤而永叹。
司马迁在对高主刘邦铲除异姓王的不义之举是非常反感的,因此《史记》的《淮阴侯列传》、《黥布列传》等颇多激愤牢骚之语。而周紫芝则把帝王功成即诛灭大臣视为一种常态,作臣子的要懂得功成身退的道理,他对险恶的帝王权术缺乏应有的批判和反思,把“多积金宝,广置良田美宅,歌儿舞女以终天年,如此,君臣之间再无嫌猜,可以两全”视为一种的常情。我们不能说周晚年失去了起码的批判精神,而是对政治权术愈来愈精到的帝王政治所持有的冷静的彻底的认识,可以说,晚年的周紫芝已经失去了读书人起码的捍卫道德的崇高感,举世滔滔,没有什么圣贤,成者王侯败者为寇。
晚年周紫芝的生活充满诗意,周遭的一草一木他都能咀嚼出其中的诗味。《告巨木文》是为移去宅前巨木写的一篇赋文。从文中“江乡之俗,岁多淫祀”可知此文也是晚年居住九江时之作。赋曰:
大木植吾敝庐百有余年,赖以不死,而其害滋多,不可不去。盘根错节横敷地,使土膏坟起以倾吾屋,不可不去也。大枝臃肿,小枝卷曲,既不足以中吾用,而败腐之叶填塞瓦渠,使上漏下湿以污吾席,不可不去也。春夏之交,柯叶如云,鸣枭哺雏以巢其颠庇遮恶鸟朝呶暮喧以耻吾耳不可不去也长蛇蜿蜒,来伺鸟雏,鸟噪蛇盘,恶类相攻,以怖吾儿,不可不去也。颠风骤雨,夜黑朝昏,凭藉势力,掀舞颓檐,使我常虞覆压之患,以忧吾心,不可不去也。夫木为吾害如此,则其戕而去之可以无憾矣。神虽欲托此以为妖祥,不可得也。今者刀锯既具,匠石在旁,酒浆前陈,巫祝在后,神逝而往,木仆而僵,我不神咎,神无我殃。尚享!
文中饶有兴趣地描写宅前大树给生活带来的种种不便,希望征得神灵的谅解,予以刈除。伐去庭中树木,这本事一件再平常不过的生活琐事,但是作者能枚举种种不便,从中体会到它的情趣,能够一本正经地写入文章,以一种悠扬的节奏表达出来,这足以说明周对晚年生活的满足。这和他早年赋中所表现出的凄凄惶惶的情绪相比,反差是巨大的,也许可以这么说,正因为有过苦命落魄的生活经历,他才如此珍惜、如此用心品味眼下的生活。
四、周紫芝辞赋以意趣为尚又得锻炼之工的艺术追求
周紫芝是位诗人,他的辞赋不以铺排为尚,而是追求含蓄隽永的意趣。同时周是当时受元祐学术影响非常明显的一位作家,他的追求意趣还与其对苏轼等为文主张的继承密切相关。周的赋,往往意思深邃而趣味横生,和同时代辞赋普遍存在的平易肤浅是有区别的。
周紫芝的辞赋善于描写日常生活景象,在景物的描写中融入作生活情趣、生活格调,不仅使人身临其境,而且深入其情、领略其思考。《听夜雨赋》是这样描写夜雨欲来的景象的:
“岁壬辰,秋七月。夜既寂,凉风登。饥虫号寒,庭树脱叶。子周子傲胡床以箕踞,耿秋怀之谬慄。依倚孤灯,爬搔短鬓,盖戚戚然有不悦焉。紞如三鼓,夜既分矣,有声飒然,起于寒蕉。静而听,屑屑骚骚。始霏微以成滴,旋淅沥而惊飘。声欲断而复续,势中微而倏高。惨元云之夜色,滞青蘋之轻飙。梦江声之汹汹,杂檐溜之嘈嘈。眇长更其愈远,睇寒窗而未朝。”凉风习习,虫声唧唧,在寂静中雨声渐渐转激,独坐一室,青灯荧荧,夜雨降至之时的欣喜跃然纸上,而且,从中我们还可以体会到他对眼下生活怀着诗情去品味的那种满足和志意陶然。风雨之夕,按常理是抒发悲情的好时机但作者却一反常情“此殆造物者恨怆而愁子也,子犹闻而乐之也耶?”由此,引出对畴昔逆旅客居听雨的景象的描写:“嘻!仆贱役也。畴昔之夜,流转倦游。吴江楚泽,贾胡滞留。岢峨巨艑,舫艋扁舟。风樯浩荡,短棹夷犹。孤蓬独夜,风雨飕飀。天寒日暮,深山穷谷。短衣匹马,逆旅独宿。主人欢笑,夫饮妇属。客子万里,百念满腹。风雨淋漓,寝不瞑目。方余处此,安能不凄?”同样的写雨,前段重在听雨的心境,这段则重在表现夜雨中主人和客人生活形态的对比,以此突出客居的寂寞和生活的落魄。有这段的帮衬,前段的心境就有了理由,也更富于意趣。在此基础上,作者进一步点出此时的心境:“其以悲反而思之,有若痛定恍惚自疑,今方振衣弹冠,脱履解靴,方床石枕,高卧茅茨,以听夜雨之垂垂,不犹愈于向者困苦羁愁,无所于归而栖栖者乎?何向者不动其心,而今反不乐以嬉乎?虽然,余犹以为未也。夫鸟不厌高,鱼不厌深。麋鹿歧之,志在山林。适有天幸者,不慭遗余。有田一廛,有芋一区。有薤百本,有橘千奴。其不然耶,犹能著短蓑,卧牛衣,烹伏雌,炊扊扅。老妻稚子,佩犊带犁,以耕春畦。然后恣倦夜之熟寝,倾浊醪以解颐。和叶上之寒声,哦晓雨之新诗。吾虽老矣,而犹可庶几也。”作者已经抛开了对雨夜的关照,而是放笔描写此时的生活,虽然穷苦依旧,但与家人团聚,和乐融融。这就为听雨时安逸的心境找到了依托。当然,作者还是巧妙地融入了安居贫贱而仍思欲奋发的思想,文中用了百里奚的典故。《乐府诗集·琴曲歌辞四·秦百里奚妻琴歌一》曰:“百里奚,五羊皮。忆别时,烹伏雌,炊扊扅。今日富贵忘我为!”作者希望此时的自己也和当年的百里奚一样,有一个发达的机会。这篇赋通过层层深入引人入胜的情景刻画,对比观照,使得雨夜闻霖充满了诗意,甚至还有些许哲理的意味。
周紫芝的《却暑赋》也是一篇相当有趣味的作品。以“却暑”为题的赋作在宋代相当多,大都通过对寒冷景象的铺排描写来驱散暑热给人的充实感和压迫感,多是游戏文字。如欧阳修的《病暑赋》、刘敞的《病暑赋》、刘子翚的《溽暑赋》等均有创作。而且这些作品大多通过对“却暑’的描写,展示富贵丰腴的生活。周紫芝的《却暑赋》也在极力描绘天寒地坼的景象但是笔锋一转通过客人之口道客大笑曰:夫子之室,枵然中空。囊无败絮,衣衾不重。念鹑衣而莫得,况狐裘之蒙茸。秋风飕飒,露泣草虫。稚子号寒,老妇改容。不于未寒而求衣,乃反大言以自盲聋。”这真是让人忍俊不禁的一幕,自己比穷人还穷,还要学着富人的样子写“却暑”的文章,一旦寒冷降临,情何以堪!作者的安贫乐道苦中作乐如在目前,而且还有一种对自己不能免俗附庸风雅的调侃。赋的结尾,主人的回答更加深了这种调侃的意味:“嘻!吾侪小人,朝夕偷安。聊复念此,以涤吾烦。岂谓夏虫,而不可以语寒。愿子速退,无败吾欢。”主人的颟顸令人解颐。其他如《蝇馆落成赋》、《招玉友赋》等,均能使人会心而笑,有所启发。
周紫芝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掘盎然的趣味,尤其是晚年生活优渥,更能体会到平凡生活中的乐趣。而且,这和当时文坛重视书写日常生活的倾向是一致的。《祭野鬼文》和《告巨木文》文风接近,应该是晚年的一篇作品。赋曰:
我方阅书,夜久人寂。有笑于外,其声哗哗。或喧以呼,或悄以默。或附吾窗,或撼吾壁。开户视之,云暗月黑。有火而青,倏起倏没。即而求之,恍兮无物。主人谓余,是鬼之场。郁其滞魄,凭其强阳。时出而游,以为祟殃。曰此馁魂,是谓不祥。举酒一酹,告以其良。嗟嗟尔曹,伊谁云伤。岂死于兵,抑殂于商?其困于役,抑逋而亡?其毒于药,抑伤斧戕?岂魔于梦,抑沉酒浆?归舍真宅,魂羇具乡。固有不幸,亦其勿臧。不得其死,以其强梁。怀奸孕毒,自有肺肠。嗜利贪荣,冥行伥伥。尔颜亦厚,尔德甚凉。孰掩尔骼,暴于康庄?人之为善,乌可不蘉?坠兹幽途,以失厥常。使我攓蓬,以效庄狂。妖以饛簋,沃以巨觞。以醉以饱,乐南面王。毋呈尔丑,以自盖藏。尚享!”
祭祀野鬼、枯骨等是辞赋中比较常见的题材,这类作品大多阐发《庄子·至乐》中那段庄子与骷髅对话的齐生死的思想,[4]周紫芝辞赋虽然句式上有意模仿庄子,以暗示此赋与《庄子·至乐》那段文字的联系,但是其思想倾向则不太相同。他没有刻意去追求思想的深刻性,而是通过对鬼魂的警告来体现对现实生活的由衷热爱。他这样告诉鬼魂,不管如何死法,既然已经死了,就该安心真宅,不要跑到人间捣乱我们看到这个祭祀的过程并不庄严周的祷文也不严肃,他是通过这一过程在玩味生活,在展示自己的人生情趣。《告巨木文》也是出于这样的动机而创作的。
周紫芝辞赋在辞章方面颇为考究,章法得当,收放自如。如前面提到的《听夜雨赋》的层层对照、《却暑赋》当中的转出新意等。《敬亭山翠云庵赋》是周早年在家乡写的一篇赋作,也是他作品中仅有的一篇山川风物赋。和其他的这类赋一样,此赋的开篇交代敬亭山的地理位置,然后描写山势,不过,这里作者并没有铺叙山的形势,而是在描写山的云雾,而后写月夜下的敬亭山美景,选取的角度较为独特,能够充分彰显此山的特色。由月色转入自然翠云庵的描写非常巧妙:“四郊云敛,万树风疏。洸洸漾漾,唯月唯予。飘若控鹤以冲天,宛如跨虹以骋虚。骇青萍之冷逼,恍阆风之我居。乃有殿阁,迥然中起,在山之阿,于宛之涘。”在恍若仙境的山中月色中引出对殿宇(翠云庵)的描写。然后由殿宇转入对其周围的树木鸟兽的描写以及在庵中纵目极望的描写。其结构以翠云庵为中心,由外而内,由内而外。结尾部分,化用孔稚圭《北山移文》的手法来彰显此山此庵使人忘世的仙界色彩:“于是薜荔绊车,橘刺搴帷。偃骞栖息,寄傲徘徊。或抱膝而朗吟,或凭栏以长啸。谷口腾欢,郊关含笑。祛尘想于须臾,恋幽岨于晚眺。”以人对此山的感受结起全篇。文章结构紧凑,角度新颖,详略得当。周紫芝的每一篇赋在谋篇上都相当考究。周紫芝的赋还擅长练字,他把作诗的功夫用在了为赋方面。有些文字非常传神,如:“平夜星垂,银河波落。寂万籁以同声,合婵娟而共榻”(《敬亭山翠云庵赋》);“形影相吊,自为朝昏”(《招玉友赋》);“老人疲倦,昼掩横门。如坐深甑,眩乎沉昏”(《却暑赋》)等。
总之,周紫芝的辞赋清晰地展示了两宋之际文风由深刻沉郁向平易而富于生活气息的转向。而这种转变的重要原因是朝廷在靖康之难后没有能积极团结朝野各种力量以形成同仇敌忾的氛围,而是在对金国的政策上包藏私心,态度暧昧,尤其是秦桧专国时候的高度专制,把文人朝政强行推出政治之外,推向求田问舍和享受生活。周辞赋中所表现的由沉郁愤懑到空幻失落再到随俗沉浮的转变,正是那个时代文人心路的一个缩影。
[1]周紫芝.太仓稊米集自序[A].全宋文(卷三五二一)[C].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2]苏轼有《蝎虎》诗曰:“黄鸡啄蝎如啄黍,窗间守宫称蝎虎。暗中缴尾伺飞虫,巧捷功夫在腰膂。跂跂脉脉善缘壁,陋质従来谁比数。今年岁旱号蜥蜴,狂走儿童闹歌舞。能衔渠水作冰雹,便向蛟龙觅云雨。守宫努力搏苍蝇,明年岁旱当求汝。”
[3]周紫芝.全宋文(卷三五二一)[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
[4]《庄子·至乐》:“庄子之楚,见空髑髅,髐然有形,撽以马捶,因而问之,曰:‘夫子贪生失理,而为此乎?将子有亡国之事,斧钺之诛,而为此乎?将子有不善之行,愧遗父母妻子之丑,而为此乎?将子有冻馁之患,而为此乎?将子之春秋故及此乎?’于是语卒,援髑髅,枕而卧。夜半,髑髅见梦曰:‘子之谈者似辩士。视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则无此矣。子欲闻死之说乎?’庄子曰:‘然。’髑髅曰:‘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从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庄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复生子形,为子骨肉肌肤,反子父母、妻子、闾里、知识,子欲之乎?’髑髅深矉蹙頞曰:‘吾安能弃南面王乐而复为人间之劳乎!’”周紫芝此赋中对鬼魂的诘问,句式与庄子此处相类。论”[EB/OL].http://blog.sina.com.cn/s/blog_ 5f226183010156g2.html
责任编辑:秦小珊
I2
A
1004-3160(2012)06-0105-08
2012-08-24
刘培,男,山西应县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唐宋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