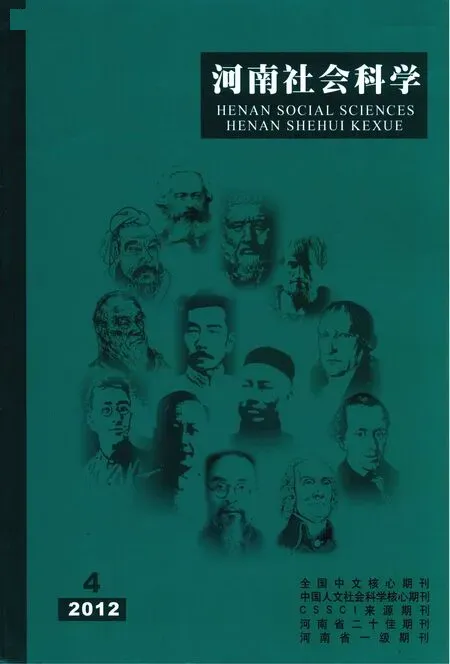民主、信息公开与国家治理模式的变迁
沈开举
(郑州大学 法学院,郑州 450001)
Shen Kaiju
民主、信息公开与国家治理模式的变迁
沈开举
(郑州大学 法学院,郑州 450001)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内,信息公开与民主制度并无关联,因为“精英民主”模式通常与保密文化密切相关,它既不鼓励公民参与,也不希望公民知悉政府的信息。直到参与式民主在近几十年取得主流话语权,信息公开才与公共参与一道成为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中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实施,不仅有利于国家治理模式的转变,而且未来必将有助于民主的发展。
信息公开;民主政治;精英治理;公共参与
对于当下中国来说,“民主”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一个“大写”的真理,在政治和法律领域,凡是被人们所称道的,都被认为是民主内在的或者必然的要求,或者至少与其密切相关。人们对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论证思路即是如此。我们并不反对民主,更不反对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然而需要明确的是,为人称道的“政府信息公开是民主政治之本意”之类的说法,并不符合人类的民主政治史,作为一项制度,政府信息公开在很长一段历史上与民主和国家治理并无关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几十年前参与式民主兴起并成为主流话语为止。
一、雅典民主、全民治理与信息公开
如今为人们公认的是,作为一种国家治理模式的民主制度最初起源于古代希腊的雅典。不过,雅典的民主制度显然不同于现代人们眼中的民主。在那里,对于每个公民来说,民主不仅仅是一项权利,而且还是必须履行的义务,雅典人甚至将不关心公共事务的人视为无用之人①。为了确保全体公民参与到雅典的民主政治当中,雅典人成立了公民大会、五百人议事会和民众法庭三个机构来实现全体公民对城邦治理。政府信息自然是公开的,而且可能制度建设比较完善,否则公民大会便无法举行,也做不出任何决议。然而,这却并非事实的全部。透过贡斯当(Benjamin Constant)那本对于自由进行经典分类的书,我们得知,除政府信息需要公开以外,为了确保雅典公民的公民德性不被腐蚀,几乎所有的私人生活也都是公开的,这就导致了“尽管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都是奴隶。作为公民,他可以决定战争与和平;作为个人,他的所有行动都受到限制、监视和压制”②。雅典民主制历来为人们津津乐道。今天不但有人称赞其为“真正的民主制”,而且还有人希望恢复其往日的荣耀,“用抽签替代选举”③。然而几乎没有人愿意重建这种不但政治透明而且社会的透明和公民私人生活的透明(通过公民彼此的监控和揭发)的民主制,因此笔者对雅典民主制就不做过多的分析。
二、现代民主、精英治理和保密政治
雅典在希腊内战中被打败后,民主制度即告中断。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和随后的美国革命,民主才作为国家治理模式的一种,重新回到人类的政治和法律生活中。出人意料的是,这种从雅典时代到启蒙运动,一直被人诅咒和谴责的制度④,不但成为“一发弗止之时代思潮”,而且逐渐获得了某种神圣的地位。不过,由于人们对于多数人暴政的恐惧,古代希腊的直接民主制度并没有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后来它反而被称为“代议制民主”的新型民主模式所取代,这种民主模式通过不断的发展和完善,不但逐渐演变为今天为人们所熟悉的现代民主政治,比如自由主义民主(liberal democracy)、宪政民主(constitutional democracy),而且造就了一种新型的国家治理模式,即精英民主和精英治理。此种民主就如同熊彼特所定义的那样,“就是那种为作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的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⑤。韦伯的描述更加具体形象,他认为“政治上利益相关者的运作”才是政治的本质,而这一运作的过程“并非政治上被动的‘群众’从自身中产生领袖,而是政治的领袖招募追随者,并通过‘蛊惑煽动’赢得群众。在哪怕十分民主的国家制度中皆如此”⑥。
在现代社会中,尽管直接民主制逻辑上讲不通,实际上办不到,但“精英民主”理论却也并不为人欢迎,因为这意味着“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古老格言仅仅在选举之日才是真实的,可以想象这对那些为了民主而战斗牺牲的人们来说,是多么大的讽刺和打击。不幸的是,正是“精英民主”理论道出了现代民主的真谛。因为现代民主制实际上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的,即尽管政治权力的合法性依然源自人民,但是由于人民自身的非专业性、易受蛊惑性以及短视、自私和对事务缺乏长远且一贯的看法,国家治理只好委托政治精英来完成,就像本杰明·拉什说的那样,“一切权力源于人民,但他们只在选举日拥有它,此后它就归统治者所有”⑦。当然,为了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不被侵犯(伯林将其称之为“消极自由”),要求由精英组成的政府完全按照经过人民同意而制定的法律规则来进行工作就显得十分必要,为此不但应该按照自由宪政主义的要求建立权力的分立与制衡机制,而且要对政府的各种管理机制都进行制度化和规范化。此后,作为个体的公民只要“每隔几年,把各政党组织事先印好发给他的选票塞到投票箱里”,他就可安心地将剩余时间和精力用于私人生活。
政府信息公开在此一模式中是否必要呢?“精英民主”理论的倡导者和坚定维护者韦伯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认为,为了加强对公民的政治教育,确立行政公开和行政监督制度,让国家公民习惯于经常密切注视(政府)如何管理他们事务的方式是极为必要的⑧。不过,韦伯的建议并没有被各国政治家们完全接受。在英国,无论是行政文化还是政治文化都不支持“阳光政府”。因为政治精英们认为,多元主义、公共参与和信息公开与其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抵触,“我们的政治传统是围绕着一套代议制政府理论建构的,根据该理论,通过我们选出的代表我们都参与了政府”⑨。1968年,英国的司法机构才首次在Conway V Rimmer案件中质疑政府拒绝给予出于诉讼目的的要求获得政府文件的权利。到1972年,尽管Oliver Franks爵士领导的致力于改革《官员保密法》的官方委员会警告说,一个“追求秘密目标,或者在有效行使其适当职能所需要的更大的保密范围内行事……的政府将失去人民的信任”,但是进一步公开政府信息的努力并没有获得成功,以至于英国行政法学家哈洛和罗林斯在1997年出版的书中依然抱怨说,英国人“从未从1911年严厉的《官员保密法》(Official Secrets Act)规定的一般披露禁令中恢复过来,实际上使所有在政府雇佣过程中获得的信息披露都构成刑事犯罪”⑩。2000年,英国版的《信息自由法》终于由议会通过,但是这部法律直到2002年才被女王批准,法案的生效时间更是被推迟到2005年1月1日。对此,Laura Neuman和Richard Calland曾经揶揄道:“如果磕磕碰碰的启动会损害一项法律的权威性,那么为法律的生效提供更长的准备时间也许是必要的。准备期应该长到足以确保公共部门有能力执行该法律并且告知公民他们应有的权利,但不能长得像英国这样,居然用了五年的时间,这样的政府有愧于它对透明的许诺,执行法律的动力也将会减弱。”
美国人宣称他们的民主制度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美国宪法之父麦迪逊在建国之初的名言“想要当家作主的民众必须用知识的力量将自己武装起来。一个民选政府若无民众的信息或无获此信息的途径,那就不过是一场闹剧或一场悲剧的序幕,抑或两者兼而有之的序幕”经常被人提及,伍德罗·威尔逊总统(Woodrow Wilson)也曾呼吁:“政府应当是对外透明而非暗箱操作的……政府可以做一切事情而让老百姓毫不知情的现象决不应该出现。”但是《信息自由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OIA)是在经历了11年的争论和妥协才于1967年实施的。有意思的是,签署这部法律的约翰逊总统一方面声称“我一直深信信息自由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只有国家安全的需要,而非公务员或平民的需求,才决定何时对信息自由进行限制”,另一方面却和联邦调查局等部门一起积极地阻挠国会通过这一法案,直至最后不得不在法案上签字时,他又不断想方设法改变呈交给众议院的版本,以便使该法案在被通过后减小对行政机关信息公开的压力。即便如此,该部法律本身也是漏洞百出,极不完善,比如没有规定政府机关对信息公开请求予以答复的期限,没有规定政府提供信息公开应当采取的收费标准,致使很多官员采用拖延和高额收费的办法阻挠民众获取信息。其结果是,信息申请者不但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感到极为沮丧,而且对行政机关产生敌意,最后对《信息自由法》的神圣目标也产生了怀疑。直到1974年国会通过《公法》93-502号在处理期限、收费标准、诉讼费用、封锁信息的法律责任等六个方面对《信息自由法》进行了重大修改,这些情况才有了根本的改观。
举出更多的例子显然没有必要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政府都有秘密政治文化和秘密行政文化的历史,这一点无论是在民主制国家,还是在号称民主的国家都不例外。当然,上述的梳理并不是说在“精英民主”理论之下,就不存在获取政府信息的途径和可能,这当然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无论是什么性质的政府,都不可能完全秘密地运作,它总会向民众提供和发布卷浩繁的新闻稿、报告和声明,甚至用强大的舆论宣传工具极力宣传这些信息。然而,这些只是政府觉得可以让我们知道,或者它希望我们知道的信息,与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公开并无大多关联。
三、公共参与、精英决断和信息公开制度的确立
很显然,以代议制为基础的现代民主制度并非完美无缺,代议制理论集大成者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对此极为清楚。他曾谈到,从其自身来看,代议制政府的反面就是官僚政治,它或许会带来某些好的结果,但却会走向墨守成规并导致公共智慧的窒息,因为它在本质上就是专制的。
如果说17—19世纪,人类不得不选择和承受这种治理模式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特别是二战以后,伴随着以下两个方面的社会和政治发展,修正精英治理模式,实现公民参与政治生活以及社会管理活动,不仅必要而且可能:一方面是传统自由放任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夜警国家”逐步被“福利国家”所取代,政府除维持公共安全和秩序以外,还需要对增进公共福祉、促进经济成长、降低社会不公、完善社会福利制度等事项负责,政府权力因此开始呈几何级数不断增长,对公民权利造成侵害的可能性和严重性不断增大,这使得传统体制下通过议会和法院对行政机关进行监控变得越来越力不从心,通过行政程序法、公众参与和政府信息公开来规制政府权力就成为必然选择。另一方面是“代议制—精英民主”理论所依赖的假设,即“民众由于自身受教育程度低下,或者为了养家糊口而没有时间和空闲参与政治,因而不得不将所有的政治事务委托政府”在20世纪以后也越来越不符合现代社会的现实。实际上,伴随着几个世纪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公民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大部分公民已经有能力、金钱、时间和精力来参与政治生活了。
社会的需要催生了理论。1960年,阿诺德·考夫曼首次提出“参与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概念,并将此一理论广泛运用于微观领域的分析,比如学校、社区、工厂。1970年,卡罗尔·佩特曼教授发表专著《参与和民主理论》,将参与从微观领域扩展至政治领域,其认为,“代议制—精英民主”仅仅是对现实政治制度运作逻辑的描述,并非充分且真正的民主,且无法透视参与对于公民培养及社会建构的根本价值。而几乎在同一时期,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A.Dah1)提出了“多元民主”理论。他指出,民主是多种利益集团相互作用,而公民的广泛参与是民主的核心,“民主是所有成年公民都可以广泛分享参与决策机会的政治体系”。
在同一方向上做出贡献的还有卡尔·科恩(CarlCohen)和巴伯(B.Barber)。科恩提出“公众参与”的民主理论,认为“民主是一种社会管理体制,在该体制中社会成员大体上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影响全体成员的决策”。而巴伯则把现代形式的参与式民主命名为“强势民主”(strong democracy),此种民主依靠的是由公民组成的共同体的自我统治的观念,力图在正视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政治冲突的前提下,通过公民参与、公共商讨与公民教育等中介来转换政治冲突。行政官僚组织当然是有必要保留的,但其作用将被限制在依照公共领域的商讨而进行决断的范围之内。
伴随着公共参与在世界范围的发展,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在越来越多的国家被确立和实施,比如日本、澳大利亚、韩国、南非,甚至牙买加、马里和尼加拉瓜。我们今天甚至可以将这两者看做是“孪生子”一般,因为参与式民主在现代的发展很明显依赖于政府信息的公开,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又将不断地促进公共参与向更广阔的领域和更深的层次发展。尽管准确绘制出参与式民主与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之间的关联图并不容易,但诚如汉娜·阿伦特所指出的那样,“对公权谋私唯一的补救办法,就在于公共领域本身,在于照亮公共领域范围内每一个行为的光明,在于那种使进入公共领域的一切都暴露无遗的可见性”。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府信息公开,那么公共参与无论是在强度上、规模上,还是在对于现代政治和法律发展的重要性上,乃至在对于腐败和保密政治的遏制方面的作用都将大大降低。
当然,参与式民主的发展和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确立并不意味着今天的人们已经完全可以实现现代共和主义作家们所构想的“公民治理”和“无干涉的自由”了,因为即便是激进式参与民主的倡导者,比如强势民主倡导者巴伯,依然认为政治官僚精英作出最后的决断是必不可少的。参与民主下的“公共参与+精英决断”国家治理模式实际上依然隐含着诸多抵制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因子:首先,大多数政府在精英治理模式下已经养成了关起门来运作权力的习惯,这种权力惯性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根本改变,即便是在民主制度下,官僚集团依然会不遗余力地抵制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要求;其次,一部分官僚们依然认为他们理所应当地“拥有”其负责的资料,公开政府信息几乎是相当于让他们交出权力,所以行政官员利用民选代表的对于行政事务缺乏经验的弱点而蔑视民意,一意孤行在各国都屡见不鲜;再次,将政府信息公之于众,还将暴露官僚们的懒惰、工作或决策失误以及无法暴露于阳光之下的贪污和腐败行为,因此抵制或者消极对待公民信息公开的要求,从而防民、设威和自保几乎成为一种官僚集团的本能。
所以,对于当下的整个世界来说,“人民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还是个新鲜的概念,是一个我们必须保持警惕,以防它受到侵蚀或破坏的概念……我们不能认为信息自由和公众知情权的概念是理所当然的”。在很多国家(包括忙于输出民主制度的美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并没有载入宪法;在另外一些建立了或者宣称建立了民主政体的国家,虽然政府信息公开法律已经公布,但那仅仅是为了吸引外资或者是为了加入一个跨国组织、地区贸易组织或共同市场,公民知情权(the right to know)并没有被广泛接受,相关法律的执行和实施举步维艰。
四、政府信息公开与中国
据说,1776年在瑞典通过的世界上第一部信息公开法是源自中国的灵感。依据瑞典信息公开法的主要发起人、教士兼国会议员Anders Chydenius的说法,问责政府观念并不是起源于西方,而是起源于东方正处于鼎盛期的清朝的御史监察制度,他认为中国是“出版自由的模范国家”,中国为其他国家树立了学习的榜样,这样一个历史的误会尽管让中国人感到哑然——很明显,Anders Chydenius先生并不了解中国“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数千年保密政治文化历史。
尽管从理论上来说,中国在建立了社会主义民主之后,保密政治应该彻底改观,实施政府信息公开应该是题中之义——按照社会主义民主优越于资本主义民主的说法,社会主义民主背后隐含着规范意义上的正当性,在于无产阶级本身的政治德性能够建立起一个以公共利益为先的“德性共和国”,在于社会主义民主并不是简单的“选主”技术,而是建立了包含“调动广大劳动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的组织技术和动员技术,实现了真正的“人民当家作主”,但是,现实并不容乐观,根深蒂固的封建传统文化,革命时期的“敌我”思维,阶级斗争依旧不曾停息的政治论断,以及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阻隔,都还在影响甚至左右着最高领导层对于政府信息是否公开或者是否保密的判断。《信息公开条例》三年多的实施效果以及《国家保密法》修订过程中所引发的争论,已经充分说明这一点。
然而,我们不应因为这些挫折而对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表示怀疑,或者丧失信心。因为政府信息公开是现代参与式民主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国家从精英治理向“公民参与+精英治理”模式转变的题中之义。如果我们坚信社会主义民主优越于资本主义民主,坚信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当家作主,那么,在吸收国内外已有信息公开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之上,依照“公开为原则,保密为例外”的指导思想,完善中国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和保密制度就是必需的。这当然会对政治体制和国家治理模式的革新提出重大挑战,但又何尝不是凝聚民心、重建信任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机遇?
注释:
①[古希腊]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徐松岩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往下。
②[法]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阎克文、刘满贵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7—48页。
③王绍光:《民主四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245页往下。
④希腊圣贤以及近代启蒙运动思想家们对于民主的批判和责难被王绍光先生详细搜集,可以参见前引王绍光书,第13-30页。当然,卢梭是个例外,他热情地讴歌民主,而且首次系统明确地提出了人民主权理论。
⑤[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95—396页。熊彼特的理论当然不是横空出世的,帕累托、莫斯卡、米歇尔斯、韦伯等人对于精英理论的认识和阐述都曾经给其直接或者间接的启发。
⑥⑧韦伯甚至认为:“积极的群众性民主化的意义在于:政治的领导人不再能够根据在一个绅士阶层的圈子里承认他经受住考验就被提为候选人,然而依仗他在议会里的出现就成为领袖,而是他要赢得群众对自己的信赖和相信,即采取群众性蛊惑煽动的手段赢得政权。从本质上讲,这意味着应用独裁专制的办法来选择领袖。”[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卷),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林荣远译,第800、807—808页。
⑦○22[美]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陈周旺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222、236页。
⑨C.Harlow,“Power from the People? Representation and Constitutional Theory”,From Law,Legitimacy,and the Constitution:Essays marking the Centenary of Diecy’s Law of the Constitution,edited by Patrick McAuslan,Londen,Sweet&Maxwell(1985).
⑩[英]卡罗尔·哈洛,理查德·罗林斯:《法律与行政》(上),杨伟东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19—222页。
责任编辑 韩成军
Democracy and Public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the Changing of the Mode of State Administration
Information disclosur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Democracy in the very long period of historical time,the model of“Elite Democracy”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ulture of secret,in which public participation is not encouraged,and the government doesn’t want the citizens to get its information.Until the nearly several decades,as Participation Democracy is popular,the Information disclosure,with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is becoming the important part of Democracy.The Disclosure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gulation,which took effect in 2008,is an important step for the change of the model of national governanc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democracy for China.
Information Disclosure;Democracy Politics;the Governance of Elite;Public Participation
Shen Kaiju
D9
A
1007-905X(2012)04-0006-05
2011-12-10
沈开举(1962— ),男,河南信阳人,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