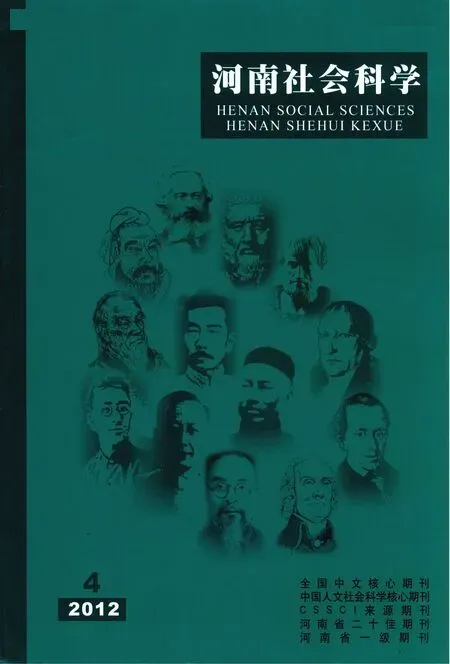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中的“实践”与“社会关系”
——兼评阿尔都塞对“社会关系”概念的拒斥
孔扬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中的“实践”与“社会关系”
——兼评阿尔都塞对“社会关系”概念的拒斥
孔扬
(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把“历史”作为新世界观的解释原则,这既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果,又是一项需要继续深入探讨的理论课题。在对“历史”的理解中,把握住其内蕴的“实践”与“社会关系”两大范畴的一体化关系是至关重要的,这直接决定了把历史唯物主义与黑格尔、阿尔都塞等人“历史无主体”的思想区别开来,以及把历史唯物主义与“实践唯物主义”解释原则区别开来的基本立足点。而要把握住“实践”与“社会关系”的一体性,首先需要我们返本开新,回到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种一体化关系原始发生的解释——人类学研究当中。
人类学;历史;实践;社会关系;阿尔都塞
把“历史”由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对象跃迁为解释原则,这在越来越广的范围内和基本结论的层面上,日益获得广大研究者的认同。不过,如何理解作为解释原则的“历史”概念,看来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需要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系统的支持——最为核心的当然还是“实践”与“社会关系”范畴的支持。本文的目的,就是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类学文本,重新思考我们所“熟知”的这两大范畴,通过发掘其一体化发生关系的角度以及评论阿尔都塞相关解释的路径,来阐发对“历史”原则的理解。
一、“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把握住“实践”与“社会关系”两大范畴的一体化发生原理
当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而把“历史”理解为这一新世界观的解释原则时,我们首先就要对“历史”概念进行界定。马克思关于“历史”的经典定义是:“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这种活动包含两个基本因素:一是“实践”,即“人对世界”的改造、人把“自己的目的”变为现实的过程,人在改造世界的同时也就改造了人自己,由此形成了不同于动物性代际复制的属人“历史”;二是“社会关系”,即在实践中形成的、一经形成又制约实践的“人与人”的关系,它既是上一代次活动的结果,又是下一代次活动的前提。这双重因素,构成了唯物史观历史科学层面“生产力”、“生产关系”范畴的哲学基础。
抛开“实践”而孤立地看待“社会关系”,则历史真就变成了一个“无主体”的过程,从黑格尔“无人身的理性”到阿尔都塞的“历史无主体”思想,它们作为对现实的表征不可谓不深刻,但最终都会陷入神秘主义;抛开“社会关系”而孤立地看待“实践”,则人又被归结为一种永恒的本质在先之存在(以“物质改造”代替“思想认识”的“主体—客体”结构),这种意义上的“实践唯物主义”是向费尔巴哈人本学的倒退。只有牢牢把握住“实践”与“社会关系”的内在同一性,才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高度。
为此,有必要认真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对“实践”和“社会关系”所作的一体化的发生说明。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中的“实践”和“社会关系”是“前异化”范畴(马克思在晚年也常常使用“异化”概念表达工人的生存状态,其含义是指工人被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所控制而丧失了个人的独立性),但这种观察本身不是“直接”面对古代社会的结果,而是“透过”现代社会“异化”范畴进行追溯的结果,这就是“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原则;人类学中的“实践”和“社会关系”不仅为唯物史观解释原则提供了一个发生学说明,而且为马克思主义的解放论提供了一个“未来学”参照——但这不是向“永恒人性”的“复归”,而是扬弃异化、走向个人独立性的本体论承诺。由此出发,我们在本文最后还将延伸论证,批评阿尔都塞拒斥“社会关系”概念的做法。
二、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研究的现代前提:大工业使人的实践性存在由隐而显
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研究的对象是“古代社会”,但他们的古代社会研究“得以可能”则在于“现代社会”。换言之,马克思恩格斯是带着现代社会才能够赋予的新世界观去观察古代社会的[2]。“世界观”的演进由人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演进作为现实基础,所以我们要先从马恩人类学研究的现代前提入手。这个现代前提,就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对自然的彻底改造,以及由此而明朗化的人的“实践”(改造世界,使自在世界不断人化)存在方式。在今天,我们都认可“实践”是人的存在方式,并将之上溯为自从人类产生以来的、人之为人的根本。但严格来说,只有经历了大工业的发展阶段之后,人才是名副其实的实践性存在。为了说清这一点,需要引入古代哲学关于人的几种“实践性”理解作为分析背景。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圣经》的“伊甸园之逐”隐喻最具代表性。人的原型亚当和夏娃因偷食智慧之果,明白了人独立于外部世界而存在。这种自我意识的结构,正是实践——人与世界的否定性统一结构的思想表征。人不再是上帝——大自然襁褓中的混沌婴儿,他要靠自己的劳作去改变自然来获取食物。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天人合一”是一个至高理想。但是,当先哲提出“天人合一”时,其隐含着的前提就是人与天已然分裂了,人在事实上成为与天相对立的存在物——这不正是对“实践”这一现代哲学范畴的远古揭示吗?又如老子等“绝圣弃智”、“绝学无忧”的观点,也都是对人类走上忤逆(改造)自然的不归之路的反思。
但是,上述理论表征毕竟还只是萌芽。古代哲学家之所以不可能把“实践”定义为人的完全性的存在方式,决不是因为他们不及马克思聪明,而是因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当中,人类实践在离开“自在自然”的路上尚未走远,人的实践活动尚不足以使得外部世界高度“实践化”,从而人的实践本质也就得不到彻底的对象化说明。在传统农业社会即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类改造自然的力度非常有限,在人化自然之外是广阔的自在自然,这种外部现实映现在人的头脑中,就使得人不可能把现实世界看成是自己实践的产物。为了体悟这种世界观,我们现代人不妨设想一下自己站在荒野里只能见到一处低矮草房时的意识状态——这时的我们只觉得人是茫茫大地中的一粒蜉蝣,而决不是玩转地球的智慧生物。对此卢卡奇说得好:“在封建社会中,人还不可能看到自己是社会的存在物,因为他的社会关系还主要是自然关系。”[3]总之,不是说古代人不靠实践来生存,而是说实践程度的低下使得他们不能把实践理解为人与世界的真实关系。
在漫长的中世纪,呈现于眼前的世界都是极为原始的、刚刚打上人类活动烙印的自然,他们所对象化的人的存在特质,只能是静态的宗教、道德、意识、语言等。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去批评古代的抽象人性论和唯心史观,是犯了一种非历史地理解思想的错误;在古代如果能有“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样的思想,反倒是错的——因为它不是对真实社会存在的思想反映。只是到了大工业时期,才可能产生历史唯物主义。《共产党宣言》写道:“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4]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尤其是机器大工业时代,对自然的改造不再是悠然的“何妨吟啸且徐行”,而是急切的“敢叫日月换新天”。“资产阶级揭示了,在中世纪深受反动派称许的那种人力的野蛮使用,是以极端怠惰作为相应补充的。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哥特式教堂的奇迹”[4],而对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之根本变化的最好概括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与资本创造的这个社会阶段相比,一切从前的社会阶段都只表现为人类的地方性发展和对自然的崇拜。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5]由此我们就直接地抓住了资本主义社会之于哲学革命的真正杠杆意义——这样一种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整个地颠倒了人们对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解,自在自然已经变成了属人世界,而人在大规模改造世界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关系,就同时成为一个令人惊异的意识对象——“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4]。
说到底,“实践”与“社会关系”范畴的出现都是新世界观冲击旧世界观的结果,新世界把旧世界中只是以“花蕾”(借用黑格尔的著名隐喻来说)来表现的实践生存方式,以“果实”形式“显化”出来。“世界”再不是一个只能靠思想去直观的彼岸的异己神秘物(如康德的X),而是明确地表现为人类活动的产物,人自己的作品了。对此卢卡奇概括为“资产阶级社会实现了这种使社会社会化的过程”,“人成了本来意义上的社会存在物。社会对人说来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现实”[3]。马克思敏锐地把握住了这种社会存在变化对于社会意识变革的决定性意义,由此就构成了其对世界进行实践化理解的历史前提。反言之,看不到世界在其存在状态上的这种质变,正是费尔巴哈哲学的根本症结所在。费尔巴哈由于远离工业实践,“在乡间过着孤寂生活”,所以思想停滞于自然主义世界观,他缺乏真实的思想素材而不得不“从他的孤寂的头脑中”“产生出自己的思想”[6]。马克思恩格斯则在人类活动史的背景下正确地看到:“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数世纪以前由于商业才移植到我们这个地区。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7]马克思恩格斯开展人类学研究(乃至一切研究)的现代前提,一言以蔽之,就是大工业使人的实践性存在由隐而显。人虽然一方面从来就是改造自然的存在,但另一方面只有在大生产使得周围感性世界彻底人化时,才有足够成熟的条件认识自己和自己的祖先。下面我们就来分析马克思恩格斯带着这种现代视野,对人类祖先活动方式所作的探讨。
三、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论“实践”的发生:源于生存需要的劳动及其对象化结构
上述前提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研究的“前理解”。换言之,对古代社会的人表现为“不知不觉”的历史性存在方式,被马克思恩格斯自觉地把握为他们的“感性活动”。人的感性活动既是“物的人化”过程,也是“人的物化”过程,人与世界的这种特殊关系可以概括为“否定性统一”(高清海语)。在这种活动中,人以物的方式从事活动,换来的则是物以人的方式的存在。这就是马克思一定要把机器、厂房这些资本“物”当做社会关系来处理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人化思想是他们早年创立唯物史观的基石,是《资本论》的哲学基础,并且贯穿于晚年的人类学研究。比如,在马克思撰写《古代社会史笔记》之后,恩格斯遵照战友遗愿写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著作,进一步揭示了人和人类世界的产生之谜,为唯物史观奠定了一个更为坚实的科学基础。《自然辩证法》写道:“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边注:通过改良)。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6]恩格斯带着我们上文所分析的现代视野,揭示了人类和人类所生存的现实世界的形成原理。
恩格斯之后,现代人类学把人类产生谜题的求解又向前推进,从物种生理结构的角度揭示了实践“何以可能”和“只能如此”的问题。改良性的获取生存资料的方式,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人成为“万物灵长”的关键,但是追究其动因,这却是劣势转化而成的优势,是人类为了不致饿死而不得不采取的“无奈”之举。哲学人类学家兰德曼揭示道:“动物的器官适合于特殊的生活条件。”比如水中的鱼、林中的兽、空中的鸟,“然而人的器官没有为了某种行为被定向”,“对(人的)生命的进步来说,这初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不利条件”,“但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却更多地得到了多种多样的能力的补偿”[8]。人类无一物种之所长,则只好具备一切物种之所长——把整个自然界变成自己的无机身体。中国有句俗话说:“人都是给逼出来的。”按现代人类学的研究结论来说则是:“人类是给逼出来的。”即人这样一个特殊物种的产生,其本身是该物种对抗自然(“意图”消灭人)宿命的结果,是在与自然环境和其他物种的生存博弈中,为了不被淘汰,而又不具备其他物种(以身体器官高度适应环境的)生存优势的被动情况下,化被动为主动,变人类适应环境为环境服从人类的结果。只有人类才配说“万物皆备于我”。
在人走向改造自然以求得生存的漫长道路上,遵循用进废退的自然法则,人手、人脑等器官发生了从结构到功能的质变,意识逐渐产生,从而就有了人与天、我与外物的区分。而在动物的生存状态中,并没有“外物”与“我”的区分,没有明晰的自我意识,动物意义上的“外物”与“我”同样按照盲目的自然规律运动,不论是按无机界的规律还是生物本能。所以吸收了费尔巴哈人本学思想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就写道:“动物和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9]这就意味着,动物的存在不可能是“对象性形式”,尽管动物也会以筑巢、挖洞、捕猎等形式与外物进行物质能量交换,但它们不能在这些活动之外用意识去直观这些活动本身,不能把自己与自己的行为区别开来。对象性形式只能是人类对象性活动所采取的形式,即由意识自觉到的,并被当做本质生存结构予以发挥发展的物—人结构。在这样一种生存结构中,物被人化,成为人的活动的产物;人被物化,人只能通过改造物的方式来维持和确证自己的存在。人是并且一定是“对象化”的存在。总之,世界经人的活动的改造,打上了人的印记、变成文化产物,这种印记、人化特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明晰地显现出来,从而使得马克思恩格斯能够“通过人体解剖来达到猴体解剖”——科学地揭示人类产生之谜,最终在人类学研究中始源地描述出“物的人化”与“人的物化”过程,即人的原初的本质的“感性活动”过程。
四、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论“社会关系”的发生:劳动范畴的人与人关系维度及其异化
以上我们只是说明了人的存在的对象化形式,也即“物的人化”与“人的物化”的统一,而人的历史性、社会性特质尚未得到清晰的揭示。换言之,上述说明为了得出“人类整体”的特点而进行了理论抽象,暂时未讨论人与人的分工差异。但正是在社会化分工当中,人的社会历史本质凸显出来了,所以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人的“感性活动”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改造主体—改造客体”的二元结构,而是以社会关系为前提,并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社会关系的历史过程。如果仅仅从主客二元结构的层面来看,我们只能把马克思的新世界观理解成为以“‘改造’的二元结构”代替“‘认识’的二元结构”的“实践唯物主义”,而改造主体内部的复杂历史关联尚缺乏具体的说明。正如有的学者(刘福森强调得最多)所说的,这样理解马克思是不妥的,甚至有倒退到费尔巴哈人本学上去的危险——只是用抽象的“实践”结构作为解释原则取代“自然”、“上帝”、“理性”、“类本质”的结果,还是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是重新把人归结为具有某种永恒本性的形而上学。只有从“实践唯物主义”上升到“历史唯物主义”,只有把改造主体即人理解为处于不断变化中的、受特定社会关系制约的“现实的人”,才能达到马克思新世界观的真实高度。
实质上,被正确理解了的实践必然是历史的、社会的,“人的感性”活动过程正是社会关系建构发展的过程,这一点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人类学阐述中被表述为:“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7]展开来说就是,生产作为创造物质产品(“生活资料”)的过程,也就是创造出人类的社会关系(“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的过程;两者是同一个东西。这一点甚至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资本学说的重要枢纽,它贯穿于马克思恩格斯思考的全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得出“资本在再生产出商品的同时也再生产出剥削关系”的著名论断源于它,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考察劳动和语言在人的生成中的杠杆作用同样源于它。以后者为例,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节中,恩格斯说明了“人的活动”与“社会关系”的同一性。一方面,人具有改造世界这一共性的、根本的属性,进行着“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统治”;“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这些正在生成的人,已经达到彼此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了”,“语言从劳动中并和劳动一起产生出来”[6]。奠基于生存需要的“社会关系”初步结成,“社会关系”是与“人”一起产生的,不存在人之外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之外的人。它们都是人这一特殊物种以改造自然为生存之道的产物:“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6]这是我们解决“实践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定位之争的钥匙,因为在这里,恩格斯明确说明了“改造主体—改造客体”(劳动的“人—物”结构)与“改造主体—改造主体”(劳动的“人—人”结构)的统一、合题。限定在主客二元结构之中的“实践”,必须被理解为社会关系范畴、历史发展范畴;“实践唯物主义”必须被理解为“历史唯物主义”。所以当历史唯物主义提及“现实的人”的时候,“社会关系”就是“人”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种劳动的“人—人”关系首先就表现在所有权上,马克思认为:“最初的动物状态一终止,人对他周围的自然界的所有权,就总是事先通过他作为公社、家庭、氏族等等的成员的存在,通过他与其他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他和自然界的关系)间接地表现出来。”[10]由此我们已经看到了《资本论》通过考察物与物的关系来揭示人与人的关系的方法论。社会关系在最初产生时是基于原始共产主义的互助,距离鲜活的物种生存本能最近,但随着私有制的产生,社会关系发生了复杂的演变,阶级与阶级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对抗及其衍生出的各种对抗成为新社会关系的主导结构。这些对抗一直被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所掩盖,而根植于阶级对抗的道德、伦理、法律等则被说成了独立发展的东西、由“永恒理性”所推动的东西。但在唯物史观看来,社会关系的变迁和它的意识形态乔装,都是与人们改造世界的方式相伴而行的,这就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原理。原始的活生生的人与人的关系,在私有制条件下异化为脱离人类个体的抽象神秘的东西;这种异化在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达到了高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主体,而资本家和工人则成了它自我实现的工具,这就是黑格尔“无人身的理性”、“理性的狡计”的现实原型。这种异化、颠倒的秘密,被《资本论》中商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二因素——劳动的个别劳动与社会劳动的二重性辩证法所揭示,一言以蔽之,就是个别劳动只有表现为社会劳动、这个人与那个人的关系只有表现为个人与整个社会的关系,才能获得认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只能通过没有人味的普遍性中介(货币)才能实现,这就是异化。
在异化条件下,社会关系以其超越某个人个体的文化性、强制性、“先验性”特点,成为历史的本质结构。历史的本质结构并不是单个人的“感性活动”,而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不是单个人与单个人之间的“主体间性”,在他们发生一定的特殊关系之前,他们之间的联系早已经由“宿命”般的普遍关系所决定了;社会关系是事先决定、制约人们如何发生某一特殊联系的总的前提或传统,是由一定社会形态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作为内核的文化之网。比如“拼爹”,“爹”不是那个掌握社会特权的男人,而是使得特权大行其道的文化、因袭、体制、传统、集体无意识。再如资本主义社会,作为无产者个体的某某可以为甲资本家所雇佣,也可以为乙、丙、丁资本家所雇佣,这就是一个看似偶然的“主体间性”选择;但他不能不被“大写”的资本家所雇佣,这就是超越于某某、甲、乙、丙、丁这些个体之上的社会关系的强制性。所以马克思才说:“个人在这里也只是作为一定的个人互相发生关系。”[5]“一定”走在了“个人”的前面,正是马克思对黑格尔“无人身的理性是历史的主体”这一歪曲但却异常深刻的思想的解密。
五、从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看阿尔都塞对“社会关系”概念的拒斥:深化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类解放思想
结构主义者阿尔都塞的最大理论贡献,就是对马克思关于社会关系的异化体超越于现实个体之上并反过来支配现实个体的思想的深度阐发。阿尔都塞为了强调上述马克思的重要发现,甚至批判和反对马克思关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提法。但正是在这里,阿尔都塞走向了对马克思人类学的误解与阉割。阿氏在《〈资本论〉的对象》一文中说:“真正的‘主体’(即构成过程的主体)并不是这些地位的占有者和职能的执行者。同一切表面现象相反,真正的主体不是天真的人类学的‘既定存在’的事实,不是‘具体的个体’,‘现实的人’,而是这些地位和职能的规定和分配。所以说,真正的‘主体’是这些规定者和分配者:生产关系(以及政治的和意识的社会关系)。但是,由于这是一些‘关系’,我们不能把它们设想为主体的范畴。如果任何人偶然想要把这些生产关系还原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还原为‘人的关系’,他就是在亵渎马克思的思想,因为只要我们对马克思的少数模糊不清的提法持真正的批判态度,我们就可以看到,马克思极其深刻地指出,生产关系(以及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不能还原为任何人类学意义上的主体间的关系。”[11]这表明,阿尔都塞成也“结构”,败也“结构”,他在强调结构—社会关系的异化形态的先验性的同时,把马克思的真正的人类学精华,即关于人与人恢复到直接性关系的宝贵思想也抛弃了。由此看来,他的反人道主义正是基于对马克思人类学的误解。
具体来说,阿尔都塞的激烈批判用一种术语上的“矫枉过正”警示人们,所谓“关系”不是张三向李四买了一袋盐、王二爱上了马六那样简单,而是在这些行为背后支配这些行动的社会结构。我们切勿将表面上人与人之间出于个体利益动机而发生的“关系”,径直理解成《资本论》意义上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毫无疑问,阿尔都塞以“结构”范畴为基点,把马克思超越于人本学唯物主义之上的思想精华提炼得很精彩;作为我们正确理解“社会关系”概念的参考,阿尔都塞的表述很有价值。但是,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确定,随同阿尔都塞一起抛弃马克思“人与人的关系”的提法则不可,因为那将意味着对马克思人类解放学说的误认。马克思在科学研究上揭露“人与人的关系”已经异化为敌视人的、控制人的“社会关系”的目的,决不是韦伯、涂尔干式的对社会现象的“中立观察”,而是自始至终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的不平则鸣。他揭示社会结构统治人的现象的目的,恰恰在于为打破这种人类个体受抽象统治的局面寻找出路,恰恰在于将黑格尔“无人身的理性”的跋扈置于个体自由之下的旨趣,即“在资产阶级社会里是过去支配现在,在共产主义社会里是现在支配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里,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共产主义运动“正是要消灭资产者的个性、独立性和自由”,“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可见,《共产党宣言》中的人类解放思想,奠基于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的实践—社会关系原理,它不仅仅满足于确认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用阿尔都塞的术语——结构)统治了个人这一事实,而是要用实践的力量再扬弃这一现实。
总之,马克思“人与人的关系”概念,正如阿尔都塞所说的,不是古典经济学家的一个个具有抽象共性的“经济人”、“理性人”出于自然意义上的互利需要而彼此发生的物质交换,但又不是阿尔都塞所说的,所谓根本无意义的“马克思的少数模糊不清的提法”。马克思非常清楚自己在说什么,他的社会关系概念是一个包含着深刻价值追求、具有历史内涵的哲学与科学范畴。首先,通过人类学考察我们已经证明,社会关系在起源上肯定发生于原始社会“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的事实,所以它奠基于实践,而不是一诞生就是神秘的“无人身的理性”(黑格尔)或“结构”(阿尔都塞)。其次,社会关系在其发展过程中特别是进入私有制阶段之后,又异化为统治人特别是劳动阶级的抽象力量,这种异化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中表现为个别劳动只有表现为社会劳动时才能实现自身,从而使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成为一个能够被清楚地认识到的对象,如马克思所说:“最初作为促进生产的手段出现的东西,成了一种对生产者来说是异己的关系。”[5]再次,被私有制条件所控制的活生生的个体的社会关系,既然是人与人的关系的异化,它就在价值论上应当被新型的人与人的关系所扬弃,因而马克思强调“只有在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12]。显然,这一点被阿尔都塞忽视了,进而他怎么也不能理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是一种人道主义。马克思在使用“人与人的关系”、“社会关系”概念时,赋予其的含义是复杂而深刻的。在分析资本主义的过程中既有对其抽象统治个体这一事实的科学描述,也有对其价值论上的尖锐批判。阿尔都塞紧紧盯着前者,遗漏了后者。被阿尔都塞拒斥的“人类学意义上的主体间的关系”,正是马克思所渴望的对“生产关系”这一异化体的扬弃,正是马克思解放论的立足点。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及其学科建设研究”和2012年吉林省教育厅社会科学研究“十二五”规划专项课题“作为批判理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定位与逻辑”阶段性成果。)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2]孔扬,姜大云.把“世界”理解为“历史”的理论意义与三重前提[J].长白学刊,2011,(6):32—37.
[3][匈]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8][德]兰德曼.哲学人类学[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
[9]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11][法]阿尔都塞,巴里巴尔.读《资本论》[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12]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 吕学文
(E-mail:dalishi_sohu@sohu.com)
A81
A
1007-905X(2012)04-0037-05
2011-11-13
孔扬(1978— ),男,吉林东丰人,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空军航空大学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
——重读阿尔都塞的《论青年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