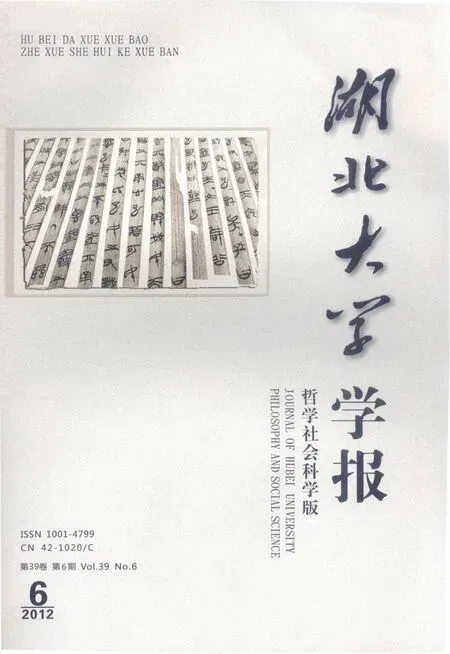论湘军的楚文化小说
李 莉
(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 恩施 445000)
湖南作家获得“湘军”美誉始于20世纪80年代。通览湘军的代表性作品,显示出一个不可忽视的共同特点——氤氲于文本的浓郁的楚文化气息。楚文化构筑了湘军的创作内核,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楚文化小说,突出表现在对楚地民间歌谣、巫术信仰、生活习俗及爱国忧民、方言土语的倾情书写与张扬等方面。
一、楚地歌谣俗语的穿插与引用
沈从文早期的小说如《边城》、《萧萧》、《长河》、《三三》等作品引入大量湘西民间歌谣、婚俗、葬俗、礼仪、方言土语等,建构了梦幻般的“湘西世界”,以地域文化作为独特视角开创了湘军特色写作的先河。新时期的古华、蔡测海、叶蔚林、刘舰平、彭见明、韩少功等作家都有承继,民间歌谣俗语成为其小说创作不可或缺的组素,浸透着深厚楚文化内涵的现实生活在如诉如泣的歌声中揭开面纱。
蔡测海《远处的伐木声》中通过民歌表达改革开放初期山村女子对美好爱情和未来的憧憬:“太阳出来照白岩,白岩上头晒花鞋,花鞋再乖我不爱,只爱你姐好人才——哎!”这首古木河上飘来的情歌给充满朝气的山村女孩阳春提供了新的生活信息。歌声召唤着她勇敢打破父亲和未婚夫古板僵化的规矩,义无反顾地走出大山,走向新生活。叶蔚林《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运用山歌民谣,刻画人物性格,增加文本的浪漫气息。放排人石牯心爱的恋人被抢走,他哼唱情歌解忧愁:“我带来镯子,你的手在哪里?我带来绸衫,你的身子却属于别人!你若还是有情,就来见面;见一面,我死也甘心……”楚地男人对爱情的执著可见一斑。韩少功的《爸爸爸》、《女女女》、《马桥词典》等作品有大量的古民歌唱出了楚文化的渊源。民族历史和文化在代代相传的吟唱中相互告知、传播、传承。
古华在山歌民谣的熟悉、理解、描述等方面展示了杰出才能。他那些反映湘南农村生活的小说不厌其详地引述了当地山歌民谣。其长篇代表作《芙蓉镇》以风俗描画著称,作家热情洋溢地将五岭山区的风俗歌《喜歌堂》引入文本。《喜歌堂》内容丰富,曲调繁复,既有山歌的朴素、风趣,又有瑶歌的清丽、柔婉。被打成“黑五类”的秦书田,借唱《喜歌堂》明示同情胡玉音的不幸婚姻,实则暗示自己对她的爱恋:“蜡烛点火绿又青,陪伴妹妹唱几声,唱起苦情心打颤,眼里插针泪水深……”当两人冲破重围相爱同居后同样唱《喜歌堂》倾诉衷肠:“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块门板背起走。生成的八字铸成的命,清水浊水混着流。陪姐流干眼窝泪,难解我姐忧和愁……”歌词皮相看是反映女子对包办婚姻的无奈,此在的含义却表达了两颗饱经磨难的心对爱的忠贞不渝。古华的另一中篇《贞女》中也不乏表达相思之情的民歌,如以一天十二个时辰为分节的《想姐歌》就是歌颂反叛传统婚姻的青年男女为自由恋爱而献身的感天动地的精神:“酉时想姐黑了天,为弟坐在大山边,月宫嫦娥看见了,也要落泪到人间!”然而小说主人公青玉对真爱的追求被横刀斩断,受制于贞节牌坊的重压而将青春年华葬送于大媳妇小丈夫式的等郎婚:“大媳妇,小丈夫,媳妇大了奶突突,丈夫小了只爱哭!要你耍,用爪抓,要你摸,用拳打!要你学个男人样,你爬在枕边打呼呼……”民歌以戏谑的方式将夫权的沉重、害人手段的残酷以及女人婚姻的辛酸深刻地揭示出来,是民间真正的黑色幽默。
古华将大量民歌应用于创作,书写民间风俗,旨在“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力求写出南国乡村的生活色彩和生活情调来”[1]213。作家在《芙蓉镇·后记》和《话说〈芙蓉镇〉》等文章中都阐述过这一观点。其包涵的创作理念既规避了主流话语对创作主体审美理想的干预,又借文化的民间力量和美学魅力委婉表达了创作主体对主流话语的真实态度。它不但反映了古华的审美理想,也是对现代湘军审美理想的经典概括。古华之前的沈从文、周立波,之后的韩少功、彭见明等,无不是将丰富的风俗民情融入文本,通过独特的楚地文化在主人公人生舞台上的尽情演绎展示社会历史的风云变幻。古华随后十余年内井喷式集中写作的三十余部(篇)小说,有力实证了地域文化赋予文学以鲜明地域色彩所具备的渗染功力:以风俗民情调侃政治的荒诞,以生活色彩装点民间的苦难,以生活情调寄寓未来的希望。
二、楚地巫术信仰的书写与关照
古华不仅熟悉民歌,对楚地的巫风医药也了如指掌。《“九十九堆”礼俗》叙述了寡妇杨梅姐与游医刘药先以“祖传医药”为媒产生的情感故事。“神医”刘药先,开着“三来灵药铺”。他在雾界山百十里山场享有“妙手回春”、“药到病除”的名气,而众口一词的传言又为人物“增魅”,增魅产生神秘,神秘产生神力,神力胁镇人心。杨梅姐被刘药先吸引并以身相许,当刘的真相揭穿后她无奈逃婚。
如果说古华揭示的是民间“神医”如何利用民众的善良博取名利,那么彭见明的《天眼》则叙述了一对父子因恪守“巫道”而历尽曲折的故事。楚地巫风盛行,数千年的时间之流冲洗了无数的文化事象,却也有诸如“看相、算命、测字、卜卦、看风水、选阴宅、画符水、给小孩治跌打损伤、收惊吓”等巫术被保存下来,变换身姿与时俱进。何了凡、何半音父子是当地有名的算命、看相、测字巫师。不经意的测算显出异常灵验的结果。名声大振的他们从乡村游巫转为定居县城的专业巫师,灵验的测算技能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甚至为当地经济发展带来新的机遇。他们诚信、仁义、厚道、薄利、固守本分的美德获得朋友的真心相助;他们也在帮助朋友的过程中遭遇挫折和不测,甚至家破人亡。何了凡父子辗转于战场、官场、商场、情场、神场,出生入死,审察人生。小说从楚文化视角揭示人生最神秘莫测最难以捉摸的“命”,通过“命”阐述生命的贵贱根由及其存在的合法性和合理性,从个体的“命”的变化演绎出社会的发展变化,展示官场、商场、情场和神场的百态世相。
彭见明在其长篇小说《天眼》的创作随感中曾这样说,他之所以选择看似怪诞的“巫道”切入楚文化,是因为他“最早接触的‘文化’,便是遍布于天南地北广袤乡野的巫道文化”,“敬神信巫带来的另一个普遍心理便是‘认命’。我们乡间一俟谈到人生这个有些沉重的话题,用得最多的是‘命’这个字”[2]164。作为地道的楚文化小说,作家的创作动机并非宣扬楚地巫术,或是猎奇以吸引读者眼球,而是“通过这个窗口去关照社会生态,将会很广阔、很深邃、很细微、很有趣,甚至很‘搞笑’很‘草根’”[2]164。事实上,楚地巫术存活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们信之,便得安慰,很多事情就会去努力并因此获得成功。换句话说,巫术医治人心。人们一旦明白“相由心生”、“相随心变”的心、相、命概念,精神上便有寄托,社会便能在相应的规则内稳定发展。文本借生存于最底层的“搞笑”的“草根”的活态文化,以具象的个体的方式诠释抽象的普遍的社会形态、社会情绪和社会心理,其深意也由此彰显。
唐浩明的长篇历史小说《曾国藩》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深受楚文化濡染和影响的历史人物曾国藩。一般的历史只能书写他明朗理性的皮相,小说却可以揭示他神秘莫测的内相。巫术信仰贯穿于曾国藩生命的始终,也贯穿在三卷本小说里。如曾国藩是蟒蛇精投胎的传说预示人生的非同凡响;丁忧时他相信道人为母坟选择的是能出将相的风水宝地而毅然出山;带湘勇出征前为图吉利他举行隆重的“血祭”仪式;祁门遭遇四面楚歌他亲自“卜卦问吉凶”;一遇心神不定情绪郁结他就会做种种怪梦;当他元气耗尽生命走向终结时天空竟降下倾盆黑雨。人心难以测算的关键性事件和人力无法把握的命运出现转折时,巫术的吉凶往往预示某种迹象,或让人定心定力,或让人灵魂震撼。伴随曾国藩一生的难以用科学解释的诸多巫术行为,不但为曾国藩曲折复杂的经历增玄添魅,也为小说罩上一层魔幻外衣,产生了怪诞而神秘的阅读美感。
此外,楚文化的巫医信仰在土家族作家孙健忠的部分小说如《猖鬼》、《烧龙》、《倾斜的湘西》中也不乏阐释;韩少功的《北门口预言》、《女女女》等作品也涉及了生活中一些看似莫名其妙的诡异现象。
三、楚地生活习俗的描摹与展示
楚地有很多不同其他地方的生活习俗。张正明在《楚文化史》中认为:楚人饮食嗜好是“调味以辛辣酸甜为佳”、“生则厚养,死则厚葬”[3]292~293。这就形成了楚人独特的饮食观和丧葬观。湖南人重视吃,注重吃的味道。湘军的很多小说都把辣椒作为饮食的重要内容,隐喻湖南人的辣椒性格。香辣可口的饭菜不但对人们生活、劳动热情产生重要作用,还能留有大方的好口碑,其地位已从日常饮食升华到社交关系、私人感情甚至思想政治等层面。
唐浩明在《曾国藩》中将人物命运和政治前途与楚地的饮食、丧葬等礼仪交织叙述。曾国藩回乡奔丧,岳阳楼上那油焖香葱白豆腐、红椒炒玉兰片、茭瓜丝加捆鸡条等菜肴“红白青翠、飘香喷辣”,加上晶莹的大米饭、地道的君山毛尖茶,让离湘十余年身心疲惫的他发出了“还是家乡好”的感叹!历尽艰险赶到家,见到的是母亲隆重庄严的丧礼。“整个灵堂变得灰蒙蒙的,只有一些质地较好的浅色绸缎,在附近的烛光照耀下,鬼火般地闪烁着冷幽幽的光。换香火、剪烛头、焚钱纸、倒茶水的人川流不息,一概浑身缟素,蹑手蹑脚。灵堂里充满着浓重而神秘的气氛。”这是规格颇高的湘中丧葬风俗,小说详尽描绘灵堂内外的布置和活动,突出曾氏家族的显赫和地位的高贵。母丧迫使刚任新职的曾国藩回乡,母坟选择的吉地又促使他下定决心墨绖出山,督办团练创建湘军,改变了人生航向。五年后他再奔父丧,趁机摆脱了诸多危险。这些丧礼均为其充满波折的命运和富有争议的一生埋下伏笔。楚地民俗文化不仅可以改变个体人物命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家和社会历史的发展进程,其作用不可谓不大矣。
古华《贞女》则是一部楚地婚丧喜庆志书。其中有两场丧事和一场婚事让作家花了不少笔墨。青玉的小丈夫少年夭折,“没办大丧”,但青玉还是要为之“带重孝”,守节八年的青玉抑郁而死。“节妇去世,萧姓全族中人,立即各各行动,报官的报官,置灵屋的置灵屋,以及备办香烛、纸钱、三牲、旌幡、酒席等等。萧四太爷发下话来,杨氏守节八载,完成功德,实仰仗列祖列宗荫德,故此应大开祠堂,既葬节妇,又祭祖宗,以振萧族家风名节。”在萧家看来,节妇的性命无关紧要,她活着就是为了死后能在名节上替萧氏家族争光斗志。其死比活重要,所以给节妇举办隆重丧礼实在无上荣光;为节妇立牌坊的计划却因辛亥革命的爆发而终止。作家采取对比手法,将新旧两个时期两种不同境况的葬礼放在同一文本中,进一步透析传统对人们生活的深远影响。桂花姐丈夫吴老大酒后驾车身亡,族人误认为是因其妻有外遇而造成的,便采取“古老的惩办害夫淫妇的习俗”,先是将尸体运回抬进到他们自己创办的酒店正堂里,炸鞭炮、贴白对联,“停尸办案”,再召集族人采挖屋后的黄土封埋酒店。陋俗最终被新思想新观念制止。这两种葬俗的结果意味着:阻碍社会前进的旧俗终会被时代的新浪潮吞噬。文本写作的意义在于:作为历史遗迹,民俗也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沉浮,其兴衰更能引起人们思索。
丧夫的桂花姐几年后找到新爱,举行热热闹闹的婚礼。酒店彩带装饰,播放有立体声迪斯科音乐,“也请有一班手执唢呐、铜钹、板胡、箫笙的民间吹鼓手,洋曲土乐相映成趣”。司仪和一班后生小伙还出了许多新式节目“为难”这对新人。土洋结合、新旧结合的婚礼正是社会转型期农村婚礼的真实写照。人们需要传统,却又不满足于传统,于是新花样层出不穷,文化也在这些“花样”里延续发展。因时代和人物身份的不同,风俗的形式也有差异。风俗的变化揭示了社会制度的演变以及由此带来的人物性格、命运的变化。文本将桂花姐的命运设置于一悲一喜的风俗中,既反映了传统风俗和观念对人们的影响,也反映了时代的重大变化和妇女社会地位的变化。女人生活的幸福与否,除了要靠自身的努力外,社会观念和思想观念的进步与解放所产生的作用力和约束力尤为重要。
湘军小说,除反映上述特征鲜明而浓郁的楚文化外,还贯穿着爱国忧民的传统,念祖、爱国、忠君,“由此养成了异常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3]109。唐浩明塑造的曾国藩、张之洞、杨度都是对社会对国家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尽管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有些仍未定论,但骨子里的精忠报国、维护国家稳定发展等理念正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写照。何立伟的“青春”小说、王跃文的“官场”系列小说、向本贵的“乡土”小说、聂鑫森的“佛事”短篇等作品都从不同视角将爱国忧民思想用不同形式表达出来,体现了作家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以及对底层劳动者的关注。残雪的小说则特别注重用新的表现手法挖掘人物内心世界,其代表作《上山的小屋》将现实世界的孤独与人物幻象、潜意识深处某种情感纠葛交织,以意识流凸显现代人的心理危机与情感危机。
湘军小说语言讲究张力和个性。何顿颇具典型,其小说语言穿透力极强,常用简洁的语言刻画鄙俗却又很有特性的底层个体者形象,透视他们的生活观念和思想观念。如中篇《生活无罪》里的狗子就很典型:“他赚钱有股疯劲,他用钱更疯,野兽般啃嚼着生活”;“好像太阳是从背后升起来的一般,妻子注定就是个不守洁的雌猫”。这就将改革开放时期人们对金钱的极度追求与极度挥霍、对情感的迫切需要又随意处置真实地再现出来。至于方言、俗语,作为楚文化的重要遗存,湘军的小说并不吝啬使用。如水运宪《祸起萧墙》擅长用方言刻画人物性格:“曾部长闪烁着明亮的眼睛,并不为别人所左右:‘都晓得都晓得。我哩电业局已经正式任命嘎哒,名单也正式报你们局哒。无么大个事,你哩招呼都无得一个就来嘎哒?太随便哒吧?我哩咯里又不是菜园门!’”一个讲究原则的干部形象跃然纸上。方言是地域文化之镜与灯,最贴近生活和人物性格,保持了语言的原生态,捍卫了语言文化的多彩情态。
综上所述,楚文化内涵经过湘军的审美处理,总括为四种:敢爱敢恨的情爱文化,敬神信鬼的巫术文化,忧国忧民的政治文化,方言楚语的语言文化。其核心精神,则表现在崇尚自然、捍卫传统、刻苦勤俭、破旧立新、开拓进取等方面。与此相应,别具一格的楚文化小说的艺术特质也可概述为三个方面:第一,文本中氤氲着神秘浪漫的气息,敬畏神灵的巫医文化以及仪式信仰为神人交流提供了平台,事件在现实与虚幻中交织发展,情感在真实与虚构中共存共生。如彭见明刻画的何了凡、何半音父子超凡脱俗的生活态度,及其测字算命、看相卜运之灵验的技能非有如此文化土壤不能纵情抒写。第二,为揭示人物性格命运的复杂与多变,作家善于将大量的心理分析与心理描写穿插于不同场景。如唐浩明刻画曾国藩性格的多重与复杂,就是在种种神秘文化如血祭、卜卦、梦境中展开。他既有刚毅顽强、忠诚廉正、重友笃情、深谋远虑、识才治学之品性,也有阴险狡诈、心狠手辣、自利自私、忧郁矛盾之一面,真实的丰满的曾国藩呼之欲出。第三,多彩多姿的民间文化的叙述,打破了过于严肃的沉闷的主流话语主宰文本的僵化模式,使文本呈现轻松活泼、幽默欢快的基调,彰显民间的乐天精神。如《芙蓉镇》、《贞女》等文本,虽有沉重苦闷的政治环境和历史事件,可一旦与民间文化联袂,人物心情和命运就会迅速逆转,文本基调乐观向上。
湘军楚文化小说的这些特质构成了其他地域小说难以具备的独特的“这一个”。个性成就了文本的独特性,也成就了文本的独特贡献。湘军楚文化小说的贡献突出表现在:第一,以艺术的形式抒写楚文化的斑斓多姿,为楚文化的传承延展提供了生动文本,也为文化的多样性存在及其保护和发展提供了艺术范例,为弘扬中华文化作出了应有贡献;第二,将人物,特别是历史人物性格置放于文化语境中考察,不但增添了文本的文化韵味,还原了人物真实性,而且为正确评判历史人物提供了文化依据和史料依据,同时,也为重估历史、重写文学史提供了参照;第三,各类小说刻画的人物形象从不同层面诠释了湖南人的风采和个性、脾气和精神,即人们普遍认同的辣椒性格、骡子精神,丰富了中国文学人物画廊;第四,地域方言的妙用、意识流小说的写作、“官场”题材的开拓、“词典体”等文体的创新显示了湘军在文学创作中既坚守优质传统又敢于创新的精神,为其他地域文学乃至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 古华.芙蓉镇·后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 彭见明.伟大的坚韧和无奈的羡慕[J].长篇小说选刊,2009,(2).
[3] 张正明.楚文化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