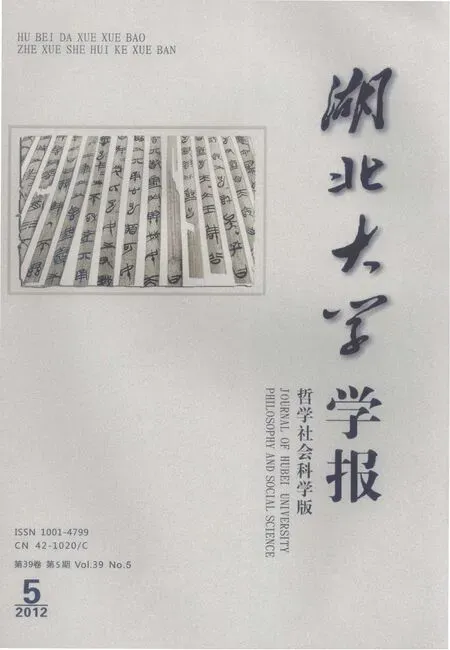“后殖民主义”的历史语义学考察
熊 伟
(武汉大学外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一书中,采用历史语义学方法,对英语里的一些具有争议且备受关注的“关键词”(如“资本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等)的词义起源、流变、“过去”与“现在”的关联性和变化性进行了记录、探源和质询。他衡量“关键词”的标准有二:一是在某些情境及诠释里,它们是重要且相关的词;二是在某些思想领域,它们是意味深长且具指示性的词[1]7。这些词的词义由于受到各种社会阶级力量的博弈、意识形态的操控而呈现出延续性和断裂性、不确定性和变异性,反映或阐释了不同的经验,并以相互关联却又相互冲突的形态持续下去。然而,威廉斯所开辟的事业还没有完成,因为“关键词”还在增加。其中之一就是“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postcolonialism)及其相关词汇“后殖民的”(post-colonial/postcolonial)、“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后殖民批评家”(postcolonialist)、“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等等。
滥觞于20世纪70年代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理论,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一种批判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文化关系的理论和批评策略的话语集合体。在其发展过程中,由于多种因素的介入,“后殖民主义”的概念变得异常复杂,飘忽不定,以至于后殖民理论家穆尔-吉尔伯特发出警告:“这一概念(后殖民主义)可能有内变为一个被任意切割的分析结构的危险……问题在于这一概念常被变动以适应于不同的历史时刻、地理区域、文化身份、政治境况和从属关系以及阅读实践。结果,就对把某些地区、时期、社会-政治构成和文化实践看作‘真正’后殖民是否正确产生了日益热烈甚至是激烈的争论……这些冲突已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仍让人怀疑,后殖民批评现在是否已经分裂为一系列相互竞争、互不相容甚至对抗的实践。”[2]8~9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从各自角度和立场争说“后殖民主义”。然而,在众声喧哗中,“后殖民主义”的涵义却越发模糊不清了。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后殖民主义”进行历史语义学考察,以期尽可能全面地理解“后殖民主义”的“名”与“实”。
一、后-殖民主义,抑或后殖民主义?
名不正,则言不顺。“后殖民主义”意义的异质性、含混性和不确定性,其实从其“名”就开始了。“后殖民主义”的英文单词有两种拼写法:没有连字符的postcolonialism和有连字符的post-colonialism。虽然两种拼写法都可接受,但它们所表达的思想、理念却有所不同,且都有模糊之处。遗憾的是,很多人并不十分了解两者间的差异,使用也颇为随意。
在英文中,post-作为一个前缀经常与名词、动词和形容词结合使用,来表达时间或次序之“后”。所以,顾名思义,post-colonialism意味着殖民主义之“后”。然而,很多学者认为,该词有“名不副实”之嫌,因为它掩盖了殖民历史的延续性,事实上很多前殖民地在取得独立后仍然受到前宗主国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控制。因此,post-colonialism的涵义还应包括“前”殖民历史,以显示一个“持续不断的抵抗和重构的过程”。而去掉连字符的postcolonialism则同其他众多后学理论,如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一样,代表着一种与“以前几乎完全不同的意识状态”[3]284。但问题是,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其实并没有彻底地与结构主义、现代主义分道扬镳,而是分别脱胎于后者,是对后者的继承、反拨和超越。美国著名批评家哈桑就明确指出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之间的继承与断裂关系,“现代主义的变化可以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现代主义并非突然中止后才能让后现代主义诞生,它们目前是共存的”[4]446。顺此思路,将后殖民主义理解为是与殖民主义几乎完全不同的意识状态也是令人生疑的。
澳大利亚后殖民理论家阿什克罗夫特对有无连字符的“后殖民的”(post-colonial/postcolonial)进行了区分[5]。他认为,两者虽然具有很多相似的政治和文化理念,但post-colonial更加凸显了这些理念。post和colonial之间的连字符是一种关于特殊性的陈述,代表着某种基于历史和文化的经验特质。它以一种特殊的“清空”姿态(“space-clearing”gesture),表明后殖民阅读和写作中所呈现出来的日益多样化的理念、重点、策略和实践。post-colonialism强调了殖民主义历史“事实”的话语和物质影响,而postcolonialism则更多地代表了一种对文化差异和各种边缘化不加区分的对待和关注,无论其是否是殖民主义历史经验的结果。post-colonial和postcolonial之间的差异有时可以简单地区分为:前者代表着英联邦的文学遗产,而后者则代表着殖民话语理论。但是,阿什克罗夫特认为这种区分过于简单化,因为post-colonial特有的物质和历史经验不仅仅只局限于文学领域,其使用范围应更为广泛,所以,最好将post-colonial理解成为是一种试图抵制优势话语相对于殖民地社会的话语实践、文本实践的优势地位的政治行动。
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h),还是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n)?到底采用哪种形式,看来是个问题。形式上的不同昭示着意义上的不确定性。
二、时间概念,抑或历史状况?
后殖民主义是一种时间概念,还是一种历史状况?这个问题的提出在相当大程度上是由“后殖民(主义)”的“后”所惹的“祸”。
“后殖民”一词最早见诸于20世纪70年代前期的政治学理论中,“用以形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摆脱了欧洲帝国束缚的国家的尴尬处境”[2]6。后殖民国家是指那些在六七十年代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此处,“后殖民”很显然主要是一个时间概念。而作为文化批评理论意义上的“后殖民”则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的西方有关文学和文化批评的学术刊物和著作中。例如,在比尔·阿什克罗夫特、加雷斯·格里菲思、海伦·蒂芬所编写的《逆写帝国:后殖民文学的理论与实践》(The Empire Writes Back: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1989),以及伊恩·亚当和海伦·蒂芬所著的《超越最后一站: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理论》(Past the Last Post:Theorizing Post-Colonialism and Post-Modernism,1990)两书的副标题中,就分别出现了post-colonial和post-colonialism两词。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两个术语逐渐在各种学术写作中流行开来,并尤指英帝国以前殖民地的文学。那么,后殖民主义到底是指一种时间概念,还是一种历史状况呢?中外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些学者将后殖民主义主要视为是一种时间概念。王岳川认为后殖民主义是“一种多元文化理论,主要研究殖民时期之‘后’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文化话语权力关系,以及有关种族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国家民族文化、文化权力身份等新问题”[6]9。从其表述来看,“后殖民”时间概念的意味颇浓。鲁宾逊认为后殖民研究的范围具有争议性,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定义,其中之一是对“欧洲的前殖民地独立后的研究;他们如何在独立期间回应、顺应、抵抗或克服殖民主义的文化遗产。‘后殖民’这里指的是殖民主义结束之后,其所涵盖的历史时期大致上是二十世纪下半叶”[7]13。很显然,“后殖民”具有时间划分的涵义。
但是,很多学者对“后殖民(的)”一词颇为不满,因为它暗含着历史的断裂性,还掩盖了后殖民地域上的复杂性。一般认为,殖民主义主要依靠政治、军事、经济等力量对殖民地进行征服和统治,而后殖民主义则转而运用文化策略。但事实上,文化的影响力贯穿着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历史,是绵延不绝的。正如穆尔-吉尔伯特所言,“后殖民”一词被用来描述“从殖民化时期到现阶段(欧洲)帝国统治过程对文化的所有影响”[2]6。肯尼迪也认为,“后殖民(的)”错误地暗示着“西方对于非西方国家统治和剥削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不过殖民主义虽然已经废弃,但全球性的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却在继续绵延”[8]89。鲁宾逊对后殖民研究的另一个定义是对“欧洲前殖民地自殖民以来的研究;他们如何回应、顺应、抵抗或克服自殖民主义之始的文化遗产。‘后殖民’这里指的是殖民主义开始后的文化,其所涵盖的历史时期大约是始于16世纪的现代时期”[7]13~14。盛宁则从“新”问题和“新”认识两方面来理解“后殖民主义”的“后”,以显示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的相关性。它是一个在所谓殖民地、殖民主义问题解决以后又产生的新问题。所谓“新”,并不是“新”在问题上,不是指又出现了什么新的“问题”,而是指对于问题有“新”的认识[9]172。
从地域上看,将曾经受到帝国殖民统治的国家或地区,甚至将某个国家内部少数群体或族裔(如加拿大的魁北克)统统置于“后殖民(的)”这个术语下,就会抹杀或模糊移民殖民地(如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与非移民殖民地(如欧洲帝国在非洲、亚洲的殖民地)在时间与空间、历史与现状、政治与经济、社会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
因此,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之间并不存在着一个“前/后”的明确时间界限,况且人为地切割时间本身就是后殖民主义所反对的“本质主义”方法。后殖民主义也不是一个所指地域范围明确的概念,存在着种种不同的殖民地状况。所以,将“后殖民(的)”理解成为一种历史状况,而不是一种单纯的时间概念则更具有涵盖性和说服力。
三、新殖民主义,抑或后殖民主义?
一般认为,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理论主要是借重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和方法来揭露和批判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文化霸权,是从西方文化的边缘地带发起的,旨在消解中心的颠覆性话语,并试图以对话代替对抗的方式来重构东西方之间的文化关系。
然而,很多学者认为后殖民主义其实是一种打着反对西方文化霸权旗号的新殖民主义。阿赫默德指出后殖民主义是一种推行新殖民主义的手段,“借此西方对全球前帝国区域的影响现在得以在一个新殖民的‘世界新秩序’中再现,更确切地说它完全可以当作西方历史上欲凌驾于世界其他地区之上意愿的新的表述”,而后殖民理论家们则在学术领域里,“再现了由全球资本主义认可的当代国际劳动分工。按照这个观点,第三世界的文化生产者把‘原’料送入宗主国,再依赛义德的爱好主要为宗主国的文化精英转变为一种‘精’产品,实际上这些精英被当作主要的听众,一部分这样的著作接着再重新作为‘理论’出口到第三世界”[2]17~18。
杨乃乔对出口到第三世界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进行了更为猛烈地批评。他指出当后殖民主义理论旅行到东方汉语语境中时,就完全退变为新殖民主义:
一言以蔽之,原创后殖民主义理论侵入大陆后在文化身份上已经蜕化得非常复杂了,如果我们把肇事于西方拼音语境下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称之为原创后殖民主义理论,那么,进入东方汉语语境下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则是变体的后殖民主义理论,说得透彻些,变体后殖民主义话语在本质上就是新殖民主义(new colonialism)。所以,当我们在言说后殖民理论时,我们不仅受压迫于西方的话语权力之下,也更被压迫在那些于西方获取显赫学术地位并栖居于西方的第三世界的东方学人的话语权力之下。在这个意义的层面上,我们就理解了为什么后殖民主义在东方汉语语境下的变体就是十足的新殖民主义,也理解了为什么在东方汉语语境下根本就没有原创的后殖民主义理论,有的只能是新殖民主义,并且这种新殖民主义对东方汉语学术界的文化批评及文学批评有着既受西方又受东方的双重压迫,这就是东方学人借西方的话语权力压迫东方学人的诡计,只不过前者是中东学人,而后者是远东学人而已。新殖民主义不同于后殖民主义的本质就在于此。[10]
但是,第三世界或东方到底有没有原创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呢?杨乃乔所指的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者或批评家有两类人:一是具有欧美文化、文学和学术背景的学者。他们代表着西方的话语权力,如弗里德里克·詹明信、塞谬尔·亨廷顿、约翰·汤林森等。另一类人是生长在第三世界,但却在西方接受教育,获得显赫的学术地位,并在西方定居、工作和写作的第三世界的东方学人,如爱德华·萨义德、佳亚特里·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然而,还有一类在第三世界生活、工作和写作的后殖民批评家和作家,如艾贾兹·阿赫默德、奇努阿·阿契贝等,遗憾的是杨乃乔忽略了他们。前两类后殖民批评家之间虽也有差异,但大致上都可以划入西方文化圈,但第三类却是第三世界本土后殖民批评家。与前两类相比,他们在文化身份、教育背景、批评视角、理论方法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同。既然如此,又如何能说后殖民主义就是一种新殖民主义,以及第三世界就没有原创性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呢?因此,杨乃乔将后殖民主义视为是新殖民主义观点本身就忽略了后殖民主义的异质性。
必须注意的是,虽然不能将后殖民主义完全等同于新殖民主义,但是也不能否认后殖民主义中确实含有某些新殖民主义因素。一些具有第三世界背景的后殖民批评家,如爱德华·萨义德、佳亚特里·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他们在西方一流大学求学、深造,接受西方的学术训练,又在西方一流大学执教。他们充分利用自己第三世界的文化背景,并运用西方的语言(英语)和各种理论来建构自己的后殖民理论,在西方文化内部反戈一击,从而助其自身从“边缘”跻身西方学术和文化的“中心”。尽管对西方文化霸权进行了批判,但他们的理论归根结底还是一种西方学术话语,并不是第三世界批评家从第三世界的角度提出的反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理论。并且,在面向第三世界时,他们还不经意地流露出某种第一世界的自我优越感和文化优越感。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他们既是西方殖民主义的批判者,同时又不自觉地充当了新殖民主义的推行者。总之,我们应该用一种辨证的眼光来看待后殖民主义,既要看到后殖民主义批判和解构西方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积极的一面,但也不能忽略其作为一种新的西方话语对第三世界的渗透和影响。
对于什么是新殖民主义,以及与后殖民主义间存在何种关系,还另有他说。张法把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并列起来,并指出它们之间的发展逻辑:“后殖民主义的主词‘殖民’,自然而然地使不少后殖民主义论者从伴随着资本主义扩张的全球化的殖民主义来理出一条后殖民主义自身的发展逻辑。从这一角度看,有两段论(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和三段论(殖民主义、新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之分。”并且,张法的“新殖民主义”与杨乃乔所谓的“新殖民主义”涵义有所不同。张认为,“新殖民主义流行于冷战时期社会主义对前殖民地国家与西方关系的描述,即殖民地国家独立之后,西方用经济和文化方式继续对前殖民地国家进行统治。”他还将三者作了话语类型的区分:“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都是政治话语,而后殖民主义则是一种学术话语……后殖民主义理论是用一种新的观点和方法,去分析资本主义自扩张以来殖民者和被殖民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殖民时期和后殖民(按两段论后殖民包括新殖民)时期的演化。”[11]张法的观点有三点值得商榷。一是他的发展逻辑说,无论是三段论还是两段论,是否表明了后殖民主义是一个时间概念呢?再者,旨在对西方文化霸权进行批评的后殖民主义难道不是一种政治话语吗?其实,融政治与学术于一体本身就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重要特征。再次,既然新殖民主义是社会主义对前殖民地国家与西方关系的描述,作为西方理论话语的后殖民主义何以能将其囊括进来呢?众所周知,后殖民批评理论只是西方学术内部自身的扬弃和整合,产生的是另一种新的西方学术话语,其关注和解决的也只是西方文化内部自身的问题。
四、后殖民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孰先、孰后?
后殖民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虽然冠有同样的前缀“后”,但人们对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却有不同的见解。
很多学者将后殖民主义定位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版图中,认为后者是前者的理论序幕。其原因主要有二:首先,时间上的涵盖。后现代主义是一种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流行于七八十年代的西方艺术、社会文化和哲学思潮,而后殖民主义的标志性著作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再者,两者共有一些特征。如对宏大叙事的质疑、消解中心、异质性等等。正因如此,王岳川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后殖民主义的理论前导或理论基础,而后殖民主义是后现代主义的政治话语和文化话语的进一步延伸。”[6]127盛宁也认为:“后殖民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声音出现,应说是七十年代以后,甚至更晚些时候的事情,也正是基于这一点,它可以名正言顺地被收入后现代主义的视界,纳入后现代主义问题的讨论。”[9]172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后殖民主义肇始于后现代主义之前。阿什克罗夫特、格里菲思和蒂芬指出:“前殖民地边缘地区对西方宗主国中心发起的挑战,先于对统一的西方主体和中心的后现代拷问,因而应当被视为后现代思想的一个源泉。”[8]90穆尔-吉尔伯特对后殖民批评和理论的历史追溯为上述观点提供了翔实的论据:
后殖民批评和后殖民理论同样都包容了一系列实践,在全世界众多不同的公共机构的各种学科内进行。许多这些实践在“后殖民”这个词开始流行前很久就已产生,现在通常被追溯为或勉强作为文化分析的后殖民模式。任何斗胆要编写这些实践历史的人都可能至少要从20世纪初开始,要从这样一些不同人物的著作写起,像非洲裔美国思想家W.E.B杜波依斯和南非思想家索尔·普拉杰(Sol Plaatjie)这些人(有人认为还可再早些)。她或是他需要研讨各式各样的文化类型,诸如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和20年代的哈莱姆文艺复兴以及四五十年代的黑人文化运动。这样的一部历史需要提到地理、思想和文化背景不同的各种人,比如大部分时间住在伦敦的特立里达人C.L.R詹姆斯,最初来自马提尼克岛但又是阿尔及利亚革命积极参加者的法朗兹·法侬,还有非洲的批评家钦努阿·阿契贝、安塔·狄奥普(Anta Diop),长期住在澳大利亚的印度史学家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为了公正地评判这段其“影响和发展”从未被适当叙述的历史,还需要注意一些拉丁美洲批评家的观点、60至70年代“英联邦”文学的研究以及以非欧洲语言写成的各种美学理论,现在这些都被当作后殖民批评的先驱。[2]1~2
后殖民主义理论具有多学科和跨学科的性质。它杂糅了法侬的民族文化理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利奥塔对宏大叙事的质疑、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巴赫金的对话理论、福柯的知识/权力/话语等理论,与后现代主义相互交错,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又各有不同。因此,简单地去争论后殖民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先后关系是没有意义的。
威廉斯认为,“从语言的任何准则来看,没有哪一个团体是‘错的’,虽然短暂时间里,居于主流的团体会强调自己的用法是‘正确的’。通过这些语词上的交锋、对立……实际上就是一种语言发展的重要过程:某一些语词、语调、节奏及意义被赋予、感觉、检试、证实、确认、肯定、限定与改变的过程”[1]2。他关于语词意义的流变性观点与后结构主义的意义不确定性观点不谋而合。此外,由于对弱势阶级和非主流文化怀有极大的同情之心,他尤其重视语词的被边缘化了的意义,因为“在社会史中,许多重要的词义都是由优势阶级所形塑,大部分是由某些行业所操控,因此有些词义被边缘化”[1]18。这些观点为考察“后殖民主义”的词义的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对“后殖民主义”及其相关词汇进行历史语义学考察,我们发现“后殖民主义”一词的涵义在其历史演变过程中呈现出多义性、变异性和矛盾性的特点,这反映了具有不同文化身份、学术背景、政治理念、阶级利益、意识形态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家在该词词义上的争执和博弈。他们都力图将“后殖民主义”这个漂浮的能指锚定到他们所期望的所指上。或许随着时间的推移,争议还将持续下去。
[1] 雷蒙·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刘建基,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
[2] 巴特·穆尔-吉尔伯特.后殖民理论[M].陈仲丹,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
[3] 朱刚.二十世纪西方文艺批评理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4] 李维屏.英美现代主义文学概观[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8.
[5] Bill Ashcroft,Bill.On the Hyphen in‘Post-Colonial’[J].New Literature Review,1996,(32).
[6] 王岳川.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7] Douglas Robinson.Translation and Empire:Postcolonial Theories Explained[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7.
[8] 瓦莱丽·肯尼迪.萨义德[M].李自修,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9] 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M].北京:三联书店,1997.
[10] 杨乃乔.后殖民主义还是新殖民主义?[J].人文杂志,1999,(1).
[11] 张法.论后殖民理论[J].教学与研究,1999,(1).
——评《后殖民女性主义视阈中的马琳·诺比斯·菲利普诗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