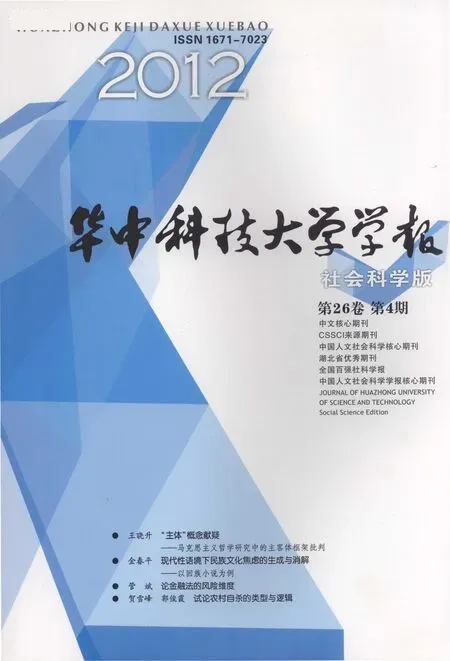谁的意志 谁的利益①——传统法视野下法律统治阶级意志论新辨
谢红星,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江西南昌 330013
谁的意志 谁的利益①
——传统法视野下法律统治阶级意志论新辨
谢红星,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江西南昌 330013
传统中国君主专制的政治形态下,君主权力几近不受约束,立法者尤其是最高立法者个人之偏见、情感、私利可毫无阻碍地作用于立法活动,法律背离统治阶级整体意志,遂成寻常之事。传统中国法律经常背离统治阶级意志的历史事实说明,法律反映统治阶级意志这一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命题,具有实然与应然双重意义,近代以前其意义多为应然,近代以后随着民主政治的建立、完善,其意义则由应然逐渐转为实然。近代民主政治的建立,是法律反映统治阶级意志成为实然之根本前提。
整体意志;立法痼疾;实然;应然
一、引言
法律是一定社会统治阶级意志的产物,这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基本观点。这里的统治阶级意志是“整体意志”,而非统治阶级中单个人或一小部分人的意志,正如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称,“这些人通过法律形式来实现自己的意志,同时使其不受他们之中任何一个单个人的任性所左右,这一点不取决于他们的意志,如同他们的体重不取决于他们的唯心主义的意志或任性一样”,“由他们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的体现,就是法律”[1]377-379。从马克思的表述来看,马克思显然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整体意志的体现。
然而,马克思主义法学虽认为法律是统治阶级整体意志的体现,但也并未否认统治阶级中个别人的意志、小集团部分人的意志等非整体意志对法律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唯物辩证法的哲学,而从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看,虽然法律在一般意义上是统治阶级整体意志的体现,但实际上统治者个人意志、统治阶级内小集团部分人的意志等非整体意志对法律的形式、内容、变迁仍有相当影响,在特定条件下,这种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正如周永坤教授所言,“在发现了唯物主义的法律观以后,马克思从未偏离辩证法,没有否认当权者个人意志对立法的影响。因为这种思想与马克思总的革命、辩证的思想体系是格格不入的。承认任何法都体现了统治阶级整体意志,必然导致‘宿命论’”[2]。基于唯物辩证法的思辨,统治阶级中非整体意志对法律既非毫无影响,则法律亦不可能百分之百体现统治阶级整体意志,在特定情形下,法律与统治阶级整体意志背道而驰,进而危害统治阶级整体利益,亦非不可能。
法律背离统治阶级整体意志,不仅是唯物辩证法的思辨,也是法律史上的事实。中国古代的法律中,就有不少背离了统治阶级整体意志,在事实上损害了统治阶级整体利益。法律背离统治阶级整体意志历史现象的存在,说明对于法律反映统治阶级意志这一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经典命题,并不能做过于简单及表面化的理解。基于此,本文以传统中国法律背离统治阶级意志的历史现象为中心,通过对实例的深层解构,分析法律背离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原因及影响,以此发掘法律统治阶级意志论这一马克思主义法学命题的深层含义。
二、传统中国法律背离统治阶级意志例析
传统中国法律背离统治阶级意志之例极多,笔者于史籍中捡得实例若干,列举并分析如下。
1.汉武帝“沈命法”
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仿温舒,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南阳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齐有徐勃,燕赵之间有坚卢、范生之属。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为檄告县趣具食;小群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于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史督之。犹弗能禁也,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诸辅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及以法诛通饮食,坐连诸郡,甚者数千人。数岁,乃颇得其渠率。散卒失亡,复聚党阻山川者,往往而群居,无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浸多,上 下 相 为 匿,以 文 辞 避 法焉[3](卷一百一十二《酷吏列传》)。
按:汉武帝统治晚年,社会矛盾激化,“盗贼”蜂起,为督促地方官员恪尽职守,捉拿“盗贼”,汉武帝立“沈命法”,规定不能及时发觉辖内“群盗”,以及虽发觉但未能全数捉拿归案者,地方官自太守至主管官吏全数处死。结果是此后地方官员虽发现“盗贼”,却因担心不能全数捕获而不上报,上下相匿,“盗贼”于是越来越多。
2.北魏孝文帝“禁酒法”
太安四年,始设酒禁。是时年谷屡登,士民多因酒致酗讼,或议主政。帝恶其若此,故一切禁之,酿、沽饮皆斩之,吉凶宾亲,则开禁,有日程。增置内外侯官,伺察诸曹外部州镇,至有微服杂乱于府寺间,以求百官疵失。其所穷治,有司苦加讯恻,而多相诬逮,辄劾以不敬[4](卷一百一十一《刑罚志》)。
按:北魏孝文帝时期,士民多酗酒喧讼,孝文帝恶士民酗酒,立法禁酒,规定除吉凶宾亲等特定时候,酿、沽、饮酒者皆斩,并设细作伺察百官过失,结果是法司以刻薄为能,被究治者为求免罪妄相诬引,刑狱由是泛滥。
3.北齐文宣帝“负罪不得告人事法”
七年,豫州检使白剽为左丞卢斐所劾,乃于狱中诬告斐受金。文宣知其奸罔,诏令按之,果无其事。乃敕八座议立案劾格,负罪不得告人事。于是挟奸者畏纠,乃先加诬讼,以拟当格,吏不能断。又妄相引,大狱动至千人,多移岁月[5](卷二十五《刑法志》)。
按:北齐文宣帝时期,有不法官员为求脱罪,在狱中诬告他人受贿,幸为文宣帝明察,未得逞。为防止此类事情再次发生,文宣帝立法规定,负罪之人不得举告他人。结果是有罪未发之人为免受他人举发,先将可能知道其罪之人诬告成罪,于是诬告之讼大增,耗费司法资源。
4.隋文帝“律外决杖法”
十七年,诏又以所在官人,不相敬惮,多自宽纵,事难克举。诸有殿失,虽备科条,或据律乃轻,论情则重,不即决罪,无以惩肃。其诸司属官,若有愆犯,听于律外斟酌决杖。于是上下相驱,迭行棰楚,以残暴为干能,以守法为懦弱[5](卷二十五《刑法志》)。
按:隋文帝性格本苛刻猜忌,晚年益甚,其认为官员犯罪多官官相护,有的犯罪以律论虽轻以情论则重,于是立律外决杖之法,规定诸司属官所犯虽轻,仍于律外斟酌决杖,结果是上下以残暴为能,以破坏律法为常事。
5.隋文帝“赏纠告者盗贼家产法”
是时帝意每尚惨急,而奸回不止,京市白日,公行掣盗,人间强盗,亦往往而有。帝患之,问群臣断禁之法,杨素等未及言,帝曰:“朕知之矣。”诏有能纠告者,没贼家产业,以赏纠人。时月之间,内外宁息。其后无赖之徒,候富人子弟出路者,而故遗物于其前,偶拾取则擒以送官,而取其赏。大抵被陷者甚众[5](卷二十五《刑法志》)。
按:隋文帝统治晚期,京师长安盗贼横行,为治盗贼,隋文帝立法奖赏能纠告盗贼者,规定凡能纠告盗贼者,没收盗贼之人家产赐予之,结果是无赖之徒假以遗物诱富家子弟拾取,然后擒之送官,诬其为盗贼,以求奖赏,因此而被诬为盗贼之人甚多。
6.隋文帝“禁坏神像法”
帝以年龄晚暮,尤崇尚佛道,又素信鬼神。二十年,诏沙门道士坏佛像天尊,百姓坏岳渎神像,皆以恶逆论[5](卷二十五《刑法志》)。
按:隋文帝晚年崇佛道、信鬼神,于是立法规定沙门道士坏佛像天尊、百姓坏岳渎神像,皆以恶逆罪论处,完全不问这两种行为的法律性质和实际危害,《开皇律》中关于恶逆罪的种种规定,由此被破坏殆尽。
7.武则天“罗告授五品官法”
则天之废庐陵也,飞骑十余人于客户坊同饮。有一人曰:“早知今日无功赏,不及扶竖庐陵。”席上一人起出,北门进状告之。席未散,并擒送羽林,鞫问皆实。告者授五品,言者斩,自余知反不告,坐绞[6]160。
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卖饼食人也,罗告,准例酬五品。于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识字。”对曰:“獬豸岂识字?但为国触罪人而已。”遂授之[6]32。
按:武则天统治初期,“革命是怀,附己为爱”[7](卷八十七《裴炎传》),为镇压潜在反对势力,立法鼓励吏民告他人谋反,规定,凡告他人谋反有实者,皆授以五品官。于是罗织之徒,多如猎者,竟告人反以求官赏,《大唐新语》载,“则天时,朝士多不自保,险薄之徒,竞告事以求官赏。左司员外霍献可尝以头触玉阶,请杀狄仁杰、裴行本。行本,献可之舅也。既损额,以绿帛裹之幞头下,常令露出,冀则天见之。时人讽之李子慎。子慎,诬告其舅以获五品,其母见其著绯衫,覆床涕泣曰:‘此是汝舅血染者也!’”[8]185
8.武则天“令人自举法”
则天初革命,恐群心未附,乃令人自举。供奉官正员之外置里行、拾遗、补阙、御史等,至有车载斗量之咏[8]189。
伪周革命之际,十道使人天下选明经、进士及下村教童蒙博士,皆被搜扬,不曾试练,并与美职。尘黩士人之品,诱悦愚夫之心,庸才者得官以为荣,有才者得官以为辱[6]7。
按:武则天一方面鼓励罗告以打击反对势力,另一方面则滥授官职以拉拢人心,其立法令人自我举荐,凡举荐者未经严格考试即授予官职,于是官员暴增,官职泛滥,贿赂公行,吏治败坏。《朝野佥载》称,“则天革命,举人不试皆与官,起家至御史、评事、拾遗、补阙者,不可胜数”[6]89,“选司考练,总是假手冒名,势家嘱请。手不把笔,即送东司;眼不识文,被举南馆。正员不足,权补试、摄、检校之官。贿货纵横,赃污狼藉。流外行署,钱多即留,或帖司助曹,或员外行案。更有挽郎、辇脚、营田、当屯,无尺寸工夫,并优与处分。皆不事学问,惟求财贿”[6]6。
可见,法律背离统治阶级整体意志,损害统治阶级整体利益,于古代中国确实客观存在。当然,传统法律中反映统治阶级整体意志的亦不少,甚至可以说占多数,但是,即便可以说传统法律中的主流仍然是反映统治阶级意志,背离统治阶级意志之法律也绝非个别可言,换言之,法律背离统治阶级意志,在传统中国虽不能说是常态,但也确实是经常发生的现象。
从本文所举实例来看,传统中国背离统治阶级意志之法律,在内容上既包括权利性规范,也包括义务性规范,如实例7武则天“罗告授五品官法”授予了罗告者担任五品官的权利,实例1汉武帝“沈命法”课加了地方官员全数捉拿“盗贼”的义务,实例2北魏孝文帝“禁酒法”则课加了吏民不得沽、酿、饮酒的禁止性义务;就种类而言,既包括刑事法,也包括行政法、诉讼法等非刑事法,如实例1汉武帝“沈命法”、实例2北魏孝文帝“禁酒法”、实例4隋文帝“律外决杖法”、实例6隋文帝“禁坏神像法”均可视为刑事法,实例3北齐文宣帝“负罪不得告人事法”、实例5隋文帝“赏纠告者盗贼家产法”为诉讼法,实例7武则天“罗告授五品官法”、实例8武则天“令人自举法”则是行政法上的规定。总之,法律背离统治阶级整体意志、损害统治阶级整体利益,在传统中国不仅经常发生,而且广泛存在。
三、传统中国法律背离统治阶级意志原因分析
统治阶级制定的法律,缘何背离其整体意志?笔者在此略作分析。
法律是统治阶级整体意志的体现,所谓统治阶级整体意志,诚如马克思所言,是“由他们(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所决定的这种意志”,换言之,整体意志是反映整体利益的共同意志,统治阶级整体利益则是统治阶级共同的、根本的、长远的利益。整体利益单凭直觉并不能轻易发现,它需要对个别、一般的利益加以抽象才能得出,这就需要立法者有敏锐的洞察能力和较强的分析能力,进而言之,即便立法者认识、把握到了本阶级整体利益之所在,他还需要恰当地选择保护这种整体利益的手段、措施,这又要求立法者具有机智的判断能力和果敢的决策能力,然而现实中,立法者未必能把握到本阶级整体利益之所在,即使把握到了也未必能作出最好的决策来保护这种整体利益,如实例1汉武帝立“沈命法”是为了督促地方官员捉拿“盗贼”,捉拿“盗贼”当然是在维护统治阶级整体利益,然而“沈命法”的后果却是地方官员缩手缩脚,不欲捉拿盗贼;实例5隋文帝虽认识到惩治盗贼对维护京师治安秩序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其应对举措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反而激化了矛盾。立法者亦是凡人,其认识能力受限于天赋条件、文化水平、心理素质,具体认知的形成则不可能不受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的综合影响,当立法者对何为其所在阶级整体利益及如何保护这种整体利益的认知出现较大偏差时,其所立之法对本阶级整体意志的背离即在所难免,故认知的偏差乃法律背离统治阶级意志原因之一。
然而,即便立法者对何为其所在阶级整体利益及如何保护这种整体利益有了正确认知,其所立之法仍未必忠于其本阶级整体利益。盖立法者乃凡人,凡人不但有理智,也有情感,有理性思考,也有七情六欲,虽说人人都希望立法者在立法时不受情感左右,但没人能保证这一点;相反,从本文所举实例来看,立法者任凭个人好恶之情感制定出背离本阶级整体意志之法律,亦非少数。如实例2北魏孝文帝因个人恶酗酒之情感,立法禁酒,徒招官民之怨,于己于国却无所助益;实例4隋文帝因个人喜好杖责官员之癖好①参见《隋书·刑法志》。其载,“高祖性猜忌,素不悦学,既任智而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恆令左右觇视内外,有小过失,则加以重罪”。,立法赋予各级长官于律外杖责属官之特权,徒然加重刑罚,激化内部矛盾;实例6隋文帝又因个人信仰偏好,立法以坏神像为恶逆,增不经之罪,坏己之良法。凡人行事既依理智,也以情感,立法者亦不能免俗,再英明的立法者在情感的支配下,都有可能制定出背离本阶级整体意志之法律,故情感的干扰可谓法律背离统治阶级意志原因之二。
退一步说,假设立法者对本阶级整体利益及其保护认知并无偏差,且立法时也基本未受个人情感之干扰,其所立之法是否就一定不会背离本阶级整体意志?答案仍然是否定的,因为立法者有其私利,这种私利未必与其本阶级整体利益一致。立法者虽说是统治阶级的代表,但归根到底,他也只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员,有自己的私利,这种私利未必与其本阶级整体利益完全一致,有时甚至相冲突。当立法者个人私利与统治阶级整体利益冲突时,其既有可能公而忘私,为维护本阶级整体利益而牺牲个人私利,也不无可能私心作祟,为一己私利而损害本阶级整体利益。毕竟,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整体利益当然要高于个人私利,可站在个人立场上,个人私利却非无关紧要,有时甚至对个人而言生死攸关,此时指望立法者牺牲小我,成全大我,显然不现实。要言之,立法者为一己私利,制定出背离本阶级整体意志、损害本阶级整体利益之法律,是完全可能的。本文所举实例中,实例7、实例8即是立法者为一己私利制定出背离本阶级整体意志法律之典型事例,笔者在此稍作分析。
唐高宗去世之后,武则天临朝称制,大权在手,便生革命代唐之心,然唐自高祖立国以来,君臣励精图治,经三代人努力,国力强盛,统治基础已相当巩固,武则天虽在高宗朝辅政数十年,“威势与帝无异”[7](卷六《则天皇后本纪》),但总体而言,李唐仍得士民之心,其存续完全符合当时统治阶级整体利益,故武则天欲代唐自立,完全是出于其个人私利,绝非其时统治阶级整体意志之反映。所谓武周代唐顺应人心、顺应历史潮流,完全是没有根据的美化之词,李唐既未暴政虐民,未失人心,则武周之立何来顺应人心潮流?武周代唐而立,武则天及武氏集团私利而已。
篡唐自立虽只是武则天的私利,但这种私利对武则天及武氏集团而言,却至关重要。武则天辅政数十年,成功培植起自己政治势力,高宗去世后更假借遗诏临朝称制,成为李唐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其所欠缺的,一个皇帝的名分而已,但如果有了这个名分,武则天即可名正言顺建立武氏政权,成为千古一女帝,武氏集团的其他人也可更上一层楼。大利当前,武则天焉能不动心?反之,如果武则天踯躅不前,不行篡立之举,则天与不取,反受其咎,此后即便想为一深宫太后亦不可得,武氏集团其他人亦必定无好下场。大害当前,武则天焉能不惊心?故篡唐自立对武则天及武氏集团来说,实在是攸关身家性命之最重要私利,其重要性绝对位于国家长治久安(本阶级整体利益)之上。
武则天如何篡唐建周,史书已有详细记载,概括起来说,无非两手,一为诛戮,一为滥赏,诛戮以铲除李唐宗室旧臣,滥赏以收拢士民之心。本文所举实例7、实例8即为武氏诛戮滥赏之明证。从实例7、8来看,武氏诛戮滥赏,实已相当程度破坏了李唐以来的统治秩序,致使纲常颠倒,人心堕落,选举失序,吏治败坏,严重损害了当时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以武氏之智,岂能不知其所作所为不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然而为了个人权位及武氏集团的小集团利益,国家的长治久安暂时被抛之脑后。要言之,武则天基于其个人权位及武氏集团的小集团利益,诛戮滥赏,制定出“罗告授五品官法”、“令人自举法”等背离本阶级整体意志之法律,可见立法者个人私利(包括其所在小集团利益)的压制为法律背离统治阶级意志原因之三。
总之,认知的偏差、情感的干扰、个人私利的压制,是导致法律背离统治阶级意志的直接原因。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时而被误解、扭曲乃至暂时舍弃,法律由是沦为个人意志或小集团共同意志之产物。
然而,如果说认知的偏差、情感的干扰、个人私利的压制直接导致了法律背离统治阶级意志,那么在任何社会(包括近现代社会),认知的偏差、情感的干扰、个人私利的压制皆是立法者难以完全克服之痼疾,缘何在传统中国,法律背离统治阶级意志便成为一种经常发生的现象?笔者对此认为,君主专制的政治形态,乃是传统中国法律背离统治阶级意志现象经常发生之深层原因。君主专制之下,君主掌握几近不受约束的权力,“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3](卷八十七《李斯列传》),于是从理论上讲,君主具备了不顾其本阶级整体利益、意志行事的权力与实力,他完全可以将个人意志凌驾于本阶级整体意志之上,将个人私利置于本阶级整体利益之上,就立法而言,只要他愿意,他完全可以不顾本阶级其他成员的反对,制定出偏离本阶级整体意志、损害本阶级整体利益的法律,也即君主专制的政治形态,使法律背离统治阶级意志尤其成为可能。
平心而论,君主的绝对权力并不必然导致法律背离统治阶级整体意志,如果君主能力超群,道德高尚,有随时为本阶级整体利益牺牲个人私利的觉悟,又能始终保持理智,不为个人情感所左右,法律背离统治阶级意志之现象仍不会发生。正如韩非所言,君主“静退以为宝。不自操事而知拙与巧,不自计虑而知福与咎”[9](《主道》),“去私曲就公法者,去私行行公法者”,“舍己能而因法数,审赏罚”[9](《有度》),“赏罚之威利出于己”[9](《二柄》)。韩非想象中的君主,能力超群,明察秋毫,处事公正,大公无私,可谓完美至极。然而如此完美之君主,在逻辑上即不可能存在,君主是人不是神,是人就会有情感,就会有认识的局限,既不可能摆脱“无知之幕”,也不可能真正斩断七情六欲,况且从现实的角度讲,君位世袭的继承方式不但产生不了韩非设想中的全能君主,甚至连一般比较优秀的君主也保证不了。君位世袭本来就是一种反智型的继承制度,其运作的后果就是就是一大批“生于宫中,长于妇人之手,未尝知忧,未尝知惧”的非正常人成为君主,于是性格孤僻者有之,人格分裂者有之,心理变态者有之,即使极端者只是少数,大部分也是五谷不分、见识狭窄之徒,缺乏必要的政治素质和能力,不具备正常统治一个国家的能力和水平。正如张星久教授所言,传统君主专制体制存在一个无法克服的内在基本矛盾,即“君主的能力与其所拥有的无限权力之间的不适应或不对称”[10]。传统专制体制下的君主,永远不会是“称职”的,更遑论完美,以不“称职”之君主掌握几近不受约束之绝对权力(包括立法权力),则认知的偏差、情感的干扰、个人私利的压制等基于人性的立法痼疾则可毫无阻碍甚至加倍地作用于立法活动,如此一来,法律岂能不经常背离统治阶级意志?
综上所述,认知的偏差、情感的干扰、个人私利的压制在任何社会均为立法中难以彻底去除之痼疾,君主专制的政治形态则使传统中国社会对此些痼疾的免疫系统基本失效,立法遂时常受其影响,而法律背离统治阶级意志,也成寻常事。
四、法律反映统治阶级意志:实然还是应然?
传统中国并非没有试图克服认知偏差、情感干扰、私利压制等立法痼疾的制度,事实上,任何制度存在之主要目的,即是为了克服人性之恶对公共治理可能的不良影响,即便是强调君主集权的传统专制体制,其中也存有对君权稍作约束,以防止君主个人肆意妄为危害国家善治之制度,单以立法而言,唐代便有制敕须经中书起草、门下审核方能发出施行的严格制度。《旧唐书·职官二》称,“中书令之职,掌军国之政令”,中书舍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凡诏旨敕制,及玺书册命,皆按典故起草进画;既下,则署而行之”,“侍中之职,掌出纳帝命”,给事中“凡制敕宣行,大事则称扬德泽,褒美功业,覆奏而请施行;小事则署而颁之”,虽之后三省制逐渐转为一省制,但制敕经政事堂宰相决议方得颁行的传统始终未改,可见君主专制下虽说“法自君出”,但君主出命之前,亦须经宰相及其他官员的集体论证审核。《贞观政要·赦令》亦称,“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足见最高立法者皇帝本人有时亦知立法须审慎为之。然而,传统专制体制下,一切尝试约束君权的机制,无论在理论上或事实上,皆远远不敌君权本身,其约束效果发挥与否、功效如何,取决于君主个人意愿。君主一时从善如流,拱手而治,并不意味着他不能、不会在另一时刻力排众议,乾纲独断,造出不经之法。要言之,传统中国并非全无制度,但其制度远不足以排除君主个人偏见、情感、私利对立法的不良影响。
推而广之,近代以前的任何文明社会,皆不可避免存在法律背离统治阶级意志之现象。将权力之猛兽拘于铁笼,乃近代以来方有之事,近代以前,任何文明社会的制度都不可能真正制约权力行使,于是就立法而言,立法者尤其是最高立法者的偏见、情感、私利则可毫无阻碍地作用于立法活动,法律背离统治阶级意志,遂成不可避免。
从最终结果来看,历史上凡背离统治阶级整体意志之法律,其生命力均不长久,其或被原有立法者废改,或被新政权废弃,这说明,法律反映统治阶级意志这一马克思主义法学基本命题,具有实然与应然的双重意义:就实然而言,无论现实还是历史,法律反映统治阶级整体意志并非仅为臆想,而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律不在少数;就应然而言,法律背离统治阶级意志与法律反映统治阶级意志之现象同时存在,但背离统治阶级意志之法律的生命力不如反映统治阶级意志之法律的生命力,此时法律统治阶级意志论以反面方式证明其意义,这正是应然性的体现。此外,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看,法律统治阶级意志论之双重意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其程度不一:近代以前应然居多,近代以后则由应然逐渐转为实然。虽说近代以前亦有法律反映了统治阶级意志,但在最高统治者具备恣意坏法毁法能力的情形下,法律即便反映了统治阶级整体意志,其于实践中能否落实,仍是一个疑问,更何况尚有许多背离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律同时存在!故法律反映统治阶级意志命题之意义,近代之前以应然居多。惟有进入近代之后,随着民主政治的建立、完善,统治阶级整体意志对其内部任何个人意志及小集团意志产生真正制约,法律方能不受单个人任性左右,法律反映统治阶级意志亦由应然转为实然。
换言之,民主政治之建立,乃是法律反映统治阶级意志成为实然之前提。民主政治之下,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意志受制于多数人意志,立法者个人偏见、情感、私利对立法过程的影响被降至最低,代议机构的建立及立法程序的完善,更促成统治阶级整体意志的形成与表达,如此,法律反映统治阶级整体意志,水到渠成。反之,若无民主政治,统治阶级整体意志既难以有机形成,也难以顺畅表达,即便形成且得以表达,亦未必敌得过立法者个人之偏见、情感与私利,所谓法律反映统治阶级意志,也只能是一种应然,这种应然性的实践,便是统治阶级整体利益反受其立法者所立之法损害,直至该法被废被改。以此言之,对统治阶级而言,民主政治可谓相对最能维护其整体利益的制度模式。
综上所述,基于法律时常背离统治阶级整体意志的历史现象,法律反映统治阶级意志这一命题,具有实然与应然的双重意义:近代以前以应然居多,近代以后随着民主政治的建立、完善,其意义亦由应然逐渐转为实然。
五、结语
虽然,民主政治的建立使法律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由应然向实然转变,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背离统治阶级意志之现象就完全不会发生在现代社会,民主并非万能妙丹,它虽能使立法最大限度排除情感的干扰、私利的僭越,却不能根本治愈人类认知的偏差及偏见,多数无知、群体盲目之下,即便法律以最民主方式制定出来,也不能完全排除其反过来砸到立法者及其所代表阶级之脚的可能。
此外,即使不考虑认知的因素,民主政治基本架构的建立,只能说为法律反映统治阶级意志由应然转向实然奠定了基础。民主政治具体制度的完善本身就是一个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具体制度越完善,法律就越接近统治阶级整体意志,但无论如何,法律永远不可能百分百精确反映统治阶级整体意志,只可能无限接近,而这正是唯物辩证法的思辨。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2]周永坤:《法与统治阶级整体意志关系之我见》,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2期。
[3](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4](北齐)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
[5](唐)魏征:《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
[6](唐)张鷟:《朝野佥载》,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7](后晋)刘昫:《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8](唐)刘肃:《大唐新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9]张觉:《韩非子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版。
[10]张星久:《试析中国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内在基本矛盾——对中国君主制度研究的基本命题的一个尝试性解答》,载《政治学研究》1998年第4期。
Whose Will Whose Interests——The New Viewpoints of Law Reflecting the Will of Ruling Class in View of Law of Ancient China
XIE Hong-xing
(Law School of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chang330013,China)
In ancient china,there was nearly no restriction on the power of emperors.The emperors' prejudice,emotion,and selfish interests affected the legislation so much that the law often deviated from the whole will of ruling class.This historical fact proves that the basic proposition of Marxist Law that law reflects the will of ruling class is“to be”and“ought to be”simultaneously:in ancient times it is“ought to be”more than“to be”,while in modern times it has changed from“ought to be”to“to be”because of democracy.In a word,democracy makes that law reflects the will of ruling class real.
whole will;Chronic illness of legislation;to be;ought to be
D929
A
1671-7023(2012)04-0087-07
谢红星(1978-),男,江西于都人,博士,江西财经大学法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法律史。
2011-12-13
① 江西财金大学校级重点课题“法规审查的方法研究”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胡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