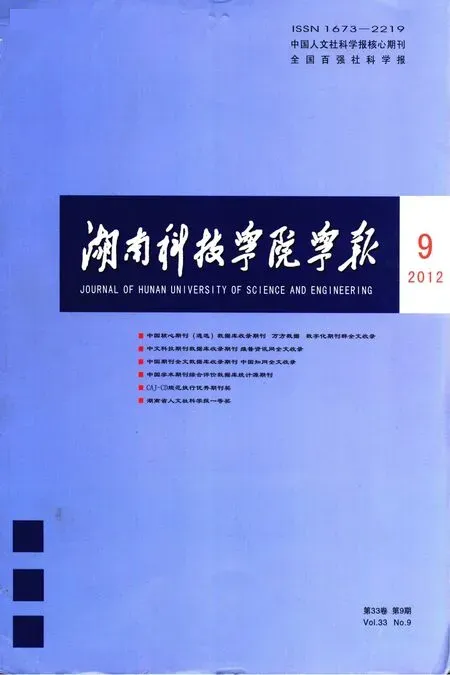“毕加索加城隍庙”
——读罗文中“老罗戏画”
王田葵
(湖南科技学院,湖南 永州 425100)
“毕加索加城隍庙”
——读罗文中“老罗戏画”
王田葵
(湖南科技学院,湖南 永州 425100)
罗文中是一位有思想有关怀的画家,“老罗戏画”以戏曲为题材,采用中国传统人物画大写意笔墨与毕加索式的印象派,立体派绘画元素二者有机融合,变形成了主要的结构方式,从而成功地创造了简洁、丰盈而奇拙的人物画,呈现出“毕加索加城隍庙”的艺术风格,反映了特殊时代的历史符码和作者的“心灵潜语”。
罗文中;戏画;思想;潜语;风格
罗文中先生人们都称他老罗,是伴随我入世以来的挚友。我们是既可以无话不谈,又不愿多谈俗务的那类莫逆友。
四十七年来,我所交之友以不修边幅,狷介高洁,如孤云野鹤,而又不甘寂寞有所作为者,唯此一人。我读过老罗 的戏画和文章,可圈可点者不少,尤以《三个解差》令我忍俊不禁,爱不释手。究其原因是恐惧。岂止是老罗,经历过“反右”、“文革”的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解差”如影随行,它几乎是我们丧失自由的共同的“心魔”。我们这一代人的一生,不是时时处处跟随着使人谈虎色变,既看不见,又无处不在的“解差”吗?可以说,因为有“解差”在,才有老罗的“戏墨”。而我本人,因为有“解差”在,才使自己像找地方下蛋的母鸡,不断孵化出像此文一样的丑八怪“小鸡”。
一 看法改变画法
老罗对我谈过,现在绘画写字的人成堆,王阳明老夫子说“满街都是圣人”,现在圣人没有看见,倒看见满街都是“艺术家”。你看,自称是“著名大艺术家”、“实力派精英”、“未来大师”等等不是满天飞吗?再加上像我这样的非专业的“随地大小便”(山东书法家于明诠题老干部书体)者,更加让人眼花聊乱了。老罗一生求学不辍,却只用八个字概括自己的一生:“少小涂鸦,老大戏墨”。“戏墨”者,戏画也。
老罗是一位有思想有关怀的画家。说他有思想,是指思想成了他的生活方式,他做到了有思想地活着。他一生都在读书,为思想而读书,在读书中“修理”自己的思想。他读的书很广,政治、哲学、文学、历史、文化史等等都有涉猎,尤喜翻阅村言野史。
他在大学读的是油画专业。这为他后来获得戏墨中了悟具象,体验自然的西方绘画技法和视域,奠定了基础。西方文化史和绘画史打开了他的眼界。但是老罗没有就此止步。他把自己的艺术触角伸向了中国传统的民俗艺术诸如彩陶、岩画、戏曲和西方的印象派、象征派、立体派的现代主义艺术领域,对莫奈、马蒂斯、塞向、贾克梅第进行认真观赏和思考,尤其对毕加索的创作经验用功最深。
他在中西绘画理论方面有比较扎实的学养。只要认真读读他的专著《千古画谜》(湖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读读他一系列论文中的代表作《水墨画和印象派的契合》你一定同意我的看法。无庸置疑,这类研究成果不仅属于今天,也属于明天。今后凡研究现代水墨画及其未来走向的艺术家们,不能不读他的力作。
老罗的思想亮点处也是他的明智处在于,在思想和实际创作过程中,重新、反复探索绘画的本质。现象学在西方已有百年历史,90年代初,以现象学为基本方法的中国具象表现绘画才刚刚起步。老罗的戏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定位和发展起来的。现象学的基本态度是回避一切成见,回到事物本身。事物本身实体通过画家主体以及结构形式作本原性呈现,也许就是绘画的本质构成方法。画家发现的视觉形式是现代艺术表现的对象,要使这种形式成为大众观赏得懂,关键在于这种形式能否接纳观众的参与意识和超越意识。寻找新的视觉形式成为现代派画家的使命。因此,创作过程中不仅仅是画的技巧方式,而是要改变观察世界的方式;而要改变观察世界的方式,首先得改变艺术家的思想。这与中国“意在笔先”有异曲同工之妙。这样看来,绘画先得用眼睛来思考,而不是用语言来思考。用语言思考是评论家的活计,而不是画家的活计。用眼睛来思考,看出普通人看不见的美及其结构形式,才能自觉做到把具象抽象化。到头来,这种形式蕴含的抽象化图画,虽然观看者参与画中的意识减弱了,但它的象征性意识却增强了。这恰恰是绘画的目的,也是绘画的本质所在。这也是为什么毕加索的《格尔尼卡》能做到让观众深刻反思20世纪人类的战争和灾难。可见,此大作的主题(观众与作者共同拥有的超越意识)在某种程度上比参与意识(与作者相一致的观看方式及收获)更重要。当然,只有画家改变传统的视觉模式,才能对事物做本原性呈现,并韫藏动人的主题。由此不难得出:哲学家通过语言以文养心,画家通过眼睛以画养心。
对此,绘画哲学家金观涛、司徒立先生也发现了这一点。“莫兰迪通过毕生写生完成了一个惊人的发现,这就是人看到了甚么取决于看它的方式,而人本质上具有无穷多种看同一对象的方式,随着这种观看方式不同,同一对象会呈现出千变万化的形态。莫兰迪通过写实,发现了人的视觉经验的无限性。”[1]老罗戏画也如莫兰迪、贾克梅第一样,是一种学术研究的绘画。它的魅力不在色彩,也不在墨韵,而在作者用画面让人们发现客观对象(戏剧人物脸谱)的观看方式,以及在观看中获得震撼的主观感受。也就是通过画面表现主观精神,并使这种主观精神深深打动观众。这也许就是戏画的境界和魅力所在。
戏画是心画的一种形式。它其所以简练而深邃,其境界来之于作者的想法和人文关怀。试想,一个不读书,不反复研习中西画艺,对人的自由无执着,对邪恶麻木愚昧的人,纵然会玩一些小技巧,他的画也绝无境界可言。
说他有关怀,关键在于跳出狭小的“自我”,拥抱无限的“天下”。有一种习惯极为重要,不能耿耿于自家之遭遇而不去思考这遭遇的社会原因和后果。正如李泽厚先生所言,人在“富有自由、机会和选择,同时即意味着偶然性不断增大、命运感日益加深、个体存在的孤独和感受更为沉重的未来征途中,追求宗教(或准宗教)信仰、心理建设和某种审美情感本体,以之作为人生的安慰、寄托、归宿和方向,并在现实中使人们能更友好地相处,更幸福地生活”。[2]这,大概就是终极关怀,是一个画家良知的反映,也是他用画笔表现的“心灵潜语”。明乎此,你就从累了的“钟馗”,病了的“包黑”,心怀叵测的“解差”,令人滋生正义感的“拷红”等等形象中读出老罗的良知和终极关怀来。
二 时代决定“潜语”
刘心武散文《心灵潜语》,向人们揭示了一个文化现象。他认为人的生命,终其一生有两种宰制无法摆脱:一是基因,二是“时代流行的符码”。“时代符码”烙进人的灵魂后,便构成自觉或不自觉的“心灵潜语”。[3]
什么是老罗的“心灵潜语”呢?这种潜语又是如何通过戏画呈现的呢?老罗曾在一则“作画小记”写道:“幼儿时常随老奶奶逛戏园子,最喜欢看大花脸、杀仗,最烦的是娘儿们咿咿呀呀……”。又说他与戏有缘。由于出身剥削阶级家庭,幼小的心灵于是承受着莫名的压力,慢慢地踏上了人生逃避之路。逃避人群和是非,喜欢孤独和寂寞。然而,命运总爱与人开玩笑,越想逃避越无法逃避。1952年,初中毕业的他便糊里糊涂走进了湖南师范艺术学校,因不愿当教师只好回到县城读高中。1959年考入湖南艺术学院油画专业,两年后此校与湖南师院合并,仍然踏进了无法逃避的教师行业。
诸葛亮在京剧《空城计》中唱道:“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诸葛亮虽暂隐于卧龙岗,然时时韫韬略之秘,俟庙堂之奋,岂能散淡?老罗对我说:“我才是一位真正散谈的人。”“散谈”,也许就是老罗藏匿在戏墨中的“心灵潜语”。我理解的散淡者,即逃避者,“隐沦者”,“局外人”的意思。
他以散淡的心态从事教师职业,不求荣誉,无望回报,并且时时谨小慎微,尽管勤奋尽力,风趣幽默,也驳得了学生的好评,但长期的惶恐使他的散谈之心蒙上了阴影。教书并没有带来乐趣,处境像作家王小波的父亲王方名。王方名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哲学教师。王小波回忆:“在老年时,他告诉我自己一生的学术经历,就如一部恐怖电影。每当他企图立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官方思想体系里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只老母鸡要在一个搬家的宅院里找地方孵蛋一样。结果,他虽然热爱科学而且很努力,在一生中却没有得到思维的乐趣,只收获了无数的恐慌。”[4]
笔者曾看到,他上大学时画的一幅小小的戏曲速写,颇有变形夸张的尝试;20世纪90年代画的油画《拷红》也成了离奇的符号以及符号背后留下的“心灵潜语”。在这些画中,画家个人的生活体验,对践踏人的正当情感的暴虐者的厌恶表现得淋漓尽致。后来,他画了一系列戏剧故事和人物,有的来自一个故事的侧面,有的则是自我组合虚构。关于钟馗打鬼的故事,荒谬的《三个解差》都呈现了是非黑白颠倒的历史符码,十分精致地诠释了哲学家哈维尔对强制乌托邦极权统治本质的深刻揭示:这样的制度只能使大多数人走向奴役之路,以至“人人是囚犯,同时人人是看守”。
老罗遁于世情,淡泊物欲名利,而对戏画则几乎倾注了数十年心力。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老罗自由主体性的确立,他的戏画才真正摆脱了油画精细、逼真的约束,而采用中国大写意画法,胸襟畅达而放怀,激情自由而惬意。
老罗戏画人物带有典型的中国古典戏剧诗意特质,深厚的中西文化积淀给他带来了创作灵感和技法。他的笔墨图式既是传统的又是个人的。他把中国传统人物画大写意笔墨和筒洁造型、毕加索式的变形、断裂,印象派的感觉化色彩二者有机地结构在一起,把线的表现力和墨的韵味张扬到了理想状态,也反映了作者对怪诞时代无休止的暴力奴役现象和人的恐惧心理的稠酽记忆。在“听戏画戏消夏度暑”的轻松题语之中,深藏着的是更为幽惧的时代体认和人生反思。而在这一系列戏墨中,花脸武生和长胡猛将使人目不暇接,在人物打杀之中刀枪有白有红,花脸有蓝有白,人物背后的故事充满了诡秘和不确定性,所有这一切,不正是画家欲言又止的“心灵潜语”吗?
三 变形创造结构
什么是老罗戏墨的审美追求呢?早在1986年,老罗在《艺术世界》第六期上发表的《水墨画和印象派的楔合》、此文被收录在《人生四韵》中,同时收录的有梁实秋、林语堂、张恨水、贾平凹等名家之作。他说:塞向的静物画之美是举世公认的。“他常常采用类似中国画散点透视的观察方法和表现方法,不惜‘歪曲’物体外形的方法,从而使这些物体获得一种独特的生命力,达到情感空间紧紧地揉合在一起,在画面结构这一意义上来说,和中国画是颇为接近的。”[5]老罗曾撰文指出,潘天寿的画在追求画面结构的稳定性上,与塞尚的画可谓多有不谋而合之处。他曾屡次向我介绍,著名画家张仃。“熟知张仃的人,称他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发展的活化石,从革命漫画、宣传画到年画、壁画、中国画,再到书法、设计和美术史论,样样达至高峰。他兼具西方艺术与民间艺术的修养,被好友华君武戏称为‘毕加索加城隍庙’”。[6]“城隍庙”是个比喻,中国人把它视为求雨、求晴、禳灾的祭祀场地。“城隍庙”比喻中国画,“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中国画的神髓。中国画写意,趋向宁静。儒、道、佛都相信人在平静中,智慧才能澄明,才能洞察宇宙秩序,体验此心之玄微,从而达到生命的高层境界。质而言之,华先生用“城隍庙”来比喻中国画的精神特质。
毕加索的变形创造借鉴于黑人艺术,熊秉明先生对此作了深入研究。他发现1907年毕加索画的《亚维农少女》,主题是坐与立的五个女体,其中有两个的面貌做了粗暴变形,扭曲斩削成黑人的木雕面具。毕加索继承了印象派对黑人艺术的模仿。印象派通过色彩效果描写外光,提升色彩的纯粹与鲜明,然而却松懈了物体的实在感。毕加索则在绘画中走向了立体主义,把视觉的现象世界解析为立方体、椎体、球体在画面上的重新组合。他沉迷于几何形体的解构与再构。
如何将毕加索的具象变形组合与中国绘画精神结合起来呢?中国的人物画意在挖掘对象的本质,实现“传神”。这就要求画家捕捉对象的内在精神,此精神乃是画家对于对象的主观认识和阐释。具象表现画家贾克梅第发现,人看到了什么,同他看世界的方式有关,因此,画家的认识论与哲学家的认识论是不同的。前者用眼睛去感知,后者则是处理主客二分关系。画家排除了一切先入为主的成见之后,把用自己独特的视觉方式所看到的事物称为绝对真实,而表现绝对真实就是画家的终极目的。画出物体的真实性,全在于作者看的方式和他的意向性。德国捷申画的素描自画像打破了“空间的在场”和“时间的在场”。同一平面画出了两个侧面,眼睛一高一低,嘴的表情各不相同。画家把他一生中的痛苦、忧郁、沉思的体验通过他自己看与思的方式呈现了出来。表面看,这幅画像是不真实的,但他表现的恰恰是自我存在的本真状态,是一种绝对真实。这样看来,现象学与中国绘画的艺术精神(心画)二者之间存在着可渗透通融的东西。老罗戏画的成功性就在于他通过艺术实践找到了这种相互渗透通融的方式。
画家把描写对象视为有生命的对话者,灵犀相通的同病相怜者,主观性是毕加索与中国画之间的共同审美追求,老罗由此找到了歪曲物体外形的方法。无论是“繁”的结构还是“简”的结构都是这样。
在老罗的“盈满章法”结构的戏墨中,大多由变形创造而成。戏剧人物脸谱,兵器与远古岩画、秦汉石刻图像相杂其间,形体的分裂,色块的穿插这些西方现代派绘画元素融合在大写意的笔墨元素之中。读这种画,你会发现与其说作者在呈现密体画,不如说在呈现一种观念,一种心境。作者一改中国画“从简”、“用减”、“笔不周”的艺术追求而模仿西方现代派之“繁”,在“繁”中窥见光怪陆高的大千世界。
老罗的脸谱系列作品是将戏剧符号与毕加索超时空立体几何符号有机结构的产物。有一幅大写意蓝眼睛、蓝鼻子的脸谱也许受到毕加索早年蓝色意象的启迪;而另一幅玫瑰红脸谱外加紫色花脸的叠加结构则熔入了毕加索“玫瑰色时期”的结构特征。
除了“盈满章法”之外,老罗一般采用“从简”结构。“从简”与中国画的诗意审美追求是一致的。恰如董其昌所说:“画欲暗、不欲明;明者如觚棱钩角是也,暗者如云横雾塞是也。”[7]
老罗是如何将“从简”的戏画结构与毕加索追求的立体派绘画结构相融合的呢?这还得回到毕加索对黑人艺术的了悟。黑人面具艺术就是以“从简”的符号化而见长,但其缺点是向外的粗犷而少含蓄,它只有刹那的震撼而无动人的深邃。这与中国人的内向的含蓄恰是两个极端。京剧的脸谱是个例外,它几乎兼有“从简”与含蓄的功能,它与黑人面具艺术一样是神秘、离奇、怪诞的符号,所不同的只是,面具是巫术文化的存留又是立体造型的;而脸谱是人脸的自然形态,美术处理之后虽然是符号化的,但却涉及诗意的内涵,即涉及人世界的历史和道德价值,人的命运以及相关联的情感诉求。
老罗戏画正因为深知这一点,他才在脸谱中融入了印象派技法,画了一系列花脸英雄,红颜美女,有时美女的裙裾成螺旋变形,有时用水黑大写意小旦加花脸,黑与白,红与黑的色彩对比强烈;有时将唐代美女的宫娥团扇横惯中心画面,有时用疏密相生章法,将英雄美女的脸形打乱重构,宛如毕加索的立体派画法。“简”而有“诗”,如他题画一则:“戏里人物,生旦涂片彩,净丑省墨块。”“省”是为了“味”。一根细线,一笔涨墨,一点彩虹,都能呈现非凡的质感和韵味,表现作者特殊的看与思的方式。作者将所有这一切色彩、符号纷呈给观众,就像一首首风俗诗,警世诗一样烙进观众的心灵。社会世相的阴阳失调,是非黑白颠倒,在这些近似脸谱与黑人面具,既粗犷又含蓄的戏画中呈观出来。
由此可见,无论是“盈满”或是“从简”,到了老罗的笔下,都可以建造出富有诗意的尺幅斗方来。
四 “融合”成就风格
老罗戏墨“毕加索加城隍庙”的艺术风格的形成,得力于三个融合。
其一,黑人面具元素与中国戏曲脸谱元素的融合。
老罗说张仃是中国留法画家中与毕加索切磋过的画家。张仃介绍说:毕加索《亚维农少女》“这种特别的自然形的断裂解体,彻底摧毁了艺术传统”。不论怎样变形和夸张,总能从他的作品中找到生活形象与时代脉搏”。他着重介绍说:“他不断探索人体结构的表现力,得到黑人艺术的启发,并且发展了塞尚的观点。”[8]那时,毕加索看到了黑人艺术,大有“先得我心”的惊喜。熊秉明也强调,毕加索及其立体派“既排斥照相式的写实,也排斥浪漫性的抒情。在他们看来,客观写实太重肉眼所得来的形色信息,使理性从属于感官,这是他们所不愿的”。他们“把三度世界现象移到两度画面的绘画问题当作一个理性的课题去解决”。他们关心空间、体积与几何图形组合的问题,而黑人的木雕面具也将几何图形作为造型元素,“在这一点上,他们觉得与黑人面具有了共同语言”[9]。
笔者不厌其详地澄清毕加索与黑人面具的艺术渊源关系,意在为老罗戏画找到其艺术风格的成因。此论关系极大,非数语所能尽其诣。请细看张仃先生的推介。
张仃高度赞扬毕加索1937年画的《格尔尼卡》,指出这幅用心灵画成的巨幅名画,它成为西班牙的国宝理所当然。他采用的虽然是立体派的画法,却极富象征含义。变形的人物、牛、马,着火的房子、举灯的人,马蹄下手握断刀的死者,死去的孩子……这一切,把对战争的愤恨如此强烈地烙在观众心上。
近年,老罗不厌其烦地画《待漏》,正是中国水墨画与毕加索象征性立体派画完美融合风格的体现。画中第一句题词:“朝臣待漏五更寒,铁马将军夜度关。山寺日高僧未起,看来名利不如闲。”整幅画展现的是形的断裂和解体,充分展现了毕加索从黑人艺术中吸收的技法,又不失中国人物画的精神。《待漏》的内在表现力似乎象征20世纪的人生境遇,反讽是机警而透彻的。在这样的世界里,老罗和我们既不是朝臣,也不是将军,无“漏”可待,也无“关”可度,只能是像高僧一样的无名无利可求的散淡者。
老罗不厌其烦地画《钟馗》,他写道:“世上画钟馗者众,画有别趣者寡。”他一改人们往往把钟馗画成怒目凶狠,宽衣长袍,手握刀斧,散须大眼的打鬼英雄,而把宽服、圆袖、纸状子,官帽这些戏曲物件,结构在一起。人们看到的是无可奈何的钟馗。再加上题曰:“钟馗累也,奈何天降大任于斯……”就更加增添了不少别趣。
其二,印象派元素与水墨大写意元素的融合。
老罗戏画简洁而丰富。这得力于他善于吸取西方印象派元素,并使其同中国画大写意笔墨元素结合起来。印象派强调在直观明证之中做到对事物本质的呈现,从而达到对表象思维的克服。这正是以现象学为基本方法的具象表现绘画所追求的。如此,戏剧人物的写意画笔墨熔铸个人的生活感情,尺幅斗方之间,造显人生百态,世相本原,洋溢着文人画的深邃思想和时代情趣。其笔墨的独特处在于简洁、丰盈、奇拙,力戒刻意经营,力求笔墨与心性相融,不事雕琢而神思弥漫。
19世纪绘画表现对象是公有现实(历史现实),从印象派开始,绘画经历了从公有现实到个人感觉的巨变。以个人视觉方式,用自己的眼睛去感知、去发现并表达绝对的真实,就像寻求终极真理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形式创造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它的后果可能是作品公共性的丧失,亦即终极关怀的丧失。老罗戏画实现了前者却避免了后者。
老罗在《李白》、《怀素》、《打雨伞的和尚》这类作品中既吸取印象派等现代主义,注重对形象主观特殊感受,又立足中国传统绘画的意义结构,关注公众的求知成份。老罗的水墨人物写意画是有印象派风格的中国人物写意画。他把李白仰天狂笑和身体变形画成了现代“摇滚”。
老罗画了一系列怀素印象派大写意画,作者的愤世疾俗激情和主观概念混合在一起。酒、笔、芭蕉、红袈裟、大胡子光头这些个人喜爱的主观理解变形物体,象七巧板般的彩色抽象构图呈现在宣纸上。他为我画的《打雨伞的和尚》则强化了墨镜、小光头、巨型脖子、红色的袈裟、带血的屠刀和会洗脑的笔……我第一次看到这幅画时,不由得想起西方哲人的洞见:“强制的乌托邦”(热布津斯基语)狂人,都是“致命的自负”者(哈耶克语)。这些充满时代和主观情感的具象巧妙地组合在一起,意在突出狂人和尚的“无法无天”。
老罗的眼睛是被挤逼的逃避者的眼睛,也是愤世嫉俗的眼睛,能发现历史人物价值的眼睛。他这种处境的危艰和愤世嫉俗颇像法语翻译家傅雷。早在20世纪20年代,傅雷与罗曼·罗兰通信时就曾说:“为国家与环境所挤逼,既无力量亦无勇气实行反抗,惟求隐遁于精神境域中耳。”当然,傅雷是桀骜不驯、愤世嫉俗、忧时忧国的,他自喻为“墙洞里的小老鼠”,意在表明忧国忧民又无力救国救民的矛盾心境。杨绛先生在她的文章中解释说:“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有自己的书斋,他也像老鼠那样,只在洞口窥望外面的大世界。”[10]老罗笔下的“密体画”,和《李白》、《怀素》、《打雨伞的和尚》也是意在引领观看者,从其心灵“洞口”窥望光怪陆离的大世界。
其三,毕加索超时空元素与中国画神韵意象元素的融合。
王维画《袁安卧雪图》,从而引起了中国美术史中“雪中芭蕉”之争。王维这幅画反映了中国画超时空艺术意象自由结构现象。到底是“关乎常情”重要?还是“造境入神”重要呢?这就是争论的焦点。无疑,以今人之见,一定会同意第二条更重要。既然承认绘画是“心画”,画家的艺术意象则必然会突破“时间在场”或“空间在场”。
老罗曾多次画“三个解差”。三个解差分别来自三个不同的剧本情节。崇公道来自洪洞县,俗话说,洪洞县里无好人,但崇公道却是洪洞县的好人。另两个押解林冲的坏解差是董超、薛霸,他们呈变形、断裂状居画面两侧;崇公道几乎占据了中心画面,坐姿,凛凛然有刚正不阿气象。他被戴上红色鱼形枷锁,“鱼者”,“馀也”,死有馀辜也,红色象征“专政”。只不过是坏人专了好人的政。这是一幅典型的跨时空,超现实的现代水墨写意画。中国诗意神韵意象元素与毕加索超时空元素天衣无缝地契合在二度空间的画面里。《解差》的神韵在于,呈现了一个时代的无处不在的一元化政治现象和精神现象。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到处以忆苦、感恩、效忠等为内容开头,而以对“牛鬼蛇神”的残酷斗争、批判为结束的模式,是那时上万次此类群众大会的标准程序。全国其所以如此高度一致,就是因为在“无限信仰”、“群众运动”、仇恨异端等等却魅型文化因素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内在逻辑和共生关系。而“反右”的意义,则为这种逻辑和共生关系提供了可操作的经验。
有作家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MM(女人)系列”是老罗戏画的重要题材。老罗笔下的女人结束了“时间的在场”,只剩下了“空间的在场”。他们几乎都采用唐人的审美标准,丰腴、白色、桃红,外加黑色衣裙,线条圆润而少棱角,他们既是唐代的,也是现代的;既是中国的,也是华人世界的。聊聊几笔,写尽了天下的,也是戏曲中的美女。
这些奇构成了超时空的女性艺术形象。该怎么领悟女性美的神韵呢?陈丹青先生曾谈到中国其实有很好的传统。例如,中国有键全的成人应该有的性观念和性传统。他说:我们还是先来恢复失落的传统,使国人知道本民族源远流长,活泼率真的性观念、性文化。根据当代中国的种种情形,参照外国的种种经验,重建成人文化,将下半身的“生命意志”匀一小点出来,转给为上半身的观看行为,让亿万中国成人的“眼神”有所归宿,有可着落,活得像个成熟的成人。[11]
眼下国人在欲望巨涨的人世间,成人的眼光日渐漂泊离散,“愈堕落愈快乐”成为最无遮拦的时代宣言,身体写作、性感日记、露点写真成为最抢眼球的热点,自杀、婚变、暴力、绯闻、摇头丸几乎成了流行文化的绚丽风景。老罗的“MM系列”戏画意在引领观众,你得像个成熟的成人一样恢复“观看行为”。这些性感女人的描写全采取了非浪漫化的处理。作者既不屑于宣扬色情,也不炮制平庸的诗意。他笔下的女性准确说来应该是性爱的图式。这些心灵图像所关注的,多是人性的堕落,以及由堕落而至情场的野蛮化。“MM系列”所兆示的“历史符码”以及“心灵潜语”,凡懂历史、有关怀的人都能读明白。我以为,与其说老罗在画女人,还不如说在“图式”历史。作者通过这类女性戏画,所呈现的时代意象和诗意神韵表明,在大风大浪的乌托邦狂热时代,人们被压抑的正常人的热情和性爱力量,现在以毫不羞怯的心态,宣泄了出来。
至此,我冒昧写了上面这些外行的话。比起戏画来,更重要的是老罗这个人,他的入世态度,他对艺术的执着以及正义感,都值得我敬佩和学习。故而吟成这首《题老罗戏画》:
如影解差惧随行,输诚散淡入丹青。
钟馗待漏真脸谱,写出人间不平声。
[1]金观涛,司徒立.作为学术研究的绘画[J].二十一世纪,45: 91.
[2]李泽厚.大同新梦[J].二十一世纪,11:5.
[3]刘心武.心灵潜语[J].二十一世纪,18:127.
[4]王小波.思维的乐趣[J].二十一世纪,45:103.
[5]罗文中.水墨画和印象派的契合[A].太初,周勤等.人生四韵[C].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601.
[6]刘子超.斯人已逝,风范长存[N].北方新报,2012-03-14.
[7][明]董其昌.画眼[A].书学心印[C].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1937.
[8]张仃.毕加索[A].太初,周勤等.人生四韵[C].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502.
[9]熊秉明.黑人艺术和我们[J].二十一世纪,11:72.
[10]傅聪等.傅雷和他的世界[M].香港:香港三联书店,1994: 17.
[11]陈丹青.与陈丹青交谈[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7: 31.
(责任编校:张京华)
J205
A
1673-2219(2012)09-0194-05
2012-08-19
王田葵(1939-),字阳之,男,湖南桂阳人,湖南科技学院教授,香港中文大学特邀教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国家书画院副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学者,主要从事比较文学、中西文化比较、舜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