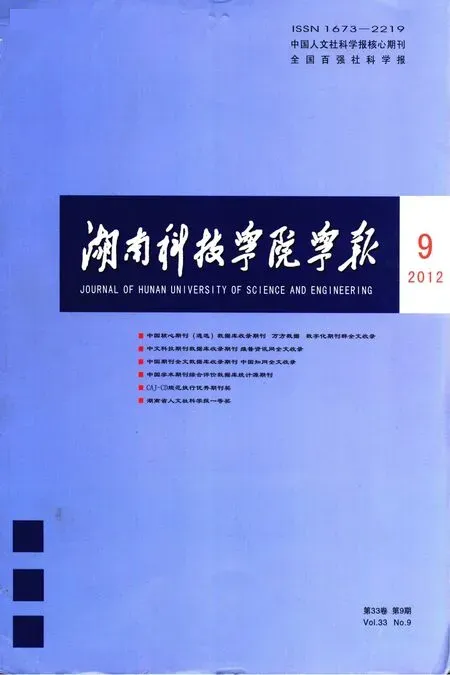存在主义思想对《围城》的影响与渗透
郑明娥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怀化 418000)
存在主义思想对《围城》的影响与渗透
郑明娥
(怀化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怀化 418000)
《围城》对存在的荒诞性的刻画与思考,带有鲜明的存在主义色彩。存在主义哲学曾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形成一股热潮,这对作家钱钟书的观念和创作思想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无可避免地使《围城》打上了存在主义的印痕。
《围城》;存在主义;影响;渗透
一 《围城》的生命力与作家对存在主义的接受
2008年底,在第9届深圳读书月“阅读中国三十年”系列活动中,公众通过各种途径从30年来的30余万本出版物中最终选出了 30本对中国人心灵影响最大的文史类读 物,钱钟书的《围城》榜上有名。可见《围城》带给人们心灵的震撼和人生的启迪,经受了历史的考验、时代的洗礼而历久弥新。《围城》的这种跨时代的生命力,得益于作家对人、对“存在”的自觉关注和深刻揭示;进一步考察,它又与钱钟书曾自觉接受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密切相关。尤其可贵的是,作家将自己对存在主义的深刻理解,在对现实生活的关注、思考及其创作实践中,完成了一种举重若轻的创造性转化,这更是《围城》具有跨时代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近代以来,伴随工业文明的发展和物质的极大丰富,人们的精神出现空前的“危机”,如人生目的消解、理想淡化、奋斗精神衰退等,人们在生活中感到越来越孤独、失落、绝望。存在主义哲学正是这一世界性的现代文明危机下的产物。20世纪30年代末法国兴起存在主义文学,其思想基础便是存在主义哲学。存在主义文学乃至整个现代派文学思潮,大都是以表现个人内心的孤独感、失落感和危机感为主导话语的。钱钟书1935年去英法留学至1946年写成《围城》,其间正是存在主义思潮在西方兴起、发展,并在中国广为传播的重要时期。他对诸如克尔凯郭尔、尼采、叔本华、柏格森、弗洛伊德、普鲁斯特、乔伊斯、艾略特、瓦勒里、劳伦斯等西方现代思想大师和文学巨匠,都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并“在40年代起就介绍过存在主义的先驱、非理性主义的代表人物克尔凯郭尔的理论”[1]。正是在此基础上,钱钟书致力于把《围城》写成一部有关“整个人类”的故事,并把现代文明和现代人生当作一个整体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而且将这种反思提升到一种形而上的高度,遂使《围城》成为人的荒诞的存在困境的本体性象征之作,一部“形象的哲学”。比如,《围城》中深刻揭示和批判的主人公的“畏怯”,以及其对存在处境的探索等,其实就与作家在写作期间曾深入研读克尔凯郭尔的名著《恐怖概念》(又译《忧虑概念》)不无关系。
总体上说,存在主义思想对钱钟书的影响,突出地表现在人生观方面。存在主义的人生哲学及其“实存状态”观和“自由选择”学说,为作家钱钟书提供了全新的人生观,并充分地体现在其创作中。一方面,存在主义的实存状态观——人的存在的本源性意义上的“虚无”,以及由此而来的那种根本性的荒诞、焦虑、孤独、迷惘和绝望等,成为钱钟书的基本人生观点,也是他在创作中着重表现的存在体验。他在《围城》中着力揭示人的存在的荒诞性以及人在失去信仰、意义之源后的畏怯与迷惘,这或多或少都与存在主义的实存状态观有关。另一方面,存在主义的自由选择观以及全面负责的思想,则成为作家钱钟书的基本人生态度,成为他在创作中着力张扬和暗示的人生精神导向。在《围城》中,钱钟书之所以竭力讽刺和批判“围城人”的怯懦、逃避和游移,其言外之旨就是强调处在根本困境中的人是无由逃避的,他必须勇敢地承担起存在的责任。小说的这一基本主题,可以说是自由选择观的一种表现。同时,存在主义给钱钟书提供了一种把文化批评和人生批评相结合的思路。《围城》中就体现了这种存在状况的分析与文化批评的联系,既加深了作品的思想深度,又拓宽了现实人生的文化蕴含。
二 《围城》思想内蕴的存在主义特征
存在主义对钱钟书的影响已深入其思想和精神深处,并直接反映和渗透在《围城》的创作中,使作品明显地带有存在主义的一些特质。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表现人的存在的荒谬
人的存在是存在主义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它首先突出的是个人现实存在的荒谬性、孤独性、虚无性、自由性,从而深刻揭示现代人的困境及其某些永恒的困惑。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人是无任何理由和根据地被抛到这个世界上来的,他不得不承担生存这个事实;“荒谬”是存在主义最基本也是最直接的生存体验。《围城》中就描述了这样的人际关系:在具有密切关系的人物之间,一方的言行举止,由于事物的偶然性、人的孤立性等原因,往往导致和行为者的愿望相脱离甚至完全走向反面的结果,对作为行为承受者的另一方产生意外的作用和影响。小说通过对这种因果悖理、事与愿违的阴差阳错现象的描述,表达了这个世界没有主宰,没有规律,不合逻辑,不合情理,人类无法用理性去理解和把握,从而表达了世界的不可知性和异己性,人的处境的荒谬性。方鸿渐的人生遭遇莫不如此。他买假文凭一来“遮羞”,二来给家人一个交代。方在这张博士文凭的遮掩下表面似乎无限风光实则胆战心惊,原本是“善意的谎言”以讨家人的欢心,实则让自己“忐忑不安”而出尽洋相。这种出于对他人的善意而给自己带来恶意的事实使方鸿渐为我们上演了一幕幕“荒诞”的悲喜剧。
在情感上,他明知自己不爱苏文纨,却一次次答应她的邀请。当他满以为自己可以跟唐小姐谈一场正式的恋爱时,孰料苏小姐从中作梗,使他功亏一篑。当分手后的唐小姐打电话给方先生时,方先生劈头盖脸就骂对方“好不要脸的东西”,他误以为是苏小姐,谁料却是唐小姐!“荒谬”似乎成为捉弄人的高手,他使方先生冥冥之中身不由己、不由自主地甘受摆布。在工作上,当初赵辛楣误以为方先生是他的情敌,为支开方先生,就推荐他到高松年的学校任教。没想到这偏偏成了方先生遭受双重打击时的一根“救命稻草”。世界有些荒谬,人的理性无法解释清楚,这里赵先生原本是不怀好意地排斥方先生,在后来的处境中却反而歪打正着地帮助了方先生,荒谬让人感到世事难料,世人摸不着头脑!在婚姻上,赵先生善意的玩笑和真诚的资助使方先生与孙小姐匆匆结合,但谁知道两人后来吵架不断最终分道扬镳。原本是一片好心好意的赵先生,却给方先生带来了恶意的后果。尤其让人不可思议的是,当初赵先生离校时留给方先生的一本书却成了解聘方先生的“导火线”!世界好像已经变得不可理喻,不可捉摸,人不能去把握他,只能去接受他。这种荒谬的生存意识与存在主义哲学关于“世界是荒谬的”观念存在着契合,这种存在体验是对哲学观点的形象解读。
(二)表现人的孤独与虚无
存在主义哲学强调人是被抛到荒诞的世界上来的,是被遗弃的,是孤独的。孤独就是与他人的隔离,与现实环境的分裂。人在世界上是孤独的,人在荒诞社会是个“脆弱的东西,淹没在无限的大千世界里,孤立软弱,每一个瞬间,虚无都在袭击他。”[2]14方先生经历了与唐小姐的失恋以后,就感悟到“人与人精神之间的不相通性”。后来方先生跟赵先生交谈时说“天生人是叫他们孤独的,一个个该各归各老死不相往来,身体容不下的东西,或消化,或排泄,是个人的事”,方感到“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3]324好像人与人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他让人对他人产生一种隔膜,每人把每人的空间隔离开。在经历失业并失恋时,方深深感到“他个人的天地忽然从世人公共生活的天地里分出来,宛如与活人幽明隔绝的孤鬼,瞧着阳世的乐事,自己插不进,瞧着阳世的太阳,自己晒不到。”[3]105这种孤独已经深入方的精神深处,让人想到萨特的《墙》,他人和方之间已经筑起一座不可逾越的心灵的“城墙”,如同一道屏障让方感到极度的孤独。
人类看似热闹非凡,人来人往,这表面上的喧嚣难掩内心深处的孤独。这种孤独叫人进而感到虚无。“什么是虚无呢?严格地说,虚无什么也不是,因为虚无就是什么也没有。”[4]12虚无对人的威胁具体表现为人的贬值、人的异化;由于摩登文明社会中“生存竞争露出了原始的狠毒”,致使其中的方先生反觉自己贬值到连微生虫也不如的地步。处身如此异化的社会,方感到人生已经完全失去意义。它越想要自己行动起来,就越发现行动毫无根据、毫无必要,所以方总是行动无力甚至懒于行动。这种虚无的意识使方先生滋生麻木、近乎绝望的情绪。比如他经历爱情失败后,不由得生出“无论你跟谁结婚,结婚后你发现她跟结婚前是两个人”,“近来对人生万事”都有诸感。钱先生在描写火铺的那个破门时,“好像个进口,背后藏着深宫大厦,引得人进去了,原来什么也没有,一无可进的进口、一无可去的去处,‘撇下一切希望吧,你们这些进来的人!’”[3]179海德格尔说,人感受虚无的方式是“畏”,就是不知道怕什么,令我害怕的是,不是什么具体的东西,而是空无所有。[4]16虚无就像一个巨大的深渊、空蒙的存在,让人感到深不可测的恐惧,因此更加“可畏”。此时,莫名的虚无透彻了方的心骨。通过方先生对孤独和虚无的切身体验,表现了人存在的勇气,也表现出存在主义对《围城》人物形象塑造的渗透。
(三)表现人的“自由选择”
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根据和理由,人本身应该就是“虚无”,正因为“虚无”,所以人应该进行绝对的“自由选择”,用自己的生存活动支撑和承担自己的“虚无”。从“虚无”中走出来,通过自己的行为成就自己,创造自己的本质,从而使人生具有价值和意义。就是说,人作为一个“自为”的存在,只能有意识地以“生存”去面对和担当。在对生存的承担中,进行绝对的自由选择,在行动中获取人存在的本质。
存在主义者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人的存在先于一切本质,它是以存在为基础、前提的,换言之,认识是以生存为前提的,只有在生存的行动中才能形成自己的本质,而此时的“本质”绝非本质主义的“本质”那样是静止的、先在的,它是整体生存过程的整体表现。存在主义强调人的存在在先,本质在后;人空无所有来到世间,本质是在后天形成的;人是在生存的过程中,不断积累知识和经验,而后造就了本质。萨特认为,除了自由,你与我都没有既定不变的“本质”,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那是你的自由;你要获得什么样的本质,那要看你怎样进行你的自由选择。[4]62对于方先生而言,在留学期间他可以自由选择就读的大学及所学专业,回国后,他自由选择了一份职业——在岳丈的“点金银行”供职。当他被迫解聘时又计划着去内地平城任职。来到三闾大学发现这里明争暗斗、尔虞我诈、乌烟瘴气,自己到处被人排挤,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多余人”。最终因为失去“靠山”而再次遭遇解聘。之后他选择了离开大学,来到了上海,在赵先生的热心帮助下,谋了一份在报馆资料室工作的职位。当沈太太叛变投向日伪政权时,方先生自作主张选择了“辞职”。他筹划着再去内地找赵先生,谋求新的职位。存在主义认为,正视自己的自由就是承担起自己的存在,自己选择自己的本质。[4]156也就是说,自由是一种选择,一种谋划,一种行动,在这种生存活动中人承担了自己的生存,成为一个实在的存在,并成就了自我存在的本质。人就是在不断地失去,不断地寻找,不断地选择,不断地失去中承担起自己的存在,进行一系列生存活动,并形成自己的本质。在这个“自由选择”的过程中,方鸿渐不断做出选择,又不断失去,再不断寻找,最后又重新选择,如此循环往复,而每一种选择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选择在银行做事,就得忍受岳丈、岳母的管束,使他显得懦弱、窝囊、被动。选择在大学任教,就得忍受领导的欺骗、同事的离间、学生的监督等。这也造就他善良、正直、懦弱的本质。选择在报馆任职,就得默然承受来自领导和家人的轻视。辞职也反映出方先生仅有的良知和爱国心。而每一种选择,都注定走进一座新的“围城”,每一次放弃意味着冲出旧的“围城”,在选择和放弃,失去和寻找之间,方先生就在“围城”内外奔波、操劳过程中,形成自己的本质,这就是对存在主义哲学的“自由选择观”的最形象的文学阐释。
(四)表现人的“为他存在”意识
存在主义认为,人是一种社会存在,在自由选择和谋划中,人与他人形成“共在”和“冲突”的关系。一方面,所谓“共在”,通俗地讲,就是与他人结为一体,共同存在。在日常经验中,人往往不是凭借与他人的冲突,而是凭借与他人的联合发现自己的。[4]143但“从根本上说,人与人的关系不能不表现为一种矛盾、冲突,乃至敌对状态,其中每个人都想保持自己的主体性,同时又把对方当作客体。”[5]26另一方面,我实际上是一种被“注视的存在”,是一种“为他”的存在;反过来,它又向我显示了无可置疑的他人的存在。[4]135萨特解释说:“一切对我有价值的都对他人有价值。然而我努力把我从他人的支配中解放出来,反过来力图控制他人,而他人也同时力图控制我。……冲突是为他的存在的原始意义。”[4]62在这种处境中,“他人就是地狱”就是人与人现实关系的真实写照。对方先生来说,假文凭在众人注视下,使方鸿渐时常产生羞耻感,就像长在肉里的一根刺,隐隐地刺痛他的内心和灵魂。我对我所是的东西感到羞耻,我通过羞耻发现了我的存在。这种羞耻也源自他人介入和干扰的生活所致,他人的存在对我构成一种威胁。在爱情的角逐中,苏小姐布置陷阱,让方处于她的控制下,并由于她的“捣蛋”让我错失梦寐以求的唐小姐。苏小姐的存在对我的存在构成一种限制和一种潜伏的威胁,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于紧张和敌对中。在派系林立的三闾大学,关系错综复杂,人与人之间互相钳制,互相利用,互相打击。方先生身处这样的罗网中,感到无所适从。先是被降格为“副教授”,后来遭到暗算,最后被逐出“围城”之外。他人的存在挤兑我的生存空间,我教学钟点少,而且不属于某一个系某一个专业,处境十分尴尬。可见,“在创造未来的过程中,个人的存在仍然是困难重重的。他发现周围的世界无时无刻在包围着它,限制着它、威胁着它的存在”。[6]144在个体与社会的关系中,存在主义将个体与他人对立,这无疑都是对存在主义的“为他存在”观点的最好注解。
三 存在主义本土化与《围城》的审美价值
西方的存在主义是一个很庞杂的思想体系,但经典存在主义哲学与文学都是一种具有明确的超越世俗性精神的艺术审美的价值意义建构。[7]但钱钟书能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大众的审美心理对存在主义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造性阐释,形成了富有中国精神、带有世俗化迹象的“中国化的存在主义”,从而创造了一个可与卡夫卡的《城堡》和加缪的《局外人》比并的、又拥有独特的品格和气韵的“《围城》世界”,堪称是对人的存在性困境的经典性阐释。这表现在:不同于《局外人》之类的作品对现实性存在困境的神圣的超越,《围城》描绘、讽喻的是“城内”世俗化存在的困窘。“正是通过方鸿渐的存在体验,钱钟书深入地揭示了人生的虚无和无奈的荒诞。”[8]211作者对世俗化生存的大彻大悟使《围城》入“俗”更出“俗”——以大俗而通大雅。另外他把时代和社会背景推得稍远,淡化西方存在主义文学中固有的象征色彩,近距离地剖析小说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而提升为人的普遍生存状态,这就在深奥、抽象之余,多了一份现实和亲切,更合乎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心理和欣赏趣味,更易于被中国人接受。这在《局外人》中的主人公莫尔索和《围城》的主人公方鸿渐身上体现得尤为鲜明,其实,人们在现实中很难像“局外人”那样超脱一切,更像方鸿渐那样面临人生真切实在的诸如荒诞、虚无、孤独的种种困境。再者,西方存在主义文学充满悲观主义气息,但钱钟书通过对一个畏怯终极性的虚无而失去存在勇气的现代人的批判,强调了不畏终极虚无而进行自我肯定的存在勇气,从而给人存在的信心和希望,所以《围城》并非悲观之作。所有这些让读者看到了西方存在主义经由钱钟书的创造性使用而使存在主义“本土化”的痕迹。
由于存在主义对《围城》的介入,使作品呈现出新的艺术—审美特点。第一,《围城》描写的具体形象场景中内含的形而上意蕴使其成为对人的存在状况的本体象征,从而使作品的语象、主题以至于所创造的整个世界都成为一个本体性象征,因而具有象征性。第二,虽然作品的描写和叙述具有情境规定性,因而其意义可感知,但我们必须承认作品的意蕴已超越了具体的写实情境,指向了更高、更广、更具普遍性的领域,一个形而上的领域,因而具有抽象的超越性。第三,《围城》悖论、讽刺的语言既是对荒诞的存在本身的折射,又是对复杂、悖谬、矛盾的人生本身的反映,其揭示的荒诞感和矛盾感更是钱钟书对整个实存世界的哲学态度和情感态度,因而具有复义性。其次,深刻的具有严肃意义的荒诞感已经成为《围城》鲜明的美学范畴和艺术风格。它与存在主义哲学和现代派文学分不开。荒诞非理性,是一种无可逃避的真实,他在我们心中引起绝望的情绪,使我们走上绝望的反抗,成为荒诞的英雄,或是无力承受重压而逃避,结果坠入非本真的存在,《围城》的主人公则成为后者。从文学上说,荒诞之美既超常又根本相关,既悖谬又不待理性去去证明。《围城》向荒诞微笑,这些至今令人心折。再次,与荒诞相连的全新的悲剧。这种悲剧表现出人类失去终极意义之源的困惑与迷惘,显示人对其存在的最深切的根本关怀。面对存在的虚无和荒诞,悲剧的主人公因为畏惧而逃避,最后萎缩为空无所有、一事无成的人。这种悲剧和悲剧形象的出现,是一种崭新的现象。最后,从非理性情绪体验的角度来理解存在,在传统心理领域开辟了崭新的领域,使绝望、恐怖、焦虑等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情绪进入了文学描写领域,这是一个新的开拓。存在主义赋予作品的种种特质,也是《围城》具有永恒生命力的深层原因。
当然《围城》与存在主义发生关系的契机也离不开 40年代上海的社会现实环境。一方面,当西方现代文明陷入危机之时,生活在中国的上海、香港这些世界性大都市的知识分子,久困于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一旦有睹现代文明、生活、生活方式,便呈现病态,这自然引起钱钟书的关注和反思。而且他也有留学的经历,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弊病和现代人生的困境有切身的感受和观察。这就为他接受存在主义思潮提供现实基础。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危机与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一拍即合,致使他们对存在主义哲学产生兴趣。另外20世纪各民族的思想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或彼此影响,不约而同达到某种契合。尤其是各民族的思想文化先锋,突破狭隘的民族范围思考一些世界性人类性问题,或者从世界、人类的观点来观察民族的局部的问题。这可以看作他接受存在主义的思想影响。所以说钱钟书突破狭隘的民族范围而把现代文明、现代人生的危机当作一个世界性、人类性的问题来思考,他的思考与存在主义相契合不难理解。
总之,由于存在主义的渗透,《围城》看待生活的视角、表达的主题思想、塑造的人物形象、作品的哲理意蕴等,都不可避免地打上了存在主义的烙印。而钱钟书对存在主义的运用又使《围城》具有了迥异于同时代文学的新特质。存在主义对个体存在的关注与探索,对荒诞性的揭示,对新时期小说、新写实小说关于孤独个体人的虚无、焦虑、自由选择、烦恼的生存意识等都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这也许就是《围城》长久不衰的奥秘吧。
[1]敏泽.论钱学的基本精神和历史贡献[J].文学评论,1999, (3):52.
[2][苏]叶甫尼娜.评法国现代派小说[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3]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4]李杰.萨特:荒谬人格[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1996.
[5]黄颂杰,吴晓明,安延明.萨特其人及其“人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
[6][法]高宣扬.萨特的密码[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
[7]杨经建.从超越性到世俗性——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本土化表征之一[J].天津社会科学,2009,(6).
[8]解志熙.生的执著:存在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
(责任编校:张京华)
I206.6
A
1673-2219(2012)09-0044-04
2012-06-11
郑明娥(1975-),女,湖南怀化人,怀化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