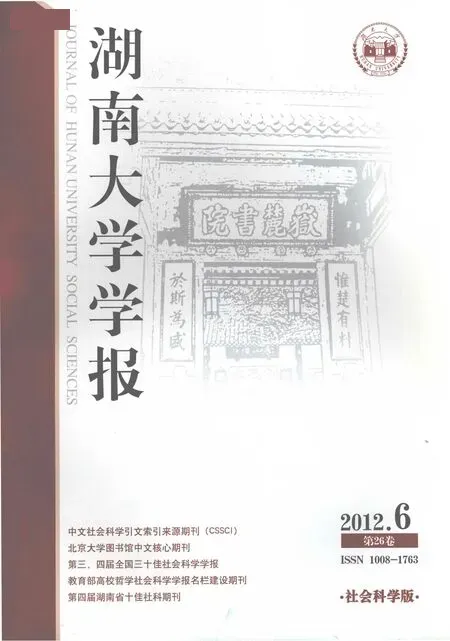邵雍“观物”说的定位*由朱子的批评而思
方旭东
(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 上海 200241)
“观物”说是邵雍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论者对它的定位很不相同。①关于晚近二十年国内邵雍研究的一般情况,可参看张显运:《邵雍研究:二十年学术史的回顾与展望》(《孔子研究》2012年第3期,33-43页);港台地区的邵雍研究,可参看杜保瑞:《邵雍儒学建构之义理探究》(《华梵人文学报》第三期,2004年6月,75至124页);英文世界的邵雍研究,可参看J.D.Birdwhistell为《中国哲学百科全书》所写的“邵雍”词条(“Shao Yong(Shao Yung)”,by Joanne D.Birdwhistell,in Antonio S.Cua ed.,Encyclopedia of Chinese Philosophy,pp.683-689.)按:杜文介绍了牟宗三、方东美、劳思光、唐君毅等四家意见,其中,牟宗三《心体与性体》对邵雍未置一词,方东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强调邵雍由道转儒,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对邵雍之说评价甚低,以其人为“山人隐士”(叶适语),其学“非正道所在”(二程语),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论邵雍最详,然议及观物说,则以为与佛家之如如现观只有微别,遂引朱熹语“康节之学,近似释氏”而结。Birdwhistell认为邵雍在历史上是一过渡性人物,在他身上,庄子、佛教的影响宛然可见。(Encyclopedia of Chinese Philosophy,p.688)具体说来,邵雍提出的“以物观物”,究竟主要是一种认识论方法,还是修养方法,抑或两者都是?在思想性质上它究竟属于儒家还是更近于佛道?如果它的本色仍是儒家,那么,在儒家经典上是否可以找到它的根据?对于这些问题,前贤时杰看法不一甚至针锋相对②如冯友兰认为,邵雍所说的“观物”既是认识论方法,又是修养方法。作为认识论方法,“以物观物”是要尊重事物的本来面目。(参见所著《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三松堂全集》第十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79-80页。)侯外庐学派则主要从认识论角度看待邵雍的“观物”方法,认为,邵雍的“观物”不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事物,而是禅观式的直观主义。(参见:《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第十章“北宋唯心主义道学的形成”,北京:人民出版社,1959年,522-532页;《宋明理学史》第五章“邵雍的象数学思想体系”,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202-203页)陈来着重从人生境界方面理解邵雍的“观物”,认为邵雍的以物观物说主要目的在于倡导一种无我的生活态度与境界,而不是为了实现某种认知的功能。(参见所著《宋明理学》,第二章“北宋理学的建立与发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94-96页),实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本文拟从朱子对邵雍观物说的批评入手,尝试对其重新做出定位。之所以由朱子而思,一方面是因为后世的一些看法大体没有超出朱子论述的范围,甚或只是祖述朱说而已,而现有邵雍观物说的研究似未见对朱子观点予以自觉检讨。另一方面,从理论上看,朱子对邵雍观物说的评论牵涉道学工夫论的内在分歧,则研究朱子之议,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邵雍之学,同时也将加深我们对朱子学乃至整个道学的认识。
一 朱子对邵雍观物说的批评
《朱子语类》卷一百专论邵子之书,其中,涉及“观物”说者主要有两条,一说其学近“释”,一说其学似“老”,几乎全盘否定。以下且观其详。
(一)近“释”
朱子以为,邵雍之学与佛家近似,区别只在他又讲数学:“康节之学,近似释氏,但却又挨傍消息盈虚者言之。”①《朱子语类》卷一百,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2544页。
此处“近似释氏”,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讲的?从朱子与门人的谈话可知,邵雍《伊川击壤集序》“以道观道”那段话被当作一个证据。
问:“《击壤序》中‘以道观道’等语,是物各付物之意否?”曰:“然。盖自家都不犯手之意。道是指阴阳运行者言之。”又问:“如此,则性与心身都不相管摄,亡者自亡,存者自存否?”曰:“某固言其与佛学相近者,此也。”(《朱子语类》卷一百,2544页)
朱子认为,“以道观道”这些话所说意思无非是“自家都不犯手”,即置身事外,让事物自行其是。与朱子对话的吴必大从中推出一个结论说,如此一来,道、性、心、身、物等就变成互不相干的东西了。朱子对此首肯,表示他所说的邵雍之学与佛学相近就体现在这里。不过,朱子没有点明观物说究竟与佛家的什么教义相近。
从文本上看,吴必大所言“性与心身都不相管摄”被朱子认可为邵雍之学与佛学相近的根据。然而,说“不以性观心,而以心观心,不以心观身,而以身观身”必致“性与心身都不相管摄”,显系对“以身观身”等语的误读。邵雍强调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不是要割断道、性、心、身、物之间的联系,而是要求从这些事物本身去考虑问题,不越俎代庖,以避免心性、身心等发生冲突时带来的麻烦,所谓“离乎害者”。事实上,“性者道之形体,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区宇,物者身之舟车”那些说法②《伊川击壤集序》,《邵雍集》,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179页。表明,道与性,性与心,心与身,身与物,在邵雍看来,是不可分割的。而且,“以道观道”这段话,邵雍后来用“以物观物”这个说法对其原则做了概括。也就是说,对于“以道观道”等语,不能再拘泥于它原来所指。无论如何,要说邵雍之学与佛学相近,还需要提供更有力的证明。
值得注意的是,朱子在此还同意“以物观物”与出自程颐的“物各付物”说在理论上有相近之处。
(二)似“老”
朱子不止认为邵雍之学近“释”,又称其说似“老”。朱子此论仍以《击壤集序》“以道观道”等语为据。
因论康节之学,曰:“似老子。只是自要寻个宽间快活处,人皆害它不得。后来张子房亦是如此。方众人纷拏扰扰时,它自在背处。”人杰因问:“《击壤集序》有‘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以身观物;治则治矣,犹未离乎害也’。上四句自说得好,却云‘未离乎害’。其下云:‘不若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虽欲相伤,其可得乎?若然,则以家观家,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亦从而可知也。’恐如上四句,似合圣人之中道;‘以道观道’而下,皆付之自然,未免有差否?”曰:“公且说前四句。”曰:“性只是仁义礼智,乃是道也。心则统乎性,身则主乎心,此三句可解。至于物,则身之所资以为用者也。”曰:“此非康节之意。既不得其意,如何议论它?”人杰因请教。先生曰:“‘以道观性’者,道是自然底道理,性则有刚柔善恶参差不齐处,是道不能以该尽此性也。性有仁义礼智之善,心却千思万虑,出入无时,是性不能以该尽此心也。心欲如此,而身却不能如此,是心有不能检其身处。以一身而观物,亦有不能尽其情状变态处,此则未离乎害之意也。且以一事言之:若好人之所好,恶人之所恶,是‘以物观物’之意;若以己之好恶律人,则是‘以身观物’者也。”又问:“如此,则康节‘以道观道’等说,果为无病否?”曰:“谓之无病不可,谓之有病亦不可。若使孔孟言之,必不肯如此说。渠自是一样意思。如‘以天下观天下’,其说出于老子。”又问:“如此,则‘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三句,义理有可通者,但‘以身观物’一句为不可通耳。”曰:“若论‘万物皆备于我’,则‘以身观物’,亦何不可之有?”〔人杰〕(《朱子语类》卷一百,2544-2545页。着重号为引者后加,下同,不再一一说明)
此条语录甚长,首论邵雍之学似老子,而后详参《击壤序》“以道观道”诸语。
关于邵雍之学与老子的相似,据朱子说,有两点:一、“只是自要寻个宽间快活处,人皆害它不得”,二、“方众人纷拏扰扰时,它自在背处”。前者可谓“全身避害”,后者可谓“与众不同”、“逍遥自在”。
关于《击壤序》“以道观道”诸语,朱子不同意弟子万人杰的解读。后者将“以道观性”四句与“以道观道”四句分开看,认为前四句说得好③准确地说,万人杰欣赏的是前三句,即:“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而对最后一句“以身观物”感到不解。在他看来,仁义礼智之性是道,性统心,心主身,换言之,道对性,性对心,心对身,每组概念之间存在主从的关系,因此,说“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是符合圣人行事之道的,是可以理解的。可是,物是身之所资以为用者,也就是说,身跟物之间,似乎不存在心跟身、性跟心、道跟心之间那样的关系,从而,“以身观物”究竟怎么观,就令人费解。(所以,后面万人杰说“以身观物一句为不可通”。)让万人杰感到困惑的是,“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已经近于圣人中道,为何邵雍还要说它“犹未离乎害”?,符合圣人之中道,后四句说得不好,近于道家崇尚自然之学。朱子认为万人杰没有领会邵雍所说的“以道观性”诸语之意,遂亲自为之分疏。在万人杰那里,性就是道,心统乎性,身主乎心。而在朱子看来,性非道所能尽,心非性所能尽,身有心所不能检处,物有身所不能尽其情态处。职是之故,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以身观物,皆有所不尽,难免遗憾,邵雍所说“犹未离乎害”即指此而言。
在对“以道观性”等语的具体解释上,朱子明显维护邵雍,他告诫弟子不可妄议。然而,当万人杰问“以道观道”之说究竟有病无病时,朱子却给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回答。这表明,朱子对邵雍“以道观道”说并不完全满意。从后面的说明来看,让他感到不满的是邵雍用语杂染了老子绪言,已非纯粹的儒家之辞。
总体上,朱子对邵雍“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以身观物”的说法是给予肯定的。据此判断,开头他说邵雍之学似老子,当指邵雍的某些用语出于老子,而不是说邵雍这些话在精神实质上与老子近似。
值得注意的是,朱子还从好恶角度对“以身观物”与“以物观物”做了辨析,认为前者是“以己之好恶律人”,后者是“好人之所好,恶人之所恶”。
朱子对邵雍观物说的评论,大略如上。从篇幅上看,它在整个“邵子之书”卷中并不显赫,但所言关系极大,“近释”“似老”云云,直指邵雍思想性质归属的敏感话题。如果只是望文生义,一定会形成朱子全盘否定邵雍观物说的印象。然而,一旦深入其中,则发现,事情并不如此简单:朱子对观物之说既有批评,也有维护,态度似在两可之间。朱子既注意到“观物”诸语与佛道的渊源,同时又肯定它与“好人之所好,恶人之所恶”以及“物各付物”等儒家思想的关联。
二 由朱子的批评而思
朱子批评邵雍观物说的两个要点,不同程度都为后世学者承继,相对而言,第一点,尤其是“以物观物”与佛教义理的相似,历代学者多袭其说;第二点,尤其是观物说与孔子“好恶与人同”思想的比较,后世则发挥不多。以下,我们逐个考察。
(一)“以物观物”与佛教义理
前已述及,朱子论邵雍之学近释,却未指明“以物观物”究竟与佛家何种思想接近。现代学者乐做解人,或谓“以物观物”即是止观法门,或谓“以物观物”近似“如如现观”。
如侯外庐认为,“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出自佛学的止观说。①《中国思想通史》,522页。《宋明理学史》则将邵雍的“以理观物”称作“无思无为的内心自省的顿悟方法”或“禅观式的直观主义方法”。②《宋明理学史》,202-203页。
按:“止观”是佛教修习的重要方法,“止”,梵文作Samatha(奢摩他),意为“止寂”或“禅定”;“观”,梵文作 Vipasyana(毗婆舍那),意为“智慧”。《维摩诘经》卷五僧肇注:“系心于缘谓之止,分别深达谓之观”。“止”是使所观察对象“住心于内”,不让注意力分散;“观”是在“止”的基础上,集中观察思维预定对象,达得智慧。天台宗强调“止观双修”,将“止观”视为一切修习方法的概括。其他宗派,如法相宗、禅宗,亦有类似说法。③参见任继愈主编:《佛教大辞典》,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271页。然而,邵雍所说的“以物观物”、“以理观物”以及“圣人反观”,中心大意是,观察事物时不要带有主体的个人立场。就此而言,它与佛教所说的“止观双修”(天台宗)、“奢摩他与毗婆舍那并行”(法相宗)或“定慧等学”(禅宗)其实并不相同。排除个人立场的“以理观物”,与其说是“直观主义方法”,不如说更近于一种“理智抽象”。无论如何,从邵雍对“以物观物”的描述来看,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它是一种“顿悟方法”。而用以分别“以物观物”与“以我观物”的性情之辨更是地道的儒家话语,典出《论语》、《大学》(详下),与佛教的“止观”了不相干。
港台新儒家唐君毅则将朱子所论“康节之学近似释氏”直接坐实为“如如现观”。
至其(引者按邵雍)观物之论之至极,则其《击壤集序》有“以道观性,以性观心,以心观身,治则治矣,犹未离于言也。若以道观道,以性观性,以心观心,以身观身,以物观物,虽欲相伤,其可得乎”,则上所谓“性者道之形体,心者性之郛廓也,身者心之区宇,物者身之舟舆”之言,盖尚非康节之究极之义。唯一切顺观,而道如其道,心如其心,身如其身,物如其物以观,乃为其究极之义。此其学之归止义,与佛家之如如现观之别,盖亦微矣。此盖即朱子之谓“康节之学,近似释氏”也。(《语类》卷一百④原文误作卷一百一十,今据实校改。)(《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28页)
唐君毅首先对“以道观道”句重新做了解读,认为,“以道观道”这段话实际上覆盖了“性者道之形体”那段话,“以道观道”才是邵雍最终要表达的意思(究极之义)。而“以道观道”等语的意思就是“一切顺观”。这种顺观,唐君毅认为,与佛家的“如如现观”思想区别甚微。
按:佛家所谓“如”,指如其本然之体性相状,与“真如”、“如如”、“实际”、“法性”、“法相”等含义相近。《维摩诘经-菩萨品》:“如者不二不异”。《大智度论》卷三二:“佛弟子如法本相观。”⑤《佛教大辞典》,576页。“如如”则是“真如”的异译,指佛教智慧所契会之真理。《大乘义章》卷三:“正智所契之理,诸法体同,故名为如;就一如中,体备法界恒沙佛法,随法辨如,如义非一,彼此皆如,故曰如如。如非虚妄,故复经中亦名真如。”意谓“如”为遍布一切法之共相,“如如”为体现为个别法中的共相。⑥《佛教大辞典》,576-577页。“现观”为法相宗(唯识宗)名词,即现前观察,意谓对所知境的直觉性观察,《成唯识论述记》卷九:“现谓现前,明了现前,观此现境,故名现观。”所谓“明了现前”,就是现量直觉的特性。同论又谓:“现观者,慧现观诸法”,则强调是以特定智慧去明了观察现前诸境。《瑜伽师地论》卷三四:“由能知智与所知境和合无乖,现前观察,故名现观,如刹帝利与刹帝利和合无乖,现前观察。”“所知智”即概念,“所知境”即现实对象。据此,以特定概念观察相应的事物,二者无所乖违,亦名现观。法相家多以“现观”为“见道”时明见谛理的一种认识活动,故有“圣谛现观”、“二现观”、“三现观”、“六现观”等说。①《佛教大辞典》,732页。
与侯外庐等人将邵雍的观物说与天台止观以及禅宗直观比附不同,唐君毅在法相宗那里找到邵雍观物说的友声。然而,跟“止观”或“禅观”的说法一样,“现观”一说仍然没有摆脱仅仅抓住观物说中的“观”字进行联想的思维模式。
原唐氏之意,“如如现观”似指当下运用直觉去明了所观察之物的本性,其说已非“如如”与“现观”二名的佛家本义。更重要的是,无论是止观还是禅观或现观乃至直观,都不能贴切地反映邵雍取自《易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中的“理”字而来的“以理观物”之意。虽然邵雍的穷理之学不如程颐、朱熹那么有名,但邵雍用来承载其观物说的理论基石是“理”和“性”,这一点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观物内篇-第十二篇》,《邵雍集》49页),“以物观物,性也”(《观物外篇下之中》,《邵雍集》152页)。
(二)“以物观物”与“付之自然”
前已述及,朱子批评邵雍之学似老子,似乎主要不是说邵雍之学的精神与老子近似②当然,就“全身避害”或“明哲保身”这一点而言,朱子批评邵雍似“老”,并非毫无道理。事实上,邵雍确实非常注意“保身”或“润身”:“君子之学,以润身为本。其治人应物,皆余事也。”(《观物外篇下之中》,《邵雍集》156页)“得天理者,不独润身,亦能润心。不独润心,至于性命亦润。”(《观物外篇下之中》,《邵雍集》156页),而是指邵雍的某些用语出于老子,比如,邵雍在论述“以物观物”思想时使用的“以天下观天下”这样的话,朱子指出,就是出于老子③《老子》第五十四章:“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邵雍观物说与道家思想的关联,真正需要认真对待的是,朱子没有正面陈述但在与学生的讨论中已经涉及,邵雍的观物说与道家的“付之自然”思想是否有共通之处。④认为邵雍的“以道观道”、“以物观物”有一切“付之自然”的意思,这个说法是万人杰在讨论中首先提出来的。朱子不同意万人杰对“以道观道”那段话的解读,但没有直接回应“‘以道观道’以下皆付之自然”这个说法,只提了一句“道是自然底道理”。因此,朱子是否认为邵雍的观物说有付之自然之意,并不清楚。
从邵雍的一贯表述来看,他对“循自然之理”的观点甚表欣赏。
《易》之为书,“将以顺性命之理”者,循自然也。孔子“绝四”、“从心”,“一以贯之”,“至命”者也。颜子“心斋”“屡空”,“好学”者也。子贡多积以为学,亿度以求道,不能刳心灭见,委身于理,“不受命”者也。《春秋》循自然之理,而不立私意,故为“尽性”之书也。(《观物外篇下之下》,《邵雍集》166页,引用时标点有所改动)
“将以顺性命之理”语出《说卦传》⑤原文为:“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下文“至命”、“尽性”等语则化自《易传》“穷理尽性以至于命”。邵雍用《易传》的“理—性—命”话语解释《论语》以及《春秋》,反映他的义理框架受《易传》影响甚深。
在邵雍看来,“顺性命之理”即是“循自然(之理)”,而“循自然之理”则要求“不立私意”。能“不立私意”就意味着能够“尽性”。
《易传》、《春秋》等书并没有出现“自然”这样的字眼。邵雍用“循自然(之理)”来诠释《易传》、《春秋》,当属个人发挥。“自然”一词带有较浓的道家气息。邵雍当然熟悉老庄之书,本段“颜子心斋屡空”一句就直接引用了庄子对颜回的评语“心斋”(《庄子·人间世》)。不过,邵雍所说的“循自然(之理)”并不就是道家意义上的(如《老子》第二十五章所云“道法自然”),而主要是指不带个人主观意见,即孔子“绝四”中的“毋意”、“毋我”(《论语·子罕》)。⑥邵雍认为,孔子“绝四”中的“毋意”、“毋我”最是关键:“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合而言之则一,分而言之则二;合而言之则二,分而言之则四。始于有意,成于有我,有意然后有必,必生于意,有固然后有我,我生于固,意有心必先期,固不化我有己也。”(《观物外篇下之下》,《邵雍集》178页)从邵雍对子贡的评价“亿度以求道,不能刳心灭见,委身于理,不受命者也”来看,“循自然(之理)”的反面似乎就是“不能刳心灭见,委身于理”。易言之,“循自然之理”就是能消除己见(刳心灭见),完全听从理的安排(委身于理)。因此,“循(顺)自然之理”的重点不在“循(顺)自然”而在“循(顺)理”。而“循理”或“委身于理”的主要表现就是“不立私意”(简称“无私”)。
《庄子》一书曾借孔子之口说出“蹈水之道无私”的道理:
孔子观于吕梁,悬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亀鱼鳖之所不能游也。见一丈夫游之,以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并流而拯之。数百步而出,被发行歌而游于塘下。孔子从而问焉,曰:“吾以子为鬼,察子则人也。请问蹈水有道乎?”曰:“亡,吾无道。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与齐俱入,与汩偕出,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庄子·达生》)
邵雍对庄子的这个概括推崇备至。
庄周雄辩,数千年一人而已。如庖丁解牛曰“踯躅”、“四顾”,孔子观吕梁之水曰“蹈水之道无私”,皆至理之言也。(《观物外篇下之中》,《邵雍集》157页)
庄子气豪,若吕梁之事,言之至者也。(《观物外篇下之下》,《邵雍集》176页)
不难看出,邵雍所说的“无私”就是《庄子》原文所说的“不为私”。所谓“不为私”,就是待人接物不以自我为中心。单就“无私(我)”而论,佛家也有破除“我执”的教导;单就“自然”而论,玄学(魏晋新道家)即说“越名教而任自然”①语出嵇康:“夫称君子者,心无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物情顺通,故大道无违;越名任心,故是非无措也。”(《释私论》,《嵇康集》第六卷,《鲁迅全集》第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87页)。关键在于,邵雍所说的“自然”是包括人伦在内的,这就使他与“弃君臣父子夫妇之道”的佛教以及视“名教”为“自然”对立面的玄学(魏晋新道家)区分开来。不了解这一点,就不明白邵雍对佛教的如下批评。
佛氏弃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岂自然之理哉?(《观物外篇下之下》,《邵雍集》176页)
同理,对邵雍有关“无为”的说法也不应与道家的“无为”混为一谈。《宋明理学史》的作者曾根据邵雍集中有关“无为”的若干表述而将邵雍的“以理观物”称作“无思无为的内心自省的顿悟方法”。
……邵雍不说由“我”观物,而说以“理”观物。这一点他在《皇极经世书》的另外地方又说,人们观物应当“无思无为”,以此来“洗心”,这也叫做“顺理”,“顺理则无为,强者有为也”(《皇极经世书》卷十二)这是否说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事物呢?不是的。实际上这是无思无为的内心自省的顿悟方法,或者叫做禅观式的直观主义方法。②《宋明理学史》,202-203页。
关于“禅观式的直观主义方法”,上文已做辨证,这里再就邵雍所说的“无思无为”的理解问题做些讨论。“无思无为”、“洗心”之说出自下面这段话:
庄子“齐物”,未免乎较量,较量则争,争则不平,不平则不和。“无思无为”者,神妙致一之地也。(所谓“一以贯之”。)“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观物外篇下之下》,《邵雍集》175-176页,引用时标点有所改动)
可以看到,“无思无为”云云,是邵雍在批判庄子“齐物论”之后紧接着讲的。而“无思无为”以及“洗心退藏于密”均出自《易·系辞》③“《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易·系辞上》第十章)“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神以知来,知以藏往,其孰能与于此哉!”(《易·系辞上》第十一章)。如果不否认《系辞》的儒家性质,那么,应该说,邵雍对儒家思想的认同是很清楚的。而且,邵雍自己在“无思无为”这句话后还加了一个注:“所谓‘一以贯之’”,联系前揭“孔子‘绝四’、‘从心’,‘一以贯之’,‘至命’者也”那段话,有理由认为,邵雍所说的“无思无为”近于“不立私意”,也就是说,语义侧重在“无思”。邵雍也曾将“无为”单独提出过:“盗跖言事之无可奈何者,虽圣人亦莫如之何。渔父言事之不可强者,虽圣人亦不可强。此言有为无为之理,顺理则无为,强则有为也。”(《观物外篇下之下》,《邵雍集》176页)“顺理则无为,强则有为”,这句话是描述“有为无为之理”,即探讨在何种情况下会出现“有为”,何种情况下会发生“无为”。以邵雍之见,“无为”是“顺理”的结果。可见,邵雍念兹在兹的不是“无为”,而是“顺理”。
(三)“以物观物”与“好人之所好,恶人之所恶”
朱子在分析邵雍观物说时引入好恶问题,按他的理解,“以物观物”就是“好人之所好,恶人之所恶”,而“以身观物”则是“以己之好恶律人”。这就将邵雍的观物说与先秦儒家经典挂搭起来。
先秦儒家经典《论语》与《大学》都有“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这样的说法。《论语》:“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大学》:“唯仁人放流之,迸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很明显,《大学》引用了《论语》“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那句话,但它也有所发展,那就是提出了“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的问题。《大学》作者是将“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作为反面教材看待的,所谓“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言下之意,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好人之所好,恶人之所恶”。至此,通过将“好人”“恶人”补足为“好人之所好”、“恶人之所恶”,《大学》对所引《论语》“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的句意做了一个不易为人察觉的推移。本来,在《论语》原文中,“人”是作为主体好恶的对象存在,可是一旦将“能好人能恶人”理解为“能好人之所好,能恶人之所恶”,“人”的角色就发生了变化,成为主体好恶的参照系。
《大学》所做的这种引申在某些《论语》诠释者那里可以找到共鸣。比如,汉代孔安国即认为,“惟仁者能好人能恶人”的意思是说“惟仁者能审人之好恶也”④何晏解,皇侃疏:《论语集解义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二。。清代焦循在《论语补疏》中对孔说表示附和:“仁者好人之所好,恶人之所恶,故为能好能恶。必先审人之所好所恶,然后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恶恶之,斯为能好能恶也。”⑤转引自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141页。
然而,从《论语》本文看,将“能好人能恶人”理解为“能好人之所好,能恶人之所恶”缺乏足够的文本支持。仅就“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分析,难点在“能”字上:何以只有仁者才能好人、恶人?像朱子这样的诠释者正面回应了这个问题。《论语集注》云:
唯之为言独也。盖无私心,然后好恶当于理,程子所谓“得其公正”是也。⑥程颐在解《论语》4.3章时曾言简意赅地评论说:“得其公正也。”(《河南程氏经说卷第六-论语解》,《二程集》,1137页)从“公”这一角度看待《论语》这段话,不独程颐,程门弟子亦然,如尹淳(和靖),《朱子语类》载:“问:和靖语录中有两段言仁:一云:某谓仁者公而已。伊川曰:‘何谓也?’曰:‘能好人,能恶人。’伊川曰:‘善涵养。’……”(《朱子语类》卷九十七,2486页)朱熹又用“无私心”来解释“公”字,以“好恶当于理”来解“正”字,“公是心里公,正是好恶得来当理”。(《朱子语类》卷二十六)游氏曰:“好善而恶恶,天下之同情。然人每失其正者,心有所系而不能自克也。唯仁者无私心,所以能好恶也。”(《论语集注》卷二,《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69页)
依朱子,何以只有仁者才能好人、恶人?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因为只有仁者无私心,从而其好恶能不失其正。这个回答的重点在于“能”字被理解为“能正确或恰当地做某事”。就经典诠释的要求来看,朱子的这种解说也存在一定问题:“好恶当于理”的“理”字在《论语》中遍寻不着,不免有“增字解经”之嫌。
朱子没有正面驳斥孔注,这或许暗示,在他的解释与孔注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关系。清人梁章钜(1775—1849)即认为:“《集注》似与孔《注》不同,而其实正相发明也。盖惟仁者好人之所好,恶人之所恶。必先审人之所好所恶,而后人之所好好之,人之所恶恶之,斯为能好恶,非公正同情而何哉?”(《论语旁证》,转引自《论语集释》卷七,230页)
无论如何,当朱子用“好人之所好,恶人之所恶”与“以己之好恶律人”分别匹配“以物观物”与“以身观物”时,他所想到的主要是公私之辨。“好人之所好,恶人之所恶”,作为“以己之好恶律人”的反面,说的无非是所好所恶不掺一丝一毫私意。“公”则“正”,“私”则“不正”。朱子用“公正”来评价“以物观物”也符合邵雍自己的定位,在后者那里,“以物观物”对应的是:性—公—明,“以我观物”对应的则是:情—偏—暗:“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性公而明,情偏而暗。”(《观物外篇下之中》,《邵雍集》152页)“偏”即“偏倚”,“公”即“不偏不倚”。
引入“好恶”问题评论邵雍观物说,显示出,在朱子那里,“以物观物”未尝不可以视作处理情感好恶的原则。
(四)“以物观物”与“物各付物”
“物各付物”是程颐常提的话头:
人多思虑不能自宁,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于事,为人君止于仁之类。如舜之诛四凶。四凶已作恶,舜从而诛之,舜何与焉?人不止于事,只是揽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则是役物。为物所役,则是役于物。“有物必有则”,须是止于事。(《遗书》卷十五,《二程集》144页)
学佛者多要忘是非,是非安可忘得?自有许多道理,何事忘为?夫事外无心,心外无事。世人只被物所役,便觉苦事多。若物各付物,便役物也。世人只为一齐在那昏惑迷暗海中,拘滞执泥坑里,便事事转动不得,没着身处。(《遗书》卷十九,《二程集》263-264页)
程颐是在讨论如何获得心灵平静的问题时谈到“物各付物”的。换言之,程颐是把“物各付物”作为修身养性工夫来考虑的。程颐认为,人之所以失去心灵的平静,是因为没有正确地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程颐所说的“事”主要是指人的伦理实践,亦即人事。“止于事”的“止”与“为人君止于仁”的“止”是同一个意思,即明确自己的位置或责任在哪里。从程颐所举的例子来看,舜诛四凶,不是舜自己起心要杀四凶,而是服从“恶有恶报”的规律,在整个事件当中,舜没有放进自己半分情感。因此,“止于事”实际就是按照事物的本性、事情的规律行事。这个规律叫做“道理”,也叫做“则”,“有物必有则”的“则”。不能“止于事”就是未能按照事物的本性、事情的规律行事,其结果是,人将陷在无尽的事务之中,无法解脱。程颐还批评学佛者要忘是非的做法,认为是非不可能被忘记,人只需要按道理行事即可。程颐分析世人觉得苦事多的原因在于人在物面前失去了主动,遂为物所役。他号召人们运用“物各付物”的方法,即按照事物的本性、事情的规律去处理,就不会为纷至沓来的事情所困扰。
可以看到,“物各付物”在程颐这里主要是作为一种处事或实践的原则提出的。朱子同意学生提出的邵雍的“以道观道”是“物各付物之意”的说法,表明他没有局限于从认识论命题来看待邵雍的观物说。
以上,我们顺着朱子对邵雍观物说批评的几个要点逐一做了讨论。在此过程中,我们了解到,称邵雍观物说近“释”、似“老”,经不起推敲。与其说“以物观物”是受佛、道思想影响,不如说它的理论源头主要来自《易传》。朱子引入好恶之说解读“以物观物”,为邵雍观物说找到儒家经典依据,亦符合邵雍本人对“观物”的理解。朱子在“以物观物”与“好人之所好,恶人之所恶”以及“物各付物”等命题之间所做的比较,启发我们,“以物观物”主要不是认识论命题,而更多地与修身养性的工夫以及待人处世的伦理实践原则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