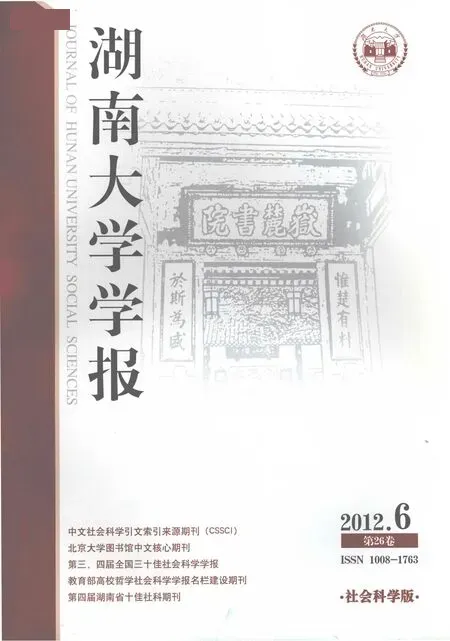朱子的境界论思想简论*
乔清举
(南开大学 哲 学学院,天津 300071)
“境界论”是现代中国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学说,中国传统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相结合的产物。著名哲学家冯友兰、金岳霖对境界问题都有十分深入的论述。我们尝试从他们的境界论的视角来研究朱子哲学。
一 境界说简论
(一)境界
冯友兰先生在《新原人》中提出了境界论和人生有四重境界的观点。他指出,人因有觉解而有境界;觉是自觉,解是理解。觉解是对于事物的意义的自觉、理解、体会和反思。“宇宙人生对于人所有底某种不同底意义,即构成人所有底某种境界。”[1](P496)他所说的“意义”,不是一般的 meaning,而是更深一层的significance。冯友兰把“境界”译为“sphere of living”。[2](P388)与他同时的另一位哲学家金岳霖也提出了境界论思想,用的是“Vista”。他说:“‘Vista’根据韦伯斯特大辞典(Webster Dictionary)的解释,指的‘首先是由沿着街道两旁延伸的树木所组成的景观或视野,其次是对于一系列事件的精神性的观点或视野。’我们保留这个词的观点和视野部分的意义,放弃它的树木、事件部分的意义。我们感兴趣的不是所见与所闻,而是从经验中获得的意味(significances)。”[3]这就是说,境界是由人对于自己与自己存在于其中的世界的关系的理解构成的。
(二)关于“天地境界”
照冯友兰所说,人对于宇宙人生的觉解,可有程度的不同。此不同程度之觉解,即构成不同程度之境界,有自然、功利、道德、天地四种。金岳霖则提出了朴素、英雄、圣人三重境界说。大体说来,朴素境界同于自然境界,英雄境界同于功利境界,圣人境界则近似于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我们集中于冯友兰的境界说。
冯友兰指出,境界有高低的差异,判断的依据是达到一种境界所需觉解的多少。需觉解多者境界高,反之低。自然境界所需觉解最少,故最低。功利境界高于自然境界而低于道德境界。道德境界高于功利境界而低于天地境界。天地境界所需要觉解最多,故最高。“至此种境界,人的觉解已发展至最高底程度。至此种程度人已尽其性。在此种境界中底人,谓之圣人。圣人是最完全底人,所以邵康节说:‘圣人,人之至者也。’”[1](P501)
在冯友兰的境界说中,自然境界是无觉解的状态,即一个人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的意义、目的,都没有自觉的反思。儿童的行为近于自然境界,但成年人的许多懵懂、不自觉、未加反思的行为,也属于自然境界。自然境界也不一定就是无所作为。一些做出很大功业的人,也可能是出于自然境界。功利境界的人有自觉和反思,他所作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的功利。功利有多方面,物质利益、生命的延长、心理的满足,都可以是功利。功利境界的人的行为甚至也可以合乎道德,但因其行为动机非出于义而出于利,故虽合乎道德而非道德行为。道德境界的人把自己置于社会与他人的关系之中,“其行为是‘行义’底”;是一种“尽伦尽职”的行为。天地境界是最高境界。有此种境界的人不仅对于社会有觉解,而且对于宇宙也有觉解。他的行为不仅是为社会、为他人奉献,而且也是为宇宙而奉献:
天地境界的特征是: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其行为是“事天”底。在此种境界中底人,了解于社会的全之外,还有宇宙的全,人必于知有宇宙的全时,始能使其所得于人之所以为人者尽最大发展,始能尽性。在此种境界中底人,有完全底高一层底觉解,此即是说,他已完全知性,因其已知天。他已知天,所以他知人不但是社会的全的一部分,而并且是宇宙的全的一部分。不但对于社会,人应有贡献;即对于宇宙,人亦应有贡献。人不但应在社会中,堂堂地做一个人;亦应于宇宙间,堂堂地做一个人。人的行为,不仅与社会有干系,而且与宇宙有干系。他觉解人虽只有七尺之躯,但可以“与天地参”;虽上寿不过百年,而可以“与天地比寿,与日月齐光”。[1](P500)
冯友兰提出了道德行为的自觉选择——意志的问题。他指出,功利境界以上,都是有自我的。功利境界是出于人的低一级的自我,是一种自私。道德行为是出于人的高一部分的自我,是道学家所说的自我主宰,这是意志自由。“西洋道德哲学中所谓意志自由,即中国道学家所谓自作主宰。”[1](P544)
冯友兰指出,天地境界的人,其境界还可进一步分为知天、事天、乐天、同天四个层次。天是宇宙。知天是人对于宇宙本身、人与宇宙的关系的觉解。“他又知他不但是社会的分子,而又是宇宙的分子。”[1](P561)“他又知他的生活,以及实际事物的变化,又都是道体中所有底程序。”[1](P562)“人有此等进一步底觉解,则可从大全、理及道体的观点,以看事物。从此等新的观点以看事物,正如斯宾诺莎所谓从永恒的形式的观点,以看事物。人能从此种新的观点以看事物,则一切事物对于他皆有一种新底意义。此种新意义,使人有一种新境界。此种新境界,即我们所谓天地境界。”[1](P562-563)在冯友兰看来,这种新的意义是超道德的意义,宇宙的意义:
无论什么事物,都是宇宙的一部分。人能从宇宙的观点看,则其对于任何事物底改善,对于任何事物底救济,都是对于宇宙底尽职。对于任何事物底了解,都是对于宇宙底了解。从此观点看,此各种的行为,都是事天底行为。《西铭》所说乾坤的观念,不必与我们所说宇宙的观念相合。其说“乾称父,坤称母”,亦未完全超过图画式底思想。但其从事天的观点,以看道德底行为,因此与道德底行为,有超道德底意义。[1](P566)
冯友兰主张,事天是参赞化育,与天地参。太极是形而上的理世界,形而下的物世界的标准和目标。“大化流行,以太极为目标;事天者赞化,亦以太极为目标”;是“穷世界之理,尽世界之性”,实现世界的善,“世界的目标”。[1](P569)对于知天者来说,不仅他的所作所为具有新的意义,而且外部事物对他来说,也具有新的意义。“如《论语》说:‘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宋儒以为孔子于水之流行,见道体之流行。《中庸》引诗:‘鸢飞戾天,鱼跃于渊。’宋儒以为于此可见‘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此说虽未必即《论语》、《中庸》之本意,但水之流行,以及鸢飞鱼跃,对于知天者,都可另有意义,这是可以说底。”[1](P567)这种新的意义,能使知天者在自然界中发现他人所不能见之乐,这即是“乐天”。冯友兰指出,《论语》中曾皙言志一段、孔颜乐处一段,都是乐天的表现。
天地境界的最高造诣是“同天”,即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人“不但觉解其是大全的一部分,而并且自同于大全”,万物皆备,物我一如,“我”与“非我”的分别完全泯灭。他不但是以太极为目标参赞化育,而且自己即有整个的太极,“太极在所有底在同天境界中底人的心中,真可以说是如‘月印万川’”[1](P569)。
冯友兰指出,同天的境界也是儒家所说的仁的境界,浑然与物同体,痛痒相关。同天的境界又是“诚”的境界,泯灭与他人、与万物的界限,内外相和。天地境界的人还是有我与无我的统一。从“我”是私的角度看,天地境界是无我的;从“我”是主宰的角度看,天地境界又是有我的。天地境界的人,同于大全。他的自我扩展至于宇宙,成为大全的主宰:“‘我’即是大全的主宰”。“在天地境界中底人则自觉他的‘我’即是宇宙的主宰。如说是宇宙的主宰者即是上帝,则他的‘我’即是上帝。”[1](P573)在天地境界的人自同于天地,亦是自同于理。无古今、无生死、无主客:
在天地境界中底人,能同天者,亦可自同于理世界。理是永恒底,在天地境界中底人觉解一切事物,都不只是事物,而是永恒底理的例证。这些例证,是有生灭的,是无常底。但其所为例证底理,则是永恒底,是超时间底。对于理无所谓过去,亦无所谓现在。在天地境界中底人,觉解理不但不是无常底,而且是无所谓有常或无常底;不但不是有生灭底,而且是无所谓有生灭或无生灭底。他有此等觉解,所以自同于理世界者,自觉其自己亦是超生灭,超死生底。《庄子·大宗师》说:“见独则无古今。”理世界是无古今底,自同于理世界者,自觉其自己亦是无古今底。……在此种境界中底人,其身体随顺大化,以为存亡,但在精神上他可以说是超死生底。[1](P623~624)
于此我们说,本书以上所说所根据底形上学,诚以为离心有所谓外界。但在同天地境界中底人,‘与物冥’,‘浑然与物同体’,所以对于他,所谓内外之分,所谓主观客观的对立,亦已冥除。[1](P626)
冯友兰指出,天地境界中的人进行道德行为,得到一种高深的觉解。他们的行为“不是由一种特别有意底选择,所以行之亦不待努力”,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这是功夫纯熟的结果。
二 朱子的境界论
可否从境界论的角度来理解朱子哲学呢?答案是肯定的。从学术渊源上看,冯友兰新理学的源头正是程朱理学。诚如他自己所说,他是“接着”理学来讲自己的哲学的。他关于境界论的一些事例和论证,如关于仁、诚、道体的见解,都是来自朱子哲学的。从内容来看,朱子哲学可谓对于社会和宇宙的一种自觉,其性质符合境界论的特点,是可以从境界论的角度来认识的。以往的朱子哲学研究,因受主客体对立思维方式的影响,把重点置于格物问题,又把格物看作单纯的主客体认知关系,削弱了朱子哲学的中国特点。此种方式,首起端者,其为冯先生乎?牟先生对冯先生固多批评,但其研究范式则未出冯先生藩篱。故其人物评价虽然与冯先生截然相反,而对于朱子哲学的不少认识,却与冯先生实无二致。①见牟宗三先生所著《心体与性体》第三册(台北:正中书局,1969年初版)有关部分。李明辉先生亦认为,朱子的心理关系是一种“认知上的赅摄”(见氏著《康德与儒家》第10页等处。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年版)。何以竟然如此?皆因二人都是在主客对立的“哲学”范式下进行研究的缘故。②朱汉民先生亦有此论。关于此我们不谋而合。冯先生之研究,有在中国建立哲学传统的意义,朱子哲学于他亦为沟通中西的桥梁。鉴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大势,此种研究自有值得肯定之处。牟先生之研究,意在彰显中国哲学的价值,亦足值得赞叹,惜乎其仍然沿用主客二分的哲学范式,未能充分实现此意。时至今日,我们再来研究朱子,已大可不必蹈前人覆辙而袭其窠臼,而应展开更加切近于朱子哲学以至于中国哲学特点的多元化研究。应一步步地将朱子哲学还原于其固有语境之下,由哲学而理学(与心学对立),由理学而道学(包括心学),由道学而经学,由经学而儒学,庶几可以不失其特点地展示其内容,进而获得新知。境界论正是我们以新的方式研究朱子哲学的一个尝试。朱子的境界论分为天理流行、仁、功夫论几项内容,其核心则是主客体的审美性统一。
(一)天理流行论
天理流行是朱子对自然世界的体会。在他的看法中,自然是一个运动着的合乎价值的整体。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是理的表现,都包含着价值;人生活在一个充满意义的世界中。下面两个例子都是由某个自然现象体会出天道流行。
1.“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朱子解释说:
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欲学者时时省察,而无毫发之间断也。程子曰:“此道体也。天运而不已,日往则月来,寒往则暑来,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穷,皆与道为体,运乎昼夜,未尝已也。是以君子法之,自强不息。及其至也,纯亦不已焉。”又曰:“自汉以来,儒者皆不识此义。此见圣人之心,纯亦不已也。纯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语王道,其要只在谨独。”[4](P113)
2.“‘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
朱子认为:
子思引此诗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谓费也。然其所以然者,则非见闻所及,所谓隐也。故程子曰:“此一节,子思吃紧为人处,活泼泼地,读者其致思焉。”[4](P22-23)
(二)仁的境界
在整个儒家哲学中,仁是一个核心概念,在朱子哲学依然如此。仁不仅是主观的人心,也是客观的天道。根本地说,它是主客观统一的原则,天人合一的重要支点。
1.仁:“爱之理,心之德”
什么是 仁?朱 子 说:“仁 者,爱 之 理,心 之 德 也。”[4](P48)“仁是性也。”[4](P48)这表明在他那里,仁从其客观存在来说是一种道理,从其主观表现来说是人的本性、人心的德性。朱子接受程子的看法,认为仁是性,爱是情;仁之性发为爱之情,爱之情源于仁之性,二者相互联系而不可分离。他在给张栻的信中说:“程子曰:‘仁,性也;爱,情也。岂可便以爱为仁?’此正谓不可认情属性耳,非谓仁之性不发于爱之情,而爱之情不本于仁之性也。……盖所谓爱之理者,是乃指其体性而言,且见性情、体用各有所主而不相离之妙,与所谓遗体而略性者,正相南北。”[5](P1410)在朱子哲学中,仁是最后的、根本的理,是太极本身,众理之源。“仁便是本了,上面更无本。”[6](P463)他说:
凡看道理,要见得大头脑处分明。下面节节,只是此理散为万殊。如孔子教人,只是逐件逐事说个道理,未尝说出大头脑处。然四面八方合聚凑来,也自见得个大头脑。若孟子,便已指出教人。周子说出太极,已是太煞分明矣。且如恻隐之端,从此推上,则是此心之仁;仁即所谓天德之元;元即太极之阳动。如此节节推上,亦自见得大总脑处。若今看得太极处分明,则必能见得天下许多道理条件皆自此出,事事物物上皆有个道理,元无亏欠也。[6](P155-156)
仁又具有普遍性与终极性:
问:“程子曰:‘“敬以直内,义以方外”,仁也。’如何以此便谓之仁?”曰:“亦是仁也。若能到私欲净尽,天理流行处,皆可谓之仁。如‘博学笃志,切问近思’,能如是,则仁亦在其中。(宇录作:便可为仁。如‘克己复礼’亦是仁;‘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亦是仁;‘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亦是仁。看从那路入。但从一路入,做到极处皆是仁。”)淳。寓同。[6](P2464)
2.仁:“天地生物之心”
朱子认为,天地以生物为心,人亦以此为心。他说:“天地以生物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为心者也。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5](P3280)具体言之:
盖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贞,而元无不统。其运行焉,则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气无所不通。故人之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义礼智,而仁无不包。其发用焉,则为爱恭宜别之情,而恻隐之心无所不贯。故论天地之心者,则曰乾元、坤元,则四德之体用不待悉数而足。论人心之妙者,则曰‘仁,人心也’,则四德之体用亦不待遍举而该。盖仁之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发而此体已具,情之既发而其用不穷。诚能体而存之,则众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圣门之教所以必使学者汲汲于求仁也。[5](P3279-3280)
朱子认为,“爱之理”和“生生”是一致的,所以,仁与生、仁义礼智与元亨利贞都是一致的。
问:“天道流行,发育万物,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为一身之主,是此性随所生处便在否?”曰:“一物各具一太极。”问:“此生之道,其实也是仁义礼智信?”曰:“只是一个道理,界破看,以一岁言之,有春夏秋冬;以乾言之,有元亨利贞。”[6](P408-409)
在《克斋记》中,朱子进一步讨论了达到仁的功夫。他指出,仁之体用本来“涵育浑全,周流贯彻,专一心之妙,而为众善之长也”。然而,人因耳目口鼻欲望之害,或至于灭天理而穷人欲。人若能“有以拔其本、塞其源,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以至于一旦豁然,欲尽而理纯,则其胸中之所存者,岂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蔼然其若春阳之温哉!默而成之,固无一理之不具,而无一物之不该也。感而通焉,则无事之不得于理,而无物之不被其爱矣。呜呼,此仁之为德,所以一言而可以尽性情之妙,而其所以求之之要,则夫子之所以告颜渊者,亦可谓一言而举也与!”[5](P3709-3710)①按,本段“拔其本、塞其源,克之克之,而又克之”原标点为“拔其本、塞其源克之,克之而又克之”,不妥,今改。所谓“粹然天地生物之心”,也就是纯粹的仁。
朱子继承程子的思想认为,仁偏言则只为四端之一,专言则包四德,四端都从恻隐之心发出:
光祖问“四德之元,犹五常之仁,偏言则一事,专言则包四者”。曰:“元是初发生出来,生后方会通,通后方始向成。利者物之遂,方是六七分,到贞处方是十分成,此偏言也。然发生中已具后许多道理,此专言也。恻隐是仁之端,羞恶是义之端,辞逊是礼之端,是非是智之端。若无恻隐,便都没下许多。到羞恶,也是仁发在羞恶上;到辞逊,也是仁发在辞逊上;到是非,也是仁发在是非上。”问:“这犹金木水火否?”曰:“然。仁是木,礼是火,义是金,智是水。”贺孙。[6](P1690-1691)
仁本生意,乃恻隐之心也。苟伤着这生意,则恻隐之心便发。若羞恶,也是仁去那义上发;若辞逊,也是仁去那礼上发;若是非,也是仁去那智上发。若不仁之人,安得更有义礼智!卓。[6](P1691)
3.公与仁
湖湘学派张栻等人以“公”释仁。朱子在给张栻的信中指出,仁可以表现为公,但公并不就是仁。因其可以“漠然无情”,“如虚空木石”,而仁却是恻隐慈爱。又,仁是生物之心,“公可以体仁”,但仁不“因公而后有”:
如熹之说,则性发为情,情根于性,未有无性之情、无情之性,各为一物而不相管摄。二说得失,此亦可见。非谓“公”之一字便是直指仁体也。细观来喻所谓“公天下而无物我之私,则其爱无不溥矣”,不知此两句甚处是直指仁体处?若以爱无之溥为仁之体,则陷于以情为性之失,高明之见必不至此。若以公天下而无物我之私便为仁体,则恐所谓公者漠然无情,但如虚空木石,虽其同体之物尚不能有以相爱,况能无所不溥乎?然则此两句中初未尝有一字说着仁体。须知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为能体之,非因公而后有也。故曰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细看此语,却是“人”字裹面带得“仁”字过来。[5](P1412)
朱子强调,“公而以人体之为仁”:
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非以公为仁,须是“公而以人体之”。伊川自曰“不可以公为仁”。世有以公为心而惨刻不恤者,须公而有恻隐之心,此功夫却在“人”字上。盖人体之以公方是仁,若以私欲,则不仁矣。。[6](P2454-2455)
“公而以人体之为仁。”仁是人心所固有之理,公则仁,私则不仁。未可便以公为仁,须是体之以人方是仁。公、恕、爱,皆所以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恕与爱在仁之后。公则能仁,仁则能爱能恕故也。谟。[6](P2454)
4.觉与仁
大程有以觉说仁的思想。这个思想由谢良佐等人加以发挥。朱子认为,仁者心有知觉,但觉只是一种感知活动,并不就是仁。仁者之觉是智的发用处,仁包四德,可以兼智,但智同样并不就是仁。他指出:
上蔡所谓知觉,正谓知寒暖饱饥之类尔。推而至于酬酢佑神,亦只是此知觉,无别物也,但所用有小大尔。然此亦只是智之发用处,但惟仁者为能兼之,故谓仁者心有知觉则可,谓心有知觉谓之仁则不可。盖仁者心有知觉,乃以仁包四者之用而言,犹云仁者知所羞恶辞让云尔。若曰心有知觉谓之仁,则仁之所以得名初不为此也。今不究其所以得名之故,乃指其所兼者便为仁体,正如言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岂可遂以勇为仁,言为德哉?今伯逢必欲以觉为仁,尊兄既非之矣;至于论知觉之浅深,又未免证成其说,则非熹之所敢知也。至于伯逢又谓上蔡之意自有精神,得其精神则天地之用皆我之用矣,此说甚高甚妙。然既未尝识其名义,又不论其实下功处,而欲骤语其精神,此所以立意愈高、为说愈妙,而反之于身愈无根本可据之地也。所谓天地之用即我之用,殆亦其傅闻想象如此尔,实未尝到此地位也。愚见如此,不识高明以为如何?[5](P1413)
不过,朱子也承认,仁是爱,爱离不开觉,觉了才能爱,二者不相悖。
《克斋记》不取知觉言仁之说,似以爱之说为主。近子细玩味,似若知觉亦不可去。盖不知觉,则亦必不爱,惟知觉故能爱。知觉与爱,并行而不相悖,恐亦无害于言仁,但不可专以知觉为仁耳。医者以四支顽痹为不仁,顽痹则不知痛痒,又安能爱?更乞开发。[5](P1939)
5.同体与仁
同体是指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这是来自大程、张载的思想。朱子的想法是,仁可以表现为与物同体,但同体不可以说就是仁。如前所述,他主张 “仁只是爱之理”,爱之理本有,“不必为天地万物同体而后有也”。他又指出,与物同体是仁之量,而不是仁之体:
曰:“龟山言‘万物与我为一’云云,说亦太宽。”问:“此还是仁之体否?”曰:“此不是仁之体,却是仁之量。仁者固能觉,谓觉为仁,不可;仁者固能与万物为一,谓万物为一为仁,亦不可。譬如说屋,不论屋是木做柱,竹做壁,却只说屋如此大,容得许多物。如万物为一,只是说得仁之量。”因举禅语是说得量边事云云。德明。[6](P2454)
他又指出,与物同体只是“仁的躯壳”:
曰:“‘西铭之意,与物同体’,体莫是仁否?”曰:“固是如此。然怎生见得意思是如此?与物同体固是仁,只便把与物同体做仁不得。恁地,只说得个仁之躯壳。须实见得,方说得亲切。如一碗灯,初不识之;只见人说如何是灯光,只恁地抟摸,只是不亲切。只是便把光做灯,不得。”贺孙。[6](P2484)
我们可以把朱子《仁说》中的一段话作为他对仁的总结:
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盖有谓爱非仁,而以万物与我为一,为仁之体者矣。亦有谓爱非仁,而以心有知觉释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则彼皆非欤?曰:彼谓物我为一者,可以见仁之无不爱矣,而非仁之所以为体之真也;彼谓心有知觉者,可以见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实也。观孔子答子贡博施济众之问,与程子所谓觉不可以训仁者,则可见矣。子尚安得复以此而论仁哉!抑泛言同体者,使人含胡昏缓而无警切之功,其弊或至于认物为己者有之矣;专言知觉者,使人张皇迫躁而无沉潜之味,其弊或至于认欲为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盖胥失之,而知觉之云者,于圣门所示乐山能守之气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复以此而论仁哉
(三)孔颜乐处
孔颜乐处是纯粹的精神境界,是对世界的一种超然随顺、素位而行、廓然大公、物来顺应的人生态度。它不是消极的适应,而是积极的发现;是从自然里发现美,从道德践履中体味美,用这种超越的美来充实人生,心明物亮两相宜,由此获得对于人生的怡悦的体验。朱子说:“圣人之心,莹然虚明,无纤毫形迹。一看事物之来,若小若大,四方八面,莫不随物随应,此心元不曾有这个物事。且如敬以事君之时,此心极其敬。当时更有亲在面前,也须敬其亲。终不成说敬君但只敬君,亲便不须管得!事事都如此。圣人心体广大虚明,物物无遗。”[6](P348-349)朱子对于孔颜乐处的说明,有以下四条。
1.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朱子指出:
圣人之心,浑然天理,虽处困极,而乐亦无不在焉。其视不义之富贵,如浮云之无有,漠然无所动于其中也。程子曰:“非乐疏食饮水也,虽疏食饮水,不能改其乐也。不义之富贵,视之轻如浮云然。”又曰:“须知所乐者何事。”[4](P96)
2.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朱子解曰:
颜子之贫如此,而处之泰然,不以害其乐,故夫子再言“贤哉回也”以深叹美之。程子曰:“颜子之乐,非乐箪瓢陋巷也,不以贫窭累其心而改其所乐也,故夫子称其贤。”又曰:“箪瓢陋巷非可乐,盖自有其乐尔。其字当玩味,自有深意。”又曰“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4](P87)
3.“吾与点也”。
朱子说到:
“点!尔何如?”……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
对此,朱子指出:
曾点之学,盖有以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视三子之规规于事为之末者,其气象不侔矣,故夫子叹息而深许之。[4](P130)
朱子又说:“其见到处,直是有尧舜气象。如庄子亦见得尧舜分晓。”“曾点见识尽高,见得此理洞然,只是未曾下得工夫,曾点曾参父子正相反。以点如此高明,参却鲁钝,一向低头捱将去,直到一贯,方始透彻。是时见识,方到曾点地位,然而规模气象又别。”[6](P1034)又说:“尧舜便是实有之,踏实做将去。曾点只是偶然绰见在。臂如一块宝珠,尧舜便实有在怀中。曾点只看见在,然他人亦不曾见得。'”[6](P1034)对于此条,冯友兰提出了很好的解释。他说:
曾点已识得此理,而尚未“实有之”,尚需下一番工夫。所谓工夫者,即以“诚敬存之”的工夫。曾点若有此一吞工夫,则到其成就时,亦是规模气象又别。[1](P586-587)
4.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
朱子解释说:
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动静以体言,乐寿以效言也。动而不括故乐,静而有常故寿。程子曰:“非体仁知之深者,不能如此形容之。”[4](P90)
(四)从心所欲
“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是心理一如,内外合一的最高境界。其步骤首先是心要安顿在义理上,使自己的心同于天地之心、圣人之心;至功夫纯熟,则理不容己,自然流出。
1.心安顿在义理上
朱子指出,学者首先要在“日间将此心安顿在义理上”,[6](P139)“将自家身 己 入 那 道理中去。渐渐相 亲 ,久之与己为一”,[6](P140)使“吾之心即与天地圣人之心无异”:
熹窃谓人之所以为学者,以吾之心未若圣人之心故也。心未能若圣人之心,是以烛理未明,无所准则,随其所好,高者过,卑者不及,而不自知其为过且不及也。若吾之心即与天地圣人之心无异矣,则尚何学之为哉?故学者必因先达之言以求圣人之意,因圣人之意以达天地之理,求之自浅以及深,至之自近以及远。循循有序,而不可以欲速迫切之心求也。夫如是,是以浸渐经历,审熟详明,而无躐等空言之弊,驯致其极,然后吾心得正,天地圣人之心不外是焉。非固欲画于浅近而忘深远,舍吾心以求圣人之心,弃吾说以徇先儒之说也。[5](P1920)
2.“一以贯之”
《论语》记载:“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子指出:
圣人之心,浑然一理,而泛应曲当,用各不同。曾子于其用处,盖已随事精察而力行之,但未知其体之一尔。夫子知其真积力久,将有所得,是以呼而告之。曾子果能默契其指,即应之速而无疑也。[4](P72)
朱子又指出:
夫子之一理浑然而泛应曲当,譬则天地之至诚无息,而万物各得其所也。自此之外,固无余法,而亦无待于推矣。曾子有见于此而难言之,故借学者尽己、推己之目以著明之,欲人之易晓也。盖至诚无息者,道之体也,万殊之所以一本也;万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万殊也。以此观之,一以贯之之实可见矣。[4](P72)
3.“不勉而中”
朱子指出,不仅心要与理为一,而且这种功夫还要纯熟,才能做到“从心所欲”。《论语》记载孔子陈述自己为学历程,“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朱子在注释中指出:“从随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过于法度,安而行之,不勉而中也。”[4](P54)他又指出,通过敬做到心与理一,可以达到从心所欲:
问:“二程专教人持敬,持敬在主一。浩熟思之:若能每事加敬,则起居语默在规矩之内,久久精熟,有‘从心所欲,不逾矩’之理。颜子请事四者,亦只是持敬否?”曰:“学莫要于持敬,故伊川谓:‘敬则无己可克,省多少事。’然此事甚大,亦甚难。须是造次颠沛必于是,不可须臾间断,如此方有功,所谓‘敏则有功’。若还今日作,明日辍,放下了又拾起,几时得见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少个敬不得。如汤之‘圣敬日跻’,文王‘小心翼翼’之类,皆是。只是他便与敬为一。自家须用持着,稍缓则忘了,所以常要惺惺地。久之成熟,可知道‘从心所欲,不逾矩’。颜子止是持敬。”浩。[6](P208)
朱子指出,功夫常熟后自然贯通,自然光明,功夫自然流出,自然见理:
某与一学者言,操存与穷格,不解一上做了。如穷格工夫,亦须铢积寸累,工夫到后,自然贯通。若操存工夫,岂便能常操。其始也,操得一霎,旋旋到一食时;或有走作,亦无如之何。能常常警觉,久久自能常存,自然光明矣。人杰。[6](P149)
心熟后,自然有见理处。熟则心精微。去伪。[6](P157)
“不勉而中”出于《中庸》:“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对此,朱子解释云:
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诚之者,未能真实无妄,而欲其真实无妄之谓,人事之当然也。圣人之德,浑然天理,真实无妄,不待思勉而从容中道,则亦天之道也。未至于圣,则不能无人欲之私,而其为德不能皆实。故未能不思而得,则必择善,然后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则必固执,然后可以诚身,此则所谓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4](P31)
心熟见理,也就是冯友兰所说的天地境界。冯友兰指出:
《论语》:‘如有所立卓尔’,程子说这是‘大段着力不得’。朱子云:‘所以著力不得,象圣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了。贤者若著力,要不勉不思,便是思勉了。此所以说,大段著力不得。今日勉之,明日勉之,勉而至于不勉。今日思之,明日思之.思而至于不思。正如写字一般,会写底固是会,初写底须学他写。今日写,明日写,自生而至熟,自然写得。”圣人是在天地境界中底人,其道德行为不是出于特别有意底选择,此所谓不思而得;亦不待努力,此所谓不勉而中。说圣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这是不错底。但如所谓贤人,是指在道德境界中底人,则说贤人与圣人的不同,在于生熟的不同,则是大错底。贤人思而后得,勉而后中。圣人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这是由于他们的觉解的深浅不同,而不是由于他们的练习的生熟不同。出于习惯底行为,可有练习的生熟不同。但在道德境界及天地境界中底人的道德行为,都不是出于习惯。出于习惯底行为,只可以是合乎道德底行为。有此等行为者的境界,亦只是自然境界。[1](P575)
4.沛然莫御
这是功夫纯熟后,心全是理,发即中节的超自律状态。《孟子》中有“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于深山之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的话,朱子指出:
盖圣人之心,至虚至明,浑然之中,万理毕具。一有感触,则其应甚速,而无所不通,非孟子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4](P353)
冯友兰在《新原人》中指出,哲学讲到天地境界,可以说是到了“‘言语路绝,心行道断’的地步”。诚然,诚然!至此,人与物、主观与客观,甚至生与死,一切的差别,全然泯灭。人的精神到了一个天高任飞,海阔凭越的无所羁绊的自由状态。这种自由,超乎认识论的自由,超乎道德论的自由,亦超乎政治学所谓自由,是儒家的存在主义哲学的最高自由。其他自由,如庄子所言,风斯下矣!
前人与时贤对于朱子的理解,往往以其功夫论掩盖其本体论,对阳明的理解则以其本体论掩盖其功夫论。朱子境界论思想的提出,使我们得以窥见朱子哲学高超的一面。
[1] 冯友兰.新原人[A].三松堂全集[C].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2] Fung Yu-lan,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M].New York,Macmillan Company,1948.
[3] Tao,Nature and Man,金岳霖学术基金委员会编.金岳霖文集(第二卷)[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
[4] (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 朱杰人等.朱子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6] (宋)黎靖德.朱子语类[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