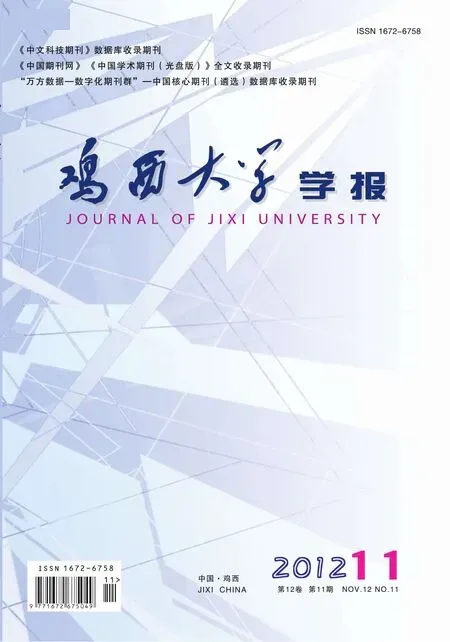从“养青松正气,法竹梅风骨”的英译谈起
杜海燕,梁冰冰
(1.山东工商学院中加学院,山东烟台 264005;2.诸由观镇羊岚完小,山东龙口 265701)
2.梁冰冰,小学一级教师,龙口市诸由观镇羊岚完小。
一 引言
校训作为一种具有训示功能的应用文体,是学校人文精神和文化内涵的物质表现形式。为了向世界推介自己,提升学校的知名度,国内各大高校纷纷将本校校训译成英语。在这种良性发展的潮流中,北京林业大学校训英文版本的久久缺席折射出东西方文化传递过程种种难以克服的困难。本文试结合北林大校训的英译探讨如何在不可逆的全球化趋势下,保持并增强中国文化的个性,完成东方文化的有效传递,弘扬优质的中国文化。
二 译文及翻译理据
1.译文。
北京林业大学校训“养青松正气,法竹梅风骨”对仗工整,读起来朗朗有力,符合中国大学校训构篇平衡对称、选词文雅优美的一贯风格,最为难得的是该校训运用“松、竹、梅”做比,既突出了自己致力林业教育的学科特点,又将育人宗旨和办学理念蕴含其内,不可谓不妙。笔者以相关理论支撑,汲取他人所长,并借鉴国外知名大学校训,提出自己的译文:unto a firm man like strong bamboo,pine and plum flower。
2.理据。
(1)从汉语表达形式到英语表达形式的转换。
任一语言,不论是低级的词层面,还是高级的篇章层面,都包括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对源语言到目标语言的转换行为而言,内容传达为转换主旨,形式仅为手段之一,在两种语言表达方式相背时,应使表达形式遵从目标语言习惯,消除不利于目标语读者接受原语内容信息的视觉障碍,激发其良好的心理反应。北林大校训的英译涉及到的汉英形式转换缘由如下:
①汉语“动词优势”与英语“名词优势”的对比。
著名翻译家钱歌川(何南林,2008)指出英语与汉语最不相同的地方在于前者偏好用名词描述动作行为,在使用频率上,较动词呈现出明显优势,属于静态语言;而后者是典型的动态语言,喜欢以动表动,这种特点在北林大校训中也得以明确体现,即动词“养”和“法”的使用。因此,英译该校训时,为了降低原文的动态量,采用介词“unto”,化动于静,且构成一个独立完整的英语语言单位。
②汉语“二元结构”与英语“一元结构”的对比。
杜争鸣(2008)曾论及汉英两种语言间存在结构方式上的“二元”与“一元”的倾向性差异,认为汉语注重句子成分之间的分别,有主谓二分等说法,而英语虽也有主语、谓语等区别称谓,却强调主语和谓语、谓语和宾语等的一致。再者,汉语文学中数量众多的对偶修辞手段,用字数相仿、结构相似的语句表达相关或者相同的意思(北林大校训可作一实例),亦是汉语具有“二元性”的有力证据。同样基于形式服务于内容的需要,译文“unto a firm man like strong bamboo,pine and plum flower”将原校训内容提炼浓缩,合两个意义重复的动词词组为一个凝练的介词短语,顺从了英语的“一元性”趋势。
③汉语校训与英语校训的语体差别。
汉语讲究工整对仗,这尤见于中国大学校训之中,比如清华大学校训“自强不息 厚德载物”和南开大学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是因为中国大学校训多属于正式语体,而英语校训却大多选词通俗,形式不一,不拘一格,趋于中性或者非正式语体,如加州理工学院校训“The truth shall make you free(真理让你自由)”和伦敦大学校训“Let everyone come to the university and merit the first prize(我们为至高荣誉齐聚于此)”。中国大学将校训英译时,多数改变了原校训的语体色彩,如南京大学校训“诚朴雄伟 励学敦行”译为“Be Honest and Intelligent,Study Hard and Act Sincerely”;北京师范大学校训“学为人师行为世范”译为“Learn to be an Excellent Teacher;Act as an Exemplary Person”。在将北林大校训译成英文时,也不能例外。
2.接通汉语与英语的隐喻思维。
东西方民族不同的历史进程使之对同一事物的情感体验不尽相同,对同一问题的审视角度和思考模式也迥然有异。隐喻作为思维方式的一种,也难免东西之别。例如,北林大校训中提到的“松、竹、梅”三种物象,因其具有不畏严寒的共同习性,生命力顽强,为中国历代文人墨客歌咏,渐渐形成“坚贞、不屈”的人格特征,宋代楼钥的“百卉千花皆面友,岁寒只见此三人”更是一语道出其高贵气节,“松、竹、梅”于是被合称为“岁寒三友”,是国人熟悉的固定的中国文化意象,也是国人隐喻思维的成果之一。与之相对的是,西方文化中却少有以此三物寄情喻志,缺乏对其隐喻含义的认知。这种思维方式的不同而造成的对同一物象的认知不完全对应致使翻译实践屡遭挫折,为了利于西方读者接受和理解,译者或无奈舍弃颇具中国特色的喻体,被迫意译,或追求“喻体共知”,片面理解“审美和谐论”,故意为之。比如,把“近水楼台先得月”译成“to have easy access to a special benefit”,把“他们做这件事也算是逼上梁山”译成“They were driven to this work”,结果致使形象全无,风采皆失。
尽管困难种种,笔者仍属意汉语深刻的隐喻特征和鲜活的喻体,力图通过在西方文化中创设空缺的对应文化语境,接通汉语与英语思维。所以竭力保留了该条校训中的喻体:松、竹、梅,将其直译。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可以从以下理论和实际中找到支持。
(1)隐喻是人类共有的思维方式。西方人虽然擅长抽象思维,但其语言中也不乏形象生动的比喻,多个欧美名校的校训采用了隐喻的修辞手段,如剑桥大学的校训为“From here,light and sacred draughts”,取喻“光”和“风”,因光能照彻黑暗,破开混沌;风凝聚力量,摧枯拉朽,以神圣(sacred)一词修饰与“光”共同比喻启明蒙昧,促人进步的智识。又如,斯坦福大学校训“The wind of freedom blows”将学术自由比作无羁的风。
(2)隐喻词项间相似点的创新性。从本质上看,隐喻是把一事物(词项一)的某些特点品质传递到另一事物(词项二)上,从而使二者具有相似相像处,但这些相似之处并不是生而有之,必经过最初的偶然并用,这种偶然源自隐喻思维的创新性。20世纪60年代以来,布莱克(Black,1962)、里科尔(Ricoeur,1978)等学者都论证过隐喻两个词项相似点的创新性,认为隐喻能够在有限的现成的句法和语义资源中生成无限的崭新意义。这意味着可以在目标文化中创建缺少的喻体意象映射域,借助人们的想象力和积极比较,使两个词项产生关联。因此,对于客观真实的松、竹、梅和主观抽象的顽强坚韧人格之间的联系,西方读者在仔细揣摩之后并非无法获得正确认识。
(3)文化喻体直译+内涵“解”译法的提出。隐喻翻译难题聚讼纷纭,争论不断。为了既能最大程度关照目标读者阅读的流畅,减少其理解障碍,又能忠实于原语文化,刘法公(2008)从翻译本位论出发,提出立足于传播中国文化和语言现实的隐喻汉英翻译原则,即“保持隐喻特征,接通汉英隐喻的关联文化内涵和根据语境弥补文化喻体缺失”的三条原则,并为第三条原则的实施创立了一个新译法:文化喻体直译+内涵“解”译。这不失为解决隐喻翻译难题和隐喻汉英翻译实际困难的一种有益探索,可谓两全其美。故而笔者依此法,在直译北林大校训中松、竹、梅三个喻体的同时,以英语单词firm(坚定的)和strong(坚强)揭示其涵盖的寓意,构建了一个信息充足的语境,并用鲜明的物质符号-like-典型的英语比喻词表明此处所用的修辞手段,提示需要付出的思维对比努力。使用这一方法能将优秀的中国文化意象完好地传递出去,有助于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对改变中国对外文化交流严重“入超”,赤字庞大,中国文化意象长期亏损的情况无疑颇具助力。另一方面,校训作为民族精神和教育宗旨的载体也表现出东西方的差异,对于个人完善的关注点有所不同:“中国哲学规定人的本质是伦理的”,所以中国大学校训大多强调“德、诚、善”等的修为;“西方哲学规定人的本质是认知的”,(顾嘉祖,2002)所以西方大学校训注重“智慧、真理、知识”的获取。运用直译加解译法,能够让西方国家了解中国所崇尚的品质和教育思想。
三 译文及翻译理据
长久以来,中国的翻译研究和实践总是在西方翻译理论之后亦步亦趋,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翻译理论体系是不存在的,中国与西方所属语系不同,文化渊源有别的实际要求汉英翻译应有自己的一套质量评估体系,本文借北京林业大学校训的翻译,探讨这一体系的实现构想,期望能对汉英翻译理论及隐喻汉英翻译理论的深入并最终推动中华文化的广泛传播有所裨益。
[1]何南林.汉英语言思维模式对比研究[M].齐鲁书社,2008:618-626.
[2]杜争鸣.翻译策略与文化[M].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63-64.
[3]刘法公.隐喻汉英翻译原则研究[M].国防工业出版社,2008:63 -64.
[4]顾嘉祖,陆升.语言与文化[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5]Black,M.Models and Metaphors:Studies in Language and Philosophy[M].New York: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2.
[6]Ricoeur,P.The Rule of Metaphor[M].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