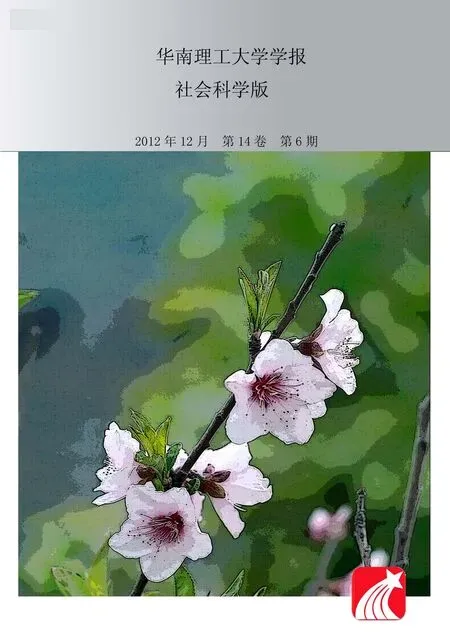白话新诗之争*——论学衡派的诗歌观
李广琼
(华南理工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一、诗歌语言:工具与本体的统一
白话能否入诗,是学衡派与胡适的主要分歧之一,而分歧的根本归结于二者对语言性质的界定。
胡适视语言为工具,“文字者,文学之器也”[1],既然是“器”,就与文学本体无大关系。学衡派则认为,语言是工具与文学本体的统一。他们认为,语言自然有工具性的一面,语言本身的工具性质决定它有载道的功能,这是毫无疑义的,“文以载道,文言文能载道,与白话文之能载道,亦无以异也”,“夫文字不过意志、思想、学术传达之代表,代表之不失使命及胜任与否,乃视其主人之意志坚定,思想清晰,学术缜密与否为断”。[2]这似乎与胡适等人所持的工具说并无二致,但是,这仅是语言性质的一个方面。
学衡派指出,语言同时又具有文学本体的一面,它应该依所载之道而定,并由此提出文言与白话可以并存的观点,“文言白话,各有其用,分野殊途,本可并存”。[3]也就是说,不论文言还是白话,语言必须与它所载的道达到一致和融合状态,这样才能真正载其道。古文白话“各有所长,不可更代混淆,而有独立并存之价值”。[4]这可看出,学衡派并不真正反对白话,而是从语言性质出发,更为学理地分析文言与白话“各有其用”、“各有所长”,语言应该是文学工具与文学本体的统一。
胡适等人视语言是一种纯粹工具,因此认为语言具有普适性。“曹雪芹诸人已实地证明作小说之利器在于白话,今尚需人实地试验白话是否可为韵文之利器耳。……我自信颇能用白话作散文,但尚未能用之于韵文;私心颇欲以数年之力,实地练习之。”[1]白话既能用于小说,又能用于散文和韵文。而学衡派将语言视为工具与本体的统一,就要求语言必须统一于本体。它不具普适性,适合此文类的语言不一适合彼文类。它的适用与否在于与本体的统一,统一则适用,否则就不成其为合适的工具。
在学衡派看来,诗歌的语言也必须达到工具与本体的统一。诗歌是一种特殊的文类,梅光迪认为,诗为“人类最高最美之思想情感之所发宣,故其文字亦须最高最美,择而又择,选而又选,加以种种格律音调以限制之,而后始见奇才焉,故非白话所能为力者。”[5]170吴宓表达了同义,“诗者,以切挚高妙之笔(或笔法),具音律之文(或文字),表示生人之思想感情者也。”[6]他们认为,诗歌是最具文学审美特性的文类,那么,与之相称的语言也应该是“具音律”的。而音律在白话新诗中处于淡化和缺失状态,白话诗句并不具备“音律”,“仅为白话而非白话诗”。[7]。李思纯强调白话诗不合中国文字之特质,他说:“文学之本体在于文学。吾国旧诗之所以有平仄、音律、五七言,盖本于汉字之特质而来,”白话诗强以“单音独体之汉字”创作“拼音文字式之诗”,非但违反常识,抑且不足称为诗。[8]他们都认为白话不适合“载”诗。梅光迪判定,“文章体裁不同,小说、词曲固可用白话,诗文则不可”。[5]168吴宓则更进一步详细地对文言与白话在每一种文章体裁中的应用加以解说和评判,结论是“小说戏剧等有当用白话者。即用简炼修洁之白话。外此文体之精粗浅深。宜酌照所适。随时变化。而皆须用文言。”[9]这种划分,诗歌领域无疑是一个不可侵犯的禁区。吴宓更是断言,“新体白话之自由诗,其实并非诗,决不可作”[9]认为,从白话新诗的创作实际来看,白话之于诗歌,并未达到工具与本体相统一的美学目的,因而反对白话入诗。
学衡派关于诗歌语言是工具与本体相统一的观点,与他们信奉的“一、多”学说有内在联系。在《认诗之创作》一文中,吴宓开宗明义:“予最服膺柏拉图之哲学,以为可以包括一切事象,解决一切问题。柏拉图哲学之精华,尤在其(1)两世界及(2)一多相关无碍之二义。”并说,以柏拉图之学说用之于文学,则知“文学之原理,真善美之本体,批评之标准。以上均为绝对的,故可完全客观论究而得公平”。[10]270在柏拉图的“一、多”学说中,“多”是现象,是可变的;而“一”则是本体,是应该保持的。如白璧德所说,“伟大的诗人或艺术家从‘多’中察觉到的‘一’,以及那种赋予其作品更大的严肃性的东西并不是一种固定的不变的绝对”。在他看来,“一”并非一成不变的规则和典范,而是一种“对普遍性的直接感悟”[11]12也就是说,“一”是一种抽象的精神和内核。在文学中,“一”也就是吴宓所说的“真善美之本体”,文学批评的标准正是应该建立在这种“一”之上的。
学衡派正是从“一、多”的关系中,来观照和审视诗歌的语言与本体之间的关系。在这里,语言是“多”,即现象,是可变的;而诗歌本体是“一”,则是应该坚守的,这里的“一”就是指诗的本质。语言的变化必须服从于“诗的本质”这一中心原则。如果遵从了“诗的本质”,所用的语言是适合的;反之,如果违背“诗的本质”,所用的语言则是不适合的。
在此框架中,学衡派对于白话新诗的批评成为一个有机的体系。而且一些看似矛盾的观点也因此得到合理的解释。吴宓曾说“新体白话之自由诗,其实并非诗,决不可作”[9],又说“在今新诗(语体诗)可作……作新诗者,如何用韵,尽可以自由试验,创造适用之新韵”。[12]267-269这两个看似矛盾的观点在“一多”结构中其实是统一的,并不矛盾。吴宓所说的“白话诗绝不可做”,是指那种违背了“诗的本质”的白话诗。在这种诗中,诗特有的艺术属性已被或多或少地抽空,沦为几行白话做成的文字。显然违背了“一、多”统一的原则,是应该反对的。而他所说的“我不是反对新诗,我只是对新诗提出了较高要求”,也是“一、多”统一原则下的观点。“韵”是诗歌独有的美学属性,其它文体则没有这种美学属性。也就是说,“韵”就是诗的本质之一,是诗所以为诗的判定准绳之一。吴宓认为,在保持“韵”这一诗的本质的前提下,白话诗是可以“自由试验”的。他进一步说明,诗必须有韵,而具体的诗韵标准,则可“归本于一(the one)、多(the many)之对峙”,“盖主多者,常主自然(nature)讥斥人为;主一者并主规律(law,convention)而力求统贯”。[13]267-269他提倡“自由试验”,“创造适用之新韵”。这正是“一多”统一在诗歌批评中的呈现。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吴宓说:“我不是反对新诗,我只是对新诗提出了较高要求”。[13]。而这个较高的要求,也就是在诗歌语言革新时,必须重视“诗的本质”这一不可或缺的美学内核。
在遵从“一”的原则下,诗歌语言在工具与本体之间达到有机统一。学衡派对白话新诗的批评与建设性思考都源于这种观点。学衡派关于白话新诗问题的观点,对当时白话诗主潮形成一种制衡与救偏。而且,其中许多不乏合理性的建设性理念,为白话新诗后来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
二、诗歌格律:诗之本能
坚持格律还是废除格律,是学衡派与胡适等人关于白话新诗的另一主要分歧。胡适主张“要须作诗如作文”,[14]91“诗须废律”。[15]他把诗的格律看成是“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必须打破这些“枷锁镣铐”,以实现“诗体的大解放”。[16]
学衡派对之提出反对意见。胡先骕和吴宓的观点颇具代表性,胡先骕从诗歌审美本体论出发提出,诗之有声调格律音韵,古今中外,莫不皆然,“诗之有格律,实诗之本能”。反对胡适将格律视为“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主张辩证地看待格律在限制与自由上的对立统一。他引用美国罗士的话:“在美术家,其媒介物之限制,即其达自由之路也”,“即此限制,每为创造之原因”。[7]吴宓指出,思想感情乃诗之内容,韵律格调则为诗之外形;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如果一味注重内容,“铲除一切韵律格调”,则诗之本体亦遭破坏,“唯有极佳之思想感情,何所附丽?何由表达?”[6]他们认为,其一,格律是诗的本质属性,不可废除;其二,格律是“限制与自由”的统一,作者在这些限制中达到创作的自由。格调的严格限制,非但不是束缚创造力的镣铐枷锁,反有助于提高文学的艺术价值。
学衡派对格律的坚持,与其古典主义美学观有关。白璧德认为,“古典的精神无论在哪里出现都会产生有益的、塑造心灵的作用”。形式最为纯粹的古典精神感到自己“是为更高的、非个人的理性服务的”,于是便产生了“克制含蓄、讲求分寸与处处谨严的感觉”。在“更高与非个人的理性”的指导与制约下,古代经典作品全面协调地发展了人类的一切官能,这样我们便超越了不断重新堕落的可能而不至于陷入“专横孤独的思考力所铸成的灵肉桎梏、感觉的泥沼或幻想的迷宫”。[17]“理性”是古典主义的关键词,古典主义注重理智、节制、讲求文学的标准与纪律。在内容上要求情感的节制,形式上讲求纪律与标准。古典主义从现实中进行选择,并且将自己“所尊敬、模仿的典范的某种比例和对称的东西”强加于它。[18]213并且将自己的文学信仰寄托于“理性”,这种理性意味着正确的判断或抽象推理,并以这种“理性或判断”“反对想像”。[19]213也就是说,古典主义坚持遵守典范,并以这种理性和判断进行文学批评。法国古典主义诗论家布瓦洛主张诗“都要情理和音韵永远互相配合”,“理性得韵而丰盈”,“忽于理性,韵就会不如人意”。[20]289-290强调诗歌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学衡派正是以古典主义美学观来进行诗歌批评的。他们认为,“诗之有格律,实诗之本能”,格律是一种纪律与标准,是诗歌之所以为诗的属性之一,如果抽除这种属性,那么,诗也就不成为诗了。格律是诗歌应该遵从的典范。吴宓盛赞安诺德的诗,认为其佳处“在其能兼取古学浪漫二派之长”,“以奇美真挚之感情思想,纳于完整精练之格律艺术之中”。其“哀伤之旨,孤独之感,皆浪漫派之感情也,然以古学之法程写出之”。[21]安诺德的诗之所以受吴宓激赏,在于其诗融趋势感情与格律艺术于一体,内容纯正,形式上也坚持了“完整精练之格律艺术”。胡先骕主张诗的形式要有规律,他称赞古典主义“格律整齐,主张正大”。关于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他认为,诗要表现“情理”,而其媒介物则要讲究“音韵”,诗之所以异于文者,“亦以声调格律音韵故”。若“使诗之媒介物,完全与普通语言之用法同,则不成为诗矣”。“整齐之句法”可“增加普通感情与注意之活泼与感受性”,可“辅助思想之表现”,“夫对仗之功用,正与句法之整齐,音韵之谐和,与夫双声叠韵,同为增加诗之美感之物”,韵“能增加唤起愉悦之能力”。[7]总之,他们强调诗歌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诗歌形式必须遵守格律。批评白话诗摹仿美国之自由诗(Free Verse),废除一切音韵格律,根本不足以称作诗。因此,白话新诗,“以改良中国之诗自命”,实则昧于诗之原理,以致“扰攘恣睢,去正途愈远,入魔障益深。”[6]在他们看来,白话新诗主张废除格律,违背了对典范的遵从。
在某种程度上,学衡派与胡适等人在诗歌格律主张上的对峙,就是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在诗歌形式观念上的对峙。古典主义强调理性节制,追求形式整齐格律;而浪漫主义偏于扩张放纵,力求形式自由创新。新诗正是胡适等人追求创新的文学产物,他们主张废除格律以实现“诗体的大解放”,是诗歌形式的放纵。这种放纵正是古典主义所极力批评的浪漫主义的放纵。
在《论诗之创作》一文中,吴宓依新旧材料格律的不同搭配,将把诗歌分做四类:旧材料——旧格律、旧材料——新格律、新材料——新格律、新材料——旧格律[10]他认为新材料与旧格律“始合于文学创造之正轨”。[9]但对归入新材料新格律诗歌代表的徐志摩也颇为激赏。认为若天假以年,徐志摩可以写出但丁式的鸿篇巨制。吴宓对徐志摩的新诗给予肯定和赞同,是因为其诗坚持和强调格律,符合古典主义美学原则。学衡派并不反对新诗,只是强调新诗应该保持对诗的典范和本质的追求。
吴宓与胡先骕等人深受中国传统诗学的熏陶,他们对格律的坚持,既受中国传统古典主义诗学的影响,又兼受白璧德古典主义影响。而这两种传统在这里达到了一种契合。
自新诗诞生始,格律取舍的讨论便一直如影随形,伴随着新诗的发展。学衡派依据古典主义美学原则,坚持格律不可废除。在新诗创作外部,批评白话新诗废除格律的声音不绝于耳,章太炎说,“凡称之为诗,都要有韵,有韵方能传达情感。现在白话诗不用韵,即使也有美感,只应归入散文,不必算诗[22]16。”陈寅恪甚至认为不仅写诗,便是“美术性之散文,亦必有适当之声调。”[23]148-149这些意见都跟学衡派的观点相近。
而且,新诗内部也在反思新诗创作的缺失,针对白话自由诗的“自由”提出补偏救弊意见,要求新诗音韵格律的重建。刘半农提出“破坏旧韵,重造新韵”,以及“增多诗体”,即分自造,输入他种诗体,有韵诗外别增无韵诗三项。[24]陆志韦认为对韵法应进行必要的改造而不赞成废韵之说,坚持“诗的美必须超乎寻常语言美之上。”[25]潘大道说,“诗不必有韵,有韵底不必是诗”。[26]后来说“妙用语言,合于音律,是诗的职分了”。[27]宗白华说“情感表现不成方式与形体,艺术则有形式,有节奏,有规则的,如舞蹈,本为情绪之表现,若欲其成为艺术,则必加以节奏或方式也”。[28]473这些提倡新诗格律化的主张均与学衡派的观点相近。《晨报·诗镌》更是宣称:“我们信诗是表现人类创造力的一个工具,与音乐与美术是同等同性质的;……我们的责任是替它们抟造适当的躯壳,这就是诗文与各种美术的新格式与新音节的发见;我们信完美的形体是完美的精神唯一的表现;我们信文艺的生命是无形的灵感加上有意识的耐心与勤力的成绩。”[29]“试问取消了form,还有没有艺术?”[30]新格律诗派凭借《晨报·诗镌》的平台异军突起于诗坛,他们主张“戴着镣铐跳舞”,提倡新诗的格律化,并以创作实绩创造了新诗的辉煌。其提倡新诗格律化的观点也与学衡派的主张相同,吴宓对徐志摩颇为肯定,其实也代表对新格律诗的肯定。
饶有意味的是,学衡派是站在新诗外部审视新诗,提出不可废格律的观点;刘半农等人及新格律诗派是从新诗内部自我反思,从而倡导新诗格律。这种从新诗内部生发的思考,及其新格律诗的发展实况,印证了学衡派关于诗歌格律的观点。虽然它们不是直接取自于学衡派的资源,但学衡派观点的合理性在其中得到了回应,这一点是无疑的。
诗歌本质就是古典性,因此,学衡派将中国传统诗学与新人文主义古典美学融合起来,对新诗进行批评,是切中肯綮的。学衡派在理论资源与批评对象之间找到了有机的契合点,使二者形成了有效对话。在这里,学衡派对新人文主义古典主义的阐释是成功的。
三、“以新材料入旧格律”:诗歌变革与文化理念的融合
学衡派维护传统文学,但并非一味固守。这与白璧德坚持古典主义,反对新古典主义的美学主张有相承之源。白璧德所说,“古典文学作品若想保持其传统的地位,就必须和现代生活的需要和期盼具有更加广泛的联系。”[17]114古典文学保持传统地位,并非一味固守即可,而是要密切联系现代生活新的需要与期盼。白璧德不无精辟地点出古典文学于传统和现代之间的辩证关系。他反对新古典主义的“教条”,认为新古典主义者所创立的“一般标准”具有“矫揉造作与生硬僵化”的弊端。
学衡派继承了白璧德古典主义的主要观点,并将之与中国文学的现实进行了有机的联系与融合,表现在他们对于中国诗歌的思考上。在新的时代之风下,学衡派也在寻求诗歌的发展之路,他们认为,新诗主张废除格律,一味创新,不利于诗歌的发展。同时,他们也看到一些旧派文人沉溺于格律的追求,也不利于诗歌的发展,这两种观念都有失偏颇。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诗歌改革的思路。吴宓的观点颇具代表性,提出“以新材料入旧格律”,他认为,新派之失,在不肯摹仿,便思创造,故唾充旧格律;旧派之失,在仅能摹仿,不能创造,故缺乏新材料。故救其弊而归于正途,只有镕铸新材料以入旧格律之一法。[31]400-401在他看来,新派一味追求创新,不思对传统的摹仿,抛弃旧格律,损害诗歌的发展;而旧派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固守摹仿,而不思创造,也阻碍了诗歌的发展。因此,新材料与旧格律“始合于文学创造之正轨”,[22]“以新材料入旧格律”是诗歌发展的唯一道路。
这当然是吴宓对于诗歌发展的思考。其实,“以新材料入旧格律”不仅仅是一种诗歌观点,它暗合了“新旧融合”文化理念,与学衡派世界与本土统一、传统与现代统一的文化思想有内在逻辑关系的一致性。
吴宓“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诗歌改革思路,“实本于黄公度先生”,[12]267-269又受白璧德古典主义的影响。本身就是中西文化融合的产物。
“以新材料入旧格律”,一新一旧的融合,仅其观点表面就包含新旧融合的理念。吴宓所说“新材料”,包括黄遵宪所提“西洋传来学术、文艺、生活器物,及缘此而产生之思想感情等所号为现代之特征者”,“旧格律”则是“吾国诗中所固有之五七言律绝、古体、平仄及押韵等。”[10]270在这里,“西洋传来学术、文艺、生活器物,及缘此而产生之思想感情等所号为现代之特征者”等“新材料”无疑是属于“新知”;而“五七言律绝、古体、平仄及押韵”等旧格律属于中国传统诗学范畴,则是“国粹”。因此,“以新材料入旧格律”与学衡派“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文化思想无疑是一致的。前者是后者在文学层面的再次阐释和具体体现。
综上所述,学衡派将中国传统诗歌的美学理念与新人文主义的“一、多”学说有机融合起来,对新诗提出了批评。应该说,这是新人文主义中国化的有机转化,其观点不无道理,其中包含许多合理的内核,对当时的白话新诗主潮是一种补充性思考,构成新诗发展理论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
[1] 胡适.尝试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2] 邵祖平.论新旧道德与文艺[J].学衡,1922(7).
[3] 吴宓.钮康氏家传·译者识[J].学衡,1922(8).
[4] 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J].学衡,1922(1).
[5] 梅光迪.致胡适信四十六通·第三十七函[M]//罗岗,陈春艳.梅光迪文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166-172.
[6] 吴宓.诗学总论[J].学衡,1922(9).
[7] 胡先骕.评《尝试集》[J].学衡,1922(1).
[8] 李思纯.与友论新诗书[J].学衡,1923(19).
[9] 吴宓.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J].学衡,1923(15).
[10] 吴宓.论诗之创作[M]//吕效祖.吴宓诗及其诗话.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270-273.
[11] 白璧德.卢梭与浪漫主义[M].孙宜学,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12] 吴宓.诗韵问题之我见[M]//吕效祖.吴宓诗及其诗话.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267-269.
[13]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
[14] 胡适.四十自述[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
[15] 胡适.寄陈独秀[M]//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32-33.
[16] 胡适.谈新诗[M]//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298-299.
[17] 白璧德.合理的古典研究[M]//文学与美国的大学.张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97-115.
[18] 白璧德.浪漫主义的想像[M]//卢梭与浪漫主义.孙宜学,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43-69.
[19] 白璧德.当前的面貌[M]//卢梭与浪漫主义.孙宜学,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212-235.
[20] 布瓦洛.诗的艺术[M]//孟庆枢,杨守森.西方文论选(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289-290.
[21] 吴宓.论安诺德之诗[J].学衡,1923(14).
[22] 章太炎.国学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23] 周祖谟.陈寅恪先生论对对子[M]//追忆陈寅恪.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148-150.
[24] 刘半农.我之文学改良观[J].新青年,1917-05-03(03).
[25] 陆志韦.渡河[M].上海:亚东印书馆,1923.
[26] 潘大道.何谓诗[J].学艺杂志.1920-04-02(01).
[27] 潘大道.从学理上论中国诗[J].中国文学研究,1927,6(5).
[28] 宗白华.宗白华全集(1)[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
[29] 徐志摩.诗刊弁言[N].晨报副刊·诗镌.1926-04-01(01).
[30] 闻一多.诗的格律[N].晨报副刊·诗镌.1926-05-13(07).
[31] 吴宓.评顾随无病词·味辛词[M]//吕效祖.吴宓诗及其诗话.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286-2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