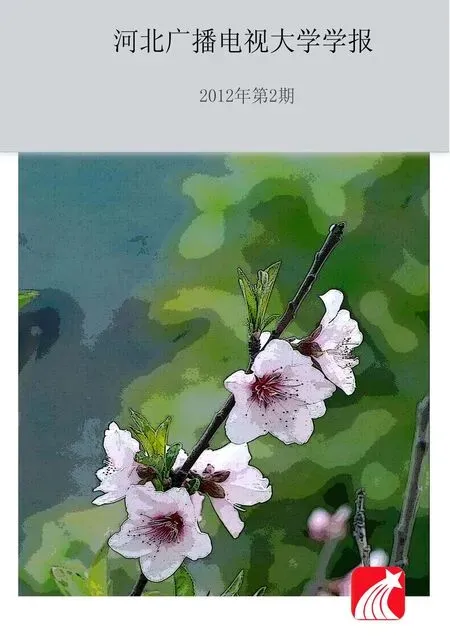《庸言》的立论维度与民初政治困局
武占江,韩 雪
(河北经贸大学,河北石家庄 050061)
《庸言》的立论维度与民初政治困局
武占江,韩 雪
(河北经贸大学,河北石家庄 050061)
从朝代更迭的怪圈到启蒙与政治的怪圈是中国古代政治到近代政治转折的一个突出特点。朝代更迭怪圈形成了在平面维度上的历史循环怪圈,专制政治在这个怪圈中只有变化没有进步。从戊戌变法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形成了一个思想启蒙与政治统治的另外一个怪圈,没有思想启蒙不能带来民主化的现代政治,这是启蒙者的共识,也是历史的事实。但是掌权者却每每以中国救主自认,认为没有强大的中央集权就不能对外应付列强瓜分,对内不能消弭动荡,而且唯有自身是民主的引导者,民间的民主诉求都是动乱、叛逆,进而采取压制舆论的政策,结果成了民主的反面力量。《庸言》经历了支持中央集权到反对专制的过程,自身几乎经历了这样一个怪圈的过程,浓缩了从戊戌到五四的思想轨迹。
《庸言》;梁启超魔咒;历史新循环;异质对抗力
一、强有力政府的主张
《庸言》创刊于1912年12月1日,第一卷是半月刊,每月1日、16日出版,梁启超任主编,1914年2月15日起,由黄远生主持,这也是《庸言》第二卷的开始。第二卷第1、2号合刊,同时依照原来编号顺序编为25、26号,但是刊物的风格已经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政论为主转向以事实评论为主。目前能见到的最后一期是第2卷第6号,时间为1914年6月5日。
民元以来,如何实现共和政治是各派争论的焦点,当时的历史任务就是建立起稳定的、能够实现民主政治的政治制度,凝聚全国力量,使国家步入自强的轨道,实际上后一个任务在各派来看更为迫切。这两个目标都凝聚在如何构建共和政体上面。具体而言,构建共和政体主要包括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的关系问题,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问题,地方政府与地方议会的关系问题,在立法与行政关系方面又存在着总统制与内阁制的争论。在这些问题上,《庸言》既有共同的倾向,论者各自又有其特点。《庸言》始终体现着加强行政机关权力的特点。
内阁制与总统制是当时争论的焦点,革命派通过《临时约法》设计了限制总统权力的内阁制,但是袁世凯集团的目的是废除内阁制,实行总统制。在这一问题上,《庸言》倾向于内阁制,但是其动机及内蕴与革命派有所不同。在创刊号上,吴贯因发表了《共和国之行政权》一文,明确提出应该实行责任内阁制。他认为总统制有三个缺点。首先,在总统制下,总统由民选产生,四年任期之内国会不得弹劾,则总统的错误将无法纠正,立法机关与总统之间的矛盾往往要通过革命的形式解决,内阁首长则随时可以弹劾去之。其次,立法权与行政权处于冲突地位,如果赋予国会弹劾总统的权力,则总统动辄得咎,对总统的权威以及国家形象都是不利的。最后,总统任期有限,如果有非常杰出的人才,在这种制度下,就不能长期活动于政坛,是国家的巨大损失,而通过内阁制就可以使这些人长期甚至终生发挥作用。因此吴贯因指出,“中国之行政权必使属于内阁,其无疑义矣。”但是吴贯因不同意《临时约法》规定的内阁由参议院选出的办法,认为这样难以使内阁形成有机的统一,使内阁负连带责任的职能难以发挥。国务总理应该由总统提名,国务员由总理决定。总统颁布法令应该由国务员附署,总统向国会提出议案也应该由国务员附署。国务院应该向国会负责,但是并不是隶属于国会,国会可以弹劾内阁,内阁也可以提请总统解散国会。吴贯因的这个设计体现了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制衡原则、加强行政权限的原则、总统无责任原则,这种思想对于克服国会与行政机关的无限纷争、提高行政效率是有益的。但是,在第7号《宪法问题之商榷》中他认为,削弱总统的权力适用于君主国,而不适用于共和国,因为总统的能力必胜过议员,这里吴氏为袁世凯张目的倾向已经很明显了。
同样是主张内阁制,出发点与目标也是有区别的,《临时约法》所规定的机制是增强国会的权力,约束行政部门的权力;《庸言》同仁的出发点与目标是指向加强行政权,强化中央的权威,吴贯因在第二号《政府与国会权限》一文中明确表达了这一立场,在这篇文章中他讨论了中央政府的行政权、立法权、外交权、财政权,主要论点是政府在这些方面的权力与《临时约法》相比,都应该扩大。
吴贯因上述观点基本上是梁启超思想的演绎和重复。梁启超1912年4月写成的《中国立国大方针》就表达了“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这一思想,《庸言》第9号发表梁启超的《同意权与解散权》一文,再度阐释这种思想。梁启超在此文中甚至认为总统解散国会的权力不必限定一次,他认为即使赋予总统这样的权力,中国也没有这样有魄力的政治家,“有之,则六种震动,万汇昭苏,吾侪方当馨香以祝”“且诚有此人,又岂死法所能制限束缚也哉!”梁启超甚至还主张总统连任问题宪法不必限制,①梁启超:《进步党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庸言》,1913年8月,第1卷第18期。即使袁世凯要当终身总统梁启超一度也并不反对,这是和他的“开明专制论”一脉相承的。对国会、内阁与总统权限问题发表意见较多的还有吴贯因与张东荪,吴贯因基本上与梁启超的态度亦步亦趋,甚至所举事例、所用词汇、所持口气都是非常相像,如吴贯因也明确提出,“纯粹共和不足以立国,必兼有几分专制之精神始可巩固”,②吴贯因:《宪法问题之商榷》,《庸言》,1913年6月,第1卷第13期。他也主张总统解散议会次数不应该限制,如果有强力总统三次解散议会则是“我国民当祷祀以求者也。何者?今之国会议员大半皆卑鄙龌龊、蝇营狗苟、寡廉少耻之徒,而数月以来,其营私罔利、误国殃民之秽史,既为天下所共见”。③吴贯因:《拟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庸言》,1913年7月,第1卷第16期。
梁启超很少直接谈论责任内阁,他主要侧重加强总统的权力。但是《庸言》在梁启超主持期间,一直唱着“责任内阁制”的调子,吴贯因谈责任内阁的时候是与行政权捆绑着谈,落实于加强政府权力,实现国家统一意志。这就是《庸言》“责任内阁制”的微妙之处。《庸言》创刊之初,基本上是革命派控制国会,责任内阁已经是既定事实,吴贯因在创刊号上就言之凿凿地主张内阁制,这是与民初的政治现实合拍的,在这种情况下,吴贯因在主张改变现行政治体制方面说话还留有余地,但这种责任内阁倾向于削弱国会对它的约束,加强内阁的权力,这在法理上也讲得通,但是主张内阁总理由总统任命,内阁就可以和总统捆绑在一起。这就使《庸言》同仁可以左右说话。总统任命总理,为总统扩张权力留下余地④吴贯因在《关于立法权政府与国会之关系》《(庸言》,1913年6月,第1卷第13期)显露了这一动机,他主张内阁应该有附署权,但是总理如果不附署,总统可以将其撤换。在这种思路下,责任内阁的权力就陈仓暗度,潜移于总统,是以这种责任内阁总体倾向上与加强总统权力不矛盾,与《临时约法》的精神不同。,1913年9月,二次革命失败,革命派势力被袁世凯逼出中央,熊希龄内阁成立,梁启超入阁,吴贯因就直接主张“不能虚悬总统”,认为只有君主国才元首虚悬,共和国不应如此⑤吴贯因:《共和国体与责任内阁》,《庸言》,1913年9月,第1卷第20期。。《庸言》同时又坚守内阁制的阵地,为梁启超势力在内阁发挥作用留下余地,因为他们毕竟不可能去角逐总统,这是《庸言》在政治斗争方面的考虑。同时,他们的主张也不止于此,梁启超集团毕竟不同于袁世凯,坚持责任内阁也可以对袁世凯有所约束,为实现梁启超“导袁世凯上轨道”留下空间⑥参见梁启超:《袁世凯之解剖》,《饮冰室合集·文集》(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3-14页。。而且《庸言》也一直有维护民主政治、防止绝对专制的追求。责任内阁制的主张就是明显的体现。《庸言》在言论方面要角除了梁启超之外就是吴贯因、蓝公武、张东荪,尤其是后期,张东荪的地位非常突出,张东荪就是一个比较彻底地坚持内阁制的人物,对《临时约法》下的内阁制也给予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与吴贯因、梁启超将民国初年政治混乱的原因一概归于革命派的捣乱的论调⑦参见吴贯因:《今后政治之趋势》,《庸言》,1913年8月,第1卷第17期。有所不同,他认为这种政治失序同时也有总统借提出权而要挟国会、内阁的原因,制度设计固然有纰漏,但是关键在于当时的政治人物不善于正确运用这种权力,而且张东荪肯定地说“临时约法之条文虽有含混之弊,然实采用内阁制固无可辩难”,同时明确主张内阁总理由下院选出,内阁颁布阁令,用人权操诸内阁。⑧参见张东荪:《内阁制之精神》,《庸言》,1913年9月,第1卷第19期。这与梁启超、吴贯因婉转曲折为袁世凯张目是有所不同的。二次革命后,也是张东荪比较敏感地意识到共和受到威胁的趋势,极力呼吁依法治国,他对民主制衡的真精神的认识比包括梁启超在内的其他人要理解得深透,而且分析得入情入理,对理想理论的介绍也比较细致,起码在《庸言》杂志上是这样的。
《临时约法》所设计的内阁制,内阁须由国会同意,其背后的理论基础是主权在民,而《庸言》则反之,这体现出以梁启超为主的《庸言》在根本理论上与革命派的分歧,这种分歧体现在政治运行中就是要推翻《临时约法》所奠定的法统,在梁启超“主权在国家”思想指导下另立一个法统。这是梁启超从事政治的核心思想,也是在民国元、二年梁启超一切行动的中心,①参见梁启超:《袁世凯之解剖》,《饮冰室合集·文集》(三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0-11页。这体现了梁启超在思想上、行动上与袁世凯的合作。所以在《庸言》中对国会以及对国会议院能力低下、道德败坏的批评连篇累牍,有些言论非常激烈。这一方面固然道出当时共和草创时期的实情,另一方面也确实是为梁启超实现这一主张张目。
二、强人政治与“国民程度”的怪圈
1906年《开明专制论》发表的时候,梁启超的政治思想已经形成。他的思想要点是以民主政治为目标,实现这一目标的首要环节是“开明专制”。在梁启超的政治思想中,民主理想与开明专制的手段两个要点缺一不可,这种思想背后的精神就是渐进改良。由于有理想,使其与一般单纯为了自身利益的政客有了区别;由于主张渐进改良,使其与激进派阵线分明。开明专制的实质仍然是精英政治,希望通过强有力的政府或者政治强人来掌控局面,通过梁启超的思想和专门知识,在有序的情况下实现政治的上轨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监督政府、向导国民”。
从中国不断走向殖民地深渊、迫切需要有效整合国民力量走向强大的事实来看,梁启超的这一设计是非常有道理的,通过最小的社会震荡,在有序的政治形势中,逐渐走向民主政治,应该是中华民族之福,日本、德国、意大利就是这条道路上的成功者,英国的民主政治也是经过长期的改良而实现的,梁启超也确实把这些国家当做效法的榜样。梁启超在言论上、理想层面也非常清楚,民主政治必须有“对抗力”②梁启超:《政治上之对抗力》,《庸言》,1913年1月,第1卷第3期。方可得以保证,但是在实践中,却将此问题简单化,把孙中山势力当做捣乱的势力,不想进行复杂、艰苦的政治斗争,甚至内心深处期盼着这种力量的消失。虽然在《庸言》中,梁启超与革命派的斗争都是思想上的、理论上的,但是在二次革命期间及稍后,《庸言》同仁对革命的失败未免有弹冠相庆的心理,张东荪就曾经说袁世凯迅速平定二次革命“功不在禹下”③张东荪:《法治国论》,《庸言》,1913年11月,第1卷第24期。。梁启超也口口声声地说,在强人政治下的自由如猫口之鼠之自由④梁启超:《开明专制论》,《饮冰室合集·文集》(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2页。,政治强人岂是法律一纸空文所能束缚?⑤梁启超:《同意权与解散权》,《庸言》,1913年4月,第1卷第9期。但是在实践中,他却总是幻想自己不会重蹈这样的覆辙,这是梁启超作为政治家的幼稚所在,也是梁启超一生乐观性格使然。
二次革命失败,在袁世凯的眼中,梁启超的作用就是为其下一步成为正式大总统制造合理依据,而且革命派的有形实力被瓦解之后,一时已经无人能够撼动他的力量了,在这种情况下,为渊驱鱼的作用基本达到,梁启超辈就不是不可替代了,其地位就无足轻重了。历史事实是1913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同月任命熊希龄为国务总理 ,9月熊内阁成立,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按说据宰辅之实的梁启超正迎来了自己大展宏图的时机,但是位极人臣之时也正是梁启超暗淡退场的开始。梁启超一生在现代法治问题、财政问题方面投入极大精力,在当时完全可以称得上是法律以及财政专家,起码他对当时这些领域的理论掌握是站在同时代人最前列的。但是在司法总长以及币制局总裁位置上,就是在他这样具有成熟腹案的两个领域也难以稍有展布,最后不得不无奈辞职,这实际上宣布了梁启超新士大夫精英加政治强人的渐进民主道路的失败。最后梁启超不得不走向他一生最反对的“革命”⑥注:在梁启超看来,用暴力手段改变现行政治的行为就是革命。道路:武力倒袁。但是梁启超并没有认识到这是思想路线的失败,只看做具体政治活动的失败,换一个人他的理想是可以实现的,于是护国运动后,梁启超在段祺瑞的身上又重复了一次与袁世凯的故事。此时,由于孙中山的势力已经退出中央,段祺瑞对任公就更不客气了,直接搞了个御用的安福国会,梁启超再次被迫谢幕。
几乎与梁启超辞去司法总长的同时,《庸言》在黄远生的主持下以新的面目出现,与前此政治团体机关报不同的是黄远生主持的《庸言》是一份以时事评论为主的月刊。黄远生在第二卷第一号《本报之新生命》中特别强调了“吾曹此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根据“综合事实而后下一判”,不再“凭恃理想”“发挥空论”。黄远生开始反思民元以来热切的理想为无情的事实所打破的根本原因,他认为社会改革不是一人一姓的事情,应该是整个民族的事情,“今日成此混乱局面,人人有其责任”①黄远生:《消极之乐观》,《庸言》,1914年2月,第2卷第25、26期合刊。。黄远生后来特别重视国民整体的觉悟与素质,认为只有整个民族素质提高了,才不会有破坏共和的历史倒退现象。黄远生的这种认识体现了知识阶层开始从直接参与政治、引导政治强人入轨道转向以提高民族素质为内容的文化建设,也就是再度启蒙,可以说黄远生主持的《庸言》某种程度上是启蒙者的新声。梁启超麾下的言论健将张东荪也逐渐由“谈政治”转向文化启蒙。黄远生发表此番言论是在1914年2月,离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已经很近了。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主体转入到启蒙的洪流中,对参与现实政治不再感兴趣。但是五四运动后,知识分子又发生了分裂,许多人又重新投入到现实政治当中。这样,辛亥革命又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一个循环,首先思想输入、宣传,探索建设国家的方案;其次是依靠强有力的政治力量希望实现民主富强,新的强人政治稍微立稳脚跟之后,甚至是在上升时期再度压制言论,破坏民主;最后就是知识分子再度失望,力量不足以反抗现行政治势力,再度转向启蒙。这是一个循环,也是一个怪圈,很难突破这个怪圈走向民主政治的坦途,这里我们可以把这个怪圈称为“梁启超魔咒”。
三、健康、成熟的对抗力
“梁启超魔咒”下的历史新循环是辛亥革命所开启的,这可以说是辛亥革命的无奈遗产,辛亥革命去掉了一个形式上的专制政权,却导致了多个打着共和旗号的实质上的专制政权,这是从形式上所看到的现象;从实质上看,辛亥革命也确实培植了专制制度的持续的、恒久的否定性力量,用《庸言》同仁的话说就是“对抗力”。下面我们引一些张东荪的文句:
无形之对抗者,国家社会内各分子互相对峙而使各不相犯之谓也。“强有力者恒喜滥用其力,自然之势也。滥用焉而其锋有所婴而顿焉,则知敛;敛则其滥用之一部分适削灭以去而轨于正矣。百年以前,各国之政治未有不出于专制者也,而千回百折卒乃或归于君主立宪焉,或归于民主立宪焉,皆发动与(作者注:原文如此,今当作“于”)对抗力相持之结果也。即在既立宪之国,期间雄才大略之君相,凭席势之党派,亦未始不跃跃然常怀专制之思也。然其不能焉者,知它方面对抗力之不可侮也。”“强健正当之对抗力何自发生焉?曰必国中常有一部分上流人士,惟服从一己所信之真理而不肯服从强者之指命”,而此一部分之人士不必尽从事于政治,但足以消极的使政治入乎正轨,滥用政权者得而惧焉。此一部分人士所恃者为潜势力,其人则散处工商农学各界,故一呼而社会响应,盖以其代表社会之各要素以谋调和各要素之利益,不使政象趋于专制,专制则各要素之利益没却矣。此谓之无形之对抗。
引号内是奥地利社会法学家艮波罗维企(Ludwig Gumplowicz,今译贡普洛维奇)Die sociologische Staatsidee的句子,张东荪认为维系政治不陷于专制的力量就是“对抗力”。对抗力的形成有两个要点:一个是有一部分“上流人士”只服从自己所信从的真理而不服从强权;其二是支持这部分人的“潜势力”,这些潜势力“散处工商农学各界”,这是上流社会能够具有对抗力的基础。上流社会与农工商各界构成的力量是“无形的对抗力”,政治家与政党的活动把这种潜在的对抗力实现为“有形的对抗力”,也就是说真正的政党政治应该是各种利益的代表,民主政治就是各种利益集团的调和。没有真正的、相对独立的利益集团,民主政治不能健康成长。张东荪进而指出,“相反之势力欲保持其对抗焉,必使其不可接触宪法、国家最高机关及武力。三者苟其一接触之,其相手(作者注:疑当为“反”字)方终不能敌,而对抗之形消矣。是故苟于宪法之下及国家最高机关之下,武力之外以行其竞争,则对抗可保持,始有政治可言,亦始终有进化之可言也。”张东荪所选择的上述理论足以解释民国以来的政治乱相以及共和实践的失败。张东荪不自觉地流露出对革命派失败的痛惜,他把民国初年的两种势力称为旧官僚与新暴徒,虽然给革命派以暴徒的“恶谥”,但这两派毕竟构成了对抗力,由于不善于运用这样的对抗形式,最终一派压倒另一派,对抗之局终究没有形成,形式虽然共和告成,但是前途暗淡。袁世凯正凭借手头的武力,逐渐掌握了国家机关、宪法,使对抗得以出现的三个保障逐一消失,共和仅仅流于形式。梁启超仅仅看到了对抗力的枝叶,也就是上流社会,张东荪看到了对抗力的根干。
就中国的实际而言,近代民主运动完全是出于工具性的动机,也就是看到民主国、立宪国之所以战胜中国是因为它们的民主政治制度,中国要自强,只有引进民主才行,民主是自强的手段,一旦其他的方式可以获得自强,或者民主带来混乱而不是团结,民主就可以抛弃,这是自康有为、严复、梁启超等人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屡屡摇摆于民主与强权之间的根本原因。由于这种工具性的民主也是自外边引进的,而不是中国内部政治走向的自然结果,所以足以构成对抗的力量就只有摇摆不定的知识分子群体,农工商的力量微小,很难说是有了自觉,这就是民元以来民主政治仅仅在形式上运行两年,国会即告瘫痪、专制苗头再起的根本原因。1914年袁世凯独裁趋势越发明显,张东荪等人就开始从经营“有形的对抗力”转向培植无形的对抗力,培植无形对抗力的方法就是再启蒙、再度教育民众,他们所注重的主要是学界,也就是以新式学堂为基础的新式学生,陈独秀也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而创办《青年杂志》从事思想启蒙的。
梁启超、张东荪所说的“上流社会的知识分子”虽然秉持民主工具论的态度,但是在曲折艰难的政治斗争中,也逐渐坚定起来,民主目的论的倾向日益突出,但是外在的侵略危机始终迫在眉睫,也使知识分子难以有机会完全秉持民主目的论的态度。把民主看作一种目的,胡适应该是第一代人,后来《庸言》同仁张东荪也坚定地加入了这一群体。20世纪30年代初期,蒋介石削平各派力量,实行其独裁“训政”,胡适扬起了民主的大旗,张东荪也再度投袂而起,创办《再生》杂志,公开反对蒋介石的训政,致力于培育真正的“对抗力”。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说人民知识、能力不及格,不能实行宪政,“则必是全国的人民都是如此。决不能有一部分人被训,另一部分人民能训。被训的人民因为没有毕业,所以必须被训。试问能训的人民又于何时毕业过呢?何以同一人民一入党籍便显分能训与被训呢?”他指出,“国民党公然主张训政,是侮辱全民的人格。”民主政治不仅是一种制度,而且是一种精神,这样,民主便没有能否实行的问题,而只有实行程度的问题。“我们可不管人民程度,总得在可能范围内尽量使民主政治为之实现。”人民程度问题,“只能实施时酌量的根据,而绝对不能作为反对或延缓的口实”。①张东荪:《我们所要说的话》,《再生》(创刊号),1932年5月20日。转引自左玉河:《张东荪传》,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页。
抗日战争时期,外在的侵略在近代历史上第一次促进了国民对民主的追求,增加了民主的力量,各种对抗力达到一种暂时的、不平衡的共存,中国的民主政治也就达到了20世纪上半叶的最高潮。但是这种对抗力仍然处于强大的武力威胁之下,党派操纵国家机关、操纵宪法的基本形势依然没有改变,所以对抗力依然没有成熟。什么时候对抗力成熟了,中国的民主政治也就基本穿越了历史的三峡②注:“历史三峡论”是唐德刚的提法,参见唐德刚:《袁氏当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5页、第92页、第121页、第168页。,走上黄金水道了。
The Argument Dimensions ofThe Justiceand Early Republican Political Deadlock
WU Zhanjiang,HAN Xue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Shijiazhuang,Hebei 050061,China)
A prominent feature of transferring ancient Chinese politics to modern political transition is the vicious circle of the change of enlightenment and politics,instead of the supersession of dynasties.The cycle of the supersession of dynasties formed the vicious circle of history in a plane dimensionality.Though various changesoccurred in autocratic politics,there was no real progress.From the period of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to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Chinese politics formed another vicious circle of didacticism and despotism.It was well-known by all torchbearers that modern politics could not be achieved without the enlightenment,which is also a historical fact.But the rulers,who regarded themselves as Chinese Savior,believed that centralism was the only way to resist aggressions of big powers and eliminate internal disorder,that they were the only guide of democracy,and that the people’s democratic appeal was a kind of unrest and rebellion.So they took actions to suppress public opinions.As a result,they became negative forces to democracy.The Justice,a famous magazine published in 1914,witnessed the period of centralism to anti-autocracy,which also revealed the track from the Reform Movement of 1898 to the May 4th Movement.
The Justice;Liang Qichao curse;a new historical cycle;heterogeneity against the force
K258.9
A
1008-469X(2012)02-0013-05
2012-02-22
武占江(1969-),男,河北沽源人,历史学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新闻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