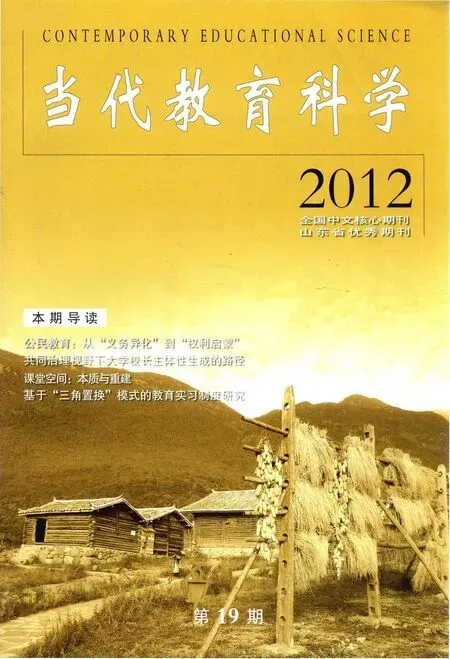学业自我淘汰机制的文化资本成因分析
●韩 月
在学习过程中,从努力角度出发,学生的学业失败是一种可被选择的结果。学生未必都对学业成功充满期待,他们可能会以自我淘汰的方式对待学业,漠视学习甚至仇视学习,乃至产生辍学现象。如果仅仅从经济角度关注学生的厌学和辍学,便不能全面解决学生对于学业的无望或逃避。学生在学校中学习,无法避免外部的社会因素对于自己观念的影响,如果仅仅将学生选择自我淘汰归咎于教师和学校便过于狭隘,但同时,教师和学校又确实具有促使学生增强学业成功期待的可能。
一、学生拥有的资本对于学业的影响
(一)学生拥有的资本的表现方式
马克思对于资本的研究引起了学者们对于这一名词不断挖掘。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所定义的资本已不仅仅具有经济领域的含义,在他的理论中,资本可以表现为三种基本的形态:经济资本,这种资本可以立即并且直接转换成金钱,它是以财产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资本,这种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社会资本,它是以社会联系组成的,这种资本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1]
国家通过义务教育政策或者助学等活动可以使一部分由于缺乏经济资本的学生具有接受教育的可能。然而,家庭所具有的经济资本越多,学生在学前阶段和课外获得的教育便越具有优势。经济资本不会直接决定个人受何种教育,但是却可以通过投资于教育机构和能传递文化的物质(如图书、工具等)进行资本转换,增加个人的文化资本,进而促进个人可接受的教育。出生在不同阶层的家庭,便为个人分配了不同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影响了家庭的消费方式、休闲方式,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对于孩子的教育给予的关注越高。父母凭借自己的学识能够更好地将经济资本转化为促使孩子学习的文化资本。父母的受教育经验影响了家庭日常的休闲方式,高教育群体能够选择一些更高雅的休闲方式,这些往往是主流文化推崇的。因此,在消费和休闲方式中都能受到相应教育或符合主流文化行为方式的学生,在学校之外便获得了不菲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在学生身上较为明显的体现为由父母的血缘、朋友所构成的关系网络。社会资本与家庭的社会地位直接相关,而且能够通过家庭日常的交际使学生感受到相似的阶层熏陶。通过社会资本,以交流的方式,学生获得了所生活的阶层的价值观念。
对于学生而言,课堂上的表现和考试的内容可能只是他们显示自身文化资本的机会。这些外显也受到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推动,使得个体在学校受到与他人相同的教育,却表现出似乎由于智力因素导致的优异。而对于资本总量较低的学生,其所处的家庭、阶层或许注定他们在学校无法简单地实现学业成功。
(二)家庭中的文化资本积累
布迪厄将文化资本分为三种形式:(1)具体的状态,即精神和身体的持久“性情”的形式;(2)客观的状态,即文化商品的形式(图书、词典、工具等),这些商品是理论留下的痕迹或理论的具体显现;(3)体制的状态,这是一种必须被区别对待的客观化的形式,它赋予文化资本一种完全是原始性的财产,而文化资本正是受到了这笔财产的庇护。[2]
家庭因素决定了个人可获得的具体形态的文化资本的差异。学校可以为所有学生提出统一的规范,给予平等的教育,然而家庭通过学前时期和日常的生活对于学生观念的影响仍十分明显。学校教育的群体性与家庭所施与的个性之间的矛盾必然存在。虽然在学校接受等量的具体形态的文化资本,但学生受父母影响而养成的习惯、价值观念和情感体验呈现出的纷繁性决定了个人此种文化资本的差异。学校能为学生提供各种与学习有关的书籍、工具,并指导个体如何通过它们来增加个人的文化资本。然而,家庭所具有的消费能力、消费方式却可以影响个人在学校以外获得怎样的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比如父母有看书、藏书的习惯便影响孩子进行模仿,通过客观的文化资本提升品位。
学校对于学生的认同表面是对学生学习能力、学习态度的认同,而家庭所造成的具体形态和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的差异则可以视为一种潜隐的因素,这种因素导致学生由于家庭而产生与学校所提倡的文化一致或疏离。而学校、教育机构或政府对于个人学业的认可,不论是通过合格考试还是选拔考试的方式,都是对于个人在学校和家庭接受的所有文化资本进行认可,并非仅从学校教育考虑体制形态的文化资本获得。在学校的学生有机会接受相似的文化资本,但个人文化资本总量的差异却由各自家庭和获得资本机会的不同而产生悬殊。个人文化资本的差异,导致的便是学业上与主流思想的一致程度,影响了个人对于学业的心理认同,以及个人需要为学业付出的努力。因此,文化资本作为一种个人的所有物影响了其在学生群体中的对于学业的态度。
二、学校中教育行动的价值误识
(一)主文化取向
在学校之中,学生处于相同的环境,用相同的教材,由几个老师分别传授知识。无论是通过显性的还是隐性的学校教育,所体现出的教学内容都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性以官方文化或社会群体持有的主文化为归宿。在一个给定的社会构成中,由于教育系统受主教育行动所支配,所以系统趋向于在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中,再生产对合法文化就是主文化专断这个客观真相的复制,而主文化专断的再生产有助于权力关系的再生产。[3]因此,学校教育虽然以学生的发展为目标,但却客观推动着学生不断走入主文化所导向的道路,并藉由学校使主文化得以传递,通过学生复制主文化,并延续主文化。教育工作是一种长期的灌输工作,它使一种文化专断原则以一种习性的形式内化。[4]当所有学生都被置于主文化环境之中时,由于个人文化资本的多寡所导致的与主文化的适切性,将导致个人是否能轻易适应主文化,进而表现出学业上的成就。学生由于继承家庭的文化资本而在学校中被分为具有不同学业发展可能的群体,这种文化地位的复制在学校完成资本的认可,在离开学校时则可以获得不同的权力。教育体制隐藏了权力运作的至关重要的秘密:它既是权力运作、传承和再生产的主要途径,同时又由于其超越功利相对自主性的形式,掩盖了权力的支配关系。[5]
(二)学生与学业之间的文化不适应
学生由于家庭的文化资本单薄,在进入学校之后会出现与主文化的差异或者不适应。与主文化的差别导致的是学生与学校导向的文化之间的差距。若实现学业成功,学生就要使自己适应学校的文化,调试自己的心态,付出很大的努力。不具备文化资本优势的学生身处学校之中由于文化差异也可能产生学业不适应,他们消极应对学业,并非是源自无名的反感,而是源于自己由于不适应而表现出的抵触。学生的学业失败的文化适应性归因,正说明学生占有的家庭文化资本对于学业表现的影响。学生源于资本而产生的文化认同或排斥促使学生学习过程中伴随有积极的或消极的情绪,由于情绪便可以产生自我效能的提升或学业的自我淘汰。
三、学业成败的归因机制
(一)令人绝望的学业成就的解释
拥有更多文化资本的学生具有更大的学业成功的可能,具有较少文化资本的学生不仅成功的可能较小,而且也更易选择学业失败。学业的成败并非由个人的智力所能全部决定的,毕竟处于高智与低智的群体占总群体中的比例较小,而大多数人的智力和理解能力都是中等的,所以个人对于学习的态度与智力相比更能够决定个人的学业成就。而高智人群可以选择不努力而厌学,低智和中智人群可以通过努力而获得成就。智力不能完全解释学习成就,而由于文化资本的多寡有时被误解为是智力或遗传的因素,将学业成就看作是学生天资的显现,或者父母智力的继承。虽然天资的差异和遗传学的偶然性可能把不同的天资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进行不同的分配,然而应认清以天资差异为外衣的受社会条件制约的文化方面的不平等,毕竟,从“本性”中可以归结出令人绝望的原因。[6]将学业成败归因于遗传或天资等非人为的因素,个体所能取得的学业成就将被固定。学业成功者将受到激励,失败者将更为自卑,由于他们的情绪所导致的学习态度将未来的学习导入不同的方向。而实质上,这些非人为似乎出生时便被注定的因素并不能决定个体的学业成就,个体由于持有的文化资本更能够决定处在相同的学校环境下并付出相同努力的学生的成就差异。
(二)社会因素所导致的学业失败
具体、客观和体制三种状态的文化资本共同影响了个体的文化建构。在社会化的环境中,个人文化资本的被评价和被比较必不可免,而反映在个体心中的则是由于文化的适切性、卓越性提升了个体的内部期待,而与之相反,则导致个体自我放逐,不抱有任何学业期待。学业分类中残存着位置和习性之间的不协调,这些不协调在入学之后倾向于得到纠正:要么是“不合适”的人“自我淘汰”——或自动放弃,或转入那些更符合他们愿望的教育机构;要么就是在最后的选拔中,或者在进入职业生涯的时刻(此时,继承所得的社会资本具有最大的效能),被排除在学业选拔之外的所有标准重新恢复了最大的效能。[7]涂尔干与韦伯虽然以不同的认知策略审视社会学,但都认为个体行动者并不十分清楚自己行动的原因,因此,他们的个体判断并不是社会学成功地解释“社会现实”时使用的材料,真正促使个体行动的,包括他们真实而被自我宣称的动机,都源于通常超出了他们控制的外在世界。[8]学业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并非是个体的主动选择或生理所决定的,与自己出生的家庭环境密切相连,与社会的文化导向不可分离。
从文化资本的角度思考学生的学业成就,个体由于出生便受到了一定的决定因素,但并非是无法改变的,资本可以由继承而获得积累,也同样可以由开创而获得提升。学生通过不懈的努力与利用外界有利的环境,可以打破自己被社会所决定的学业失败的倾向,而走向成功。
四、提升学生学业期待的对策
家庭对于学生文化资本的积累有着重要的意义,学生的学业劣势也许无法通过家庭而获得改变,这时便需要通过政府、学校的“有为”来促进学生更好地获得文化资本。
(一)政府的能为
职业的分工、个人接受教育的水平差异,都会导致不同家庭拥有文化资本的差异。而在家庭之外,政府作为公共资源的分配者,应为学生接受更好的教育,并通过更好的教育获得更好的生活而负责。政府所具有的权力和职责,能够为个人获得更满意的文化资本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政府通过开放图书馆、博物馆等具有教育意义的公共场所,可以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客观形态的文化资本,以促进个体知识的增进;政府借助具有文化价值的物化形式,鼓励全民读书、学习,能够构建一个学习型社会,而使身在其中的人都有机会通过与人交往获得具体形态的文化资本;政府通过组织考核以认可学生或校外人士能够掌握的知识进行认证,以促使各种文化都得到认可,在尊重个体和亚文化的同时也将扩大体制化文化资本的内容,并使个人从中获利。
(二)学校的可为
布迪厄强调,学校教育功能在于具备无意识(或深深影响着的)模式系统的个人,这种系统构成他们的文化,或者在更好的情况下构成他们的生存心态——教育改变着集体的精神文化遗产,使之成为个人的或共同的潜意识。[9]学校教育可以将集体文化施与个人,也可能造就不适应的人,但学校在进行教育中不应只见群体,不见个体。教学的特殊化,课堂上学生的主体性发挥都是在思考学校如何使个人的发展获得尊重,在群体中不被淹没个性。学校对于学生而言不是简单的获得知识的场所,学校不应是“无为”的机构,而应该能够积极主动应学生的需要提供各种获得文化资本的机会。凭借自身的优势,学校应该在了解每个学生的基础上,针对他们的文化劣势进行弥补,通过鼓励教师和同辈群体对其关怀与帮助,以使学生能够通过学校获得因家庭差异导致的文化资本的相对差距。
每个人都无法决定生于何种家庭,生活在何种阶层,当学校平等地对待所有学生而所有学生又以相同的努力对待学业时,由于继承获得的文化资本对于个人的学业便可以具有决定作用。然而,看到学校无法改变自己的文化劣势,排斥自己的文化身份时,学生有时以自我淘汰的方式进行着无声的反抗。学校与政府在个人的学习过程中不应当是无为的,它们的有为可以为最需要文化资本的学生提供机会,进而改变自己学业失败的走向。
[1][2]包亚明.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布尔迪厄访谈录[Z].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192,192-193.
[3][4][法]布迪厄,帕斯隆.邢克超译.再生产——一种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40,45.
[5]朱国华.权力的文化逻辑[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4,83.
[6][法]布迪厄,帕斯隆.邢克超译.继承人:大学生与文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99.
[7][法]布尔迪厄.杨亚平译.国家精英:名牌大学与群体精神[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8.
[8][英]鲍曼.郇建立译.被围困的社会[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8.
[9]高宣扬.布迪厄的社会理论[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4,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