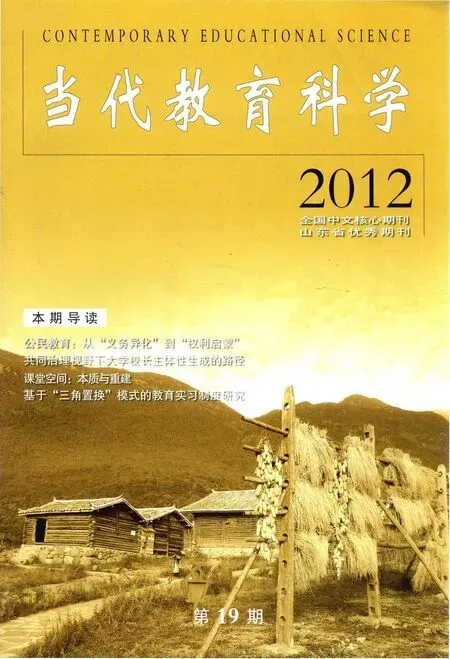义利与人性:墨子教育思想的伦理建构*
● 郭智勇
春秋战国时期,私学已然兴盛,“学在官府”的传统随着学术环境的开放,渐为民间特色的政治宣教活动所取代,“上说下教”已经成为一种表达政治思想的普遍形式。所以,孔子认为,教育就是把孝道、礼仪传播到社会中去,从而间接地对政治活动施加影响,故“《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论语·为政》)。但是,孔子教育思想中多少还残留着先天命定论的束缚,还有所谓少数“生而知之”的“上智”者与“困而不学”的“下愚之民”,甚至认为“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与此相反,墨子对教育的关注不在于先天的命,而在于后天的人及人“力”,反对“命富则富,命贫则贫”的宿命论,强调教育的作为,故其曰:“夫岂可以为其命哉?固以为其力也”(《墨子·非命》)。因此,墨子更加注重用积极的教育来改变社会,弘扬人间“良道”,希望“有道者劝以教人”,而不应该“隐匿良道而不相教诲”(《墨子·鲁问》)。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墨子对教育何以存在的理解,更加贴近当时社会人们的生活需要,并从人性 “欲生”、“善生”的视角探讨了教育得以存在的伦理基础。
一、义利统一:教育价值和谐
墨子思想的核心在“兼相爱”,在其看来,道德教育是实现人人相爱的主要路径,“厚乎德行”要通过教化,才能普及天下,合乎天下之义。所以,墨子曰:“万事莫贵于义”(《墨子·贵义》),义在墨子那里是至高的伦理境界,《墨子·大取》篇云“义,利也”。义就是利,就是利人、利天下之义,也就是“凡言凡动,利於天鬼百姓”(《墨子·贵义》)之义,这是普天之下的最高目的。墨子以天志言义,此义为天义,天希望天下之人兼相爱,交相利,从而实现天下之治。所以,“天欲义而恶不义”,“天下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治,无义则乱。”(《墨子·天志上》)所以,天之所欲在义,天希望天下人都能生活富裕,能够弃乱而天下治。而现实生活中的人,也希望生活安定,人人相爱而天下有序,这是合乎人性的,是常人生活追求的正当性所在。所以,人们应当顺天意,兼相爱,交相利,“顺天意者,兼相爱,交相利,必得赏。”(《墨子·天志上》)因而义就是天意,只有天下人相爱相利,才能实现天下之治。因此,义既是上天之意,也是万民之欲。正是这个缘故,天欲义而恶不义,民也欲义而恶不义,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义为天下之大。这就要求天下之人,皆应顺天意而为仁人之事,仁人顺天意而“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兼爱上》)。墨子以此要求天下人皆以兼爱行天下之利,这个利的具体内涵究竟是什么呢?墨子在《兼爱上》中将之概括为“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这样才会实现“诸侯不相战,家主不相篡,人与人不相贼”的和睦社会。所以,天下人人相爱,强不执弱,富不侮贫,以至君臣惠忠,父子慈孝,兄弟相和,这才是墨子追求的天下之利、天下之义。
人与人相爱的这样一个理想的状态是利人的,为仁义之本,这是人与人相处的应然之道。但是,人与人之间是否生来就能为善行义并相利呢?至少在墨子看来,不是这样的,人有善有恶,有爱人者、有利人者,如“昔三代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者是也。”(《墨子·天志中》)然而,也有恶人者、害人者之流,如“昔者代暴王桀、纣、幽、厉者是也。”恶人者、害人者常常不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仁人而兼爱以利天下的,他们常常违反义的要求,“从事别,不从事兼”(《墨子·天志中》)以至“大国则攻小国,大家则乱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谋愚,贵傲贱”,所以,“观其事,上不利天,中不利鬼,下不利乎人。三不利,无所利,此非仁也,非义也。”(《墨子·天志中》)对这样的恶人者、害人者,应当使其得到天的惩罚,“夫憎人贼人,反天之意,得天之罚。”(《墨子·天志中》)除此以外,墨子认为对社会更多的人而言,还应当通过教育劝导的方式,劝其从善,使之为义。所以,“故圣人以治天下为事者,恶得不禁恶而劝爱?故天下兼相爱则治,相恶则乱。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劝爱人者,此也’。 ”(《墨子·兼爱上》)通过劝人爱、教人“义”,从善弃恶,则天下之义,必然实现。因此,义的实现需要人人相勉、相教,这是教育的应然选择。
二、性恶之实然:教育价值建构的人性论基础
先秦论性,派别繁多,见于《孟子》者大致有三,其中告子认为,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凡物皆因际会而成,人性亦犹是也。[1]这一认识与墨子关于人性的认识颇为相似。有研究者以为,墨子在人性善恶的认识方面,强调后天生活环境的影响作用,认为人性的善恶得之于后天的社会环境,它不是先验的。人性的善恶、道德品质的好坏,是后天的生活环境造成的,后天的环境对人格形成和自身道德水平的提升起决定性作用。[2]与此相似的观点还有秦彦士的“素丝论”,他认为墨子的人性并无善恶之分,人的善恶都是后天习染造成的。[3]而有部分学者观点则与此相反,其中,杨俊光的观点颇有代表性,他认为,墨子人性论的基础在于人之性恶的一种潜在的认同,在他看来,墨子“无善无不善论,似不必是”,他例举引用了肖公权、陶愚川等人的观点,认为墨子似有暗示人之性恶的立论,尤其赞同肖公权所引的《墨子·尚同上》的例证,“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以至“隐匿良道,不以相教”,[4]这是有道理的。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发现墨子在人性论方面是认同人性恶的观念的。在《墨子·兼爱上》中,墨子以为,天下之乱源起于人与人之间不相爱,“子自爱,不爱父,故亏父而自利;弟自爱,不爱兄,故亏兄而自利;臣自爱,不自爱君,故亏君而自利。虽至天下之为盗贼者亦然,及至大夫相乱家,诸侯相攻国者亦然”。所以,人性在生活中确有恶的倾向存在,他举例证曰:“今天下为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劳,其籍敛厚,民财不足,冻饿死者,不可胜数也。”(《墨子·节用上》)正是由于恶的存在,不能实现人人相爱,才导致天下大乱,相互攻伐,荼毒生灵。所以,他倡言要行教诲之道,使人人知义而安天下。这从其天鬼论的赏善罚恶的论述之中,也可窥见其端倪,“是以吏治官府之不洁廉,男女之为无别者,鬼神见之;是以吏治官府不敢不洁廉,见善不敢不赏,见暴不敢不罪…是以莫放幽间,拟乎鬼神之明显,明有一人畏上诛罚,是以天下治。”(《墨子·明鬼下》)这里墨子实际上已经预设了人性之恶的先验性存在,也正因为如此,鬼神赏罚之明也才能得以明证鬼神的存在,鬼神行赏罚之能的先验性认识,即是以恶的先验性存在为前提的。所以,墨子在论证鬼神神明存在的过程中,实际上已经表明了其人性论的基本态度,即人性是恶的,所以才需要予以惩戒、教化。
对人性之恶的先验性推论并不能完全消除世人对人性之善的虚妄,还需要在现实生活的感受中予以确证。墨子第一个系统提出“历史经验、人民现实经验的真理性标准”,[5]尤其突出人民大众在现实生活中对善恶的体验。所以,墨子在有关非攻、节用等论述中,从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等方面举证了人性之恶的实践经验感受,同时,他也力举了很多人性之恶的种种表现,确证了人性之恶的客观存在,甚至在言箕子、微子、周公旦等圣人之前,都有相应的恶人比之存在,“昔者,商王纣、卿士费仲”以及“关叔为天下之暴人”(《墨子·公输》),通过与圣人比照,这样才能突显圣人之圣、仁者之仁。因此,在墨子看来,恶是一种人性,是一种现实存在,难以回避。人性既然是恶的,就应当予以教化,通过教育来使人明义而知礼,这也是人之为生的实然所需。
三、人性可为:教育价值建构的至善追求
人性虽恶,然而在墨子看来,人性不是生而不变的,人性的善恶受到后天诸多因素的影响,通过教育感染是可以改变的。孔子“性相近,习相远”与“上智与下愚不移”的矛盾,墨子予以坚决否定,他认为,“教人学而执有命,是犹命人葆而去其冠也”(《墨子·公孟》),这是不可思议的。
人在生活中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因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教育等环境的好坏,其人性之善恶也会表现各异,在不同的情境中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故“子墨子言,见染丝者而叹曰: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墨子·所染》)。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人,环境对人性的养成和发展趋向影响很大。因此,“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墨子·所染》)这样看来,环境的选择非常重要,应认真对待,慎重为之。工匠染丝的这个道理对国家、对社会、对个体存在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墨子认为,“非独染丝也。国亦有染。舜染于许由、伯阳,禹染于皋陶、伯益,汤染于伊尹、仲虺,武王染于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与圣人相交,受到圣人思想的教化,则为贤臣良相,善政可为以致功名传扬天下。反之,则如“夏桀染于干辛、推哆,殷纣染于崇侯、恶来等。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僇。举天下不义辱人,必称四王者”(《墨子·所染》)。墨子以此例证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比较,说明环境对人性养成的熏染是多么重要。所以,墨子主张为君者欲求天下安定,一定要“行理性於染当”(《墨子·所染》)。认真选择人性养成的环境,这样才能行事合理,天下善治。
循此路径,墨子由国及士,认为交友皆是仁义之士,遵纪守法,家道就会日兴,如果交友不当,“皆好矜奋,创作比周,则家日损,身日危,名日辱,处官失其理矣。”因而,士人交友所处环境的当与不当,对人的发展和家庭的兴旺和睦也有很大的影响,正如《诗》曰:“必择所堪”、“必谨所堪”者(《墨子·所染》),此之谓也。
墨子上述所证人性善恶之变,与环境影响关系甚大,这个环境在墨子所举的例证中,几乎都是指人的环境。从舜、禹、汤、武到桀、纣、厉、幽,以至后举士之交友两端,无不说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影响的客观存在。这种存在既可以向好的方向发展,也可以引导人们为恶,对于人与人相交之间善恶的把握和欲求,墨子在其兼爱的伦理旨趣中已经明言,即“兼相爱,交相利”,“夫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墨子认为,人与人的交往应该向爱人、利人的方向发展,应当发掘人性之善,扬善去恶,这是天下的治道。正是基于这样的一种人性可为的理念,墨子认为人性的变化主要受后天的教育环境影响,教育的好坏决定人性的变化,人性的善恶由环境和教育塑造而成。因此,墨子关注教育,重视教育之于人之修善的积极意义,他强调修身取义,并在教育的过程中实现“兼相爱,交相利”之义。这样理解墨子的人性可为,则教育确实应当、也可以成为人与人交往的正当性与人性至善的一种伦理选择。
四、墨子教育伦理建构的当代解绎
墨子教育伦理的立基在于人性可为与社会生活的至善追求,关注人与人相处的和谐之道,确有生活意义。对于教育应该如何的探讨无论如何不能脱离当下的实际。目前教育乱象的整治不在于某种短期功利目标或任务的达成,单纯地以某些数据来确证当下教育的合理性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教育是否合宜既在于人性的解放,更在于生活的和谐。以此审视教育的正当性,我们不难发现,教育的价值偏移是客观存在的,施教者经济价值追求或社会身份地位的确证,有时甚嚣尘上,背离了人的培养的本质内涵,甚至扼杀人的精神与生命。如何实现教育的人性之爱,不妨借鉴墨子教育的伦理之思,回到人的培养的本真意义,淡化功利,以“兼相爱”的和谐理念,化解教育资源分配的矛盾,把教育办成一项利于人之善生、宜生的民生工程,使教育具有某种矫正正义的色彩,因为“矫正正义在自由权利维护与展开、社会长治久安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6]因而,当下教育的自我矫正与社会矫正意义重大,唯有实施改革,匡扶教育正义,使教育成为人之生活优良的一部分,这样教育的理性价值才能得以彰显,从而克服“把人的价值理解为人的效用价值”[7]的认识迷障,使教育真正回归于人们应有的真实生活。
[1]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96-97.
[2]袁建辉等.墨子道德教育思想述评[J].赣南师院学报,2003,(4).
[3]秦彦士.墨子考论[M].成都:巴蜀书社,2002,252.
[4]杨俊光.墨子新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98.
[5]杨文.墨子的思维语言艺术[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6]高兆明.支付能力的正义向度[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7]王玉樑.人道价值论反思的意义与局限[J].天府新论,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