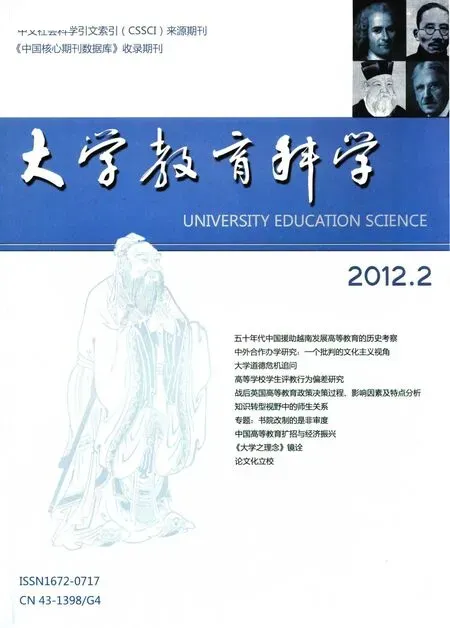知识转型视野中的师生关系
知识转型视野中的师生关系
□ 陈科平 冉 晋
从客观主义到建构主义思想转型中,知识正在发生质变。客观主义的知识传统,使师生关系沦为一种技术、秩序与服从的关系;然而,师生关系在建构主义的知识视野中,却是一种共生、对话与理解的关系。
客观主义;建构主义;师生关系;共生
一、知识转型:从客观主义到建构主义
20世纪60年代以来,建构主义作为西方世界兴起的一股文化思潮,对客观主义的合理性提出了深刻的质疑,并对人类的科学知识形态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由客观主义所坚守的科学知识的恒定、绝对、静止、普遍、客观的性质,正在向经验建构主义所强调的“知识的变动、相对、不可预测、特殊、主观”等性质转变[1],这就是笔者所强调的知识转型。在知识论上,知识观已从客观主义的“客观知识、书本知识、学科知识”,转变为建构主义的“建构知识、个人知识和实践知识”。正如利奥塔所说的,当前的知识与科学所追求的已不再是共识,精确地说是追求“不稳定性”。而所谓的不稳定性,正是悖误或矛盾论的实际应用和施行的结果[2]。这就意味着,建构主义对所有“自然法则”和各种先验主张的拒绝,对科学的绝对性和普遍性进行质疑和批判。
从追求普遍到尊重特殊。客观主义的知识观认为,科学知识是由事物的本质决定的,是人类对事物本身属性及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的认识成果。科学知识超越各种社会和个体条件限制,是可被普遍证实和接纳的认识对象,因而具有普遍性。与此相反,建构主义认为,科学知识根本不是人类对认识对象的“镜式”反映,因而不具有普遍性质。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社会环境中形成经验,并对自己的经验作出判断和取舍,从而使知识具有了个体性质与特殊性质。
从崇尚绝对到认同相对。客观主义认为,科学知识来源于事实基础之上,并通过理智思维被发现。因而,知识是稳定的、绝对的、客观的、理性的建筑物。建构主义认为,对于心灵之外的世界,我们无法认识。如波普尔就认为,我们永远不能证明我们的科学理论正确,因为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它们原来是不是错的。由单个经验演绎普遍结论的过程永远没有最后的确定性,因为自然规律本身没有我们所认为的必然性[3]。所以,我们的心灵不可能获得与客观世界一一对应的联系。这一观点随着相对论、量子力学和分子生物学等现代科学理论对以牛顿经典力学为标志的“机械论”的冲击而变得越来越被部分人接受。
从崇拜知识到批判知识。客观主义认为,现代知识的增长方式主要依靠学科知识的积累,当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才会产生突破,知识才有所发展。建构主义则认为,现代知识的增长方式,既依靠某门学科知识的积累,更依靠知识的怀疑、猜测、争鸣和反驳。前者的道路是惟一的,资料的占有成为科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资料的发现成为知识发展的动力,最后的结果是趋向一致的结论;后者的道路是多样的,新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产生,新的理论就在什么地方出现,知识发展的方向是无限多样的。
从发现一元到建构多元。客观主义之所以孜孜不倦地寻找基础、设定基础,是因为他们热衷于统一的价值,希望构筑一个完整严密的知识体系。建构主义却将客观主义的同一性思维视为扼杀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过时之物而加以抛弃,他们追求多元、边缘、差异,热衷于寻求差异性和多样性,强调对事物的多元化的理解。他们看来,知识不是客观的,它不可能以实体的形式存在于个体之外。尽管语言赋予了知识一定的外在形式,并且获得了较为普遍的认同,但这并不意味着学习者对这种知识有同样的理解。真正的理解只能是由学习者自身基于自己的经验背景和认知取向而建构起来的。
从遵守恒定到坚信流动。客观主义认为,由于知识是价值中立或价值无涉,所以,知识不是主观的东西,而是完全确定的、永恒的、客观的东西。经验建构主义却认为,知识被放在历史的长河中考察,它是“流动的”,而不是静止的;它是在人们过去经验的影响下被创造出来和被理解的,是个体在与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具有不确定性特征。所以,知识的价值不在于给人现成在的东西,而在于给人提供不断创造的材料和起点。知识不是一潭寂静的死水,而是滚滚向前的河流,创造赋予它的生命与价值。
二、技术、秩序与服从:客观主义知识观中的师生关系传统
在客观主义的知识传统中,由于崇尚同一、绝对、稳定、中心和权威的知识价值,教师往往是以知识化身、教学主体和道德权威的形象出现。这就使教师在学校生活中拥有有了崇高地位,从而导致了师生之间的种种不平等关系,具体表现如下:
技术特性关系。客观主义坚信,教育面对的是一个纯粹的事实世界,知识的增长方式是在已有知识基础上,以一种线性、客观、累积、渐进、不断叠加的方式增长的。由此,客观知识、书本知识、学科知识就成为知识的合法性源泉。教学可以根据知识的本质进行技术限定,将知识的目标和内容演绎成一套统一的标准体系,将教育过程演变成一套可操作的、程序的、规范的机械过程[4]。这就使师生关系具有了强烈的技术程序色彩。教师在这一关系中无疑充当了知识组织的技术角色,他们“宁愿采用科学的方法——或是演绎的、或是归纳的——作为他们从事哲学思维和写作的范式。井井有条、严密精确、内涵确定,便是他们必定遵循的思维模式”[5]。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教学演变为一个机械化的程序,而且连同学生的成绩、思想、品德与人格也在工具、测量、统计与计算中进行考核,教育这一具有强烈人文艺术性质的活动被活生生地科学化。“那些终极的、最高贵的价值,已从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它缺乏对人的内心世界、精神生活与人生意义的追求,教育变得古板和机械,忽视了人的主体存在性。因而,这种技术程序型师生关系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我们对待真理过于相信会降低我们灵魂的重量,但我们对待自我过于狂妄与自大同样会使我们的灵魂变得轻浮,而没有价值。[1]”其结果是,人被技术所规范、所限定,人只能技术地被展现。在这里技术不再是人的使用的手段,相反人变成了技术的人力物质[6]。这正是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异化现象,即教育的目标没有达到人与社会的目的,而是异化成人与社会的对立面。人既没有成为社会需要的人,也无法实现自己的人生幸福。
秩序特征关系。在客观主义的知识传统中,单向的知识传授关系决定了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被动地存在于教师设计的教学逻辑之中,成为一个教学组织的“边缘人”角色。在此秩序,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将主流社会认可的知识、规范、技能等传递给学生;而学生的任务便是能够准确无误地记忆、接受、背诵教师所教授的内容。教师和学生分别充当知识传递者和接受器的角色,两者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由教师到学生的单向的、规约与秩序的关系。这种规约秩序的师生关系,与人类教育的传统形成某种共振。千百年来,无论是古代的“作为神启的教师”、“作为官吏的教师”,还是近代“作为专业化的教师”,他们一直扮演着知识的化身,充当社会主流意识代言人的角色,是肩负着特殊的社会职责的人。在我国,由于长期受封建社会“师道尊严”以及传统教育模式的影响,在教学中一直以教师为中心,学生在教学中被对象化、物质化和同质化,并最终沦落为一个学习的被动者,同时也是一个学习的被压迫者。这种秩序过分夸大了教师的知识权威与教育主体地位,忽视了学生的个性、情感与非理性因素扼杀了学生独特个性的发挥。这种规约秩序关系的本质,是一种社会秩序在师生关系中的反映。现代师生关系不仅没有根除根深蒂固的传统社会秩序观念,而且,现代文明中的功利主义、客观主义与权利关系网络,尤如一条新的枷锁,牢牢地套在人性的脖子上。结果,“支配”与“服从”成为师生关系的主体模式:“教师按经济的‘利’塑造学生,学生成为某个商品;教师按政治的‘力’规训学生,学生成为某个利益的代言人;教师按文化的‘理’启蒙学生,学生成为社会的批判者。[7]”在这样的教育之下,学生什么都是,唯独不是其自身。
服从关系。客观主义以客观知识、书本知识、系统知识、学科知识为重,强调学科基础、及相应的经典理论、概念体系和规范法则,注重知识的难度、深度、结论、练习与稳定性。就知识传承的角度而言,它容易形成绝对理念与统一规范的教育行动,从而可以带来知识传承的效率、方便与大面积的成功。然而,过分迷信知识的客观性、规范性与绝对性,忽视个人创生知识的能力以及个人知识的意义势必导致教师的知识权威地位,从而决定了学生对教师的绝对服从。对于学生来说,教师的知识权威在本质上是一种外在的,从而也是一种与自己对立的关系。教师把学生当成知识的接受器,学生则把教师看成攫取客观知识的合法来源[8]。为获得知识,学生容易对教师权力迷恋、崇拜、甚至盲从。今天我们教育中广泛存在的分数为本、名次至上、题海战术等教育现象均与教师的知识地位有关。结果,出现了“高分低能”、“有才无德”的“空心人”。这种师生关系,在客观上严重地忽视了人的复杂性与非理性因素,在教学中容易排斥异己、差异和个性,导致了教育中的压迫、专制与暴力。
教师的话语霸权,使教师对于学生具有了优越的权利,也使学生潜移默化地对秩序和权威绝对服从。实际上,教师是学者和实践者,他们的任务并不是简单的传递知识,不仅仅使知识概括化和客观化,而且应该促使学生成为具有批判性、负责任的、民主社会的成员。教师要以开放的姿态看待事物,接纳新的思想,不断地对学生进行反思和批判。同时,教师也应该如其本来地对待学生,而不是把外界的价值或虚妄的预测强加于学生。正如蒙田所警告人们的那样:“既然接受了这许多外来的那么强又那么伟大的头脑,他自己的就不得不收缩和折叠起来,以让位给别人。[9]”这就意味着,对客观知识的迷信与捍卫过及,则容易使学生迷信权威,丧失自我。
三、共生、对话与理解:建构主义知识观中的师生关系建构
客观主义向建构主义的转型,对传统的师生关系提出挑战,赋予了师生关系新的意义。教师应实现从传统的知识传播者到教学的组织者、促进者和帮助者的角色转变。学生也应抛弃消极接受者这一传统角色。师生间不再是客观主义衍生的技术、秩序与服从的关系,而是一种共生、对话与理解的生命关系,具体表现如下。
共生特征关系。师生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他们之间具有阴阳共生的关系,两者之间相互转化,相互包含,彼此消长,共生互进。北宋周敦颐在其《太极图说》中提出,“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一动一静,互为其根”。建构主义与太极思维具有同曲异工之妙,它们都强调人和自然,时间和空间,自我和他者的内在联系。在这个世界,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正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同构成了人与他者之间的互补关系,构成了自我和他者交往的基础。同时,自我和他者从更高的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是一个整体,离开了他者,自我实际上是无法生存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师生关系中,学生可以转化为教师,教师也可以转化为学生,这正是建构主义提供我们的一个新的视野。在这一关系中,学生跨越知识发现与知识传承的边界,被赋予了知识发现与创造的机会。他们在建构知识的同时,也塑造了个人知识创造者身份,重构了成为社会主人的机会。他们不仅摆脱了一个被动的“知识边缘人”身份,而且被看做一个知识的批判者、怀疑者和重构者而使自己具有了独立的精神与知识主人的合法地位。因此,学生的角色是一个积极的学习者和知识的探索者,对他们来说,任何的“知识”、“真理”、“权威”都要接受怀疑、接受批判。知识不再具有客观真理的意义,它们必须通过学生的理解与意愿而进入学生个体的经验,从而使学习获得了存在与生命的意义。
对话关系。在经验建构主义这里,知识是动态的、开放的,被视为不断生成与建构的文本,而不是封闭的、稳定的、从外部即可加以研究的意义系统。知识既然是非客观的、不确定的,那么知识的形成和获得就需要教师和学生双方的主动参与。所以,建构主义反对单向的知识传授,主张师生两个认识主体之间的平等对话与咨询研讨。学生是师生双方作为自由、自主的人投入到教学中,各自独立而又相互对话的过程,是双方互相包容与尊重,以达到一种“双赢”的新境界。对话是一种对他者及其经验的一种尊重、接纳和开放的态度,也是师生之间的经验、视界、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的共享和融合。师生双方既带着对历史、自然与他者无边法力的虔敬之心,又带着对于自己的弱点与局限的更深切的自惭形秽之情去理解自己、他人、知识与世界。教师不是以往那种高高在上、居高临下的领导者,而仅仅是作为学习者团体的一个平等的成员。学生并非在知识之外的旁观者,而是处于知识的生产系统之中,并通过其交往实践活动把握它。师生的共同任务在于使双方形成良好的习惯与学养,掌握相应的学习策略,尊重差异,主动质疑,激发自己的学习动机等。在这种对话中,师生是共同在场、互相关照、互相包容、共同成长。它不仅仅是师生交往的一种方式,也是一种弥漫、充盈于师生之间的教育情境和精神氛围,更是个体形成人格与素养的生命与生活过程。一方面,这种对话关系具有民主性。在这种对话关系之中,师生之间平等待人,相互尊重,相互信任,通过双向交流和沟通活动,使双方理解知识与技能、价值与情感、方法与过程。另一方面,这种对话关系具有包容性。即处于交往对话的师生需要相互敞开自己的灵魂,需要双方的默契与合作,共同推动对话向前发展。并且,师生要以整个身心投入到教学交往活动中,从而达到主体间真正的理解与互融。
理解关系。客观主义随着奠基于经典物理学的绝对主义世界观的被颠覆,知识的绝对客观地位已被动摇,知识只不过是认识主体与其他主体、客体交往实践活动过程中的产物。为了实现与客观世界关系的平衡,建构主义实现了从主体性向主体间性的转变,使师生关系成为一种理解与包容的关系。它认为知识不应该只关心真理问题,还应该关心正义、幸福和美的问题。这样的知识观消解了科学知识的权威性,认为科学的知识和艺术的知识之间是平等的关系。建构主义认为,任何一个存在的主体都不是封闭的,而是一种心灵相互敞开的过程,交往的双方既说又听,彼此间自发地进入对方的视域,变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不断转化的关系。既然科学知识的发展不是简单的线性累积过程,而是伴随着偶然、机遇、环境和突变的过程,那么,理解与包容就是知识分子应该具备的学术人格。师生间的理解使教师的教学智慧将会得到极大的发挥,教学的火花将可能随时迸发,教师将乐于与学生一起共同探索,实现新知识的理解,形成民主的意识,从而使教学焕发自由与人性的光辉。理解与包容的目的不是为了寻求一致或共识。教师不再是知识的绝对权威,只是在某一方面具有优势。学生在很多方面,比教师有着更惊人的学习潜力。理解意味着生命个体与环境的互融,它在教育世界中是双向的,它交融于师生的感情、认知与行为“作为理解主体的师生与理解对象沟通,感情、认知与行为上筹划并实现生命可能性的过程”[10]。这种双向性理解其实就是师生互惠式的感情交流,认知合作、行动关联与共进发展。师生在合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合作,已成为学校教育中不可轻视的内容[11]。
[1]刘传红,唐松林.知识质变中的学术人格冲突及调和[J].高等教育研究,2011(7):19-23.
[2][法]利奥塔.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M].岛子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1996:73.
[3][美]拉德克里夫.休谟[M].胡自信译.北京:中华书局,2003:42.
[4]唐松林,张辰宸.两种外在的教育评价主体的价值取向:差异、辩证与对话[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 学版),2011(3):86-89.
[5][美]理查德·鲁玛纳.罗蒂[M].刘清平译.北京:中华书局,2003:3
[6][德]马克思·韦伯.学术与政治[M].冯克利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8:48.
[7]熊华军.师生关系的三重境界[J].大学教育科学,2010(6):62-65
[8]樊杰.教育的强制与生命意义的丧失[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J],2011(1):8-9.
[9][法]蒙田.有血有肉的语言[M].梁宗岱,黄建华译.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108.
[10]熊川武.理解教育论[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5:78.
[11]吕耀中.后现代主义教育视野下的师生观[J].青岛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4):94-97.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Knowledge Transformation
CHEN Ke-ping RAN Jin
During the process of 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from objectivism to constructivism,the knowledge is making a qualitative change. The intellectual tradition of objectivism makes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become a kind of technique, order and obedience; however, in the knowledge perspective of constructivism, the rela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turns to be one of symbiosis, dialogue and understanding.
objectivism; constructivism; 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symbiosis
G645
A
1672-0717(2012)02-0051-05
2012-2-1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委托课题“面向新型工业化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体系改革理论研究”;中央高校科研业务费人文社会科学定向组织重点项目“卓越工程师计划实施研究”(2010ZDB20)。
陈科平(1968-),男,湖南湘乡人,工学博士,中南大学讲师,主要从事地质工程研究;
(责任编辑 陈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