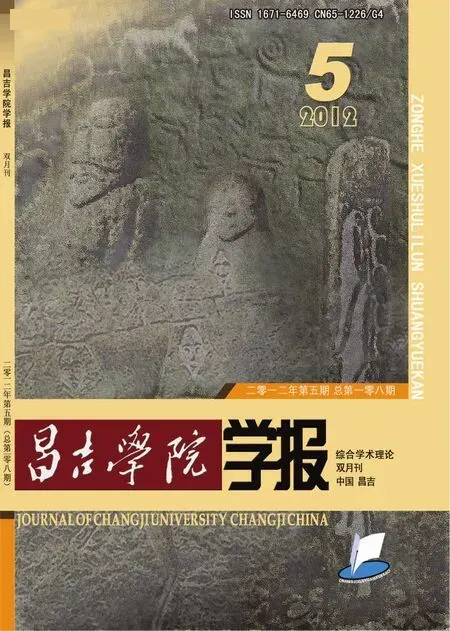新疆扬琴的源流探考
方 媛
(昌吉学院音乐系 新疆 昌吉 831100)
“扬琴属击奏弦鸣乐器。”[1]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流传,有数千年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亦有不同的称谓。比如,在阿拉伯地区称为“santur”;在欧洲的英语国家称为“dulcimer”或“psaltery”;在匈牙利称为“cimbalom”;在波斯(现今的伊朗)被称为“santir”;在印度被称为“san⁃toor”;在瑞士被称为“hackbrett”;在朝鲜被称为“yanggum”;在我国称为“扬琴”,而在我国新疆以及中亚地区和俄罗斯都被称为“chang”。[2]关于这些扬琴的源流有许多种说法,并且至今仍没有定论。
目前在新疆被广泛使用的扬琴有两种,一种是几百年来被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等少数民族所使用的民族扬琴——锵(chang);另一种是在中国汉民族的传统扬琴基础上改革、发展而来的转调扬琴。这两种扬琴在称谓、形制结构上都有不同,尤其是音位排列和律制迥然相异。显然,这两种扬琴的源流不同,也不是同时传入中国的。1988年中央音乐学院首届硕士扬琴研究生黄河在其所著的《从扬琴音乐创作看扬琴艺术的发展》一文中,将新疆扬琴列入全国五种主要地方风格之一进行专题研究。[3]自此,新疆扬琴作为中国扬琴体系的一个地方风格流派被确立下来。十几年来经过各族扬琴演奏家、教育家、工作者的努力,新疆扬琴艺术在形制结构、技法技巧、作品创作、专业教育方面都有很大发展。因此,作为一名扬琴工作者不仅要掌握新疆扬琴的技法技巧和风格,进行作品创作,还必须进一步对新疆扬琴的产生、成长的历史进行一番追本求源。其目的不仅是为了开阔我们的知识视野,还使我们能够站在历史的高度认识新疆扬琴的独特性,更好地改进它、丰富它。
一、中国扬琴的源流探究
要搞清新疆民族扬琴的源流和历史,首先还应了解中国扬琴的源流,扬琴并非中国所产而是由海外传入,这从明、清时期的中国人一直把它称为“洋琴”就可以证明。在清代徐珂的笔记体类书《清稗类钞》第十册《音乐类》的几个条目中都有这样的记载:如《金赤泉听洋琴》诗文中“乾隆时,钱塘有金赤泉典簿焜有好音樂,常听洋琴而作歌以紀之,歌曰:云和之琴空桑瑟,至人掳思中音律。庖牺不作古乐亡,杂沓筝琶始竞出。此琴来自大海洋,制度一变殊凡常。取材讵用斫桐梓,发声亦自循宫商。圆形宛然如便面,中絙铁弦百炼。钿灯节比排两头,二十六条相贯穿。携来可击不可弹,双椎巧刻青琅玕。”再如条目《洋琴》中“康熙时,有自海外输入之乐器,曰洋琴,半于琴而略阔,锐其上而宽其下,两端有铜钉,以铜丝为弦,张于上,用槌击之,槌形如筯。其音似箏、筑,其形似扇,我国亦能自造之矣。”
虽然从以上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知道扬琴自海外输入,但究竟从哪个国家、哪个地区输入并没有明确的记载。目前根据史料和文献的记载,以及对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扬琴的研究大致有欧洲传入说[4]、波斯——阿拉伯传入说[5]、新疆传入说等几种起源说。这几种关于中国扬琴“始传地”的说法可以说是“众说纷纭”,每种说法都引经据典、颇有道理,但又缺乏足够的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而通过对史料、文献的仔细分析和研究,并结合对扬琴传入中国的路线,在中国流传的特点以及中国扬琴的形制结构特点的分析,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扬琴由欧洲从海路传入是比较可信的。原因有三点:
第一,《清稗类钞》、《冲绳与中国艺能》、《中外戏法大观图说》等大部分文献都记载了扬琴是从海路出入中国的[6];第二,从扬琴最初在中国内地出现的地点是广东沿海和闽浙一带,这些地区在明代都是中国的重要港口,是中国与欧洲、西亚进行贸易往来的必经之地。而此时新航路的开辟使欧洲对中国有了更多认识,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大批的商人和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了欧洲的商品和文化,同时也带来了欧洲的乐器。如果扬琴是由波斯——阿拉伯的“桑图尔”(santur)通过新疆由丝绸之路传入中国内地的,为什么所有文献都没有提及过,并且不是首先出现在中国的西北或中部地区而是距离新疆非常遥远的东部沿海地区?第三,从中国扬琴最早的史籍记载《冲绳与中国艺能》一书中可以知道起码在17世纪扬琴已传入我国沿海地区。而从史料中所载的这一带扬琴的形制来看,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小扬琴Dulcimer很相似。如:桥马,左马置于琴面五分之二处,使两侧构成五度音程关系。而西亚的扬琴是单个琴马,左马两侧为八度音程关系(设在三分之一处)。所以说,中国内地所使用的传统扬琴来源于欧洲而不是西亚,也不是波斯——阿拉伯的桑图尔经新疆传入内地的。现今在中国广泛使用的转调扬琴“402型”、“401型”以及“501型”是改革开放后,为了适应现代音乐的演奏和教学,由扬琴演奏家、律学家、乐器制作家根据我国的传统扬琴和欧洲的十二平均律大扬琴进行改良得到的,不仅在内地专业音乐院校和演出团体得到了普遍推广和使用,20世纪80、90年代进入新疆后也得到了维吾尔民间音乐艺人们的认同。
二、新疆民族扬琴——锵的源流探究
扬琴在新疆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称为“锵(chang)”,传入我国新疆地区以后,由于适合表现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音乐明朗活泼、热情奔放的风格,而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流传下来,并且成为了木卡姆音乐的主要伴奏乐器之一。关于锵的源流问题,大部分观点都认为是由西亚地区的一种古击弦乐器“桑图尔”(Santur)传入新疆后演变而来的。例如周菁葆先生在其文章《木卡姆探微》中载:“桑图尔,也就是扬琴,过去人们认为扬琴是明代从海上通过沿海一带传入的。其实它是阿拉伯人的乐器,早就传入天山南北了,很可能是由新疆传入内地的,这个乐器维吾尔人继承了下来。”[7]
在万桐书先生的《维吾尔族乐器》一书中记述:“锵最早流行于波斯、伊拉克、土耳其等国,后遍布亚洲、东欧各国。公元十七世纪中从海路传入中国广东沿海,叫做洋琴、蝴蝶琴和扇面琴,后广泛流传,约十八世纪传到东疆哈密。与此同时从另一条路由中亚传到新疆喀什。”[8]在中亚地区,包括苏联几个加盟共和国土库曼、乌兹别克、塔吉克以及俄罗斯都把扬琴称作“锵”。徐平心在其的论文中论述:“至今中亚的锵的形制与波斯的桑图尔仍很接近。所以说锵很可能直接来源于西亚,而不可能是沿海一带的扬琴传去的。”[9]“chang”是两千多年前波斯竖琴的称呼,在古代波斯萨珊王朝的雕刻遗迹上可以看到这种竖琴,而扬琴有可能与竖琴有某种亲缘关系。桑图尔(Santur),来自波斯语,意为“百弦”。据《格罗夫音乐大辞典》[10]关于“Santur”条目记载:“桑图尔的原始形状可从竖琴中见到,它是被平置,用两支槌敲击,见于古巴比伦(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911年)和新亚述(公元前911年至公元前612年)时期的图像资料中”。
由此,这些专家和学者大概可以推断“锵”可能继承了西亚古老扬琴的传统,从形如竖琴的拨弦乐器发展到击弦的桑图尔,并在于西域的交流中传入新疆,然后通过西域与我国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而传入了中国内地。近一百年来由于疆界变迁、民族迁徙、战争、经济文化交流等原因,流行于中亚的扬琴又受到欧洲大扬琴和中国内地传统扬琴的影响,如苏联中亚加盟共和国的扬琴(chang)吸收使用了东欧大扬琴的制音器踏板;新疆维吾尔族扬琴(锵)也吸收使用中国沿海一带扬琴早已由“琴槌”改用的竹制击弦工具——“琴竹”,而在乐器形制、音位排列等方面,锵和苏联中亚地区的扬琴(chang)仍保持着一些共同的特点,如采用两排琴马,纵向音位排列为小二度排列等。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锵源于中东亚速、波斯等古代阿拉伯国家流行的一种拨弦乐器,名叫索尔特里琴(Psaltery)。“Psaltery”来自希腊文,意为“拨弹”,既指拨弹的箱形乐器。在《外国音乐辞典》中关于索尔特里琴的描述是“齐特尔琴类拨弦乐器,其形如扬琴,但扬琴为击弦乐器,是对称的梯形,而索尔特里琴则呈翼状。”[11]根据以上的描述可以看出索尔特里琴与桑图尔或扬琴并非同一种乐器,而是拨弦古钢琴的前身,或可能是在我国新疆流传的另外一种乐器“卡龙”的同类乐器。有很多文献和论著经常把扬琴和卡龙这两种在外观上十分接近的乐器混为一谈。如《清稗类钞》中关于卡龙的记述:“喀尔奈,回乐也。状类洋琴,木胎中空,左端直,右端曲。左端上面施木梁,以击铜,弦之末施轴,入于右端立面孔內,转其轴以定弦之缓急,以手冒拨指,弹之取声”,喀尔奈即卡龙。在岸边成雄所著的《伊斯兰音乐》中也把卡龙和桑图尔说成是一种乐器。[12]据《格罗夫音乐大辞典》的说法,桑图尔与皮萨泰里(索尔特里琴)同源,这说明卡龙和扬琴很可能是由古老的箱形竖琴或其他同一种乐器演变而成的形状相似而演奏方法不同的两种乐器。虽然卡龙和锵都属于板型齐特类乐器①,但卡龙使用右手持木拨拨奏琴弦,左手持一滑弦器在琴弦上滑奏的乐器,且形状为不等腰梯形,因此它们绝不是同一件乐器。最早记载卡龙的文献出现在元代,清代有很多官方和民间的文献都对卡龙的形制和演奏做了详细的描述,并附有图片。在西亚和中亚出土的古老细密画中也描绘了与卡龙极为相似的乐器。根据新疆南部的维吾尔木卡姆老艺人们回忆说:“卡龙是锵的爸爸。”意思是说在新疆南部地区卡龙比锵出现的早。但在新疆解放以后,由于音量小、音域窄、演奏方法复杂等原因卡龙被锵逐渐取代,现今只在新疆刀郎木卡姆音乐的演奏中使用,笔者在调查过程中采访的木卡姆老艺人(70岁以上)都证实了这一点,但他们对于锵是什么时候在他们生活的地区出现的却又说不清楚。因此,可以肯定卡龙在清代以前就在新疆南部地区广为流传,并在维吾尔民间音乐的表演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是维吾尔最为古老的乐器之一,而锵在新疆流传的时间尚不能确定。
三、结语
通过以上的论述,在新疆所使用的扬琴中内地传入的由传统扬琴改良的转调扬琴的源流我们似乎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但新疆民族扬琴——锵的源流问题仍然留下了很多疑问,还没有一种传入说能够真正站得住脚。据传扬琴在新疆已经流传了几百年的时间了,乐声在《中华乐器大典》中提到:“新疆的锵,则是由西亚——中亚一代经‘丝绸之路’直接传入新疆喀什的,其时应早于明末,18世纪末又传到东疆哈密”。[13]可是,对于锵描述和记载大多是在解放以后的文献中出现的,且在写于1854年的,研究维吾尔音乐最重要的文献《乐师史》中没有关于“锵”或类似乐器的记载,清代和清代以前有关于西域的文献也均没有提及“锵”这件乐器。如果锵在明代就传入了新疆地区,那么在有关于西亚音乐东渐的历史文献中,为什么有关于琵琶、箜篌、胡琴等乐器的文献记载,却没有关于锵或西亚桑图尔的任何记载呢?虽然锵与西亚的桑图尔属于同一类乐器,但不能确定它是由桑图尔演变而来的,这两种乐器的历史演变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根据以上对于“锵是几百年前从西亚传入并由桑图尔演变而来”说法提出的疑问,我们可以知道锵传入新疆地区的时间并不像一些文章中说的那么久远,至少根据文献记载和田野调查确定锵出现在新疆地区的时间,只能追溯到新疆解放以前至清末的一段时间,更早的历史因为没有记载而无法考证。所以笔者只能推测:很有可能是清末时期维吾尔民间艺人们结合了本地音乐的乐律和演奏特点,将从内地传入新疆地区的中国传统扬琴进行改良得到的新疆民族扬琴——锵;或者锵是18至19世纪直接从毗邻的中亚地区传入,后又受到中国扬琴的影响将击弦工具由琴槌改用琴竹,但由于维吾尔音乐文化不属于中国传统音乐体系,因此不仅在名称上仍与中亚保持一致,称为“锵”(chang),而且在形制上仍保留了与中亚地区相同的音位纵向小二度的排列。当然,由于没有确凿的文献记载和考古证明,这个观点现在只能是猜测,一时还难以对这样复杂的历史源流问题下结论,有待于对中亚、西亚地区的锵、卡龙、卡侬②、桑图尔等这几件奇特类乐器进行系统、综合的研究,将这些具有历史性和世界性的古老乐器的历史发展脉络进行较为清晰的梳理,从而进一步对中亚、西亚、欧洲以及中国内地在新疆进行的音乐文化交流的历史做更加深入地研究。
注释:
①根据萨克斯—霍恩博斯特尔乐器分类法,扬琴和卡龙属于弦鸣乐器中的板型齐特类乐器。
②卡侬与卡龙属于同一种拨弦板型齐特类乐器,西亚、北非和中亚的伊斯兰国家称之为“卡侬”,形制和演奏方法与维吾尔卡龙稍有区别。
[1]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编辑部.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Z].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2]鲁斯·米德格雷等著.关肇译.世界乐器[M].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
[3]吴军,黄莉.新疆扬琴的民族特色[J].中国民乐特刊,2000.
[4]赵艳芳.论中国扬琴的文化内涵——世界性和中国品格[J].中国民乐特刊.2000.
[5]中国音乐研究所.中国音乐史参考图片第二辑[Z].新音乐出版社,1954.
[6]项祖华.中国扬琴历史源流[J].中国民乐特刊,2000.
[7]周菁葆.丝绸之路的音乐文化[M].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415.
[8]万桐书.维吾尔族乐器[M].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57.
[9]徐平心.中外扬琴的发展和比较[J].中国民乐特刊,2000.
[10]Dick,Alastair.Surmandal,“The New Grove Dicionary of Musical Instrument”1984.
[11]上海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编译.外国音乐辞典[M].上海音乐出版社,1988.
[12][日]岸边成雄.伊斯兰乐器[M].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47.
[13]乐声.中华乐器大典[M].民族出版社,2002: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