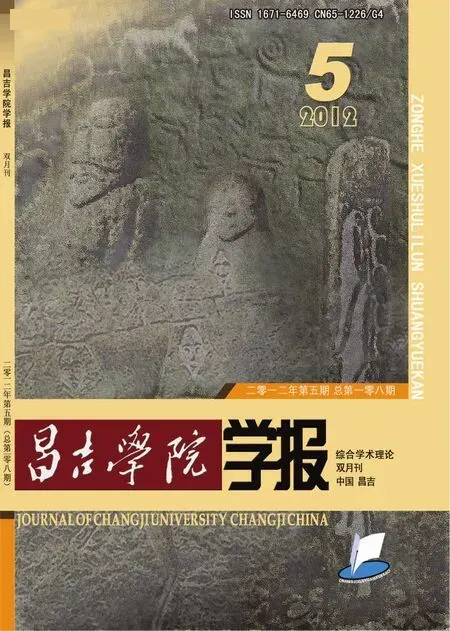文艺发展论中的“顶峰”说述论
刘求长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文艺发展论和文学艺术史论中有一种思想观点,它或者确认某一个民族的某一个历史时期的文学艺术达到了最为完美的程度,后世无可企及;或者确认某一个民族的某一种艺术形式在某一个时代达到了最高峰,后人望尘莫及;或者确认某些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成就可称顶峰,如黑格尔就说:“拉斐尔达到了艺术完美顶峰。”[1]等等。这就是“顶峰”说。顶峰说中的“顶峰”一词含有多重意义:一是表明它是一座高峰,它的巨大成就与美学价值永载文学艺术史册,后人对之“高山仰止”;二是表明它一经产生,在后世的文学艺术史上便不可能再次以同样的形态同样的高度出现,后世不可能超越它;三,用“顶峰”这个描述词并不是说人类文学艺术史上只能有那么唯一的孤零零的一座不可超越的高峰。相反,它认为各个民族各个历史时代都有可能出现具有自己独特面目的文学艺术顶峰。
一、中外文论中的文艺发展顶峰说
顶峰说这种文艺思想理论,广见于西方理论家的论著之中,也见之中国文论家或作家的文论篇章,同时还见之于马克思的著作。
认为某个民族的某个历史时期的文学艺术达到了人类文学艺术发展的“顶峰”,即达到了最为完美的高度,这在德国美学家的理论论述中很常见。歌德说:“如果我们需要一个样本的话,我们应该回到古代希腊人那里,他们的作品总是描绘出人类的美。”[2]与歌德的这一论断相比,黑格尔给古希腊艺术所做的“顶峰”定位就更为清楚和坚定不移。黑格尔认为艺术发展中出现了三种类型的艺术,即象征型艺术,古典型艺术,浪漫型艺术,而最能体现他确认的理想的美的艺术是以古希腊艺术为典范的“古典型艺术”:“象征型艺术在摸索内在意义与外在形象的完满统一,古典型艺术在把具有实体内容的个性表现为感性观照的对象之中,找到了这种统一,而浪漫型艺术在突出精神性之中又越出了这种统一”[3]。古典型艺术“使艺术达到完美的顶峰。”[4]他说明:“用‘古典型的’这个词当然也采用艺术完美这个意义”[5]。“古典型艺术是理想的符合本质的表现,是美的国度达到金瓯无缺的情况。没有什么比它更美,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6]他说:“在希腊诗里,纯粹的有关人性的东西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艺术形式上,都达到最完美的展现。”[7]他还一一评析古希腊艺术在哪些领域达到了完美的境界。他肯定古希腊的悲剧和喜剧“都达到完美的高峰。”[8]他认为古希腊的史诗是“正式史诗”的范例,他一再称赞荷马史诗:“个别事件与其它材料交织得最好的典范是《奥德赛》”[9]。“我们已对史诗的实体性的基础提出了两点要求……在这方面还是《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提供了范例。”[10]“雕刻是古典型艺术的中心”[11],而“代表着古典理想的真正伟大和崇高”的正是“希腊雕刻”[12]。“它们在自由生动方面达到了最高峰”[13]。总之,在论说古希腊艺术时黑格尔是毫不犹豫地毫无保留地使用了表示最高级的词语的。我们不难发现,马克思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与由温克尔曼开始,歌德、席勒、黑格尔继之的极力推崇古希腊艺术的思想传统保持一致的,在写作于他思想成熟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困难不在于理解希腊艺术和史诗同一定社会发展形式结合在一起。困难的是,它们何以仍然能够给我们以艺术享受,而且就某方面说还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14]将古希腊艺术和史诗说成是“一种规范”和“高不可及的范本”,这样的用词用语我们是似曾相识的,它们在我们上文引述的歌德与黑格尔等人的论述中可以找到相类的同义词,与歌德、黑格尔等不同的仅仅在于马克思加了个限定性语句“就某方面说”。
“顶峰”说更是被广泛运用于描述人类某些具体的艺术形式的发展进程,亦即指明,某种艺术形式在某个历史阶段达到了顶点,后代再也拿不出更佳的成果可以与之比肩。神话和史诗就是两个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最适合于神话产生与繁荣的时代是西方文化传统中所说的“神的时代”,最适合于史诗产生与繁荣的时代则是“英雄时代”。随着人类社会进入“人的时代”神话和史诗都失去了自己生长与繁茂的土壤,因此在西方文学艺术史乃至整个人类文学艺术史上,以古希腊神话和史诗为代表的古代神话和史诗便是这两种艺术形式发展的顶峰,尽管后代人也还写“神话”,但那些都只是“模拟神话”而已,绝对不可能是本色的真正的神话;尽管后代人也还写“史诗”,但如果后人觉得自已写的“史诗”超过了古代人的史诗水平,那就只能沦为笑柄。马克思就曾借用莱辛的话来嘲笑伏尔泰的思想和作为:“既然我们在力学等等方面已远远超过了古代人,为什么我们不能也创造出自己的史诗来呢?于是出现了《亨利亚特》来代替《伊利亚特》”[15]。又如悲剧,前面我们引述了黑格尔,他认为古希腊悲剧达到了“完美的高峰”。歌德认定古希腊的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他们的创作是悲剧的顶峰:“在著名的三大悲剧家之后,没有出现过同样伟大的第四个、第五个、乃至第六个悲剧家”[16]。“继三大悲剧家之后,任何诗人都看不到出路了。”[17]朱光潜也认为古希腊悲剧让后人望尘莫及:“莎士比亚和歌德作品中还有多少仍然可以与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作品媲美呢?”[18]
中国文论中,苏轼是观点鲜明的顶峰论者,他说:“诗至杜子美,文至韩退之,书至颜鲁公,画至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书吴道子画后》)鲁迅则专就中国的绘画艺术发展发表了顶峰说:“我以为宋末以后,除了山水,实在没有什么绘画,山水画的发达也到了绝顶,后人无以胜之,即使用了别的手法和工具,虽然可以见得新颖,却难以更加伟大。”[19]王国维的顶峰说影响更大:“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辞,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史·自序》)。“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就是说后世无法超越已有的那些成果,它们已是顶峰。王国维此说在中国文学发展史论中几乎已经成了定论,它相当合乎实际地肯定了中国古代文学中一些重要的文学形式其发展历程中的顶峰之所在。
二、顶峰说是描述文艺发展一种特殊规律之论
包括文艺理论、文艺发展史、文艺批评在内的文艺学以及文艺美学都不是精密科学,因此上文引述的中外文艺理论家的文艺发展顶峰说,将什么时代、什么人物等等定为人类全部艺术或某个国家、某个民族的某种类型艺术的顶峰,这种论断不可能像精密的自然科学结论那样被人们普遍认可。这是很正常的。我们重视的是,这些中外文论家都肯定了文学艺术发展中“顶峰”现象的存在。我们认为,顶峰说是如实表述文艺发展中一种特殊规律的理论。
(一)文艺发展中不存在犹如自然科学发展中存在的那种后胜于前,今胜于古,不断上升与进步的规律
德国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说:“人类文化分为各种不同的活动,它们沿着不同的路线进展,追求着不同的目的。”[20]沿着不断上升与进步的发展路线前进的文化形态主要是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在这个文化领域里,随着人类实践经验与科学知识的不断积累,随着科学实验条件的不断改善改进,随着全社会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随着人们科学思维方式的改进与思维视野的扩展,随着全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需求与依赖程度的不断提升,科学技术的发展总是处在不断提高的趋势之中。在当今时代,尤其是在技术科学领域,其发展方式简直是突飞猛进,永不停顿地胜过前人,超越前人。在科学技术这个文化领域里,从来不存在,永远也不会存在后世不可逾越的“顶峰”。即使科学技术上那些已成定论的辉煌成果,随着科学家科学观念科学视野的改进与扩展,随着实验与生产条件的改进与完善,后人仍然可以对它们进一步精密化、优化。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存在最后的终极的真理,这一点首先就表现在自然科学与技术科学领域里。人类头脑中的“进步观念”,“这种观念的萌发是与自然科学的兴起及其对人类生话的影响有关的。”[21]但文学艺术是与科学技术十分不同的文化领域。人类创造文学艺术,一不是为了要认识与揭示客观世界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二不是为了要提高生产效率或工作效率以实现实际的功利目的。对于文学艺术创作,人们不能用揭示客观规律的精确程度与生产效率与工作效率的高低去衡量它们的优劣。早在18世纪中叶,英国美学家休谟就已经说到:艺术是虚构的产物,它无所谓真假,无所谓真理与谬误,艺术的优劣标准处于科学判断的方式之外。[22]文学艺术是以与人类生命同构的感性形式展现人类自身的本质力量,即展现人的情感、理想、价值、生命欲求等等。文学艺术又是展现人的自由创造力的方式,是人的自我实现的途径。而通过文学艺术创造以展现自由创造力的这种巨大能力,决不是只为现代人所具有的。在人类尚处于“童年”的阶段时,在科学技术发展与物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的古代社会里,人类便已创造出辉煌的神话、史诗杰作,令后世的各代“成人”自叹“高不可及”,这是艺术文化发展进程中十分正常的现象。
(二)文学艺术中的“顶峰”的出现是由特定的社会时代的文化环境与社会条件造成的
随着社会时代的变迁,原有的那种形成“顶峰”的条件便永远失去了,不可能再次复制复现,于是业已产生的文学艺术高峰便成为永远的“顶峰”,后世永远无法超越它。仍以神话来论。神话产生和繁盛于人类的童年时代,那个时代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尚未诞生,人们对自身与对自然的实质茫无所知,却又充满着对自身与自然的强烈的好奇心与要解释自身与自然的强烈愿望,童年时代的人类头脑尚处在原始思维状态,想象力极为旺盛,深信万物有灵。这样的时代文化条件,是科学逐渐产生并发达起来的后世所不能复制的,因此马克思说:“成为希腊人的幻想的基础、从而成为希腊[艺术]的基础的那种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能够同走锭精纺机、铁道、机车和电报并存吗?”[23]史诗这座艺术高峰只能耸立于“英雄时代”。马克思说:“就某些艺术形式,例如史诗来说,甚至谁都承认:当艺术生产一旦作为艺术生产出现,它们就再不能以那种在世界史上划时代的、古典的形式创造出来”[24]。因此马克思断言:“当今时代不可能写出史诗”[25]。黑格尔描述了最合乎他心目中的艺术理想的最为完美的古希腊艺术所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条件:“这个民族值得我们尊敬,因为他们创造出一种具有最高度生命力的艺术。按照他们的直接现实生活去看,希腊人生活在自觉的主体自由和伦理实体的这两领域的恰到好处的中间地带。他们一方面不像东方人那样固执一种不自由的统一,结果产生了宗教和政治的专制,使主体淹没在一种普遍实体或其中某一方面之下,因而丧失掉他的自我……另一方面希腊人也还没有走到主体沉浸于自我,使个人与整体和普遍性的东西割裂开来,以便陶醉于自己的生活……希腊人的世界观正处在一种中心,从这个中心上美开始显示出它的真正生活和建立它的明朗的王国”[26]。黑格尔以上的描述显然得到了马克思的基本认同。马克思说:“有粗野的儿童和早熟的儿童……希腊人是正常的儿童。”[27]古希腊人所处的这种社会阶段和文化心理状态,不是后世所能复制复现的,因此希腊艺术对于后人便也是如马克思所说的“高不可及”。中国古典诗歌(这里指不包括词、曲在内的古典诗歌)的顶峰是盛唐诗歌。盛唐的那种社会、时代、文化条件,后世也是不可能复制和复现的,后世不可能再出现一个“盛唐气象”,因此“盛唐气象”就成了“顶峰”,后世不可能超越。
(三)意味着辉煌成就的文学艺术高峰都是高度个性化的
特定的社会时代是一种难以重现的个性,特定的民族性也是一种难以重复的个性,具体的作家艺术家更是一种独特的个性。克罗齐说:“艺术……是个别性相,而个别性相向来不复演。”[28]不能复演就意味着不能超越。个性独特的李白就是一座顶峰,他对于后人便是高不可及。李白处在一个特定的社会时代,他有着自己特殊的生平经历,有自己特有的文化修养,他有着如杜甫诗《赠李白》所言的“飞扬跋扈”的性格,他有超凡的艺术天赋与奇特才情。刘大杰这样描述李白:“他是一个英气勃勃狂放不羁的人,作起诗来,便不屑于细微的雕琢与对偶的安排,他用着大刀阔斧变化莫测的手法与线条,去涂写他心目中的印象和情感。无论是长诗或是短诗,一到他手里,好像一点不费气力似的,一点不加思考似的,便那么巧妙那么自然地写成了。”[29]这样的一个“诗仙”,后世岂能复制和复现,谁能对他“从头越”?
三、“顶峰”说对实际的文艺发展活动的积极意义
“顶峰”说既是对文艺发展的一种特殊规律的如实描述,那么其具有的理论与学术意义自不待言。下面我们主要说一说“顶峰”说对于实际的文艺发展与文化发展活动的积极意义。
(一)顶峰说有利于破除或阻止文艺思想观念和实际的文艺活动中存在的那种蔑视人类文学艺术遗产,在文艺发展中不断掀起“断裂”运动的思想和行为
认为人类无论在哪个领域哪个方面都今胜于昔,新优于旧的“进步”观念在现代人头脑中是相当普遍地存在着的,将自然科学发展的规律与生物进化论生硬地移植到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人文文化领域中,这在理论界是很常见的,它们对文艺创作者产生很大影响。科技的现代化带动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运动,与社会现代化运动或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文学艺术现代运动也不断涌现,在这些现代的文学艺术运动中,虽然也可以见到“复古”式的运动,如现代派绘画中效法原始艺术的运动,但大半还是以与古典文学艺术决裂为主要指导思想的激进运动。法国新小说派的领袖人物阿兰·罗伯-格里耶的言论很有代表性:“19世纪的小说决不再是一个‘好工具’”,“没有任何人会为了保护这一工具的形象而把联合收割机看做是镰刀的改进”[30]。他把古典现实主义小说比之为“镰刀”,而将他们自己创作的“新小说”比之为“联合收割机”,而且断然表明后者不是对前者的“改进”,即二者决不是继承基础上的革新发展关系,而是一种本质上的“断裂”关系。这里蔑视古典文学艺术成就,抛弃古典文学艺术成果的态度十分显明。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曾出现过狂热推崇西方现代派文学艺术的思潮,那时也有一个相当流行的比喻:现实主义是蒸汽机时代的文学,现代主义则是电子和原子时代的文学。[31]这个比喻与罗伯-格里耶的比喻在思想实质上是一样的,都是在文学艺术领域简单搬用套用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结果。现代人的这种轻蔑古典文学艺术的心态,我们可以略为修改上文引述过的马克思嘲讽伏尔泰的那些话来加以描述:既然我们在力学等等方面已经远远超过了古代人,我们今天的文学艺术创作水平自然也就远远超过了古代人。既然今天我们拥有了先进的“联合收割机”,我们当然要扔掉前人的落后得可笑的“镰刀”。当今在全人类面前摆着一个紧迫的课题:及时地有效地保护好正在遭受现代化运动的粗暴破坏和遗弃的人类文化遗产。要解决这个课题,首先在思想意识上要明确认识到:前人创造的一系列文学艺术成果对后人来说永远是“顶峰”,我们对前人的创造不仅要胸怀敬重,而且要胸怀敬畏,要对它们敬重有加,备加爱护。
(二)各个时代之所以产生文学艺术顶峰,都因为那个时代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有利于文学艺术发展的社会与文化方面的条件
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随着社会整体的现代化,古代所具有的许多有利于文学艺术发展的条件已经失去了。黑格尔指出过“我们现代生活的偏重理智的文化”不利于艺术。[32]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过科学技术的发展阻遏了神话式的幻想。在现代社会里,社会管理部门确实习惯于用指导和管理理智文化的那一套方式指导和管理所有部门,包括包含文学艺术在内的人文文化部门。比如我们国家在20世纪50-70年代就完全无视艺术的特殊规律,强制任何文学艺术门类都要为现时政治服务。在市场经济时代又往往出现要求无论何种艺术都要走向市场的思想与作法。我们这个时代确实不可能再恢复古希腊和盛唐时代的社会文化条件,但是我们应当研究人类文艺史上“顶峰”出现的诸多条件与原因,努力在新的社会历史时代创造更多的有利于产生文学艺术顶峰的社会文化条件。
(三)顶峰论启发我们立足现时代,大力张扬本土文化与作家艺术家的个性,努力创立新的文学艺术顶峰
历史上的文学艺术“顶峰”的存在,文艺发展理论中的顶峰说的存在,都不是对新的创造的阻遏。顶峰说其实完全不是一种厚古薄今的理论。以黑格尔来说,他推崇古希腊艺术为顶峰,认为在许多艺术类型中,后来的艺术都不如古希腊艺术。但就是这位在艺术发展论中被今人推为艺术退化论与艺术消亡论的代表人物的人,却满怀信心地展望艺术发展的前程:“在我们这个时代里……限制在一种特殊的内容和一种适合于这内容的表现方式上面的作法对于今天的艺术家们是已经过去的事了,艺术因此变成一种自由的工具了,不管是哪一种内容,艺术都一样可以按照创作主体方面的技能娴熟的程度来处理。这样,艺术家就可以超然站在一些既定的受到崇敬的形式和表现方式之上,自由独立地行动,不受过去意识所奉为神圣永恒的那些内容意蕴和观照方式的约束。任何内容,任何形式都是一样,都能用来表达艺术家的内心生活,自然本性,和不自觉的实体性的本质;艺术家对于任何一种内容都不分彼此,只要它不违反一般美和艺术处理的形式方面的规律。”[33]这就是说,今天的艺术家比过去时代的艺术家享有了更大的创作自由,完全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再以马克思来说,据英国学者柏拉威尔提供的资料,马克思心目中的“文坛泰斗”名单中虽然大多是古典作家,但也不乏他自己时代的人物。马克思的这份“文坛泰斗”名单是:荷马、埃斯库罗斯、奥维德、卢克莱修、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海涅、但丁、狄德罗、科贝特、巴尔扎克、狄更斯等。[34]马克思固然认为古希腊艺术从某方面讲是高不可及的范本,但显然他不是一个厚古薄今的人,而是“不薄今人爱古人”。那么今天的拥有了更大的艺术创作自由的艺术家如何使自己的创作或自己时代的本民族创作成为新的文学艺术“顶峰”呢?他们需要努力研究、学习、借鉴顶峰型的古代文学艺术,以便使自已走上文学艺术发展的正路,并以前人的艺术杰作为养料使自己得以壮大丰富。除此之外,至关重要的是,一个具备了非凡的艺术天赋与才气的作家艺术家,他必须要能够把自己民族的自己时代的乃至自己所处地域的社会文化特征融汇到自己的个性之中去,作家艺术家本人应当造就鲜明的个性,当他以既建立在人类审美心理共同性之上而又具有自已特有的鲜明特色的艺术风格去创作,去开辟新天地之时,他或他们就有可能造就新的艺术顶峰。切忌忽视本土文化和自己的特色一味模仿别的国家或民族的文学艺术,如20世纪80年代前后中国许多搞文学艺术的人专事模仿西方现代派艺术那样;切忌一味依傍已有的大家,如那个时期中国许多搞文学艺术的人一味依傍卡夫卡、乔伊斯或毕加索那样,那都是成就不了艺术顶峰的。齐白石老人告诫他的弟子: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理解:只有善于学习先辈大师才可能获得丰沛的艺术生命,但若一味模仿与依傍旁人,哪怕模仿与依傍的是大师,不会走自已的路,其结果就是走上了艺术的死路。
[1][11][12][13]黑格尔.美学(第3卷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320,117,137,137.
[2]伍蠡甫.西方文论选(上卷)[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469.
[3][4][5][6][26][33]黑格尔.美学(第2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6,273,174,274,169-170,378.
[7][8][9][10]黑格尔.美学(第3卷下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7,301,152,153.
[14][23][24][2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28,28,29.
[1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论文学与艺术(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99.
[16][17]爱克曼.歌德谈话录[M].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86,87.
[18]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32.
[19]鲁迅.鲁迅论文学与艺术[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800.
[20]卡西尔.人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90.
[21]姚军毅.论进步观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陶德麟.序言.
[22]朱狄.当代西方艺术哲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480-481.
[25][34]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M].北京:三联书店,1980:21,539.
[28]克罗齐.美学原理·美学纲要[M].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3:147.
[29]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466.
[30]柳鸣九.二十世纪现实主义[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322.
[31]沈太慧,陈全荣,杨志杰.1979-1983文艺论争集[C].郑州:黄河文艺出版社,1985:534-535.
[32]黑格尔.美学(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