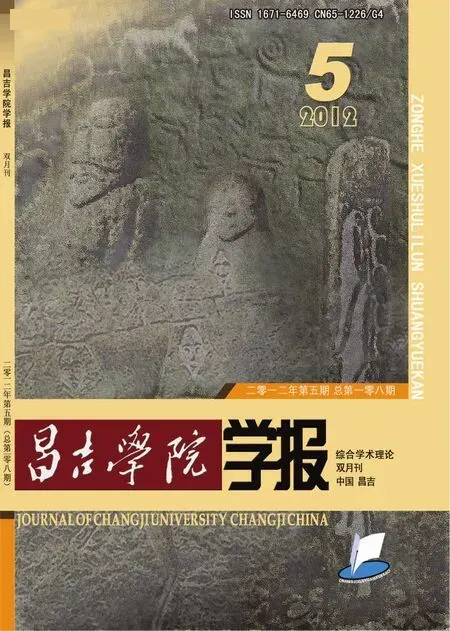聆听女性话语──《珀涅罗珀纪》中的女性叙述声音
邵珊
(兰州大学文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荷马史诗是西方世代传颂的古希腊经典神话故事,其中《奥德赛》的故事情节成型于古希腊时期,此时的神话体系已逐渐具有父系社会的思维模式,无疑《奥德赛》是一部站在男性中心主义角度上的神话。加拿大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新作《珀涅罗珀纪》,巧妙地改编了荷马史诗《奥德赛》的故事,将话语权交给了珀涅罗珀和被吊死的十二女仆,从女性的视角对荷马史诗进行大胆质疑,重新阐述《奥德赛》。阿特伍德认为,千百年来,男性掌握着文化符号体系的操纵权、话语理论的创作权和语言意义的解释权。女性总是处于边缘角色和缺席地位,无法获得自己的话语权力。因此有必要对神话经典中的男性人物去神圣化,归还其本来面目,同时激活处于弱势的女性形象。[1]
福柯的“话语即是权力”理论给予女性主义研究者启示:女性想要获得权力,改变相对于男性的“他者”位置,就必须要改变女性话语的边缘位置。因此,争夺话语权,解构和颠覆男性话语,建构女性自己的话语声音是女权主义者努力的目标。《珀涅罗珀纪》中以被父权社会边缘化的女性话语为全新视角,对经典的《奥德赛》进行了反叙述,在上层女性为代表的叙述声音和底层女性的叙述声音中渗透出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强烈的女性意识。在有意识地争取话语权力的同时,阿特伍德提高了被边缘化的女性话语,力图将男性话语挤压出文本,以此解构男性为中心的主流话语。
一、女性意识觉醒,反抗男性话语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上,对话语权的争夺体现出女性具备了主体意识,置换叙述角度是重述神话的重要写作策略。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采用解构手法重新演绎《奥德赛》的古老故事,去反抗经典文本中的男性话语,塑造了不同于男性话语叙述下的女性形象。
在荷马史诗《奥德赛》里,珀涅罗珀被描述成一个典型的贞妇。贞妇是男权社会为了教化目的而特意塑造的理想化、礼教化的女性角色。在荷马史诗中,我们听不到珀涅罗珀开口为自己言说,她的形象只是“一个训诫意味十足的传奇,一根用来敲打其他妇人的棍棒。”[2]但是阿特伍德赋予她话语权,从她的视角去讲述这个故事。珀涅罗珀“意识到当这些重大事件都过去了,蜕变的不再那么有传奇色彩之后,有多少人在背后嘲笑我”,“当满世界都是蜚短流长时,一个妇道人家能做什么?”[3]阿特伍德借珀涅罗珀之口,道出了社会中充斥着男性话语权和男性意识形态。男性通过话语的运作把女性置于社会的边缘,女性的声音被歪曲、湮灭了。正因为此,阿特伍德重述神话时,选择了将话语权交给处于被挤压在父权社会边缘的女性群体。但是阿特伍德所做的创新不仅仅在于从女性角度去重新诠释神话,更深层的意义在于阿特伍德将视野触及到了一群被忽略的女性,那就是以十二女仆为代表的底层女性的生活状况。
这些女孩子出生卑贱(父母或是奴隶,或是农民,或是女奴),从小就被人买走或者拐走,送到宫中做苦工,还要忍受主人的责骂和侮辱。她们在史诗中出现的频率极低,出场的时间非常短暂,命运极其悲惨。如果说珀涅罗珀作为上层贵族女性还能为自己说上几句话,那么处于社会最底层,受到奴隶主与男权双重压迫的女仆们根本就没有说话的权利,替自己鸣冤叫屈也是不可能的。阿特伍德在《珀涅罗珀纪》的前言中提出,这些被绞死的女仆一直以来萦绕在她的心中。因此,阿特伍德利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扩展荷马的文本,选择了将一部分叙述权交给十二女仆,让她们组成合唱队,力图让从未拥有过话语权力的底层女性开口诉说自己的故事,也向读者揭示到底是什么力量把她们推向了绞架。
二、女性话语内部的对立
在《珀涅罗珀纪》中,阿特伍德同时将话语权给予两个不同身份的女性角色——珀涅罗珀和十二女仆,她们分别代表了上层女性和底层女性。这两种女性话语不仅一起反抗了经典文本中的男性话语,同时还在这两种女性话语内部又进行一场话语权力的争夺。巴赫金复调小说理论指出,复调小说有着众多的各自独立而不相融合的声音和意识,由具有充分价值的不同声音组成真正的复调。不是某一个人的完整统一意识,而是众多地位平等的意识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总体。[4]《珀》就是比较典型的复调小说,女主人公珀涅罗珀和十二女仆同时具有话语权,两种女性话语拥有各自不同的声音和意识。
在父权社会中,底层女性和上层贵族女性的声音都遭到压抑和湮灭,女性为自己建立话语权威时,都会选择不同的叙述声音:珀涅罗珀代表了个人型叙述声音,十二女仆代表集体型叙述声音。这种独特的双重女性叙述声音在揭露男权社会给女性带来的痛苦和伤害的同时,也在声音内部产生相互质疑和相互对立,随着故事的步步推进,两种话语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强烈。
珀涅罗珀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时,用大量笔墨渲染她和这十二个年轻女仆之间的情谊,“我们一边做着破坏工作一边讲故事;我们出谜语;我们编笑话。我们简直成了姐妹。”[5]并且用心的训练她们,作为自己最信任的耳目,盘桓在求婚人周围去打探消息。可是在后文的女仆合唱队中根本就没有提及与王后珀涅罗珀的姐妹情谊。可见珀涅罗珀单方面的叙述只是一言之词,所叙述的真实性得到了质疑。
在《奥德赛》故事中,最令读者疑惑的就是珀涅罗珀是否对婚姻忠诚。在珀涅罗珀为自己辩护的言语中,她承认“故意引诱求婚人,还私下里向其中一些人作了承诺”,但是这只是个“策略”并且强调“奥德修斯本人见证并赞许了我的行动”。[6]当珀涅罗珀为自己辩护时,紧接的下一章节就是众女仆合唱队演出的舞台剧《珀涅罗珀之险》,道出了“另外一个故事”,剧中直接说到“珀涅罗珀谨慎贤淑,有上床的机会可毫不含糊!”[7]这与珀涅罗珀的话语形成了鲜明的对立,女仆的表演彻底颠覆了珀涅罗珀的辩词,让读者看到了她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女仆合唱队表演的舞台剧中描述了在奥德修斯即将归来之时,珀涅罗珀与老女仆欧律克勒亚商量,让老女仆“指证这些女仆软弱而不忠,被求婚人非法掳去又受到娇宠,道德败坏,恬不知耻,”“为封住她们的嘴”要把她们“送进鬼门关”。[8]十二女仆的死亡,珀涅罗珀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至说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十二女仆的诉说中,珀涅罗珀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声誉而亲自谋划将钟爱的女仆送入鬼门关的。可是,“事实很少是铁板钉钉”,十二女仆的话语可能也并不是完全可信。在女仆和珀涅罗珀的叙述之外,也许还是存有被遮蔽的情节。“是什么把女仆们推向了绞架?珀涅罗珀扮演了什么角色?”《奥德赛》并没有把故事交代得严丝合缝,而这部小说也没有给出最终答案。
三、不同阶层女性话语对男性的批判
荷马史诗《奥德赛》的故事是从奥德修斯的角度叙述,主要展现他的英雄特征。阿特伍德剥离了奥德修斯的神圣化、英雄化,将英雄庸俗化处理。在珀涅罗珀和十二女仆的叙述中同样都揭露出奥德修斯的反英雄形象,但是两种叙述声音中存有差异。
在珀涅罗珀的叙述中对奥德修斯虽含有怨言,但却没有仇恨,反而在心思缜密地看清丈夫的诡计后,推波助澜地帮助丈夫弯弓射死一百多求婚人。她“明白他狡黠的很,说谎成性,”“对于他的圆滑,他的狡诈,他狐狸般的诡秘,却视而不见,三缄其口”。珀涅罗珀在拥有话语权之后却依然对丈夫的行为保持着沉默。尽管她宣称“拥有一个像奥德修斯这样的丈夫绝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所有本地人都景仰他,来找他请愿及求教的络绎不绝。”她的语气中看似充满了对丈夫的敬仰,但是话锋一转,“他以善于解开最复杂的结而声誉卓著,尽管有时候他采取的办法是打一个更复杂的结”[9],包含了一丝不屑和嘲讽。珀涅罗珀作为被赋予话语权的上层女性,并不是坦诚地批判奥德修斯的杀戮行为,她虽有不满,却难以反抗。
相反,十二女仆对奥德修斯的评论则是充满了愤怒的控诉,奥德修斯看似英雄壮举般杀死求婚人的行为只是“怨恨的行径,是泄愤的行径,是为了保全荣誉的杀戮”。当众女仆无法通过法律途径得到公正的判决,只能求助于复仇女神去实施惩罚和复仇,立誓“无论奥德修斯去哪儿都要嗅出他的踪影!从一处追到另一处,从此生追到来世,不管他伪装为何人,不管他变成什么形状,都要将他抓到!以我们残破的身体,我们可怜的尸体模样!让他永不得安宁!”[10]
珀涅罗珀作为男权社会的潜在被害者和奥德修斯的妻子,不免讽刺和批判的力度较微弱,仅仅是为了澄清自己被误解的经历,而被害的众女仆则是以充满血泪的呐喊声去争取自己话语权力。如果说珀涅罗珀只是以嘲讽的口吻揭露奥德修斯的种种不堪的行为,那么十二女仆的控诉则是充满了战斗色彩。阿特伍德在作品中赋予众女仆集体型叙述声音更强有力的批判力度。
阿特伍德关注底层人群的生活境遇,尤其是底层女性所处的悲惨生活境遇和受到的压迫和蹂躏。她们不仅遭受到父权社会中男性给她们的压迫,也受到了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带给她们的压迫,因此她们比上层社会妇女的反抗更为积极勇敢。阿特伍德认识到在女性群体内部之间由于阶层等因素而造成很大差异,不能把女性看作一个一元化的群体,不能将女性社会地位低下的原因笼统地归咎为父权制的压迫。女人的身份不仅仅是女性,她还隶属于某个阶层,有其自己独特的生活体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性不仅遭受父权制的压迫,还要遭受来自于上层女性的歧视和剥削。她在作品中并没有将两种不同阶层的叙述声音笼统化为同一层次女性声音,而是有意将其对立,丰富叙述层次,使相互对峙的女性话语在碰撞中产生新的意义,让作品不仅成为一部为女性主义立言的女性神话,还是一部对底层妇女鸣不平的呐喊之词。
四、结语
阿特伍德重新解读经典文本,发掘出处于边缘的女性声音,并将其置于舞台中央,有意识地争夺话语权力,重新评估被男性话语挤压的女性话语,并同男性话语处于一种相互对立抵抗状态。因此,《珀》中丝毫听不到男主人公奥德修斯的叙述声音,男性处于相对失语的状态。阿特伍德通过把男性话语排斥出文本来建立起女性自己的话语,讲述关于女性的神话,反而将男性话语和女性话语处于失衡的不等式中,将女性话语过度拔高。建构女性话语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并不是女性话语自顾自的言说,并不是简单地推翻现有的以男性为中心的主流话语体系。真正以女性为主体的话语必须是与其他话语并存的。只有在多元话语并存的条件下,才能逐渐动摇男性话语霸权地位,才能有利于女性话语的创造[11]。
阿特伍德在重述神话中,通过置换叙述角度,以女性视角和生存体验去叙述《奥德赛》中未被人注意到的空白和断裂点,如果说《奥德赛》呈现出的是好斗尚武的男性世界,那《珀涅罗珀纪》中展现的就是宁静平和的女性世界。更值得肯定的是,阿特伍德清楚得认识到女性身份不是抽象的概念。女性有不同的等级地位之分,面临不同的生活状况,拥有不同的生活体验。阿特伍德在《珀涅罗珀纪》中让被压抑的不同阶层的女性重新寻找自己的话语去打破男性中心主义,使文本中的女性叙述声音多元化,有利于女性话语的建构。
[1]袁霞.生态批评视野中的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上海:学林出版社,2010:119.
[2][3][5][6][7][8][9][10](加)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韦清琦译.珀涅罗珀纪:珀涅罗珀与奥德修斯的神话[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5:3,4,94,118,121,124,51,152.
[4]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第二版(增补本)[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61.
[11]王琛.女性话语主体的建构及其可能性[D].郑州大学,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