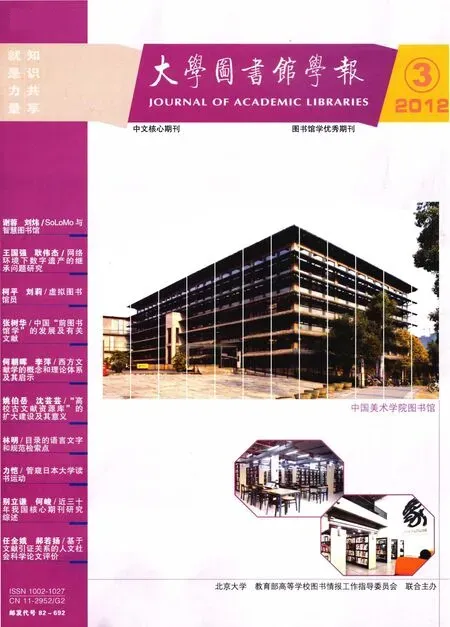目录的语言/文字和规范检索点——试读《国际编目原则声明》和RDA的语言/文字原则
□林 明
《国际编目原则声明》的“规范检索点”章节开宗明义地指出,“当一个名称以几种语言和/或文字表达时,规范检索点的语言和文字应当首先依据以原语言或文字表达的作品的载体表现中出现的信息;但是,若原语言或文字并非在目录中正式使用的语言或文字,则规范检索点可依据载体表现或参考来源中出现的、以最适合目录用户的一种语言或文字表达的形式。”[1]该表述延续了《巴黎原则》的语言选择原则,而且更加准确全面[2]。
RDA的有关章节细述了这一规定,并指出“名称”就是“个人、家族或团体的选用名称或名称形式”、以及作品的“常见题名”[3],但 RDA 用“首选检索点”代替“规范检索点”,两者涵义基本相同。
对以上表述,我们可以理解为:第一,若一个名称的原语言/文字形式与目录采用的语言/文字一致,该名称的规范检索点就采用原语言/文字形式;第二,若一个名称的原语言/文字形式与目录采用的语言/文字不一致,该名称的规范检索点就采用在资源上发现的与目录的语言/文字相同的形式;实际上也可将第二条视为第一条的补充。由此可见,一个名称的规范检索点在不同语言/文字的目录中可以有各自的语言/文字形式,并非只能是唯一的原语言/文字形式。在编目实践中,对第一条的理解和贯彻似乎没有问题,但对第二条却常常予以忽略或曲解,有鉴于此,本文着重探讨第二条的涵义和实际应用问题。
《国际编目原则声明》和RDA的语言/文字原则表明,一个名称规范检索点须采用习见形式,但其前提是以用户熟悉的语言/文字去表达,体现了“用户便利”的最高原则[4]。但是,用户是有民族性的,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用户所熟悉的语言/文字肯定是不同的,因此这一原则也表明,在制订和使用编目规则时,应注意将国际化和本地化相结合。
1 关于语言和文字
语言文字是一个复杂的学术问题,为了便于理解和论述,先将有关语言和文字的基本概念概括如下:
语言(Language)是人类特有的用于社会交流的发声符号系统。
文字(Script)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是扩大语言交流的最重要辅助工具。
除了原始社会只有简单语言而没有文字以外,在文明社会中语言和文字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种关系大致分为三种,第一种关系是多种语言采用一种文字,这一类文字包括拉丁文字、西里尔文字、阿拉伯文字等,例如,拉丁文字除了用于英、法、德、西班牙语言外,欧洲还有33种语言,以及一些亚非国家的语言也采用拉丁文字。第二种关系是一种语言使用或曾经使用两种文字或更多的文字,比如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目前通用拉丁文字和西里尔文字。还有些国家的语言在历史上曾经多次变更文字,比如印度尼西亚语经历了从印度字母改为阿拉伯文字,又改为拉丁文字的几次变迁,土耳其语由阿拉伯文字改为拉丁文字,越南语由汉字改为拉丁文字,等等。第三种关系是,一种语言只有唯一的文字体系,比如汉语只有汉文字,日语只有假名与汉字混杂的文字,希腊语只用希腊文字,等等。
另一方面,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在当今世界分为表音符号和表意符号两大系统,表音符号就是拼音字母,只要拼写出字母就能读出发音,拉丁字母、西里尔字母、阿拉伯字母都是表音符号。而表意符号是一种古老的文字符号,它的历史渊远流长而复杂。粗略说来,表意符号是用特定的象征性符号表示字和词,与发音没有必然联系。汉字就是一种十分稳定成熟的、也是世界上唯一存世的表意符号系统①参见:周有光.周有光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24-171。
1961年制订的《巴黎原则》只考虑到西方各国语言都使用拉丁文字,因此仅用“语言”一词代表西方各种语言,忽视了世界其他语言和文字之间的复杂关系,《国际编目原则声明》和RDA改用“语言/文字”表述,添加“文字”一词,表明更多地考虑到了世界各种语言和文字的复杂历史和现状[5]。
2 关于目录的语言和文字
2.1 关于字顺目录
在图书馆范畴内,目录就是“按照某些特定计划而排列的一种收藏、一个图书馆或一批图书馆的图书馆资料清单”[6]。这种特定计划,可以按作品的内容属性分类排列,也可以按载体表现的某些物理属性排列,但对用户而言,最便利的检索莫过于使用按文字排列的目录,即字顺目录。无论是查找资源题名,还是查找著者名字,或者采用主题词检索,都离不开字顺目录,字顺目录在图书馆中是使用最广泛的目录。
任何字顺目录的排列,都只能基于一种特定文字,不可能囊括所有文字。按照各国编目规则,虽然一条书目著录的大部分内容应按载体表现上的文字转录,但检索点必须采用编目机构为目录选定的一种文字,才能将该记录排列进目录中。比如美国国会图书馆对中文图书进行编目时,可以用汉字或汉字的罗马化形式著录题名、责任者和出版者等书目信息,但检索点就必须用罗马化形式而不能直接用汉字,对其他非拉丁文字图书的编目亦是如此。
根据不同文字的特点,世界各国的字顺目录体系分为两大模式,第一种是将所有资源按一种文字集中排列的目录,可称为集成目录;第二种是将不同语言/文字资源按不同文字分别排列的目录,可称为分立目录。《国际编目原则声明》指出,编目规则“可用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和其他团体创建的书目和其他数据文档”[7],但是,采用哪一种字顺目录模式,要根据收藏机构的文化背景、机构规模及其任务性质而定,考虑到语言/文字的复杂性和差异性、以及对书目文档的不同需求,《国际编目原则声明》并不对字顺目录模式做出规定。
2.2 将所有资源按一种文字集中排列的目录
拉丁文字是大多数国家语言的共同文字,这些国家的图书馆都采用拉丁文字的字顺目录,无论何种语言,只要是用拉丁文字拼写的,均可在同一目录中排列。在当今世界,以拉丁文字出版的出版物在世界上具有绝对优势。据有关资料,全世界近200个国家中有120多个国家使用拉丁文字,全世界的资料库有80%用英语。联合国的6种工作语言中,原始文件80%用英语,15%用法语,4%用西班牙语,而中文、俄文和阿拉伯文总共只占1%。可见,采用拉丁文字的字顺目录在当前目录世界中占据着主导地位①。
在西方各国图书馆,特别是大型的综合性图书馆,以非拉丁文字出版的资源的馆藏百分比很小,因而就没有必要为种类繁多、数量稀少的非拉丁文字资源分别设立不同文字的目录(专业图书馆的特殊需要除外),因此一般采用集成目录的模式,将所有资源都按拉丁文字排列。对非拉丁文字资源上出现的名称检索点,只要加以罗马化转写(Romanization),就可以列入目录,罗马化是将非拉丁文字的资源排列于拉丁文字目录的唯一途径。国会图书馆对各种非拉丁文字建立了十分完善的转写规则,例如俄文、日文、阿拉伯文、韩国文、中文等几十种转写方案。国际标准化组织也通过了一系列罗马化转写标准,比如《汉语拼音方案》就是用拉丁字母拼写汉字的国际标准(ISO-7098,1982年由国际标准化组织通过)。《国际编目原则声明》还提出,“若需要音译,应遵循有关文字转换的国际标准”[8],RDA也制定了适用性规定[9]。这些标准或规定,主要针对以拉丁文字音译的情况(非拉丁文字的罗马化),但对其他文字的音译标准也有指导意义(拉丁文字的非拉丁文字音译,如英语的汉字音译)。
罗马化转写虽然解决了集成目录的排列问题,使一个名称的规范检索点得以统一,但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原有字形丢失,须借助读音勉强辨识,这个矛盾不仅在不同表音文字间大量存在(如西里尔字母、阿拉伯字母转写为拉丁字母),而且在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间更为突出(如汉字转写为拉丁字母),关于这一矛盾,下文还要谈到。
上文已提到,虽然大多数国家使用拉丁文字,但各国语言不同。根据ISBD的规定,某些著录项目的术语“要用国家书目机构或其他书目机构所选择的语言和文字著录”[10],如载体形态项的用语、附注项的描述等,这使得各国的书目著录不可能完全统一。更重要的是,各国读者的检索习惯不同,各国编目机构为同一名称所建立的规范检索点形式也不会完全一致,因此,即使同属拉丁文字体系的国家,一个国家的目录并不能完全适用于另一个国家。尽管存在以上矛盾,但AACR2和欧洲各国编目规则都遵循或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巴黎原则》和ISBD,这种“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做法,体现了西方各国编目工作将国际化与本地化相结合的精神,值得国内编目工作借鉴。
2.3 将不同语言/文字资源按特定文字分别排列的目录
在使用非拉丁文字的国家或地区,包括我国大陆和台湾、香港等地区,以及周边国家如日本等,因语言/文字及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差异,各国或地区图书馆目录的情况有较大差异。中国大陆地区自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来,在第一代归国留学生的倡导下,国内图书馆普遍创立了按不同文字分立的目录体系,即分成中文目录、西文目录(注:国内对以拉丁字母拼写的语言通称为西文)、日文目录和俄文目录几大目录,这是符合我国国情的。我国图书馆收藏的中文图书远远多于外文图书,以我们独有的汉语言文字特点,既不可能沿袭西方国家的集成目录模式,也不宜照抄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某些具体政策。我国采用的分立目录模式,是我国语言文字和藏书构成的特点决定的,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也是编制和使用本国编目规则的物质基础。
分立目录的优点是读者可以直接采用自己熟悉的语言/文字检索,不需要借助各种复杂生疏的音译转写方案,避开了音译给读者带来的困扰。但存在的问题是:同一名称的规范检索点将会产生不同形式,比如鲁迅的名字在不同目录中就会有不同的规范检索点形式。另一个问题是,在分立目录模式下,一些稀少语种的资源,比如阿拉伯文、希腊文、印度字母的文献,要实现资源共享或沟通还有一定困难。
总而言之,无论集成目录还是分立目录,都是一定语言文化的产物,各有利弊,并无谁优谁劣的问题。我们只能探索适合于自己的道路,借鉴他人做法时,要注意避免陷入“南橘北枳”、“邯郸学步”的误区。
3 关于国内目录的语言/文字
在国内图书馆的分立目录中,规范检索点要选择目录所采用的文字。比如在中文目录中,中国人名和团体名称的规范检索点使用汉字,外国人名和团体名称要用汉字音译或意译,西文目录反之亦然。本文根据《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2版)和《西文文献著录条例》(修订扩大版),对中西文目录中的个人和团体规范检索点和统一题名进行比较,以便举一反三,融会贯通。
3.1 个人名称
在中文编目规则中,外国人名通常以汉字音译,如,英语原名:William Shakespeare,汉字音译:莎士比亚[11]。
在西文编目规则中,中国人名通常以汉语拼音音译,如,汉语原名:曹雪芹,汉语拼音:Cao,Xueqin[12]。
3.2 团体名称
在中文编目规则中,外国团体名称通常用汉语意译,如,英语原名:International Network for Bamboo and Rattan,汉语意译:国际竹藤组织[11]。
在西文编目规则中,中国团体名称通常用正式英译名,如,汉语原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英语意译: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12]。
3.3 统一题名
在中文编目规则中,外国作品统一题名用著称的汉语意译名,如,作品原名:Bible,汉语意译为:圣经(注:Bible实际是英语惯用名,圣经旧约原语言是希伯莱语,新约原语言是希腊语);又如,作品原名:Romeo and Juliet,汉语意译:罗米欧与朱丽叶[11]。
在西文编目规则中,中国作品统一题名难以确定惯用英译名时,可采用汉语拼音,如,“易经”的汉语拼音:Yi jing,又如,“红楼梦”的汉语拼音:Hong lou meng[12]。
显然,无论中文还是西文编目规则都共同遵循了以下原则:第一、若名称的原语言/文字形式与目录采用的文字不同,名称的规范形式就选择目录采用的文字;第二、人名优先音译,团体名称优先意译,个别惯用形式例外。
4 规范检索点语言/文字在不同目录模式中的矛盾
《国际编目原则声明》指出,“若原语言或文字并非在目录中正式使用的语言或文字,则规范检索点可依据载体表现或参考来源中出现的,以最适合目录用户的一种语言或文字表达的形式”[13],也就是说,为一个名称建立规范检索点时,应依据所编目的载体表现或参考来源上出现的语言/文字和使用目录的读者习惯。
个人名称仅是将一个人与其他人相区分的符号,一般采用音译即可。但团体名称则不然,它是代表特定含义的一组词语,比如团体的性质、宗旨、地点、范围等。如果团体的原语言/文字形式与目录采用的文字不同,就面临音译或意译的选择问题。以国会图书馆的目录为例,由于它面对所有语言/文字的载体表现,对非拉丁文字载体表现上出现的团体名称,其规范检索点须予以罗马化,如将中文图书出现的中国团体名称予以罗马化。而我国分立目录不然,它面对的只是特定语言/文字的载体表现,比如西文目录中,中国团体名称的规范检索点基于西文图书或参考来源上出现的意译形式,不可能是中文图书上的汉字或其拼音形式。反之,中文目录对外国团体名称的规范检索点,也只能基于中文图书或参考来源上出现的意译形式,而不是原语言/文字形式。从这些区别可以窥出集成目录和分立目录之间的一个深层次区别,即,不同目录体系编目所依据的载体表现或参考来源的语言/文字,决定了规范检索点形式,因此,在集成目录中的一个名称规范检索点形式,未必都适合于分立目录。这也是在国内编目实践中经常令人困扰的问题。
要提及的是,对于原语言/文字为非拉丁文字的团体名称,AACR2有一个语言交替规定,“若目录使用者不熟悉团体名称所用语言,则采用适合目录使用者语言的名称形式”,如对不懂日语的读者而言,日本某团体标目可以采用英译名Japan Produc tivity Center,不用罗马化形式 Nihon Seisansei Hombu[14],RDA 继 承 了 这 一 交 替 性 规 定[15]。 可见,团体标目的音译或意译应依据用户习惯,而且意译形式通常方便于音译形式,因此“意译优先”是国内中、西文编目的一贯传统。例如,我国西文编目一贯以意译原则处理非拉丁文字的团体标目,例如1961年出版的《西文普通图书著录条例》[16],1985年出版的《西文文献著录条例》[17],2003年出版的《西文文献著录条例(修订扩大版)》[18]都明确规定非拉丁文字的团体名称采用英译名,这些规定是符合AACR2的语言交替规则的。比如,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标目使用正式英译名China.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中国农业科学院土壤肥料研究所用英文名称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Institute of Soil and Fertilizer,都不用汉语拼音。
在1983年召开的西文图书编目标准化与自动化研讨会上,确立了国内对AACR2“基本采用,个别修订”的编目政策,这主要是指中国人名、团体名、统一题名标目的语言/文字形式要适应国内读者习惯[19],会议的一个讨论焦点就是中国团体标目问题,经过认真讨论,与会专家“一致同意中国机关团体的外文出版物,如此机关团体为标目时,其名称一律采用该机关团体正式的英文对外名称”,并将这一意译方针写入《西文文献著录条例》,这一方针突出反映了国内编目界将AACR2本地化的思想。但是,近年国内出现一种不同观点和做法,在西文编目中规定中国团体的“各级标目采用汉语拼音”[20],如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用汉语拼音zhongguo ke xue ji shu xie hui,不用正式英语名称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这显然与《西文文献著录条例》发生矛盾。又如,中文编目也出现了外国作品中译本采用原语言/文字为统一题名的做法,这与中文编目规则以“著称的”中文题名为统一题名的规定相矛盾[21]。以上做法显然全盘照搬了国会图书馆的标目规范,与国内中西文编目规则的既往方针明显不一致。
还要谈到汉语拼音在国内编目工作的应用问题。由上文所述,汉字是一种表意符号,需要一种表示读音的方法,自古以来用“反切”法读音,1918年国内创立了“注音字母”(至今台湾地区仍在使用),1922年采用“罗马新字母”(与 W-G氏拼音相似,以便于外国人学习汉语),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会议通过了“汉语拼音方案”,法定以拉丁字母注音。汉语拼音的主要用途是给汉字注音、推广普通话、国际交流和技术应用。由于汉语词汇的拼音还存在困难,我国政府又推出了“汉语拼音正词法”,作为“汉语拼音方案”的补充,相继制订了中国人名、地名的汉语拼音规则,其中后者成为中国地名国际拼音标准(1977年联合国第三届地名标准化会议批准)[22]。但是“汉语拼音正词法”还存在局限性,没有解决诸如分连写、同音词、声调、大小写的问题,对拼音的输入输出还存在识别的问题,很难识别团体名、书名、谚语成语等词组形式。周恩来总理在1958年1月10日《当前文字改革的任务》报告中强调,“汉语拼音方案是用来为汉字注音和推广普通话的,它并不是用来代替汉字的拼音文字”,这是切合实际的政策,避免了无谓的争论。可见汉语拼音不是独立文字,而是一种拼音的辅助工具。
在国内图书馆,汉语拼音主要用于检索,在中文目录中可用于输入拼音、输出汉字,但在西文目录中仅用于输入输出中国人名和地名的拼音。国会图书馆虽然于2000年开始改用汉语拼音拼写中国人名、地名和团体名,但对中国团体名称的拼写法仍然沿袭W-G氏拼音按单个汉字注音,而不是根据我国法定的“汉语拼音正词法”按词连写,识别很困难。由于汉语拼音存在以上难以解决的诸多问题,《西文文献著录规则》明确规定中国团体名称采用在西文载体表现上出现的正式英译名,以符合国内语言政策和读者习惯。
5 几点思考
5.1 FRBR模型
FRBR(书目记录的功能需求)作为一个概念模型,着重显示不同书目实体的属性及其内在关系,而《国际编目原则声明》作为编制编目规则的指南,着重于检索点形式以及基本检索点的选择,以有效实现目录的职能。FRBR作为一个抽象的资源整合模型,并不考虑各国语言文化的差异,而《国际编目原则声明》考虑到这一差异,强调检索点要采用目录的语言/文字,以适合于读者的习惯。因此,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编目实践中要完美实现FRBR模型是不可能的,一般而言,在西方国家通行的集成目录体系中,特别是在英美目录体系中,FRBR模型尚能在较大范围内实现,但在分立目录体系中,由于一个名称有不同语言/文字的检索点形式,FRBR模型在不同语言/文字的目录中必然是并行的分裂状态。解决这一问题的前景是采用“并列标目”形式,所谓“并列标目”,就是同一实体名称根据不同编目规则形成不同语言交替规范形式,以便在不同语言/文字目录间建立连接[23]。
5.2 不同编目规则适用于不同目录体系
一般而言,AACR2和RDA面向所有语言/文字资源,适用于以拉丁文字排列的集成目录体系,国内的分立目录体系面对的是不同语言/文字资源,因此需要以RDA为底本编制不同编目规则,以适合于分立目录体系,例如《西文文献著录规则》仅面向西文资源而不是所有资源,因而不存在将非拉丁文字团体名称罗马化问题,又如,《中国文献编目规则》仅面向中文资源,不应当简单照搬国会图书馆的西文规范形式。也就是说,在编目实践中,应避免过分追求FRBR的理想化而盲目照搬不同编目规则的个别规定。
5.3 国际化要和本地化相结合
“国际化”就是国内编目规则要积极采用《国际编目原则声明》和RDA提出的概念、结构和方法;“本地化”就是国内目录体系的设置、著录和检索点语言/文字和习见形式要适合本国读者的习惯,也就是将“读者便利”放在第一位,无论检索点采用什么形式,首先要考虑读者方便,而不是给读者制造麻烦。美国编目大师卡特主张“目录用户的方便要大大高于编目人员工作上的方便”,目录要适应“读者的习惯看法”,即使是在当今编目工作已实现全球资源共享也是如此。
5.4 建立全国性的权威性编目协调机构
国内各行业各部门图书馆应积极响应2006年第一次全国编目工作研讨会提出的《武汉宣言》的呼吁,对现行编目标准或规则中已有的规定,应当贯彻采用,避免政出不一,各行其是。一切重大问题需通过专家认证和广泛而公开的讨论,并经过权威机构认可,而不是以“长官意志”行事,以利于国内编目资源共享,为融入国际目录体系打下良好基础。《国际编目原则声明》和RDA编制中的民主化决策和经验,是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
1 Statement of International Cataloging Principles(December 18,2008,Final):6.3.2.[2012-03-26].(http://www.ifla.org/VII/s13/cip/)
2 原则声明7.1.见:1961年国际编目原则会议论文选译.北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1962:11
3 RDA :Resource description &access.Chicago: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2010:8.4,9-11
4 同1:2
5 同2
6 Anglo-American cataloguing rules.2nd ed.,2002rev.Ottawa:Canadian Library Association,2002:Appendix D-2
7 同1:1
8 同1:6.3.2.2
9 同3:0.11.2
10 国际标准书目著录(统一版).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31-32
11 中国文献编目规则.第2版.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348-349,366-367,374,379
12 西文文献著录条例.修订扩大版.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333,342,407
13 同1:6.3.2.1.1
14 同6:24.3A
15 同3:11.2.2.5.2
16 西文普通图书著录条例.北京:中国科学院图书馆,1961:47,54,62
17 西文文献著录条例.北京:中国图书馆学会,1985:148-149
18 西文文献著录条例.修订扩大版.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3:379
19 西文图书编目标准化与自动化研讨会会议录.北京: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印,1983:11-12
20 CALIS西文图书编目业务培训教材(普通班).北京:CALIS联机合作编目中心,2009:116-118
21 CALIS中文图书编目业务培训教材(普通班).北京:CALIS联机合作编目中心,2009:30
22 语言文字规范手册.1997年重排本.北京:语文出版社,1997:295-342
23 Guidelines for authority records and references/revised by the IFLA Working Group on GARE Revision.2nd ed.Munich:K.G.Saur,2001:4
——以河北大学图书馆为例